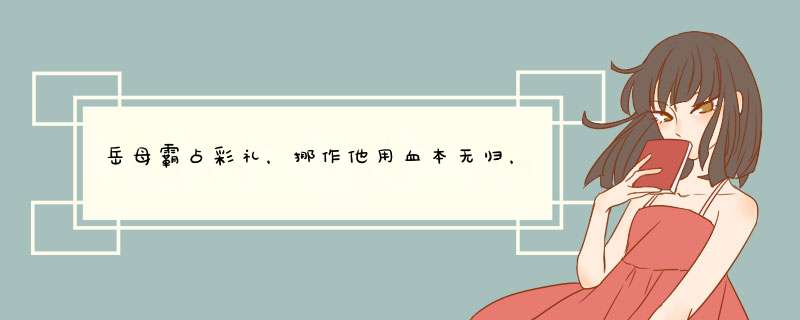
今天再来说说彩礼。
了解禾田飞歌的读者都知道,对于彩礼,禾田飞歌一贯的态度是:彩礼,是夫家给予新家庭的启动资金,是对孩子幸福生活的期许,最后是要随新娘带回小家庭的。
中国传统的婚嫁,男方带着聘礼到女方家下聘,而女方家可以不留、也可以留下聘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由新娘带回。同时,新娘还要带回与彩礼差不多数目、或略高于彩礼的陪嫁,“十里红妆”那是古时陪嫁的高规格了。这就是婚嫁中的礼尚往来。
尽管到现在,好多婚礼习俗都从简了,但彩礼陪嫁,大部分地方依然还盛行。
彩礼与陪嫁是一对搭档,怎么搭配都是有讲究的。
如果不要彩礼,那么女方家给不给陪嫁都是可以的。因为陪嫁是女方家给新娘应对风险的一份保障,一般的家庭都会给女儿一些傍身钱;
如果两家协商的结果是要彩礼,彩礼的数目由两家根据当地习俗来确定,一般都不会超出男方家庭的承受能力,那么女方家就要给出相应数量的陪嫁。
都说“人亲财不亲”,也说“见财起意”,还说“人心隔肚皮”,这三个词联合起来想说的意思是,在谈婚论嫁中,因为钱,也就是彩礼和陪嫁问题,两个相亲相爱的人最易生出嫌隙,闹出事端。
有收了彩礼不愿意给陪嫁的,也有不给彩礼觊觎女方陪嫁的,还有不顾男方家境死命要高价彩礼的,更有嫌彩礼少故意在接亲时为难新郎的、婆家嫌彩礼给得多羞辱新娘的,把一场场人间喜剧硬生生变成斗争剧,甚至是悲剧。
现实的婚姻需要谈钱,但钱不是幸福婚姻的唯一要素。婚姻是以物质为基础,相偕同行一生,首先还是要有爱。因此,在谈不拢的时候、在见财起意的时候,多想想那个人是不是你愿意陪伴一生的,如果是真爱,那就各自退让、相互体谅。
如果一方不顾礼数、也不顾对方难处,只知一味索取,婚姻往往都不会有好的结果,要么未进入婚姻就已分道扬镳,要么把婚后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所以说,天价彩礼不是婚姻破裂的原凶,人的私欲与贪心才是。
今天之所以又提到彩礼问题,是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投稿。
读者名叫玉娟(化名),结婚两年多,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小宝宝。两年的婚龄、又有了孩子,怎么说婚姻都还是有热度的。可玉娟却说,因为彩礼问题,她一直在夫家感受着冷空气、低气压。她要是知道会因为彩礼问题,老公与她有隔阂、公婆对她像空气,说什么她也不会同意母亲那样做的。
她说,这两年多的婚姻生活就是一地鸡毛,而把她的生活薅得一地都是鸡毛的,是她的母亲。
玉娟和老公葛鹏飞(化名)是相亲认识的,两人相处了一年多,感情很好。有人说相亲没有感情,只有条件,但玉娟却觉得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
她说,有一次,她去外地出差,一连十天,每天都接到葛鹏飞问寒问暖的信息,让她要注意身体,注意营养,并说等她回来的时候,要去火车站接她。
结果那天南方下了大雨,玉娟乘坐的火车晚点将近六个小时。玉娟以为葛鹏飞一定已经走了。没想到在深夜的火车站,葛鹏飞足足等了六个小时,才等到玉娟。他对玉娟说,他担心坏了,没有她的消息,怕她出事。
玉娟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知什么时候关机了。在葛鹏飞的怀里,她感受到有男人牵挂的幸福,心里暖融融的,那时她就打定主意要嫁给他。
结婚这件事,虽然玉娟愿意,但她一直矜持着,等葛鹏飞向她求婚。
葛鹏飞家条件不算太好,婚房倒是早买好装修好的,所以手上没有多少现金。葛鹏飞告诉玉娟,他们家准备了10万,还剩几万块钱给玉娟买三金、买衣服、办酒席,估计就差不多了。
玉娟很满意,因为当地彩礼一般都是在8万左右,葛家给出10万,那是相当有诚意了。
没想到的是,玉娟母亲不同意,非要20万彩礼。她对葛鹏飞说:“你放心,这个钱是要还回去的。我们嘛,老年人,你要理解,不过就是想要个面子,让玉娟嫁得风风光光的。”
你想要个面子,也得葛鹏飞家有啊!这下葛鹏飞犯难了,要凑足这20万彩礼,全家就要举债了。他不希望自己一结婚,就背上债务,他对玉娟也明确了这一点,希望玉娟去跟母亲商量一下,毕竟没有哪个新娘子嫁过来就要跟着还债吧。
玉娟没能说服母亲,相反被母亲说服。母亲告诉她,彩礼问题不光是我要面子,还可以试探出他葛鹏飞对你的感情,如果他真爱你,砸锅卖铁他也会去想办法。再说,这笔钱是肯定会带回葛家的。
玉娟听母亲说得也有道理,对呀,不过是让钱转一圈而已,不会有太大损失,葛鹏飞一定会愿意的。
但葛鹏飞心里却很难受,他觉得,既然玉娟爱他,就应该为他分忧,面子不面子的真有那么重要吗?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呀,再说,人心隔肚皮,这个钱真能转回来吗?他相信玉娟,却不相信玉娟母亲。
玉娟态度很坚决,葛鹏飞真是没有一点办法,他只能到银行作了抵押贷款,凑足了给丈母娘要的彩礼钱。但心结却落下了,心里不高兴,脸上的笑容就很勉强了。
等婚礼一结束,清点完礼金,葛鹏飞问玉娟:“彩礼钱呢?”
喜滋滋的玉娟这才想起,母亲承诺要还回来的彩礼没有拿回来,马上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却有些生气:“你看他们葛家小气巴拉的,再说这钱我也只是还给你呀,是你们小家的钱。过两天我送过去。”
一听亲家母这么一说,婆婆不高兴了,彩礼没回来,陪嫁也没有,婆婆脸上挂了霜。
葛鹏飞看到母亲这个样子,就催着玉娟盯紧点。
好几天过去了,也没见玉娟母亲拿回彩礼钱。玉娟只得再次回娘家去问个清楚,这一问,把玉娟吓出一身冷汗,原来,玉娟母亲把这笔钱放了出去。
玉娟一把抓住母亲的手,慌慌张张地说:“你赶紧把钱拿回来,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万一崩了,你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呀!”
母亲得意地说:“你放心,我已经在他们公司投了大半年了,每个月回款都是按时的。这次更高,但是门槛也高,要30万,所以我才把彩礼钱和给你的陪嫁钱一起放进去了。下个月就可以拿钱了。”
玉娟急了:“你糊涂呀,又不是没见过跑路的,你赶快把彩礼钱给我,他们家不高兴。”
因为钱刚放进去,拿不回来。玉娟只能把实情告诉了葛鹏飞。
葛鹏飞也慌了,一家人提心吊胆地拿了三个月利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公司负责人卷款跑了,这下,玉娟在葛家的日子可想而知。
先不说玉娟妈妈昏过去好几次,葛鹏飞现在是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情就会冲玉娟发火,婆婆更是破口大骂她是“丧门星”,公公从那以后连一句话都没跟她说过。
玉娟自知理亏,只能极力地对他们家人好。本来没有想那么早要孩子的玉娟,也顺了婆婆的心,早早生了孩子。但是他们家人只对孩子有笑脸,对玉娟还是不咸不淡的态度。
玉娟后悔不已,她在留言中说,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做主,父母的意见要听,但不能全听,要有自己的判断。其实男人也不容易,葛鹏飞借的那笔彩礼钱,已经还了两年了,还有一年多才能还完。现在最大的那笔钱没了,换作谁都会不好受。他没有闹着要离婚就已经不错了。
彩礼本就是给小家庭添砖加瓦的启动资金,双方家庭一定要坦诚、没有私心地安置这笔钱。在这过程中,女孩子一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要动脑子想想清楚别人的提议;还要在内心衡量一下彩礼对男方家的压力程度。如果爱他,就不要计较太多,大不了两人婚后一起奋斗,不能因为彩礼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婚姻。
两个人因爱结缘并共同生活,物质虽然重要,但为对方着想、相互体谅的感情更为可贵。
刘备,仁厚在《三国演义》中被写成了仁的化身。
关羽:忠义,但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在《三国演义》中被写成了义的化身。
张飞,勇而莽,性格缺点是脾气暴躁,“不恤小人”“暴而无恩”。
玄学影响中国文学,一个重要的途径,是通过影响中国文人的处世态度、生活情趣、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到文学。从魏晋士风可以看到,玄学思潮振荡之时,士人性格确实有很多新的特点,主要有任诞率真、以入俗为超俗、淡泊宦情、追求高雅超逸风度几种类型。在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中,竹林七贤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
《晋书》卷四十九阮籍等传末史臣叙论说:“嵇、阮竹林之会,刘、毕芳樽之友,驰骋庄门,排登李室……至于嵇康遗巨源之书,阮氏创先生之传,军谘散发,吏部盗樽,岂以世疾名流,兹焉自垢?”这是说,任情任诞之风的兴起,嵇、阮领其先。
嵇康其实不同于后来的任诞之士。他的不愿受礼法束缚,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不愿入仕。当然生活上也有,如《与山巨源绝交书》讲的七不堪之事,其中就有“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一条。但总体来说,嵇康是任性率真,而不是任诞。另外,他性格比较清峻,这表现出当时文人性格的另一方面。
较为任诞者为阮籍。《世说新语·德行》二十三则注引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他在生活方面有很多不拘礼法、不拘细节的故事。
《世说新语·任诞》十一则:“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这是说他居丧“散发坐床,箕踞不哭”。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有出入,但阮籍居丧不拘礼则是事实。
《世说新语·任诞》第七则:“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世说新语·任诞》第八则:“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注引王隐《晋书》又说:“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
阮籍之不拘礼,带有浓厚的厌弃世俗的色彩。他的《东平赋》、《亢父赋》、《猕猴赋》,借写风土之污秽,写世俗之污秽。他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毫不掩饰地发泄他对礼法之士的厌恶。他的任诞,是用自己的行为,表明对世俗礼法的极端鄙夷,如他所说:“礼岂为我辈设也?”
他的任诞,也是个性受现实政治压抑,不得伸展,寻找另一途径来表现的结果。他一生处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小心翼翼,靠无是非、入于无何有之乡而得以自全。他的任诞,其实带有某种强烈表现被压抑个性的色彩。
不过,阮籍有任诞的一面,也有率真的一面。他居丧,虽不拘礼,却是真悲真哀,他为兵家女哭丧,卧于邻家妇之侧,却终无他意,所以《世说新语》说他“外坦荡而内淳至”。
阮籍之后走任诞一路的,有刘伶、阮咸、谢鲲、阮孚、阮裕、胡毋辅之、毕卓、王尼、光逸这些人。刘伶、阮咸就属于竹林七贤。这些文人的行为确实放诞不羁:阮咸、诸阮与群猪共大盆饮酒;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说:“死便埋我。”
这些文人的任诞,其实与阮籍已有很多不同。阮籍的不拘礼法背后是厌弃世俗,任性率真。后来这些文人之所为,性情率真之意已很淡,一些行为看似与俗不同,实际原为低俗、污秽。任诞是从厌俗开始的。但在这些文人那里,已经从另一个极端把厌俗重又变为低俗。历代评家都把这些文人的任诞行为和阮籍联系在一起,而其实,联系是有的,但其价值评判已不能同日而语。
任诞的某些行为,如裸裎,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是当时又一风气。服寒食散之后,要喝热酒,然后裸体冷浴。饱酒兴奋时,也会脱掉衣服。但这更可能与文人性格有关。道教服药、饮酒,均非魏晋独有,而裸袒之风却以魏晋为盛。而且,当时还有当众露秽之风,文人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乐。文人性格当然也可能与服药有关,服药会引起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引起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如一些士人因服药性情变得暴躁。但文人性格变化的原因,更可能在于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中,玄学任情自然的影响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而这当中,竹林是士风变化的主体。
二
魏晋一些士人以入俗为超脱,这是玄风之下文人性格的又一特点。竹林七贤身上也体现了士风的这一重要变化。
这一特点仍要从阮籍讲起。
在处世态度上,阮籍和嵇康不一样。嵇康厌弃世俗又厌弃仕途,避物而处。阮籍虽厌弃世俗却未能弃绝仕途,他是入于仕途而又寻求超脱,在险恶政局的夹缝里寻找空间,因此在入仕为官的问题上,他极为谨慎。入仕为官,必然卷入政治纷争,特别在当时的险恶政局中,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完全不为官入仕,又会让人觉得你不与他们合作,也容易从另一方面引来杀身之祸。嵇康就因为过于清峻,导致被杀的悲剧结局。在这个问题上,阮籍简直是小心翼翼,一切顺着来,躲得过就躲,躲不过就先依顺,依顺之后再想办法躲。能不做的官尽量不做,躲不过非要做的官则尽量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总之,既要做官,又要避祸,他一生就是这样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寻找极小的生存夹缝。30岁以前他没有做过官。30岁以后,做太尉的蒋济要辟他为吏,他不是愤而拒绝,而是顺着来,写了一个奏记,虽然拒绝,但说得很委婉,对蒋济大加奉承,让蒋济觉得舒服甚至以为他答应了。当然蒋济最终知道他走了,还是大怒,这时,乡亲们劝他出仕,他仍然是顺着来,不是断然拒绝,而是姑且依顺着答应下来,然后托病辞退。38岁时,曹爽辅政,召他为参军,他已看出曹爽败亡的迹象,于是托病屏居田里,没有应召。不久,曹爽果然败亡,他得以免祸。司马氏当政,要他出仕,他不敢不做,做了从事中郎,又做了散骑常侍,一次也没有公开拒绝,但又在想办法远离政治纷争的中心。他自请去东平为官,说,我去过东平,觉得那里风土很好,能不能让我到那里去做官。其实,他对东平一点好感也没有,他写有《东平赋》,写东平的风土极为污秽,民情极为险诈。他的真实意图,是东平偏僻,远离京师政治纷争之地。后来他又自请为步兵校尉,理由是步兵厨营人很会酿酒,他去那里的目的是想喝美酒;而其实,他的目的也是避祸。司马昭为后来的晋武帝求婚于他的女儿,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集团,但他不敢拒绝,也不愿答应,于是便喝酒,一醉60日,让司马氏没有办法开口,这事不了了之。
与出仕为官相联系,是与名教礼法之士交往,也是处处小心。他从内心鄙视名教礼俗之人,这从他骂他们是藏在开裆裤里的虱子、从他的青白眼中就可以知道。他所鄙视的人中,包括司马氏。他对司马氏始终保持一种距离,这从他拒绝司马昭的求婚可以知道。但他不敢过分得罪名教礼法之士,特别是司马氏集团的权势人物。他给嵇喜以白眼,但钟会来了他还是要接待。他从内心厌恶司马氏,但他和司马氏交往很密切。应司马氏之召入仕,就是一种交往。即使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辞去了官职,他还是“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他的苦心,是让人们看,他对司马氏没有丝毫对立不满的情绪。
政治上他非常谨慎。凡政治上的是非得失、时事人物,他决不发表任何议论,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也是他终生遵奉的准则。
阮籍为人谨慎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李秉《家诫》,说到李秉和司马昭讨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李秉说到:“为官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司马昭非常赞同李秉的看法:“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又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
他内心当然一切都清楚,他不愿做的事情很多,但他都做得很顺从。包括他54岁时,为郑冲写劝进表,劝司马昭接受曹魏的禅让,这实际是劝司马氏篡逆,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事情,也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但这事是没法推辞的。他想喝醉酒赖掉,公卿们派人找他取时,他正伏案酣眠。使者告诉他,他推辞不了,于是,他还是写了,不但写了,而且当着使者的面,一挥而就,一字未改,辞清语壮,得到大家称赞。可以说,他是参与了司马氏的行篡逆。从写劝进表可看出,即使事涉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只要于自己生存有危害,他也不得不违心地去做。
可以说,他心目中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是非观。是也好,非也好,作腾飞于九天的大鹏也好,作蓬蒿间飞来飞去的小鸟也好,在他看来,已没有任何区别。世间的一切是非,物累,他都可以不顾,可以超越。正是靠着这样一种处世态度,他才在险恶的政局中得以自全。
这样处世,并非阮籍的发明,《庄子》早就作过探讨。庄子说,要“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接近又不要太陷入,和顺又不要太显露。要顺,“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他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你也跟着像婴儿一样天真无知;他没有什么限制,你也跟着没有什么限制。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心神任随外物变化而遨游,而不强加任何主观作用。要齐同万物。既然万物齐一,何必计较什么是非得失?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得失是非,这就可以无待,可以游于无穷,可以游入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可以与天地为一,可以逍遥游,就成了至人。
庄子有傲世的一面,也有顺世游世的一面,阮籍主要走的是顺世游世的道路。或者说,他是内心傲世,而实际处世则顺世游世。他是进入了庄子所说的没有是非、外物无累乎己的无何有之乡。
庄子逍遥游的境界,或者说“无何有之乡”,只是一个哲学的境界,阮籍把它变为实有的人生境界,从而找到了在险恶政局中自全的处世之道。后代很多士人如苏轼,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从庄子是非齐一、物我两忘的思想里得到解脱,都表现出这一品格,这实际已成为一种文人性格。阮籍是这类性格的典型代表。
三
淡泊宦情,冥于自然,是玄学影响士人性格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竹林七贤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性格。
嵇康是典型代表。嵇康是厌弃仕途的。曹氏当政的时候,他先为郎中,后拜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是一个仅备顾问的没有任何实权的散职。后来,他再没有任过什么官职。景元二年(261年),山涛将去选官,举嵇康以自代,嵇康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愤然拒绝。
嵇康为什么厌恶仕途?有人从曹魏与司马氏的关系考察,说嵇康是曹魏集团人,只愿为曹魏效力,而不愿为司马氏所用。根据有二:一、嵇康为曹氏的姻亲,因此心存魏室;二、说嵇康曾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这两个根据都有很多疑点。《世说新语·德行》十六注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据此,嵇康为曹操之孙沛穆王曹林之女婿,但嵇康只不过是七品散官,并非曹氏集团重要成员,而且,没有根据说他对曹魏集团人有好感。当时士人对曹魏都没有什么好感。曹魏在曹操甚至曹丕时,士人对他们多有好感,政治上有很强的凝聚力。但后来,曹魏集团中人都腐败无能,如曹爽、何晏辈。当时士人包括嵇康对他们都已失望。
说他参与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是根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说》的一条材料。这条材料说:“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但对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人们提出很多怀疑。嵇康没有任何实权,在军队中他没有任何力量,如何在洛阳起兵策应毋丘俭?还有一些怀疑。比如,前引《三国志·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大将军是指司马师。司马师欲辟嵇康,当在毋丘俭反前后不久。如在此前,则毋丘俭反时嵇康已“避之河东”,何由参与其事?若在此后,又若嵇康已参与谋反,则在司马氏眼中,显然是反臣,司马师何以还要征辟其入仕?
可能有避祸全生的考虑。嵇康《五言赠秀才诗》说:“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答二郭诗三首》其二说:“坎凛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其三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这当是从险恶的现实政局中得到的切身感受。在嵇康看来,遭司马氏杀戮的那些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都因为趋名趋利。
但是,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的情势是,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真要避祸,最好的办法是投向司马氏,和他们合作。阮籍、王戎、山涛都走的是这条路。这些人不但最终都得以全生,而且有的仕途还相当顺畅。嵇康恰恰相反,不和当权者合作,结果自招祸害,最终被司马氏所害,这一点嵇康不会不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路呢?
可信的解释是,嵇康从感情上厌弃世俗,他有他的生活追求,在他的生活追求里,没有名位利禄的内容。
他在思想上,人格上,与司马集团格格不入。司马集团是以名教礼法自居的,然而却以维护名教之名行篡逆之实,再者穷奢极欲,极端虚伪。
嵇康对这一切极为厌恶。他写《太师箴》名义上写的是历史,实际处处写现实,是大家看到的,“夭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沈。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哪一句不是对现实的抨击呢?
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过是借以抨击现实中司马氏的篡逆行径。《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可见这番话传到了司马氏耳中。这句话是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说的,而且,他说的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可见他经常这样,也许,他本来就不想隐瞒,或者说,他是要公开宣告鄙夷司马氏的态度。
《三国志·嵇康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说:“钟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钟会为大将军所昵,这一点嵇康应当很清楚,或者就因为他知道钟会是司马氏的得力人物,所以才有意冷落他。不但不为之礼,还问上两句,这无异于当众嘲弄他。嘲弄钟会,实无异于嘲弄司马氏。
这一切,都可看出嵇康极为厌恶司马氏的态度。这样一种态度,当然不可能出仕,不可能投向司马氏。
他有他的追求,有他所希望的生活。
《与山巨源绝交书》说的他有“七不堪”:“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不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简单地说,他厌弃俗务,喜欢自由自在,随性自然。
《与山巨源绝交书》又说:“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恬淡而有生活亲情,清俭而精神闲适。他向往的是这种生活。
他在诗作里反复写到他这种追求。《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第二章:“鸳鸯于飞,啸侣命俦。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咀嚼兰蕙,俯仰优游。”《四言诗》:“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这可能是嵇康实际生活的写照,但更可能理想化了。他写的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从他动情的描写可以知道,他向往的,是冥于自然,宁静恬淡,是自由自在,优游自适。
嵇康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他的任自然,不是走向任诞,也不是走向纵情适性,以入俗为超俗。他的返归自然,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高洁人格,用《卜疑》里的话说,是“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但事实上,内不愧心他做到了,外不负俗他没有做到,也做不到。
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当然来自庄子。嵇康主要接受庄子傲世的一面。返归自然的人生,庄子早就提出过,但庄子主要是哲学的论证,嵇康把它变为现实的人生,并且有所选择。他想保持高洁的人格,也因此冥于自然,归于宁静,树立了一个高洁的玄学人格,成为这一类文人性格的典型。
四
玄风下文人性格又一重要之点,是追求高雅情趣和超逸的风度,其主要表现在崇尚风姿气度,爱好雅淡,怡情自然和艺术。这一性格的有些方面,在东晋文人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竹林七贤也同样体现了这一性格特征。
崇尚风姿雅量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外在风姿气质之美,二是人物内在气度雅量之深。
就人物风姿的崇尚来说,东汉末年有对郭林宗等名士风流的崇拜。魏晋时期,对名士风姿的崇尚之风愈盛,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就因风姿之美而受到士人推崇。《世说新语·容止》五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注引《康别传》则说:“康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还有王戎,《晋书》本传说他“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而为裴楷绝口赞叹。
雅量,是临危不惧,临事不乱,荣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就对雅量的崇尚来说,也始于东汉末年,而到魏晋时期尤为士人推崇,成为他们的一种追求。
《世说新语·雅量》说“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便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这实际被看作一种高雅气度的修养。这种修养,可能与庄子超然物外的思想有关。《庄子·逍遥游》说:“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石焦而不热。”《齐物论》又说:“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要“死生无变于己”。庄子是以之喻不以物累的人生,而魏晋士人既以其作为一般人生态度,又以之作为性度修养,因此高雅的气度,也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性格。
怡情自然和艺术,是这时文人追求高雅情趣的一个突出表现,竹林七贤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怡情自然,主要是怡情山水。早在东汉末年,山林生活就为士人所向往,与士人生活发生联系。魏晋以来,山水进一步进入士人生活。竹林七贤更是向往自然,阮籍嵇康都曾游赏于山水,他们或旨在隐遁避世,或旨在求仙学道。《晋书·阮籍传》说籍“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阮籍不是隐居,但他在山林中向隐者学过道术;嵇康则有过隐居的经历。
表现士人雅趣的,还有对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的爱好。阮籍、嵇康均善弹琴,嵇康临终前一曲《广陵散》,令千古士人赞叹。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音乐、书法、绘画,给人的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上的满足。士人们似乎意识到,显示自己身份,仅仅有世俗的物质享受不行,仅仅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也不行,还要在文化修养上显示出自己的优越地位。因此,怡情艺术和游赏自然山水成为此时士人的一种生活追求,竹林七贤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