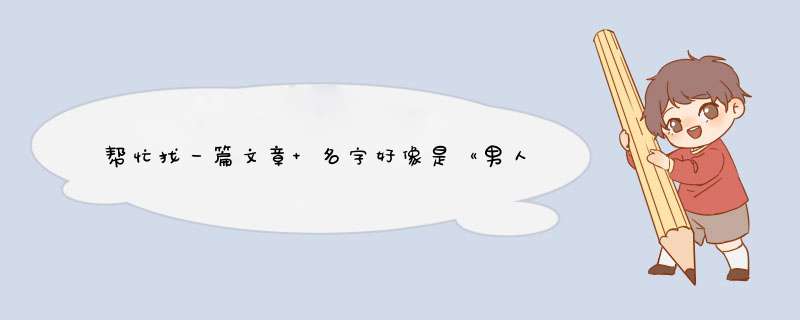
男人一生应该做的事
保护弱者男人的强大如果表现在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场所,他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男人。
同大龄女人约会女人成熟的魅力不仅是使她们更有女人味,而是让与她们交往的男人更像男人。没有试过她们的关爱和鼓励,小女人的撒娇只是一块国产的牛奶糖。
向挚友倾诉真实想法男人一生真正有机会吐露心声的时候并不多,那自私,极端的想法除了朋友没有人愿意听到。
参与公职竞选尝试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努力让大家都相信你喜欢你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经历,但千万别当真。
挽救一条生命除了为人父母,你能给别人生命的惟一机会就是挽救他的生命。(医生除外,那是他们应该做的)
环球旅行世界真奇妙,不看不知道,夏威夷姑娘的草裙跟咱们家乡的蓑衣可是天壤之别。
拔掉电视机插销一个月,即使不去做一个有格调的人,适时适当的离开电视机一段时间肯定会使你的生活真实一些。
说你没冒过险,没征服过自然可能就是骂你不像个男人。
写个简单的回忆录,自我欣赏,别说你的经历太简单,大英博物馆的地毯才是你踱来踱去的脚印,你现在正坐着马克思坐过的椅子。告诉你一句实话,自己不欣赏自己,就别指望别人欣赏你。
读一本太太刚刚放下的书,并与她讨论一下书中的情节太太的要求一般不会直接跟你说,假如碰巧她正在看言情小说,你必须重视起来。
学一门外语这不是钱或者本事的问题,如果你会塞尔维亚语,你可以在北约导弹落在南联盟之后跑去安慰受惊的斯拉夫美女。
为美味佳肴忘我工作口腹之欲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是你工作一天只能吃一块麦当劳的汉堡包才让人瞧不起呢!
模仿一位摇滚歌手,看看自己能不能取悦追星族先不管它庸俗还是高雅,你的魅力如果在模仿时还散发不出来,你有必要找个地方进修一下。
有遭人解雇和跳槽的经大没被人踢过就不知道怎么踢人。
做一笔赚钱的生意,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总是紧紧巴巴地过日子,总是蹭朋友豪华的晚宴,为什么不自己动动脑筋让自己也风光一下?
买别人不看好的股票,然后收藏起来,但千万别忘了凡事走偏门不太对头,偶尔下一个歪单可能是种远见。至多把29的大彩电换成14的七彩小画仙。
习惯染发和变换发型一成不变的头发很容易让人认为你有一颗僵硬死板的头脑,换换发型其实不过是让自己换换空气。
剃个光头留一脸胡子没当过劳改犯和导演,剽悍的感觉总得体验一回。
隐姓埋名在一个荒芜地带住段时间默默无闻的生活过后,你也许能明白活着和活过有很大的区别。
写首诗歌最浪漫的时候都学写过情诗的男人不妨找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抱着大树站一会儿,然后把最先想到的字词和句子分两行排列。
在公共场合穿黑色西装,看看周围人的反应既然不是参加葬礼,你也没必要太紧张,如果周围人的眼神太痴情,你可以哀怨地注视他几分钟。
缝一次扣子谁还记得小小针线包的歌曲,如果缝一个扣子对你难得像编一个崭新的计算机语言,你还指望自己在生意场上挥洒自如吗?
学会钓鱼没有耐心肯定就没有收获,等待浪费的时间决不比你闲逛的时间更长。
禁食一周饥饿的感觉像什么,伊斯兰的斋戒还不够长,七天下来你会清醒很多,也会清瘦很多。
追求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品位有谁强迫你做一个上流人士你就痛打他一顿,但是3000元的月收入已经足够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有品位的生活。
身体发福更要悠闲自得先别忙着减肥,一生中难得有次怡然放纵的机会,舒服一阵子再说。
风餐露宿街头你给过要饭的钱吗?自己拉下脸试试,有半天的时间就够你受的。缄默一个星期,别说你是个习惯沉默的人,一星期不说话你会看到许多你从来没注意的事情,也会发现交流对人有多么重要。
结婚安家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六十都不算晚,只要你结婚,城里城外的事儿还不都由着你的性子来。
丢次东西何必总那么严谨,没有丢过东西也没人给你发奖牌,丢了东西你才明白对你重要不重要。
创造家庭纪录每个人都希望名扬四海,偏偏忽略了身边最需要打破的记录。在家里刷碗最多的丈夫在妻子眼中比泰坦尼克上的麦克更有魅力。
用眼睛盯紧歹徒把你的勇气和力量通过眼神传达给他们,让罪恶从你眼前消失。穿过警戒线,大着胆子往前冲,留个心眼找退路。
结婚生子让自己的生命延续,让体内的父爱有一个流淌的途径。
尝试冲浪和风搏击有没有太多的风险,主意不错。
买一把吉他,学学弹奏曲子玩玩吉他可是最简单的音乐入门游戏,一个月让你弹唱流行歌曲,还不用学五线谱。
把荣誉让给别人好东西别老自己把着,抱多了金条还不压死你。
握紧权利好像不太好,不过有权利总比没权利更容易做些好事。
指责无辜的旁观者,然后接受遣责目的就是找骂。
学唱歌五音不全可不耽误你唱敖包相会,人们喜欢你才说唱得比哭还难听。
同5岁的孩子猜谜语成人智力究竟在什么时候比儿童高了,10个谜语里你肯定不如孩子猜出得多。
透支信用卡然后立即还清知道信用卡的透支功能为什么从来没试过?
自己建房或者设计房间鸟窠兽巢都是自己的杰作,人怎么倒没机会自己盖个窝。
说点瞎话,但不能习以为常小事上张嘴就来是脑瓜灵活的表现,大事乱讲就有些不负责任了。
参加体力劳动玩命干一天保证让你一个晚上不失眠。
学会自我陶醉成绩是自己的就应该自我陶醉。
赞美朋友和同事他们再不济也是你的熟人,他们要是没优点,你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何不实事求是地赞美他们呢?
录个像,看看自己在电视上的模样经常觉得自己潇洒不羁,可在屏幕上却像个傻瓜,与其将来看了后悔,不如现在把缺点改一改。
和同事在老板的房间睡个觉当不了老板先在老板房间过过瘾好了。
随时变换职业永远做一个行业只能让你当这个行业的老古董,随时变换职业却能让你永远拥有新人的面孔。
给孩子换尿布不是你的孩子也不要紧,关键你要见识一下把孩子带大有多么不容易。
联系多年失散的朋友感情越老越值钱,老朋友的意义在于相互慨叹彼此的变化。
给误解你的人打电话,表达歉意和懊悔即便是他不对,你也没有必要硬撑着,谁服个软并不说明谁懦弱,关系改善了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炸弹——对令人生厌和呕吐的饭菜拒绝付费花钱可不是买罪受,行使自己的消费权利也是督促改进的方法。服务员照顾不周不妨嗤之以鼻他们应该做到的一步不放松,不该他们做的一个也不要求。
出外旅游不用指南书相信导游手册上的说法只能使你不迷路,随意观光才算是旅游。
当百万富翁有机会谁也不会放弃,没有机会想也白想。
拥有一件按照风俗礼节制作的服装和鞋子就是一套长袍马褂或者锦缎袄和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拥有一套漂亮的西装和一双做工讲究的皮鞋先准备出一万元人民币,不然等等再说。
有发明立即申请专利眼镜腿上加个勾都能成为专利,你的发明不抓紧,比尔盖茨可不管你的自尊心。
为慈善机构捐款真情假意都不算过分,实惠到了位什么还不好说。
当当教练好为人师表的人类通病如果没有适当的渠道发泄不妨去当当教练。
挑选一首自己葬礼上播放的音乐体面地活着可别邋遢地走。
买一顶适合身份的帽子除了绿色,款式便是最重要的标准。
搞一次恶做剧整死人,笑死自己,不然别搞。
帮助陌生人真正毫无目的,不求回报地奉献一次吧。
善待邻居和朋友谁也没有忍受你坏脾气和无理的义务,要是你希望有一天被人莫名其妙地殴打一顿,继续你的粗暴吧。
工作量力而行做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隶包含了不做自己工作的奴隶,适当、适量的标准会让你生活得充实但是不辛苦。
保护弱者。男人的强大如果表现在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场所,他会成为理所当然的男人。
同大龄女人约会。女人成熟的魅力不仅是她们更有女人味,而是让与她们交往的男人更像男人。没有试过她们的关爱和鼓励,小女人的撒娇只是一块国产的牛奶糖。
挽救一条生命。除了为人父母,你能给别人生命的惟一机会就是挽救他的生命。(医生除外)
拔掉电视机插销一个月。即使不去做一个有格调的人,适时适当地离开电视机一段时间肯定会使你的生活真实一些。
读一本太太刚刚放下的书,并与她讨论一下书中的情节。太太的要求一般不会直接跟你说,假如碰巧她正在看言情小说,你必须重视起来。
买别人不看好的股票,然后收藏起来,但千万别忘了。凡事走偏门不太对头,偶尔下一个歪单可能是种远见。
习惯染发和变换发型。一成不变的头发很容易让人认为你有一颗僵硬死板的头脑,换换发型其实不过是让自己换换空气。
剃个光头留一脸胡子。没当过劳改犯和导演,剽悍的感觉总得体验一回。
隐姓埋名在一个荒芜地带住段时间。默默无闻的生活过后,你也许能明白活着和活过有很大的区别。
写首诗歌。最浪漫的时候都学写过情诗的男人不妨找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抱着大树站一会儿,然后把最先想到的字词和句子分两行排列。
缝一次扣子。谁还记得小小针线包的歌曲,如果缝一个扣子对你难得像编一个崭新的计算机语言,你还指望自己在生意场上挥洒自如吗?
学会钓鱼。没有耐心肯定就没有收获,等待浪费的时间决不比你闲逛的时间更长。
禁食一周。饥饿的感觉像什么,七天下来你会清醒很多,也会清瘦很多。
追求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品位。有谁强迫你做一个上流人士你就痛打他一顿,但是3000元的月收入已经足够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有品位的生活。
风餐露宿街头。你给过要饭的钱吗?自己拉下脸试试,有半天的时间就够你受的。
缄默一个星期。别说你是个习惯沉默的人,一星期不说话你会看到许多你从来没注意的事情,也会发现交流对人有多么重要。
结婚安家。三十、四十、五十甚至六十都不算晚,只要你结婚,城里城外的事儿还不都由着你的性子来。
创造家庭纪录。每个人都希望名扬四海,偏偏忽略了身边最需要打破的记录。在家里刷碗最多的丈夫在妻子眼中比泰坦尼克上的麦克更有魅力。
用眼睛盯紧歹徒。把你的勇气和力量通过眼神传达给他们,让罪恶从你眼前消失。穿过警戒线,大着胆子往前冲,留个心眼找退路。
买一把吉他,学学弹奏曲子。玩玩吉他可是最简单的音乐入门游戏,一个月让你弹唱流行歌曲,还不用学五线谱。
把荣誉让给别人。好东西别老自己把着,抱多了金条还不压死你。
同5岁的孩子猜谜语。成人智力究竟在什么时候比儿童高了,10个谜语里你肯定不如孩子猜出得多。
透支信用卡然后立即还清。知道信用卡的透支功能为什么从来没试过?
自己建房或者设计房间。鸟窠兽巢都是自己的杰作,人怎么倒没机会自己盖个窝。
说点瞎话,但不能习以为常。小事上张嘴就来是脑瓜灵活的表现,大事乱讲就有些不负责任了。
赞美朋友和同事。他们再不济也是你的熟人,他们要是没优点,你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何不实事求是地赞美他们呢?
录个像,看看自己在电视上的模样。经常觉得自己潇洒不羁,可在屏幕上却像个傻瓜,与其将来看了后悔,不如现在把缺点改一改。
和同事在老板的房间睡个觉。当不了老板先在老板房间过过瘾好了。
随时变换职业。永远做一个行业只能让你当这个行业的老古董,随时变换职业却能让你永远拥有新人的面孔。
联系多年失散的朋友。感情越老越值钱,老朋友的意义在于相互慨叹彼此的变化。
给误解你的人打电话,表达歉意和懊悔。即便是他不对,你也没有必要硬撑着,谁服个软并不说明谁懦弱,关系改善了才是应该关注的问题。
出外旅游不用指南书。相信导游手册上的说法只能使你不迷路,随意观光才算是旅游。
拥有一件按照风俗礼节制作的服装和鞋子。就是一套长袍马褂或者锦缎袄和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为慈善机构捐款。真情假意都不算过分,实惠到了位什么还不好说。
挑选一首自己葬礼上播放的音乐。体面地活着可别邋遢地走。
买一顶适合身份的帽子。除了绿色,款式便是最重要的标准。
搞一次恶做剧。整死人,笑死自己,不然别搞。
帮助陌生人。真正毫无目的,不求回报地奉献一次吧。
善待邻居和朋友。谁也没有忍受你坏脾气和无理的义务,要是你希望有一天被人莫名其妙地殴打一顿,继续你的粗暴吧。
工作量力而行。做任何事任何人的奴隶包含了不做自己工作的奴隶,适当、适量的标准会让你生活得充实但是不辛苦。
驴打滚儿
换绿盆儿的,用他的蓝布掸子的把儿,使劲敲着那个两面的大绿盆说:
“听听!您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
妈妈用一堆报纸,三只旧皮鞋,两个破铁锅要换他的四只小板凳,一块洗衣板;宋妈还要饶一个小小绿盆儿,留着拌黄瓜用。
我呢,抱着一个小板凳不放手。换绿盆儿的嚷着要妈妈再添东西。一件旧棉袄,两叠破书都加进去了,他还说:
“添吧,您。”
妈说:“不换了!”叫宋妈把东西搬进去。我着急买卖不能成交,凳子要交还他,谁知换绿盆儿的大声一喊:
“拿去吧!换啦!”他挥着手垂头丧气地说:“唉!谁让今儿个没开张哪!”
四只小板凳就摆在对门的大树荫底下,宋妈带着我们四个人我,珠珠,弟弟,燕燕坐在新板凳上讲故事。燕燕小,挤在宋妈的身边,半坐半靠着,吃她的手指头玩。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我问。
“跟你一般儿大,九岁喽!”
小栓子是宋妈的儿子。她这两天正给我们讲她老家的故事:地里的麦穗长啦,山坡的青草高啦,小栓子摘了狗尾巴花扎在牛犄角上啦。她手里还拿着一只厚厚的鞋底,用粗麻绳纳得密密的,正是给小栓子做的。
“那么他也上三年级啦?”我问。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儿?他成年价给人看牛哪!”她说着停了手里的活儿,举起锥子在头发里划几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个,可得回家看看了,心里老不顺序。”她说完愣愣的,不知在想什么。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其实丫头子的故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宋妈讲过好几遍。宋妈的丫头子和弟弟一样,今年也四岁了。她生了丫头子,才到城里来当奶妈,一下就到我们家,做了弟弟的奶妈。她的奶水好,弟弟吃得又白又胖。她的丫头子呢,就在她来我家试妥了工以后,被她的丈夫抱回去给人家奶去了。我问一次,她讲一次,我也听不腻就是了。
“丫头子呀,她花钱给人家奶去啦!”宋妈说。
“将来还归不归你?”
“我的姑娘不归我?你归不归你妈?”她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奶?为什么到我家当奶妈?为什么你挣的钱又给人家去?”
“为什么?为的是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呀!小栓子他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挣钱!”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那一天,是个冬天,她穿着大红棉袄,里子是白布的,油亮亮的很脏了。她把奶头塞到弟弟的嘴里,弟弟就咕嘟咕嘟地吸呀吸呀,吃了一大顿奶,立刻睡着了,过了很久才醒来,也不哭了。就这样留下她当奶妈的。
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来了,拉着一匹驴,拴在门前的树干上。他有一张大长脸,黄板儿牙,怎么这么难看!妈妈下工钱了,折子上写着:一个月四块钱,两付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过了一年零四个月才许回家去。
穿着红棉袄的宋妈,把她的小孩子包裹在一条旧花棉被里,交给她的丈夫。她送她的丈夫和孩子出来时,哭了,背转身去掀起衣襟在擦眼泪,半天抬不起头来。媒人店的老张劝宋妈说:
“别哭了,小心把奶憋回去。”
宋妈这才止住哭,她把钱算给老张,剩下的全给了她丈夫。她又嘱咐她丈夫许多话,她的丈夫说:
“你放心吧。”
他就抱着孩子牵着驴,走远了。
到了一年四个月,黄板儿牙又来了,他要接宋妈回去,但是宋妈舍不得弟弟,妈妈又要生小孩子,就又把她留下了。宋妈的大洋钱,数了一大垛交给她丈夫,他把钱放进蓝布袋子里,叮叮当当的,牵着驴又走了。
以后他就每年来两回,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墙犄角,弄得满地的驴粪球,好在就一天,他准走。随着驴背滚下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面不是大花生,就是大醉枣,是他送给老爷和太太我爸爸和妈妈的。乡下有的是。
我简直想不出宋妈要是真的回她老家去,我们家会成了什么样儿?老早起来谁给我梳辫子上学去?谁喂燕燕吃饭?弟弟挨爸爸打的时候谁来护着?珠珠拉了屎谁给擦?我们都离不开她呀!
可是她常常要提回家去的话,她近来就问我们好几次:“我回俺们老家去好不好?”
“不许啦!”除了不会说话的燕燕以外,我们齐声反对。春天弟弟出麻疹闹得很凶,他紧闭着嘴不肯喝那芦根汤,我们围着鼻子眼睛起满了红疹的弟弟看。妈说:
“好,不吃药,就叫你奶妈回去!回去吧!宋妈!把衣服、玩意儿,都送给你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
宋妈假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走喽!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哟!”
“我喝!我喝!不要走!”弟弟可怜兮兮地张开手要过妈妈手里的那碗芦根汤,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碗。宋妈心疼得什么似的,立刻搂抱起弟弟,把头靠着弟弟滚烫的烂花脸儿说:
“不走!我不会走!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小丫头子!”跟着,她的眼圈可红了,弟弟在她的拍哄中渐渐睡着了。
前几天,一个管宋妈叫大婶儿的小伙子来了,他来住两天,想找活儿做。他会用铁丝给大门的电灯编灯罩儿,免得灯泡被贼偷走。宋妈问他说:
“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好吧?”
“嗯?”他好像吃了一惊,瞪着眼珠,“我倒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舅那儿来的!”
“噢,”宋妈怀着心思地呆了一下,又问:“你打你舅那儿来的,那,俺们丫头给刘村的金子他妈奶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吗?”
“哦?”他又是一惊,“没没听说。准没错儿,放心吧!”
停了一下他可又说:
“大婶儿,您要能回趟家看看也好,三、四年没回去啦!”
等到这个小伙子走了,宋妈跟妈妈说,她听了她侄子的话,吞吞吐吐的,很不放心。
妈妈安慰她说:
“我看你这侄儿不正经,你听,他一会儿打你们家来,一会儿打他舅舅家来。他自己的话都对不上,怎么能知道你家孩子的事呢!”
宋妈还是不放心,她说:
“我打今年个一开年心里就老不顺序,做了好几回梦啦!”
她叫了算命的来给解梦。礼拜那天又叫我替她写信。她老家的地名我已经背下了: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交冯大明吾夫平安家信。
“念书多好,看你九岁就会写信,出门丢不了啦!”
“信上说什么?”我拿着笔,铺一张信纸,逞起能来。
“你就写呀,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尽顾得下水里玩。我给做好了两双鞋一套裤褂。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道乏。拿回去的钱前后快二百块了,后坡的二分地该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要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这封信太长了!”我拦住她没完没了的话,“还是让爸爸写吧!”
爸爸给她写的信寄出去了,宋妈这几天很高兴。现在,她问弟弟说:
“要是小栓子来,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
“给呀!”弟弟说着立刻就站起来。
“我也给。”珠珠说。
“等小栓子来,跟我一块儿上附小念书好不好?”我说。
“那敢情好,只要你妈答应让他在这儿住着。”
“我去说!我妈妈很听我的话。”
“小栓子来了,你们可别笑他呀,英子,你可是顶能笑话人!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宋妈说的仿佛小栓子等会儿就到似的。她又看看我说:
“英子,他准比你高,四年了,可得长多老高呀!”
宋妈高兴得抱起燕燕,放在她的膝盖上。膝盖头颠呀颠的,她唱起她的歌:
“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哥哥出来卖菜,里头坐个姑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她唱着,用手板住燕燕的小手指,指着鼻子和眼睛,燕燕笑得咯咯的。
宋妈又唱那快板儿:
“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姑娘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太阳斜过来了,金黄的光从树叶缝里透过来,正照着我的眼,我随着宋妈的歌声,斜头躲过晃眼的太阳,忽然看见远远的胡同口外,一团黑在动着。我举起手遮住阳光仔细看,真是一匹小驴,得、得、得地走过来了。赶驴的人,蓝布的半截褂子上,蒙了一层黄土。哟!那不是黄板儿牙吗?我喊宋妈:
“你看,真有人骑驴来了!”
宋妈停止了歌声,转过头去呆呆地看。
黄板儿牙一声:“窝哦!”小驴停在我们的面前。
宋妈不说话,也不站起来,刚才的笑容没有了,绷着脸,眼直直瞅着她的丈夫,仿佛等什么。
黄板儿牙也没说话,扑扑地掸他的衣服,黄土都飞起来了。我看不起他!拿手捂着鼻子。他又摘下了草帽扇着,不知道跟谁说: “好热呀!”
宋妈这才好像忍不住了,问说:
“孩子呢?”
“上上他大妈家去了。”他又抬起脚来掸鞋,没看宋妈。他的白布袜子都变黄了,那也是宋妈给做的。他的袜子像鞋一样,底子好几层,细针密线儿纳的。
我看着驴背上的大麻袋,不知里面这回装的是什么。黄板儿牙把口袋拿下来解开了,从里面掏出一大捧烤得倍儿干的挂落枣给我,咬起来是脆的,味儿是辣的,香的。
“英子,你带珠珠上小红她们家玩去,挂落枣儿多拿点儿去,分给人家吃。”宋妈说。
我带着珠珠走了,回过头看,宋妈一手收拾起四个新板凳,一手抱燕燕,弟弟拉着她的衣角,他们正向家里走。黄板儿牙牵起小叫驴,走进我家门,他准又要住一夜。他的驴满地打滚儿,爸爸种的花草,又要被糟践了。
等我们从小红家回来,天都快黑了,挂落枣没吃几个,小红用细绳穿好全给我挂在脖子上了。
进门来,宋妈和她丈夫正在门道里。黄板儿牙坐在我们的新板凳上发呆,宋妈蒙着脸哭,不敢出声儿。
屋里已经摆上饭菜了。妈妈在喂燕燕吃饭,皱着眉,抿着嘴,又摇头叹着气,神气挺不对。 “妈,”我小声地叫,“宋妈哭呢!”
妈妈向我轻轻地摆手,禁止我说话。什么事情这样重要?
“宋妈的小栓子已经死了”,妈妈沙着嗓子对我说,她又转向爸爸:“唉!”已经死了一两年,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一阵子总是心不安,一定要叫她丈夫来问问。她侄子那次来,是话里有意思的。两件事一齐发作,叫人怎么受!“
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
我听了也很难过,但不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又不敢问。
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吆喝她,我轻轻地喊: “宋妈,妈叫你呢!”
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噎的哭声,到屋里来。妈对她说:
“你明天跟他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
“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么?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宋妈红着眼狠狠地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呆定在我们家不走了。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
“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敢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
“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四十岁了没儿没女的,谁知道是真话假话!”“问清楚了找找也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妈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旧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妈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
“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
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扑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链儿的歌儿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把她的丈夫扔在门道儿里不理他。他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巴达巴达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它在地上卧着,忽然仰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它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给踩倒了两三棵。驴子吃上干草子,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招手叫我出去。
我跑出来,宋妈跟我说:
“英子,别乱跑,等会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帮我找地方。”
“到哪儿去?”我很奇怪。
“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她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撮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
“好的。”我答应着。
宋妈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
“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得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 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
“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
“是呀,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就顾得玩水。”
“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
“那时候黄板嗯,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
“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他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
“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送给人?”
“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要花钱就花吧。”宋妈说。
我们从绒线胡同穿过兵部洼,中街,西交民巷,出东交民巷就是哈德门大街。“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
“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
“我是后悔后悔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
“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
“嗯。”宋妈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
我们走到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他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在用**的面粉做一种吃的。
“宋妈,他在做什么?”
“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
“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
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妈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吃。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是买给丫头子的吗?”
出了东交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了,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落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
“走那边吧”,她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说:
“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那
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
“你们是哪儿的?”
“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
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 “在家哪,胡同底那家就是。”
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
“劳驾,找人哪!”宋妈喊道。
其中一个小孩子便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
“姥姥,有人找。”
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
“你这院里住几家子呀?”
“啊啊,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 “您可有个姑娘呀!”
“有呀,你要找孩子他妈呀!”她指着三个男孩子。
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便说:
“找错人了!”
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说:“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
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她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她又问我:
“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儿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湿溶了。我嘴里念了一声:“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
我对宋妈说:
“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儿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她看,“像驴粪球不?”
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
“吃罢!”
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子的影子。
树荫底下听不见冯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地呆看着,没有一句话。
冬天又来了,黄板儿牙又来了。宋妈让他蹲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他说话。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雪》的课文: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妈妈说:“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叫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
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
“你瞧怎么样?”
宋妈这才说:
“也好,我回家跟他算帐去!”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
“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
“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
宋妈看着我说:
“你念书大了,可别欺侮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
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
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她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她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强,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梨炖冰糖给她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捎了来;珠珠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唉!”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
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了许多这钱那钱给她;她丝毫不在乎地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 “说走就走了!”
“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
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
“那年个,上京来的那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儿,四年了!”
她的那件红棉袄,也早就拆了;旧棉花换了榧子儿,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了。
“妈,宋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
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儿,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声地对我说:
“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
“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
“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
“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也这么催,多寒碜!”
“明天早点儿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雪就被抖落下来,掉在驴背上。
我轻轻地穿上衣服出去,到下房找宋妈,她看见我这样早起来,吓了一跳。我说: “宋妈,给我梳辫子。”
她今天特别的和气,不唠叨我了。
小驴儿吃好了早点,黄板儿牙把它牵到大门口,被褥一条条地搭在驴背上,好像一张沙发椅那么厚,骑上去一定很舒服。
宋妈打点好了,她用一条毛线大围巾包住头,再在脖子上绕两绕。她跟我说:
“我不叫你妈了,稀饭在火上炖着呢!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样儿。”说完她就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
黄板儿牙拍了一下驴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雪地上印下了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儿牙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得、得、得、得。”
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的清新空气里,响得真好听。
第四章是《驴打滚儿》。
主要内容:
讲述了作者英子家中的奶妈宋妈,因为生活困难而来做奶妈,做事勤快所以便留在了家中。她一直给家里寄平安信和她的工资,是想让她丈夫把田地买回来,想让她儿子小栓子过的更好些。
可是她的丈夫却把钱拿去赌钱,没钱的时候就去向宋妈要钱,所以英子的父母都很讨厌他。后来宋妈才知道原来小栓子几年前就死了,宋妈很伤心。
宋妈想要找回她的另一个孩子,名叫小丫头子。因为他们重男轻女,所以小丫头子从小就卖给了别人,现在没了儿子就想要找回女儿。于是宋妈带着英子去找她的女儿,可惜一无所获,了无音信。后来,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了。
扩展资料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该作品通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
创作背景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为背景创作的。
在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间,林海音一家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居北京,小英子即在北京长大。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作者心头。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一去不还。
作者因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时的那些景色和人物,于是把它们写了下来,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这是林海音写这本小说的初衷。
后世影响
《城南旧事》一书既是作者童年生活的写照,更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也是她最具影响的作品,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1999年列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选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单。2000年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新课标中学生必读丛书”。其中的多篇作品还被选入中学教材。
《城南旧事》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之一,该书系既是有史以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
1983年由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在中国上线公映。并获得了中国**金鸡奖、菲律宾马尼拉国际**节金鹰奖、厄瓜多尔基多城国际**节赤道奖、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思想奖。
--城南旧事
换绿盆儿的,用他的蓝布掸子的把儿,使劲敲着那个两面的大绿盆说:
“听听!您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
妈妈用一堆报纸,三只旧皮鞋,两个破铁锅要换他的四只小板凳,一块洗衣板;宋妈还要饶一个小小绿盆儿,留着拌黄瓜用。
我呢,抱着一个小板凳不放手。换绿盆儿的嚷着要妈妈再添东西。一件旧棉袄,两叠破书都加进去了,他还说:
“添吧,您。”
妈说:“不换了!”叫宋妈把东西搬进去。我着急买卖不能成交,凳子要交还他,谁知换绿盆儿的大声一喊:
“拿去吧!换啦!”他挥着手垂头丧气地说:“唉!谁让今儿个没开张哪!”
四只小板凳就摆在对门的大树荫底下,宋妈带着我们四个人我,珠珠,弟弟,燕燕坐在新板凳上讲故事。燕燕小,挤在宋妈的身边,半坐半靠着,吃她的手指头玩。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我问。
“跟你一般儿大,九岁喽!”
小栓子是宋妈的儿子。她这两天正给我们讲她老家的故事:地里的麦穗长啦,山坡的青草高啦,小栓子摘了狗尾巴花扎在牛犄角上啦。她手里还拿着一只厚厚的鞋底,用粗麻绳纳得密密的,正是给小栓子做的。
“那么他也上三年级啦?”我问。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儿?他成年价给人看牛哪!”她说着停了手里的活儿,举起锥子在头发里划几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个,可得回家看看了,心里老不顺序。”她说完愣愣的,不知在想什么。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其实丫头子的故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宋妈讲过好几遍。宋妈的丫头子和弟弟一样,今年也四岁了。她生了丫头子,才到城里来当奶妈,一下就到我们家,做了弟弟的奶妈。她的奶水好,弟弟吃得又白又胖。她的丫头子呢,就在她来我家试妥了工以后,被她的丈夫抱回去给人家奶去了。我问一次,她讲一次,我也听不腻就是了。
“丫头子呀,她花钱给人家奶去啦!”宋妈说。
“将来还归不归你?”
“我的姑娘不归我?你归不归你妈?”她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奶?为什么到我家当奶妈?为什么你挣的钱又给人家去?” “为什么?为的是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呀!小栓子他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妈自己挣钱!”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那一天,是个冬天,她穿着大红棉袄,里子是白布的,油亮亮的很脏了。她把奶头塞到弟弟的嘴里,弟弟就咕嘟咕嘟地吸呀吸呀,吃了一大顿奶,立刻睡着了,过了很久才醒来,也不哭了。就这样留下她当奶妈的。
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来了,拉着一匹驴,拴在门前的树干上。他有一张大长脸,黄板儿牙,怎么这么难看!妈妈下工钱了,折子上写着:一个月四块钱,两付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过了一年零四个月才许回家去。
穿着红棉袄的宋妈,把她的小孩子包裹在一条旧花棉被里,交给她的丈夫。她送她的丈夫和孩子出来时,哭了,背转身去掀起衣襟在擦眼泪,半天抬不起头来。媒人店的老张劝宋妈说:
“别哭了,小心把奶憋回去。”
宋妈这才止住哭,她把钱算给老张,剩下的全给了她丈夫。她又嘱咐她丈夫许多话,她的丈夫说:
“你放心吧。”
他就抱着孩子牵着驴,走远了。
到了一年四个月,黄板儿牙又来了,他要接宋妈回去,但是宋妈舍不得弟弟,妈妈又要生小孩子,就又把她留下了。宋妈的大洋钱,数了一大垛交给她丈夫,他把钱放进蓝布袋子里,叮叮当当的,牵着驴又走了。
以后他就每年来两回,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墙犄角,弄得满地的驴粪球,好在就一天,他准走。随着驴背滚下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面不是大花生,就是大醉枣,是他送给老爷和太太我爸爸和妈妈的。乡下有的是。
我简直想不出宋妈要是真的回她老家去,我们家会成了什么样儿?老早起来谁给我梳辫子上学去?谁喂燕燕吃饭?弟弟挨爸爸打的时候谁来护着?珠珠拉了屎谁给擦?我们都离不开她呀!
可是她常常要提回家去的话,她近来就问我们好几次:“我回俺们老家去好不好?” “不许啦!”除了不会说话的燕燕以外,我们齐声反对。春天弟弟出麻疹闹得很凶,他紧闭着嘴不肯喝那芦根汤,我们围着鼻子眼睛起满了红疹的弟弟看。妈说:
“好,不吃药,就叫你奶妈回去!回去吧!宋妈!把衣服、玩意儿,都送给你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
宋妈假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走喽!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哟!”
“我喝!我喝!不要走!”弟弟可怜兮兮地张开手要过妈妈手里的那碗芦根汤,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碗。宋妈心疼得什么似的,立刻搂抱起弟弟,把头靠着弟弟滚烫的烂花脸儿说:
“不走!我不会走!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小丫头子!”跟着,她的眼圈可红了,弟弟在她的拍哄中渐渐睡着了。
前几天,一个管宋妈叫大婶儿的小伙子来了,他来住两天,想找活儿做。他会用铁丝给大门的电灯编灯罩儿,免得灯泡被贼偷走。宋妈问他说:
“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们小栓子好吧?”
“嗯?”他好像吃了一惊,瞪着眼珠,“我倒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舅那儿来的!”
“噢,”宋妈怀着心思地呆了一下,又问:“你打你舅那儿来的,那,俺们丫头给刘村的金子他妈奶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吗?”
“哦?”他又是一惊,“没没听说。准没错儿,放心吧!”
停了一下他可又说:
“大婶儿,您要能回趟家看看也好,三、四年没回去啦!”
等到这个小伙子走了,宋妈跟妈妈说,她听了她侄子的话,吞吞吐吐的,很不放心。
妈妈安慰她说:
“我看你这侄儿不正经,你听,他一会儿打你们家来,一会儿打他舅舅家来。他自己的话都对不上,怎么能知道你家孩子的事呢!”
宋妈还是不放心,她说:
“我打今年个一开年心里就老不顺序,做了好几回梦啦!”
她叫了算命的来给解梦。礼拜那天又叫我替她写信。她老家的地名我已经背下了: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交冯大明吾夫平安家信。
“念书多好,看你九岁就会写信,出门丢不了啦!”
“信上说什么?”我拿着笔,铺一张信纸,逞起能来。
“你就写呀,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尽顾得下水里玩。我给做好了两双鞋一套裤褂。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道乏。拿回去的钱前后快二百块了,后坡的二分地该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还有,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要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这封信太长了!”我拦住她没完没了的话,“还是让爸爸写吧!”
爸爸给她写的信寄出去了,宋妈这几天很高兴。现在,她问弟弟说:
“要是小栓子来,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
“给呀!”弟弟说着立刻就站起来。
“我也给。”珠珠说。
“等小栓子来,跟我一块儿上附小念书好不好?”我说。
“那敢情好,只要你妈答应让他在这儿住着。”
“我去说!我妈妈很听我的话。”
“小栓子来了,你们可别笑他呀,英子,你可是顶能笑话人!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宋妈说的仿佛小栓子等会儿就到似的。她又看看我说:
“英子,他准比你高,四年了,可得长多老高呀!”
宋妈高兴得抱起燕燕,放在她的膝盖上。膝盖头颠呀颠的,她唱起她的歌:
“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哥哥出来卖菜,里头坐个姑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她唱着,用手板住燕燕的小手指,指着鼻子和眼睛,燕燕笑得咯咯的。
宋妈又唱那快板儿:
“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姑娘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太阳斜过来了,金黄的光从树叶缝里透过来,正照着我的眼,我随着宋妈的歌声,斜头躲过晃眼的太阳,忽然看见远远的胡同口外,一团黑在动着。我举起手遮住阳光仔细看,真是一匹小驴,得、得、得地走过来了。赶驴的人,蓝布的半截褂子上,蒙了一层黄土。哟!那不是黄板儿牙吗?我喊宋妈:
“你看,真有人骑驴来了!”
宋妈停止了歌声,转过头去呆呆地看。
黄板儿牙一声:“窝哦!”小驴停在我们的面前。
宋妈不说话,也不站起来,刚才的笑容没有了,绷着脸,眼直直瞅着她的丈夫,仿佛等什么。
黄板儿牙也没说话,扑扑地掸他的衣服,黄土都飞起来了。我看不起他!拿手捂着鼻子。他又摘下了草帽扇着,不知道跟谁说:
“好热呀!”
宋妈这才好像忍不住了,问说:
“孩子呢?”
“上他大妈家去了。”他又抬起脚来掸鞋,没看宋妈。他的白布袜子都变黄了,那也是宋妈给做的。他的袜子像鞋一样,底子好几层,细针密线儿纳的。
我看着驴背上的大麻袋,不知里面这回装的是什么。黄板儿牙把口袋拿下来解开了,从里面掏出一大捧烤得倍儿干的挂落枣给我,咬起来是脆的,味儿是辣的,香的。
“英子,你带珠珠上小红她们家玩去,挂落枣儿多拿点儿去,分给人家吃。”宋妈说。 我带着珠珠走了,回过头看,宋妈一手收拾起四个新板凳,一手抱燕燕,弟弟拉着她的衣角,他们正向家里走。黄板儿牙牵起小叫驴,走进我家门,他准又要住一夜。他的驴满地打滚儿,爸爸种的花草,又要被糟践了。
等我们从小红家回来,天都快黑了,挂落枣没吃几个,小红用细绳穿好全给我挂在脖子上了。
进门来,宋妈和她丈夫正在门道里。黄板儿牙坐在我们的新板凳上发呆,宋妈蒙着脸哭,不敢出声儿。
屋里已经摆上饭菜了。妈妈在喂燕燕吃饭,皱着眉,抿着嘴,又摇头叹着气,神气挺不对。 “妈,”我小声地叫,“宋妈哭呢!”
妈妈向我轻轻地摆手,禁止我说话。什么事情这样重要?
“宋妈的小栓子已经死了”,妈妈沙着嗓子对我说,她又转向爸爸:“唉!”已经死了一两年,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一阵子总是心不安,一定要叫她丈夫来问问。她侄子那次来,是话里有意思的。两件事一齐发作,叫人怎么受!”
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
我听了也很难过,但不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又不敢问。
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吆喝她,我轻轻地喊:
“宋妈,妈叫你呢!”
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噎的哭声,到屋里来。妈对她说:
“你明天跟他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
“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么?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宋妈红着眼狠狠地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呆定在我们家不走了。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
“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敢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
“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四十岁了没儿没女的,谁知道是真话假话!”
“问清楚了找找也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妈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旧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妈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
“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
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扑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链儿的歌儿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把她的丈夫扔在门道儿里不理他。他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巴达巴达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它在地上卧着,忽然仰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它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给踩倒了两三棵。驴子吃上干草子,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招手叫我出去。
我跑出来,宋妈跟我说:
“英子,别乱跑,等会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帮我找地方。”
“到哪儿去?”我很奇怪。
“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她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撮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
“好的。”我答应着。
宋妈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
“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得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 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
“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
“是呀,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就顾得玩水。”
“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
“那时候黄板嗯,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
“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他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
“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送给人?”
“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要花钱就花吧。”宋妈说。
我们从绒线胡同穿过兵部洼,中街,西交民巷,出东交民巷就是哈德门大街。”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
“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
“我是后悔,后悔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
“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
“嗯。”宋妈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
我们走到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他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在用**的面粉做一种吃的。
“宋妈,他在做什么?”
“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
“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
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妈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吃。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是买给丫头子的吗?”
出了东交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了,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落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
“走那边吧”,她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说:
“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那
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
“你们是哪儿的?”
“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
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
“在家哪,胡同底那家就是。”
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
“劳驾,找人哪!”宋妈喊道。
其中一个小孩子便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
“姥姥,有人找。”
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
“你这院里住几家子呀?”
“啊啊,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
“您可有个姑娘呀!”
“有呀,你要找孩子他妈呀!”她指着三个男孩子。
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便说:
“找错人了!”
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说:“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
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她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她又问我:
“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儿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湿溶了。我嘴里念了一声:“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
我对宋妈说:
“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儿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她看,“像驴粪球不?”
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
“吃罢!”
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子的影子。
树荫底下听不见冯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地呆看着,没有一句话。
冬天又来了,黄板儿牙又来了。宋妈让他蹲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他说话。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雪》的课文: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妈妈说:“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叫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
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
“你瞧怎么样?”
宋妈这才说:
“也好,我回家跟他算帐去!”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
“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
“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
宋妈看着我说:
“你念书大了,可别欺侮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
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
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她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她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强,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梨炖冰糖给她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捎了来;珠珠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唉!”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
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了许多这钱那钱给她;她丝毫不在乎地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
“说走就走了!”
“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
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
“那年个,上京来的那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儿,四年了!”
她的那件红棉袄,也早就拆了;旧棉花换了榧子儿,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了。
“妈,宋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
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儿,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声地对我说:
“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
“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
“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
“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也这么催,多寒碜!”
“明天早点儿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雪就被抖落下来,掉在驴背上。
我轻轻地穿上衣服出去,到下房找宋妈,她看见我这样早起来,吓了一跳。我说:
“宋妈,给我梳辫子。”
她今天特别的和气,不唠叨我了。
小驴儿吃好了早点,黄板儿牙把它牵到大门口,被褥一条条地搭在驴背上,好像一张沙发椅那么厚,骑上去一定很舒服。
宋妈打点好了,她用一条毛线大围巾包住头,再在脖子上绕两绕。她跟我说:
“我不叫你妈了,稀饭在火上炖着呢!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样儿。”说完她就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
黄板儿牙拍了一下驴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雪地上印下了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儿牙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得、得、得、得。”
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的清新空气里,响得真好听。
1、内容摘要
宋妈的丈夫,一个好吃懒做的赌徒,宋妈生下一双儿女后,就去了林英子家做奶妈了,他丈夫把她的女儿给送人了,儿子据说是掉到河里淹死了。过了好几年,宋妈才知道,之前宋妈还在一直给她的儿子——小栓子做新服,新鞋子往家里带呢。几年后宋妈在大雪天又跟了那个丈夫回家去了。可能那个年代象宋妈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吧。
2、原文
换绿盆儿的,用他的蓝布掸子的把儿,使劲用着那个两面釉的大绿盆说:
“听听!你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儿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
妈妈用一堆报纸,三双旧皮鞋,两个破铁锅要换他的四只小板凳,一块洗衣服板;宋妈还要饶一个小小绿盆儿,留着拌黄瓜用。
我呢,抱着一个小板凳不放手。换绿盆儿的嚷着要妈妈再添东西。一件旧棉袄,两叠破书都加进去了,他还说:
“添吧,您。”
妈说:“不换了!”叫宋妈把东西搬进去,我着急买卖不能成交,凳子要交还他,谁知换绿盆儿的大声一喊:
“拿去吧!换啦!”他挥着手垂头丧气地说:“唉!谁让今儿个没开张哪!”
四个小板凳就摆在对门的大树阴底下,宋妈带着我们四个人——我,珠珠,弟弟,燕燕——坐在新板凳上讲故事。燕燕小,挤在宋妈的身边,半坐半靠着,吃她的手指头玩。
“你家小栓子多大了?”我问。
“跟你一般儿大,九岁喽!”
小栓子是宋妈的儿子。她这两天正给我们讲她老家的故事;地里的麦穗长啦,山坡的青草高啦,小栓子摘了狗尾巴花扎在牛犄角上啦。她手里还拿着一只厚厚的鞋底,用粗麻绳纳得密密的,是给小栓子做的。
“那么他也上三年级啦?”我问。
“乡下人有你这好命儿?他成年价给人看牛哪!”她说着停了手里的活儿,举起锥子在头发里划几下,自言自语地说:“今年个,可得回家看看了,心里老不顺序。”她说完愣愣的,不知在想什么。
“那么你家丫头子呢?”
其实丫头子的故事我早已经知道了,宋妈讲过好几遍。宋妈的丫头子和弟弟一样,今年也四岁了。她生了丫头子,才到城里来当奶妈,一下就到我们家,做了弟弟的奶妈。她的奶水好,弟弟吃得又白又胖。她的丫头子呢,就在她来我家试妥了工以后,让她的丈夫抱回乡下去给人家奶去了。我问一次,她讲一次,我也听不腻就是了。
“丫头子呀,她花钱给人家奶去啦!”宋妈说。
“将来还归不归你?”
“我的姑娘不归我?你归不归你妈?”她反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给奶?为什么到我家当奶妈?为什么你赚的钱又给了人家去?”
“为什么?为的是——说了你也不懂,俺们乡下人命苦呀!小栓子他爸爸没出息,动不动就打我,我一狠心就出来当奶奶自己赚钱!”
我还记得她刚来的那一天,是个冬天,她穿着大红棉袄,里子是白布的,油亮亮的很脏了。她把奶头塞到弟弟的嘴里,弟弟就咕嘟咕嘟地吸呀吸呀,吃了一大顿奶,立刻睡着了,过了很久才醒来,也不哭了。就这样留下她当奶妈的。
过了三天,她的丈夫来了,拉着一匹驴,拴在门前的树干上。他有一张大长脸,黄板儿牙,怎么这么难看!妈妈下工钱了,折子上写着:一个月四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床新铺盖,过一年零四个月才许回家去。
穿着红棉袄的宋妈,把她的小孩子包裹在一条旧花棉被里,交给她的丈夫。她送她的丈夫和孩子出来时,哭了,背转身去掀起衣襟在擦眼泪,半天抬不起头来。
媒人店的老张劝宋妈说:
“别哭了,小心把奶憋回去。”
宋妈这才止住哭,她把钱算给老张,剩下的全给了她丈夫。她嘱咐她丈夫许多话,她的丈夫说:
“您放心吧。”
他就抱着孩子牵着驴,走远了。
到了一年四个月,黄板儿牙又来了,他要接宋妈回去,但是宋奶舍不得弟弟,妈妈又要生小孩,就把她留下了。宋妈的大洋钱,数了一大垛交给她丈夫,他把钱放进蓝布褡裢里,叮叮当当的,牵着驴又走了。
以后他就每年来两回,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墙犄角,弄得满地的驴粪球,好在就一天,他准走。随着驴背滚下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面不是大花生,就是大醉枣,是他送给老爷和太太——我爸爸和妈妈。乡下有的是。
我简直想不出宋妈要是真的回她老家去,我们家会成什么样儿?谁给我老早起来梳辫子上学去?谁喂燕燕吃饭?弟弟挨爸爸打的时候谁来护着?珠珠拉了尿谁来给擦?我们都离不开她呀!
可是她常常要提回家去的话,她近来就问了我们好几次:“我回俺们老家去好不好?”
“不许啦!”除了不会说话的燕燕以外,我们齐声反对。
春天弟弟出麻疹闹得很凶,他紧闭着嘴不肯喝那芦根汤,我们围着鼻子眼睛起满了红疹的弟弟。妈说:
“好,不吃药,就叫你奶妈回去!回去吧!宋妈!把衣服,玩意儿,都送给你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
宋妈假装一边往外走一边说:
“走喽!回家喽!回家找俺们小栓子、小丫头子去哟!”
“我喝!我喝!不要走!”弟弟可怜巴巴地张开手,要过妈妈手里的那碗芦根汤,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碗。宋妈心疼得什么似的,立刻搂抱起弟弟,把头靠着弟弟滚烫的烂花脸儿说:
“不走!我不会走!我还是要俺们弟弟,不要小栓子,不要小丫头子!”跟着,她的眼圈可红了,弟弟在她的拍哄中渐渐睡着了。
前几天,一个管宋妈叫大婶儿的小伙子来了,他来住两天,想找活儿做。他会用铁丝给大门的电灯编灯罩儿,免得灯泡儿被贼偷走。宋妈问他说:
“你上京来的时候,看见我信栓子好吧?”
“嗯。”他好像吃了一惊,瞪着眼珠,“我倒没看见,我是打刘村我舅舅那儿来的!”
“噢。”宋妈怀着心思地呆了一下,又问:“你打你舅舅那儿来的,那,俺们丫头子给刘村的金子他妈妈着,你可听说孩子结实吗?”
“哦?”他又是一惊,“没——没听说。准没错儿,放心吧!”
停一下他可又说:
“大婶儿,您要能回起家看看也好,三四年没回去啦!”
等到这个小伙子走了,宋奶跟妈妈说,她听了她侄子的话,吞吞吐吐的,很不放心。
妈妈安慰她说:
“我看你这侄儿不正经,你听,他一会儿打你们家来,一会儿打他舅舅家来。
他自己的话都对不上,怎么能知道你家孩子的事呢!”
宋妈还是不放心,她说:
“打今年个一开年,我心里就老不顺序,做了好几回梦啦!”
她叫了算命的给解梦。礼拜那天又叫我替她写信。她老家的地名我已经背下了:
顺义县牛栏山冯村妥交冯大明吾夫平安家信。
“念书多好,看你九岁就会写信,出门丢不了啦!”
“信上说什么?”我拿着笔,铺一张信纸,逞起能来。
“你就写呀,家里大小可平安?小栓子到野地里放牛要小心,别尽顾得下水里玩,我给做好了两双鞋一套裤褂。丫头子那儿别忘了到时候送钱去!给人家多道道乏。拿回去的钱前后快二百块了,后坡的二分地该赎就赎回来,省得老种人家的地。
还有,我这儿倒是平安,就是惦记着孩子,赶下个月要来的时候,把栓子带来我瞅瞅也安心。还有,……”
“这封信太长了!”我拦住她没完没了的话,一还是让爸爸写吧!”
爸爸给她写的信寄出去,宋妈这几天很高兴。现在,她问弟弟说:
“要是小栓子来,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
“给呀!”弟弟说着立刻就站起来。
“我也给。”珠珠说。
“等小栓子来,跟我一块儿上附小念书好不好?”我说。
“那敢情好,只要你妈答应让他在这儿住着。”
“我去说!我妈妈很听我的话。”
“小栓子来了,你们可别笑他呀,英子,你可是顶能笑话人!他是乡下人,可土着呢!”宋妈说的仿佛小栓子等会儿就到似的。她又看看我说:
“英子,他准比你高,四年了,可得长多老高呀!”
宋妈高兴得抱起燕燕,放在她的膝盖上。膝盖头颠呀颠的,她唱起她的歌:
“鸡蛋鸡蛋壳壳儿,里头坐个哥哥儿,哥哥出来卖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她唱着,用手扳住燕燕的小手指,指着鼻子和眼睛,燕燕笑得咯咯的。
宋妈又唱那快板儿的:
“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姑娘都来到,就差我的姑娘还没来;说着说着就来了,骑着驴,打着伞,光着屁股挽着髻……”
太阳斜过来了,金黄的光从树叶缝里透过来,正照着我的眼,我随着宋妈的歌声,斜头躲过晃眼的太阳,忽然看见远远的胡同口外,一团黑在动着。我举起手遮住阳光仔细看,真是一匹小驴,得、得、得地走过来了。赶驴的人,蓝布的半截褂子上,蒙了一层黄土。哟!那不是黄板儿牙吗?我喊宋妈:
“你看,真有人骑驴来了!”
宋妈停止了歌声,转过头去呆呆地看。“
黄板儿牙一声:“窝——哦!”小驴停在我们的面前。
宋妈不说话,也不站起来,刚才的笑容没有了,绷着脸,眼直直瞅着她的丈夫,仿佛等什么。
黄板儿牙也没说话,扑扑地摔打他的衣服,黄土都飞起来了。我看不起他!拿手捂着鼻子。他又摘下了草帽扇着,不知道跟谁说:
“好热呀!”
宋妈这才好像忍不住了,问说:
“孩子呢?”
“上——上他大妈家去了。”他又抬起脚来掸鞋,没看宋妈。他的白布的袜子都变黄了,那也是宋妈给做的。他的袜子像鞋一样,底子好几层,细针密线儿纳出来的。
我看着驴背上的大麻袋,不知道里面这回装的是什么。黄板儿牙把口袋拿下来解开了,从里面掏出一大捧烤得信儿干的挂落枣给我,咬起来是脆的,味儿是辣的,香的。
“英子,你带珠珠上小红她们家玩去,挂落枣儿多拿点儿去,分给人家吃。”宋妈说。
我带着珠珠走了,回过头看,宋妈一手收拾起四个新板凳,一手抱燕燕,弟弟拉着她的衣角,他们正向家里走。黄板儿牙牵起小叫驴,走进我家门,他准又要住一夜。他的驴满地打滚儿,爸爸种的花草,又要被糟践了。
等我们从小红家回来,天都快黑了,挂落枣没吃几个,小红用细绳穿好全给我挂在脖子上了。
进门看见宋妈和她丈夫正在门道里。黄板儿牙坐在我们的新板凳上发呆,宋妈蒙着脸哭,不敢出声儿。
屋里已经摆上饭菜了。妈妈在喂燕燕吃饭,皱着眉,抿着嘴,又摇头又叹气,神气挺不对。
“妈,”我小声地叫,“宋妈哭呢!”
妈妈向我轻轻地摆手,禁止我说话。什么事情这样地重要?
“宋妈的小栓子已经死了,”妈妈沙着嗓子对我说,她又转向爸爸:“唉!已经死了一两年,到现在才说出来,怪不得宋妈这一阵子总是心不安,一定要叫她丈夫来问问。她侄子那次来,是话里有意思的。两件事一齐发作,叫人怎么受!”
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
我听了也很难过,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又不敢问。
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呵叱她,我轻轻地喊:
“宋奶,妈叫你呢!”
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田的哭声,到屋里来。妈对她说:
“你明天跟他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
“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么?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宋妈红着眼狠狠地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呆定在我们家不走了。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
“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敢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待!”
“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
“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四十岁了没儿没女,谁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假话!”
“问清楚了找找也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奶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日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奶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
“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
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
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扑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连儿的歌儿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把她的丈夫扔在门道儿里不理他。他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它在地上卧着,忽然仰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它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又给踩倒了两三棵。驴子吃上干草了,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鹰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
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招手叫我出去。
我跑出来,宋奶跟我说:
“英子,别乱跑,等会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帮我找地方。”
“到哪儿去?”我很奇怪。
“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她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撮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
“好。”我答应着。
宋奶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
“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要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
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
“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
“是呀,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净顾得玩水。”
“他摔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
“那时候黄板——嗯,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
“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他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
“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送给人?”
“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要花钱就花吧。”
宋妈说,我们从绒线胡同走,穿过兵部洼、中街、西交民巷,出东交民巷就是哈德门大街。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
“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
“我是后悔——后海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
“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
“嗯。”宋奶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
我们走到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他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在用**的面粉做一种吃的。
“宋妈,他在做什么?”
“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
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奶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
“是买给丫头子的吗?”
出了东交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了,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落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
“走那边吧,”她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说:
“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
那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
“你们是哪儿的?”
“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
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
“在家哪,胡同底那家就是。”
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
“劳驾,找人哪!”宋妈大声喊。
其中一个小孩子就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
“姥姥,有人找。”
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
“您这院里住几家子呀?”
“啊周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
“您可有个姑娘呀?”
“有呀,你要找孩子他妈呀?”她指着三个男孩子。
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就说:
“找错人了!”
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
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对我说:
“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
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她用手使劲捏着两届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她又问我:
“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儿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溶湿了。我嘴里念了一声:“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
我对宋妈说:
“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儿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她看,“像驴粪球不?”
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
“吃罢!”
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的影子。
树阴底下听不见冯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地呆看着,没有一句话。
冬天又来了,黄板儿牙又来了,宋妈把他撂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他说话。
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奶喂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下雪》的: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
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
妈妈说:
“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请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
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问:
“你瞧怎么样?”
宋妈这才说:
“也好,我回家跟他算账去!”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
“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
“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
宋妈看着我说:
“你念书大了,可别欺侮弟弟呀!别净给他跟你爸爸告状,他小。
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
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她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她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因,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儿梨炖冰糖给她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捎了来;珠珠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唉!”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
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了许多这钱那钱给她,她毫不在乎地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
“说走就走了!”
“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
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
“那年个,上京来的那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儿,四年了。”
她的那件红棉袄,也早就拆了,旧棉花换了榧子儿,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用了。
“妈,宋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
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儿,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轻地对我说:
“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
“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
“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
“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了也这么催,多寒储!”
“明天早点儿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雪就抖搂下来,掉在驴背上。
我轻轻地穿上衣服出去,到下房找宋奶,她看我这样早起来吓一跳。我说:
“宋妈,给我梳辫子。”
她今天特别地和气,不唠叨我了。
小驴儿吃好了早点,黄板儿牙把它牵到大门口,被褥一条条地搭在驴背上,好像一张沙发椅那么厚,骑上去一定很舒服。
宋妈打点好了,她把一条毛线大围巾包住头,再在脖子上绕两绕。她跟我说:
“我不叫醒你妈了,稀饭在火上炖着呢!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大姐样儿。”说完她就盘腿坐在驴背上,那姿势真叫绝!
黄板儿牙拍了一下驴屁股,小驴儿朝前走,在厚厚雪地上印下一个个清楚的蹄印儿。黄板儿牙在后面跟着驴跑,嘴里喊着:“得、得、得、得。”
驴脖子上套了一串小铃铛,在雪后新清的空气里,响得真好听。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