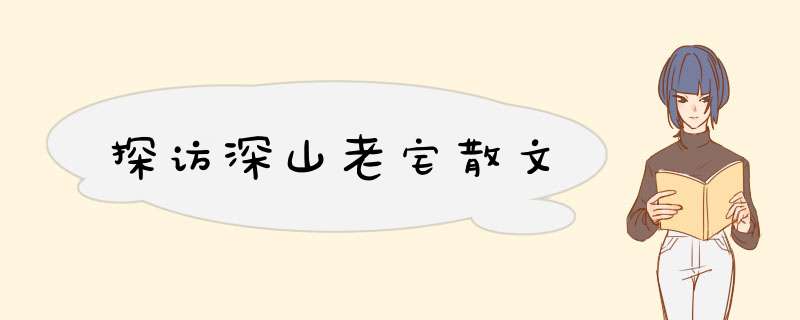
话说国庆期间我随摄影组前往二百里开外的奉新九仙村采风,吃过中饭后,整整一个下午,大家行走在远离尘嚣、群山环绕的九仙村,尽情呼吸着山野清新自然的空气,徜徉在一片接一片的金色稻田间,心里感到无比舒畅。
直到傍晚十分我们才尽兴而归,美美睡上一觉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清晨不到六点钟,行走在秋天的乡间小路上,感觉空气格外清凉,几个穿着单衣的摄友,不禁后悔没多带一件外套来。
“快来看,远处有一栋老房子!”走在最前面的一位摄友忽然发出了一阵惊呼声,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般的惊喜!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朝西边望去,但见在一片郁郁苍苍的翠竹掩映之下,一栋赭**的老房子默默伫立,仿佛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正向我们招手。竹林背后是蔼蔼青山,之上是湛蓝的天空,上面点缀着几朵白云,此时从老屋上方正冒起缕缕炊烟,这一切组合在一起,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画面!
看着老屋离我们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要到达并非易事,因为一路上杂草丛生,但闻小溪发出淙淙的声响却不见其踪影,仔细一看,原来溪水隐于石边深草之下,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踩到水里去,或者被杂草绊着。我们小心翼翼,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西边那一栋老屋走去,望着几只小鸟翩然掠过头顶,我忽然灵机一动,一首五律遂从心底划出:
但闻溪水响,石上拨清弦。
鸟入苍山远,人行幽草牵。
松风摇竹海,墟舍起炊烟。
君问桃源处,心悠地自偏。
半路上,走在后面的我无意间转过身来向东望去,竟然又瞥见一幅令人震撼的画卷:清晨的太阳刚爬上山坡,一株颀长的杉树挺立在层层的梯田之上,太阳光恰好透过这棵杉树射向地面,整个画面或明或暗,色彩分明,怎不令人怦然心动!
一路上且行且赏,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踏上一块块青石板铺成的小路走进了老屋的院子。住在老屋里的是一对年约六七十的老两口,当我们说明来意后,这两位朴实善良的老人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屋。老妇人告诉我们,儿女们都出外打工去了,家里只剩下他们老两口看家。问起老宅,她告诉我们自从她嫁到这里来老宅就有了,那时还不算很新,这样看来,少说这座老宅和二位老人的年纪相当。
走近前一看,一扇扇木门虽然没有雕刻得十分精细,但却是镂空的,看上去十分大方而古朴,可以想见当初建成时并不简陋,还颇有几分气派,当时就算不是富庶人家,也是积攒了些钱才建成的。门下方斑斑点点的旧漆有些脱落,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就这样我们饶有兴致地围着老宅四处走走逛逛,院子里的两只大白鹅见到陌生人来,立刻警惕地伸长了脖子叫着,看到我们并无恶意,于是依然在闲庭漫步;一抬头,发现墙上方悬着一排用芒草扎成的'扫把,下面挂着一篮红椒;来到厨房,一眼就看见锅灶下跳动着红红的火焰,原来两位老人正在忙着弄早饭。虽然老宅处处洋溢着生活气息,但我总感觉还缺点什么,望着两位留守老人孤独的背影,我心里不知怎的涌起一阵心酸。
婉谢了二位老人一起用早餐的好意,我们告别了老宅。渐行渐远,老宅孤独而苍老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里也越变越小,然而,它在我心目中反而越来越大,因为其中装满了岁月的沧桑,游子的思念,父母的期待!从此这座隐于深山竹林边中的老宅,在我心里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挥之不去。
我家的老宅,是个普通的院落,低矮的房屋,草顶土墙。
我家的老宅,又是个特殊的院落,院中有院,院中套院,而这种格局并非古时大户人家那种前庭后院的布局,完全是一个“怪胎”。
走进矮矮的大门,首先是我家,正房三大间,住着祖父母,东配房三小间,大爷一家住两间,另一间是我们四口之家的小天地,按正常布局,与东配房相对应的是西配房,但西配房的位置却是一独立小院,有大门和院墙,是二祖父一家的生息之地,紧随我家正房其后的又是一小院,安荣大爷一家住在里面。他们两家人出得自家大门,便是我家的天井,这两家人若想上大街,必须从我家的大门走出去,这种格局在当地极少见。如果有人想找我们三家中的任何一位,只要说三家走一个大门的,全村没有不知道的。
记得那时院中有一石磨,是几家人的公用设施,因人口多,石磨闲时极少,但从未因用磨闹过矛盾,几家人非常和睦。我时常站在石磨旁看大人不知疲倦似的一圈圈推磨,倾听石磨发出有节奏的“吱扭”声。石磨旁有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梧桐树,树身足有水桶般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树冠宛如一把巨伞遮在院子上空,每有小雨,站在树下竟淋不到身上,当艳阳普照、和风吹过时便枝叶腾挪、参差披拂,地上树影斑斑、婀娜多姿。
最让我们几个小伙伴高兴的是,每到冬季天刚黑,麻雀便栖身于树丫杈,用手电筒一照,强烈的光刺得那小东西目不视物,于是,便乖乖的做了我们的俘虏,第二天自然成了一顿美食。夏天,树下更是热闹异常,那时乡下没有电,吃罢晚饭,几家大人便不约而同地坐在树下,仰望月挂中天,手摇蒲扇,纳凉拉呱,王家长李家短了、谁家的儿子不孝顺了、谁家的日子不易了,每说到令人心酸处,大人们便慨叹一番,说到开心的事,欢快的笑声便充满了整个院子。
我们小孩子是坐不住的,围着石磨追逐嬉戏,闹得人仰马翻,大人们就吓唬说:“谁再不老实,老马猴子就来吃他。”不知道这老马猴子到底是何种猛兽,听了大人的话我们再也不敢打闹,一个个正襟危坐于磨盘上,听大人们侃大山,但这安静是短暂的,不一会就把大人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打闹继续进行。
说话最多的要算安荣大爷了,他读过很多书,知道的事特别多,他常给大家讲故事、出谜语,什么嫦娥奔月了,薛刚反唐了,朱元璋炮轰庆功楼了,诸葛亮舌战群儒了……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我和小伙伴调皮,叫他“故事篓子大爷”,喊得时间长了嫌绕嘴,干脆喊他“篓子大爷”,他也不生气,只是慈祥的看着我们笑笑,然后装上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吸上几口,阵阵青烟便袅袅升起,只让我们看着越升越高的烟雾出神。有一次,他给大家出了几个字谜,至今我还依晰记得几个,第一个谜面是:又在村里面。大家没费多大劲就猜出是树,第二个谜面是:十五天。经过苦思冥想猜出是胖,第三个是:刘备哭、刘邦笑。这下可把大伙难住了,抓耳挠腮的半天也未猜出,最后还是安荣大爷说出了谜底,这个字是翠,并给大家解释一番,他说:“羽指历史上的'两位名人,就是关羽和项羽,卒是死的意思,关羽死刘备当然要哭,因为他俩是桃园结义的弟兄,项羽死刘邦自然笑,因为楚汉争霸天下,这两位是死对头。”大家这才恍然大悟,由于年岁太久,其它字谜我已记不清了,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故事和谜语的熏陶,我从小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加工作后便拿起笨拙的笔学习写作,虽多次失败,但偶然亦有小豆腐块文章见诸报端,这与儿时在老宅那段令人难忘的生活之影响是分不开的。
记得有一年夏天深夜,闷热了一天的天空突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隐约听到院子里倒下了什么,吓得我双手紧紧捂着耳朵,心里直打鼓。早晨推门一看,天哪!梧桐树被拦腰折断,偌大的树冠塞满了整个院子,屋顶上墙头上也被树枝树叶占领了,人在屋里只能猫着腰从树枝的缝隙里钻出去。大娘婶子窃窃私语,很神秘似的,凑近仔细一听才知,原来树上有妖物,被老天爷连树带妖一块劈死了。我几步跑到磨旁,天真的站在磨盘上,想看看被劈死的妖物是否青面獠牙,有没有流血,身上有没有长毛,结果只看到崭新的树身断茬。
自从大树倒下后,再也没有人到树下乘凉拉呱了,大家可能是怕那妖物的灵魂还没有走。每到夜晚院子里死一般寂静,黑黑的,静静的,没有了故事,没有了追逐打闹,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出来,只好坐在煤油灯下,看着墙上微微晃动的身影发呆。现在回想起来,还为那棵大树的命运颇感惋惜。当然,我也早已明白了树倒下的真正原因。
在梧桐树倒下的那年,随着我和姐姐渐渐长大,一间小屋明显不足,贫穷的父母依然决定再盖间南屋,经过东拼西凑材料基本凑齐,只檩条还不够,父亲忽然想起我二大爷家盖房时曾借用我家的檩条,并许下我家用时一定还给我们,父亲决定前去讨要,檩条未带回来,带回的是满身的伤痕,原来二大爷夫妇失口否认此事,生性耿直的父亲又气又急,三人发生了冲突,二对一的格局,吃亏的自然是父亲。几根檩条对现在人来说根本不屑一顾,但在那贫穷的年代,可是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后才换来的。那时,幼小的我,还不懂人格是怎么回事,只是望着伤痕累累的父亲,和姐姐失声痛哭。
四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老宅早已完成了她的使命,悄无声息的消失了,然而,老宅的胸膛还在,在她的怀抱里,矗立着钢筋水泥的构体,时代赋予了她新的生命。
老宅是一副寒伧的面孔,矮矮的院墙、粗陋的房屋、挂满灰尘的墙壁,但她给我的童年带来的是欢乐的笑声、温馨的感受、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热爱。虽然父辈的恩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曾留下过创伤,有过对人格的迷惘,但那伤痛是短暂的,老宅就如柔和皎洁的月光,轻轻地、细细地抚慰着我的心灵,愈合着我的伤口,我在她温暖的怀抱里,不但肉体健康的成长着,思想也在健康的成长着,当我在事业上或生活中遭遇坎坷时,便想起老宅里那温馨的场面,那快乐的笑声,心里就平静的如一泓秋水,波澜不惊,怀着一颗平常心,去面对困难、面对人生。
从梦中醒来,那熟悉而模糊了的老屋一点一点清晰了起来。
记忆中在七八岁前是和奶奶和三叔一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爷爷奶奶和四叔五叔住北屋的三间,我们一家五口住东屋的北间,三叔一家四口住东屋的南间。童年的家就在这样一个亲密拥堵狭小的空间里。这所老宅也是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
清晰的记得,老宅的对门是供销社(国营的商店)。家门口有一对半圆且光滑的石凳子,其实只是杵在门口的两个石头,我们常常坐在上面玩耍。黑漆的木门吱吱呀呀,它常是敞开的。我们姐妹们常常一人站在一边门后,比赛谁先爬上门顶。门后有插门的木栓,往上往下还有几根固定的横木。我们便沿着这横木爬上爬下。然后听着木门吱呀着,我们站在上面手扶紧了使劲晃着门,或者干脆让下面的姐妹来回的推着门,这时在上面就会有种飞的感觉,很神气的样子。倘被大人发现,免不了会被训斥几声,然后乖乖的爬下去,趁着没人注意,再爬上去享受那种快意。这就是我们叫的大门洞。这里还常常会放有一个两轮推土车。那会这也是我们的乐园。一个大几岁的叫姑姑的经常扶着车把,让我们四五个小的坐在车上,她一上一下压着,像跷跷板。她翘起来时,我们得扶好车身使着劲,不然就统统从车身后掉下去了。待她压下去时,我们被高高的翘起,几个孩子便嘻嘻哈哈,娃娃丫丫的叫起来,一阵嬉闹打笑。有时,自己也想试试扶车把翘起的感觉,因为太瘦小,力气不够,而常不能如愿。
走过大门,穿过一段露天走廊,便到了第二个门洞。门进院处有一个刻有木纹雕饰的红木门,在右手边还有一个侧门,这个门常常是锁着的。我常常猜测里面是不是别有洞天,是不是个小花园?总之在有记忆的好多年里这里一直是个迷,是个神秘的所在。我们几个孩子也常常想法进去,却一直未果。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只知道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大人们大概是午休了。总之是没人。我们几个孩子偷着往外溜时,发现这扇神秘的大门上面的锁竟然是挂着的,只要拿下来就可以进去了。不知是谁手快,已拿下锁子。我们迅速跳进去,看见的是满目野草,心里有些怕,怕有虫子,神鬼什么的。踌躇了半天,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几双小脚在草丛里小心翼翼的'穿梭着,除了草就是对面的墙,宽有十几米,长度大约是宽的几倍。我们沿着长向西走,忽然发现一口井,幸亏走得小心,不然掉进去可就惨了。年长的堂姐说,听说这井里有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埋在这里呢。我们争着向井沿上看,希望能看到些什么,却是深不见底,什么也看不见。这会恐惧心理又来作怪,万一从井里飞出个什么鬼怪来,我们怎么办?几个孩子哗的一下全跑开了,继续往西,却发现于邻家的院落连在一起了,石榴树,枣树,桃树……不知谁提议,快走吧!别让人发现了。轰的一声,我们顺着来时的路,踏出那扇神秘之门,还没忘把锁子挂上。这次神秘的探险宣告结束。
进得二门,便是大院了。靠近二门的东边便是我的家了。西边靠南墙处是猪圈和厕所,向北走是养鸡的小房,似乎还养过羊啊狗啊的。正北面就是正房了,爷奶和未成家的叔叔们住在这。记得夏天下了雨,妈妈就说我们欢了辫子(高兴的意思),疯跑向院里,蹦啊,跳啊,唱啊,喊啊!最好的是有风的雨,因为这时苹果树上会掉下许多苹果,平时奶奶看得紧,从不会让我们摘一个未成熟的果子。每次当我拿回100分的考卷给妈妈看时,妈妈常会嘱咐我去让奶奶看看,记忆中的奶奶一边擀着面条,一边象征性的表扬一番,我就带着满足的幸福回到妈妈身边。童年就是在这种捡拾与幸福中一天天溜走了。
离开老屋住进新家大概是8岁左右。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听爸爸说快搬进新家了,中午时去看着新房。我自报奋勇的主动要求去。得到允许后,连蹦带跳的拿着钥匙飞了过去。记得爸爸说西屋是我和姐姐的卧室,我美美的来到西屋东摸摸西看看,累了就想躺在炕上睡会,可刚躺下,就发现窗户上爬满了黑壳会飞的虫子,嗡嗡的几次快撞上我的头发了,我吓得尖叫着,再顾不得什么看家的诺言了。我拔腿就跑,路上碰见了不放心的爸爸。我描述了自己的恐惧,爸爸拉着我的手告诉我,那是臭大姐,碰到它,会散发难闻的臭味。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的第一种虫子。
搬进新家记忆最深的就是院里的两棵梧桐树,只几个月的样子,两棵小树超过了我的个子,几年后就是枝繁叶茂碗口粗了,我只能仰视。不记得是哪年,只记得是我第一次看见下冰雹。下午时分,天黑漆漆的,狂风怒吼,雷鸣闪电,坐在外屋聊天的爸妈和婶子们突然说,快看,下冰雹了。我好奇地隔着门看到砸到地上的黄豆大的水晶颗粒。当时还觉得好玩,好看。紧接着吱呀呀的一声,厨房门口的那棵大梧桐树呻吟了几声,巨大的手臂从空中掉下。不一会,梧桐树连根一点点的从土里崛起,眼看着他挣扎着,坚持着,最终一下子瘫软在南边房檐上,彻底地倒塌了。与他邻近的水管,污水沟也受到破坏。那是我自记忆中第一次理解天灾这个词,第一次目睹大自然的力量。
新家在一天天一年年的风霜雨雪里巩固完善着。曾经的南厨房,我第一次烙饼的影像,第一次包饺子‘煮饺子的笑话,第一次蒸出雪白馒头的成就感,第一次和姐弟在半夜等父母回家的焦急……少年时代就在这等待和诸多第一次中不知不觉的溜走了。
如今的新家已被视为老家,它静静地观看着曾经的辉煌,热闹,默默的等待着新的变迁……不动声色,不悲不喜,不恼不怒,不卑不亢的依然矗立!
怀念那所老屋,其实更多的是怀念儿童时代的快乐与无忧,惋惜现在孩子的所谓快乐与无休止的补习班。若是时光可以逆转,不知道现在的孩子是喜欢现在的电视电脑和各种班的乐趣,还是喜欢我们那种无忧无虑的与大自然为伴的快乐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