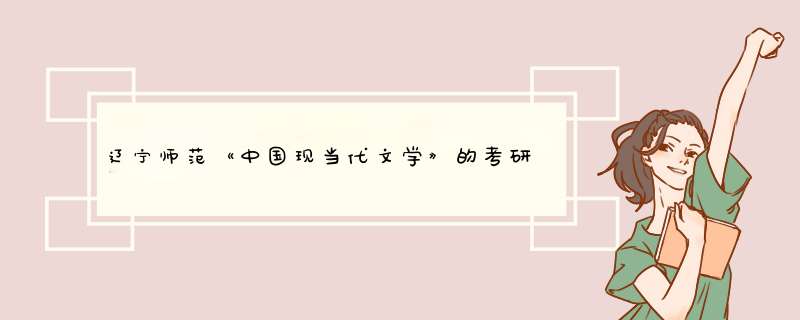
首先,学校指定的书目都是针对专业课的。每个学校都是导师自己出题。
其次,不同的学校考的科目和指定书目都不一样,而且本科的教材全国存在南北差异。
第三,就文学基础而言,包括文学史的所有最基本的知识,不同学校不同导师要求不一样,有的会包括外国文学史内容。
第四,北方的学校一般都是用高教出版社的书,个别重点大学,如人大,北大,复旦等,会用自己老师编的书。
感觉你对考研知识了解的比较少,还是多自己查查吧。考研学校都会指定复习的书目的。
传神的和科学的中外艺术审美之比较
《一》
王子年《拾遗记》里有一段记述∶“烈裔骞霄国人,善画。始皇元年献之。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精点,或点之飞走也”。从这则故事看来,早在始皇元年,中西艺术就开始有交流了。当然,那时的西,还是指西域一带。可惜,《拾遗记》是一本志怪小说,不能与史书同等视之,不过,以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中华的气势看,推断那时有外国工匠来朝拜献艺,亦不算过分离谱。那时候绘画的工艺很强,大概个别工匠还身怀绝技,这位故事中的画家也许就是一例。用当今的眼光看,他应是一位了不起的先锋派兼细密画家,只是这个“点精术”实在已属神话了。然而,偏偏就是这个“绝招”影响深远。见诸文字记载的,至少有西晋卫协,画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睛;东晋顾恺之;每画人成数年不点睛。一次还在瓦官寺画维摩诘像,以表演点睛为寺庙募损达百万之巨;而张僧繇的画龙点睛破壁而飞的故事,至今还作成语使用。
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就更大了,敦煌莫高窟等古迹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如果从犍舵罗艺术特徵而论,那可以说已经间接地引进了正的西方艺术了。当然,直接的传入,还是在明清之后。於是,首先是使中国从此增添了一个新的画种。其次,就是对中国画本身产生深刻影响,徐悲鸿、林风眠等大师的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
而中国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也是显著的。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工艺品带到西方暂且不说,比较直接的,是唐代中国艺术传到了日本。而日本艺术对西方现代艺术出现是有著特殊意义的。后印象派的许多大家都曾受到过日本绘画的影响。在马奈的《左拉肖像》。梵高的《唐吉老爹》、《一只耳朵扎著绷带的自画像》等作品的背景中都出现了日本浮世绘版画,而梵高还曾认真地用油画临摹过日本版画。高更的《静物和日本版画》中,日本版画已直接进入主题。塞尚出於门户偏见,曾经称高更为“中国式人物的,制作者”。(9) 赫伯特.里德在追寻现代艺术在视觉和技法宗源时,就曾指出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英国。在论述日本的影响时他说∶“有许多印象派画家表面上受了日本浮世绘木刻影响,但是只有在梵高和高更的作品中才明显地看出这种艺术的充分影响效果。两位画家都试图以油画的语言去创造类似的艺术形式,的确,像惠斯勒这样的画家就曾模仿过日本版画的结构和构图的特点,他却在这种体制上添加一种讲究气氛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想像,这是借助於中国绘画的,但本质上却没有脱离莫奈或德加的风格”。(10)至於西方现代艺术又反过来冲击中国艺坛,这则是在本世纪末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可以设想,将来还会有更广泛的交流,还会相互有更深刻的影响。
《二》
塞尚曾藐视地称高更为“中国式人物的制作者”,这种观点是居於他对装饰因素的排斥。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对中国艺术的无知。塞尚是否见过中国画原作,未作考证。不过,一些来华的传教士见到中国画后,总觉得人物是单薄的,在衣裳里似乎没有躯体。诚然,一种异域文化的出现,其内涵的确是很难一下子为人所理解的。当西方油画传入中国之初,国人亦曾藐视称此等作品“匠气”,对其毫无笔墨可言时有耻笑。当然,那时多为传教士带来的宣传品,不过,即便见到大师之作,由於观念的差异,想亦未必能增加几分崇敬。清末的林纾,对西画的态度算是客观的了,他在《春觉斋论画》中曾谈到西画, 对其写实功夫是备加赞赏的∶“夫像形之至肖者,无若西人之画。”“画境极分远近。有画大树参天者,而树外人家树木如豆如苗。即远山亦不逾寸。用远镜窥之,状至逼肖”。但是,他依旧认为∶“似则似耳,然观者如睹照片,毫无意味”。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交流渐频,相互认识逐步加深,而相互排斥也依然存在。如康有为在游历欧洲之后,就曾励赞希腊罗马艺术,其中就提到了作品中人体结构的准确刻画的意义,认为筋脉不见,精巧不出。再后来,西方也陆续有人来华学习中国画。但是,作为一种时代的创造,西人并未给中国艺术同等的地位,作为一种商品的流通,西人也未把中国艺术放到同等的水准。当然,这里首先是受制於经济实力、政治等等大前题,然而,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举个例子,西人毕竟不能像国人一样体味中国传统术尤其是中国画中纸、笔、墨所产生的神韵,甚至还偏偏计较这些材料本身,认为仅仅是在纸上涂抹几笔,片刻即成,不过为西画之水彩而已。而油画又是在又是油彩,又是外框又是内框,工序复杂、制作艰难、保存长久等等,价格当然不与一张“纸”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尽管西画对国画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影响,但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又重新反思这段路程,一些美术院校的中国画专业开始不像以前那样完全按西画的方式画素描了,这就是一种理性的反应。
《三》
其实,以中国观去论西方艺术,亦未必没有共同语言。苏格拉底就十分重视通过眼睛去刻对象的“心境”、“精神方面的特质”,他与画家巴拉苏思的对话就是通过层层剥离,步步进逼的手法,论证了人常常用朋友或敌人的“神色”去看旁人,而绘画可以“把这种神色在眼睛里描绘出来”。并且,“高尚和慷慨,下贱和鄙吝,谦虚和聪慧,骄傲和愚蠢,也就一定要表现在神色和姿势上”,所以,“美的善的可爱的”和“丑的恶的可憎的”两种区别很大的性格都能描绘出来。(11) 达文西也强调“精神状态”、“思想意图”、“内心意图”等,不过,他更重视通过动作表现。他说∶“绘画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动作都应表现它的精神状态,例如欲望、嘲笑、愤怒、怜悯等”。又说∶“在绘画里人物的动作在各种情况下都应表现它们内心的意图”。(12) 这些论述,实质上就是要“传神”,尤其前者,几乎就是“阿堵传神”了,而且,如果上述的传神是属於对象的神的话,那到了高更,梵高以及后来的表现派等等,则可以说是传作者的神了,而且非常鲜明、强烈。
此外,还可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例。如我国古代有所谓“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声诗”的说法,而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也提出了同一的命题,他们的说法是∶“绘画是哑诗,诗是能言画”。又如,我国古代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说法,在古希腊作品中,路德维希宝座的浮雕《阿沸洛狄忒的诞生》那种湿淋淋的贴身衣裳的刻画,《胜利女神尼开》中那种迎风招展、衣带飘扬的雕琢,正好做这两句话的注脚。王维《袁安卧雪图》画了雪中芭蕉,遭人非议,而沈括却为之辩护,说这是“造理入神,回得天机,此难与俗人论也”。并且认为“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梦溪笔谈》)。这类艺术处理,在西方艺术中就更多了。即使是写实性很强的作品都能举出不少例子。古希腊米隆的《掷铁饼者》据有关体育运动专家分析,运动员的这种手脚配合的姿势掷起来必定要跌跤的。无疑,具有至今都难以企及的技巧的古希腊雕刻家并非雕不好这个动作,而相反恰恰是以此服从一种理想的追求。安格尔的《大宫女》被认为脊椎多长了一节,这也并非这个学院派大师的失误,而恰恰是他服从画面构图的著意安排。而歌德对荷兰画家吕邦斯的一幅风景画的论述,则更为接近。在这幅品中出现了树丛的投影与光源矛盾的违反自然规律的现象,歌德说∶“吕邦斯正是用这个办法证明他的伟大,宣示出他本著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来处理自然。...他用这种天才的方式向世人显示∶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它有它的规律”。(13) 这显然也是一种“造理入神”的议论。可见,“奥理冥造者”在中西画界并不“罕见”的。也正因为有这个共同的“理”,所以艺术才能成为超越东西南北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
至此,话应该说回来了。看来,中、西艺术,其终极目标还是一致的。不过,由於民族精神内涵不同,加上工具、材料有异,至使其各具自身的特色。孰长孰短,难以一概而论,取长补短,才是科学态度。随著中西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人们将从比较中更多地认识各自民族艺术的精粹,在新的体验与阐述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艺术。
前面,就各自的差异追溯到了老庄和毕达哥拉斯,其实,就最初的著眼点上他们也有某种共同之处。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差不多,也许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有时也会很相近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统摄万物的最高原则是数,认为“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认为“美是和谐与比例”(14) 。首先用数的观点解释音乐节奏和和谐,如发音体的长短、震动速度的快慢就决定了声音的长短与高低,从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音调。此外,不同的数的比例就出现了不同的音程等等。这也就是美学中“寓整齐於变化”理论之滥觞。这里,是用剖析的眼光去对待艺术,去“切割”艺术,於是,“切割”出了听觉上的音调,视觉上的“黄金比”...“寓整齐於变化”,侧重的是“变化”。在老庄学说中,宇宙万物的规律就是“道”,它有著永恒绝对的本体意义。《老子》中解释万物演变就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数”,不过,与毕氏的“数”相比较,前者是一个实数,后者是一个虚数。也许,最根本的同一性与差异性都在这里了。
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树立了一种有机的整体统一的关念,并以此去解释自然和人。不过,我们侧重总体,侧理“合”,於是,突出的数字是“一”。“一”“太一”,“一元”以至后来的“天人合一”...“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淮南子.诠言篇》),“太一生两仪,两仪生阴阳”(《吕氏春秋.大乐》)。这里的一是指从道派生出来的混沌之气,而在混沌之中又有两个相互依存的阴阳对立面。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从而提出“天人感应”说;朱熹也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语类》)。在这里,人和自然都在一个混沌的整体中有规律地运行,“小周天”和“大周天”是统一的,能相互感应的。这里没有上帝、没有戒律,没有主宰一切的神。即使是生万物的道、还得“道法自然”,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这种混沌观,使中国艺术美学中就出现了一连串混沌的,让人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字眼∶“神、气、韵、骨、意、灵、性、情、理、逸、妙、趣、味...”,仅仅一个字,如此简单,然而使用起来又是那样贴切。这是对艺术美的不同理想境界的最精炼的概括,是中国艺术形式上的追求。
人和物也是混沌的。《圣经》的神话中,上帝做了第一个女人的时候就动用解剖手术— — 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而做出了夏娃,这里又实行了“切割”,当然,有很高的科学技术。而中国造人说则是∶“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於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这里也是“捏合”的。
也许更能体现这种辨证统一观念的还是中医。与西医以解剖的方式去认识人不同,中医以气精骨血、阴阳五行等去解释人体的物质存在及其内在运动,以经络去说明人体的有机联系。此外,在观察人的健康时,总是把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把人的精神因素与生理卫生因素联系在一起。《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就谈到∶“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璁、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璁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中医以阴、阳分别解释系统及其功能,脏器的名称实质上是一个系统的象徵。所以,所谓“伤肝在怒,伤心在喜,伤脾在思,伤肺在忧”等等,实际是指这些心理因素对总体生理机能的影响。而这些经验总结,也越来越为现代医学所重视。有意思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有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健康的身体是由於体内寒热湿燥的平衡”(15) 朱光潜在《西方美术史》中谈得更具体∶“他们提出两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看法,一个是‘小宇宙’(人)类似‘大宇宙’的看法(近似中国道家‘小周天’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体就是天体,都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辖著。人有内在的和谐,碰到外在的和谐,‘同声相应’,所以欣然契合。因此,人才能爱美和欣赏艺术。另一个看法是人体的内在和谐可以受到外在的和谐的影响。他们把这个概念用到医学上去,得出类似中国医学里阴阳五行说的结论。不但在身体方面,就是在心理方面,内在和谐也可受到外在和谐的影响...”。不过,他们并没有顺著这条路子走下去。在对大自然探索的长途跋涉中,中西方有时会在一条起跑线上,只是脚步迈开以后就分道扬镳了。西方人十分理智地去分析解剖每一个局部,中国人极富感情地去体悟玩味那混沌的整体。於是,中国人按按脉,看看舌头就能知道什麽病,而且头痛未必治头,脚痛也不一定医脚。针炙口诀有所谓“头项寻后溪”,脚板下的涌泉穴竟与治鼻炎有关,而在耳中能够找到全身的部位...。
推广之於物,就是“目无全牛”、“前身相马”的理论。尤应细说的,还有器物之“无中生有”,《老子》第十一章是一段典型的论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有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有了毂中间的空洞,才有车的作用,有了器皿中间的空虚,才有器皿的作用;有了门窗四壁中间的空隙,才有房屋的作用。有与无是辨证的统一体。而且,正是“无”决定了“有”的作用。於是,就形而下观之,就有了顾恺之的忽略“四体”与重“阿堵”;就有了中国画的主要以线的自身变化和相互给合构成的特色;就有了中国画的勾、皴、点、染的程式;就有了山水树石在皴、点上的不同类型;就有了用墨和整个画面处理上的“计白当黑”。同时,也有了中国戏曲的程式,虚拟...於是,中国人把“画”画视为“写”画,写生、写真、写意、写心、如书写一样一气呵成地写出自己的胸臆;中国人把“演”戏说成“唱”戏,把“看”戏说成“听”戏,听那如歌如诉的唱腔,抒情、咏志。它们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天地,它们主要不是想说明对象是什麽,而是想借对象说明“我”是什麽。於是,中国人信奉那个古老的道理∶“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易.系辞上》。
最后,如果还是要从那个“数”开始去作总结的话,那就是他们是个实数,我们是个虚数;他们是精确数学,我们是糊模数学;他们重物质,我们重精神;他们侧於分析的,我们偏於综合的;他们偏於理智的,我们偏於感情的;他们侧重形而下的,我们侧重形而上的。耐心寻味的是在方法上是恰恰相反的,大概因为他们著眼时太重视对象局部的解剖分析,所以在著手时则非常强调从总体出发。油画是这样,首先要考虑轮廓、色调、块面;话剧是这样,首先要考虑整个舞台节奏和环境气氛。而我们,大概著眼时太重视有机整体的统一了,所以在著手时往往直接从局部开始,中国画是这样,先画好眉眼,再扩展全身。而中国的戏曲,主角在唱,配角站在一旁,无需呼应...中国画的“笔”字,作为工具的意义,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物,它只译作“刷子”,而“画家”则是“油漆匠”的同义词。而作为一种意味,“笔墨”的“笔”字则更难找到一个贴切的意译。油画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中国画是用笔“写”出来的,前者侧重其结果,而后者则兼顾到过程。各自都有其长,有其短。就表现对象的分量感、逼真性而言,西画比国画强的多。如历史画的创作,显然油画更具说服力。然而,若拿他们的天使与我们的飞天相比,那无疑又是后者更具神仙感。西画中那些敦敦实实的人体即便是长著一双翅膀,人们依旧难以相信他们能飞起来...中西交流,相互影响,首先一方面就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是知己知彼以后,反其意行之,扬己之长,避人之短,立足於自身特色之发挥。在当前也许后者更为重要。
世界艺术有许多高峰,中华民族的是一个,西方民族的又是一个。全面把握中西艺术的美学特质,不但便於交流,而且更重要的还在於攀登— — 我们攀登这些高峰的时候,将更为自信;我们观赏这些高峰的时候,将更为清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