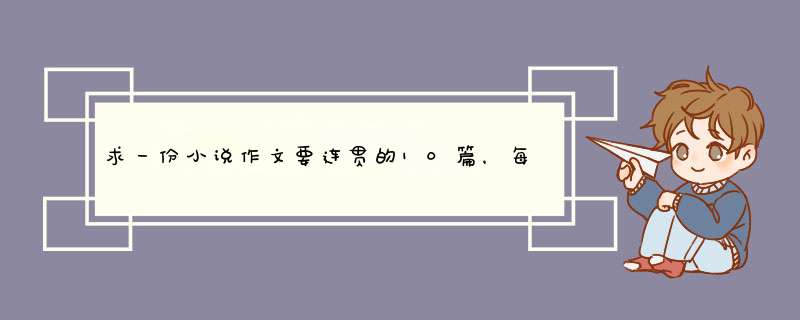
一只狗的命运
巴胥臣
题记:其实,现实中哀号的不止是它自己
周日,晴。
前所未有的好天气,漫长的星辉,交织成一片,只有那冷清的月,孤单单的,无人相伴。低头走在这条远离了闹市的僻静小路上。脚下,支离破碎的斑驳树影无奈地向后退去。在这里,我也许是第一次遇见了你,在这偌大城市的一角。不由自主地扭过头来,找寻那嬉笑声的源头,恍然看到了从黑暗中逃出的你,那一双眼中,又燃起了来两簇火苗,似乎是一种乞求,那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追了上来,石子、砖头落在地上,弹到墙上,发出几声空荡荡的回音。
你仓惶地躲闪着,乞求得到一些庇护,而我只是冷眼旁观,最后,你失望了,悲凄地嚎叫了一声,狼狈地逃了,那孩童们又开始了新的追捕。四周空荡荡地,月孤单单地,怅然若失,再也没了走下去的念头。
周二,微冷。
又冷了些,许多的店铺也都早早打烊了,月亮才露出头,略略地显出一圈圈白。前晚的一幕幕都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希望今晚可别再遇上。
可偏偏前面又传来了那梦寐一般的笑闹声,我连忙转过身,“吱—”身后刺耳的刹车声划落天际,惊醒了沉睡的星宿。赶快扭过头,是你,怎么又是你?惊栗地蜷伏在一辆电动车前,半天,才微睁开眼,讨好地向车主摇摇尾巴,那车主从车上蹦下来,绕着车子走了好几圈,恶狠狠地走向你,你连忙站起来,向他迎去,尾巴在皎洁的月光下摇成了一朵怒放的鲜花。
飞起一脚,来不及躲闪,已被踢到了马路中央,又是一声长长的呜咽。车主忿忿地啐了一口,骑上车子,绝尘而去,又一辆汽车横冲直撞而来,径直碾过,“呜—”一声撕心裂肺的声音使人毛骨涑然,“哈哈哈!”那在行人群中突然爆发出的大笑是那么尖锐、刺耳,惊飞了几只倒栖在树上的蝙蝠,如海水般,没过了那声哀呜。那轮月也越发的无助孤单起来……
周四,雨。
不只为什么,从此不敢在夜间行走,特别是那样的月夜。妈妈购物回来后说,这阵子总有一只狗孤魂野鬼般地四处游荡,跛着一条腿,马路上有了一滩来历不明的血迹,半夜,总会听到声声长嚎,淋浴着月光,如泣如诉。
我一下子想起,那会不会是你……
“莎莎,周六有没有空?”阿洁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一包“幸福海苔”往嘴里塞,整个人慵懒地摊在沙发上,肆无忌惮地往外扔电话费。“什么?莎莎,不会连你也抛弃我吧?!算了,拜拜!”阿洁眼睛里的光芒暗了下来,失望地放下话筒,这个周六贩贩贩怎么办?她在心里说。
阿洁,一个18岁的女孩,从小就爱吃幸福海苔,而且是原味的。她的家庭属于绝对美满的那种,爸爸是某知名公司经理,妈妈开了一家公司,收入颇丰,而阿洁从小就异常聪明,成绩优异,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可阿洁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幸不幸福,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从他们家被旁人无形地定为模范家庭开始,幸福就不再是原味。
阿洁望着眼前一大堆的行李,平时思路清晰的大脑突然变得混乱起来。爸爸妈妈已经有三年没有好好陪过她了,周六也不例外。阿洁翻着日历,眼睛直直地盯着全家福,“他们根本不爱我,周洁,你不要再妄想了!”阿洁大大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晶莹的东西,是泪吗?应该吧。
“叮铃铃!”刺耳的的电话铃声把阿洁从感伤中拉了回来。“喂,阿洁,我是妈妈,周六贩贩贩”“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一个人拎得动。就这样了。再见!”“砰”的一声,阿洁把电话挂了。转身瞬间,阿洁的泪流了下来,她努力想听妈妈讲下去,可是她实在没有勇气!
转眼到了周六。
阿洁左右手各拎一个大包,还拖了一个行李箱。她却不觉得重,反而,心里却很沉重。到了火车站了。这是一个悲剧吧。最出人意料的是,阿洁没有带幸福海苔,她想,幸福,对她来说早已淡了,也许这一辈子她都注定不能受到幸福女神的眷顾。“阿洁!阿洁!”好像很熟悉贩贩贩是爸爸妈妈!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不敢回头看,怕是又空欢喜一场,直到一只宽大和一只细洁的双手勾住了她的脖子,她才哭着叫了一声:“爸爸,妈妈!”她的泪水决堤而出,是感动的泪,更是幸福的泪。“你看,我们给你带来了什么?”“幸福海苔!”“我知道你没它不行,所以给你带来了!”阿洁紧紧捏着原味幸福海苔,大喊了一句:“谢谢!我爱你们!”直到这一刻,她才明白自己的幸福永远都是原味,永远贩贩贩
原味的幸福不是长长久久地欢聚,而是一刹那爱的洋溢。
产品名称:颜红(这个名字可真够土的,不过倒过来就是“红颜”,所以同学“红颜红颜”地叫,以至于考试时她差点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红颜”!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就用“红颜”这个名字写了)
生产日期:6月1日(是双子座兼儿童节。有时红颜在想,再过个几年,别人已经不过儿童节了,而她可以不停地过自己的生日兼儿童节,直到老得头发都白了,说话都说不动了,还能过儿童节,肯定很有意思!)
生产者:颜严、柳红
功能:粉碎老爸老妈的一部分金矿,同时让老爸老妈不停地制造金矿,当然,是为了让红颜过得开开心心,舒舒服服,最重要的一点,她,是他们的女儿。
产品说实话,一开始红颜真的很讨厌自己的名字,颜红颜红,昵称就是小红,这让她想到裹着红头巾,挎着竹篮的乡村妹,俗得很,抑或是那种只会叽叽喳喳的一二年级小姑娘,幼稚得很。直到有一天——其实也就是她进入中学的第一天——一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人,对着她的名字研究了半天,最终,得出一个结论——颜红,红颜也。就打那一刻起,颜红红颜真的对那个姓高名诗诗的女生感激涕零,不仅后来和她成了死党,就连毕业后也形影不离,你说奇不奇!红颜想,也许,这就叫缘分吧。
红颜在班里绝对是少她一个不少,多她一个不多的女孩,考试成绩始终是半瓶水,在认真的边缘徘徊,像大型的考试吗,到考试前夕就恶补,年级也能混个二三十名吧。还好她老爸老妈对成绩这种东西不是很重视,最多只是要求她尽力就行了。每当高诗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对她“哭诉”周六周日,暑假寒假有多少多少补习班时,就轮到红颜拍拍她肩膀,故作深沉地对她说:“唉,听天由命吧!”“唉,你不会了解我的痛的!”看着高诗诗痛苦的样子,红颜很迷茫,也许,只能暗自庆幸自己摊上了一对好爹娘吧。
说起红颜的家,真的好“老”,颜严叫柳红“老婆”,柳红叫颜严“老公”,嘿,这个红颜也不缓和缓和家里的“老气”,索性“一老再老”,配合着叫颜严“老爸”,叫柳红“老妈”。悲哀!虽然这个家“老”了一点,但这不影响红颜对他们的爱,以及老爸老妈对红颜的爱。红颜她老爸是做编剧的,老妈做作家,以红颜的理解,不管是编剧还是作家,反正都是坐在家里赚钱的呗!照道理,老爸老妈都是搞文学的人,生出来的女儿也应该是文邹邹的,可红颜就是木鱼脑袋不开窍,写出来的东西除了让座就是蛋炒饭,除了蛋炒饭就是骑自行车,总之,不堪入目!老爸颜严时常“痛心疾首”地对她说:“唉,红颜啊,在这么浓郁的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下,你怎么还是贩贩贩唉!”老爸说话总是一套一套的,弄得红颜都背出来了,每次听训都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还好老妈不是这样,不然红颜会疯的!
产品禁忌:千万别在本产品面前说“红颜多薄命”之类的话!不然,后果就是贩贩不堪设想!
原本以为,这个世上,只有我自己相信我曾见到过阳光,这样的够了。
巨趴在我的画纸上,懒洋洋地,他说他就喜欢这样,眯缝着眼睛看着从窗口射进来的阳光。他又说,我的画纸上有一种好闻、洁净的味道——一种只属于阳光的味道。
于是,我好奇地问:“巨,你说阳光是什么颜色的?”
巨有意考我:“你猜猜。”
“是金色,金色的,对吧?”我颇为沾沾自喜,谁也不知道,我亲眼见到过这东西。
“阿金,你怎么,怎么知道的”巨的话儿在打颤,这家伙,一兴奋就是这样。正当我准备眉飞色舞大侃一番后,巨却叹了一口气,像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头似的。我一时语塞,又陷入了僵持,巨的叹气不是莫名其妙。
巨是一只明眼的蚂蚁,这样说来有些废话,谁知道蚂蚁会不会瞎眼呢?巨在那些巨所谓的”坏小孩“的手眼夹击下大战了七七四十九回合逃后余生。一开始,他管自己叫英雄,后来又觉得太空泛了。大概是跑到我这儿的第二个早晨,他冲我抱怨:
“上帝真不公平,为什么把蚂蚁塑造得那么小呢?你说啊,阿金,如果你没见过蚂蚁,你会认为那是一种很大的动物吗”
“会比太阳大吗?”
我是很认真地问他。
“哪儿跟哪儿,阿金,你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巨的口气不掩失落。可怜的巨,每每陷入这个苦恼时,却要忍不住幻想一下,可是他却永远不知道太阳有多大。
我想说,巨,你的愿望永远不可能实现,却不忍心巨在我看不见的情况下暗自伤心。“我的愿望是看到阳光。”我相信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半晌,我在心里又补充说,”我一定会看到阳光的。”
空气中飘浮着巨忧愁的苦笑,还有凝滞的,带有同病相怜的目光吧。也许,瞎子的眼睛是瞎了,可是心却是明亮的。
我一直忘我地画着阳光,在那个窗台边。一片嘈杂声惊扰了我的安静,巨说的坏小孩们来了。不过,我不觉得他们是坏小孩,能看到阳光的都是好孩子——阳光是多么美好的事物啊。
马上有人问我:“你在干什么啊?”
我笑笑,刚想拿起画笔,却不知被他们中间的谁拿走了。巨说,那支画笔能画出阳光般的颜色,怪不得我握着它觉得暖暖的呢。
“我在画阳光!”
我嘴角的弧度骄傲地保持着,有人一下子“哈”了出来。接着,一阵冷笑,不知是谁,抓着我的手,在上面放了什么东西。
啊——巨,它一定是被发现了,它费劲地在我手心里翻滚,喉咙里发出难受的咳嗽。是啊,如果他长到比太阳还要大,就不用被欺负了。
“哎,小瞎子,这就是阳光”
戏谑的口气,一个男孩的声音。可怜的巨在我手心里咒骂着他,也许是因为盲孩的缘故吧,我竟能和一只蚂蚁正常沟通。过了一会儿,他们大概是走了。哎,明眼的孩子总是这样,不过,我依然相信他们是美好的孩子,没有坏心眼。
谁知,一切迅疾令我无法想象,包括那如雪纷纷的碎纸。
那天的巨不知为了什么事,像是已经变成了比太阳还要大的生灵。“阿金……这是你画的吗?”巨的话儿又打颤了。
呵——笨笨的巨,当然是我画的喽,谁会教我这小瞎子画阳光啊?
“你画得真像耶”这是巨的感叹吗?我正感觉他跨过我手臂上的绒毛,好像是隔着千山万水,步子磕磕绊绊,前一步还没站稳,后一步就迈出去了。巨在激动我画得好吗?
“这真的是你画的吗?”
巨的声音一次次在我耳边回旋,拉长又截短,我竟被弄得不真实起来,舔了一下发干的嘴唇,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等我思索,那群孩子像是风风火火地进来了。一个孩子立马叫起来:“快看,阳光跑到他的纸上去了。”声音未落,又被另一个声音抵住了:“笨蛋,这不是阳光。”听得出,他就是那个曾嘲弄过我的男生。
男生的脚步威胁着我的神经,无法预料,他几秒钟之后将会有怎样的举动。我下意识地压住我的画纸,嘴唇紧闭,可——天有不测风云,顷刻,那团压在我臂弯下暖暖的东西不见了。是谁?是哪双手把他拿走了?我的呼吸急促起来,且不均匀。
“不好,阿金!”是巨在一旁惊叫。
顿时,“刺啦刺啦”的声音划破了空气,轻轻悠悠地,或许是零碎的小块儿,有几片划破了我原本淡定寂静的脸。
窗外分明有那种叫阳光的东西射进来。巨,你在哪儿?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巨,你告诉我,是我的阳光碎了吗?
那群坏蛋终于走了。巨傍着我冰冷的指尖一言不发。在那时,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撕碎了,化作精巧的蝶,空灵而又凄伤地拍着翅膀。
“阿金——”巨艰难地叫出了声。
我的泪落下来,会打湿那些静静飞落的碎片吧。忽然地,泪水仿佛淡却了在眼前横旦的黑色,我能看到,我的泪融化在阳光里,也有阳光的温度。
“巨,你知道我唯一认识的是什么颜色吗?”
我苦笑着:“是黑色,黑色侵占了我的世界。”
“不是啊,阿金,你不是知道阳光的颜色吗?是金色,难道你忘了?金色是你的名字!”
巨的口气像极力辩解什么。
……
泪竭,梦却醒了。
一个梦,一个梦吗?回答我的只有阳光——真实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还有一张被口水弄湿的画纸。
我冲着阳光微笑,尽管谁都不知道,巨和阿金在另一个世界与它邂逅。
只是,那个只属于阿金的梦,却被揉碎了。
有时候,糖吃起来,未必是甜的!
——题记
家——无奈
她是家中的长女,因为父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没有消退,从而导致她家已是拥有六姐妹的严重性超生家庭,面临着她母亲那带着落后思想而每日增大的肚皮,她的思想里只有——那个是男生。
她家并不贫穷,住着商品房,但因为超生的原因,付出天价般的罚款……她父母卖车又卖房,落迫到要去每月对于他们已是沉重负担的600元仅有40平方的出租房。生活的压力,加剧了她父母对于金钱的需求量,不用的尽量不买,能省的尽量节俭。无疑,她父母的决定,会落在她作为长女的身上……
校——等待
学生会主要干部,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她,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喜爱。她节俭,使她成为了学校的环保大使;她勤奋,使她的名字总能出现在光荣榜前列;她热心,使她的人缘好,与同学相处融洽。她喜欢学校的生活方式,轻松。但她却总是在最放松的时候,想起家中母亲能否独自照顾好她的妹妹,想着立足在社会上的父亲能否安全工作,顺利回家。
常常想起这些,使她脸上常常浮起的,不是学校中的快乐,而是忧心忡忡。同学们看见平时的开心果不再有以前的笑声,老师们看见平时的好问女不再有以前的辫子,便都想问问是什么事困扰着她,而她,家中迫使她不能说出实话,学校里的一切,她的思想控制着她说不想被污染,然而她,选择用苦笑来面对着那些全因出于关心她的老师和同学们的问候,长大就好,她经常说这句话,或许,那是真的吧……
家——逼迫
果真,那些不好的一切,都在同一时间降临在她身上了。
放学后的她,看见父亲额头上的皱纹,像似乎一日之内增加了许多,而母亲那曾经对每日充满憧憬的眼睛,换做了浮肿而又通红。原来,父母亲为了她的学业问题,争吵的许久,可最终的结果,不意外,就是让她退学。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走近她那她最亲爱的母亲前,拥抱的,她母亲眼眶中的眼泪,像泉水般涌出……
校——离开
第二天,同学们照样像往常那样早早起床去到课室进行早读,也像往常那样书声朗朗,只是,课室的一角里的一个座位空了出来而已……过了早读后,同学们也便知道了她退学了,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各种说法也在一时之间传出,生病,出国,移民,休学……唯一就是没有说她是被生活逼的。
一年后的她,回到了学校,那些昔日曾经同窗的伙伴,已经上了初三,她今次回来学校,背后背着一个小孩,是个男孩,而她手上拿着一大袋东西,看见了以前的同学,也便打开了那个被刺眼的阳光照的别样通红的袋子,拿出一个印有喜字包装袋的糖果,放在我们的手上,每个人都有。她说,她妈妈开始工作了,爸爸也当上了馆长,很快她就可以重新上学了,而这颗糖,是因为弟弟满月才派的。我想她等这颗糖,也等了很多年了吧,可糖迟迟不来,导致她的肩上,多了一个不应该是她所承担的负担。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重新上学吗?还是,那只是个寄托在远方的一个愿望……
我打开手,看了看她那颜脸上所忽隐忽现的辛苦,我拆开糖的包装袋,把那颗红色的糖放入口中,为什么,我吃不出甜味……
一块橡皮
一块橡皮,它静静地、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桌上。我刚刚用它的一角擦掉了本子上铅笔描绘的图画。它不再干净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黑色的一角就像它张大的嘴巴,它在向我无声地哭诉。这不禁令我想起了豆——一个曾经是我童年时的伙伴,她也曾这样向我哭泣过。
豆以前就住在我家隔壁,我们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的阳台只隔了一米多远。早上,谁先起来,跑到阳台的窗户前,向对面大喊一声:“懒猪起床啦!”就能看到另一个穿着睡衣揉着眼睛光着脚丫“啪嗒啪嗒”地跑过来含糊不清地嘟嚷上几句,然后上学路上互相交流着夜晚如何与周公相会,再一边吃吃地笑。
我和豆不在同一个班,但我们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淡薄,每天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有时还一起吃饭,无论是亲人还是同学都说我们形影不离像连体姐妹。
豆很爱笑,她笑起来时嘴角边会有两个可爱的酒窝,和她在一起,我也会被她灿烂的笑容所感染,情不自禁地挂上笑脸。
只是我们幼小的心灵却又都是那样敏感脆弱,禁不住风雨的折磨。
那天早晨,我们还有说有笑地一同去上学。傍晚,豆在我家,和我一起写作业,那时我们还用铅笔,橡皮是必不可少的。几天前我刚刚央求妈妈给我买了一块淡**的橡皮,橡皮中间有一部分是镂空的,中间装了一个小铃铛擦作业本上的字时,“叮当叮当”的声响很是引人注目。豆常常拿起我的橡皮赞叹,羡慕:“好好看的橡皮!嗯,又很好玩,我也让我妈帮我买。”
可是这天我打开笔袋准备取出橡皮,谁料翻了好几遍就是看不到那抹**的影子,正巧豆拿起自己的橡皮。我想再找吧,把作业先写完。将豆的橡皮拿在手上,我突然觉得很是熟悉,那也是中间装有铃铛的淡**橡皮,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像我丢失的那块。
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豆偷了我的橡皮!”没错,应该就是她!不喑世事的我一口咬定就是豆拿走了我的橡皮。
“豆,你是不是拿了我的橡皮!”我用生硬的语气问她。她抬起头,眨着大眼睛,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什么?这是我妈妈帮我刚买的呀。”
我的无名火一下子冒了出来:“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写作业,那我的橡皮哪儿去了?”
豆怯怯地说:“我,我真不知道,我只是看你的橡皮好看,才让妈妈买了一块给我,我没有拿你的橡皮,……没有……没有!”豆急了,竟大声地哭了起来。妈妈正在炒菜,闻声跑过来,我指着豆对妈妈不满地说:“豆拿了我的橡皮,她不承认!”妈妈叫来了豆的家长。
豆的妈妈说,那橡皮是她买给豆的。可当时脾气暴躁,心眼又小的我怎容解释?我不依地哭闹起来:“反正就是她拿了我的橡皮,就是她嘛!还我橡皮,快还我橡皮!”
豆被她妈妈带走了,走之前,她回头望了我一眼,嘴巴张了张,似乎想说些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口。豆哭得很厉害,满脸满手的泪水。
好几天过去了,我每次看到豆,依旧是气鼓鼓的样子,有时碰面,我都侧身走开,理都不理豆。
又过了几天,我的气消了些,同学帮我在桌缝里找到了我的橡皮,我才知道自己错怪了豆。
那快橡皮脏脏的,就像那时流着泪委屈的豆,满脸的泪痕。
只是年少的我们又是多么倔强,为了面子,我不愿再向豆道歉。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和以前那样和好如初了。
长大了一些,感到自己是那么不可理喻,然而豆却搬家了,我和她也失去了联系,我再也找不到向她道歉的机会了。
如今,再一次看到这样的一块橡皮,我不禁想起了那个曾经是我的好伙伴的女孩——豆。
懒惰的朝阳还未露出惺忪的睡眼,整个城市处于昏睡之中。惟有城郊的菜场,渐渐苏醒……
老王斜倚床沿,叼着劣质香烟,眉头紧蹙,叹息不止。寂寞的烟雾萦绕周身,仿佛多年的老友般安抚着他。地上掉落的烟蒂,还为熄灭。
“这月底,儿子要带多少钱去?”
“大概500吧。”
“怎么这么多?”
“我也问过他,他还气愤着呢,说老师说除去生活费,还得另外交200,至于是交的什么费老师就不告诉了。”
老王不语,眉头又往里深了一层。这些日子,生意不见起色,一直亏本,管委会来催房租,儿子学校又要交钱,还有自己腰部一直犯病,这可怎么办?
他颤颤巍巍地从抽屉里层摸出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的钱,一遍,二遍,三遍地数着,哎,再数也只能是这么多啊。他摸了摸口袋,里边只有30块钱。
老伴也摸摸荷包,拿出了唯一的一点钱给了老王,总算凑够了。
老王望望窗外,朝阳终于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她温暖的光泽洒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却惟独遗忘了菜场。菜场里永远那么潮湿,那么阴暗。
老王点亮了昏暗的白炽灯,开始一天的忙碌。老伴在一旁打下手。生火,洗菜,放调料……一切具备,只欠顾客。
可是却迟迟不见有人朝自己的摊点瞥一眼。老王越来越绝望。
“老王啊,咱店这墙都破得不成样子了——对了,自来水管也破了,管委会怎么还不来修啊,你到底跟他们说了没啊?”
“我说了,可他们说,要修就得自己掏钱,否则,你就搬出去,我这还有别人会来!”
“他们这些人就会欺负我们穷人!哼,前几天,小李的水管也破了,人家还没开口,那些管委会的就屁颠屁颠地跑去给修好了,还不是因为人家小李后面有个当官的亲戚!”
“嘿,没办法啊,咱们没钱没势。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儿子抚养成人,等儿子考出去后,咱们的重担也算放下了。”
“是啊,你一定得督促儿子好好学习,免得他以后沦落成我们这样。”
嗯。老王点燃一枝香烟,佝偻着坐在板凳上,他望望外面的阳光,内心顿生希望。一切都会好的,老王想。
伊晓云很疲惫地将一大箱书拖上楼,手痛得发胀,她一路安慰着自己,现在总算能解脱了,用不着天天看着父母吵架,用不着天天听到碗筷咣当咣当被暴怒的父亲摔在地上的声音,即使再无助,又怎么样,不是都习惯了吗?
以为我会哭吗?伊晓云甩下周围人们同情的目光,很随意地甩甩刘海,脸上甚至浮上了一丝微笑,伊晓云,她真的很坚强,而且倔强。
这个新家打理得很精致,就好像是一间伊晓云做梦时无数次幻想过的房子。她打扮得很时尚,也很得体,一袭黑色印花的连衣裙,衬得她白晰高挑,
牵着儿子的手站在门口,父亲也笑眯眯地立于一旁,伊晓云讷讷地站着,她像个多余的人。
“晓云,过来,进来呀!”声音软软的。
“晓云,干什么呢?妈妈在叫你呢!”父亲冲着她说,“哼,妈妈,我只有一个妈妈,她是我什么人?”伊晓云愤愤地想。
“晓云!”她又亲切地叫着,跨出门拿过晓云手中的箱子,不由自主地伊晓云跟了进来,在父亲和弟弟间坐下。一下午的时间,连同晚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晚上,她带晓云进了一个漂亮小巧的房间,絮絮叨叨地讲着,只是晓云闷闷的,侧着脸,躺在床上,连一个笑容也不给。
第二天,迷迷糊糊地醒来时,感到浑身滚烫,啊,又发烧了!晓云心里一惊,这才发现她也坐在床沿,更是一脸的惊慌失措,“完了,完了。”晓云的心“咚咚”直跳,不安地转了个身,“妈妈,你别坐在那了,再不走,我上学要迟到了。”她那宝贝儿子大声地喊着,“快走吧!我……呀,上学?!这怎么办呢?”想着,硬撑着,要起床,被她一把按住了,“爸爸上班了,你发烧了。”又听她转头喊道:“乖,今天自己去上学,妈妈要送你姐姐去医院。路上小心些。”
“晓云,妈妈先替你去倒杯水。”又是妈妈,不知不觉,泪水溢满了眼眶,晓云轻轻地拭去了,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哦,这是含泪的微笑,完美的眼泪。
—闯入魔法城堡
我叫丽莎,是四个人中最小的。老三叫丽可,(是朱艺茹)。老二叫丽珊,(是廉开伟)。老大叫丽娜,(是杨淑丹)。
我们四人是姐妹,住在同一个家里,都有音乐天分。称呼一般都喊名字叫人,就叫姐姐或妹妹。
“喂!妹妹们,快一点,晚会就要迟到了!”丽娜说。
“好了我们准备好了”我说。“出发吧!”丽娜说。
“let'sgo!”。
我们登上舞台,我弹起钢琴,丽娜唱起歌,丽珊弹起吉他,丽可敲起鼓。
台下的人又唱又笑。我看在台下这群人中有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女巫,她鬼鬼崇崇,不知在搞什么鬼。我收回心思,弹完曲字。我们一鞠躬,转眼下台。
“姐姐们!嘘,看见那个女巫了吗!”
我指着那个女巫问。
“我看见了,她鬼鬼崇崇地干什么?”丽珊说。
“要不要跟踪她?”丽可说。
“过去看看!”丽娜说
我们悄悄地跟了过去,只见她转身捡了一个东西就跑了,我们紧追不舍,她钻进了一扇门里,我们也跟着进去,里面有一些田鼠,坏鸟,这些都是她变的。
原来,这里就是魔法城堡,她一拍手,整个房间变得金光灿烂。
她真坏她,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动物,还有,魔法城堡的王后变得很好可爱,她变成了一只小白兔,丽可把她装进口袋,没想到我们被女巫发现了,她念着咒语,我们眼前一闪,就进了一个白色的世界。
这里一片洁白,有点凉,我们四人紧紧地挨在一起,手拉手。走啊走,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有出口。突然,从我们面前闪过一双眼睛,“哈哈哈哈,你们逃不掉了!”只听一个鬼叫声。
“完了,快跑!丽娜说。于是,我们跑进一个黑洞洞的地方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