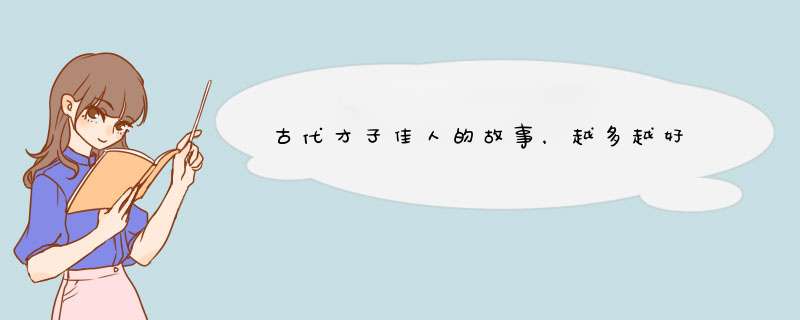
才子与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多见诸中国古代小说,寄托着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爱情乌托邦。上周六的省图东南周末讲坛,来自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王枝忠教授,在古代文学海洋中浸*多年,为大家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才子与佳人,及双方择偶标准的几经变迁。
才子与佳人这两个词,是谁首创的呢? “较早出现佳人形象,是在《诗经·关雎》中的‘窈窕淑女’。词的出现是在汉代李延年歌中‘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而才子概念的出现也是在汉代以后。”
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王教授认为,最早的要算汉代《西京杂记》里“鼎鼎大名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司马相如见卓文君风流漂亮,便‘以琴心挑之’,后就导致文君夜奔。而在此处较强调相如的文采、文君的相貌,即男才女貌。文中如此形容‘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这便成为后来美女的标准”。由此开了先河。
魏晋南北朝的《世说新语》也不忘给才子佳人留下一幅幅缱绻画卷,但王教授指出,“其中比较完整、写得细腻感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是唐代,特别是传奇小说,60%写才子佳人的故事。”
“《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张生见到相国之女惊为天人,但实际上,莺莺**不仅有貌,还有诗才,比如她写‘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熏疑是玉人来’。这代表着唐传奇小说与以往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变化:男女均有才有貌;此外,唐代是诗国,互诉衷曲,靠的是诗来诗往。《霍小玉传》对后代同样影响很深,和《莺莺传》一样是才子佳人定位,以诗传情。但唐代很重门第,小玉名为霍王之女,实是小婢所生,地位卑微,于是门第拆散了他们。还有《飞烟传》,飞烟也是位才女,临死时说:‘生得相亲,死亦何恨!’……总之,唐才子佳人小说对双方才貌强调比较多,用诗歌大量体现,但大多以悲剧收场,对后世戏曲影响很深。”
宋元则为才子佳人小说的过渡时期。 “故事更多样化。男主角多为著名文士,女主角身份多样,比如宋代话本小说《流红记》的‘红叶传诗’,是真实发生的故事,甚至有人指出男主角是中唐著名诗人顾况,而女主角则是一宫女。还有明代白话小说代表《三言二拍》中《苏小妹三难新郎》,不再是早期的私相幽会、两情相悦,而且大多是喜剧结局。”
到了明末清初,则是才子佳人小说的高峰期,甚至影响到了《红楼梦》。虽然明太祖朱元璋重理学,女性在男性社会中被大量丑化,可见《水浒传》《西游记》中。但物极必反,导致一批文人专门写女性是多么美好。
“《好逑传》典型表现了当时才子佳人的三种条件,有才有貌,人品也要好,之前是不问人品的。该小说中的男女主角,共处一室一夜谈诗论文,绝无越礼。男性的择偶标准也比从前苛刻,认为才很重要,说:‘前者(相貌)易得,后者(才华)难求,若无后者,宁可不娶。’”
而清代小说绕不过的是《聊斋志异》,这其中除了佳人多为鬼狐花妖,又有了新的变化。“才子有不少是先读书,后经商,为儒商,性关系也比较开放,但也有终身只做红颜知己,如《娇娜》。”同时,清代还有个很大的变化,佳人不再局限于良家女子,而是风尘女子。如福州魏秀仁著的《花月痕》写“秦淮八艳”的,“这些才妓都工诗善画,文人认为只有风尘女子中才有红颜知己,因此对她们极尽褒扬。即‘青楼原有掌书仙,未可全归露水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大胆借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来重新解读唐代爱情传奇,探讨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女性意识问题,使唐代爱情传奇的研究有了新突破,但他们也得出了一些有失偏颇的结论。
有论者认为研究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唐代女权的伸张和强化的历史内涵;还有论者认为研究唐代爱情传奇中女性形象的升华不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开始动摇,还可以倾听到唐代男性带动女性走向解放的步伐。这些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历史前提:唐朝仍然是一个男性中心文化占中心地位、封建正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被广泛认同的社会。还有一些论者从分析唐代爱情传奇中所透露出的男性叙事视角入手,发现其背后强大的男性文化和封建正统的价值观念。这样的论述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抹煞了唐代爱情传奇中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对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和封建正统价值观念的反叛和冲击的历史意义,所以这样的论述也是有失公允的。
因此,笔者想在整合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一点粗浅思考,对以上的种种偏颇做一番纠正,从而对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再认识,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女性意识。笔者认为:唐代爱情传奇中确实存在着女性意识初步觉醒的表现,但这是以不动摇当时的男性中心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封建正统观念的主导地位为前提的,这样的看法也许更符合历史的实际。
下面笔者分别从唐传奇故事情节的设置和故事构成模式两个大的方面来谈谈对唐代爱情传奇中女性意识的再认识。
一、从故事情节的设置来看
首先,在唐代爱情传奇的故事情节设置中,有些女性形象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代替男性话语的符号。它随时可以满足男人的性欲,顺从男人的要求,迁就男人的错误,表达男人的思想,几乎没有个人的主体话语和心理特点。它所想的说的做的全是男人的想法和需求,缺乏对于男性的独立个体话语。这本身也是女性依附于男性的表现。任氏为报答韦生的恩情主动要求为他勾引美女。崔莺莺面对被弃的命运,不仅不谴责张生,反而还写信给他,表达相思之苦。霍小玉尽管知道李益对自己的爱靠不住,仍然“深明大义”地劝他去考取功名。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情节是因为他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来设置情节,过分强调男性心理感受,使那些女性形象受到心理的压抑。
其次,有些作者不懂得爱情是两情相悦的事情,是男女双方的行为,常常只顾男性的情感体验而忽视了女性的感情需要和心理活动。使女性只保留了一张美丽的外皮,缺乏真正的人的神采。《长恨歌传》本来写李杨的爱情生活,但大量的笔墨却用来描绘唐玄宗的感情,对杨贵妃的描写只寥寥数语,涉及其感情体验的则更少,使平等的爱情生活成为男人的情感渲泄,缺乏对等的女性情感回应。
再次,唐代爱情传奇里的故事缺乏对女性公平的道德评判。作品大量描写幽会私奔、调笑戏谑的男女之欲,以及钻穴相窥、逾墙相奔的媾合过程,其实质是对女性情感的猥亵。《任氏传》、《莺莺传》、《飞烟传》都有这方面的描写。在崇尚明媒正娶风气的封建社会,这些情节描写明显带有歧视女性追求爱情的倾向。
最后,作者幻设出的美女为妖、为鬼、为怪的故事,也是对“红颜祸水”的暗示,进一步为男人的负心行为做开脱,为男人的偷情取乐放宽尺度,加剧了“占有美女不用负责”的道德沦落。《李章武传》、《焦封》、《孙恪》都写男人偶遇美女,先同居后弃之的故事,尤其是《李章武传》还写被弃之妇追踪情人不止,死后化为魂魄相陪,并赠美玉之事。不仅没有谴责李的负心薄情,反而还有大加赏识之意。这些都可以看出唐代爱情传奇的作者们的男性中心主义价值观念。
二、从故事构成模式来看
唐代爱情传奇大多是“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模式。这一模式也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
从《莺莺传》、《李娃传》到《霍小玉传》,尽管其中有着始乱终弃、终成眷属等不同的结局,但青年男女一见钟情,男为“色”倾倒,女为“才”仰慕,却是始终不变的。《柳氏传》中说:“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两情皆获,喜可知也。”[1]《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对霍小玉说得更直接:“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相好映,才貌相兼。”[2]才貌是青年男女互相吸引和爱慕的关键,这是沿袭了几千年直至今日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心理。这种表面的“相映”和“相兼”,潜存着一种极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它直接将女性的外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而男子的才气,既是婚姻的砝码,又是女性终生依附所系――凭着才气,男人的风流倜傥、高官厚禄以及各种保证爱情与婚姻幸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会源源而来。在封建文化结构中,女人无主体性可言,幼年时代是父亲的女儿,一迈入豆蔻年华,便得寻觅夫家,出嫁之后,她们便只具有别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从姓氏到整个身心都系于丈夫的掌心中。她们的一生是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下的各种名份之中――为女、为妻、为母。除此而外,她们没有其它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封建社会衡量人,尤其是男人的价值标准是取决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出身门第的高低往往直接影响着人的荣辱、尊卑和贵贱,因此,作为人生的重要抉择――“合两姓之好”、“事宗庙”、“继后世”的婚姻,自然要讲门当户对了。李益起初钟情于霍小玉的花容月貌,但最终还是迫于母命,或者说是为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实际权衡而放弃了与小玉的爱情。他与门当户对的出身望族的卢氏结为“秦晋之好”,这样做更有利于自己仕途的畅达。
上述“才子佳人”的故事构成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千古不变的男性主义观念:男人必须强大,他是女人依赖和获取希望的源泉。从唐代爱情传奇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构成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对男性的物质和精神依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唐代爱情传奇中确实有着女性意识初步觉醒的表现,但其背后又有着强大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和封建正统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的文人士子对男性中心文化和封建正统观念既有所突破又有所遵循的困惑。
注释:
[1]叶桂刚、王贵元主编:《中国古代十大传奇赏析》,第427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叶桂刚、王贵元主编:《中国古代十大传奇赏析》,第50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参考文献:
1、赵明政:《文言小说:文士的释怀与写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陈周昌选注:《唐人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5、廖雯:《女性艺术――女性作为方式》,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6、刘慧英:《走出男权的樊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批判》,三联书店,1996年版。
7、史仲文:《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程毅中:《唐人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9、汪辟疆:《唐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0、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三联书店,1997年版。
王明家,湖北大学文学院2004级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研究生;沈秋菊,湖北孝感孝南二中教师。
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有美人名虞”,但是并没有以后世流传的“虞姬”其名称呼;直到唐《括地志》等书才出现“虞姬”其名。当然,“姬”只是代称,并非虞姬的本名。虞姬其人有姓无名,名早已漶灭在历史断裂的黑洞里了,五代时期的词牌名则乾脆以“虞美人”呼之。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中《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著,至南宋时亡佚。毫无疑问,司马迁著《史记》时参考过《楚汉春秋》一书:“盖司马迁撰《史记》据《楚汉春秋》,故其言秦、汉事尤详。”(王利器)
可是,《楚汉春秋》中记载的“美人和之”的和歌,注重细节兼好奇的司马迁却没有录入《史记》。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引录了这首和歌:
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一直以来,就有人怀疑这首和歌是后世的伪作,理由是秦汉没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但是,《汉书·外戚传》记录的戚夫人哀歌却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郦道元《水经注·河水》记录的秦时民谣也已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因此,《楚汉春秋》所录的这首和歌并非伪作,应无问题。
《楚汉春秋》和《史记·项羽本纪》是“霸王别姬”故事的最早记载。二书都没有涉及虞姬的结局。以常情度之,虞姬不可能活下来,否则就不会有民间口耳相传的虞姬自刎情事,就不会至唐时尚有“项羽美人冢”的地望方位。垓下一战,四面楚歌声中,饮剑楚帐只能是虞姬惟一的结局。
通说以为:“霸王别姬”故事,反映的是虞姬和项羽感天动地的爱情;楚霸王英雄末路,虞姬自刎殉情。这悲情一瞬,已定格在中国文学的字里行间,定格在中国戏曲的舞台上,成为中国古典爱情中最经典,最荡气回肠的灿烂传奇。
对历史事件的追根溯源,揭破真相,只能依赖于对原始文本的读解。仔细玩味虞姬的和歌,我从中发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疑点。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头两句是客观纪实,同时也是虞姬即将抒发感慨的情境铺排。虞姬对形势的判断和项羽的疑惑是一致的——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虞姬对形势的判断居然直接导致了对项羽精神状态直至未来命运的否定!大王您继续战斗的意气已经到头了,我也不愿苟活了。虞姬凭什么判断出“大王意气尽”了?仅仅凭项羽闻楚歌而“夜起,饮帐中”吗?如果这是激将之辞,以自己不愿苟活激励项羽继续战斗,那么项羽和诸将的反应就不应该是“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而应该是怒发冲冠,决一死战。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话语的煽动力和传染性,虞姬精心设计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这一情境铺排所产生的奇妙效果——它真的让项羽和诸将失去了决战的意气!
虞姬的态度是非常奇怪的。作为项羽最宠爱的女人,当项羽遭逢末路,但尚未完全失败的时刻,她应该挺身而出,激励项羽,而不是附和项羽“时不利”的藉口,诱惑项羽在恶劣的形势面前低头。毕竟项羽才三十余岁。她深知项羽一生百战,出生入死,也曾有过“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从而击败秦军,起死回生的经典战例,也曾有过以三万人杀汉卒十余万人,逼迫刘邦数十骑逃跑的经典战例;可是此时,虞姬非但不用以前的类似处境鼓励项羽,恰恰相反,反而哀叹“大王意气尽”!此刻项羽身边尚有八百余骑,俱是精兵良将,无不以一当十,即使打不过刘邦,起码可以保护项羽全身而退,以图东山再起。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项羽突围而出,到了乌江边,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可见项羽不是没有渡江生息的机会,只是项羽固执地认为“天之亡我”,不愿渡河,“乃自刎而死”。虞姬为什么不等所有的机会都用尽,再无生路时殉情,就这麽匆匆忙忙就判了项羽的死刑呢?
虞姬这首被人赞誉为“坚贞爱情结晶”以及我国最早的五言诗(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的和歌,就这样散发出了可疑的气息。我甚至怀疑她是刘邦效法西施而派往项羽身边的美女间谍。以刘邦的智力和行事风格,以项羽的“妇人之心”和不听劝谏刚愎自用的性格,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史籍漫漶,不仅刘邦、项羽、虞姬的籍贯之间找不出丝毫的蛛丝马迹,就连虞姬最早追随项羽的时间也无可考了。
在大多数国家,王室为了继承,往往会由上一届的国王去决定王子未来的王后是谁,用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说是父母包办婚姻,大多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我觉得那样并不幸福,两个人相爱在一起才能够幸福,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不丹国王和王后的甜蜜爱情故事。故事还要追溯到18年前,当时的旺楚克还只是王子,不过这个王子却非常低调,谦虚,从来不把自己身份抬得有多么尊贵,就在一次家庭野餐聚会中,他碰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佩玛,在当时佩玛对旺楚克一见钟情,当时的佩玛只有有七岁就和旺楚克表白了,旺楚克被佩马的认真所感动了,就与佩玛约定,如果在长大以后,男方未娶,女方未嫁,并且还都惦念对方,那么两个人就在一起。就是这样,童话般的故事,也就是这样,命运的安排,但是旺楚克和佩玛身份是悬殊的,旺楚克是高高在上的王子,而佩玛只是一介平民,所以在佩玛的心中总是充满着不安,很怕在旺楚克当上国王之后,就会娶了别人,旺楚克为了不让佩玛担心,就提前将她接到王室同居。也是旺楚克的婚姻,打破了以往以来政治的联姻,而佩玛也并不是无才能的人,她是美貌与才华兼备的王后,非常能受到不丹民众的追捧,两个人可以说是佳偶天成,就连他们的婚礼也是低调的,参加婚宴的并不是什么王室贵族,而是居住在附近村庄的村民,这样的国王与王后怎能让人不喜欢?就是这样童话般的故事邂逅在了两个被上天眷顾的才子佳人身上,他们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浪漫结晶。
读完了这篇故事,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甜蜜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