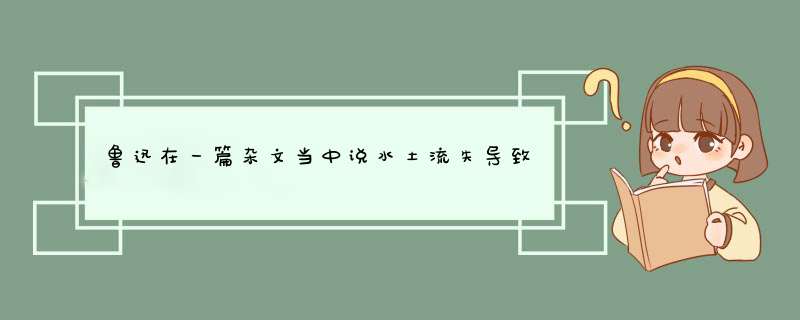
鲁迅 理水
这时候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舜爷〔2〕〔3〕的百姓,倒并不都挤在露出水面的山顶上,有的捆在树顶,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还搭有小小的板棚,从岸上看起来,很富于诗趣。
远地里的消息,是从木排上传过来的。大家终于知道鲧大人因为治了九整年的水,什么效验也没有,上头龙心震怒,把他充军到羽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儿子文命少爷,〔4〕乳名叫作阿禹。〔5〕灾荒得久了,大学早已解散,连幼稚园也没有地方开,所以百姓们都有些混混沌沌。只在文化山上〔6〕,还聚集着许多学者,他们的食粮,是都从奇肱国〔7〕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够研究学问。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
界上真有这个禹。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8〕
“古鲁几哩……”
“O.K!”〔10〕
飞车向奇肱国疾飞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声,学者们也静悄悄,这是大家在吃饭。独有山周围的水波,撞着石头,不住的澎湃的在发响。午觉醒来,精神百倍,于是学说也就压倒了涛声了。
“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鲧的儿子的话,”一个拿拄杖的学者说。“我曾经 搜集了许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很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个结论:阔人的子孙 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 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
“O.K!”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说。
“不过您要想想咱们的太上皇〔11〕,”别一个不拿拄杖的学者道。
“他先前虽然有些‘顽’,现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远不会改好……”
“O.K!”
“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 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 ‘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不过鲧却的确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还亲眼看见他到昆仑山脚下去赏梅花的。”
“那么,他的名字弄错了,他大概不叫‘鲧’,他的名字应该叫‘人’!至于禹,那可 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
于是他勇猛的站了起来,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树皮,用吃剩的面包末屑和水研成 浆,调了炭粉,在树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写上抹杀阿禹的考据,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 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叶,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给一贝壳鲜水苔。
横竖到处都是水,猎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种,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是闲工夫,来看的人 倒也很不少。松树下挨挤了三天,到处都发出叹息的声音,有的是佩服,有的是皮劳。但到 第四天的正午,一个乡下人终于说话了,这时那学者正在吃炒面。
“人里面,是有叫作阿禹的,”乡下人说。“况且‘禹’也不是虫,这是我们乡下人的 简笔字,老爷们都写作‘禺’,〔12〕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吗?……”学者跳起来了,连忙咽下没有嚼烂的一口面,鼻子红 到发紫,吆喝道。
“有的呀,连叫阿狗阿猫的也有。”
“鸟头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辩论了,”拿拄杖的学者放下面包,拦在中间,说。“乡下 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谱来,”他又转向乡下人,大声道,“我一定会发见你的上代都是愚 人……”
“我就从来没有过家谱……”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们这些东西可恶!”
“不过这这也用不着家谱,我的学说是不会错的。”鸟头先生更加愤愤的说。“先前, 许多学者都写信来赞成我的学说,那些信我都带在这里……”
“不不,那可应该查家谱……”
“但是我竟没有家谱,”那“愚人”说。“现在又是这么的人荒马乱,交通不方便,要 等您的朋友们来信赞成,当作证据,真也比螺蛳壳里做道场还难。证据就在眼前:您叫鸟头 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鸟儿的头,并不是人吗?”
“哼!”鸟头先生气忿到连耳轮都发紫了。“你竟这样的侮辱我!说我不是人!我要和 你到皋陶〔13〕大人那里去法律解决!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 你懂了没有?要不然,你是应该反坐的。你等着罢,不要动,等我吃完了炒面。”
“先生,”乡下人麻木而平静的回答道,“您是学者,总该知道现在已是午后,别人也 要肚子饿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真是对不起得很,我要捞青 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后,我再来投案罢。”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网兜,捞着水草,泛 泛的远开去了。看客也渐渐的走散,鸟头先生就红着耳轮和鼻尖从新吃炒面,拿拄杖的学者 在摇头。
然而“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呢,却仍然是一个大疑问。
二
禹也真好像是一条虫。
大半年过去了,奇肱国的飞车已经来过八回,读过松树身上的文字的木排居民,十个里 面有九个生了脚气病,治水的新官却还没有消息。直到第十回飞车来过之后,这才传来了新 闻,说禹是确有这么一个人的,正是鲧的儿子,也确是简放〔14〕了水利大臣,三年之 前,已从冀州启节〔15〕,不久就要到这里了。
大家略有一点兴奋,但又很淡漠,不大相信,因为这一类不甚可靠的传闻,是谁都听得 耳朵起茧了的。
然而这一回却又像消息很可靠,十多天之后,几乎谁都说大臣的确要到了,因为有人出 去捞浮草,亲眼看见过官船;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了回避得太慢一点了, 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这就是大臣确已到来的证据。这人从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 争先恐后的来看他头上的疙瘩,几乎把木排踏沉;后来还经学者们召了他去,细心研究,决 定了他的疙瘩确是真疙瘩,于是使鸟头先生也不能再执成见,只好把考据学让给别人,自己
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每只船上,有二十名 官兵打桨,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后都是旗帜;刚靠山顶,绅士们和学者们已在岸上列队恭 迎,过了大半天,这才从最大的船里,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 武士簇拥着,和迎接的人们一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
大家在水陆两面,探头探脑的悉心打听,才明白原来那两位只是考察的专员,却并非禹 自己。
大员坐在石屋的中央,吃过面包,就开始考察。
“灾情倒并不算重,粮食也还可敷衍,”一位学者们的代表,苗民言语学专家说。“面 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虽然未免有些泥土气,可是很肥,大人。至于那 些下民,他们有的是榆叶和海苔,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并不劳心,原只 要吃这些就够。我们也尝过了,味道倒并不坏,特别得很……”
“况且,”别一位研究《神农本草》的学者抢着说,“榆〔16〕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 W〔17〕的;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两样都极合于卫生。”
“O.K!”又一个学者说。大员们瞪了他一眼。
“饮料呢,”那《神农本草》学者接下去道,“他们要多少有多少,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敝人指导过许多次了,然而他们冥顽不灵, 绝对的不肯照办,于是弄出数不清的病人来……”
“就是洪水,也还不是他们弄出来的吗?”一位五绺长须,身穿酱色长袍的绅士又抢着 说。“水还没来的时候,他们懒着不肯填,洪水来了的时候,他们又懒着不肯戽……”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 有蚩尤氏之雾……哈哈哈!没有法子……”〔14〕
“O.K!”
这样的谈了小半天。大员们都十分用心的听着,临末是叫他们合拟一个公呈,最好还有 一种条陈,沥述着善后的方法。
于是大员们下船去了。第二天,说是因为路上劳顿,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三天是学者 们公请在最高峰上赏偃盖古松,下半天又同往山背后钓黄鳝,一直玩到黄昏。第四天,说是 因为考察劳顿了,不办公,也不见客;第五天的午后,就传见下民的代表。
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开始推举的,然而谁也不肯去,说是一向没有见过官。于 是大多数就推定了头有疙瘩的那一个,以为他曾有见过官的经验。已经平复下去的疙瘩,这 时忽然针刺似的痛起来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宁死!大家把他围起来,连日连 夜的责以大义,说他不顾公移益是利己的个人主义者,将为华夏所不容;激烈点的,还至于 捏起拳头,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负这回的水灾的责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与其逼死在 木排上,还不如冒险去做公益的牺牲,便下了绝大的决心,到第四天,答应了。
大家就都称赞他,但几个勇士,却又有些妒忌。
就是这第五天的早晨,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来,站在岸上听呼唤。果然,大员们呼唤 了。他两腿立刻发抖,然而又立刻下了绝大的决心,决心之后,就又打了两个大呵欠,肿着 眼眶,自己觉得好像脚不点地,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了。
奇怪得很,持矛的官兵,虎皮的武士,都没有打骂他,一直放进了中舱。舱里铺着熊 皮,豹皮,还挂着几副弩箭,摆着许多瓶罐,弄得他眼花缭乱。定神一看,才看见在上面, 就是自己的对面,坐着两位胖大的官员。什么相貌,他不敢看清楚。
“你是百姓的代表吗?”大员中的一个问道。
“他们叫我上来的。”他眼睛看着铺在舱底上的豹皮的艾叶一般的花纹,回答说。
“你们怎么样?”
“……”他不懂意思,没有答。
“你们过得还好么?”
“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他又想了一想,低低的说道,“敷敷衍衍……混混……”
“吃的呢?”
“有,叶子呀,水苔呀……”
“都还吃得来吗?”
“吃得来的。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只有些小畜生还要嚷,人心在坏下去 哩,妈的,我们就揍他。”
大人们笑起来了,有一个对别一个说道:“这家伙倒老实。”
这家伙一听到称赞,非常高兴,胆子也大了,滔滔的讲述道:
“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剥树皮不可剥光,要留下一道,那么,明年春天树枝梢还是长叶子,有收成。如果托大人的福,钓到 了黄鳝……”
然而大人好像不大爱听了,有一位也接连打了两个大呵欠,打断他的讲演道:“你们还 是合具一个公呈来罢,最好是还带一个贡献善后方法的条陈。”
“我们可是谁也不会写……”他惴惴的说。
“你们不识字吗?这真叫作不求上进!没有法子,把你们吃的东西拣一份来就是!”
他又恐惧又高兴的退了出来,摸一摸疙瘩疤,立刻把大人的吩咐传给岸上,树上和排上 的居民,并且大声叮嘱道:“这是送到上头去的呵!要做得干净,细致,体面呀!……”
所有居民就同时忙碌起来,洗叶子,切树皮,捞青苔,乱作一团。他自己是锯木版,来 做进呈的盒子。有两片磨得特别光,连夜跑到山顶上请学者去写字,一片是做盒子盖的,求 写“寿山福海”,一片是给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额,以志荣幸的,求写“老实堂”。但学者却 只肯写了“寿山福海”的一块。
三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 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份子分福禄寿三种,最少 也得出五十枚大贝壳〔19〕。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 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20〕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21〕的鼻子跟 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 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
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22〕,有的是仓颉鬼哭体〔23〕,大家 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 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评定了中国特有的之后,文化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于是来考察盒子的内容了:大家
一致称赞着饼样的精巧。然而大约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议论纷纷:有的咬一口松皮饼,极口
叹赏它的清香,说自己明天就要挂冠归隐〔24〕,去享这样的清福;咬了柏叶糕的,却道
质粗味苦,伤了他的舌头,要这样与下民共患难,可见为君难,为臣亦不易。有几个又扑上
去,想抢下他们咬过的糕饼来,说不久就要开展览会募捐,这些都得去陈列,咬得太多是很
不雅观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奇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
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只拦住了气喘吁
吁的从后面追来的一个身穿深蓝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妇女。
“怎么?你们不认识我了吗?”她用拳头揩着额上的汗,诧异的问。
“禹太太,我们怎会不认识您家呢?”
“那么,为什么不放我进去的?”
“禹太太,这个年头儿,不大好,从今年起,要端风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别了。现在那
一个衙门里也不放娘儿们进去,不但这里,不但您。这是上头的命令,怪不着我们的。”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
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25〕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2
6〕!这没良心的杀千刀!……”
这时候,局里的大厅上也早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
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
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
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27〕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
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
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
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
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禀大人,他们都是以善于吃苦,
驰名世界的人们。”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
另请女隗〔28〕**来做时装表演。只卖票,并且声明会里不再募捐,那么,来看的可以
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
“一面派人去通知奇肱国,使他们知道我们的尊崇文化,接济也只要每月送到这边来就好。
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说的倒也很有意思,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
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
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玩想的那么精微的。知人论事,第一要凭主
观。例如莎士比亚〔29〕……”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
‘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30〕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
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
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
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31〕,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
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
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32〕,”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
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
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
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3
3〕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3
4〕,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
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
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
铸的一样。
四
禹爷走后,时光也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京师的景况日见其繁盛了。首先是阔人们有
些穿了茧绸袍,后来就看见大水果铺里卖着橘子和柚子,大绸缎店里挂着华丝葛;富翁的筵
席上有了好酱油,清炖鱼翅,凉拌海参;再后来他们竟有熊皮褥子狐皮褂,那太太也戴上赤
金耳环银手镯了。
只要站在大门口,也总有什么新鲜的物事看:今天来一车竹箭,明天来一批松板,有时
抬过了做假山的怪石,有时提过了做鱼生的鲜鱼;有时是一大群一尺二寸长的大乌龟,都缩
了头装着竹笼,载在车子上,拉向皇城那面去。
“妈妈,你瞧呀,好大的乌龟!”孩子们一看见,就嚷起来,跑上去,围住了车子。
“小鬼,快滚开!这是万岁爷的宝贝,当心杀头!”
然而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
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
〔35〕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皇上舜爷
的事情,可是谁也不再提起了,至〔36〕多,也不过谈谈丹朱太子〔37〕的没出息。
禹要回京的消息,原已传布得很久了,每天总有一群人站在关口,看可有他的仪仗的到
来。并没有。然而消息却愈传愈紧,也好像愈真。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
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似员。临末是一
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舜爷所赐
的“玄圭”,连声说道“借光,借光,让一让,让一〔38〕让”,从人丛中挤进皇宫里去
了。
百姓们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正好像浙水的涛声〔39〕一样。
舜爷坐在龙位上,原已有了年纪,不免觉得疲劳,这时又似乎有些惊骇。禹一到,就连
忙客气的站起来,行过礼,皋陶先去应酬了几句,舜才说道:
“你也讲几句好话我听呀。”
“哼,我有什么说呢?”禹简截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孳孳!”
“什么叫作‘孳孳’?’皋陶问。
“洪水滔天,”禹说,“浩浩怀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里。我走旱路坐车,走水路坐
船,走泥路坐橇,走山路坐轿。到一座山,砍一通树,和益俩给大家有饭吃,有肉吃。放田
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
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
“对啦对啦,这些话可真好!”皋陶称赞道。
“唉!”禹说。“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
舜爷叹一口气,就托他管理国家大事,有意见当面讲,不要背后说坏话。看见禹都答应
了,又叹一口气,道:“莫像丹朱的不听话,只喜欢游荡,旱地上要撑船,在家里又捣乱,
弄得过不了日子,这我可真看的不顺眼!”
“我讨过老婆,四天就走,”禹回答说。“生了阿启,也不当他儿子看。所以能够治了
水,分作五圈,简直有五千里,计十二州,直到海边,立了五个头领,都很好。只是有苗可
不行,你得留心点!”
“我的天下,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劳弄好的!”舜爷也称赞道。
于是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退朝之后,他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
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
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
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
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
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40〕
流传于柳州武宣壮族居住区。道具用竹蔑制成鸟形,外糊绿绸缝以绿绒线作羽毛。当地人喜爱翡翠鸟毛色碧绿,啼声清脆,性情温和,视其为吉祥的象征。春节期间,一男子扮裴翠鸟,另一人扮老者,率鸟沿问到各家拜年演出祝福。表演时舞者进道具内,两手分执或勾住鸟头、眼、嘴、翅膀操纵杆,鸟头转动,眼张合,嘴作响,表现飞翔、觅食、饮水、洗澡、磕睡等亲切、动人的动态。舞毕从道具上拔一根“羽毛”送主人,祝愿主家人丁兴旺。主人酬以酒肉、红包。表演的技法与傣族孔雀舞近似,各类鸟形道具的舞蹈融入了壮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
《理水》是鲁迅改编的中国传统神话大禹治水的故事,却隐晦深刻地联系现实,塑造了大禹以及其他协同治水的实干家,文化山的只有空论的学者,昏庸的官员等鲜明的有指向性的形象。
第一段,写治水前的情况。先写舜爷的百姓遭到了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百姓们淹在水中,过着苦难的生活。,舜决定把治了九年水不见效的鲧充军,让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这些都与神话故事中的情节一致,但和写作时间结合来看又另有所指,一种看法是,本文写作时间1935年,鲁迅写《理水》前两年的1933年,黄河决口达五十多处,淹没了冀、鲁、豫等省六十多个县,受灾人口达三百多万。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死活,以“视察”,“贩济”为名,从中渔利,更加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曾揭露过这种“大水,饥荒”的现实。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宣扬尊孔,演奏“韶乐”,祸国殃民的罪行。当时,江南一带十四个省大旱,江、浙、皖三省受灾面积达几千万亩,仅安徽一省灾民就有几百万,浙江余姚还发生农民争水互殴致死的悲惨事件。鲁迅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残害人民的种种惨状,感到极大的愤慨,对灾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示无限的同情。《理水》中舜爷的百姓在“洪水滔天”中挣扎的惨状,实际上正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缩影。
而后面的内容更包含了鲁迅对现实的讽刺。“文化山”上的学者讨论暗指一九三二年十月北平文教界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等三十余人向国民党政府建议明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我国东北,华北也正在危殆中;
国民党政府实行投降卖国政策,抛弃东北之后,又准备从华北撤退,已开始准备把可以卖钱的古文物从北平搬到南京。江瀚等想阻止古文物南移,可是他们竟以当时北平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有重要性为理由,提出请国民党政府从北平撤除军备,把它划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区域的极为荒谬的主张。他们在意见书中说,北平有很多珍贵文物,它们都“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又说:“因为北平有种种文化设备,所以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一旦把北平所有种种文化设备都挪开,这些学者们当然不免要随着星散。”要求“政府明定北平为文化城,将一切军事设备,挪往保定。”(见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北平《世界日报》)这实际上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同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理论”如出一辙。当时国民党政府虽未公开定北平为“文化城”,但后来终于拱手把它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古文物的大部分则在一九三三年初分批运往南京。作者在“九一八”后至他逝世之间,曾写过不少杂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主义,对所谓“文化城”的主张也在当时的一篇杂文里讽刺过(参看《伪自由书·崇实》)。本篇在“文化山”的插曲中所讽刺的就是江瀚等的呈文中所反映的那种荒谬言论,原文中有的宣扬反动的“遗传学”,说什么“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并据此推断,鲧治不好洪水,禹当然也治不好。也有一个唯心主义的“考据学家”,则根本否定禹的存在,以至考据出“`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的荒谬结论。此时,他们声嘶力竭地否认华夏有治水的人才,这和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崇洋媚外,毫无民族自信的鼓吹何其相同。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指出:这批吃的是飞肱国运来的面包的学者,又是腐朽官场的宠物,他们乃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特产。正
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毫无民族尊严、民族自信,才会这样断然否定在中国可以崛起民族自救自新的力量。这些人在特大洪灾面前无动于衷,不关痛痒,言谈举止十分荒唐。更有甚者,他们乘机大肆咒骂劳动人民都是“愚人”,宣扬“上智下愚”谬论。其中几个所谓学者,是以当时文化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模型的。例如“一个拿拄杖的学者”,是暗指“优生学家”潘光旦。潘曾根据一些官僚地主家族的家谱来解释遗传,著有《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书;
他的这种“学说”和欧美国家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种的“学说”是同一类东西。又如鸟头先生,是暗指考据学家顾颉刚,他曾据《说文解字》对“鲧”字和“禹”字的解释,说鲧是鱼,禹是蜥蜴之类的虫(见《古史辨》第一册六三、一一九页)。“鸟头”这名字即从“顾”字而来;
据《说文解字》,顾字从页雇声,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顾颉刚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歌谣研究会工作,搜集苏州歌谣,出版过一册《吴歌甲集》,所以下文说鸟头先生“另去搜集民间的曲子了”。
乡下人对禹的解释是禺的简体字,有根有据的反驳了学者。“禺”《说文解字》:“禺,母猴属。”清代段玉裁注引郭璞《山海经》注说:“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据《说文》,“禹”字笔画较“禺”字简单,所以这里说“禹”是“禺”的简笔字。
在这一段里,小说对“文化山”上的“学者”的面目,作了维妙维肖的刻画,同时,用“乡下人”踏实、机智、勤劳的形象进行生动对比,更显出这些“学者”的丑恶嘴脸。实际上,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文人以及“正人君子”、“洋绅士”、“土绅士”们的有力揭露和抨击。
第二段,写治水活动的开始。先写舜爷派来“胖胖的大员”和“穿虎皮的武士”,威风凛凛地到达了灾区。他们吃的好住得好,只能听到学者们的不实之言,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听也听不懂,如“面包是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鱼也不缺,……很肥”,“那些下民……有的是榆叶和海苔,……味道倒并不坏”,“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的,海苔里有碘质,两样都极合于卫生”,还有什么“饮料呢····一万代也喝不完。可惜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的。”接着描写了“大员”们“传见下民的代表”的可笑情状。这班大员可以“不办公,也不见客”,但却兴致勃勃地“在最高峰上赏古松,山后面钓黄鳍,一直玩到黄昏”。好一副官僚老爷相。里在“传见”下民代表时,群众互相推诱,“做代表,毋宁死!”生动表现了大家对做代表的严重恐惧心理。广大灾民从长期痛苦的经历中体会到,见了官,除了加重灾难之外,是得不到任何益处的。官民之间的阶级对立是何等严重。可是,“下民的代表”最后总还是推举出来了。但去反映情况时,他同样也没有反映受灾的真情,什么“托大人的鸿福,还好”,什么“我们是什么都弄惯了的,吃得来的。”当他受到几句称赞时,就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地说:“我们总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顶好是做滑溜翡翠汤,榆叶就做一品当朝羹……”云云。这一副令人作呕的阿谈奉迎相,满嘴唾沫四溅的谎言,多像当时国统区的一些所谓的“国民代表”。这些“学者”、“下民”的“代表”反映灾情的结果,当然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减轻灾民们的苦痛。《理水》中,鲁迅用文化山的下民代表形象,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病态社会中不觉悟群
众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对他们在反动统治下形成的精棒枷锁,如:遇到灾难临头时心做代表去见官相间的冷漠;陈述灾难时的自欺欺人及传达官员吩咐时的二重性格等等,也进行了嘲讽,又一次向我们强调了他“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鲁迅在这里也同样是以“袁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严肃态度指出,这种愚昧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反动黑暗统治者赖以顽固地守旧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是最容易受黑暗势力所利用的。
第二段,借用大人们也无心听,无心为百姓做事的形象,学者的不实之言同“国民代表”的形象深刻地讽刺当时昏庸的官员,趋炎附势的学者、百姓。
第三段,写禹的到来。这段着重描写了禹的治水方针与反动官员们之间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段先写大员们“考察”回来,“休息了几天”,“大排筵席”,着重刻画了他们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情形。“一边是庄严地工作,一边是卑鄙与无耻”。在描绘了群丑的情态以后,紧接着,作者以强烈的对比,描述了大禹到来时的情状:“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这简捷的几笔,把大禹和他所带领的治水大军历尽艰险为治水而奔忙的伟大形象表现出来了。“黧黑”,“黑瘦”,“黑脸”均是形容夏禹及其一同治水的人们,他们这些人坚定、坚决,正是他所谓的“拼命硬干的
人”,是“中国的脊梁”。大禹等“闯”入局里的气概,轩昂的姿态,正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威武形象的写照。写禹太太追上来寻找丈夫而不得进见表现了大禹毫无私利,带头遵守法纪的精神。禹太太在门大口“骂”丈夫,这一“骂,固然说明了她对丈夫的伟大精神不理解,更重要的是,“骂”,恰恰是更加有力地表扬了大禹,说明他“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具有一心为大众解除水害谋求福利的伟大品德。
作品通过叙述大禹和官员们之间的一番对话,生动地表现了在治水方针上尖锐激烈的斗争。“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展现了他豪迈而壮美的形象!禹到了以后,不讲任何虚伪的客套,而是立即查问灾情,表现出他心里想的、说
的和做的,都是治水。他坚定地说:“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这几句话,千净利索,斩钉截铁,铿锵有声,力重千钧!
大厅上许多大员就不支持,不表态,消极怠工;有的以反动“孝道”来阻挠改革,有的“愤激”地骂禹是“蚩尤”的法子,还有的想以亲戚关系动摇他改革的决心。尽管群丑们如何阻挠,
但“禹一声也不响”。最后,禹“微微一笑”,然后以不可动摇的誓言宣告:“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第三段,写出了大禹的决心和官员们无用的阻挠。
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写出他向往的“民族的脊梁”的同时,又写了瓦解这些英雄的一群庸众,使大禹他们“真诚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与价值。
第四段,写大禹治水的成功。小说并没有仔细铺叙大禹治水的经过,只是用“景况日见其繁盛”,说明治水见了效。小说画龙点睛地写了关于禹爷的新闻传说,特别是夜里化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说明禹为了治水,足阱手服,昼夜苦战,流尽了血汗,付了很大代价,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作者采取白描的手法,生动描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后回师的情状:
····
一个半阴半晴的上午,他终于在百姓们的万头攒动之间,进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并没有仪仗,不过一大批乞丐似的随员。临末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腿弯微曲,双手捧着一片乌黑的尖顶的大石头……
这就是治水成功“地平天成”以后的大禹形象!禹还是保持着他那种可贵的“土气”:“粗手粗脚”,“黑脸黄须”,“乞丐似的”,既没有居功自傲的神态,也没有因功得赏的表现;所不同的,由于出外治水多年,“腿弯微曲”,患了关节炎后腿弯变得有些畸形了。小说在结束前,描写禹与舜的一段对话,叙述大禹治理国家大事的主张,补叙用“导”的方法治水的经过,以及自己
对家庭、婚姻、孩子问题的看法。小说最后写到“皋陶也和舜爷一同肃然起敬,低了头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并以“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作结,对大禹作了崇高的评价,有些研究认为本文是在写大禹的中国脊梁精神。然而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写出他向往的“民族的脊梁”的同时,又写了瓦解这些英雄的一群庸众,使大禹他们“真诚努力,牺牲,都成了表演而消失了意义与价值。能看出《理水》的结尾则具有颠覆力量,那个在人们口中众说纷纭的貌如乞丐、一脚老茧、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实干家大禹,回京后“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 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在庸众和昏官的包围下,成了特权阶层的禹的硬骨头被软化了。“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一切照旧,禹似乎并没有将他的实干精神投入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社会上的广大百姓仍过着蒙昧的生活,官员们依旧昏庸。一切如旧的现实是对大禹英雄形象最强有力的消解。
不难想象,禹以后的生活将在一片太平的平庸中度过,尽管他也许不会面对后羿那样的生存困境,但二者完成英雄壮举后堕入平庸,被庸众软化的命运却是何等的相似,透过羿和禹,我们仿佛看到了魏连殳、吕纬甫的影子开始时革命、维新,有着实干家和革命家的风范,可是最后却不得不与旧世界、旧观念妥协。鲁迅将这些英雄们拉下神坛,还他们以凡人的面貌,对他们的崇高性和正义性进行了无情解构与反讽。在这些群小的重重围剿中,大禹终于做出了某种妥协,维持着所谓的“太平”。尽管《奔月》和《理水》中的庸众们并不像《补天》、《铸剑》和《非攻》中那样成为导致英雄悲剧的直接动因,但他们却像无数把软刀子,消磨着英雄的斗志。后羿和大禹的形象与女娲、黑色人、墨子的形象互为对照和补充,显现了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们的某种困境: 或者被自己所为之奋斗的庸众所利用乃至杀害,或者在庸众的合围中被逐渐同化。
鲁迅把古代事件拉到现代,把神话中的英雄变成平凡卑微的现代人,把禹还原为平常人,有平常人的甘苦,也有平常人的弱点,以平凡作为标尺来构建大禹的人物个性,实现了对荒诞的超凡表达。当禹作为一个胜利者回到京城时,自然成为被众人看的对象,这是鲁迅小说经典的看客模式,“百姓们在宫门外欢呼、议论,声音像浙水的涛声一样”。
正是在“万人传颂”中,大禹治水的真实奋斗被故事化了,成为供人鉴赏的荒诞无稽的谈资。而在“万头攒动”间,大禹本人也以“高明的表演”供众人效仿,在充当残忍的娱乐的材料下,一切英雄真实的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开始禹的行为异常积极、活跃,却是孤独的,而最终在现实中失去了平衡。英雄早期的孤独与末期人们的效仿相互对照,奠定了小说荒诞的基调。《理水》取得了违背历史文本的荒诞效果,这恰恰与现实世界的各种不合理不谋而合。为此,我们会发现,在荒诞艺术的驱使下,鲁迅始终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出乎意料的《理水》的结尾,正是作品的精妙之点,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它使读者不致沉醉于荒诞的情节中,而是从其背后去窥测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和人情世态的冷暖炎凉。
《理水》的语言表达方式也独具匠心,造成了小说叙事话语的碰撞和语境的不谐和。细细回味后,不难从作者荒诞的表达中,领悟到个中寓意。在鲁迅的语言表述中,尧舜的天下不仅有满嘴外语以做学问谋生的学者,还有幼稚园、飞车等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物。鲁迅有意将现代话语和事物植入到古代的时空环境中,使时间错综交叉,呈现出非古非今、亦古亦今的特征,使文本的结构呈现出反讽的艺术形态。这种时空结构的反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方式,同时体现了鲁迅对生命和生存的独特感知,是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折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