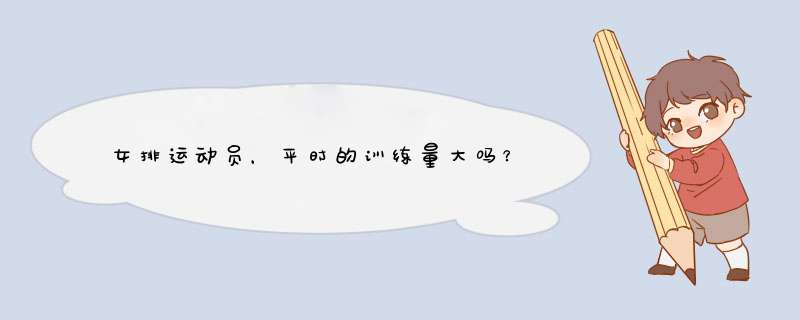
女排运动员,平时的训练量大吗?
1训练量很大。毕竟是职业排球运动员,好成绩是要付出的。女排的工作人员透露,她们每天光是为女排接排球就要走两万多步,姑娘们的训练量可想而知。平时训练量很大,因为这项运动本身就需要很大的体力,所以平时的训练时间也比较长。训练量特别大,每天有2/3的时间花在训练上,训练的强度也比较大,所以这些人才才能变得这么优秀。
2与塞尔维亚不同,塞尔维亚在决赛后给球员放假,中国女排立即为世界锦标赛做了更紧张的准备。在北京训练期间,中国女排还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旗仪式,旨在提高队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像世锦赛这样的大赛中,精神战斗力的加分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3郎平还谈到了朱婷高标准的自我要求。在训练和比赛中,他不仅需要擅长自己,更需要在帮助和揉捏队友中起到核心作用。如何促进整个团队的进步,对集体更有利。中国女排新封闭训练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郎平透露,中国女排的核心智慧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教练和运动员需要共同努力解决技术问题,团队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相互配合,这体现在教练组的日常训练需要给予足够的压力,运动员应该考虑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相互抱怨。
4扣球训练,陪男教练和暂时不参与扣球的助理进攻手站网对面拦网。在最夸张的时候,一个人扣球,要面对五个盖帽。朱婷扣球成功率很高,郎平也要求给弟子制造困难。他大喊:“堵网加油!”“拦住她!拦住她!”郎平安排后,袁志和李彤奋力起跳,但没能挡住朱婷。球穿过了他们的拦网。
中国女排是中国体育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中国三大球6支国家队中成绩最好的球队。为什么中国女排能成为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答案藏在每一天的训练中。
熟悉女排的朋友都知道国家队不仅有主教练和运动员,还有几名男性陪打教练,负责协助郎平训练球队。郎平身经百战满身伤病,她已经不可能亲自上场和球员过招,只能让男陪练模拟对手和女排国手对抗,这是女排国家队的训练常态。
在前两天的公开报道中,中国女排时隔三个月重新出现在球迷面前,这一次的地点是在国家队的训练馆,女排正在进行防守训练。可以看到有两名男陪练站在另一个半场的台子上,旁边放着一筐球,另一边是接受训练的女排国手。
训练开始之前,郎平对男陪练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打,要真打!防守训练看起来很无情,男陪练打出的球速度非常快,同时每一个都很重,这也是女排国家队之所以需要男陪练的原因,因为男性有体力优势。为了防止教练员因为心软而放水,达不到训练效果,郎平在开打前特意叮嘱一番。
训练开始后,男陪练居高临下大力击球,排球像炮弹一样往下砸,而防守队员必须要将球防起来。事实上大家现在看到的训练内容已经是升级版,球网上挂有白色的布片,目的是阻挡球员视线,让防守球员在排球飞下来之前看不清助教会向哪个方向击球,更加考验队员的反应速度和灵敏程度。
这样做的效果很明显,女排国手在下面被“打”的很惨,有些重球防不起来的后果就是防守球员也随之倒地。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只有专门负责防守的自由人需要进行这项训练,而是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训练。这个项目对身高较矮的丁霞还算比较友好,毕竟她1805厘米的身高还算灵活,真正难受的是1米98的朱婷和2米01的袁心玥。
女排国手能在比赛中展现实力,实现升国旗奏国歌的壮举,但陪打教练却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他们不会登上领奖台。前中国女排主帅陈忠和就是陪打教练出身,他亲身经历了老女排时期的辉煌,并带队夺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金牌,是女排队史上的传奇教练。
这种看似无情的训练却能有效提升队员们的水平,帮助国手在比赛中击败对手夺得冠军。对于一名志在夺冠的球员而言,每天训练中的伤痛远远比不上失败那一刻的痛苦,甚至连万分之一都不到。中国女排就是这样训练,每一天都是这样,这就是她们能成为世界冠军的秘诀。
10月13日消息,本次日本女排世锦赛期间,中国女排刻苦训练成为赛场之外的一道靓丽风景,据女排工作人员透露,自己光是替女排姑娘们捡排球每天就要走上2万步以上,姑娘们的训练量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中国女排历史上最杰出的运动员,女排负责人朱婷接受了《中国体育英雄联盟》第三集的专访。当面对主持人邓亚平时,朱婷也谈到了自己多年来的想法。她还着重感谢教练郎平,因为在朱婷看来,结识郎平是她一生的运气。
朱婷在接受邓亚平采访时还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郎平回到中国执教后,能够追赶郎平的教练,这是她以前不敢想象的。在当时的中国体育界,能够进入17或18岁的国家队非常罕见。朱婷还觉得,在她可以雕塑的年龄,她碰巧遇到了像郎平这样的优秀教练。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荣誉
每天给每支球队安排了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的训练时间,但主教练郎平感觉训练量不够,于是每天都要租用民间场馆进行训练。日本场馆租用规则是在截止日期前所有人都可以申请,最后抽签决定谁来使用,因此找球馆训练都是个难事。因此,女排训练使用的场馆都是综合体育馆,需要自己搭球网和标志杆,用完后还需要一切复原,清理垃圾带走。
女排租用的场馆大多在郊区,开车需要一个小时。每天一天两练是常态,如果晚上有比赛,姑娘们7点多就得从酒店出发,9点开始一天的训练,每次训练都是雷打不动的3小时,个别球员如果没能完成任务可能还得加练。一位女排工作人员透露,每天光是帮忙捡球就能走2万多步。而担任央视解说嘉宾的惠若琪来探班时,也会在人手不够去帮忙捡球。
虽然训练强度大很辛苦,但是姑娘们却能够苦中作乐,训练结束,龚翔宇拿起水壶举过头顶,小苹果袁心玥配合地做出了喝水状态。网友开玩笑,“小宇别再浇苹果树了,够高的了。”
结束了全运会资格赛征程的中国女排转战宁波北仑,开启为期八天的新一期集训。本次集训队员、教练、工作人员一共有32人,总教练郎平率先抵达北仑,随后助理教练包壮率领袁心玥、姚迪、李盈莹等第一批抵达,随后朱婷等队员第二批抵达。天津女排新秀王艺竹跟随天津队的队友们一起抵达北仑,参加这一期的封闭集训。
队长朱婷在全运会资格赛中率领母队河南再次闯进决赛圈,在比赛结束第二天,朱婷启程北仑参加国家队训练的时候,河南队的教练、队员一起给她送行。朱婷与没有参加全运会资格赛的世界冠军刘晏含同行,两人还一起拍了合影。
中国女排在抵达北仑之后,受到了当地球迷的热烈欢迎,球迷们向她们送上鲜花,还簇拥着她们前往驻地。
关于此次集训,郎平表示:“北仑是我们奥运会最后一个冲刺阶段的集训,这一期的第一阶段是比较短的,只有8天的时间,做一个很快的恢复和配合,就要去日本参加奥运会测试赛。”中国女排预计4月25日从北仑出发,前往日本东京,在5月1日与日本女排交手。郎平直言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可以在奥运会比赛场地与日本队进行比赛。她称赞国家队队员最近的表现还都不错,不过最近打的都是国内的比赛,特别期待着国际比赛的检验,希望能找到打国际比赛的感觉。
在队员们训练的时候,郎平每天都会抓紧时间做一些力量训练,维护自己的肌肉,让自己随时可以上场给队员们当陪练。郎平解释道到奥运会赛场教练名额有限制,不可能所有陪打教练都出现在球场上,郎平就要上场去客串陪练。在漳州训练场馆里,放置了几把特制的椅子,它们比其他的椅子高出一截,这是给特意给郎平定制的,让一身伤病的她在场边休息的时候能做得稍微舒服一些。
现在中国女排正在进行第二轮集训,队员的平均身高都很高,而且整体的实力和水平也非常给力。
中国女排是东京奥运会夺冠的热门,所以自身的训练并没有放下来,郎平教练针对中国女排制定了非常切合实际的训练计划。
中国女排在六月底结束了第一轮集训以后又开始了。从七月到九月的第二轮集训。训练时间非常紧张。而且整个训练都是在密闭的环境中进行的,所以并没有受到疫情太大的影响。
中国女排身高水平如何?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女排的平均身高都是非常高的。在第二期的集训中,身高最矮的是林莉,她的身高是171米。身高最高的是袁心玥,她的身高是201米。所以说整个球队的身高都非常高。
身高突出是中国队一个典型的优势,因为身高有优势的话,可以在高度上压倒对方,获取进攻的主动权。
中国最的最低身高是171米,最高身高是201米。这在整个世界排球队中都是非常少见的。由此可见,身高优势是郎平教练的一个重要战术。
以下是具体的身高数据:自由人:王梦洁173米、林莉171米、倪非凡177米二传:丁霞180米、姚迪182米、刁琳宇182米、梅笑寒184米、孙燕188米接应:龚翔宇186米、曾春蕾186米主攻:朱婷198米、张常宁195米、李盈莹192米、刘晓彤188米、刘晏含188米副攻:袁心玥201米、颜妮192米、王媛媛195米、杨涵玉198米、胡铭媛186米由此可见,整个中国队的身高优势是非常的明显。队员基本上都在一米八以上,而且还有队员达到了两米。这在赛场上对对手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估计这些人上了赛场对方会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大家同样可以发现在自由人组合中身高都普遍比较低。因为自由人不需要扣篮,所以他不需要太多的身高优势,只需要行动灵活,能够接球就可以了。身高太高的话反而会成为累赘。
二相比之下主攻和副主公的身高优势就非常明显了。他们一般身高都会在一米九到两米之间。因为在赛场上他们需要扣篮,需要通过身高来压制对方。所以身高的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小总结:中国女排有一股奋斗的精神,在第二期的集训当中,中国女排肯定会加紧训练。提高自己的战术能力,和应对问题的能力。
相信在这轮集训之后,整个排球队的水平都会有质的提升。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创造更多的辉煌。为祖国争光。
郎平自传
失踪的球袜
1998年11月1日我们从东京直飞鹿儿岛。
鹿儿岛在日本的西部,是个小岛。我们下榻的旅馆正对面是个“活火山”,可紧挨着山脚却住着很多的人家。我奇怪,这些人家为什么不搬走?日本的陪同人员告诉我,因为这些住户喜欢、留恋这儿独特的风景,就是不愿离开,一旦有预报再走也不晚。
在鹿儿岛是参加小组赛,我们和韩国队、克罗地亚队,还有泰国队分在一组。第一阶段我们必须全胜,然后在第二阶段,我们还要碰到古巴队、意大利队和保加利亚队。在这样的两个阶段,我们必须获得前两名,才能和另外两组的前两名共同进入前四名的半决赛。但从这几年的比赛情况看,我们打古巴队一直处于下风,几乎没胜过。因此,第一阶段的小组赛我们非打第一不可。但分析小组赛的阵容,我们并不乐观,克罗地亚队很强,他们吸收了原苏联队的三名队员,1995年我们和克罗地亚队打过一场,3∶2险胜,以后再也没有交锋,奥运会以后我们换了一些年轻队员,这些队员都没打过克罗地亚队,心里不是特别有底,赛前,我们的针对性训练,更多地放在克罗地亚队身上,我们还把意大利队请来,打了两场比赛,让我们的队员适应一下欧洲的打法。李艳的状态很好,我还是提醒她:“现在,很多国家都熟悉你、研究你,你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技术上的,心理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警惕。”
再说打韩国队,这三年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输过,但我还是再三强调,打韩国队不能大意。
我的预感是有根据的。
在东京日立佐合公司训练时,我每天都仔细地观察队员,发现队员在赛前不是很兴奋,我隐隐地担心:她们是不是疲劳了?队员们确实很辛苦,打完全国联赛,她们没有时间休整,直接来国家队报到。但在出国之前,我已经安排了相当长时间的调整训练,队员不应该再出现疲劳状态。我和张蓉芳分头找队员聊天,了解她们各自的内心活动。吴咏梅说,她很有信心,还特别提到1994年世界锦标赛输给韩国队那场球:“我特别不理解,她们怎么会输给韩国队的?”张蓉芳还有心地追问道:“吴咏梅,你觉得这次打韩国队有多大把握?”吴咏梅说:“心很定!”张蓉芳向我转述了吴咏梅的话,我心里反而有些不安了,韩国队的顽强是不可小看的。
打韩国队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在窗前坐了坐。
我们住在海滨,20层的楼,高高在上,拉开窗帘,海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不一会儿,亚文进来说,打赢克罗地亚队,队员们情绪很好,又有大海的景色做伴,大家都说,但愿我们自始至终都能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我的心却放不下,不敢轻松,总感觉没到愉快的时候,特别是打韩国队,好像觉得能赢,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打这种球,很难受,心老提着。
不知为什么,到了鹿儿岛,老是要发生一些意外、一些差错。
打克罗地亚队那天,队员们做准备活动,我在帮他们捡球时,只听我的膝关节“咔嚓”一声,当时没太在意,马上比赛了,精力都集中在比赛上,对别的事情都没有感觉了。打完第一局,站起来换场地,我才发现我的左腿直不了了,很疼很胀,但我这时候不能瘸着腿走路啊,主教练要注意形象,我硬挺着。打完比赛,我的膝关节肿得像个大馒头,在食堂里马上用冰做紧急处理,田大夫把我的腿加固了,晚上睡觉,腿也弯不了,24小时以后才慢慢能走路,外国队员笑话我:“中国队队员没伤,教练先受伤了。”打韩国队前一天的傍晚,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让我稍稍地揪了揪心:吃过晚饭,我洗了双袜子,用衣架晾在阳台上,然后召集队员开赛前的准备会,队员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说,打韩国队有把握,打得好3∶0,打不好3∶1。我提出了和她们相反的看法,我说,我们不能按一般的情况来判断,在大赛中,绝对不能有错误的判断,哪怕一丝一毫,都会使你变主动为被动。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国队教练已经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怕中国队怕了三年,你怕也得打,不怕也得打,还不如放开手脚打。我要求队员一定不能有侥幸思想。但在准备会上,我感到队员们谈得都很一般,赢了克罗地亚队,大家还是松了点劲。开完会回到房间,我突然发现,晾在衣架上的袜子少了一只,我四处找了找,才看到那只失踪的袜子挂在阳台的栏杆上,几乎是只挂住一根细细的线,我挺敏感,心猛地收紧了一下:这只袜子差一点从阳台上掉下去,是不是在说明点什么?我想,这不是迷信,我很能体会自己,这些微妙的、不为人觉察的心理变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只袜子根本不值钱,丢了就丢了,我的心为什么会为此一动?我不由得想到,这次锦标赛我们会怎么样?
和韩国队比赛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在阳台上站了会儿,看到克罗地亚队员一个个都在海边散步,她们昨天又输给韩国队,也许是时差没倒好,她们没有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这时,我听到隔壁阳台上何琦在对吴咏梅说:“你看你看,克罗地亚队昨天输了,想不开了,在底下溜弯呢。”我随口接一句:“希望我们不要爆冷门啊!”何琦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的。”
但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我又想到昨天夜里寻找那只“失踪的球袜”的情景。
“差一点掉下去的球袜”似乎真是一种预兆。
中韩赛开始了,袁伟民却要上飞机去广州出差,临走前,他在办公室看卫星转播,前两局中国女排输了,袁伟民坐在办公室里不动了,走不了了?!有人来催了,飞机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开始,眼看起飞的时间实在紧迫,袁伟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机场。一下飞机,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询问:结果怎样?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令人懊丧:中国女排2∶3输给了韩国队。
自我执教中国女排以来,韩国队从来没有赢过中国队,但金炯实接手教鞭以后,韩国队为打中国队做了长期的准备,今天的比赛她们是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情,一定要打赢中国队。中国队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势领先,最后却让对方连追6分。第二局,中国队又以6∶3领先,但仍然被韩国队追成8平。12平以后,中国队又连连失误,以15∶17又丢一局。显然,中国队今天输给韩国队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误太多,特别在关键的第五局,失误送了6分之多。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说,郎平带队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高的失误率。据说,李岚清同志也有点坐不住了,打电话到广州找袁伟民:给郎平打个电话吧。但是,这个电话该怎么打,是批评还是安慰?!袁伟民为难了、犹豫了。
输了这场球,大家就缓不过劲了,有的队员当场就哭。我不许队员当着别人的面哭:你只能赢不能输?!当然,我们输得实在太关键了。
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意大利队主教练佛利哥尼看到我,亲切地说:“放松点,中国队没有问题,我看了录像,我真不敢相信韩国队打得这么好,但我不相信她们场场都能打得这么好。”古巴队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后还有机会。”
体育不相信眼泪
我能控制自己,毕竟见过世面,经历过很多失败了,在公开场合,我知道该怎么做,尤其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要回答记者不愉快的提问,我必须说得有理有节。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电视台采访,到会晚了,我一进会场,有记者就问我:“郎教练,你今天输给韩国队心里一定很怨?”因为在场的国际排联的人也都认为中国队胜韩国队应该没有问题。我没有对“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说:“韩国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而且,是一支有特点的队伍,在上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是第四名,我们和韩国队较量,一直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场球是韩国队这几年来发挥得最好的,我们首先要祝贺她们,相比之下,我们在技战术的运用以及思想的准备上面,都不如韩国队那么充分,打韩国队我们虽然有把握,但到了关键时刻反而怕输,精力没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问题导致了技术的发挥。相反,韩国队有输的准备,干脆放开打,反而打得轻松。从比赛中,我们看出运动员心理的微妙变化,实力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两强对阵,就看临场的处理和发挥,谁发挥得好就能取胜,以弱胜强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闻发布会开到10点多,我又召集教练班子先碰头,统一思想,我的话很踏实、很坚决:球可以输,人不能输,进不了前四,第五也要争,不到最后一场球,不到最后一局球,不到最后一分球,我们决不能放弃!
连夜我们再召开全队会议。会议的气氛始终很沉重、很压抑,形势一下子变得如此严峻,哪个队员的心里不追悔莫及?吴咏梅很自责,一边讲一边哭,她是队里比较强的一个副攻手,她说对方把她看得很严,她没有发挥好,更主要的是,对困难准备不够。孙王月也一直在抹泪,认为自己没带领好大家,只有几个新队员说,问题在于二传分配球不合理,听到这样的话,打二传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让队员们讲,最后,我做总结,我说得比较严厉,我对她们说:“现在,我不要求你们考虑名次,特别在困难的时候,要做到有难同当,团结一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防止“身落万丈”的悲剧重演。1994年世界锦标赛是前车之鉴,那时候也是一场交叉球,也是输给韩国队,队员没有了斗志,结果一泻千里。
痛苦的鹿儿岛之夜
队员们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呆呆地看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海,还有“活火山”,心里像着了火,仿佛这鹿儿岛上的“活火山”,真的爆发了!
给队员们说了那么多话,把心里最重的话都说了,而这些话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给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伤的膝关节还在痛。吃了两颗救心丸,还有止痛片。我膝关节的伤是最重的,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打开我的膝关节都吓一跳,医生说,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我的肌肉很年轻。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一瘸一拐的,像个半残废,心里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时候,看我走路的样子,会笑话我,那时候,她一见我高兴,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朝我扑过来,我就紧张,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浪浪大了,有朋友来约我们跳舞、滑雪,她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我才40岁,到了60岁怎么办?
这几年常常生病,确实干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心累。白天训练,一到球场,我教练的脑子就开始转动,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别队员,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点劲,你得看着她,还得点她,她练累了,你还得想办法调动她。尤其是封闭训练时,一到晚上,我要带队员看录像,队员分组看,星期一是二传,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个组都要帮她们分析。我脑子里全是球啊,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根据李艳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我对袁指导说:“你的承受力还是比我强,看来,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
长期积劳,体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我感到难受、无助。我的宿舍不朝阳面,开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间年久失修,屋角的墙皮斑斑驳驳地往下掉,平时忙,不注意这些,一生病,情绪低落,我想得很多: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看看周围的人,譬如我姐姐朗洪,人家也不干什么大事业,平平稳稳地过日子,该过节过节,该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家,有丈夫、有女儿,老少一起生活,心宽体胖,多好。可我呢,丈夫没有了,女儿也不在身边,我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那样大的反差,这使我心里的渴望格外强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爱情,那是最美满不过的了,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这个郎平有什么?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拿亚军,多么伟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就是肯付出罢了,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如果1995年不回来,说不定我又成家了,和别人一样地过日子,尽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实实在在。
当然,身体好了,这些在生病时比较灰调的想法便烟消云散。尽管身体常常出问题,但这个事业没干完,我不会倒下,我挺坚强,病一好,又忙碌起来,队里的工作又斤斤计较,一点都不肯马虎。
“特别倔强、特别认真,郎平从小就这样。”郎洪评价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我就挺能认错的,郎平不这样,她要是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承认。她做事又特别认真,不管干什么,干了就一定要干好。我们俩小时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挣零花钱,一大盒才给一角六,我们俩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让我妈知道。我干活比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个个都给挑了出来:你这不行!我说,一两个没粘好怕什么,那么多呢,谁还给你一个个检查?她不干,非让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别认真。”
太认真,一丝不苟,郎平才“心累”。谈到郎平的“累”,性格稳实的郎洪,神情便忧郁起来。“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说话,她似听非听。只有打完比赛,她才高兴,去商店买这个、买那个,俏皮话也多了。”
郎平心累,还因为她对人对事太细致,无论打球、执教,无论做母亲、做妻子、做女儿,担当任何一个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将就,总想尽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难以保证打球不输、感情不败。
人的感情是一部历史
打完亚特兰大奥运会,又拼了整整两年,本想,这次世界锦标赛打进前四,我真的可以告别球场,没想到,这个“别”,还没那么好告。可是,我的身体,我的心理,还能不能继续支撑下去?打预赛就障碍重重,后面还有古巴队,还有俄罗斯队,还有巴西队,强队林立,还会出现怎样的险情?
软软地倚着栏杆,我突然感到一阵很无助的孤独,好像从山顶滚落到深深的峡谷,耸立四周的是悬崖、是峭壁,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来拉我,我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我觉得浑身软弱无力,心跳、心慌。以前,这样的心跳、心慌,往往是在半夜里做梦突然醒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哪里?身边没有人,无依无靠,像在一座大山里,很冷,很空,心,没着没落的,仿佛迷失了,很可怕。这样的空白停留几分钟,意识才会苏醒。但这会儿的“空白感”分明不是梦,我很清醒,是醒着的孤独。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就像面对这夜色茫茫的大海,无言无语,没有人能对我说点什么。
“铁榔头”从回国的那天起,便是孤军奋战,她身后的那个家,像经历了地震摇晃后的房子垮塌了。对于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场“地震”,郎平精练地概括了她的想法:“我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想了很久。我最看重的是心情,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不能两方面都没有,物质上没有,精神上也没有,你会觉得很贫穷,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生活。”正因为郎平太重感情,所以,她才有理性的决定。
有几天,从早到晚都在聊,不免会聊到家、婚姻、爱情,这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沉重的话题。郎平说着、说着,便不由得叹气。可以想象,这“话题”里有不少“荆棘”,触到了她心底最深的痛楚。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智,她不想更多地谈论感情生活中那些是是非非的往事,更不想涉猎别人,埋怨什么、指责什么。生活是一部历史。她只想接受“婚姻失败”的事实。
我回国执教,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女排身上,我不愿意让大家对我的个人生活评头论足。对生活的这种结局,我自己已经很痛苦,对方也痛苦,我不能因为我是名人而让女儿的父亲也跟着被传媒说东道西,这会伤害我,也会伤害他,伤害他的家人。所以,这些年,有关我的生活问题,我没有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我不想谈离婚的事,这会让我分心,我回来是带女排打球,不是来制造新闻写我、炒我,这一点,我很清醒,特别小心,我也不和国内的朋友谈我离婚的事,再好的朋友也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根本没这个必要。我在家里都很少说我自己的事,我母亲很心疼我,我不想再给她增加压力和痛苦。当然,我给家里人说说,我自己宣泄了,轻松了,但老人没工作,整天会琢磨,我等于把痛苦转嫁给母亲了,我不能这样。
可郎平的生活问题仍有一些小报小刊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拿来大做文章。一位76岁的老球迷用长者的关心给郎平写信,他说,他在《体育天地》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郎平:情感纠缠何时了?”的文章,“才得知你面临离婚的痛苦,作为一名超级老女排迷,我深表同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亲爱的郎平同志,不要悲伤,不要灰心,你是坚强的,好样的,相信你会处理好感情问题,战胜自我……”
读到球迷写来这样的信,不知为什么,郎平会感到更深的无奈、更重的烦恼。
1999年年初,深圳举行“风云际会话当年”的老女排队员聚会,说好每个老队员都带上丈夫和孩子———这是老女排队员离开球场后最活生生的内容。
坐在台下,听老女排队员一个接一个数说他们的家庭、她们的幸福,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有点坐不住了,她低下头,不敢正视站在台上的郎平,此时此刻她是什么心情?曾经,郎平也有过燕尔之乐的幸福:新婚那天,他们一起去西山放风筝,像两个大孩子一样地玩耍,着实让人羡慕。每次比赛归来,他去机场接她,两人坐在大巴士的最后一排“嘀嘀咕咕”悄悄话说一路,记者们想采访也插不上话……但郎平不再回忆。今天的郎平独自站在队伍的末尾,别的老女排队员都是团团圆圆的景象,如果节目主持人走到郎平面前提问,她该怎样诉说她的家庭?女儿在美国读书,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她不能飞来中国参加母亲的聚会,除此以外,她无法再说什么了。但郎平的表情,一脸坦然。
我的美国朋友
我不是铁人、“女强人”,太痛苦的时候,我会关着门给我的美国朋友打电话、写信,有时我会在电话里哭。我没有想到,感情的纠纷会让我感到这样痛苦难忍。年轻的时候很天真,一听父母叨叨说:“不要着急结婚成家,你现在很简单,不明白,这是终身大事,找不好要后悔一辈子!”那时候,我特烦听这样的说教,我心想,结婚还有什么难的,我世界冠军都拿了,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那种训练的苦,苦到残酷,我都不敢回忆,但我挺过来了,所以,我自以为,我在生活中肯定是个强者,能有什么问题克服不了?现在回想父母的话,还真是这样,我不是克服不了自己的问题,而是无法让对方按照你的意愿为人处事,那种精神和观念的差异以及对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像物质的东西好解决。不过,我不后悔,毕竟爱过,也幸福过,只是,要把爱和幸福变成永久的事,太难了。这种“难”,让你束手无策、进退两难,有时真的很绝望。劳尔告诉我,她离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劳尔的前夫约翰,我很熟悉,他是个工作狂,爱排球爱得不得了,写有关排球的理论著作,每天写到半夜两三点,一早又接着写,叫他吃饭,如果有电话谈工作,他一谈四五十分钟,劳尔一个人也没情绪吃饭了,一到周末,两个人出去玩玩吧,约翰又出去讲课。约翰对人一腔热情,谁有困难,只要来个电话,他立刻开车去援助,他这样的,做朋友特别好,但不能做丈夫,中国有句俗话:胳膊肘往外拐。所以,作为妻子,劳尔就觉得很不满足,她觉得家庭没乐趣,享受不到生活。现在,劳尔又结婚了,戴维是个建筑设计师,还带着两个孩子和劳尔一起生活,他很会生活,一下班就回家,劳尔做饭,他总在厨房里帮忙,晚上,他们和孩子一起休息、娱乐,周末,劳尔带队去比赛,他也陪着一块儿去,最近,他们又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了,劳尔感到很幸福。
但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劳尔,约翰人那么好,为什么离婚?现在我明白,婚姻的成与败,不是好与坏的冲突,也不是黑与白的反差。我们中国人爱用一个“缘”字来一概而论,我对“缘”的理解,是这样一句成语:气味相投,是冥冥中的默契。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