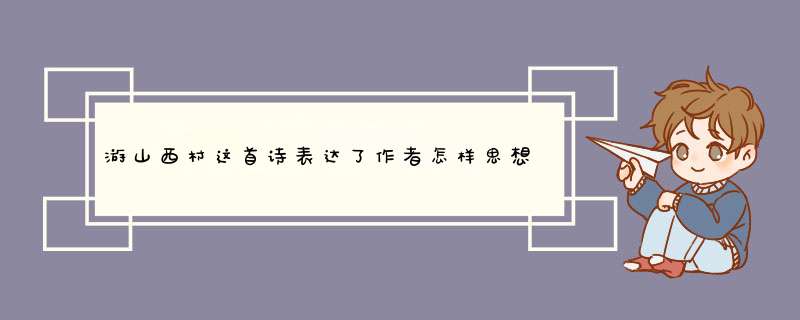
这首诗是陆游蛰居山阴老家农村时所作。本诗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光,对淳朴的农村生活习俗流溢着喜悦、挚爱的感情。 诗人陶醉在山西村人情美、风物美、民俗美中,有感于这样的民风民俗及太平景象,反映了他乡居闲散的思想感情。 诗人陶醉于在山野风光和农村的人情里,表现了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恋恋不舍的情感。诗人在语调极其自然亲切的诗句中向人们展示了农村自然风景之美、农民淳朴善良之美,并把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高尚情操美融于其中。
沉醉和陶醉的区别在于情感状态和行为表现。
沉醉是指在某种刺激下,情感状态变得极度兴奋或狂热,往往伴随着行为上的放纵和失控。例如,沉醉于音乐、酒精、毒品等。而陶醉则是指在某种美好的情境下,情感状态变得愉悦、舒适和放松,往往伴随着行为上的自然流露和内心的平静。例如,陶醉于自然风景、艺术作品、文学作品等。两者的情感状态和行为表现有明显的差异。
在生活中,应该尽量避免沉醉,而多去追求陶醉的美好体验。
《枫桥夜泊》是唐代诗人张继的名篇,这首诗通过一个“醉”字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
在诗中,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的时候,吟咏着远处河畔的景色,欣赏着漫天繁星,流连忘返。在这种美妙的环境下,张继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自然美景之中,用一个“醉”字来形容他的心情。
这个“醉”字,不仅仅是表达了诗人张继在美景中的陶醉,更深层次地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念。张继倡导“诗以言志”,提倡把真情实感融入诗中,以达到表达思想感情的目的。他的这种诗学观念与唐代诗歌的“自然”和“真实”的主张相符合,因此张继的《枫桥夜泊》在诗歌中极富代表性,成为唐代自然诗的杰出代表之一。
因此,通过一个“醉”字的运用,诗人张继表达了他在自然美景中的陶醉与情感表达的诗学观念。
1、陶醉,汉语词语,读音为táo zuì,表示很满意地沉浸在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沉醉于某种事物或境界里,以求得内心的安慰。
2、近义词:沉迷、耽溺、着迷、入迷、迷恋、沉浸、沉溺、沉醉。
3、反义词:清醒。
4、出处:
(1)唐崔曙《九日登仙台》诗: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2)徐特立《纪念“五四”对青年的希望》:“如果都只为个人打算,陶醉在小圈子里,那就不可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3)杨沫《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一章:“她觉得自己想入非非,不觉脸红起来。整个心灵被年轻人的狂热的幻想陶醉了。”
词目:陶醉
读音 táo zuì
释义:
(动)很满意地沉浸在某种境界或思想活动中
沉醉于某种事物或境界里,以求得内心的安慰
英文翻译
[be intoxicated with;revel in] 忘我地沉浸于某种情境中
(近)着迷|沉溺|入迷|沉迷
相关诗句
1唐崔曙《九日登仙台》诗:"且欲近寻彭泽宰,陶然共醉菊花杯"本谓酣畅地饮酒而醉后以"陶醉"谓沉醉于某种事物或境界里面
相关名言
1青春是一种持续的陶醉,是理智的狂热
--拉罗什富科
2世人皆说清醒好,唯我喜陶醉
基本解释:
[be intoxicated with;revel in] 忘我地沉浸于某种情境中
他们为光明的前景而陶醉
自我陶醉 [编辑本段]详细解释 唐 崔曙 《九日登仙台》诗:“且欲近寻 彭泽 宰,陶然共醉菊花杯”本谓酣畅地饮酒而醉后以“陶醉”谓沉醉于某种事物或境界里面
徐特立 《纪念“五四”对青年的希望》:“如果都只为个人打算,陶醉在小圈子里,那就不可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柳青 《创业史》第一部题叙:“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庄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 杨沫 《青春之歌》第二部第一章:“她觉得自己想入非非,不觉脸红起来整个心灵被年轻人的狂热的幻想陶醉了”
相关文段
陶醉给我一个望文生义的想象是,陶的破碎陶醉是形式的失去,自我的暂时消失就像人们追求理性认识一样,在另一方向上,无论是在情感、意识还是体验上,渴望陶醉成为一种强烈的欲望人们甚至使用能够对精神状态发生作用的植物来改变意识和体验由于当代文化的享乐特性,追求陶醉已经成为快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主导价值如果说在古典时期文化的主要价值是对意识生活和理性建构的追求,那么追求陶醉和满足陶醉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炼丹士所制作的灵丹妙药酒店,歌舞厅,游乐园和影院等等,以及一些其他灰色地带,是正当地出售“文化娱乐药片”的合法场所当代文化把欲望和对欲望的满足形式置于首位
在陶醉感的实践中,有一些相对安全与合法的方式,某些植物只是轻微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感觉经验,它改变了平淡的感觉带来轻微的兴奋,而不是全面地改写了感觉经验这些植物的精神作用是“透明”和安全的我们文化中的茶、烟草、咖啡,就是如此,它们对于意识的作用相当温和轻微,使用这些植物或植物制品的人,并不改变自身的时空坐标,也不强烈地改变自我意识,它们不妨碍日常生活和厉行其职责,还会有助于它然而另外一些强有力的植物的使用却完全改变了使用者的时空体验和自我意识,使他们灵魂出窍飘离了时空坐标和他们自身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巨大的神秘诱惑:面临陶醉的危险深渊,自我意识的彻底丧失
也有学者将意识的改变理解为一项基本的人类活动诗人和艺术家是以特殊的形式创造影响人类意识和体验的人,他们以此为务,就像后期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追求通灵,追求感觉器官的全面错轨,在这里,陶醉似乎是一种手段或者途径这种现象甚至还发生在儿童自发的行为中,他们会旋转个不停,一直到晕头转向,当然现在儿童乐园里有了各种各样的设施以达到这样的极限体验改变人类意识状态的方式还有许多,传统的冥想、修行(苦行)、辟谷、高唱圣歌和其他神秘的宗教体验,追求陶醉、满足陶醉感甚至可能是许多对宗教入迷的人们的隐秘动机之一传统而世俗的方式如
饮酒以及食用风味浓烈的食物也是满足陶醉的方式,现代的各种极限运动、观看恐怖片或感觉剥夺试验,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改变意识状态和情绪体验的功能当然,强烈入迷的情感经验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功能,只是它不能够由行为主体操控,也不能随意进
行重复体验因此人们只能在单调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想念奇遇
在所有这些追求陶醉的形式中,最有效也最具争议的是各种植物麻醉品的使用植物麻醉品是人类快乐的正当性的一个隐喻焦点一种可以直接改变人的感觉和意识的具有魔力的植物,既是快乐的天堂偶像,也是地狱里的恶魔,既是祝福又是诅咒,既是解放的力量也是禁忌陶醉体验涉及毒品和文学、哲学、宗教共同具有的一些范畴与经验:它们涉及哲学和法律上的主体性,自由与依附,自然与文化,解放与压抑等许多问题,而陶醉是这些问题的一个隐喻焦点
这些植物是一种精神工具原始宗教和巫医学最早地使用了它人类热烈崇拜这些麻醉性的植物(民族植物学家们把它们称为“神在其中”的植物),就像古代印度的苏摩教,据圣典《夜柔吠陀》称,苏摩是一种具有神的力量的能够作用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植物,人们把它视为通向神的知道的一条神秘途径陶醉既是一条通向神灵的道路,也几乎是人类的神性体验不可分割的要素
许多麻醉性植物可以缓解人类的痛苦是它具有快感特征的一个例子,一些麻醉性植物可以使人释放压抑,激发欲望,缓解压力,解除禁忌,平息社会生活给人带来的负面感受这里我们将很快遇到一个争论或隐喻的歧义马克思著名的断言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尽管用其负面意义,他也无法把痛苦的安慰功能从毒品的修辞学中彻底消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说烟馆和酒馆是穷人们的地上天堂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在感觉革命和非压抑社会的理想中无疑赞同了麻醉性植物释放压抑的解放功效,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不同意19世纪两位先知的预见,陶醉和解除压抑不仅是穷人的需要也是富人所需某种陶醉感或着魔状态,是某种艺术家、赌徒、英雄、信徒、沉思冥想者、神秘主义者所共同具备的甚至可以在极度痛苦和快乐的时刻的人、祈祷中的人身上看到这种陶醉性的品质无论赞成还是批评,他们都在把麻醉性植物的使用视为一种精神工具无奈这些植物身上凝结着过于复杂多义的隐喻赞成或批评者在使用它的部分隐喻
陶醉感涉及这些思想性的主题:自由与依附,快感与痛苦,自我与社会“陶醉”这个词有着一个区域广阔的语义学光谱它被不同的思想体系赋予了有时完全不同的色彩与含义德里达在《毒品的修辞学》一文中说,毒品的概念有一个被赋予的和制度化的定义:“不管是清晰的还是概略的,它包含了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习俗、价值观、规范,以及纠结一团的话语的整张网络,一种修辞法”围绕着它所形成的不是科学的而是道德的和政治的价值判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被赋予了意义它本身是规范和禁忌,一种法令,也是一个玄妙的术语在我们所能够意识到的关于毒品与吸毒的制度化的特性中,两种不同的“伦理——政治”公理进行着抗衡它贯穿着两种不同的修辞与逻辑站在“自然”一边反对“制度”,或者站在制度一边反对自然然而,“自然主义并不比约定主义更自然”因为制度保护的是法则总体的可能性:“通过禁止毒品,我们保障了有决断力的主体、公民及诸如此类的人们的正直和责任没有意识明确、警醒和正常的法定主体,即他或她自己意念的和欲望的主人,就不可能有法律存在”
然而与毒品相伴随的快感、欲望、幻想和逃离世界即使作为消极的自由,也作为重要的思想隐喻性的存在于文化现象之中比如,它存在于宗教和文学之中吸食毒品所造成的自我同世界的割裂,从现实中对自我的放逐,远离客观世界和真实而恼人的社会生活,进入一个幻影和虚构的世界,这些也是宗教和文学所允诺给人们的,也是文学在现代社会仍然迷人之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些特性不会遭受人们的谴责,尤其是在文学的形式中文学的虚构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文学和诗歌与致幻剂之间的幻想修辞仍然存在着区分,尽管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虚构的体验”文学不会使人彻底丧失现实感,他甚至能够生产一种新的结构,用以使复杂的现实得到理解,而且他是一个生产者,他的产品至少被理解为真实的一个特殊的资源,尽管文学的真实来自于虚构的媒介在文学中,虚构与虚构的体验的因为虚构主体所具有的生产性或创造性,因为这个创造虚构体验的主体所具有的更加复杂甚至可能是更加清醒的意识经验而重新获得了合法性,使他的活动产生了价值即使如此,文学和诗歌所具有的快感与游戏特性,它的虚构性和幻想,在人类历史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起诉如果诗人的作品没有在起码的意义上承担哲学家的政治学,没有承担载道的道德功能,那么诗人就会被认为沉湎于无益的幻象世界被逐出公共领域和共和国
文学家和诗人是虚构和虚构体验的主体,他是一个生产者,但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虚构体验的消费者,因此读者更接近从中吸食快感的消费者,更容易陷入不能自拔的幻象之中,人们常说某人书读得太多了,那口气就如同说“你(酒)喝得太多了”一样确实,即使在文学自身的历史中看,也有许多对沉湎于书本、陶醉于文字的幻象所伴随的批评,堂·吉诃德读了太多的骑士小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意识和现实感,包法利夫人读了太多的浪漫主义爱情小说以至不能生活在真实中在不同的程度上,文学作品成为毒品的一个修辞性的延伸,文学充当了制作美妙幻觉和致幻剂的功能作为虚构、虚构的快感和幻象世界的体验与表达,可以说诗歌和文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某些限制即使在文学的社会功能,娱乐、审美和道德教化等等功能之中,也一直存在着没有明言的虚构或文学的政治性问题表述的制度某些作品被接受的程度,某个历史时期文学本身被接受的程度都涉及到虚构的政治权利,或文学的政治性表述的制度即使文学被接受,文学也是在虚构的政治权利和表述制度本身的框架内的接受,这种制度区分出不同的领域,如私人空间和公共领域,娱乐和政治,叙事话语和论证话语,私人文本和权威文本等等之间的区别,允许虚构话语和虚构经验在不干预公共领域、论证话语逻辑和政治的权威文本的基础上拥有它的有限合法性就像宗教虚构叙述和启示性话语早已被合理化地驱逐出公共领域,而只能在它的信徒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一样在文学的虚构体验和幻象世界被社会作为惯例以制度化形式接受之外,仍然存在着被社会的某些核心部分秘密地、非公开地拒持在外的合法性
人类想以某种形式从日常体验中超越出来的欲望,不仅在宗教中得到了表达,而且也在其他世俗化的努力中得到了表达,它们可能深深地受到了麻醉性植物的影响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说,可能存在着一部与麻醉性植物有密切关系的人类“想象的自然史”,以及与麻醉性植物有关的“文学的自然史”、“宗教的自然史”或“哲学的自然史”在这么一部历史的某处,应该有谈论**和大麻在浪漫主义想象中的作用的一个章节许多浪漫主义诗人试验了它这些麻醉性植物在人们称为浪漫主义的“人类敏感性革命”中扮演着革命和启蒙的角色有人在柯勒律治的言论中认出了**和大麻的修辞学痕迹:想象是一种可以“消融、漫射、驱散”,以便来重新创造的精神能力,朝向偶然性、即兴和无意识领域不仅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立体派和爵士乐或者是摇滚乐,都得益于这种转换性想象的观念这些植物的生化毒素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诱导有机体突变的物质来起作用,它们是一些具有改变精神结构力量的化学物质,可以激发新的比喻、新的看事物的方式
曾经有过一个时代,所有的写作都作为一服良药呈献给国王与臣民,但在柏拉图看来,“写作”这服药无助于好的、真正的回忆,它总是充满遗忘和幻影,德里达写道:“正是凭着真正的、活生生的记忆和真实,才能指控写作这剂坏药是一剂不仅引向遗忘,而且引向不负责任的药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是漫游和玩耍迹象的孤儿状态写作不仅是一种药(毒药),也是一种游戏,如果不受对哲学真理关怀的制约,写作就是坏游戏于是在一个家庭情景的修辞学中,不存在对写作问题作出回答的父亲,也没有生动的、纯粹活生生的言语能帮助写作”有趣的是,德里达指出,不仅是昆西和阿尔托这些瘾君子的写作,从荷马到但丁这些在最肯定、最具有生产性、最不可简约的意义上的写作,这些占支配性地位的人物,也卷入了这一历史作家诗人所求助灵感、缪斯、神灵和精灵,并让自己的整个身心为这个幽灵所占据,“这是一种追随(“灵魂出窍的”)毒品某一天占据了空闲的位置的历史,或扮演一个衰弱的幽灵角色的历史这可能是一个方法上的挑衅,是一个召唤幽灵的技术问题:神灵、鬼怪、灵感和指令”诗歌是自我表达的领域,似乎也是一个幽灵般的“他者”的显现之地
写作一直是一个与身心的亢奋或恍惚状态有关的主题,这个写作自身的主题涉及“幽灵”和“本体论”,涉及一个二元对抗的观念谱系:虚拟和真实,自然与文化,自由与依附,解放与异化,公共和私密等等,这些两元对立的概念光谱也极其容易从一端过渡到另外一端从昆西和阿尔托,到福柯和德里达本人,都面临这个幽灵的诱惑:如果可能,无论在字面意义还是隐喻意义,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我们难道不应该尝试某种起支配性作用的历史,也就是说,尝试那些被称为(创造和寻求)“灵感的历史”这里隐含的问题似乎是:在对毒品所提供的“虚构的体验”中,什么依然是“令人亢奋的”“灵感状态”它与文学诗歌所产生的虚构体验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拿一片植物的叶子或者一朵花来改变我们的意识体验,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另外一种非常不同的圣礼,它与我们更为高傲的自我意识不同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写道:“我倾向于认为这样一种圣礼有时也是同样值得去做的,哪怕只是作为对我们狂妄自大的一种警示也是值得的植物们具有修改我们思想和感知的力量,可以激发隐喻和惊奇,这对于人们所看重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信念是一种挑战这种信念相信我们那个有意识的、思考着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自然界分离开的,而植物却使它达到了某种超越如果我们发现了超越本身来自于一些化学分子,它们流淌在我们的大脑中,与此同时也流淌在园子里的植物中,对于那种过分美化了的自画像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有一些最光彩照人的人类文化的果实事实上是深深扎根于黑土地,与植物和菌类有关的,人们会怎么想呢植物仍然会如同我们以前一直设想的那样沉默吗这是不是意味着精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尼采曾经给予狄俄尼索斯的陶醉以至高无上的艺术价值,把这样的陶醉描绘为“自然的无法抵挡的大脑”但对于希腊人来说,陶醉是一种谨慎限制的仪式,绝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使是那些认可这些植物的文化实践,也需要给它们的使用精心制作种种规则和仪式,作为容纳和规范它们的方式他们知道狄俄尼索斯的陶醉既可以使我们成为天使,也会让我们成为野兽而野兽是更加属于自然的且不说植物制造的高潮体验使人倾向于偶然性的行为,失去时空现实意识,陶醉是危险的,容易面临危险也易于成为危险
说实话,即使为了“精神目的”为了创作诗歌而使用麻醉品仍然让人觉得太过廉价,以此种方式所获得的想象力及其成果,如同一种赝品我始终没有愿望阅读《瘾君子自白》之类的作品,如果思想与感受成了一种受控的生物化学反应,而且引起感觉变化的化学物质来自于外面而非内部,那么精神创造活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事实上这种过程已经取消了自主的精神活动当一个人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可能是艰辛卓越的),从事心智的或道德的甚至英雄的业绩,他的内部也许会产生他无从知晓的生物化学反应,使他产生愉快的感受或陶醉感而社会对这样的负责任的行为所给予的肯定也使这样的陶醉感升华如果这个过程被倒置过来,注入某种可以引起生化反应的物质,使其产生升华感和陶醉感,那么这种快乐就是虚幻性的,没有了它的社会基础由于使快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