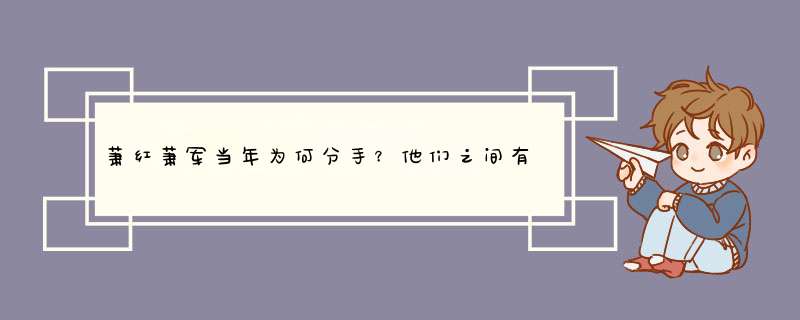
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萧军脾气太坏,经常沾花惹草。在萧红怀着孩子的时候,萧军会踢萧军,这让萧红对萧军彻底失望,没想到萧军会是这样的男人。萧军经常在外面和一些女人调情,尤其是萧红怀孕后,萧军也整天在外面闲逛,有时会整夜不呆在家里。
起初萧军和萧红都是进步的年轻人。见面后,他们发现他们对文学和社会的看法非常相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越来越了解对方,并逐渐有了良好的印象。
二、相识萧军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天才青年。当时,他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作品。中学时期,萧红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作品,积极参加抗日示威活动。这两个进步的年轻人在思想上非常相似,在文学上同样热情,并且有许多共同语言
来到上海后,萧红经常去鲁迅家,因为她有很多问题要问鲁迅。不管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在不在,萧俊乐是否不甘心,单纯任性的萧红很快就在圈子里对鲁迅有了越来越多的猜测。萧军迅速爆发,一天到晚嘲笑萧红。这种咄咄逼人的局面让萧红很生气,有几天没有回家。而萧军经常在外面通宵。肖红从八卦中了解到,萧军喜欢已婚女子。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三、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萧红觉得,她和萧军已经没有爱情了,与其留在痛苦中,不如分开。虽然这影响了她的创作,但萧红意志坚定,她的文字和生活一起脱轨。萧红始终坚持用文字独立表达她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不以任何力量转移。当时,萧红没有像萧军那样去当时的革命总部延安,而是来到了香港这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注定与萧军不是一路人。
楼上的大篇幅是在描述她的作品,请参考一下我的这个。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萧红一生都在渴望爱,追逐爱,但却被爱折磨得伤痕累累。
她坎坷的人生,正是因为从小缺失爱和温暖。
萧红在原生家庭中体会到的是父亲的残暴专横,和母亲的冷漠,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萧红本应该是刻薄、冷漠、退避、自私、怀疑和不敢爱。
但年迈的祖父给了年幼的萧红心中唯一的温暖和慰藉,让她相信世间还是有爱,她要不断去争取。
正是这缺失爱和温暖的原生家庭塑造了萧红孤寂敏感的性格。
幼年萧红
父母亲的冷淡和无情使得萧红对家庭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和抗拒,当唯一爱她的祖父离世之后,萧红也长大了,祖父给她的关爱是深刻的,也是她穷尽一生都在追寻的,萧红从未停止过对温暖和爱的追寻。
她的爱是盲目的、炽烈的,她一旦爱上,就不能自拔,试图在他们身上找到她童年失去的爱,结果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屡屡受伤。
剧照
原生家庭,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模样。
萧红是民国时期最出名的才女,文坛上的她风华绝代、光芒四射;但她却是一个不幸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家庭抛弃,原生家庭的阴影导致了她整个人生的悲凉。
作为一个作家,她终其一生书写故乡,却一路颠沛流离,最终客死他乡;作为一个普通人,她的内心无比渴望爱与温暖,却又不断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
萧红一生都只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剧照
这只能是她的企盼,孤独、寂寞、敏感的性格,贯串了她的整个人生,更深刻地影响到了她日后的情感生活和文学创作。
剧照
萧红带着无尽的爱恨与不甘永远离开了,她的坎坷人生从此画上了句号,年仅31岁。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萧红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她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时,鲁迅列举了茅盾、丁玲、张天翼、田军(萧军)等人,又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六年后,萧红于香港匆匆辞世,战争和疾病没有给她留下足够的时间“接替丁玲”。
不过,即便上天假萧红以时日,鲁迅的这一预言也终将落空。和丁玲不同,萧红很少直接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她被纳入左翼阵营,多是基于她与左翼作家的关系:她的爱人、朋友、导师,都属于这一阵营。萧红早期的创作,从主题上而言,关注底层,呈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死生挣扎,当然符合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萧红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仍带给左翼批评家们不少困惑和遗憾。胡风在肯定《生死场》的同时,也强调萧红的弱点,一是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二是人物性格不够突出;三是语法句法太过特别。换言之,就是萧红的创作主题不够突出,缺乏典型人物,语言不够精确,前两点恰恰是当时左翼文学主流最为看重的东西。
对于读者而言,萧红的个性化写作确实容易让人无所适从。梅志回忆当时读萧红的小说,感动喜欢之余,总觉得她的小说不连贯也不完整,不像小说的写法。这说法大概可以代表许多人初读萧红时的感受,《生死场》之后,萧红并没有依照左翼文坛的要求来改变自己,她对此的回应是:“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作,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民族战争兴起的1930年代,左翼文坛的中心词必然是政治、救亡、阶级、宣传、群众……而萧红却在纷飞战火中从《生死场》走向更为诗意、更为个性化、散文化的《呼兰河传》。难怪在抗战期间,批评家要指责萧红的创作消极、苦闷、与抗战无关。可以想见,这样的萧红,多半会与丁玲“擦肩而过”。
虽然未能取代丁玲成为左翼阵营中最有分量的女作家,但在建国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萧红毫无疑义地被纳入左翼作家的进步阵营并受到肯定。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学标准的《生死场》被视为其代表作,而《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名作此时则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马伯乐》,从诞生至八十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萧红除了是文学史上那个进步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萧红的名字最容易和她描写“火烧云”的一段文字联系,虽然他们未必知道这段文字的出处是《呼兰河传》。自1950年代初,这一片段便入选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汉学家葛浩文在翻译完《呼兰河传》后,曾拜访萧红笔下的龙王庙,那是1980年,龙王庙还是呼兰河的一所小学校所在,他在一个班上讲了几句话后准备离开,一个小朋友走来把他有多处磨损的课本递给葛浩文看,里头正有“火烧云”一文,这课本葛浩文一直保存至今。
从九十年代始,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
1938年,聂绀弩在与萧红分别时,做了个飞的姿势,并用手指着天空。这动作缘自两人几天前的一场对话,聂绀弩鼓励萧红像大鹏金翅鸟高飞,萧红却回答:“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也有她的友人曾说过,萧红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个女人。
自1990年代初起,身为“女性作家”的萧红突然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萧红的“女性”身份与其写作之间的关联。1989年,大陆学者孟悦和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将《生死场》解读为发自女性的历史诘问和审判,并认为至《呼兰河传》时期,萧红的女性主体思想已然成熟。对于学界而言,从女性写作、女性立场、女性主义等方面,重新阐释萧红成为热门,这一研究热潮持续到2002年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出版达一 。刘禾对《生死场》基于某种女性主义立场的精彩解读,展示了男性文学批评如何抹煞了萧红对主流话语的颠覆。
对萧红的女性身份的解读确实重塑了一个萧红,她的文字、她的家庭、她的情感、她的命运,在这一视角的关照下都有了新的解释,然而面对铺天盖地的女性视角的萧红解读,也许萧红自己并不会满意,毕竟,她在文学上的“野心”还不在此,她曾经为萧军、端木蕻良将他们的创作放在自己的之上而感到愤愤;也曾和友人谈起自己想要超越鲁迅,创作出比《阿Q正传》更了不起的小说。恰如她自己所说:“‘人生’并没有分别着男人或女人的。”
与学界的萧红研究热相反,1990年代熟悉萧红的普通读者却似呈减少之势。批评家摩罗在一次学术讲座中询问在座学生有多少人看过萧红,发现举手者寥寥。摩罗觉得“这正说明萧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大家的距离确实大了一点,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来关心萧红讲座的人肯定大部分都读过她的小说。“出现这一状况,或许与1980年代渐渐兴起的新的文学评判标准有关。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经过“重写”的现代文学史选择在“搁置”或“淡化”政治标准,突出“艺术”。此前备受冷遇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出口转内销”的成为热门作家,而左翼作家的创作则受到质疑。引发这一“转变”的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偏偏“遗忘”了萧红,“萧红的长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极具真实感,艺术成就比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高”,是他这本文学史留给萧红的仅有的评语。
事实上,在写作这本书后不久,夏志清便在《中译本序》中补充说明自己对萧红的疏忽是个错误,并在此后提到“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萧红仍然错过了这一次重写文学史带动的阅读热潮,在林贤治看来,和在左翼文学阵营中被低估了一样,萧红又一次成为这轮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但不可否认地是,从九十年代始,萧红在文学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理解,她创作中那些个性鲜明、曾被视为不合时宜的作品如《呼兰河传》,渐渐被推上现代文学经典的位置;而在张爱玲红遍两岸三地并被推为民国女作家第一人的同时,萧红的魅力则在较为小众和文艺的阅读圈中悄悄扩散。
民国热兴起后,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及相关史料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萧红热”
“萧红热”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
2011年,萧红诞辰一百周年,各种学术会议的召开、论文资料的出版,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同年,为纪念萧红而拍摄的**《萧红》关机。2013年,这部**选在三八节上映,虽然是标准的“冷门片”,上映前还是做了些宣传工作,宣传热点之一便是“文学洛神”萧红的浪漫情史——一她如何“点燃了六个男人”。
在此前后,“民国女性”已然成为阅读时尚之一。不论是因“绿茶婊”一词而躺枪的林徽因;还是被视为“最后的闺秀”的合肥四姊妹;或是张爱玲遗作陆续出版引发的阅读热潮;在“民国范儿”、民国教材、民国史等更大范围的“民国热”带动之下,民国女子们的才情和感情共同成为“八卦”的对象,而萧红的一生,恰恰不缺少这类“谈资”。
身为女性的萧红,感情世界的复杂暧昧,和相关史料的缺失,为这一轮萧红热提供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宋佳版《萧红》中萧红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之间的情爱关系本就充满戏剧感,再加上**中对萧红与鲁迅关系充满暧昧的“表述”,使得萧红的私生活俨然成为消费热点。
事实上,在对萧红的言说、书写中,相关的质疑和猜度一直存在。就鲁迅和萧红的关系而言,在1980年代之前的萧红研究中,着重于肯定鲁迅对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指点或精神层面的感召,多将其两人情谊定位为“师生”关系。而此后,对两者关系的阐释则更为复杂。余杰在其文章中声称自己怀疑鲁迅和萧红的情感超越师生,“还有别的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虹影也在其中篇小说《归来的女人》中以文学的方式对两人的关系进行大胆猜想。所持的依据也多来自萧红对鲁迅的回忆和许广平等人回忆中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在这一轮萧红热中,对萧红私生活的不满与斥责之声越来越大,张耀杰在《民国红粉》中直接用“智商极高而情商极低”总结萧红,并称之为“命贱”;端木赐香则宣称要“扒开萧红的洋葱皮”,认为萧红“只有叛逆的心与放纵的欲,就是没有自立的技能与自尊的身心”;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对《南方周末》记者称自己羡慕萧红的文笔,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妈妈,我非常鄙视她”,因为萧红曾在无奈中放弃自己的孩子。
不知萧红面对这些来自后辈,来自同性的道德谴责,会作何感想,倒是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在1990年代初,看到时人对萧红生活和作品的贬低时,曾做出回应:那些“自以为清洁”、“眼皮向上高举的人”,他们的“牙如剑,齿如刀,在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别人看低了,这都是徒劳的。”
端木的意思很明白,萧红的困苦与穷乏,却成了那些自以为清洁的人看低她的资本。
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女性、革命、自由、爱情,叛逆、逃亡、寂寞、温暖……,每一个词放在萧红身上都别有意味。葛浩文曾说我们很难对萧红在中国20世纪文坛地位下一放之四海皆准的断语,但她至少留下了三本或更多传世的作品。《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有了这些,萧红的身影或将永远有人摹画。
而关于她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一则是:
林斤澜回忆文革中自己下放农场,被派到果园守夜,摸黑闲聊,说及三十年代的女作家,文采数萧红第一。有人斟酌,历数女作家。骆宾基大声喝问:男作家又怎样?气势仿佛兴师动众。林斤澜回答男作家排名已定,鲁郭茅巴老曹。“骆宾基倒吸一口气憋住,喉间犹有喘息”。
我觉得,骆宾基的不甘,也正是萧红一生的不甘。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