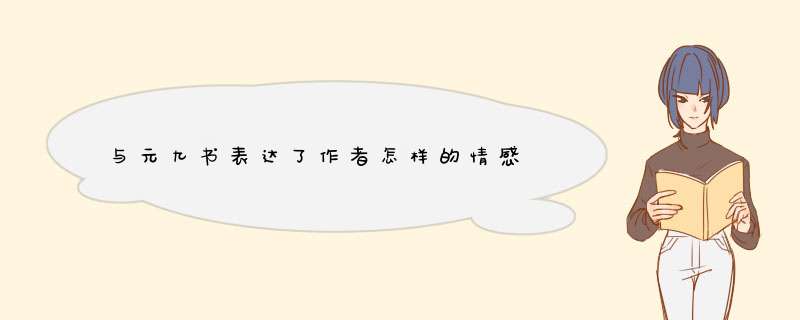
元九是元稹,《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寄给元稹的一封信,白居易在信里向元稹表达了自己在诗歌理论以及人生观。
这首诗创作于公元810年(唐宪宗元和五年),当时白居易三十九岁,在朝中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对好友的无限思念,无限关心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明确说出,作者只是写自己写完书信后,将信纸装入信封:又觉得似乎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完,似乎还应当补充或修改些什么,于是又把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但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什么。
因此心潮不定,思绪万干,茫然不知所从。诗人这时具体都想了些什么,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其他诗中推断出来。例如,这里有作者对元稹生活起居的关心,如作者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犹恐清光不同见,江陵卑湿足秋阴”;更有作者对元稹不幸遭遇的同情和他对朝廷里那股恶势力的无限愤慨,正如作者在另一首诗中写道:“况在名利途,平生有风波。
“深心藏陷阱,巧言织网罗”。此外也有作者对自己从前思想行为的总结回顾,和自己日后究竟当怎样生活、怎样处世的展望。因为作者写了《秦中吟》,已经使“ 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由于作者写了《登乐游苑望》又使“执政柄者扼腕矣”;而《宿紫阁山北村》更使“握军要者切齿矣”。
白居易和元稹,他们两个之间的友情,值得为后人称颂。他们两个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个诗会上,他们两个刚好坐在彼此的对面。本来白居易很不愿意参加诗会这种活动,在诗会上大家都有着自己各自的观点,表面上和和气气,但是内心却极为不合。但是白居易当时在诗词界有一定的地位,他不得不来。在这场诗会上,他感觉到很无聊。但正是因为这一次诗会,让他交到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元稹。
当时的白居易已经名满长安,他从小就是一个十足的学霸,在做诗上非常有天赋。他写的诗句被百姓广为传颂,他在世人心中已经是一位大诗人。而且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考中了进士,是当时最年轻的进士。在当时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但是就是因为年少成名,白居易心里也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
和白居易不一样的是,元稹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名气。但是在白居易第一眼见到元稹的时候,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元稹这个人虽然说话很少,但是说出来的话很有水平,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这次诗会上,元稹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向清高的白居易,在见到元稹之后,主动要求和他交换联络方式。他们两个在诗会上也讨论了对于诗词改革的看法,他们两个的看法惊人的相似,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这一次诗会之后,他们两个也一起相约讨论诗词,后来最有缘分的就是在科举考试放榜的那一天,白居易在大榜上看见了元稹的名字,元稹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走上了仕途。
后来最有缘分的是,他们两个被一起任命为校书郎,被分配在同一个部门,在同一个职位一起工作。他们两个在一起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两个人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却有高度的默契,对待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很契合。正是因为有了两个人彼此的陪伴,所以在工作上也更加顺心,他们两个在工作上相互鼓励对方,在生活上也经常一起谈诗喝酒。
他们两个在一起总能碰撞出许多新的想法,共同倡导了科策。但是他们两个在官场上却并不顺利,都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但很有缘分的是他们两个连升官和贬官的时间都一样,在白居易被贬官的时候,恰巧元稹也遭遇变故,他们两个可谓是难兄难弟。在两人同时被贬去不同的地方后,他们两个也没有断了联络,经常通信,信件超过了一千多封。彼此被贬官的痛苦和心中的孤寂只能和彼此述说,他们永远是最懂彼此的那个人。共同经历了官场的黑暗,也一起倡导过诗歌的改,他们是彼此人生路上扶持的知己。
他们在一起也编撰了诗集,对中国古代的诗词史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在看到他们来往时所写的诗句时总会被感动。他们两个在经历磨难之后仍然相互扶持,热爱生活,正是有了彼此的存在才能让生活变得美好,消除痛苦。就算后来身处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两个的默契依然没有减少,总是能第一时间准确的猜到彼此的想法,这就是灵魂真正契合的好朋友。元稹和白居易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驿站的途中,他们当时想尽了办法,才最终见面。见面之后,两个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每当谈起彼此各自贬官时的经历时,都会泪流满面。这也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会面,在不久之后,元稹就去世了。白居易听到元稹去世的消息时悲痛不已,整个世界都要坍塌了。亲自赶到元稹的墓前为他撰写墓志铭,留下了现在仍感人至深的诗句。
后来白居易的一生都在怀念元稹,每当听到别人吟诵元稹的诗时都会泪流满面。他最好的朋友先他一步走了,从此以后整个人生就剩下了他自己。元稹死后,白居易的诗也多用来怀念他。没有了元稹的陪伴,白居易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也少多了。他感慨自己的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遇见陪自己走过所有磨难和幸福的好朋友元稹。白居易经常去他们一起走过的地方回顾他们两个走过的路,创作了许多令后世感动的诗篇。一辈子清高孤独的白居易遇到元稹,是他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元稹为人刚直不阿,情感真挚,和白居易是一对挚友。白居易这样评价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并说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而元稹对白居易关心,更凝结成了千古名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除了流芳千年的“元白之谊”,元稹和妻子韦丛的半缘情深也为人津津乐道。
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小女儿年芳20的韦丛下嫁给24岁的诗人元稹。此时的元稹仅仅是秘书省校书郎。韦夏卿出于什么原因同意这门亲事,已然无考,但出身高门的韦丛并不势利贪婪,没有嫌弃元稹。相反,她勤俭持家,任劳任怨,和元稹的生活虽不宽裕,却也温馨甜蜜。可是造化弄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韦丛因病去世,年仅27岁。此时的31岁的元稹已升任监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爱妻却驾鹤西去,诗人无比悲痛,写下了一系列的悼亡诗。最著名就是:
《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用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来表达对亡妻的无限怀念,任何女子都不能取代韦丛。
不过也有人说元稹的作品与真人并不相符 这些可以信但又不可全信
白居易和元稹是爱情吗:不是,元稹和白居易是同门关系。
扩展知识
1背景介绍
白居易和元稹皆为唐朝初期著名诗人,两人之间传闻有着奇特的关系,尤其是在他们在官府工作期间,两人更是同事兼好友,素有“元白之好”之称。但是,对于两人关系的真实性质,历史上并没有可以证实的记录。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史料中所留下来的信息来推测他们的关系。
2知情人的回忆
《白氏长庆集》中有一首题为《哀愁引·元稹游池上》,内容叙述了白居易和元稹在一起赏花赏草的情景,其中写道:“五陵年少思悠悠,恰足风流半醉楼。轻摇玉扇逐香风,花烟弄月池塘头。”这首词仔细揣摩,个人感觉描述的有些暧昧,但具体是否有爱情因素参杂其间,仍不确定。
3诗歌解读
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被许多研究者通过他们的诗歌得出了一些结论。例如《元稹集》中收录了一首关于白居易的诗,写道:“正直如坚石,烦劳似浊流,千里来相送,更恨别离愁。”这样一首诗歌,其表达的情感令人无从分辨是否是友情或者爱情。
4史学家的观点
在学界中,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一些史学家认为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同性恋关系,但是鉴于唐朝时期的封建礼教和道德限制,两人并没有真正发生肉体上的交往,只是彼此之间情感上的依赖和信任。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表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同袍之谊”,彼此相互扶持、忠诚和信任,并没有发展成为爱情关系。
5结论
综上所述,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我们无法确定白居易和元稹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其是否涉及到爱情因素也缺乏确定的证据。因此,我们需要避免进行主观臆断,尊重历史事实,并保持对历史和文学高度的客观性和理性。
我觉得说到这个问题,我真的是要点名表扬一下苏轼苏辙。这两个人虽说是兄弟关系,但是这一对文人兄弟的手足之情也真的是个典范了。这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热恋中的情侣一般情深意切,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对文人兄弟吧。
首先素食是苏辙的哥哥,他们之间差两岁。从年龄差上来看,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同龄人了,所以,交流起来应该也没有什么代沟。苏轼和苏辙是同一件高中进士的,一起当了官。在当官期间,这两个人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那真的是叫一个默契。就像是热恋中的两个人谈诗作赋一般那样和谐美妙。
在当官这条路上,这两个人的追求差不多,目标也比较一致。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却是截然相反的,苏轼的性格是那种比较锋芒毕露的那种,但是苏辙这个人的性格比较温顺而且很谦虚。苏轼的仕途之路也是非常的坎坷,各种贬谪各种被诋毁。但是苏辙就很稳当,一路顺利的升到了副宰相。
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被关进了牢狱。苏辙也没有停止为自己的哥哥辩解,他也是付出自己的一切,想要让哥哥出狱。甚至还写了一篇《为兄轼下狱上书》,这篇文章写的是真卑微,一字一句都显得那么让人心疼,虽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苏辙的这篇文章确实是看了让人难过。而且,他们兄弟俩一有机会就在一起聚会,但是毕竟聚少离多,也是很心酸。
元,指元稹;白,指白居易;郊,指孟郊;岛,指贾岛。
“元轻白俗”是对元稹和白居易诗风的评语,谓前者轻佻,后者但俗。元稹和白居易后被誉为“元白”。
“郊寒岛痩”是对孟郊、贾岛简啬孤峭的诗歌风格的评价。因为二人作诗都是苦吟,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特征都比较相似;另外,二人的身世遭遇也有诸多相似之处。
出自宋代苏轼的《祭柳子玉文》,选自《东坡全集》。
扩展资料
苏轼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存诗3900余首。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
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的并称“苏黄”。在书法方面开创“尚意”书风,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是苏洵的次子,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曾在立新法中反对王安石,被贬到黄州。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苏轼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中,合称“三苏”。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元轻白俗
对唐代诗人元稹和白居易诗风的一种评语,谓前者轻佻,后者俚俗。
“元轻白俗”。元诗“轻”大概指有些作品“轻佻”、轻薄,如《会真诗三十韵》等艳情诗,这是中唐文学世俗化的表现之一。另外可能也与《莺莺传》 (又名《会真记》)的影响有关。“白俗”指白诗通俗平易。
同意这个《会真诗三十韵》: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栊。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帝宫。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警乘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
李肇提出元稹诗章“*靡”,那么“*靡”的本义到底是什么呢?元稹诗章“*靡”又是指什么呢因为诗章既包括内容,又包括语言形式。说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诗歌的内容,还是指元稹诗歌的语言,亦或是兼而有之?由于元稹曾作过“艳诗”,并且影响很大,人们首先把“*靡”和“艳诗”的联系起来。如周勋初先生就认为:“说元诗‘*靡’,主要指内容而言的;……可见十体之中,五、七言今体艳诗和五、七言古体艳诗发生的影响尤为巨大,所以《国史补》中标举‘*靡’二字,用来概括元诗的特点。”[1]周勋初先生又引杜牧《李戡墓志铭》中李戡的话加以强调。按周先生之意,元稹诗章获得“*靡”声名乃因为其“艳诗”,“*靡”乃针对元稹诗的内容而言的。
要弄清元稹诗章“*靡”的具体内蕴,不得不提到杜牧、李珏,因为除了李肇的评价外,唐杜牧和李珏也都曾评价过元稹的诗章,并且,杜牧、李珏二家的评价一出,后人往往引用他们的话来贬低元稹的诗。杜牧、李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和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评价元稹的呢?他们的话真的能够用来说明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诗的内容吗?如若“*靡”不是指元诗的内容,那又是指什么呢?
为此,有必要就李肇、杜牧、李珏与元稹的关系做一番考论,看看实际情况若何;再就“*靡”的具体义蕴作一番溯源性探析,再看看元稹同时代的人及后人对元诗的评价;由于人们易把元稹“艳诗”与“*靡”挂起钩来,因此,同样有必要对元稹“艳诗”的实情作一番考证;最后就元稹诗章的语言实际情况作一分析,以明确“*靡”的具体所指。
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李肇、杜牧、李珏对元稹诗歌评价实情考辨
首先考察李肇对元稹诗歌的评价。
李肇,史书记载不多。我们从现存资料可知其与元稹生活在同一时代,并且同在朝廷做官。考察李肇与元稹的关系,李与元相互关系还不错,或许还可以说李肇与元稹是相知的。何以见得?这可从元稹密友李景俭“醉酒骂宰相”一事的前因后果中探知。
长庆元年(821年)二月,元稹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穆宗常向元稹“访以密谋”,深得宠幸,随时有升任宰相的可能。(元稹《翰林承旨学士记》)。元稹与裴度有隙——由于长庆元年的进士考试被段文昌告以不公,元稹、李绅、李德裕赞成重试,经是年四月白居易、王起的重试,裴度的儿子裴撰被黜落;裴度是宪宗朝功臣、元老、宰相,十分恼怒,以此裴度怀恨在心。——十月,裴度劾元稹交结宦官,“挠乱国政”,元稹罢翰林学士,为工部侍郎。元稹密友李景俭为好友元稹的遭遇鸣不平。“其年(长庆元年)十二月,景俭退朝,与兵部郎中冯宿,……司员贺外郎李肇,……同谒史馆独孤朗,乃于史馆饮酒。景俭乘醉诣中书谒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颖名,面疏其失,辞颇悖慢,宰相逊言止之,旋奏贬漳州刺史。是日同饮于史馆者皆贬逐。”[2](P4456)(《旧唐书·卷171·李景俭传》)“贬司勋员外郎李肇澧州刺史,坐与李景俭于史馆同饮,景俭乘醉见宰相谩骂故也。”[2](P493)(《旧唐书·穆宗本纪》)当时白居易做中书舍人,上《左降独孤郎等状》为独孤朗、温造、李肇、王镒鸣冤。两个月后,即长庆二年二月,元稹出任宰相,立即召回李景俭,复为谏议大夫;李肇虽未被召回,勋位却得到升高,任中散大夫。(见白居易《李肇可中散大夫郢州刺史王镒朗州刺史温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独孤朗、温造、王镒等为元白好友,李肇与之饮酒并同被贬,可知李肇同情元稹并且与元稹友善;元稹作宰相,李肇马上得到升勋的好处,须要指出的是,“升勋”发生在被贬的两个月后,这也能说明元稹与李肇即使不是相知也是同道之人。
既然元稹与李肇乃同道之人,很难令人相信他会特意批评元稹的“艳诗”,并把元稹诗章“*靡”之“*靡”当成后人望文生出的含义“*秽靡烂”。
考诸史实,元稹在元和间已获得“元才子”的称号,但元稹获得“元才子”的声誉并非仅其“艳诗”,据元稹元和十四年写给当时宰相令狐楚的《上令狐相公诗启》可知,给元稹带来声誉的主要是其元和五年至元和十五年间作出的长篇排律与写景抒情的小碎篇章。《旧唐书·元稹传》也说:“稹聪警绝人,……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既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俄而白居意亦贬江州司马。虽通、江悬邈,而二人往来赠答,凡所为诗,有自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者。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 元稹的长篇排律与写景抒情的小碎篇章,很多是抒发自己的高洁志趣、贬逐的忧伤及朋友之间的友情,是这些感人的诗篇让元稹获得崇高的盛誉。就连令狐楚在读了元稹进的诗歌后,就“深称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李肇岂能避开这些事实,独批评其“艳诗”。如果元稹的声誉来自其“艳诗”,并且其“艳诗”“*秽靡烂”的话,宰相令狐楚岂不会以“伤风化”为由治元稹的罪吗?如不治罪,宰相就失职了,令狐楚担当得起失职的责任?正因为元稹的声誉不来自“艳诗”,宰相令狐楚才会“深赏”之,才会有令元稹给他献诗的要求。
既然元稹的传闻天下的并且让时人摹仿的诗篇是那些“状咏风态物色”的“小碎篇章”和抒写“流离放逐之意”的“三十、五十韵乃至百韵”的长篇排律,李肇独拈出元稹的“艳诗”并加以指责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再则,如果说元诗“*靡”是指其“艳诗”并且“*靡”的含义是“*秽靡烂”的话,就不符合李肇对元和文坛的整体风格的评价即“尚怪”了;因为“*靡”的含义若取“*秽靡烂”的话,“*靡”二字是“尚怪”二字无法概括的,“尚怪”显然没有包含“*秽靡烂”的意思。
因此,李肇的元诗“*靡”说是否指元诗内容就值得一问,或者说,我们还不能轻易断定李肇的“*靡”说是指元稹诗歌的内容。我认为元诗“*靡”应当另有所指。
再看杜牧对元稹诗章的评价。
杜牧(803—852年)对元稹诗章的评价特低,认为其诗“纤艳不逞”、“*言媟语”。首先要指出的是,杜牧对元稹诗章的指责是杜牧倾泻他对元稹的私恨,是因党派斗争的缘故而作出的不真实的评价。凭何而知?先看杜牧在开成二年(837年)作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其中写道:
“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人雅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3](P88)
刘熙载《艺概·诗概》言:“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4](P64)(笔者按:《唐书·白居易传》指《旧唐书·白居易传》)刘熙载认为杜牧的话是文人相轻的结果,这还不准确,实际上,是因白居易做诗《不致仕》讥讽杜牧祖父杜佑,杜牧耿耿于怀,借李戡之口,主要是发泄对白居易及白的友人元稹的不满及仇恨;这种发泄是巧妙的(通过李戡之口说出),因这时白居易还健在,不过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元稹已于六年前(831年)去世了。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完成于元和五年暮春之前,其五《不致仕》写道: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白居易《秦中吟》一出,影响很大,“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6](白居易《与元九书》)不过,白居易也没冤枉杜佑,据《旧唐书·杜佑传》[7](P3978)载:
贞元十九年(803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69岁)
元和元年(806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卦岐国公。(72岁)
元和二年(807年),十一月,诏杜佑每日入中书视事。(73岁)
元和七年(812年),被疾,六月,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78岁)
元和七年(812年),十一月,薨,寿七十八,废朝三日,册赠太傅。(78岁)
按礼制规定,大臣年满七十应该主动退休,杜佑年高而不退休(直到七十八岁高龄,去世前五个月才因病离职),贪恋禄位,不仅白居易不满,裴度也曾借给高郢写致仕制的机会讥讽他。据中唐李肇《唐国史补》“高郢致仕制”[8](P40)载:
高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闻。近代寡廉,罕由期道。”是时杜司徒年七十,无意请老。裴晋公为舍人,以此讥之。
高郢元和五年九月致仕,杜佑此时年已过七十五,还在执政,因此被裴度讥讽。
白居易做诗讥讽杜牧祖父杜佑,杜牧岂能不知。因此,杜牧是借李戡之口来发泄对白居易的愤怒,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诗风相近,同在元和、长庆文坛享有盛誉,同遭指责;所以,周勋初先生把杜牧的话用来证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诗的内容是不公正的。有趣的是,李戡的话却说明了元白诗的流传广,影响深。
(上引李肇《唐国史补》“高郢致仕制”这则材料显示,李肇从裴度的制文中看出裴度在讥讽杜佑,并把这一发现以正史补的名义写入《唐国史补》,还可以说明李肇与元白都对“年高而贪恋禄位”的杜佑都很鄙视,也间接表明李肇与元白相善。李肇与杜牧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骂元白。)
杜牧对元白的指责还当与牛李党争有关。据《资治通鉴》卷244载:“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9]《新唐书·杜牧传》:“牧字牧之,善属文。……又为牛僧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10]牛僧孺为牛党的领袖,杜牧做其属官,自然也就卷进了牛李党争,在这种情况下,杜牧对属李党的元稹以及元稹的朋友白居易(白居易倾向与牛党)也就不会有好的评价了。
当然,元稹也确实作了象《春晓》、《梦游春七十韵》、《会真诗》那样的艳诗,白居易也作了一些艳诗,如 《长恨歌》、《和梦游春一百韵》。元白好作爱情题材诗,好作艳诗,是受了当时市民文学的影响,不过,元白诗也只是刚露出了一点市民文学的苗头,那些被指责的庸俗的色情描写是少的;元白“艳诗”中的用语或许还可以说是含蓄的。元白充满“*言媟语”的艳诗毕竟是少数,更何况元稹作艳诗,本在风教。
杜牧指责元稹诗“*言媟语”,当然是针对元诗中的艳诗而言的,前面已说过元稹充满“*言媟语”的艳诗只是少数,杜牧不顾及“元和体”中那些优秀的诗歌,不顾及象《连昌宫词》那样的杰作,咬牙切齿地说,“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借李戡之口说出的一席话,能不让人觉得他是在发泄私恨吗?杜牧的指责,是不公正的,同时也让人觉得他缺乏君子风度。按照杜牧的标准,他自己的诗作不是也有一些充满了“*言媟语”吗?也应当“用法以治之”。
当然,平心而论,杜牧的指责也并非全无道理,元稹的《会真诗》铺叙了性爱内容,可以说是“*言媟语”,我想说的是元白的诗可以指责的是少数,杜牧的话过分了。
李珏对元稹诗歌的评价又如何呢?
李珏(784—853年),文宗开成年间宰相。李珏对元稹诗歌的评价如同杜牧对元稹诗歌的评价一样,很低。李珏认为元稹乃“轻薄之徒”,其诗好“摛章绘句”。与杜牧对元稹的讥讽情况相似,李珏对元稹人格的污蔑和诗歌的鄙视是牛、李两党在政治斗争中相互倾轧的表现。
据(宋)王谠《唐语林》二文学类“文宗欲置诗学士”[11](P149)条载:
文宗好五言诗,品格与肃、代、宪宗同,而古调尤清峻。尝欲置诗学士七十二员,……李珏奏曰:“……臣闻宪宗为诗,格合前古,当时轻薄之徒,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实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玷黯皇化,实非小事。
有人认为“摛章绘句”、“聱牙崛奇”指韩愈的“奇诡”与孟郊的“矫激”,“讥讽时事”指元稹、白居易、张籍等作的讽喻诗。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元和体诗”引李珏的话,他在“摛章绘句,聱牙崛奇,讥讽时事”之后注“此指玉川子《月蚀诗》之类”[12](P349)。卢仝《月蚀诗》虽有“聱牙崛奇,讥讽时事”的特点,但李珏特别提到“尔后鼓扇名声,谓之元和体”,考虑到元稹、白居易乃元和文坛的主盟,“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元和体”确肇始和形成于元白,因此李珏所说的“轻薄之徒”是指元白,“轻薄”乃是对元白的攻击。
李珏为什么要攻击元白呢?原来,李珏的话也含有党争的火药味。《新唐书·李珏传》:“李珏字待价,……珏以数谏不得留,出为下邽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书记。还为殿中侍御史。宰相韦处厚曰:‘清庙之器,岂击搏才乎?’除礼部员外郎。僧孺还相,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为翰林学士,加户部侍郎。……及李宗闵以罪去,珏为申辨,贬江州刺史。……开成中,杨嗣复得君,引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李固言皆善。三人居中秉权,乃与郑覃、陈夷行等更持议,好恶相影和,朋党盖炽也。……”[13](P5360)杨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雅相善”。由此可知,李珏属于牛党,并且是牛党重要人物。据《旧唐书·李绅传》:“穆宗召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情意相善。” 因此,元稹乃李党人。李珏属于牛党,自然也就对“元和体”的代表、李党人物元稹持否定态度。李珏反对文宗立“诗学士”,目的乃防止李党人物借机主政。可见,李珏的攻击夹杂着党争因素。
李珏指责元稹诗歌“摛章绘句”,倒也看清了元稹诗好雕琢语言的特点。在语言上的雕绘本也是元稹所长。
据以上考证可知,李肇的元稹诗章“*靡”说不大可能是指责元稹的“艳诗”;个人的恩怨,党争的激烈是造成杜牧对元稹作出不公正评价的缘故;李珏的指责夹杂着明显的党争的因素;因此,杜牧与李珏的话不应当用来作为元稹诗章“*靡”是指元稹的“艳诗”的理由。
二 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
——“*靡”的含义溯源及元稹同时人与后人对其诗的评价
先看“*靡”的含义。
据《辞海》(1989年版)可知,“靡”有①倒下②奢侈③华丽等意思。与“靡”结合的常用词语,如“靡丽”,奢侈,华丽;“靡曼”,美丽;“靡靡”,行动迟缓,柔弱,富丽。
“靡”用来修饰文学作品,是“美”的含义。如陆机《文赋》云:“言徒靡而弗华。”五臣注:“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华也。”[14](P51)“诗缘情而绮靡”,“绮靡”之“靡”也作美丽讲,诗歌因情而生,当然要求文词鲜艳美丽。《诗品》评宋征士陶潜(372—427年):“至如‘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15]“清靡”是说陶潜诗“清新美好”。《诗品》评鲍煦:“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元之靡嫚。”[16]“靡嫚”也指辞采美丽。《诗品》评江祀诗“明靡可怀”,“明靡”乃明媚美好意。
据《辞海》(1989年版)可知,“*”有①浸*②长久③沉溺④邪恶等意思。与“*”结合的常用词语有:“*巧”,过于奇巧而无异之物;“*祀”,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祠”,滥建的祠庙;“*辞”,夸大失实之词等。
“*”用来修饰文学作品,多做“过分”讲。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艳,倾炫心魄,……斯鲍照之遗烈也。”[17]“雕藻*艳”是说辞藻过分美丽,并未含太多贬义;虽说是“鲍照之遗烈”,但鲍照(414—466年)的诗用的词是优美的,“为诗欲词格清美,当看鲍照、谢灵运。”[18](P66)
“*”与“靡”连用来修饰文学作品,当指辞采过分绮丽。其实,用“*靡”来形容某人的诗章,不是始于李肇,钟嵘就用过。钟嵘《诗品》评齐惠休上人:
“惠休*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颜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19]
钟嵘《诗品》卷下在评价齐的另七位诗人时提及惠休:
“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殆已动俗。唯此诸人,傅颜、陆体。用固执不如,颜诸暨最荷家声。”
(梁)沈约(441—513年)《宋书·徐湛之传》曰:“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20](P1847)
钟嵘所评的“齐惠休上人”也就是沈约提及的“沙门释惠休”,惠休本姓汤,字茂远,宋孝武帝(454—465年在位)命始还俗,官至扬州从事史。钟嵘对惠休的评价是“*靡”,沈约的评价是“辞采绮艳”;又惠休可和鲍照匹敌,而鲍照为诗“词格清美”,可见“*靡”应等同于“辞采绮艳”。
因齐粱才大规模兴起宫体诗,沈约被称为宫体诗的“始作俑”者,惠休诗歌在大明、泰始(457—472年)年间获得“美文”声誉时,沈约才二十多岁。由此可见,惠休诗“*靡”并非因“宫体艳诗”而得。
所以,“*靡”是可单用来修饰辞采的,意即“辞采美丽”。
“*靡”最初是用来形容诗歌的语言美的,为什么我们一见到李肇评元诗所用的“*靡”,就立刻把它等同杜牧所说的“*言媟语”呢?李肇评元诗所用的“*靡”二字不应等同杜牧所说的“*言媟语”;元诗“*靡”是指元稹诗章辞藻绮丽。
说元诗“*靡”是指元稹诗章辞藻绮丽,这还可以从元稹同时代的人及后人的评价中得知。
下面看看元稹同时人与后人对元诗的评价。
元稹诗章得到时人及后人的高度评价,元稹被推为“元和主盟”,《旧唐书·白居易传》:“若品调律度,扬搉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有人赞美元诗“有风骨”重风教的,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连昌词》似胜《长恨歌》,非谓议论也,《连昌》有风骨耳。” 但人们赞美的焦点却在元稹诗歌语言的优美上。如:
刘禹锡称赞元稹诗:
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
纵使真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
——《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
白居易赞曰:
“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
——《〈放言五首〉序》
“词飘朱槛底,韵坠绿江前。”
“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
“收将白云丽,夺尽碧云妍。”
“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
——《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
“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
——《酬微之》
韦縠赞曰:
“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 [21]
——《才调集序》
李恒赞曰:
“(元稹)游戏资身,明经筮仕,累应科选,盖振芳华。茂识宏才,登名曹董之列;佳辞丽句驰声谢鲍之间。……”[22]
——《元稹同州刺使制》(《全唐文》卷六十四)
(宋)曾巩也曾赞元稹诗,据潘淳《潘子真诗话》载:
“南丰先生、曾子固言阿旁宫赋。……又言《津阳门诗》、《长恨歌》、《连昌词》俱载开元、天宝间事。微之词,不独富艳,至‘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委任责成,治之所兴也。‘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险诐私谒,无所不至,安得不乱。稹之叙事,远过二子。”[23](P303)
——《潘子真诗话·杜牧赋元稹诗》
(宋)洪迈赞曰:
“唐人播之歌诗,固亦极挚。……‘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元稹《连昌宫词》)。此皆李、杜、元、白之丽句也。” [24](P675)
——《容斋五笔·卷四·作诗旨意》
刘禹锡赞元稹诗章有如“锦绣堆”,“文章似锦气如虹”;白居易对元稹诗章倍加推崇,“句句妍辞缀色丝”;韦縠说“词丽而春色斗美”,元诗美丽的词句艳如五彩斑斓的春天;李恒赞元稹词美可比谢灵运、鲍照;南丰先生、曾巩(子固)说元稹诗“富艳”;宋洪迈说元诗有“丽句”。由此可见,元诗辞藻的优美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
又如晚唐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一文中所赞:
“余常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喻,谓之闲适。即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25]
此段话也含着这样的重要信息:元稹诗章语言“靡”、“丽”。皮日休指出当时人只知道学习元白语言的“靡”“丽”却失去了其“立教”之旨,所作诗只是虚得“元白体”之名,并且损害了“元白”之名;元白诗章不仅在于立教——政治与思想道德教化,而且“词”雍容宛转。皮日休说的“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明确地说的是元稹诗歌的语言具有“靡丽”的特点,皮日休和元稹生活的时代接近,其说当值得可信。
唐李商隐的一段话也可证元稹诗歌语言“绮靡”的特点。李商隐(813—858年)在《献侍郎钜鹿公启》中曾说:“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因元稹曾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杜甫推崇备至,“推李杜”者自然指元稹等人,“怨刺居多”指元稹的新体与旧体乐府;“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沈佺期、宋之问完善了律诗,元稹擅长律诗,并开创了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可为“效沈宋”者,“绮靡为甚”是说元稹的律诗语言特别美丽。
总之,元稹的诗显示出了他高超的语言艺术,元诗词句优美,得到时人及后人由衷的赞赏。“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名不虚得。
三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论元稹的“艳诗”与教化
元和十年(816年),元稹三十七岁,他在四川通州给白居易写了一封信,名《序诗寄乐天书》,书有言:
“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余首。词有今古,又两体。”
元稹艳诗现存的主要有《有所教》、《离思五首》、《白衣裳二首》、《杂忆五首》、《恨妆成》、《闺晚》、《会真诗》、《梦游春七十韵》、《古决绝词》、《刘阮妻二首》等。韦縠《才调集》共选诗一千首,选元稹诗五十七首,其中就包括前面列举的二十二首,韦縠乃晚唐人,元稹艳诗的精华当保存在《才调集》中。后人可以由《才调集》推知元稹艳诗的主要情况。
元稹艳诗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女子的外貌、神态、气质,意在干教化;二是大胆写男女性爱,数量少,似乎仅有《会真诗》,但却格调高雅,艳丽而不邪。
试看元稹的第一类艳诗: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有所教》
山泉散漫绕阶流,万树桃花映小楼。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
——《离思五首》之二
红罗着压逐时新,杏子花纱嫩曲尘。第一莫嫌材地弱,些些纰缦最宜人。
——《离思五首》之三
雨湿轻尘隔院香,玉人初着白衣裳。半含惆怅闲看绣,一朵梨花压象床。
——《白衣裳二首》之一
藕丝衫子柳花裙,空着沉香慢火熏。闲倚屏风笑周昉,枉抛心力画朝云。
——《白衣裳二首》之二
山榴似火叶相兼,亚拂砖阶半拂檐。忆得双文独披掩,满头花草依新帘。
——《杂忆五首》诗之四
春水消尽碧波湖,漾影残霞似有无。忆得双文独披掩,钿头云映退红酥。
——《杂忆五首》诗之五
芙蓉脂肉绿云鬟,掩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
——《刘阮妻二首》之二
以上是近体诗。
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
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
满头行小梳,当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