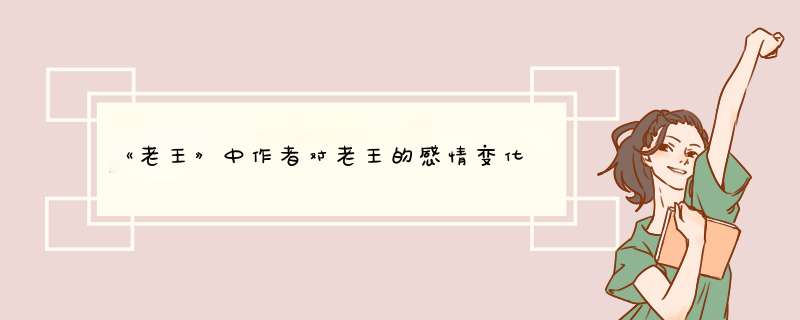
《老王》中作者对老王的感情变化:同情——尊敬——愧怍。
《老王》是著名作家、文艺翻译家杨绛写的一篇写人记事的散文,作者笔下的老王是一个命苦心善的不幸者,在荒唐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精神世界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善良诚实,忠厚老实,知恩图报。
。如此足以表达“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突出关怀不幸者的写作意旨”。然而,杨绛先生采用了“愧怍的结尾”。“杨绛的‘愧怍’”更是一种深刻的反思!内心反思、自我批判才会诞生“愧怍”。
文章的语言像是淡淡的带有某种吝啬的闲聊,比如“我常坐老王的车”、“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恶病,瞎掉了一只眼。”而作者觉得老王瞎了眼很是不幸、“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等等。字里行间表述的虽是对老王的关心和同情,然而这种闲聊式的叙述似乎也在隐约地流露着另一种情感,即作者对老王的凉凉的不曾被感动的情感,这是作者刻意要表现的,是她在对老王认识的反思后对自己的“麻木”、“吝啬”、“冷漠”的情感进行自我批判。比如送冰的事:“老王愿意给我们家代送,车费减半他送的冰比他的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这件事让作者对老王的认识只是“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紧接着说“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没想到这点。”更充分说明这一点。其实老王要为作者家代送冰愿意车费减半并非是客气地要揽到这笔生意,而是有意报答一下作者家对自己的同情和帮助,所以他既然拗不过作者家不要他减半收费就又多送一倍的冰。那时“我”怎么没意识到老王的善意呢?——麻木!作者为此感到愧怍。
再比如当钱家也沦为不幸者的那个时期老王送钱先生看病的事:“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坚决”一词表明老王是真心不肯要钱,而一个“却”字则是表达出乎作者意料,没想到老王会有这样的举动;“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这个“笑”是对老王的谢意,作者意识到了老王的好意。“哑着嗓子悄悄问”、“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映射着老王对钱家的同情和关怀是多么贴心。那时“我”怎么没被老王的举止所感动呢?——吝啬!作者为此感到愧怍。
又比如文章在写病重的老王给“我”家送香油鸡蛋时对老王的描写好像在毫不动情地观察一幅,一句“说的可笑些”则更觉无情,“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突出了让作者震动的只是老王表面的可怕,——冷漠!作者为此感到愧怍。“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直到老王的去世才真正触动了作者的心灵,她开始思考。在老王生前我只注意到他外貌的丑陋,没有体察到他外表下面的美;在老王生前我只注意到他身体的残疾,没有体察到他残疾下面品性的健全;在老王生前我只注意到他生活中的贫苦,没有体察到他情感上的富有。我们对老王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同情却赢得他终身的敬重,其实不止是敬重而更是对我们以心相托以心相交,这点从“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代他传话了。”一句不难看出老王对作者家亲情般的牵挂。这怎不叫人愧怍!我没能及时体察他的善意、理解他的为人、感动他的纯洁,这怎不叫人愧怍!我真正认识了老王他却早就不在了,这怎不叫人愧怍!我只是同情了老王的不幸,却漠视了老王的高尚,这怎不叫人愧怍!
这是作者对不幸者的认识的反省和自我批判,同时也是对所有幸运者对待不幸者的认识的警醒,不是吗?作为幸运者同情和关注不幸者的时候往往都是给予,诚然这种高尚的给予是不幸者所急需的、是让人感动并值得赞美的。但是,却往往又都无意间漠视了不幸者身上也许能够感动你我、感动社会的善良的情感或高贵的品性。
原文
老王
作者: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登,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登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登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登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
作者对不幸者老王的愧怍还有一点。她想,自己身处危难时,老王忘记自己的不幸,不怕受牵连,勇敢而坦诚地送理解,送温暖,送慰藉,帮助自己从危乱中挺了过来,自己是何等的幸运!现在死神严峻地逼在老王面前了,老王形同“僵尸”了,却还是依然“忘我”,艰难上楼,亲自登门,给自己送油送蛋,这是怎样的崇高啊!自己是怎么回报的呢?自己不是千方百计帮助他赶走死神,而是继续用“等价”的钱去“侮辱”他,这是何等的低俗,何等的麻木,何等的愚蠢哪!为了把这种愧怍强烈地表达出来,她就对结句作了如前文所说的修改,让“幸运的人”同不幸者、低俗同崇高构成鲜明对比,以突出“拷问自己灵魂”的主旨。
通过对平凡人物老王的描写 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关心老王这样的好人。提倡老王的一种“善”的精神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