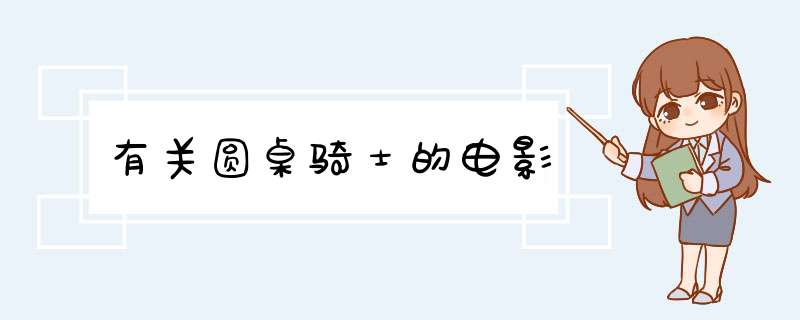
大法师传奇
一千五百多年前,作恶多端的莫德与他邪恶的母亲摩根娜,被史上最强的 大法师 梅林(瑞克梅尔,「 古堡守护灵 」)用魔法困住,然而当一位科学家(蒂雅卡瑞拉,「反斗智多星」、「 魔鬼征服者 」)意外发现时空隧道时,却也让莫德有机可趁逃到了二十世纪;随后觉醒的亚瑟王(派屈克柏金,「 魔鬼猎物 」、「 爱在我心深处 」)与梅林亦跟着来到现代,再度与邪恶的莫德、摩根娜母子展开正邪大对决…
都是魔法的对决 涉及到了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有点长,不过很值得看
婚姻是男女两性间建立的一种社会公认的夫妇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确立,在老北京,在封建的旧社会,从择婚、议婚、定婚到嫁娶等方面都有繁多博杂的禁忌事项。
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婚姻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定发展时期的产物。婚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婚姻的形态发生着种种演变和进化。在中国古代从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起,至周代结合政权的分封制时,就基本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宗族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家庭与社会的财产、财富全都计算在男子的名下,按着严格的辈份、嫡庶关系确立尊卑,明确递继。因而,婚姻的缔结便直接影响到一个宗族系统的发达与否。所以,婚姻虽属吉事,但顾忌也很多。
在择婚上,禁忌表现在外婚制和内婚制上。说白了,就是在择婚上禁止血亲间发生性关系,而同时又要表现出一种维护血统、属性稳定且纯正的意向。因各地习俗不同,便有了氏族外婚禁忌、氏族内婚禁忌、民族内婚禁忌、同姓不婚禁忌、表亲婚禁忌等等。从京城婚俗发展史上不难看出,这种禁忌也是有的。清初满汉不能通婚,后来为了统治者的需要,这种禁忌才被打破,但在等级禁忌上,时至今日也有所体现。在中国,整个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中,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差别。这种等级制度,在礼制上和法律上都对婚姻产生了种种限制作用,使“门当户对”成为中国传统婚姻最重要的标准,等级限制成为人们婚姻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等级限制主要表现为良贱不婚和士庶不婚的禁忌,“家之婚姻必由于谱乐”,门不当,户不对,便不可能缔结婚姻。
在择婚上尤其禁忌血亲婚。在旧时有“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民间是指单向舅表婚。舅表婚又称中表婚,中表即内外,舅为中、为内,姑为表、为外,俗以为姑母和父亲的血脉相同,娶姑家的姑娘为媳妇便是“回头婚”。因此,“骨血不倒流”的说法是仅对姑家的女儿给舅家的儿子的。汉、满都有此忌讳。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上也有明确的规定,近亲不能结婚。当然这是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的。
在议婚禁忌上,我们先谈媒人禁忌。俗语说: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却反映了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虽说自由恋爱历代均有,但毕竟许许多多的婚姻是经人牵线搭桥后缔结的。这牵线搭桥者,便是媒人。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大地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人。女娲感到十分孤独,便用黄土造了人。人总是要死的,怎么办呢?女娲又想了一个办法,让男人和女人配合,让他们繁衍后代,于是,后人奉女娲为婚姻之神,尊为媒祖,建庙祭祀。
女娲是神媒,那么人间的媒人是何时产生的呢?在杂乱婚或对偶婚时代,男女结合是自由的,自然不用媒人牵线。真正需要媒人和媒人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在一夫一妻制确立以后。这个时候,女性逐渐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丧失了她们原有的权力和自由。这样,男娶女嫁,就需要有人从中作介。“媒”字的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在《卫风·氓》一诗中,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句子。“媒人”一词,最早见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中有“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的句子。
媒人的产生,在中国的婚姻舞台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媒人成为“合法婚姻”的主要标志。没有媒人撮合的婚姻,要遭到道德、礼教及世俗的谴责和否定,被视为“大逆不道”。
由于媒人在婚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逐渐把媒人推到了代表婚姻道德标准,监督婚姻合法化的角色。同时,由于在旧社会盛行“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大防”的封建思想,统治阶级大力宣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贞女品德,因此,许多人家的姑娘总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男女婚姻自然奉行“无媒不交”的原则。因此,在沟通两性联系、促成婚姻缔结方面,媒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媒人施展巧嘴利舌这一“特长”的“市场”。
媒婆一般都能说会道,所以在过去,求媒婆说亲的人不敢慢待了媒婆,对媒婆的招待与送“媒礼”都是周到和丰厚的。如果哪一方无意间得罪了媒婆,因她的从中作梗,三言两语,会把一桩好姻缘给搅散了。还有一些根本不相配的婚事,因媒婆受了厚礼,也会昧着良心,瞒天过海,弄假成真,把婚事说合成功。如果婚后双方不满意,媒人并不负责,因为媒人“只包入房,不包一世”。
作为媒人,一般说来,忌讳四处张扬,在说媒开始,往往尽量避人耳目,否则可能婚事不成,却弄得满城风雨。其实,现在一些年青人,不论是自己认识的,还是由介绍人介绍的,开始也都是隐密的,到了一定程度才逐渐公开。
结婚不能没有媒人。民间以为,媒人是负有神圣使命的,他们能让冥冥中注定合该结为夫妻的人结合在一起,这本身就说明他们是可以上达神明的,是有一定的魔法威力的。因此,人们对其怀有一种敬畏的情感,不敢得罪于他们。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的需要,他们又是对民间婚嫁禁忌知之最详,记忆最深,传统观念保留最完整的人物。一切撮合事项,有赖于他们的穿梭奔忙,有关的风俗礼数,有赖于他们的传播、提醒、协助办理。
问名禁忌。问名,是男方求婚后请媒人问女方姓名及出生年月日准备合婚的仪式。近代北京的问名习俗,主要是看男女生年属相是否相合。不是马与牛、羊与鼠、蛇与虎、兔与龙、鸡与犬,猪与猴等在一起,即可合婚。
在“合八字”时,有不少的忌讳。就写庚书而言,桌上要放一对烛台,红烛高烧,中间放笔墨砚台。笔要两支,墨要两锭。磨墨时,两锭墨要同时磨,写男方庚书用一支新笔,写女方庚书用另一支新笔。笔墨皆成双,意味着双喜临门,好事成双,表示吉庆。庚书中男女的生庚,字数必须成双。
在旧时的议婚阶段中,纳彩、问名等婚仪顺利通过之后,便该纳吉一项了。纳吉就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消息告知女方的礼仪。旧京城有句俗话,叫“成不成,三杯酒”。是指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先后要去三次,每次都要带一瓶酒,成不成要第三次才知道。也就是说,第三次喝酒,是订婚仪式。
在婚娶上也有禁忌。
结婚大礼,安排在哪一年份内,在民间有许多讲究。如,无春之年,即当年无立春之月,是“寡年”,不吉利,不能成婚。在老北京,还有本命年不成婚之说。
过去,北京多选在腊月二十五至腊月三十这五天内嫁娶。届时,一顶顶红绿花轿、一队队送亲迎亲队伍,吹吹打打,气派非凡地穿街过巷。为什么要选在这几天嫁娶呢?这与人们对灶神的信仰有关。据《帝京岁时纪胜》载:“二十五日至除夕为乱岁日,因灶神已上天,除夕方旋驾,诸凶煞俱不用事,多于此五日内婚嫁,谓之百无禁忌。”原来,人们是将这几天认定为吉日。吉日婚嫁自然寓含“吉祥如意”的良好愿望。
近代,婚嫁不受季节限制,一年四季都可以。不过,以春节前后和节日为多。至于时辰,北方多在早上“日出前后”。在北京则有午前将新娘接回家,否则是二婚再嫁。
当代婚姻十分自由,嫁娶不拘时日。不过,多数人都选在“国庆”、“元旦”、“春节”,或其他节日举行婚礼,认为这样有纪念意义,祝贺的人多,热闹一些,也是图个吉祥的含义。
婚礼的高潮是迎娶新娘,六礼称“亲迎”。这是人生大礼中最隆重、最繁缛的仪式。
婚嫁日祝贺的人多少都无妨,但最忌有人上门要债、闹事。婚姻是喜庆的事,假如往日有冤仇的人家,此时上门来闹事,则是大大破坏了吉事,是最受忌恨的。
喜庆之日,燃放爆竹,有驱鬼之意含在其中,民间说是“崩崩邪气”!久而久之,由于条件反射,一放爆竹,人们就猜想是办喜事,所以放爆竹便又增添了喜庆热闹的一层含义。而办喜事不放爆竹也就更多了一层忌讳的理由了。
但现今北京城禁放爆竹,婚庆之日,也就少了声响。京城人也很有办法,买些小气球放在地上,迎娶新娘入家时踩上几个,几声脆响,也增添了喜庆。
旧时,男子娶妻俗称“小登科”,是可以穿九品官服的,新娘则必用凤冠霞帔,以象征吉祥。据《清稗类抄》云:“凤冠为古时妇人至尊贵之首饰,汉代唯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之首服,饰以凤凰。其后代有沿革,或九龙四凤,或九翚四凤,皆后妃之服。明时,皇妃常服,花钗凤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可见,当时新娘不用凤冠霞帔,已成为一种忌讳。一是伯不吉利,二是怕人说不是嫡妻。辛亥革命后,随着帝制的垮台,此俗逐渐变革。现在多以漂亮、崭新的西服、时装为时兴婚嫁衣。新娘佩戴红绒花,以谐音“荣华”象征富贵。近几年,婚纱在京城成为新娘最时髦的嫁衣。
在旧京城,婚娶多用轿子。结婚时的喜轿,具有特别的装饰,一般在红绿绸缎的轿围上绣些吉祥图案,如百鸟朝凤、富贵花开、丹凤朝阳、百子图等。讲究点的,再绣些金丝银丝,镶点钻石。喜轿有四人抬、八人抬。旧时的北京,汉人根据贫富不同用一至三顶轿子:一顶红轿,另两顶围有部分绿色轿围——前者乘坐新娘,后者乘娶送亲的太太;但北京的满人则只用一顶红轿,供新娘坐。北京的新娘对花轿还有个讲究,坐“头水轿”,必须是第一次使用。若此轿曾被人用过了,新娘可以拒绝上轿。
新娘子上轿时忌讳足踏土地,旧京城满、汉都有此习俗。不踏土的理由据说是怕沾走了娘家的灰土,带走了娘家的福气。有人认为这原是新娘依恋娘家不肯离去的缘故,有人说这是表示高贵的身份,还有人说这是为了避邪求吉。
上轿前,新娘要蒙上红盖头。红盖头即是一块二尺见方的红布,可蒙住新娘的头面脖肩,使人不能看清她的面目。新娘从上轿前蒙上盖头,直到下轿、拜天地、入洞房之后,才能由新郎掀开。不蒙盖头或者过早掀开都是遭忌讳的。下轿时,新郎骑着马鞍,手持弓箭,照新娘脚下虚晃三箭,借以驱魔除妖。
汉族民间俗信居处多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窗有窗神。就是门坎也有门坎神。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本领,不能慢待,都要敬重。所以新娘子进男家门时特别忌讳触犯各种神灵,尤以门坎为最要小心之处。新娘子绝对不能用脚踏在门坎上,据说会触怒门坎神的。门坎民间又称门限,那是一家之坎,门里门外、家里家外的分野。新娘子若踏了门坎,就是踩了丈夫家的威风,甚至还会妨死公婆。
不过,现今已没有用轿娶亲的了,大多数是用小汽车。再加上大力提倡新婚俗,一些忌讳也在年轻人心中完全消失掉了。
婚宴忌讳寡妇、孕妇及戴孝者参加,否则不吉利。吃完喜酒,收拾盘碟时,忌讳将空盘相叠,以免犯了“重婚”之讳。
新郎、新娘上床安寝时,新郎要特别注意把自己的鞋放在新娘踩不到的地方。万一被新娘踩住了,新郎就一辈子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新娘忌讳踩新郎的鞋,如踩了新郎的鞋就是对新郎的莫大侮辱。衣服也一样,忌讳新娘的衣服放在新郎的衣服上面,否则,丈夫将被妻子挟制一辈子。
洞房花烛夜点燃的灯烛忌吹灭,要一夜长明。相传新婚夫妇谁要先把灯吹灭,谁就先死,所以二人谁也不吹灯。因此也就有了“守花烛”的习俗,即新婚之夜,新郎、新娘通宵不睡,看守着洞房花烛不让其熄灭。俗有“左烛尽新郎先亡,右烛尽新娘先亡”的说法,故一烛灭时,随将另一烛也熄灭,取“同生死”之意。满族洞房花烛忌吹灭,因而是用扇子扇灭。
在婚姻上还有许多禁忌。但是,婚姻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一些旧的禁忌已经消亡,所以不再一一叙述
在旧时代,婚姻的目的有很大成分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并非看重男女间爱情的分量。所有婚姻的程序、习俗、礼仪都是向社会表明婚姻的合法化,而并不在于表明男女间感情的笃诚与真挚。随着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婚嫁要素逐步由外界的条件、环境转向男女双方的内心世界,一切旧的习俗、禁忌都相应地被改造或抛弃了。这种变化和物质文明的进程也是相适应、相同步的。轿子的消失使所有关于轿子的习俗禁忌随之消失或者转化;西装革履的兴起淘汰了凤冠霞帔以及围绕着凤冠霞帔的一切习俗禁忌;自由恋爱使得媒婆和这个职业逐渐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婚姻介绍所等公益事业。
总之,现代婚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当今的大都市中,几乎完全不见昔日婚俗的旧影,旅行结婚、集体结婚等新式婚俗逐渐形成时尚,许多婚姻禁忌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中已是荡然无存了。
京城婚俗的“嫁妆”
老北京城婚俗的禁忌
“嫁妆”,是娘家陪送自己出嫁他姓的女儿的,故也叫“陪奁”。陪奁是实用性的,也是礼仪性的。
“嫁妆”,是娘家为出嫁的女儿送的物件。这是女家聘姑娘办喜事的开始。按礼仪程序,有条件的要治筵招待亲友一至五天不等。讲究的富户有“前三后二五”的安排。即第一天“添箱”,第二天“送妆”,第三天为聘女,第四、五两天为庆祝。但一般人家只安排聘女正日这一天,至于贫户之家,也就没有了治筵庆贺的各种举动了。
有钱人家预备妆奁嫁妆要够“抬”(由十六抬至一百二十抬不等。六十四抬为全份,三十二抬为半份),抬多在吉期前一天送往男家,抬少可以当日送去。嫁妆的多寡一般是根据女家家庭经济状况决定的,中等之家大多为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贫者则为十六抬、十二抬、甚至八抬、六抬。有的则是根据男家过礼的抬数决定的,有相应还礼之意。如果男家过礼为八抬,女家则陪奁十六抬,原则上以增一倍之数还礼。
抬的样式是长方桌似的,有如过去的茶桌、油桌,四面用红围子挡上,上面四边有荷花栏杆,红漆雕花,也是两人一抬。这与过礼时用的食盒不同,嫁妆有如小轿,两边各有两根抬竿,双手或双肩抬着。通常是些樟木箱子(内放四季衣服、鞋、帽)、“子孙箱”(内放平日喜爱的物件和储蓄钱)、八仙桌、梳妆台之类的家具摆设。但必须有座钟一架,盆景一对,帽镜一座,掸瓶一个(内插毛掸),烛台一对。此外,脸盆、脚盆、尿盆、“子孙盆”(洗骑马布的),是必须要有的。那时称女人出嫁有三宗宝,即“夜净儿”、“子孙盆”、“长合灯”。如系富户可多至百八十抬,鼓乐前导,充溢于街巷,多引人注目围观。所送妆奁,除循例不陪送剪刀外,余者必求周全。首先是花梨、紫檀、硬木螺钿镶嵌的家具,例如:顶箱立柜、架几案、方桌、圆桌、琴桌、炕桌、炕几、太师椅、方凳、绣墩,以及西式沙发、靠椅之类。其次是古玩、字画、挂屏、座钟、挂表、金银首饰,各种化妆、生活用品,无不应有尽有。甚至将陪送姑娘的买卖商号(只抬一块商号匾额),房产(只抬一块瓦),土地(只抬一块土坯,上压红贴,写着亩数、顷数)也排进嫁妆行列。正如当年老北京童谣所唱:“月亮月亮照东窗,张家姑娘好嫁妆,金皮柜,银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锭儿粉,棒儿香,棉花胭脂二百张……。
嫁妆送至男方门口时,男方照例出来四人至八人迎妆。势派大的还要有鼓乐吹奏。
大宅府第,妆奁到后,当即由媒妁二人挈同新婿前往女家“谢妆”。这个礼节很简单,新婿进至上房中间,循例向上三叩首,即礼成,也不必客套寒暄,即可走出来,登车而返。女家虽由其父母或尊长在旁立候,然而并不接送,也不招待烟茶。
小户人家嫁女,嫁妆自然较少,若再少不够时,可雇“窝脖”扛往男家。老北京人谓扛肩的为“窝脖”,他们在肩、脖之间放一根木棒,上面放着内盛嫁妆的箱子,一路不停,一直送到男家。“窝脖”的“窝”法是:先将物品摆在一长二尺五寸、宽一尺七八,用软线绳捆好的长方木板上,然后请两人抬起,放在“窝脖”的肩上。窝脖人蹲身低头将物件“窝”起。行走时,他一手扶大木板边,一手前后甩动,二目向前平视,迈大步急行。到目的地后,下肩时也由两人抬下。据说,这个行业干久了,窝脖人都留下残疾,脖上有个大包。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天下事,有谁当?千斤万两我来扛。埋头负重,都为人忙。扛上去,血汗淋淋;放下来,明月一肩。”这段顺口溜如实反映了窝脖这种艰苦的劳动。窝脖“窝”去的嫁妆不管多少,必须在前一天送到。送妆的娘家人必须是近亲,方能按着新娘的习惯安妆。
独幕剧表现的是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场景里,比如说那个打酱油和俯卧撑的事件,发生在公园里,人来人往,有人落水,有人围观、有人下水救人等等。
[思路分析]
独幕剧与多幕剧相对应而言。要在一幕内完成的小型戏剧。剧中一般人物较少,情节线索单纯,从一个生活侧面反映社会矛盾,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戏剧故事。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契诃夫的《求婚》、J·辛格的《骑马下海人》、格雷戈里夫人的《月出》以及田汉的《名优之死》、丁西林的《压迫》、洪深的《五奎桥》等,都是独幕剧的代表作。
[解题过程]独幕剧示例
《冬夜》(独幕剧)
Neith Boyc著
小石改译
人物:
顾继光
顾阿慈
董四奶奶 (邻居孀妇)
设景:西山顾氏农居内一间外屋。
静极了!屋里只有左边壁炉龛内吊着的水壶,还断断续续地吐出低微单调的沸声。室内大半是黑默默的,正中圆桌上的洋灯都瞌了眼,这两天整夜地点着,连它也有些疲倦了。屋里不见一个人影,有的只是从正面两隔窗户漏进来的月光,射在窗前的花盆上,亮黑的圆桌上,老旧的椅子上,幻成种种寂寞、哀愁的影儿。屋内沉静;屋外更沉静。窗户外面,枯树不动,远山寂寥,田野沉沉地压盖着一片积雪,明月冷清清地照在上面。雪面的白光四处反射。屋外的景物异常清朗。屋内房顶也反耀出一片亮光。这样屋内约莫看出许多模糊的轮廓:近角远隅也有一点安微的光明;像是右边立着一只书柜,上面仿佛挂着一架静默的钟、旁边隐隐约约斜挂着的,大概是一杆猎枪;侧旁一定是一方穿衣镜:壁炉的火焰正吐着舌头在镜里晃耀着;左边壁炉前边多半睡着一张大躺椅;正面清清楚楚地排着一架缝衣机、一张沙发,一隔窗户下放着一个。月光冷静静地照着,地板上横的竖的都是沉死的黑影。
车声辚辚,由远而近。房前马声,铃声,足步声突破长久的寂静。一个男子的声音: (声音)到了!站着!站着!〔锁钥转动声。门——在后墙正中,介于二窗前——大开,顾阿慈进,转身向外。
阿继光,最好你看着长工把马盖好。不到明天早晨,温度一定冷到零度以下的。
光 (台外)好,好,我会管。你把门关严了吧。
(阿慈关门;脱下厚厚的皮大衣,走到圆桌旁,把灯点上。进来的女人是一位中年的太太,穿着一身灰白的衣服,头上戴着一个黑帽子。她坐在桌旁一张摇椅上,叹一口气,神色散漫,望着房内的东西。灯光下,屋内的陈设显得异常精致——木器都是白色的,窗帷、椅垫、桌布都是鲜红的颜色。地板上还铺着几张长方的小地毯,红的、绿的,横一块、竖一块都有。书柜内一行一行地排列着西洋书籍,上面放着几张照像和石刻。窗台上还有几盆冬天的花草点缀着。稍时,阿慈把黑纱帽取下,看了半天,放在桌上,不觉回头望望书柜上的像架。出了一会神,她把自己的头发理了一理,手抱着手,又呆呆地坐着,空望着前面。左面足步声。继光抱着一束木柴,提着一个风雨灯进来。他穿着一件厚重的大衣,戴着皮帽。进门把灯吹灭,靠在壁角里;然后走至炉旁,放下木柴,取帽子,脱大衣。他里面穿一件灰白的长袍,套上一件黑马褂,太紧了,显得他益发消瘦。他的头发己呈灰黑色,不过面上还剃得干净整洁。他望望阿慈,知道她在出神;于是添柴引火,在炉旁烘手,一面紧紧地看着阿慈。
光阿慈,你一定饿了,弄一点东西吃,好吧?
阿 (神不守舍)我不饿,我一点不想吃。
光这乡下的路总是这么坏——这一路又远又冷,我看你喝一杯茶解解寒吧。
阿用不着,我还好。刚才进大门的时候,你听见长工的话了么?他说隔壁董四奶奶已经找过我一趟,说今天晚上她一定要过来陪我一夜的。
光是么?
〔他由圆桌上把茶壶拿来,冲满开水,斟上一杯热茶,放在阿慈面前。阿慈正看着自己的白孝衣出神,没有瞧见他。
光喝茶吧,阿慈。你一定很冷了,今天叫你从家里二直走到教堂坟地,也亏你累的。
阿 (突然回头)我还不累。(她拿起茶杯,缓缓喝了一口)真是怪事!我不觉得累,什么也不觉得,回家的时候连冷也不觉得。刚才风就在后边吹,可是一到家里——(她打了一个寒战)这路真远!
光 (将椅移在圆桌对面坐下)实在,今天晚上你住在外国牧师家里顶好了。下完葬之后,他们请你住在他家里,我以为你就可以住下。
阿为什么?我自小上学堂的时候,就不愿意跟那些假道德的牧师在一起。这一次要是继贤的遗嘱不主张葬在教堂坟地里面,我无论如何不愿意找他们的。
光我不过是想你回到家里一定很寂寞的。
阿寂寞?这真叫人觉得怪,在这块地方,就看不见他了。继光,你想奇怪不奇怪?这真是怪,你跟我孤孤单单地在这儿——旁边就没有继贤了。我真不相信他没有了!
〔光忙走到右边衣架旁,把一件古铜色皮袍取下换上,由袋内取出烟斗烟袋,装好烟斗,在茶桌上找洋火。
阿继光,死真是一件猜不透的东西。死来了,什么东西都变了。你看这些书,这些学问,他在国外研究多少年的东西;人完了,什么也都没有了!(呆视)继贤走了,不见了!
光 (哑声)嗯。
(阿慈叹息,回首见继光,惊讶。
阿你已经把白袍子换了!
光那件白袍子我穿得太紧。你看,那件袍子……阿慈,你不怪我吧?
阿我说的时候,我并不是有意指摘你。不过,我觉得你出去的时候,总要把那件袍子穿一下。继贤是你的亲弟弟,他过去了,名份上你总要穿的。
光 (忙说)自然!自然!
阿 (坚决状)为什么丈夫死了,女人就要穿这种白惨惨的衣服,我顶恨这种颜色!(叹气)可是他死了,我一定为他穿的。在生前我对得起他,死后我还要对得起他。
光 (不停地走)是的。
阿继光,这些年你总算对他尽了做哥哥的责任。
光但望如此。
阿 (拿起黑帽,解开帽上的带子)他一病这几年,你对他对我真是一个好哥哥。我想起来,真不知道以后没有你怎么过。(她叹气)
(光走到窗前瞰望,无意中碰倒一盆花,落在地上摔破。
阿 (起身)啊,怎么啦?这是我的秋海棠!(光俯身拾碎片,烟斗同时落地)继光,怎么回事?你把自己的烟斗也摔断了!今天你怎么这么粗心?(走到他面前)怎么,你的脸白得跟雪一样?哦,我明白了,你晚饭还没有吃呢?(向右门走)
光不必叫厨子!他们都在坟地里还没有走回来呢。阿慈,其实我不饿,我一点不想吃晚饭。
阿 (坚持)哦,你一定是饿了!你不吃也要吃一点,我先跟你弄点点心吧。继光,家里死了人,活人依旧是要吃饭哪!
(叹息,出右门。光看她出去,把两段的烟斗拾起,叹一口气,望望书柜上亡人的像片,再回首顺着阿慈走出的方向望去,低头沉思。行至屋中,阿慈走进,围白围裙,裙角系着有一付红缎结。她端一盘火腿面包,走到圆桌前。
阿 (刚把围裙系好,才想起厨房今天一天没生火。还好,柜里还有一盘现成的火腿和面包。)你坐下,先吃一点,等下人回来再弄点热东西吃。
光 (坐下)阿慈,我不想吃。
阿你太伤心了!继贤过去,我没想到你这样难过。你平时不好说话,可是我知道你对手足的感情很厚的。你总是替继贤打算这个,打算那个;可怜,继贤有时在床上闷得难过,时常还对你说些不讲理的话,我从来没听过你抱怨过他的。唉,搬到农场养病已经有十年了,你在外面累,我在家里累,到了,他还是死了!(叹息)继光,你不吃点东西么?
光我简直不想吃,吃也咽不下。
(他略将椅推后,仰视身旁的阿慈,不觉注意到她围裙上面的红缎结;阿慈觉察出来,把缎结抽出。
阿哎,我没留心这上面有一条红带子。
光 (伸手)阿慈,给我吧。
阿缎带子?你要这个做什么?
光也说不出做什么,我只喜欢这个颜色。我向来是爱看红的东西。
阿 (给他)拿去吧。这类颜色我也爱——大红的颜色,鲜亮亮的,就是紫色也好看,那种深紫的颜色。(叹息)现在我不应当想这种东西啦。这时想起这些事情,真是傻气!
(她把圆桌上的火腿、面包放在近炉的茶几上,把桌上收拾干净。
光这一点不傻气,像你这样爱颜色,把家里收拾得很美观,这真是你的聪明。这所老房子到你手里都变了样子了。你没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这所房子荒凉得没有人管;你来了之后,房子的气象都改了。满处都是快乐光明,屋里也放着花,冬天都开得旺旺的。哦,我想起来了,(他走到窗前)我几乎把你的花忘记了。今天夜里一定要冻。不到明天早晨,房里一定很冷的。(他把花分移在茶几上,圆桌上)我真对不起你,把那盆秋海棠摔了。
阿那要什么紧?(她走到窗前)外面看着很冷,我想董四奶奶不会来了。
光我猜她要来的。她说今天晚上不要你一个人在屋里坐着。
阿这总是人家一番好意,不过我想还不必要她来陪我。我现在不愿意多谈些闲话,我只想一个人坐着想想自己的事情。继光,把窗帘拉拢吧,月色惨惨地,外面像是异常地冷似的。
(光拉开窗帷,把两隔窗户遮好。阿把摇椅放在炉旁坐下。
阿我只想我能够找点事情做,这样闲坐着,我真忍不住。对了,那儿放着张太太的衣服——可是今天晚上,我安安静静地缝衣裳,我也太无心肝啦,继贤才抬到坟地里……
光阿慈,不是这么说法。这同你自己的感情有什么关系?你要那件衣服么?
阿不要——也好,你把那个篮子拿过来——自从继贤病的最重那两天起,东西大概都没有动——可是董四奶奶来了,不要叫她看见我缝衣服;他们乡下人有许多讲究。固然他们的意见无关轻重,然而也犯不着叫他们大惊小怪的。
(光将筐蓝由缝纫机上拿过来)
光那怕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世界上尽是些聪明人,不必管他们。不过你要顾忌他们的口舌,我替你看着就得了。
〔阿不理他,由篮内拿出一身紫色的衣服。
阿这颜色倒美,可惜这材料太贱。我向来不喜欢坏材料。
(她起首缝纫。光在屋内徘徊。他从墙钩上把一支猎枪取下,拉一张椅子靠近阿慈,熟视枪,塞枪弹。
光今年西山又出狐狸了。我想早晚有一天夜里,我要把那只狐狸捉着。今天早上我又看见它的脚印,恐怕我们养的鸡又叫它吃了几个。
阿 (心不在焉)真的么?(停)继光,我算算,我进了这个门已经有二十一年了。你想想,这不是一场梦么?
光嗯。
(他装好枪子,把枪倚在膝旁。
阿六月里,我嫁给继贤。等到明年六月,整整二十二年。那时他二十一,我二十。你大概比他大四岁,是吧?
光比他大五岁。
阿你看着还比他大些。你总是这样奇怪,这样安静。继光,你真不应当不娶亲,要不然,现在你不会孤孤单单一个人了。
(光立起,预备把枪挂在墙上。
光只要你在这儿,我一点也不孤单。
阿我怕不能够长在这个地方啦。
(光手里的枪落地。阿跳起,膝上的篮亦翻下。
阿哎呀!你怎么啦?枪不是上好子弹了么?
光 (哑然)嗯,上满了!
(他把枪拾起,低首呆视。
阿我简直以为你喝醉酒了。我从前跟你订好约,不许喝酒,你不会破约又喝了吧?
光我没喝!这十年工夫,我一滴酒也没沾过,这你知道。
阿好啦,你把枪挂好吧。我看你最好睡觉去,看你的举动,一定是累过火了。
(她拾起篮,又坐下。
光我不累。我不是这个意思。(挂好枪)我是……
阿是什么?(他背她站立,低首下视)是什么?继光,你的怪脾气又发起来了。说真的,有时候我实在不懂你;真的,比懂城里现在这一般时髦女子还难。二十年工夫,我们不拘形迹,天天在一起……
光天天在一起,哎,天天在一起。你刚才不是说我孤单么?我的意思就指这句话。(他突然回头,走到她面前)你说你不能长住在这儿……
阿我说过么?哦,是的。刚才我是这么想。
光你想什么?
阿我想我这一生在家里也过够了。现在时代也变了,从前继贤常骂我激烈,现在新人物都说我守旧了,可是我自己原来也不打算在家里过一辈子的。 (她穿针缝纫,低首说话)继光,我早有我的野心,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一,我自己觉得我这一生的事情像是还没有完似的。继光,你知道,这里太没有事情干,太闲在啦?假如现在我有一两个小孩子,这又当别论,但是每天只照护你们两个男人家,并且你还常在外面管农场上的事——这事情实在不够我做的,太轻松了,所以我教小孩,找许多衣服做。我找这些事并不是想弄钱,我只是喜欢忙,喜欢累,喜欢帮助人家。多少年我就有一个计划,当时我想谈出来,不但没有用,反叫继贤着急,所以就没有提。我想做买卖,开一家女子衣服店,找一个大地方——也许是天津——设立一家。我手下也有一点资本,就是不要农场我自己的那一块地,我也开办得了。现在我总算自由了,(她放下衣服,眼巴巴地望着光,光直立不动)我从前总想活着要有生趣,有工作,有自己的事业,现在我都能做得到了。哎,继光,你不知道我这一生多么喜欢好看的颜色,好看的材料。我只想替旁人做好看的衣服。我只想把那绒啊、绸啊,鲜艳的材料,剪给人家小孩子们穿。想起来我就高兴。我也说不出为什么原故——这原来也傻气。然而一看见我所喜欢的颜色,深紫啊、深红啊,有时我几乎快活得落泪。我太喜欢哪!
光我怎么办?(阿停语,抬头惊顾)我问你,我呢?你只打算着走,把我扔下,好像……好像……
阿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看法?怪不得许多人都说你是一个怪人。
光你就没替我想想!(精神紧张,来往徘徊)你只打算把我放在这儿,丢开我,自己走,你不知道我这一生都为的是你。
阿为我?继光?
光自然,为的是你!你想想,我为什么住在这儿?难道旁的事情我不可以做么?你想,我学了许多年的工业,我就没有野心么?男子汉的心胸我就没有么?你为什么想,我在你旁边过活还孤单呢?阿慈,难道你还不明白么?
阿 (立起,物落地)继光!
光你不知道我这一生只有你在我心上么?
阿 (喘气)继光,你弟弟的尸首在坟地里面还没有冷呢!
光哦,阿慈,他不懂得你!父亲替他把你订下,他就娶了你;他只认得他的书,他不懂得你。我一见你,我就明白你。这二十二年,我的心一点没有改。难道你不觉得么,难道你不觉得么?(他逼近阿,阿后退!终于他在阿近处站立)他没有跟你见面,我已经见着你,明白你。我这一生,这一辈子都为的是一个人!你能说你不知道么?
阿 (粗声)你疯了?
光阿慈,我疯了?也许吧!听你冷冷淡淡他说我不应该不结婚,说我这样太孤单!孤单?我从前真是孤单么?除你以外,我怎么能够再想旁的人?是的,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应该跟你谈这些事情,可是我没有法子,我实在忍不住了!阿慈,刚才你说你要走,我听着简直想哭起来了!
阿继光,你……你完全是疯了!你是一个老头子,我是一个老太太。这种思想简直可怕!简直可怕极了!你不要忘记你的弟弟,即便我不是刚刚把他安葬……
光阿慈,这没有关系,他总算活过了,可是我从来没有活过,你也不是活着。阿慈,我知道,你对他并没有多少感情。
阿你怎么敢对我说这种话?我?这几年这样尽心尽意地帮助他,照护他,我不跟你说话了!
(战栗。她取下围裙,折好,向门走去。
光阿慈,不要生气。请你明白我这点苦衷。
阿明白?你的话我就不愿意明白,我跟你讲,你已经昏了头了!
光 (挡住她的去路)阿慈,你一定得听我说。这些年我都放在心里没有讲。你自然不相信我心里早已存在着你,你不知道我对你多少年的感情。这是永远不会变的。阿慈,现在我依然不改;我不能够觉得我老,我更不觉得你老,年龄是管不住感情的。阿慈,我对你的情份,现在你不要轻意丢开,你不要看不起一个人的感情。假若你不愿意在这儿跟我一块住,那么你到哪里,让我也跟着你去。阿慈,带着我去!没有你我活着一点意味也没有了。
阿继光,躲开我!
光不成。你为什么这样待我?难道我对你发生感情就错了么?就是结婚,现在法律也不能干涉我们。
阿结婚?这简直是禽兽!
光为什么结婚不可以?法律干涉不了的。我想我们住在一块许多年,彼此相得,结婚原来是很自然的事。我知道,你所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可是你对我的感情一向是很好的。
阿我对你是兄妹手足的感情,可是现在……
光现在怎么样?
阿现在你我最好分开——越快越好。
光不成!我离不开你。多少年前,假若我走得开,我早就离开此地了;可是我办不到,我就住下。你当时也没反对我住在这儿。不但如此,我这些年下雪下雨每天出去为你做的事情你都安然受下,我对你的好意你已经承受了。即便你说你不知道,你已经承受了!阿慈,现在你欠我的,你该我一点东西。
阿继光,这农场一半归你呀。假若你还嫌少,你全拿去也可以。
(光抓住她的臂膊。
光阿慈,你不应当对我说这种话。这太没有心肝。你应该明白得多!从前你总是和和气气地管理家事,所以我没有细处看你,明白你。原来你这种人只会尽责做事,不懂一点感情的。可是你不能够跟我说这种话。无论如何,你欠我的情份。
阿让我走。我真怕跟你在一起。我早就知道你心里总有点疯疯癫癫的东西。我跟你讲,再这样下去,你要入疯人院的。
光 (放开她,退两步)你这是一句真话,你就能赶我进疯人院。要是你离开我……我……
阿继光,听我说。我们这些年住在一起,我不愿临了这样分开。过去呢,你帮过我的忙,我也帮过你的忙,我们一向是和和气气的。几年前,你喝酒喝得很凶,要不是我,你早就醉死了。我想你还记得。
光那时死了倒好。
阿醉死了倒好?那个时候我把你救出来,从那以后,你清清白白做一个好人。也许你已经有些疯疯癫癫的思想,可是那时你明白,你放在自己心里头。现在还是请你放明白些,知道事情终久要变的。你应当想想,我不能够住在这里的。你还要办农场呢,你就办下去;不然,我们卖了它,都随你的意思。
光这么说,你要走了?
阿我当然是要走。我在这里等于住监狱。这些年我已经住够了。
光 (声音低哑)阿慈,带我去!你愿意到哪里,我都跟你去。我能够帮助你,替你做许多事情。
阿继光,这不成!这不成!我先要回我的娘家,找着机会再做生意。
光那我在附近找一个地方住。
阿 (喊出)这不像话!你没想想你说了这些话没有一件办得到么?这样我一分钟都坐不住了。谁能够想出种荒谬的思想——你跟我结婚!
(她狂笑。
光 (惊)阿慈,不要笑!
阿 (镇定)这句话说出来不是糊涂么?可是我猜你一定是怕一个人留在这儿,才说这些话,你心里头绝不是这个意思的。好,从这时起,我们干干净净地忘丢它。
光 (迟钝)我们忘丢它。……
阿 (有些惊惶)这才对。我们和和气气地分开!将来还要见面。像我们这两个老东西,我们不能再想那些事情啦。
(她又狂笑。
光 (转面抓住她的手)不要笑!
阿哦,天哪,他疯了!救命!救命!
(她从他手里挣脱,向门冲去。
光 (蹒跚欲倒,扶着椅背喘气)阿慈,我不害你——你别怕——你……你……你——我永远不会害你的。我不再说了,我们忘了吧!——忘了……
〔跌入靠桌的椅内,头埋在手里。
〔门外足步声,长工与一女人说话。
阿啊,可来了!这一定是董四奶奶!(开门,董进,阿猛拉着董的手)我以为你永远不来呢。
董 (把阿拉过门口,关上门)说什么我也要来的。今天晚上,我可不能叫你一个人在家里守着。头几天晚上,总得要个妇道陪着的。顾大先生呢——唉!真可怜!他也是不好受。
阿 (忙说)我们大哥也是很难过的。董四嫂,把东西部脱下——来,过来暖和一下。今天晚上太冷了。(打了一个冷战,为董把帽子斗篷脱下,放在一旁。两个孀妇都站在壁炉旁)唉,董四嫂,我万分谢谢你,你到这儿来陪我。
董唉,顾太太,我也是过来人。唉,我明白。刚一来,是不好过。孤孤单单地好像一个人就活不了似的。(光慢慢起来,不看她们,呆滞的神气,拿起枪走出房门。阿有点惊奇,看着他上去)可是,顾太太,人活着总得吃饭不是么?以后凡事都忍着点,每天念念老爷待我的好处,修修来世就得了。唉,可怜,顾先生是真不好受。难怪,他们兄弟俩也太好了。像他这样没成家的人,本来也遭不得世。好在这些年他跟你们住在一块,也是他的运气。他脾气太怪,跟旁人都合不上来。可是这么大的农场他一个人管这个,管那个,我看这真是他的好处。你们老爷病着不能管事。你们真是得靠哥哥啦。好啦,现在你也可以憩憩,安安静静地享享福啦。苦了这些年,你也应该……(外面枪声一响,她们都惊起)这是什么?
阿这是继光,我们大哥。他出去了,你看他带着枪出去的。
董这半夜里拿枪干什么?
阿这一定是那只狐狸。今天晚上他说要打那个狐狸的。近来我们的鸡已经丢了不少了。(她走至窗前,拉开窗惟)董四嫂,我怎么看不见他。
董顾太太,你怎么啦?你直打战。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我出去看看。
董你想些什么?怎么,你抖得都站不住了。来,我看看去。
〔她拿起斗篷,阿向前捉着椅背倚佐。董四嫂出。阿全身靠着椅上喘气。
〔外面大喊,愈喊愈近。董四奶奶跑进,斗篷落地。
董 (声音尖锐)在……在马号里,他……他的头都炸碎了!顾太太!顾太太!
〔她倒在地上!抓着阿慈的膝头。阿躲开,把耳掩上。
——幕
(原载《南大周刊》第77期,1929年12月31日)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