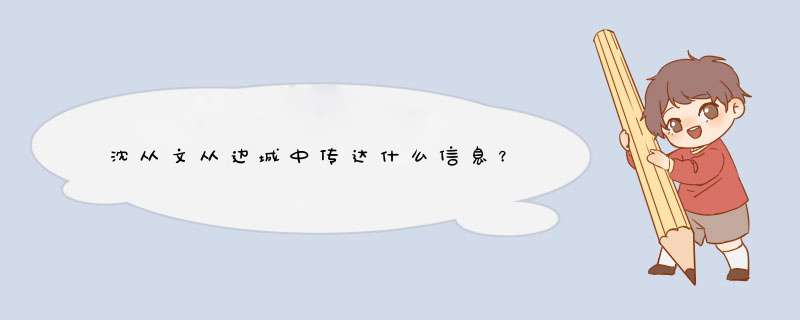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边城》故事梗概:
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在端午节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哥哥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原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 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事去世了,不久后爷爷也去世了,翠翠一个人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扩展资料:
故事中边城的真实地点:
边城茶峒即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边城镇,原名茶峒, 地处湘黔渝三省交界处,“一脚踏三省”。文学大师沈从文的著名中篇小说《边城》把茶峒优美的风景、善良的风俗和淳朴的人情等融为一体,勾画出田园牧歌般的边城风貌,引得国内外无数文人骚客前来观光采风,从而带动了当地旅游业。
2005年茶峒正式更名为边城镇 。为与国内其它以边城为名的地方相区别,媒体常以边城茶峒指称该地 。这里西与重庆秀山县接壤,南与贵州松桃县接壤,界以一河相隔,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人口居多,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
参考资料:
边城— 边城茶峒—沈从文的《边城》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相互友爱。
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
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扩展资料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一、思想情感:
表达对湘西人民美好纯洁的单纯感情的赞美。例如祖孙亲情,男女爱情,村民之间朴实的情感的赞美。同时也是对这类感情的艳羡。又表达了在现代化的脚步下,山村的原生态被破坏的惋惜和遗憾以及追忆之情。
二、不同:
沈从文在生机勃勃的湘西语基础上,吸取了书面语、文言语的特长,使他的小说长句精确、曲折而富韧性,如“出货物物俱由脚天用桑水扁担压在肩膊上挑抬而来,入口货物出莫不从这地主成束成担的用人刀搬去”,短句则重感兴,活乏有灵气。
如“酽洌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案桌上了”。
沈从文的小说从不附加词藻,文笔总是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形成的是一种恬淡的语言艺术风格
三、鉴赏:
作品鉴赏
1、主题思想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
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
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2、艺术特色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
其方法多种多样: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
翠翠离奇的“胡思乱想”,让人感到渐渐有了自己心理的少女的孤单寂寞,以及爱情的幼芽时心灵的躁动;翠翠“顶美顶甜”的梦境,展示出对朦胧爱情的甜蜜感受和潜意识里对爱情的向往。
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翠翠“带着娇,有点儿埋怨”地一再央求爷爷丢下渡船上的活回到她身边,让人感受到翠翠对爷爷的无比依恋之情。
听着爷爷唱的“那晚上听来的歌”,“翠翠自言自语说:‘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则让人感受到情窦初开的翠翠对甜美爱情的神往。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在作者笔下,啼声婉转的黄莺、繁密的虫声、美丽的黄昏、如银的月色……奇景如画,美不胜收。这些又都随着人物感情世界的波动而自然展开。
或是以黄昏的温柔、美丽和平静,反衬翠翠爱情萌动的内心的躁动、落寞和薄薄的凄凉;或是以柔和的月光、溪面浮着的一层薄薄的白雾、虫的清音重奏,烘托翠翠对傩送情歌的热切期待,以及少女爱情的纯洁和朦胧。
扩展资料
内容简介
在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主人公翠翠和她爷爷老船夫。茶峒城里有个船总叫顺顺,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送。
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nuó)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并提前托媒人提了亲。天保告诉傩送一年前他就爱上了翠翠,而傩送告诉天保他两年前就爱上了翠翠,天保听了后也吃了一惊。
然而此时,当地的团总以新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给傩送。而傩送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也要与翠翠成婚。
兄弟俩没有按照当地风俗以决斗论胜负,而是采用公平而浪漫的唱山歌的方式表达感情,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心灰意冷,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
碧溪边只听过一夜傩送的歌声,后来,歌却再没有响起来。老船夫忍不住去问,本以为是老大唱的,却得知:唱歌人是傩送,老大讲出实情后便去做生意。几天后老船夫听说老大坐水船出了事,淹死了……
码头的船总顺顺因为儿子天保的死对老船夫变得冷淡。船总顺顺不愿意翠翠再做傩送的媳妇。老船夫只好郁闷地回到家,翠翠问他,他也没说起什么。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
第二天翠翠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翠翠去找爷爷却发现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 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也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边城
《边城》是一部怀旧的作品。沈老曾经告白读者:“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作品所描绘的人生,是在一种洋溢着诗情画意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的特定环境中展开的,社会背景与矛盾被诗化了,淡化了。这与当时动荡残酷的社会现实是有很大距离的。有人认为这表现出作者对现实政治的隔膜。而我却认为这是沈老故意为之,他刻意创造了一个纯美的世界,表达了他内心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那么诗意的理想化世界;那么纯真的两个年轻人;那么美好的一段刚萌芽的爱情,结果却是悲剧。这是作者的有意处理,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痛惜和思考。正如题记所写:“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即是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辨与批判。创作《边城》时沈老虽然宣称是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而实际上却正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与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粘附”起来,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所以认为他的创造太过于天马行空,不切合当时政治背景,是对他的误解。沈从文是一位以“美”和“爱”来反观黑暗现实社会的人道主义作家,而且具有深厚的悲剧意识。读了《边城》且内心涌动出一股哀伤情绪的人,就会理解。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作者以纯净的笔触谱写出一首爱与美之歌。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绚丽清新,是一幅优美别致的风土人情画卷。而青年男女的情爱,父子祖孙间的亲爱,人民相互之间的友爱,以及自然万物之爱与湘西之美糅合在一起,了无痕迹地融人了全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 象之中。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的青山绿水是美的,边城的故事是美的,边城人那种沉浸于生活、融会于自然的心态也是美的。
纯朴的人情
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古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边城》第三节)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
1.翠翠
翠翠天真善良、温柔清纯。她和外公相依为命,对外公关心备至。因为外公不理解她的心事,她就幻想出逃让外公去寻她,可是想到外公找不到她时的无奈,又为外公担心起来,为自己的想法的后果害怕自责。她爱上了傩送,感情纯洁真挚。节选部分以后,傩送远去,她又矢志不渝地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表现了她对爱的执著。
2.外公
外公保有着中国传统的美德,他对孙女翠翠亲情无限。为翠翠的亲事操心担忧,尽力促成翠翠爱情的实现。在生活上,对翠翠也是无比关怀,不让翠翠坐热石头,惟恐翠翠生病;在感情上尽力体谅翠翠的心思,翠翠忧伤寂寞时为她讲故事、说笑话、唱歌。
3.天保
天保个性豪爽、慷慨。他是船总的大儿子,却爱上了贫苦摆渡人的孙女。他知道弟弟也爱翠翠,两人唱歌“决斗”,他却因为自己先提了亲,“作哥哥的走车路占了先”,一定要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他知道自己不是“敌手”,就很大度地成全了弟弟,充分表现了他的手足之情。后来他外出闯滩,既是为了弟弟的幸福,也是为了消解自己心中的失望和难过,“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最后意外遇难,可以说他是为了亲情和爱情而死。
四、孤寂的内心
作为封闭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湘西,人们的身上也流露出孤寂的色彩。
1.翠翠
翠翠自幼父母双亡,内心无比孤独。虽然有外公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但是并不能真正理解她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情怀。她“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没有人能体会一个思春少女的感情,所以她感到“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她为这无奈的生活而痛哭,外公不能明白她内心的哀痛,只能哄劝她说:“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对于一个花季少女,这样的话太不切实际了。天保和傩送为了她唱歌“决斗”,她却毫不知情,只能在梦中希望爱情的实现,现实好像和她毫无相干。最后天保闯滩而死,傩送离家出走,外公为她的婚事忧愁而亡,她却并不能了解这一切的前因后果,只能凄凉地守着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人能告诉她要孤独地等到什么时候。
2.外公
外公因为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翠翠害怕地痛哭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他给孙女讲母亲的故事,更让孙女感动不已。对于天保兄弟的选择,他却没有直接告诉翠翠,反而让孙女“心中不免有点乱”。他对翠翠“温和悲悯地笑”,表现了他内心的矛盾,既爱孙女,又害怕她再走母亲的老路,却不能直接说出来。节选部分以后因天保的死造成孙女的悲剧,他又无能为力,不能向任何人求助诉说,只能撒手而去。可以说他是在孤独中死去的。
3.天保兄弟
天保喜欢翠翠,托媒被糊里糊涂地拒绝回来,他不知道翠翠喜欢傩送,傩送也喜欢翠翠。在不知情中踏入了爱情的纠葛中。最后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希望,只能孤独地离开伤心之地。最后死于意外,也许正是他孤独的归宿。
傩送也可以说孤独地追求着爱情,和哥哥的“决斗”,夜半唱情歌,却并不为心上人所知。最后也孤独地出走,不知飘泊到什么地方。
可以说,《边城》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中挣扎着,最后“也许明天回来”不过是孤寂中的自慰罢了。
五、文化内涵
作者的理想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作者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作者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关于沈从文的《边城》的问题
为什么天保的死,傩送认为与老船夫有关?
翠翠母亲的故事和翠翠的故事有什么关联?
不只是傩送这么认为,而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在两兄弟比歌的转天早上,老船夫在那里碰到大老的时候,将他误以为是夜晚唱歌将翠翠的灵魂浮起来的那个人。而实际上并不是大老,他心里听老船夫这么说当然揪心了。何况老船夫在这之前立场一直是摇摆不定,那些人们会这样认为是正常的。
翠翠母亲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她爱上了一个既要名誉又要爱情的人,但是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吗?没有!倔强如翠翠的母亲,那个人都已经离开了,她还活在世上做什么。殉情,这是最凄美的爱情结局!
老船夫总觉得翠翠在走她母亲的后路。因为翠翠对爱的执着,这点跟翠翠的母亲如出一辙。如果她这辈子都等不到那个人——傩送或者被迫嫁人,翠翠都极有可能走上为爱殉情这条不归路~
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
《边城》的忧郁不是作者故意渲染出来的,而是从作品中自然流淌宣泄出来的。作品的忧伤基调没有削弱作品的可读性,反而增加了作品的厚度与魅力。通过几个主人公的种种悲剧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不能自主地把握命运,一代又一代继承悲凉的人生命运的深深慨叹。
背景: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作者的代表作。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风情美和人性美。
深层寓意:作者的理想是要在小说中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作者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作者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