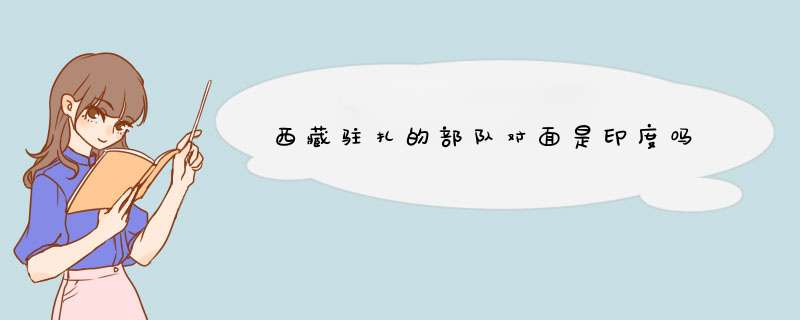
是。1952年组建的西藏军区无疑是中印边境防务的“直接责任人”,负责中印边境东段的防务。西藏驻扎的部队对面是印度有包括山地部队在内的12个师。锡金是中印实控线上继达旺之后印度驻军最密集的地区,也是解放军在西藏边境重点防守的区域。
解放军报《云中的哨所》------------世界屋脊边防哨所的一曲感天动地的时代颂歌
人生总是要面临许多选择,生死关头的高尚取舍最能折射出心灵之光。——题记
这是发生在世界屋脊边防哨所的一曲感天动地的时代颂歌。
西藏军区边防某团五连六班驻守詹娘舍哨所的战士们,在雪崩袭来、生命危险时,表现出英勇顽强、团结互助的精神,生动再现了当代边防军人的高尚品德。
6月13日,成都军区在拉萨举行命名大会,授予六班“英勇顽强团结互助模范班”荣誉称号。
面对雪崩的选择——
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
西藏亚东县气象局局长加穷:
今年2月以来,亚东县境内连降大雪,詹娘舍哨所山口一线积雪厚达2至4米,凹地积雪最深处厚达40至60米,风力达10级以上,百年不遇,史所罕见。
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詹娘舍哨所官兵一直过着夏天吃雨水、冬天吃雪水的生活。
3月2日,卫生员王鑫和战士于辉吃过午饭,背着背囊到距哨所15米左右的地方背雪回来化水。在近80度的陡坡上,两人将一锹锹积雪往背囊里放。
13时30分,一声闷响,划破了詹娘舍哨所上空的宁静。于辉脚下的积雪突然崩塌,连人带锹被卷入300米深的悬崖。
“班长,于辉掉下悬崖了!”王鑫气喘吁吁地跑回哨所向班长靖磊磊报告。
“快!值班员留下,其余同志跟我来!”靖磊磊当机立断,带领副班长梁波、战士杜江南、杨恒升、赵勇及卫生员王鑫迅速下山救战友。
由于下山通道被积雪覆盖,靖磊磊坐着铲雪用的铁锹迅速滑下山崖。找到于辉,靖磊磊将他抱在怀里,一边呼喊他的名字,一边掐他的“人中”。大约30分钟后,于辉终于醒了过来。
寒风呼啸,乌云翻滚。“快走,要打雷了。”靖磊磊说完,将背包绳系在自己腰上,背上陷入半昏迷状态的于辉,指挥大家撤回哨所。
向哨所攀登的“路”,是一个80度左右的陡坡。杨恒升拿着铁锹边往上爬边铲雪开路,副班长梁波带着杜江南、赵勇边走边将脚下的积雪用劲踩实。前面的战士每上一步,就将靖班长腰上的背包绳往上拖一步。走在最后的王鑫双手插进积雪中,用头紧紧顶住班长背上的于辉。
当战士们爬到距离哨所约100米远时,杨恒升发现上方积雪裂出一条巨大的弧线。“班长,可能又要发生雪崩!”杨恒升的话音刚落,积雪突然崩塌,战士们再次被卷下山崖。
不知过了多久,第一个醒来的靖磊磊带着剧痛刚坐起身,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他用力支撑起身体爬过去将其他战士一一摇醒,并将赵勇和于辉从积雪中刨出。
此时,于辉已重度昏迷,其余战士都不同程度受伤。
眼看大家伤势太重,雪深坡陡,加之天色渐暗。靖磊磊当即决定:“我留下照顾于辉,你们赶快绕道返回哨所报告团里,请求派人来营救。”
“我是卫生员,我留下,你们快走!”王鑫恳求。
“班长,要走一起走,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另几名战士说。
在生死抉择面前,战士们表现出了边防军人高尚的情怀。
靖磊磊命令:“我和卫生员留下照顾于辉,你们就是爬也要爬出去向上级报告情况,然后请人来营救!”
山风呼啸,雾气升腾。梁波等4人爬上一个山梁,回头望去,只见靖磊磊和王鑫在冰雪地上将于辉搂在怀里,焦急地向他们打着“快走”的手势。
夺眶而出的泪水,在4名战士脸上凝成了冰花。
面对绝境的选择——
英勇顽强团结互助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高山病防治专家李素芝:
常人每天所需热量为2000大卡,野营、行军等重体力劳动,日消耗热量3200至4200大卡。一个常人在不补充食物的情况下,在海拔4000米以上、零下10摄氏度以下的雪地里通常只能存活12小时。
梁波带着3名战士向哨所急行。他们4人分两组,杜江南在前面10米处开路,梁波同杨恒升、赵勇在后面跟进。突然,只听“咔嚓”一声,杜江南脚下的冰层破裂,身子随即陷进积雪中。
“快,杜江南掉进雪窟窿里了!”梁波立即指挥大家救人。
积雪下的树枝划破了战士们的双手,刨出的雪被鲜血染红。冷、痛、饿……各种困苦交织在一起,侵蚀着战士们的身体。忍耐、坚持!20多分钟后,大家终于将杜江南拉出雪窟。杜江南手臂、头部被划破,额头上的鲜血不住往外流,浑身不停地打颤。
夜黑风高,险情四伏。战士们走出约1000米,又是“咔嚓”一声。
“副班长!”走在梁波身后的杨恒升见梁波滑进冰河,失声大叫。
“快,接人桥。”战士们趴在刺骨的雪地上依次抱着对方的腿,将梁波慢慢从冰河里拉上岸。
上岸后的梁波衣服顿成“冰甲”,鞋子也掉了,不住地打着寒颤。
饥寒交迫,伤势加重,行走困难。走着走着,梁波双眼开始模糊,双腿渐渐不听使唤。他对大家说:“我可能不行了,你们快往前走,好叫人救班长他们,不然一个人也走不出。”
“副班长,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抛下你。”杨恒升哭着硬背起梁波,艰难地往前挪动。其实,杨恒升的腿已在雪崩中受了伤。
在艰难的行进中,战士们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突然,杨恒升眼前一黑,和梁波一起栽倒在雪地上。
“只有尽快报信,才能营救战友!”杜江南、赵勇奋力前进。刚走出1公里左右,腿部和面部受伤的赵勇也昏倒在雪地上。
杜江南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一定要火速把信息传递出去!他用手捂住伤口,爬一段,滚一段,连滚带爬地向哨所行进。
23时30分,经过近10个小时的生死行程,满脸是血的杜江南终于将战士遭遇雪崩的情况报告给上级。
部队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组织力量营救。很快,梁波、杨恒升、赵勇3人获救,但没能发现其他3名战士的踪迹。
战士生命重如山。军委首长、成都军区及西藏军区领导十分关心失踪战士安危,多次指示采取非常手段开展营救工作。军区领导决定紧急起用直升机飞往西藏边防搜救。同时,团里派出搜救小组利用晚上气温低、积雪硬等有利条件,逐步向前推进,实施地毯式搜索。
3名战士终于被找到了,但他们已永远和雪山融在了一起。
面对艰苦的选择——
云中孤岛无私奉献
西藏军区边防处处长李军安:
海拔4655米的詹娘舍哨所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东段,面积40平方米,每年10月至翌年5月为雪季,6至9月为雨季,1至6月为雷电多发期,气温10℃至-30℃。
3月12日,就在3名战士牺牲后的第10天,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栏目播放了反映詹娘舍哨所官兵生活的电视片《云中的哨所》。半个小时的电视片,再现了烈士生前的音容笑貌。烈士王鑫的母亲直到节目结束还在擦眼泪:“没想到娃儿在那么苦的地方当兵,每次打电话却说一切都好。”
人称“云中孤岛”的詹娘舍哨所,生活条件异常艰苦。
哨所缺水,战士们夏天接雨水,冬天取冰雪化水。这两类水都缺少矿物质,常年饮用会脱头发、凹指甲。为增加矿物质含量,战士们在水缸里放上各种石头。为节约用水,早上一盆水众人洗脸,晚上加热一起洗脚。
哨所地处风口,一年刮风时间超过300天,风力均在六级以上。每年,哨所战士走下雪山,回到亚东县城,不用开口,人们都知道他们是詹娘舍哨所的兵——因为严重缺氧和强紫外线长期照射,他们有着紫黑色的脸、稀疏的头发、紫红肿胀的手、下陷成小汤匙状的指甲,那是詹娘舍留给他们的印记。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是边防官兵所向往的。30年来,每一个上詹娘舍哨所的官兵都是自己主动申请的。
在一些同龄人尽情享受现代生活时,哨所官兵心甘情愿地挤在20多平方米的吊脚楼里,在雪山之巅为祖国站岗放哨,接受大自然残酷的锤炼……
詹娘舍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魅力,让官兵无怨无悔爱着她?
是中国军人为国戍边的使命感。梁波告诉记者:在詹娘舍哨所站岗放哨,最能体会什么叫国境线,什么是国家主权,最能真切感受到作为雪域卫士的光荣和自豪。
是到艰苦环境中接受锻炼的进取心。赵勇告诉记者:人活着,就要有追求。当兵戍边,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能吃下詹娘舍哨所的苦,可以直面任何困境,接受所有挑战。
是战友间雪一般纯洁的兄弟情。杨恒升告诉记者:今年1月,靖磊磊收拾好行囊正准备回家完婚,得知老班长王国昌的姐姐患尿毒症须换肾,家里让他马上回去以备不测,他当即决定再次推迟婚期,把休假机会让给了老班长,没想到他和未婚妻竟再也不能完婚。今年春节,哨所官兵全部病倒,所有的药都吃光了,靖磊磊挣扎着起来给大家熬了一锅辣椒汤。
其实,记者知道,战士们有句话没有说出口:哨所是很艰苦,可再艰苦也得要人去守。我不吃苦,就意味着别的战友要去吃苦,所以宁可把苦留给自己。更何况,为祖国守边防,苦中有乐,苦中有光荣。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平凡,而又伟大。
翻过海拔4200米的嘎隆拉雪山,就到了西藏墨脱县境内。虽然2010年贯通的嘎隆拉隧道,让墨脱告别了全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县的历史,但每年也只能季节性通车,剩余的8个月,大雪封山,墨脱闭塞得犹如“雪域孤岛”。
8月31日清晨,经过7天7夜的艰难跋涉,西藏军区“墨脱戍边模范营”巡逻官兵又一次登上某山口。在墨脱,他们已戍守了整整50个春秋。
50年间,该营有29名官兵牺牲,其中大部分是倒在巡逻途中。
倒下的是身躯,不朽的是精神。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戍边军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集体?
寸土不丢 捍卫主权
都说西藏苦,最苦是墨脱。
在别处计量路途用公里,而墨脱得用天数。千百年来,通往墨脱的路,是一条人脚马掌踩踏、雪水乱石冲出来的崎岖山道。从西藏林芝进墨脱,要走三四天,除了翻多雄拉山,越过6条冰川,穿过8道飞瀑、几十处悬崖峭壁,还要穿越毒蛇出没、蚂蟥肆虐的原始森林。这条路上,马死人亡的事年年发生。
“都说走进墨脱苦,其实,墨脱官兵巡逻更苦!”林芝军分区司令员杨吉贵告诉笔者,“墨脱戍边模范营”官兵巡逻的地域多为原始森林,巡逻全靠两条腿。
巡逻一次,最短需要3天,最长需要15天,一路风餐露宿。老营长文豪在墨脱工作11年,趾甲盖走掉了31个。
翻开林芝军分区泛黄的《墨脱军人档案》,白纸黑字勾勒出一幅幅壮烈的景象:
2004年7月7日,24岁的一连班长饶平冒雨巡逻至一处陡峭山坡时,突遇泥石流。他奋力推开战友颜云潮,自己被泥石流冲下了山崖。陪伴烈士长眠在此的,还有两架因恶劣气候条件折翼的黑鹰直升机。
那年,带队巡逻的副教导员张继品挥砍刀开路时,一群毒蜂突然扑向他,将他蛰得直至休克。医生急救时,从他身上拔出了71根蜂针。
那次,战士颜乐巡逻时突然倒地。战友们解开他的衣服,才发现67条蚂蟥正在拼命吸血。
这些困难都吓不倒墨脱官兵。铭记着“绝不把领土守小,把主权守丢”的誓言,“墨脱戍边模范营”在一次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的重要军事行动中彰显着承诺的分量。
2011年7月26日,一支外军非法越过边境线,在我方一侧设置所谓“主权标志”。该营领导立即带队巡逻,将外军蚕食我国领土的标识全部清除。
2011年9月26日,4名可疑人员在边境出没。二连连长过小华带领14名战士,靠吃干粮、喝生水,在毒蚊、蚂蟥肆虐的丛林中设伏7天,将可疑人员全部抓获。执勤归来,15名官兵中有4人腹泄、4人患疟疾、4人感冒发烧。
“我们的身后,是伟大的祖国。我们必须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绝不后退半步!”过小华的话代表了一代代官兵的心声,他们在塌方、雪崩、泥石流频发,“盛产”毒蛇、蚂蟥、毒蜂的边防线上,徒步巡逻960余次,32次胜利完成重要任务,抓获刑事犯罪分子150余人,缴获反动宣传品1万余份。
把苦日子变成甜生活
“山顶在云端,山脚在河滩,说话听得见,走路要一天”,墨脱沟壑纵横、河流众多,当地民谚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有的地方虽然隔江相望,但绕行几天几夜也很难到达。
“墨脱难,难在路。”教导员刘永福告诉笔者。千百年来,人们渡河过江,靠漂牛皮筏子或在空中坐藤条笼子,每年都有人因此丧生。
为了把被江河“分割”的墨脱紧紧连在一起,1963年,墨脱官兵在雅鲁藏布江上打响了架桥保通的战役。副营长李春带着75名战士,翻雪山,攀绝壁,钻密林,整整走了100天,才将所需的12根长300米的钢绳运进墨脱,并用炮弹把钢绳送到了对岸,建起了墨脱的第一座钢索大桥解放大桥。李春的身上不仅留下了23道伤疤,还差点掉进江中。
2000年6月,解放大桥被洪水冲毁。可一年多后,又一座解放大桥矗立在原址不远处,这是官兵们与群众并肩奋战一年多后的重建成果。50年间,该营协助当地政府,建起了200多座桥梁,方便了群众出行,也便于边防管控。
过去,驻墨脱部队所需的物资,全靠人背马驮和直升机运输,1公斤大米从林芝运进墨脱,运费高达15元。有一年山体滑坡,运送的10万公斤粮食被阻在路上,全部霉烂。
一定要“把苦日子变成甜生活”!“墨脱戍边模范营”官兵用行动改写着“雪域孤岛”的历史:他们建起了墨脱第一座电站,每年为群众无偿供电30万千瓦时;他们向荒山要粮、要菜,共开垦荒地400多亩,使粮食、蔬菜自给率达到75%以上。近10年间,官兵们在墨脱种出稻谷50多万公斤,仅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约运输费上千万元。
2008年7月,“墨脱戍边模范营”想大力发展生猪养殖,解决官兵“吃肉难”问题,但苦于无种猪。林芝军分区闻讯,当即为营里买了一对种猪,由于不通公路,无法将种猪运进墨脱。这事层层上报,惊动了中央军委。
军委首长特批,用直升机将这对种猪空运进墨脱。如今,这对种猪成了建设墨脱的“功臣”,子孙后代遍布军营和村寨。此后,军分区又向上级申请,用直升机把鱼苗、种鸡、种鸭、种鹅运进了墨脱。
50年里,该营在墨脱创造了“28个第一”,结束了墨脱不通电、不通电话、不通网络的历史;帮助地方培养2000余名各类技术人员;引进优良农牧品种、推广新农作物项目12个,帮助800多名群众走上了致富路。
8月5日,笔者在该营听到两条喜讯:营部军医郑宗钊、地球站站长刘磊考取了研究生,战士徐志远被军校录取。
可22年前,该营的18名战士,冒险闯过多雄拉山后,却在全国军队院校的招生考试中全部落榜。
这一情况刺痛了墨脱官兵的心。随后,营党委决定办文化夜校。2009年3月,林芝军分区党委作出决定,凡是准备报考军校的墨脱官兵,报考前一年到林芝补习文化课。20年来,该营先后有22名官兵考上各类军事院校,38名战士直接提干,9名干部考上研究生,600多名官兵获得本科和大专以上文凭。
“让我回墨脱吧”
2000年,一位得了无名疾病的年轻妇女,被送到卫生所。作为唯一的医生,22岁的军医亓三彭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她疼得满地打滚,直到生命终结。这件事,连同缺药缺器械的窘境,给新来不久的他当头一棒。
亓三彭决心要做点什么。没有药,他自己上山挖草药;业务不足,他多花时间钻研。2005年5月,驻地发生流行性腮腺炎,他冒着被疫情传染的危险,逐村逐寨为群众诊治,使流疫得到了控制。
12年里,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部队的好‘门巴’(藏语:医生)”的他,步行4000多公里,为民治病3100余例,做手术50余次。
今年3月,林芝军分区党委考虑到亓三彭长期在墨脱工作,身患多种疾病,家人长年得不到照顾,准备将他调到林芝工作。他找到司令员杨吉贵、政委昂旺说:“墨脱需要我,我热爱墨脱,就让我留在那里吧。”

李素芝。2004年在卫翰韬、黄伟明、袁英明执导的电视剧《杨门女将之女儿当志强》中出演宋太祖第四子、宋太宗侄八贤王;2006年主演根据西藏军区总医院院长李素芝将军的先进事迹而改编的电视剧《雪域情》,饰演林书芝(原型为李素芝)。
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西藏军区,新疆军区。后改为七大军区。即把西藏军区归为成都军区,新疆军区归属兰州军区。但至今西藏和新疆军区比其它省军区高半个格,即司令员和政委是中将。其它省军区司令员为少将。
山楂树之恋老三爸爸现在是息影状态,山楂树之恋老三爸爸扮演者是孙海英,因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被观众熟知。孙海英最后的作品拍摄于2019年的传承电视剧,此后没有作品出示。截止2023年5月30日处于息影状态。孙海英,1956年10月07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先后进入西藏军区话剧团、沈阳话剧团等剧团。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