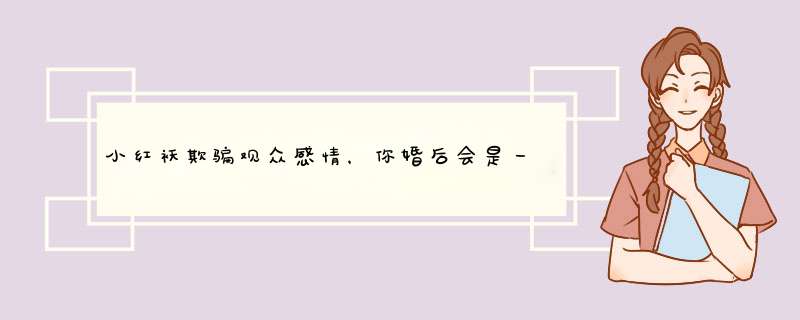
对我来说,家人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女生一般都会比较顾家啊,这是毋庸置疑的。可能在结婚前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自己未来的发展,但是在结婚之后,尤其是有了宝宝之后,会把大部分的精力转移到家里,因为对于孩子来说,陪伴比较重要,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在谈恋爱的时候,爱情比较重要,再结婚以后是宝宝和家人比较重要。
对家庭负责任,我觉得应该是每个结婚以后的人应该做到的一点,这个是很基础的一个点,不能因为工作上的忙碌,或者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发展而忽略家人的感受,以及很少的时间陪伴在孩子的身边,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他们需要陪伴的这一段期间没有陪伴他们,那时候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你是后续弥补不了的。
可能你在没有陪他们的时间里,让你的事业更进一步,或者是未来发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孩子们的心里,他们就是没有母亲陪伴的,那么他们对你的感情就没有那么的深。哪怕以后你每天陪在他们身边,都弥补不来那一段时间,你不在他们身边的陪伴。对父母来说,孩子是最重要的,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先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去考虑。
自己辛苦努力的挣钱,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所以不能本末倒置。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我觉得不管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对另一方负责,还是在结婚以后对一个家庭负责,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尽到的义务,因为如果结婚后和结婚前没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没必要去结这个婚。一个人,他对自己的家庭都不负责任,那你想她在事业上能有什么成就呢,她又能对谁负责呢。
闺女拼音: gui nv
闺女解释: <轻>(1)没有结婚的女子。(2)<口>女儿。
闺女造句: 1、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2、看来,在找到下一份活儿之前,埃尼斯就只好跟他那已经嫁了人的闺女呆在一起了。但是他心里头美滋滋的,因为在梦里,他又见到了杰克。
3、两个闺女跑了,那个最小的男孩儿和她丈夫一起过。
4、你好吗,我的美国闺女?
5、有一天,妈妈得到一块红布,她拿针给小闺女做了一件小红袄。
6、一旦你闺女的头发够长了,你就给她扎起俩小圆髻。
7、我的大闺女将告诉您 “两天了,我们没有一块面包,四个大人,内人害着病。”
8、从此,她妈妈管小闺女叫“小红袄”。
9、这位当妈的透露她希望他们家闺女能同罗素·克劳家的公子泰尼森结婚。
10、我的好闺女!
11、闺女们看过吗?
12、这大家伙喜欢你们家小闺女真令我惊讶,不过孩子和动物之间经常有些我们大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13、本来,计划好的,回来的时候由毛姐把两个孩子从学校接出来,然后,把我闺女安排在回来的班车上,她。
14、到家了,还发什么愣,快,抱你闺女下车了。
15、和她闺女去她妈妈那里过中秋。
16、梁妈教闺女喝酒,是16岁之前的事。
17、徐丑子的大女儿在不经意间便出落成为一个大闺女。
18、为了你自己掐 操出的闺女。
19、老人十分疼爱这个女孩,好像她是自己的亲闺女。
20、亲我闺女之前,得到批准了吗?
21、他们并不想扔掉三个闺女。
22、几个月前我从不看这个节目。后来大闺女要求把节目录下来这样她就能在她自己的时间段收看。
23、我所住的地方不允许养宠物。这让我非常感激。因为不然的话“大闺女”总会要不断为此事缠着我。
24、他有两个孩子,一个闺女,一个小子。
《新世界》小红袄结案,8大证据锁定一人,万茜亲自透露:是他!
播报文章
小猫追剧
发布时间: 2020-02-06 20:08娱乐领域创作者
《新世界》是一部由徐兵编剧及执导,孙红雷、张鲁一、尹昉、万茜、胡静、李纯、赵峥等人主演,周冬雨、宋丹丹、周一围、李成儒等人客串,首播于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的现实题材剧。
如果要说《新世界》中最大的悬念,那必然是小红袄,虽然剧中给出的线索不少,网友众说纷纭,但小红袄的真实身份目前仍无定论。最新剧情里小红袄重出江湖,杀害了一名卖菜的女子,根据哈德门香烟和莱卡3D这两条线索来看,李成儒饰演的丁师傅成了最大嫌疑人,小猫君也误以为小红袄就是他。然而,这不过是编剧放出的又一个烟雾弹而已,小红袄其实另有其人。
小红袄此次作案时,尽管用帽子和围巾将脸遮得严严实实,让人看不出他的真面目,但是暴露了他的几点特征。小红袄逃离现场时动作飞快,说明是一个行动敏捷的年轻人,据此我们可以排除4个嫌疑人,分别是徐允诺、警署的老胡、李成儒饰演的丁师傅、一大把年纪的关老爷;小红袄个子不高,又可以排除铁林(张鲁一饰)、周一围饰演的高医生;根据小红袄的面相、眼睛、手来比对分析,不难看出小红袄就是十七(洪洋饰)。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有以下8点推论:
1、十七(洪洋饰)是本地人,常年居住在胡同里,符合小红袄的关键特征;
2、十七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给新入狱的犯人拍照,这说明他跟宝元馆周老板(梁天饰)一样,都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女人,同时由于爱好、擅长拍照,他就机会接触到莱卡3D相机;
3、十七(洪洋饰)家中只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未曾结婚,符合单身独居的特点。而且他长期在监狱上班,平时见不到什么女人,会有强烈的性压抑和性冲动,这一点符合田丹的分析;
4、小红袄的作案规律是一年杀一个人,杀的都是穿红袄的女子,可是这次却不符合正常逻辑。联想到十七因为没有看管好田丹(万茜饰),被金海(孙红雷饰)暴打一顿,心里憋屈的他无处发泄,于是又出来作案;
5、小红袄三个字一共十七划,骆驼两个字恰好也是十七划,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编剧刻意为之,反正小红袄和骆驼都跟十七联系起来了;
6、在官方发布的一则预告片中,十七说”我很能忍的”,画面阴森诡异,令人不寒而栗。田丹(万茜饰)在狱中的时候,偶尔会有十七的镜头一闪而过,回想他看田丹的眼神,分明有些异样和变态;
7、有人指出,小红袄杀卖菜女子一案中,十七没有作案时间,但这实际上并不准确。金海只是让十七继续守在关亲王的那座监狱,假装田丹还在狱里,事实上并没有将十七囚禁,因此十七仍有活动自由;
8、十七性格懦弱孤僻,平时唯唯诺诺低眉顺眼,从不与人对视,从不与人争吵,连到手的金条都要让给同事,看上去良善无害,没什么存在感。但这种人长期生活压抑,体内的负能量一旦爆发,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十七变成小红袄这种变态杀手,没什么可意外的。
《新世界》的大结局是完美的,田丹和徐天在一起了,金海在南方舟山等待大樱子和刀美兰的消息,他们一起回到了北平,大樱子和燕三结婚了,坏人都死了。
1、坏人都死了。
《新世界》用漫长的70集终于拍摄完了这22天。电视剧里面有几个反派角色,首先是权利最大,老谋深算的沈世昌,他在得知田丹没有死之后,在新世界来临的前一天收拾所有的东西想逃出北平,在出去的途中被田丹他们抓到,沈世昌想最最后的挣扎,为田丹的同事出手当场打死。跟随者沈世昌一起出来的七姨太被抓走,心灰意冷的她因为无所依靠听天由命的跟随着解放军。沈世昌的女儿柳如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面的坏人,但是她毕竟帮助沈世昌完成了好几次刺杀,最后也被抓走,和七姨太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沟通,柳如丝趁乱逃走,回到自己的别墅当中,在浴室镜子面前,看着自己美丽的面容,自杀。这个电视剧中最让人生气的反派铁林最后被自己的老婆出卖,被徐天抓到,徐天想让他到新世界接受审判,在这个途中铁林逃跑,劫持了大樱子,被徐天一枪打死。冯清波则是被铁林打死。
2、好人都获得了爱情。
电视剧中最大的惊奇就是金海没有死,他通过假死逃到了舟山,在新世界来临以后,刀美兰通过田丹知道了金海在新世界不会受到处罚,就和大樱子一起去到了舟山,他们三个人一起回到了北平,而徐天则在石景山当探长,在金**的稻田世界里面,邂逅了前来寻找他的田丹。大樱子也和燕三结婚了,他们在家里打扫卫生,幸福的味道徜徉在他们每个人身上。
你看了吗?
皮草吧!小貂,嘿嘿。内搭和裤子可以时尚亮丽些。
皮草短上衣,中长款的裙子,靴子。
我是私人形象顾问,若是搭配不好可以来找我。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6%AC%BC%BE+%BB%E9%C0%F1&in=8764&cl=2&cm=1&sc=0&lm=-1&pn=42&rn=1&di=73680968&ln=140 这样的礼服当地应该有出租的。
她与父亲的决裂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吧?我不预备装摸作样把我这里所要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吧!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妨站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的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的把木匠找了来。
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始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盏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颁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什么干什么于。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晚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核桃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久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阿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善成粉,搀人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于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拍屉看看,渐渐疑心张于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忧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土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大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面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中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札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巳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挎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搪前挂下了中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项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宇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绘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婉婶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策。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妨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弄堂房于里。(我父亲对“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调张,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摸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被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磕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借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人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 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自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①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①Beverley Nichols,通译贝弗利。尼科尔期(1899- ),英国作家。著有小说《序曲》、《自我》、《无情的时刻》,自传《二十五周岁》、《父亲的形象》等。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①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① 《九尾鱼》是近代作家张春帆(漱六山房)所著的狎邪小说。
花园里养着吸狐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邀遏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闻,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绘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习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定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
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