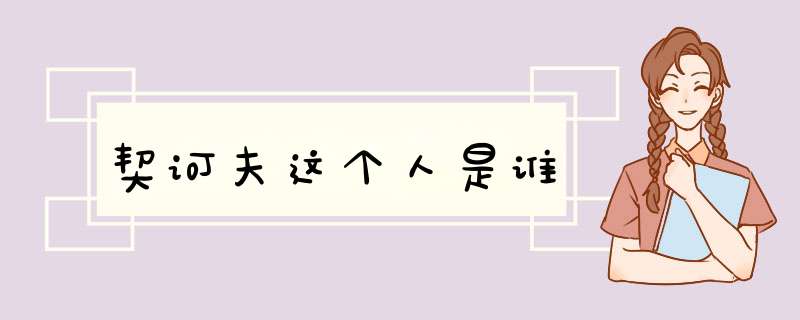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2020年9月13日22点52分,距今仅仅两个月之前,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一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就是原航天工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知非。老人家为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奉献了一生,享年92岁。
同时陈知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开国大将陈赓和烈士王根英的遗孤。
陈知非1929年,在上海出生,由于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父母没有办法亲自抚养他,因此自从4岁和父母分开后,陈知非便再没有见过母亲。
而陈知非对父亲的了解,则多是从外婆和舅舅那听到的。舅舅和外婆总会告诉他说父亲又到哪了,父亲又打了什么胜仗了,每次听到这些,陈知非都会很高兴。
一直到抗战胜利后,17岁的陈知非才见到父亲。
陈赓这也是在阔别十三年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儿子。
眼看如今的儿子已经不再是4岁时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个高大的小伙子。陈赓的内心十分的激动,这位大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碰到了。
他把陈知非从头摸到脚,边看边说:“你真像啊,真像啊”。
陈知非听着父亲的话,也流下了泪来。
他知道,父亲陈赓这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王根英。
王根英,原名庶心,1907年出生于上海。由于出身贫苦,为了补贴家用,王根英只能很早地就来到纱厂做工。
正是在这里,王根英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立志投身革命,也正是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陈赓。
提起陈赓大将,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位文武双全的大将,出身黄埔一期,深得当时的校长蒋中正先生的器重,同蒋先云、贺衷寒一起被称为“黄埔三杰”。
此时的陈赓,正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有时候会去工人夜校兼任教员。
来听课的人大多数是工人,在这其中有个17岁的纱厂女工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女工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工人领袖,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王根英。
在斗争中王根英深感自己的文化低,所以夜校一成立,就约了妹妹和十几个女伴,成为夜校的第一批学生。
陈赓来自湖南农村,开口闭口总爱讲点“农民理论”,可王根英却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
所以开课不久,她就和陈赓争论起来,而且学员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陈赓,一派支持王根英。
这当时在夜校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可能也是缘分的一种吧,毕竟很多时候,鸳鸯都是从冤家发展起来的。
两人就这样争论,越争,陈赓越觉得眼前这个姑娘可爱。
陈赓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看着眼前的王根英,陈赓便总是有意无意地去找她搭话,但是当时的王根英太沉迷于学习,对于陈庚的示好并没有太多反应。
但是陈赓可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眼看王根英对自己的示好没有表达,便直接跑到了王根英的父母家中。
陈赓十分的聪慧,来上海没多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因此王根英的父母十分的喜欢陈赓。
而陈赓也借此机会向王根英表白,但是王根英还是拒绝了陈赓,因为此时的王根英觉得,自己欠缺的学习实在太多,必须要抓紧时间去学习,怎么能有时间去考虑儿女私情呢?
因此,自己第一次主动出击的爱情,就这样基本夭折了。
其实在认识王根英之前,陈赓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1917年,当时的陈赓年仅14岁,还在小学读书,家里由父母做主,给他定了一门亲事,让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媳妇。
但是对于这种包办婚姻,陈赓根本就不满意,所以在新婚之夜,陈赓非但不入洞房,还一再要求父母把媳妇送回娘家。
陈赓的父母并不让步,甚至以武力威胁陈赓,陈赓见此,便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临走时,他对女方说:“我要走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有可能一辈子都不回来,你还是回到娘家去吧”。
就这样陈赓一去不回,一年后,陈赓的父母也只好赔了一笔钱,然后把这个儿媳妇送回了娘家。
而这一次遇到王根英是陈赓第一次真心实意的喜欢一个姑娘,虽然第一次的进攻没有成功,但是王根英已经彻底地占据了陈赓的内心,是他久久不能忘怀。
在1924年陈赓进入了黄埔军校学习,在学校期间,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陈赓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几天几夜没合眼,查找出了凶手。
何香凝一看陈赓如此的果断、勇敢,并且为人正直,便想把小女儿许配给他,但是却被陈赓婉言拒绝了,因为这个时候陈庚的心里只有王根英一个人。
本来以为不知道什么才能再相见,但是老天还是眷顾了两个人,在3年后,陈赓和王根英两个人又再一次相见了。
在陈赓走后的几年里,王根英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1926年10月至1927年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王根英都积极参加了,在这期间,王根英逐渐的成长为了一个工人运动领袖。
周恩来很欣赏她的组织能力和勇敢精神,因此提议她当妇女执行部长。
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成立,她当选为市人民委员。
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根英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
而此时的陈赓,则正领导警卫营担任整个大会的警卫工作,而且他也是代表之一。
在人群中,陈赓很快地就认出了王根英,几年前的火热的内心一下子被点燃了。
在大会期间,陈赓特意选了个距离王根英近的座位,虽然会场极其的严肃,但是陈赓的内心却总是会被王根英所吸引走。
实在无法按耐自己心情的陈赓,突发奇想,拿起笔来写了一个纸条,递给了王根英。
此时的王根英正在专心地听报告,一看一个纸条递到了自己的面前,然后回头一看,是陈赓,脸一沉,气哄哄把纸条拿过来。
她打开一看里面的内容,上面写着:"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我想向你郑重求婚,希望你嫁给我!陈赓。"
王根英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然后回头看了一眼陈赓。
此时的陈赓跟原来也不一样了,更加的英姿勃发,十分的英俊。
王根英心头一喜,但是马上就有些生气了,她对于陈赓这种求婚的方式,感觉很不满意,有些太随意了。
王根英心中灵机一动,她决定捉弄一下陈赓,于是她小嘴一嘟,转身就将纸条直接贴在了身边的墙上,然后继续坐正了听报告。
陈赓一看,一张纸条过去了,久久没有回应,显然是石沉大海了。
但是陈赓这个小伙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而是又写了一张纸条传了过去:"根英,我爱你!我请求你做我的妻子!"
王根英收到后,瞥了一眼,又将纸条贴到了墙上。
陈赓一看,这倔强劲儿也上来了,于是继续写:"根英,我发誓娶你为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但是这第三张纸条传到了王根英手上的时候,王根英索性连看都没有看,而是直接贴到了墙上。
这个时候,大会正好看到一半,会议中场休息,一看墙上贴着的纸条,大家就都围了上来。
围着纸条,看着纸条上的字,都笑了起来,有人就问王根英:“王根英啊!你这样处置陈赓的情书,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陈赓这时候倒是发扬了自己“脸皮厚”的精神,不仅不觉得不好意思,还特意挤到人群里顽皮地说:"根英这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正在向她求婚呢!"
而王根英,脸一红,就跑出了会场。
虽然,王根英对于陈赓的这种方式比较不喜欢,但是她还是能感到陈赓的确是真心的喜欢自己。
当时代表开会的地方,就在陈赓他们特务营驻地附近。
黄昏时分,陈赓又把王根英约了出来,两人一起到江边去散步。
在只有两人的情况下,王根英也就没有那么拘谨了,两人在江边漫步,陈赓不断地讲着军中的故事,王根英听得十分地入神。
王根英亲热地挽着他的胳膊,静静地看着陈庚。
陈赓突然话头一转:“你怎么不说话”
“叫我说什么”
“说你要嫁给我嘛!”
王根英用拳头直捣陈赓的胸口:“瞎讲!”
陈赓一本正经:“根英,说真的,咱们结婚吧。”
王根英深深叹了口气:“我不是不想结婚,可是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有了孩子,我们怎么斗争”
陈赓呼地站起来:“斗争都得是光棍”
“你小声点!”王根英把手放在他的手心里,“再等…4年!”
“什么你要我等成老头子”
“那再等……两年。”
“不行,顶多等——两天!”
“啊”王根英急了“现在大家正在开会,你让人家笑话。”
说罢,又生气地走了。
陈赓回到军营,免不了被兄弟们笑话一顿。
但纵然这个时候,陈赓还是没有忘记自己幽默的本色,躺在铺上, 还在开玩笑:“你们谁要能说动王根英和我结婚,我就给他当众磕三个响头”
大家说笑一通并不在意,可这话传到了周恩来耳中,周恩来便来到了陈赓的宿舍。一进屋,就被大伙围在中间。
周恩来往床上一坐问:“陈赓呢他怎么不过来”大家一听“有戏”,立刻将陈赓架了过来,要他给周恩来磕三个响头。
周恩来笑了:“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来找我”
陈赓脸一红:“我欠了你的债呢。你忘了么去年我给你当秘书,颖超千里迢迢来广州,你让我拿着她的照片到码头去接,我个大活人就楞没接着,害得颖超摸了半夜才到…”
“这有什么嘛我们不就是当天结的婚吗这次,我一定让你明天当上新郎。”
说罢,周恩来又把陈庚埋怨一番,说他这个爱情细胞太缺乏,这求婚方式太过于奇葩,众人大笑一番之后,周恩来便出门给陈赓去办事了。
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来到了王根英的住处,一番谈心之后,王根英点了点头,同意马上结婚。
其实本来王根英就对陈赓有好感,只不过是一时生气而已。如今经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说,自然也就同意了。
但是王根英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新婚之夜,不许陈赓那帮兄弟来“胡闹”。
于是到了第二天,陈赓和王根英的被子搬到了一起,就算是完了。
两个彼此钟情已久的年轻人,终于结为了夫妻。细算下了,这一别几年,两个人在自己的战线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又能再次重逢还能最终走到一起,这不得不说,实在是上天注定。
婚后的生活是无比甜蜜的,两人终于没有彼此之间最后的隔阂,彼此只属于对方,这是王根英和陈赓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可是就在两人结婚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夏斗寅叛变了!
没几日,汪精卫又密令何键屠杀革命者,“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个漏网。”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
鉴于形势的严峻,王根英奉命要回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此时两人刚刚成婚,却马上就要面临分别,这可能是人世间最残忍的事情了。
正所谓相见时难别亦难,两人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能服从组织的安排。
王根英走的那天,周恩来赶来送行。
他们在新房中把最后一点米面全都做了干粮,并给周恩来做了一盘他爱吃的红烧狮子头。周恩来对陈赓说:“你找了个好媳妇,心灵手巧,你可别忘了人家。”
“忘不了的,我们相约,每晚相思一刻钟” 王根英又被他说得脸红了。
陈赓滔滔不绝地说笑着,借以掩饰他内心的难舍难分。
就这样,王根英秘密潜回上海,而陈赓则跟周恩来去了九江。
不久,南昌又爆发了“八一”起义,陈赓奉命来到了南昌,参加起义,一对刚刚结合的恋人,此时天各一方,为民族的事业奋斗在生死线上。
王根英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工作繁忙而危险。回到上海之后,王根英一直惦记着陈赓的安危,但是久久没有消息,这使得王根英揪心不已。
结果,没多久,就传来了陈赓负伤的消息。
原来陈赓在南昌起义后,随军进军广东,在途中,陈赓左腿中了三弹,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了,无奈之下,只能来到上海养伤。
此时距离两人新婚仅有数月,但是再见到陈赓,却比原来消瘦了许多,王根英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随后王根英将他安顿在家中,尽心照料,而陈赓也在组织的帮助下留了下来,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
在此后的生活中,斗争环境日益的险恶,在这条特殊的秘密战线上,王根英全力掩护和协助陈赓的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参与营救了大批被捕的同志,保卫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的安全。
在这期间,两个人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陈知非。
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进一步严峻,生活变得十分的困难,一家人需要不停的搬家来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
每一次搬家,陈赓和王根英最先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地形适不适合逃跑。
但是,这一段时光,也是两人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共同生活的时光,因此虽然艰险万分,但是却也弥足珍贵。
1931年底,陈赓奉命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王根英则继续留在上海,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
此后的日子,王根英和陈赓基本都是天各一方。
彼此虽然挂念着彼此,但是想见面却是极其的困难,甚至连互通消息都是极为困难的。
这使得两人开始很怀念前几年在上海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毕竟两个人还在一起,每天还能看到彼此,这就已经很难得了。
陈赓走后,王根英的生活也更加的艰难,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王根英只能带着儿子陈知非和一个烧饭的汽炉子,东躲西藏,开战起来了“城市游击战”。
有一天,王根英正在伏案写东西,忽然有人从背后抱住她,她回头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想念的陈赓。
“什么时候咱们永远在一起…”王根英对这离别的日子多多少少有些忧伤。
陈赓告诉她:“快了,组织上让你和我一道去江苏苏区。明天就走。”
王根英高兴得眼眶里流出泪花:“咱们终于要在一起了。”
“你快收拾收拾,把知非托给他姥姥。我出去一趟,钱壮飞也在苏区,我去问问她女儿有什么话要捎给他,很快就回来。”
可陈赓一走,几天未回,王根英便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了,又过了几天,陈赓还是没有消息,王根英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内心,便出门去寻找陈庚。
结果,同行人打听回来的消息是,陈赓被捕了!王根英听到后,瞬间就晕倒了。
原来,陈赓离开王根英后,到丽都大戏院去找钱壮飞的女儿,被一个叛徒给盯上了。陈赓跟他扭打起来,因为腿受过伤,没能脱身,被关进了老闸捕房西牢,后经党组织营救,又逃了出来。
陈赓逃出来之后,他回到岳母家去找王根英,岳母告诉他:打你出事后,她就抱着个孩子东躲西藏,门口老有人探头探脑,她不敢在家就躲到杨家滨乡下亲戚家去了。
陈赓一听,心里稍微地安稳了一点,也不能在上海久留,离开上海去了江西境内。
这年12月,王根英回到娘家,听到陈赓已经逃了出来,悬着的心就算是放下了。
丈夫没事,这对于王根英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可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这个厄运又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由于叛徒的出卖,回家后没几天,王根英就被捕了。
王根英被捕后,辗转押解到了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和帅孟奇、夏之栩等关在一起。
她在狱中三年多的时间里,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但是王根英凭借着自己坚定的信念,一直坚贞不屈。
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和蒋介石和谈时,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和叶剑英等到狱中看望了王根英,当场点名释放了她。
后来,王根英跟着周恩来到了西安,又来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分别数年的夫妻两人,终于再次相逢!
这些年来,陈赓自从知道王根英被捕之后,这颗心就没有一天安心过。
妻子跟着自己实在是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自己作为丈夫,没有办法保护妻儿,这使得陈赓非常的自责。
而作为一名革命军人,陈赓只能将这种苦楚深深的埋在心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场上消灭更多的敌人。
此时的陈赓已经是八路军386旅的旅长了,再次见到妻子,陈赓的眼泪喷涌而出,他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心中虽有千言万语,可却一句都说不出。
正所谓:小别胜新婚。这是形容恋人分别后重逢的心情。
而陈赓和王根英自从武汉新婚之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先是陈庚负伤,然后整日躲躲藏藏,然后两人又相继入狱。此时王根英在狱中四年后终于被放了出来,再见到恋人,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陈赓在1937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然而,就在两人历经磨难终于重逢之后,仅仅半个月,王根英便接到了组织上的通知,让她去延安陕甘宁党校学习。
两个人的心中极其的难受和不舍,毕竟才刚刚重逢,却马上就要分别,这对于分别数年的两个人来说实在太难了。
但是作为革命军人,服从组织的安排,是第一原则,因此陈赓和王根英都没有说什么。
对于王根英来说,自从被捕之后,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陈赓了,她深知都留好了遗书。
而今再次见到爱人,而且爱人还 健康 的活着,听罢后点了点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隔三差五的见上一面,已经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9月15日,陈赓将王根英送走,回到屋里,心里空落落的,他在日记中写到:离别时,彼此表面上都故作镇静,但是根英已背着我流泪矣
1938年秋天,从党校毕业的王根英被分配到了129师工作,担任 财经 干部党校政治部指导员,而当时陈赓的386旅,正在往这一带集结。
王根英十分的开心,终于又能再见到久别的丈夫了。
某一日,在队伍正在行军,陈赓骑在马上,远远就看到了妻子,兴奋的陈庚,狠狠的抽了一下马屁股,高兴地冲了过去。
到了近前,陈赓抱着王根英就转了三个圈:"喜从天降!喜从天降!天上掉下个王根英。"
这时候,看到旅长如此的兴奋,身旁的战友们哈哈大笑起来,纷纷起哄。
王根英一下子脸就红了:"看你那疯劲!"
陈赓依旧是当初在武汉写情书的时候的“厚脸皮”模样:"情不自禁嘛!"
但是,本来以为以后可以不再饱受相思之苦的两人,这一次见面,竟然成了永别!
1939年3月,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突袭, 财经 干部学校的师生们在转移的过程中受到了日军的袭击。
在混乱的过程中,师生们都被日军烧光了村庄,在混乱之中,师生们被冲散,王根英则带着一部分伤员,艰难的逃亡。
为了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伤员的安全,王根英将自己的骡子让给了伤员,自己则和警卫部队一起徒步突围。
就在好不容易刚刚冲出了被包围的村子之后,王根英却发现装有公款和重要文件的包没有拿。
她焦急道:"不好,还有一笔公款没有带出来。"说完,她不顾身边人劝阻,立刻前往驻地取回公款。
而就在她去了包裹,快要逃出村的那一刻,日军发现了她,很多同志们躲在远处看到她被机枪扫中倒下。
战友一看王根英倒下,立刻红了眼,立刻组织起队伍杀回村子。
等来到王根英面前的时候,王根英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对要背着她突围的同志,王根英低声 的 说道:“不要管我,我不行了,你们快快突围!请转告陈赓,让他狠狠的消灭日寇,转告陈赓”
就这样,年仅32岁的王根英,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这时候的陈赓正率领着八路军386旅越平汉线西进,一日陈赓正在给部队讲话,通讯员送上了一份电报。
他一看,浑身就是猛然的一震:王根英同志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壮烈牺牲!
陈赓忍不住痛哭,愤怒的他猛然拔出了手枪,对着天空砰砰射出子弹。
他流着泪水,独自在积雪尚未融化的树林里站了很久。
然后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来20个字:"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此后,陈赓就中断了日记。
陈赓强忍着夫人离去的痛苦,坚持到了百团大战胜利之后,陈赓病倒了。
半个月持续的高烧和昏迷,使得陈赓整个人都脱了相,虽然身边马海德等名医,但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是啊,再高明的医生,再好的药,又如何能医得了陈赓心中的创伤呢?
众人围坐在床前,看着昏迷的陈庚,只听到他在不停的喊着:根英!根英!
王根英牺牲之后,陈赓许诺要为他守节三年。
三年之后,他才开始重新考虑组建家庭,和傅涯结婚。但是陈赓对于王根英的思念,却延续了一生。
陈赓生前不止一次在傅涯面前诉说着自己失去王根英的痛苦。
1961年,陈赓病逝,在弥留之际,陈赓一直喊着“怀申,怀申。”
“怀申”陈赓孙女的名字,申就是上海,而这个名字,也是陈赓对于自己和王根英在上海那段岁月的怀念。
那是他们一生中仅有的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陈赓去世后,傅涯整理了陈赓的日记和文字资料,同时不断 的 奔走访问故人,为王根英烈士写下了传记——《报国何计女儿身》。
用傅涯的话讲:“这也算是偿还一点自己对陈赓同志照顾不周的心意吧。”
傅涯作为陈赓的第二任妻子,同为女人的她,对于王根英,一直十分的敬重。在她2010年去世之前,她特地叮嘱孩子们一定要将王根英和陈赓的遗骨葬在一起。
遵照傅涯的遗愿,2011年,王根英烈士的遗骨迁往湖南省湘乡县,和陈赓大将合葬。
在整理王根英烈士的遗骨的时候,人们在她的尸骨中发现了两枚子弹。
经过鉴定,一枚是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的枪弹,一枚是三八大盖的子弹,可见当时的王根英被机枪扫中之后,并没有立刻死去,而是随后又被敌人补射了一枪。
而这两枚子弹,也成了王根英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物。
陈赓和王根英这一对革命伉俪,生前为了民族独立舍弃了小家,经历了太多的分别,如今终于可以长眠在一起,再不用经受分离之苦!
吾辈众人,应当铭记先辈创业之艰辛,珍惜现在的生活。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