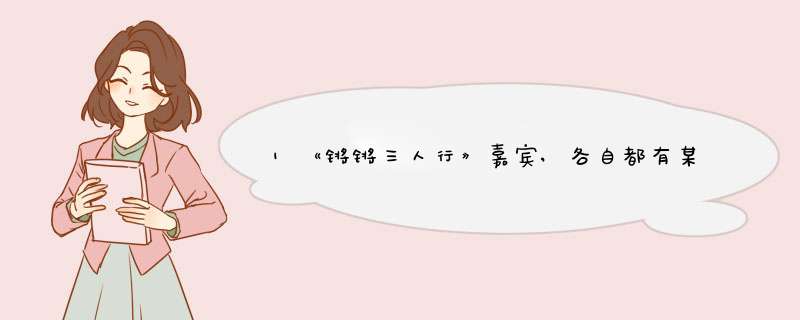
窦文涛和《锵锵三人行》
我当年刚到凤凰,是做娱乐节目,然后做《锵锵三人行》,是说自己的事。这是在香港的习惯,就是你只要不是新闻记者,你主持的节目都是娱乐,教人做菜的节目你也是艺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签合约,就叫艺员。
在去香港之前,各种类型的节目我都做过。那时我被称为采、编、播全能的,因为我是学新闻的,你能说得出来的节目我都做过,从儿童节目、游戏节目、新闻节目到讨论节目,后来又做节目监制,做管理工作。到了香港,这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凤凰的记者都不用扛机器,有人扛机器,不需要你扛。凤凰最初的机制是按香港的规矩,你是艺员,你说的话都是有人撰稿的,你是演员,你要声情并茂演绎得很活泼。
《锵锵三人行》的“母亲”是老板刘长乐,节目的点子是他想的,也是他点我来主持的。我唯一的创造就是这么一种聊天的方式。《锵锵三人行》,我是以很个人的面目出现的,而这又打破了过去所有的分工,其实这是一种复归。这个节目长期只有我一个人,每天一集。现在我有一个助理。我一个星期要做一集《文涛拍案》,要做五集《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有一个组的人在做,《锵锵三人行》长期以来只有我一个人,这在传统的谈话节目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说凤凰卫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此凸显一个人的个性,是因为它给了你舞台,这个舞台除了你还是这个舞台,于是乎你就有充分的空间去展示你的个性。可是实际上,这个节目要继续做下去,也会出现没有支持的难处。因为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锵锵三人行》,这个私人聊天的方式,其实是凤凰逼出来的,它给你的净是不利的条件,它每次都没有人帮你去请嘉宾,谈什么内容也不会有人告诉你,咱没那队伍,每次就我一人,然后嘉宾最好固定,每次都是这三人。其实人都是很懒惰的,脑子里通常都有一个传统:做谈话节目就得请嘉宾,找人来谈,找人策划谈什么内容。但是在凤凰,它不提供这一切,所以你就不可做,但是你又得做,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倒是莫名其妙地就被逼出这么个方法。
当我知道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有什么事老是这三人在说,聊的还是这社会上各方各面的事,聊的还是大家喜欢的?然后我就苦思冥想,想得脑袋疼。离录像不到一个礼拜了,有一天凌晨,我恍然大悟。那天想明白了很多事情,那天想明白的事情到今天还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原来如此”。就是生活里什么事情天天聊,而且还老是这三个人聊呢?那不就是聊天吗?生活里就有!你可以整天和你的同事、朋友聊,通宵达旦,再好的电视剧你都可以不看,你可以和你的朋友侃大山,老婆催你都不回家,说明这件事情里面肯定有吸引人的想法。“豁然开朗”有个特征,就是把一切不利条件都变成了应当的条件,于是这就成就了《锵锵三人行》。聊天往往是强调一个聊的过程,我就不会苛求真理,大家图的是个乐趣,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畅所欲言,享受的是这个。原来我们说谈这个新闻,你不是专家呀,即便你是专家,即便你学富五车,没一个人谈什么事情他都是专家。但是如果只是聊天,你就不会苛求他说的是真是假,说他的水平是高是低,大家享受了这种交流和聊的过程,就够了。一直到今天,这个东西都在帮助我,那是对我意义重大的一次突破,因为我知道了我应该怎样在电视上说话。在此之前,我干了多少年了,但是一直都模糊着,当然在电台工作多年,也有些帮助。
虽然想明白了,但是有的时候真正去做就得壮士断腕,放下那些套路,你才能够真的回复到真我——就是我本来是怎么说话的。我们不习惯在电视上那么拿着架子说话,我们喜欢自然地在电视上说话,但是有时自然是需要极不自然才能达到,真诚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在电视上,说句假话是容易的,脸不变红,心不跳,说句真话是会脸红心跳的,这是主持人必须经历的过程。一开始也会有人骂你,讨厌你,不习惯,但是凤凰允许你张扬你的个性。所以我说凤凰真的是改变了我,真正地改变了我怎么说话!
我这个人本质上是胸无大志的,我不会想着去改造,去革新,而且我这个人有点自卑,碰到什么挑战,我这个人本能的反应是畏缩。如果没有凤凰,我不知道我能做这么多。有时候它非理性地给你一些任务和压力,它也不管你合适不合适,它就让你干,而且干得十有八九都不如意,但是凤凰允许你失败,允许你待着。比如说来了个主持人,给你个节目,观众反应也不好,但是它也不炒了你,你就先待着吧。过几年又有个事,你再试试。
《锵锵三人行》,每天半小时,已经有2000集了,甭说节目的好坏,对节目主持人的练习,这里既要你一个人说话,又要和人交谈,还要倾听,又要提问,又要你把握时间节奏,因为这个是直播式的录播。天天在干这个事,对我真的是很好的经历。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又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个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你以为我口才很好吗?我没觉得。《锵锵三人行》里我经常会结巴,经常会词不达意。这个口才在普通人里至多也就中等偏上。我的注意力不在口才,与其说是思维,不如说是状态。我们这个行业最关键的问题和表演行业很类似,就是进入状态。人只要进入状态,笨嘴拙舌,词不达意都关系不大,人人都能感觉到你要传达什么。而当你没有进入状态,你说的话就像是语言的尸体,整理成文字,说文字非常好啊,但是没有用处。
从前我做的节目,都是我从头到尾做的。我更像个手工作坊,不是大工业时代的人,假如我生产出了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从头到脚都是我做出来的,我认为一个主持人的诚意到最纯洁、最纯粹的地步,就是要到这样一个程度的。
关键问题是节目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在这方面,就暴露出我们凤凰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凤凰的奇迹,照我来说就是一个侠客行,就是这么些人风云际会,凑在一起,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是也正因为是这种草莽、这种浪漫主义,产生了一些奇迹,这是正常的班子里面的人做不出来的东西。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它的奇迹是什么奇迹呢?我为什么叫它侠客行呢?侠客行就是因人而起因人而废。侠客的特点是一鸣惊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下子就出来,但是侠客的结局往往是悲剧,而且侠客往往是只能一回。侠客不老实,不稳定,对节目是靠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创造了新天地新概念的话,那这是创业了。但当你创出来一个平台,这个品牌你要继续维持,这个品牌要深入人心,这是一天一天要做的事,这就需要机制去保证。因人而起,比如说《锵锵三人行》,因我而起。好,把我的精力一转移,我那边的投入就不足了。因我而起,我做着做着也会烦了,但你要顶着这块牌子,烦了也得做,因为它卖钱。我都不想做了,你还要我做,我就只能做。你有什么机制保证它?那侠客哪还有激情?这是一门科学,但我们过去太不懂科学了。这就是我说的凤凰现在的危机。这其实是极简单的事情,但这就是我们的传奇。
希望对你有帮助
票房不懂你的浪漫
看到一部烂片收获满溢的票房,你总会愤愤,然而世界总不是绕着你一个人转的。刻意留意了下各个**院的排片,《我的唐朝兄弟》的场次寥寥。在众多新片和大片夹击的环境里,这部对我来说相当惊喜的影片,可能就此湮没在票房的洪水里。即便票房死得很惨,我希望影片本身可以畅往不朽。 不是每个导演都能将娱乐和情怀完美地交融,所以才会有大导演小导演和烂导演的区别。杨树鹏是个小导演,资历平乏,又显年轻,但他用一部《我的唐朝兄弟》扫平了去往大导演的山头阻路的荆棘。放任着大嘴去夸赞一个人,总让我觉得危险,就会下意识地提防下自己的目的,然而当你在《我的唐朝兄弟》中看到一种彻骨的草莽浪漫精神驾临苦竹林时,你就忍不住醉了。 两个唐朝强盗抢劫,意外救人,却喜欢上被救之人,于是习惯了一起闯荡江湖的两个人开始有了罅隙。对于这样的故事,我并没有抱多大期待。幽默轻松的台词和古典质感极美的画面萦绕着前半场,你会以为又是一部恶搞的喜剧片。然而村官里正的告密泄露了杨树鹏的秘密,人性成为他障眼法之下清风古马的表达,影片显得厚重起来。 杨树鹏没有刻意升华,而是顺着剧情溪水一样安静叙述,安静地让你起鸡皮疙瘩。就像安静的村庄被这两个闯入的强盗打破沉寂,命运的漂泊无定和纠缠就在这样的随遇而安里显示出它独到的天分。已经很久没有中国**这样“好玩着”说人性这个我们似乎已经淡忘的基本概念了,冲动的村庄在里正家长制的“官本位”思维下,逆来顺受却又怨愤满心,想跟孙悟空一样举棒造反又怕出事,于是一张张现实的嘴脸在镜头下鲜活起来。很熟悉,就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大多数国人:善良、懦弱、随大流、不具威胁性。只有一个人例外:小孩子长寿,可惜他是痴傻的。 黑泽明的美学一直隐藏在影片的某个角落,但在两个强盗兄弟感情的转换上似乎又有一些马丁o斯科塞斯《愤怒的公牛》的影子。 没有谁可以十全十美,成长总需要一个掩面而泣的过程。姜武可以不断吐唾沫说脏话,胡军也可以讲着黄段子手忙脚乱着女屠户难解的裤扣,然而这不妨碍一个叫“侠义”的词儿出现在作为强盗的他们身上。 善恶不过一念,侠义的寒光一闪,你就是草莽英雄。大唐开放的民风让一干豪云之士忘记魏晋,泥泞稻田里的打斗,现代摇滚精神的浪漫内核,古惑仔一样的传奇江湖梦,金风玉露一相逢时的酣畅性爱,诗人遍地行走的不羁和慵懒,都在泥浆四溅的干脆声中化作打动你的因子。 想起唐朝,就会冒出放荡不羁等豪迈的词儿,所以这也是一部适合梦回唐朝的人做梦的**。暴力与血腥,从来都是点缀。影片一开场已然定下了基调,浪漫的,浪漫的,浪漫的。懒洋洋的村庄,《卧虎藏龙》一样的竹林,远处可听见的鸭啼蝉鸣,还有紧束胸衣的美人,一种既粗犷又温柔的美感,就这样斜插进中国武侠**的类型群阵里。 据说影片删减掉了杨树鹏个人最喜欢的段落:“陈六强暴完罗娘,趴在树林里,月光打在他的背上,照着他背上的文身,是唐朝那种黑漆文身,文身有十二个字:生不怕官家人,死不怕阎罗王。”于是又得老生常谈分级。分级?那似乎是个跟唐朝一样遥远的梦。而失掉这样维系两个强盗兄弟感情转换重要基础的镜头,剧情有些跳跃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在这样的尴尬里,杨树鹏还要说更多的深刻内容,就让影片显得有些失控。简单点,也未尝不深刻。 当然整部片子,你基本上还是在笑的,只是临近结束,略显悲伤的情绪还是让心里不免有点堵得慌。这肯定不是杨树鹏要做的。于是他给出了一个光明的结尾:稻香、姑娘、笑声、清风拂面。就像杨树鹏一直想拍出的塔可夫斯基式的**:辽阔而深沉,风吹过荒野,把桌子上的花吹倒。 现在**结束,会有一百个不同于杨树鹏的解读,对于我,则只想沉浸在哗啦啦而下的浪漫雨中,吟唱失落的草莽青春:“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得像我年轻的岁月,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