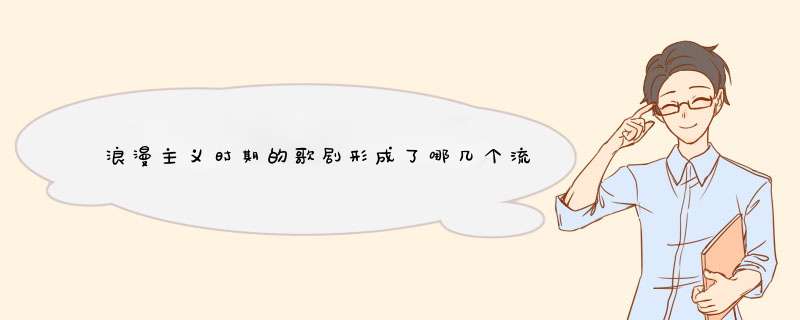
流派很多,主要以四大流派
意大利歌剧《阿依达》、法国歌剧《浮士德》、德国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俄罗斯歌剧《叶甫盖尼 奥涅金》。
十六至十七世纪之交,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这是文艺复兴时期音乐艺术发展的结果。歌剧是一种新艺术,公称opera,源于意大利语opera in musica,即音乐作品的简称,opera为opus(作品)的复数。它是音乐与喜剧相结合的综合艺术,最早称为“音乐做事”(favola in musica)或“音乐戏剧”(drama per musica)。
歌剧是音乐、戏剧、诗歌、舞台美术、舞蹈等交融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是高度集中的舞台表演艺术,也是声乐艺术中难度最大,最具艺术魅力的重要艺术形式。
歌剧产生于16世纪末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它是著名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1597年,诗人努尼里奇,作曲家佩里卡奇尼等根据神话故事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歌剧《达芙内》可惜早已失传,1600年作曲家丁·佩里所写的《犹里狄茜》是西方公认的第一部西洋歌剧,开创了歌剧的新纪元。到17世纪上半叶(1637年)世界上第一座歌剧院在意大利威尼斯建立,名叫“圣卡西阿诺歌剧院”,标志着歌剧已开始走向平民百姓,加之这时的歌剧在创作上的发展与创新、使歌剧从简单的叙述形式改变为戏剧性形式,从而使歌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到17世纪末,音乐发展达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产生了几位划时代的大音乐家,其中包括意大利的斯卡拉蒂,法国的拉穆和德国的巴赫与亨德尔。当时在罗马影响最大的斯卡拉蒂,他一生写了115部歌剧,确定了歌剧咏叹调的ABA基本形式,并在A段反复时加上装饰音及华彩段,极大地发展了人声的歌唱艺术,丰富了歌唱的表现力,推动了歌唱技术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只顾炫耀技巧的不良风气,当时歌剧舞台上活跃着阉人歌唱家,人们挑选出一些音色优美的男孩,给他们施行阉割手术,使他们在保存高音音域的同时,保存了男子的力度;另一种不良现象是,剧院为了吸引观众,引进某些与剧情关系不大的奇特情景,豪华的布置或盛大的场面,这样做削弱了歌剧的戏剧性和思想内涵的表达,使歌剧的整体性与艺术性有所下降。
格鲁克是歌剧史上的改革者,他提倡音乐服从戏剧的效果,主张歌剧的戏剧性和音乐性的完美统一,反对故弄玄虚的浮夸做法,主张除掉那些同戏剧和台词无关的装饰音乐。同时,格鲁克还提倡用本国语言创作,以发展各国歌剧,他的改革使歌剧通向了意大利浪漫主义的道路。
罗西尼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歌剧的先锋,他创作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威廉退尔》等杰作,标志着意大利歌剧步入成熟期,与他同样有名望的作曲家有多尼采蒂、贝里尼等,他们作品的特点是演唱者不仅需要有高超的声乐技巧,而且音乐旋律也优美迷人,把歌剧艺术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迄今为止,演唱难度最大的歌剧基本上都出自这三位作曲家之手,人们还常把这一时期的歌剧称为歌剧的美声时期。
在这三位作曲家之后,意大利歌剧的主要代表人物要数威尔弟,他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几乎全部都是艺术精品,如《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阿依达》、《奥塞罗》等,至今仍为世界各大顶尖级歌剧院的保留剧目。
在浪漫主义时期欧洲歌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各国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歌剧作品,如柏辽兹的《浮士德的沉沦》,古诺的《浮士德》,比才的《卡门》等等,到了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文艺界又出现了一股抨击浪漫主义幻想,揭示人类本性真实主义的作品。如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雷昂卡瓦洛的《丑角》等,普契尼是一位带有真实主义倾向的作曲家,但他的作品抒情色彩很浓,旋律优美,舞台效果很好,他的作品如《卡门》、《托斯卡》也能找到真实主义风格的影子,但从整体上讲,它们也是浪漫抒情的。
意大利歌剧在相当长时间统治着欧洲的歌剧舞台,随着它的发展和普及,在各国音乐家的努力下,逐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歌剧流派,如意大利歌剧、德国歌剧、法国歌剧,俄罗斯歌剧。但意大利歌剧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德国歌剧最早出现于17世纪,18世纪时汉堡歌剧已有了一定的声望,但尚未形成流派。格鲁克提倡歌剧的民族化,才使其渐渐成长起来,形成了占有一席之地的“德国民族歌剧”流派。莫扎特使德国歌剧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他的《后宫诱逃》和《魔笛》已是德国歌剧的传世佳作。韦伯是德国歌剧的重要作曲家,他的《自由射手》标志着德国浪漫派歌剧的开始,乐曲曲调带有民族民间音乐的特色,合唱在全剧中起着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形成德国歌剧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是瓦格纳,他主张把所有的艺术协同起来,共同创作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他认为音乐应成为表达戏剧内涵的工具,为剧情服务,他提高了乐队在歌剧中的地位,他一生创作的大量作品,如《飘泊的荷兰人》、《汤豪塞》、《罗思格林》、《尼伯龙根的指环》等,都是德国歌剧的典范。
法国歌剧是从1650年,一个叫贝兰的神父创作的用法语演唱的歌剧《牧歌剧》开始的。到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就出现了类似于正歌剧的法国大歌剧,法国歌剧的特点还在于剧本的文字性较强,语言比较含蓄,声音也较为圆润,因而比较典雅高贵,浪漫多情,抒情性较强,称之为“抒情歌剧”,如古诺和托马的歌剧《浮士德》、《迷娘》、《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到后来比才的《卡门》,德彪西的《佩利亚斯与梅丽桑法》的出现,使法国歌剧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俄罗斯音乐在欧洲尚不太为人所知道的时候,作曲家格林卡创作的《依凡·苏萨宁》及《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成为俄罗斯歌剧的奠基之作,对其后的歌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随后柴可夫斯基写出了《叶甫根尼·奥涅金》、《黑桃皇后》、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创作了《金鸡》、《萨特阔》,穆索尔斯基创作了《鲍黑斯·戈杜诺夫》、鲍罗廷创作了《伊戈尔王》等,都是典型的俄罗斯式歌剧,可能由于语言的原因,俄罗斯歌剧远没有意大利歌剧,德国歌剧,法国歌剧那样流行。
此外,随着歌剧的不断发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歌剧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普及和推广,一些结合本民族特点而创作的新作品不断问世,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有德沃夏克的《水仙女》,斯美塔那的《被出卖的新嫁娘》等,这些作品都是世界歌剧宝库中的明珠。
随着时代的发展,20世纪初,在美国、英国又出现了一些集爵士乐、踢踏舞、喜剧性话剧和轻歌剧于一体的艺术形式——音乐剧。音乐剧表现手法灵活,音乐、舞蹈、舞台美术都很现代化、因此,很快成了二十世纪最为重要且发展得最快的一项文化成果。风靡了全世界。经典剧目有《音乐之声》《猫》《悲惨世界》《西贡**》等等,都已被世界艺术界广泛认可,得到了很好的票房价值,流传到世界各地。
和西洋歌剧相比,中国歌剧产生和发展得较晚,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新的、先进的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作曲家黎锦晖创作了一批儿童剧,如《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我国歌剧的萌芽。1934年,田汉、聂耳创作了我国表现革命的第一部歌剧《扬子江风暴》,真正使我国歌剧发展起来的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掀起了盛极一时的新秧歌运动,创作了一批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中国特点的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白毛女》、《刘胡兰》等。1945年《白毛女》的问世则是我国新歌剧成型的标志。全国解放以后,又陆续涌现出了《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草原之夜》、《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歌剧舞台一时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崭新局面。“十年动乱”使我国的歌剧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推残。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的歌剧又有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批多种风格、多样体裁的中国歌剧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具有西洋歌剧模式的有《伤逝》、《原野》、《第一百个新娘》等,具有民族歌剧模式的有《党的女儿》、《木棉花开》等,这些歌剧在艺术性和时代性以及人物塑造等多方面有了相当明显的提高,中国的歌剧也日益走向成熟,慢慢发展开来。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夏尔·波德莱尔给的定义是:“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
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浪漫派》(初版于1919年)说的是19世纪德国的政治浪漫派——几个在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既无关国朝的政治浪漫派,也非干云集在《甲申文化宣言》大纛下的文化浪漫派。《政治的浪漫派》之所以值得一读,仅仅因为这本书一如施米特的成名作《政治的概念》,谈的是人类生活的秩序问题。当然,施米特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而是职业的公法学家,因此,他的问题域只限于如何是可能的人类生活秩序,而非如何是好的人类生活秩序。
施米特认为,包括政治浪漫派在内的一切精神历史现象,“无论自觉与否,都以某种正统或异端的信条为前提”〔1〕,“首先,基于看待世界的特定态度,其次,基于某个确定的最高权威、某个绝对中心的观念”〔2〕。换言之,“形而上学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基尔克的中肯之言,我们不能通过摒弃我们对它的意识而摆脱它”〔3〕。关键在于,在一个晨报代替晨祷的时代,“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即超验的上帝,被摒弃了”;两种新的世俗实在——“人民”和“历史”——成了人类生活秩序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4〕。
首先走上前台的是“人民”,政治浪漫派的鼻祖卢梭第一个在《社会契约论》中宣布了“人民”的全知全能,因为社会契约规定了“每一个合作者以及他的所有权利都让渡给了整个共同体〔即人民〕,每个人都完全放弃了自我”。在革命实践中,契约论的自由主义成份(即个人的自然权利)被抛弃了,政治(即人类生活秩序)变成了宗教,政客变成了教士。正是对“人民”这个“至高存在”的顶礼膜拜,激发了雅各宾主义清除一切政治异端的嗜血热情——人民公敌=无神论者;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名义下释放的却是可怕的人性私欲和疯狂的权力意志〔5〕。
如果说,“人民”是革命家的上帝,那么,“历史”就是保守派的神只。在博纳德、迈斯特和伯克等法国大革命的敌人看来,正是“历史”把天下一家的人类共同体(即人民)确定为具体的、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并使之具备了创造特定法律和特定语言以表达其独特民族精神的能力;惟有“历史”的持续性才能证明人类生活秩序的正当性,惟有时间的久远才是正义的终极基础。迈斯特甚至有“正当的篡权”(即在历史上可持续的篡权)之说辞,全不顾这话本身就有颠覆当下秩序的危险性,因为谁也不曾见过千年王朝,旧僭主的正当性很可能须臾之间让位于新僭主的正当性〔6〕。
黑格尔的原创性在于,他用自在自为的“世界精神”统一了被理性化为(民族)国家的“人民”和“历史”这两种世俗实在,于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上帝最终被挤下了神坛。虽然民族精神作为世界精神辩证发展的工具而继续发挥作用,其功能也足够强大,但“人民”这个实在中的革命酵素也得到了妥善保存。因此,从黑格尔体系中破茧而出的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地使“人民”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再次成为革命的造物主,不过这一次它同时宣称自己是“历史”的主宰——从而集两种正当性于一身。在此意义上可以断言,尽管在黑格尔那儿有反动的因素和基督教用语,黑格尔主义仍然充当了攻破传统基督教形而上学的特洛伊木马〔7〕。
施米特指出,“浪漫派的思想状态的基本特点是,他不让自己和自己的主观人格投身于诸神的斗争之中”〔8〕。于是,人民和历史都被浪漫化了。在浪漫派那儿,革命者的上帝——人民,“变成了忠实的、有耐心的、总是好脾气的人民,供那些没耐心的、神经质的和有抱负的知识分子赞赏”,变成了像儿童一样有无限可塑性的原始人,成为可供浪漫派支配的、非理性资源的承载者〔9〕。保守派的神只——历史,则被浪漫派当作逃避当前现实的手段,历史既是实在、又是非实在,无论是中世纪骑士的高贵,还是中国皇帝的庄严,都是反抗平凡、否定现实的一张王牌。虽然浪漫派往往把天主教会变成其情感的最后避难所,但上帝一点都不浪漫,因为永恒的和谐之前是最后的审判〔10〕。
施米特认为,以马勒伯朗士为代表的机缘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而上学——它把世界和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上帝用来恢复秩序和法律的机缘,以克服笛卡尔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精神与自然“悲莫悲兮生别离”的难题〔11〕。虽然这不是心物二元论的真正解决之道,连缓解也谈不上,只是把烫手山芋扔给了上帝,但在信仰者看来却并非意味着“牵强而浅薄”,因为“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职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能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新约·哥林多前书》,12:4-6)——在上帝那儿是不存在二元论的。问题是机缘论到了浪漫派手中被主体化了,其表达式则变形为:“我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无限数列中的第一位数,是一部无结局小说的起点”。换言之,一切理性形式、一切因果关系、一切规范和秩序都被浪漫派消解为“机缘”二字,消解为“一种游戏,就像一切游戏一样,它是用来引起惊奇和让人上当受骗的”〔12〕。施米特指出:“一个没有产生基于自己的预设的伟大形式和代表的时代,必定会陷入这种心理状态,认为一切有固定形式和正规的东西都骗局。因为,没有形式的时代是无法生存的,不管它在经济方面有何表现。假如它没有不断发现自己的形式,就会在其他时代和其他民族的真正形式中寻找成百上千的代用品,但也只是为了把这些代用品作为赝品立刻抛弃”〔13〕。
施米特认为,机缘论的要害不在于它的形而上学预设,而在于它的伦理实践、在于它否定了人的自由决断能力。马勒伯朗士把上帝的自由意志变成了普遍秩序、变成了完美的和谐,甚至神宠的结果也呈现为自然法则。笛卡尔在上帝的意志中看到了道德规则的基础,马勒伯朗士则把道德规则看成是永恒的秩序,甚至上帝也不能改变其中的一切〔14〕。人格神的上帝变成了自然神论的上帝,一如绝对君主制变成了立宪君主制;诚如博纳德所说:自然神论即是隐蔽的无神论。施米特指出,正是在这样一个以机缘论为形而上学背景的、市民阶级的理想秩序世界里,浪漫派的“精神革命”得以大行其道——分离的、孤独的和获得解放的个人不仅成为自己的教士、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诗人,甚至成为自己的国王、自己的终审法官和自己的上帝;审美情感替代了道德判断,一声叹息替代了政治决断〔15〕。于是,“梅特涅的警察国家在浪漫派看来也成了有机的、持久的、有根基的、稳定的、和平的和合法的”〔16〕。
施米特细致地辨析了浪漫派政治与政治浪漫派的区别,似乎在为自己日后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中的政治失足预先作好了注脚。施米特写道:“本质上不是浪漫派的人〔比如施米特自己〕,也可以受到浪漫主义观念〔比如多伯勒的长诗《北极光》〕的激励”〔17〕。“强大的政治能量没有能力找到自己的目标,它把巨大的力量用在了机缘性的时刻。这种以浪漫方式设想机会的政治,其不朽的典型是堂·吉诃德,他是个浪漫主义的政治形象,但不是一个政治浪漫派。他不去理解更高的和谐,而是能够分清对错,作出在他看来有利于正义的决定。……对自己骑士理想的热情和对假想的不义的愤慨,驱使这位可怜的骑士不自觉地对外部现实视而不见;……他的战斗荒唐可笑,然而这仍是战斗”〔18〕。然而,施米特不得不承认,堂·吉诃德“这个西班牙贵族常常接近于一种主观的机缘主义。他宣称自己对杜尔西妮亚的思念比杜尔西妮娅的真实面貌更重要。这是因为杜尔西妮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依然是理想奉献的对象,这鼓舞着他做出伟大的举动”〔19〕。那么,谁是施米特心目中的杜尔西妮娅呢?当然不是希特勒,而是一种以“彻底的概念化,即一种被逼入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一以贯之的思维”为前提的“法理概念社会学”、一种类似于凯尔森纯粹法理学的纯粹政治法理学——其核心命题为“主权就是决断非常状态”〔20〕。在施米特看来,关于主权者是一群信仰坚定的耶稣会士、还是一伙政治成熟的恶棍之类的问题,应该交给上帝去决断;公法学对此无能为力。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