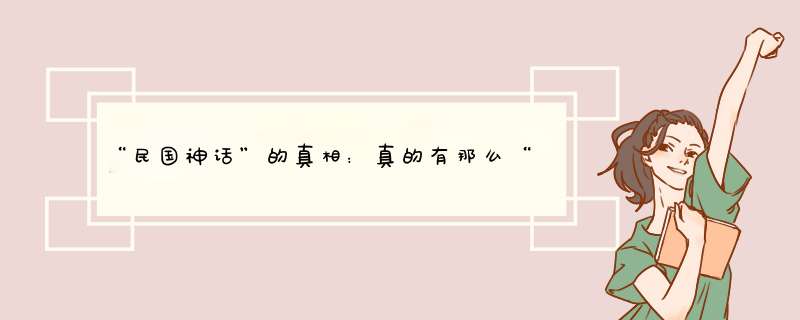
原文在这里
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我并无意于简单地彻底否定什么,只是想提醒,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对待文化,去看取历史。
■让“过去”回到过去,意味着让我们知识写作的历史叙事尽可能体现历史丰满的真实,而不是被单向度记录的过去。
■我们必须摆脱自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用更全面眼光对待文化看取历史
2003年参加上海城市精神大讨论,我在《城市:寻找精神的力度》一文中写道:“在文人骚客、名流淑媛、昔日豪门、官宦后裔、达官贵人的推动下,三十年代的上海被打扮成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流布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海上繁华梦,日益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价值判断的趋向。历史其实并不太长,人们竟这么快地遗忘了,三十年代上海曾经有过的腥风血雨,民不聊生,曾经有过的代表着未来的革命力量和代表着腐朽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我们赞美着名门淑媛从豪宅楼梯上风情万种款款而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杨树浦走在瑟瑟寒风中面黄肌瘦的芦柴棒、小珍子。怀旧之风毫无阻拦的流行,体现了我们精神世界的过于同一,精神判断的软弱苍白和混乱。”其实,当时我这样表达,并无意于简单地彻底否定什么,只是想提醒,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对待文化,去看取历史。
其后,我在各种文化研讨中不断提出,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的文化有其鲜明特色,也有它值得肯定的历史业绩,特别是作为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简单、粗暴地否定,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可是十几年下来,这一“神话”愈演愈烈,形成了相当一部分文化人知识写作的主要内容。请注意,我说的是“知识写作”,不是网民情绪化的吐槽,而是一部分以知识学养为依托、为背景,当然也包括一些看似有知识其实也未必真正消化了知识的,乃至一知半解的名人、大V的写作。在这样大批量的写作和大规模的传播下,在不少人心目中民国文化、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一时成了与当代文化抗衡的关于文化的历史叙事的主流,甚至简化成了一面对当代文化充满对立,而不是有借鉴、启发意义的被扭曲变了形的镜像。民国教材、民国范、民国知识分子、民国“自由宽松”的文化生态,成了公众生活中的热词和竞相追逐的文化时尚。
“民国热”应依托历史真实“剧情”
那么,历史真实的“剧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民国神话”真有那么“神”吗?不妨先看看最近几年被热炒的民国教材。
首先,民国教材本身是一个笼统的全称概念。被大家追捧的主要是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他们并不能代表民国教材的全部。而且,有些被大家称之为教材的读本,名为教材,实际上是课外阅读。完整的民国教材,既有民间编修的,也有官方编写的。含糊地赞美“民国老教材到底有多美”实际上是简单使用了全称肯定判断。我的大学老师一再教导我,论述命题切记慎用全称肯定。所谓民国教材,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空洞概念。具体来说,对民国教材的肯定和赞美又在于,其编写的童心、非政治化和美文的特色。但实际上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些(请注意,我这里不用“民国教材”,而用“这些”)教材的特色。排除官修教材,即以民间编修的教材来看,已经有专家指出商务印书馆教材和开明书店、世界书局教科书之间的差异。
商务版以培养新中国新国民为主旨,连课本名称都谓之 《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国文教科书》和《复兴国语教科书》,将教科书的编辑密切联系当时的国民革命,特别重视雪耻救国的内容。而开明版则更强调,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幸福自立,在于身心的健康。在教育思想上,商务版突出以“灌输”为主,强化以成人观点、经验通过教育让儿童接受,非常在意“讲什么”。开明版和世界书局版则突出“启发”,希望“童子依据自己的经验”,自为教师,自行探究,自定推理,在“怎么讲”上用功更勤。在政治性上,商务版编辑大意中即写明“灌输党义,提倡科学”。特别是后两版书中,有不少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当时伟人、英模,还有“大总统”、“平等”等与“共和国”相关的内容。1912年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新教科书》初小国文第一册首页,就印了当时的五色国旗,同时配以课文:“我国旗,分五色,红黄青白黑,我等爱中华。”即使童趣盎然的开明版中,也有政治领袖人物的故事。而且,不管什么版本,都贯穿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在蒙着眼睛赞美民国教材的朋友们眼里,是否还那么美呢?还要强调说明的是,即使如此我也不会就去简单否定那些教材,它们仍然有可资今天语文教材编写借鉴的一些东西。针对有学者认为“民国教材选的都是美文”的说法,年届80高龄、一生从事语文教育的孙绍振先生曾回忆说,他当年读小学接触的就是“民国老课本”。有一本教材第一课就是蒋介石写给儿子的信。谈到美文,他记忆清晰地表示“大量课文是时文”,不仅没有文学性,而且文章遣词造句中时而有语病,时而夹杂着方言。而且,随着时事的变化,民国政府实行训政,后期对于教材的管理更是越趋收紧。
“民国神话”之二是把民国政治虚幻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天堂和乐园。一位应该懂点历史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把民国描绘成“民主受尊重的时代”。具体就是“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我想,这位学者说的应该是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的民国。当时文化是不是有想象中那样大的自由尺度,其实只要稍微查查资料,就可以搞得明明白白的。略举两条:一是,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上海查禁文艺图书140余种。鲁迅先生在《且介亭二集》后记有非常详细的记载。1924年到1934年,前后禁止发行887种书刊。二是,笔者前些日子写柯灵先生的一篇短文,认真阅读了文汇报姚芳藻的《柯灵传》,其中记载,先是1946年先生主办的《周报》被“逼令停刊”,而后是1947年5月27日,上海《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停刊,柯灵本人也亡命天涯。在主观描写了“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后,有人直接提出了“民国当归”。出版界也相继推出了一批书籍。
民国有没有它闪亮的片刻,有没有文化发展的某种自由度,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点没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它的另一面,而且很可能是更本质的一面。其实民国的文化自由,更多的是因为上海的租界华界分治格局而造成的管理缝隙,使得文化有了一定的腾挪空间。也有的时候是因为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的无法管理。而有些文化业绩,如被称为“民国的真滋味”的那些后来被视为中国现实主义**经典的民国老**《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实际上也受到中国***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即使在租界,《十字街头》 也几乎过不了工部局的审查关,把《思故乡》的歌词和东三省地图一剪了之。抗战胜利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 也都是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一批左翼**工作者汇集的昆仑影业所拍摄。至于说到知识分子的民国范儿,其中既有刘文典这样当面顶撞蒋介石的清高教授,也不乏翁文灏、王云五这样在国民党政府颓败之际出任高官,并且政绩乏善的知识分子。即使胡适也呈现着复杂的多面性。
摆脱绝对化思维,全面还原互相倾听
因为几十年历史的局限,我们的知识写作带有一定的政治工具性。我反对坚持过去极左理念的知识写作,并称之为旧的过时的意识形态写作,同时我把上面的知识写作定义为新意识形态写作。这种写作仍然把自己牢牢地绑在另一种文艺政治工具论的战车上。一是在出发时就刻意追求反效果,在结论上凡是过去否定的他就肯定,凡是过去肯定的他就否定。二是在写作方法上以貌似的、经不起推敲的“真实”和细节,代替真实的历史。以局部肢解整体,或替代整体。
譬如西南联大,是我非常敬重的高等学府。三所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师生在艰苦的抗战中,颠沛流离三千五百里,坚持学业,感天地,泣鬼神,显示了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坚韧崇高的精神力量。但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什么?在近年汗牛充栋的关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写作中,西南联大只剩下了从西方接续过来的民主和自由传统,和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恰好我手边保留了初版于1946年由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在这本保持了原始资料充满时代体温的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于理想和光明的追求。在代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长沙临大两千多学生到西南联大六百余学生,作者自问自答,这大部分同学到哪里去了?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到了陕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推动救亡工作。“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大简史》里写道: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可见爱国主义是西南联大精神的主干之一。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曾是西南联大一员、已在海外学有所成的学子们,不惜千里万里,排除千难万险,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报效自己的祖国。其后即使有委屈也少有怨言,如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三强。他们在祖国沉重的忧患中出生、成长,爱国主义是他们最基本的精神底色。但是在最近的一些写作中,历史的丰满被抽取,历史的全面的真实被片面解读,历史的丰富性被那种先验既定的政治观念过滤。
我提供这些大家熟悉的材料,并无意于全面彻底地否定此类写作中或许有的有益部分,补充了我们一度可能被忽略的某些东西。但我反对那种“新”的刻意的政治理念,着意于用被扭曲变了形的历史叙事去代替丰富多面而真实的历史。在我们拥有了比从前越来越开阔的言论、思考和研究的空间之后,我们是否还要重蹈覆辙,让知识写作再度陷入一种先验的新意识形态写作,一种为了观念牺牲历史真实的陷阱?如果曾经的民国真是像一些写作所呈现的天堂般的美好,我们怎么去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怎么去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怎么去读懂鲁迅先生留下的以血荐轩辕的沉重的文字?历史,说到底,是人心向背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民国当归吗?民国可以回去吗?让“过去”回到过去,意味着,一,让我们知识写作的历史叙事尽可能体现历史丰满的真实,而不是被单向度记录的过去;二,不说时间的不可逆决定了当下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回到民国,就说人均寿命35岁,有谁愿意回去?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激荡的大时代,也是一个最接近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的时代。我们还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必须寻求共识,必须艰难前行。我们必须摆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上页 下页
2谈谈“民国那些人”———钱理群(1)分享到:
sina qzone renren kaixing douban msn email
——钱理群在北大的演讲
今天,我是来和大家一起读这本书的。
最近出版的《民国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来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当编辑,他写这本书,是因感觉到自己,以及周围年轻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主要是一种精神的缺失。于是,就想去看看“民国那些人”,当年那些大学里的老师、学生,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求学、教书、治学,怎么工作,怎么为人、处世;他们追求什么,有什么理想,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范;对我们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么启示——我想,这些问题,也是在座的诸位想过,并且感兴趣的。
而“我”今天来领着“大家”一起读这本书,和“民国那些人”相会,这本身就有一个时空的交错,是很有意思的。“民国那些人”是上一世纪初,即“1900年后”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后”一代人;而诸位则大多数是“1980年后”一代人。这三代人相遇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为什么“并不遥远”又“相距甚远”?
我们先来读这段话,它是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的:“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时间上他们其实离我们很近”,而我们又觉得他们“与我们相去甚远”呢?——然而,真的很远吗?我们能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由“远”而“近”?
我们面对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当代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和历史上的大学老师、学生、知识分子的关系。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假设“民国那些人”,今天真的来这里参加聚会,在座的大学生、研究生们,和这些前辈有共同的话题吗?这共同话题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我要和诸位讨论的问题。
2、“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注意到书中提到的一位当代大学生的反应,他说:“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这话说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我对当代大学生,也即所谓“80后一代人”的看法。我总是强调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要靠自己解决。但也总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也很想听听你作为一个年长者对这一代人存在的问题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们来思考吧。
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以“考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现在如愿以偿,进入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的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你们这一代有,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曾经以“革命”为自己的信仰,现在我们却发现“革命”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种失落感。不过,我们年纪已经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惯性生活;而诸位不行,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过下去,于是,就有了许多苦闷与烦恼。
(本文文字由雅馨原创于美篇,来自网络)
近日阅读收听一些民国风范的文章,凌叔华渐渐在我脑海里立体了起来,说起民国才女,林徽因、陆小曼声名贯耳,冰心也被人熟知。凌叔华和冰心是同学,风流诗人徐志摩一生中有三个半女人,前三个分别是结发妻子张幼仪,情人林徽因,和一生最爱陆小曼,至于那半个,就是红颜知己凌叔华。
提起凌叔华,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她身上的香艳情事。事实上,凌叔华出身豪门书香官宦之家,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人钦羡。在文人画和文学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是名副其实的大才女,而她的情感经历也被人津津乐道,尤以嘲笑讥讽、八卦好事的居多。拙文也是在看了很多资料后,以女性的角度分析凌叔华的才貌痴情,试图了解她,走近她,并无褒贬立场。
上图为无名氏,网络
一、才凌叔华1900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直隶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在妻妾成群的年代,她父亲有六个老婆。她的母亲是四姨太,生了四个女儿,凌叔华排行第三,而在父亲所有的孩子中,她排行第十。“小十”在这个大家庭中与她的母亲一样,恬静、温和、隐忍、不露锋芒、善解人意。其父精于词章、酷爱绘画,喜欢结交文人墨客、丹青画家,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种家庭生活环境,使她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陶冶,幼年时, 她的老师有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有精通七国语言的一代怪杰辜鸿铭,有山水兰竹画家王竹林,女画家郝漱玉等,自小就打牢了绘画、古典诗词和英文根基。 她是画坛高手,所作的山水花卉曾被波城和印城博物馆购买保存。1968年英国大英艺术协会也曾借出在法国展出的文人画在伦敦展出。
上图为无名氏,网络
她在文学方面更是强大,是民国时期读者们心中的伟大作家, 和苏雪林、冰心、丁玲、冯沅君齐名,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 她曾被泰戈尔夸赞“比林徽因‘有过之而不及’的才女。”大才子徐志摩也曾称赞她是中国的“曼斯菲尔德”。她是文学界大文豪们眼中的“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1924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女儿身世太凄凉》。1925年1月10日,凌叔华发表了奠定她在文坛上的地位的成名之作《酒后》,之后佳作不断见诸于当时的著名刊物。凌叔华的画犹如她的人,许多人评论凌才女时总说她人淡如菊、秀韵天成、温婉如春。凌叔华的文学作品涉及小说、散文、剧作。有人赞美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
上图为青年凌叔华
她出身名门闺秀,外表看起来斯文、隐忍,实际上她的内心却激荡如火,不仅表现在她惊世骇俗的出轨上,这种潜在的性格或心理在她的作品中也时有呈现。 比如她的成名小说《酒后》中,细腻地描写一位美丽 的内心活动,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睡在她家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因为她一直倾慕他的才华与风度,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先是不能接受,但他是个君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后还是允许妻子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在最后一秒她的理智战胜了感情,她失去了吻他的勇气。
凌叔华在作品中的这种大胆狂放是不是现在所说的“闷骚”呢?
上图为陈西滢与凌叔华
二、貌才女被后人记住,不仅仅靠才,美貌或许占有更重要的分量。 凌叔华的美并不是十分扎眼,不够艳丽,比不上林徽因的清新脱俗,比不上陆小曼的娇俏纯净。她的美是一种秀气温婉、落落大方。她的眼神清澈、沉思、善解人意,同时还有一点迷离、恍惚,呈现出一种梦幻的气质,这对男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加上她出众的才华,显赫的家世,以及本人不争强好胜、温婉大气的性格和气韵,凌叔华是当时 最理想的“国民媳妇” ,当时中国文坛有一句趣话: “嫁君要选梁实秋,娶妻先看凌叔华” 。徐志摩的父亲就把凌叔华看成是最佳儿媳妇的人选。
上图为陆小曼
大家闺秀凌叔华在风华正茂的24岁时,主持了一场规格巨高的大party。泰戈尔访华,很多人都知道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双双迎接,然而接上后到哪里来个欢迎宴呢?中国人习惯的吃吃喝喝太俗,想来想去,party定在凌叔华的书房,凌叔华准备了精美的鲜花饼、杏仁茶招待客人,高雅不俗。泰戈尔来到中国,多人文人在他面前都是谨慎有加、畏畏缩缩,凌叔华却大胆调皮,第一句话就“责难”泰戈尔:“今天我们办的是绘画party,敢问阁下会画画吗?”泰戈尔当即在准备好的扇面上挥毫作画,留下几幅墨宝。凌叔华的热情、大方给泰戈尔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一年林徽因20岁,相比之下,凌叔华更加端庄大方、风情万种,加上是自己的主场,虽然林徽因风华绝代,但那个party上其风头始终超不过凌叔华,泰戈尔夸赞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图为林徽因
三、情凌叔华是风情万种,又是大胆主动的 。1921年,21岁的凌叔华考进燕京大学。有门功课“新文学”,讲课老师是周家二先生周作人。凌叔华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作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多么率真、勇敢而又充满自信的一个妙龄女子!她大胆又有分寸,因此初见文学泰斗泰戈尔也敢放马过去调皮地挑衅。事实证明,这种效果好极了,不得不佩服凌叔华的八面玲珑、长袖善舞。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高情商”吧?
在凌叔华24岁欢迎泰戈尔的party上,她与徐志摩、林徽因都是重要人物,此前林徽因已情定梁思成,徐志摩在失恋之余经常向凌叔华倾诉,两人半年通信六七十封,但是徐志摩从没向凌叔华表露过什么,不是他含蓄,他向来是浓烈 的,而是他对凌叔华确实是一种“友情之上、恋人未满”的感觉。相信凌叔华是爱徐志摩的,虽然她一生不曾承认,但是她的女儿说她临终前念叨的名字是徐志摩,这个人在她心里藏了六七十年。至于为什么勇敢大胆的凌叔华始终没有向徐志摩表白,估计是怕捅破那层窗户纸连朋友也不好做,也许这也是爱到深处的一种智慧处理方式。
上图为泰戈尔访华图
在那个party上,凌叔华初识陈西滢。 陈西滢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有印象,他就是鲁迅笔下的“丧家的资本金的乏走狗”。 鲁迅骂人的水平太高了,骂陈西滢是走狗,还是丧家的,资本家的,还是乏的。然而掸去历史的烟尘,剔除掉个人恩怨,陈西滢应该以他本身的面貌被我们认知,他是留英博士,当时是北大的教授,一身才艺不输徐志摩。相比于徐志摩的光芒四射,陈西滢学识渊博却内敛沉静,敦厚寡言。
或许凌叔华知道徐志摩这样的大众情人自己无法驾驭,或许觉得徐志摩始终对自己不是爱情,彼时的徐志摩已经狂热地爱上了陆小曼。陈西滢却是一个合适的丈夫人选。当然,那个party上美丽与才情怒放的凌叔华早已映在了陈西滢的心头。那一次party,她清秀的面容、绝佳的口才、纤细的身姿,穿梭于名流之间,简直是倾倒众生,特别是陈西滢。
上图为陈西滢、鲁迅
两人后面的进展却是凌叔华在主动布控,她邀请陈西滢去她那喝茶,他去了,一迈进大宅门,前院,二院,三院,后院,东厢房,西厢房,院套院,屋连屋,门房带路,老妈子迎接,丫鬟通报,才被告知“**在里面”,好比进了一趟大观园。看这凌叔华多么会调情!
这两位才子佳人,都喜爱文学、绘画,都精通外语,陈西滢又是留欧归来的博士,两人自是有很多共同话题。凌叔华是个善解人意,又会调节气氛的高手,再加上她迷离、恍惚、梦幻的气质,这让本就衷情于她的陈西滢情网深陷, 更何况陈西滢那么欣赏她的才华,两个人很快就情投意合。凌叔华的父亲对陈西滢满意至极,很快就为他们操办婚事,用28间房子做陪嫁。因此后面 鲁迅骂陈西滢时还说他“娶了有钱的女人。 ”
现在看来,凌叔华与陈西滢是闪婚闪恋,这桩婚姻在任何人看来都是那么般配。 凌叔华婚后,和老公过了一段波澜不惊的安静日子。一到1929年,陈西滢应聘去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之后,他们的婚姻有点像晴空万里的长空,开始阴云密布,越积越厚,最后遭遇到了狂风暴雨一样的险情。
上图为陈西滢、凌叔华婚纱照
四、痴婚后的陈西滢忙于各种事务,再加上他本身沉静木讷的性格,两人之间说的闲话越来越少。他们两人互相独立,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平静如水。作为文人的他们都爱写作,但他们写出的文章未经发表前互相保密,两人各有各的书房,各有各的生活空间。渐渐地,凌叔华在悠然娴雅的生活之余也许会有些许的沉闷乏味。
其实,无论是多么高层次的男女,只要是相爱的,就总有说不完的废话、闲话,哪怕说的话再无聊,也想与ta一直交流。哪怕ta调侃、批评、嗔怪,也能独自品味出丝丝甜蜜。和ta交流心中始终有温情流淌,仿佛少男少女在体验初恋。但是 陈西滢和凌叔华的婚姻生活却出现了可怕的静寂,陈西滢没有觉察,凌叔华心里已暗生空洞,这就是人们时常感叹的那句话吧?婚姻的疲乏经不起岁月的伤。
上图为凌叔华
在凌叔华35岁那一年, 她平静的婚姻生活被一个年轻英国诗人朱利安的到来而打乱。也许很多人的一生都会遇到一个自己的“生死劫” ,比如花千骨是白子画的生死劫。这位集才情、 与帅气的诗人朱利安当时才27岁,被陈西滢聘到武汉大学任教,签约三年。朱利安很有来头,他的姑姑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的母亲凡尼莎·贝尔则是一位知名画家,他艺术家的因子也是来自家族遗传。
英俊活泼的朱利安成为陈西滢的部下,凌叔华的同事后,内心浪漫的凌叔华与朱利安因为彼此都喜爱文学、热爱绘画,视艺术为生命,自然交往很多。一来二往,朱利安就狂热地爱上了凌叔华,并且热烈地追求她。 凌叔华更加狂热地痴恋着朱利安,为取悦他开始烫头、化妆。 朱利安一直保持给母亲写长信的习惯,喜欢在信里坦陈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他与女人之间的隐私。他爱上聪明、可爱而并不特别美丽的院长夫人之后,就一一告诉了母亲,在给母亲的心中,他充满诗意地写道:“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的儿媳妇的女人。”又对母亲说,“她说,过去没有爱过。”后来,还留下一首诗:“只是当时已惘然/我的爱人在她那冰冷的被窝里入睡/窗外的风将窗帘卷起层层波浪/她的脑海里追逐起种种幻影/哪儿才有上天的恩惠,美丽的生活。”里边的“爱人”、“她”就是凌叔华。
上图为朱利安
但是,风流倜傥的朱利安女友实在太多了,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只要提到女朋友,用的都是编号,凌叔华是他的第11个女友,编号是K。很多年后,女作家虹影的小说《K》即以他们之间的三角恋爱为主线,因书中过于渲染了男女情爱之事而被凌叔华的女儿告上法庭,最后以虹影败诉而告终。
在朱利安的持续疯狂追逐之下,外表贤淑实则内心狂野的凌叔华很快成为爱情的俘虏。这两人一个出于猎奇,一个出于寂寞,在情感出轨的路上一路狂奔,他们本人也对这段感情发展的速度之快惊讶不已。
我有个学生结过三次婚,第三任妻子小他二十多岁,每次聚会时同学们都调侃他,表露出些许羡慕,更多的是嘲讽,而他特别真诚、眼含泪花地对我说:“老师,我的每段情都是投入了我的全部!”我相信他的每段情都是完全投入的,因此 我也相信,朱利安与凌叔华也是真心相爱的。尤其是凌叔华,在她青春即将逝去的35岁又一次遇到了一位 的诗人,婚姻的疲倦感被一扫而光,心中燃起熊熊烈火。
上图为凌叔华、陈西滢与同事朋友
凌叔华疯狂痴恋朱利安 ,释放着内心深处火一般的 与浪漫情怀。当她知道朱利安有众多女友、情妇,凌叔华不顾自己名门闺秀、院长夫人的身份,经常身揣老鼠药,以死威胁。爱到这种程度,是有多么疯狂?这和一般的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何区别?或许爱到深处都是一样吧?眼里只有那个爱着的ta,别的一切,荣誉、地位、身份、舆论、脸面、亲情……统统抛诸脑后。 凌叔华多次表示要和朱利安结为正式夫妻,并多次表明自己“找不到回去的路。”这就是说,从情感上她已经找不到回到丈夫身边的路。
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1月,凌叔华和小她8岁的朱丽安整整进行了长达16月的姐弟恋。 妻子红杏出墙,虽然早就沸沸扬扬,最后知道的才是那个可怜的丈夫。 有一次,凌叔华与朱利安终于被陈西滢抓了现行。陈西滢怕是气的肝胆欲裂,但却表现出真正的君子风范,把那个插足者撵出门之后,压制住满肚子怒火,没做任何声张,只是关好房门,向凌叔华提出三点要求,一,离婚。二,不离婚,分居。三,与朱利安断绝来往。考虑到朱利安的花心与陈西滢的大度,凌叔华选择了三。
上图为中晚年的凌叔华
朱利安被辞退回国,陈西滢要求朱利安永不再见凌叔华。然而朱利安改变回国的路径,在广州逗留,还是等到了前去私会的凌叔华。我们可以谴责朱利安背信弃义,不是正人君子,我们可以鄙视凌叔华的水性杨花、不知廉耻,但也更加证明了这两人是真心相爱的。在错误的时刻遇到对的人是不是错爱呢?爱的对错,或许我们真的不好去评判。
朱利安不仅是浪漫多情的诗人,他身上也洋溢着狂热的爱国主义。回国后的朱利安去西班牙参战,死在了战场,年仅29岁,这一年凌叔华37岁。据说,临终前,朱利安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生渴望两件事——有个美丽情妇,上战场,我都做到了。”
上图为中晚年的凌叔华1
重回婚姻的凌叔华与陈西滢实际上多年来保持着分居的状态,但对外,他们依然扮演者一对恩爱夫妻。朱利安死后,凌叔华与朱利安的母亲和姑姑长期通信,共同回忆、缅怀朱利安,在朱利安那个伟大的作家姑姑和有名的画家母亲的帮助下,凌叔华的文学、绘画作品的风格都有明显的改变和提高,也逐渐在国外陆续出版、展出,蜚声海外。1946年开始,凌叔华、陈西滢夫妇长期定居欧洲,他们的名声在国内逐渐湮灭。
晚年时,他们的女儿陈小滢问父亲为何没有和母亲离婚,陈西滢幽幽地说,在那个年代,离婚对女人来说是件声名狼藉的事情。 陈西滢虽与凌叔华分居多年,他始终是深爱她的,爱她的才华,她的一切,这是他一辈子唯一的女人。
上图为凌叔华(右)及女儿(左)、外孙女(中)
作者网名雅馨,头条号雅馨说历史,主要说历史上女性的感情。
都是(115)图为(9)泰戈尔(3)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