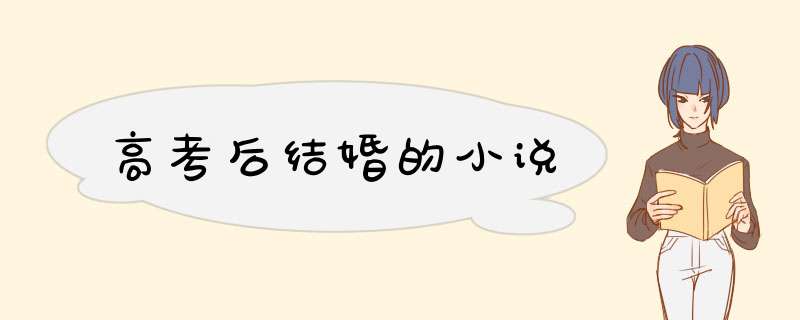
《高考完就结婚吧》。
简介:高二那年夏天,俞欢又见到了沈之桁,只不过沈之桁忘记了他。那时候俞欢以为这是和沈之桁见的最后一面。过了两个月,俞欢收情书收到手软,但大部分不是送给他的,而是给他同桌的。俞欢把那封淡粉色的情书拍到他同桌的桌子上:“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再不行,我们两牵着手,你发个朋友圈。”
“我只和喜欢的人牵手,至于喜欢的类型嘛,”沈之桁轻轻地打量着他,笑道:“比我笨,爱炸毛又好哄,喜欢玩音乐的那种。”听完,俞欢看着他默默地竖起了中指:屁事真多,您还是单着吧。四年后,俞欢再次回到以前……
其他言情小说推荐
1、《微微一笑很倾城》顾漫(著)
一个是被无数人仰望的传奇人物、名校顶尖牛人,一个是计算机系的系花,于游戏中相遇,在现实中相吸,爱情最美之处就是我喜欢你,偏偏你也只喜欢我!
2、《来不及说我爱你》匪我思存(著)
已订婚的她,在无意间救下了一个英俊又权倾一方的贵公子,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擦肩而过的邂逅,谁知道他居然甘冒奇险,在婚礼上把她抢了过来,而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王子与灰姑娘走入城堡的童话。
3、《大漠谣》桐华(著)
西汉武帝时期,小狼女玉瑾被西域匈奴单于帐下的一汉人救起,跟随他学习诗书武艺,并与单于的王子们一起长大。匈奴一场政变,小玉被迫来到长安,路上先后遇到温文尔雅的孟九和和英姿勃发的霍去病,一场爱情故事拉开帷幕。
《十年一品温如言》( 里面的这首My prayer很不错)
《岂言不相思 》
《淳淳的森林》《安之若素》《安之若牧》《城府》
《灯火阑珊》《医生,一生何求》《衾何以堪》《迷心记》《宁愿》
《婚》《十年之久》《我爱你,你爱我,一辈子,好不好》
《无尽相思风》《小米》《幸福的苹果控》《一树梨花压海棠》
《寡人有疾》《月上重火》《怎么才算情深》《何须浅碧轻红色》《胡同奇闻录》
《嫁给林安深》《城府》《灯火阑珊》《医生,一生何求》《衾何以堪》《迷心记》
《宁愿》《婚》《流光溢彩》《相思君陌染》《似此星辰非昨夜》《请继续,爱我到时光尽头》
《流烟凝眸》《初熏心意》《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静在不言中》《将就》《奢侈》
《阿门阿前一葡萄树》《杯具女王》《不就偷你一杯子!》《大城小爱》《大约是爱》
唔,唐七公子的书也很不错。
怎么说呢,这些都是经典好看、令人怦然心动的爱情故事。 望采纳o(∩_∩)o
仲夏明媚的阳光普照英格兰。当时那种一连几天日丽天清的气候,甚至一天半天都难得惠顾我们这个波浪环绕的岛国。仿佛持续的意大利天气从南方飘移过来,像一群灿烂的候鸟,落在英格兰的悬崖上歇脚。干草己经收好,桑菲尔德周围的田野己经收割干净,显出一片新绿。道路晒得白煞煞仿佛烤过似的,林木葱郁,十分茂盛。树篱与林子都叶密色浓,与它们之间收割过的草地的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施洗约翰节前夕,阿黛勒在海村小路上采了半天的野草莓,累坏了,太阳一落山就上床睡觉。我看着她入睡后,便离开她向花园走去。
此刻是二十四小时中最甜蜜的时刻——“白昼己耗尽了它的烈火,”清凉的露水落在喘息的平原和烤灼过的山顶上。在夕阳朴实地西沉——并不伴有华丽的云彩 ——的地方,铺展开了一抹庄严的紫色,在山峰的一个尖顶上燃烧着红宝石和炉火般的光焰,向高处和远处伸延,显得越来越柔和,占据了半个天空。东方也自有它湛蓝悦目的魅力,有它不事炫耀的宝石——一颗升起的孤星。它很快会以月亮而自豪,不过这时月亮还在地平线之下。
我在铺筑过的路面上散了一会儿步。但是一阵细微而熟悉的清香——雪茄的气味——悄悄地从某个窗子里钻了出来。我看见图书室的窗开了一手掌宽的缝隙。我知道可能有人会从那儿看我,因此我走开了,进了果园。庭园里没有比这更隐蔽,更象伊甸园的角落了。这里树木繁茂,花儿盛开,一边有高墙同院子隔开;另一边一条长满山毛榉的路,象屏障一般,把它和草坪分开。底下是一道矮篱,是它与孤寂的田野唯一的分界。一条蜿蜒的小径通向篱笆。路边长着月桂树,路的尽头是一棵巨大无比的七叶树,树底下围着一排座位。你可以在这儿漫步而不被人看到。在这种玉露徐降、悄无声息、夜色渐浓的时刻,我觉得仿佛会永远在这样的阴影里踯躅。但这时我被初升的月亮投向园中高处开阔地的光芒所吸引,穿过花圃和果园,却停住了脚步,——不是因为听到或是看到了什么,而是因为再次闻到了一种我所警觉的香味。
多花蔷蕾、老人蒿、茉莉花、石竹花和玫瑰花早就在奉献着它们的晚香,刚刚飘过来的气味既不是来自灌木,也不是来自花朵,但我很熟悉,它来自罗切斯特先生的雪茄。我举目四顾,侧耳静听。我看到树上沉甸甸垂着即将成熟的果子,听到一只夜莺在半英里外的林子里鸣啭。我看不见移动的身影,听不到走近的脚步声,但是那香气却越来越浓了。我得赶紧走掉。我往通向灌木林的边门走去,却看见罗切斯特先生正跨进门来。我往旁边一闪,躲进了长满长春藤的幽深处。他不会久待,很快会顺原路返回,只要我坐着不动,他就绝不会看见我。
可是不行——薄暮对他来说也象对我一样可爱,古老的园子也一样诱人。他继续往前踱步,一会儿拎起醋栗树枝,看看梅子般大压着枝头的果子;一会儿从墙上采下一颗熟了的樱挑;一会儿又向着一簇花弯下身子,不是闻一闻香味,就是欣赏花瓣上的露珠。一只大飞蛾嗡嗡地从我身旁飞过,落在罗切斯特先生脚边的花枝上,他见了便俯下身去打量。
“现在,他背对着我,”我想,“而且全神贯注,也许要是我脚步儿轻些,我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
我踩在路边的草皮上,免得沙石路的咔嚓声把自己给暴露。他站在离我必经之地一两码的花坛中间,显然飞蛾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会顺利通过,”我暗自思忖。月亮还没有升得很高,在园子里投下了罗切斯特先生长长的身影,我正要跨过这影子,他却头也不回就低声说:
“简,过来看看这家伙。”
我不曾发出声响,他背后也不长眼睛——难道他的影子会有感觉不成?我先是吓了一跳,随后便朝他走去。
“瞧它的翅膀,”他说,“它使我想起一只西印度的昆虫,在英国不常见到这么又大又艳丽的夜游虫。瞧!它飞走了。”
飞蛾飘忽着飞走了。我也局促不安地退去。可是罗切斯特先生跟着我,到了边门,他说:
“回来,这么可爱的夜晚,坐在屋子里多可惜。在日落与月出相逢的时刻,肯定是没有谁愿意去睡觉的。”
我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尽管我口齿伶俐,对答如流,但需要寻找藉口的时候却往往一筹莫展。因此某些关键时刻,需要随口一句话,或者站得住脚的遁词来摆脱痛苦的窘境时,我便常常会出差错。我不愿在这个时候单独同罗切斯特先生漫步在阴影笼罩的果园里。但是我又找不出一个脱身的理由。我慢吞吞地跟在后头,一面在拼命动脑筋设法摆脱。可是他显得那么镇定,那么严肃,使我反而为自己的慌乱而感到羞愧了。如果说心中有鬼——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那只能说我有。他心里十分平静,而且全然不觉。
“简,”他重又开腔了。我们正走进长满月桂的小径,缓步踱向矮篱笆和七叶树,“夏天,桑菲尔德是个可爱的地方,是吗?”
“是的,先生。”
“你一定有些依恋桑菲尔德府了——你有欣赏自然美的眼力,而且很有依恋之情。”
“说实在,我依恋这个地方。”
“而且,尽管我不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察出来,你已开始关切阿黛勒这个小傻瓜,甚至还有朴实的老妇费尔法克斯。”
“是的,先生,尽管性质不同,我对她们两人都有感情。”
“而同她们分手会感到难过。”
“是的。”
“可惜呀!”他说,叹了口气又打住了。“世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他马上又继续说,“你刚在一个愉快的栖身之处安顿下来,一个声音便会叫你起来往前赶路,因为已过了休息的时辰。”
“我得往前赶路吗,先生?”我问。“我得离开桑菲尔德吗?”
“我想你得走了,简,很抱歉,珍妮特,但我的确认为你该走了。”
这是一个打击,但我不让它击倒我。
“行呀,先生,要我走的命令一下,我便走。”
“现在命令来了——我今晚就得下。”
“那你要结婚了,先生?”
“确——实——如——此,对——极——了。凭你一贯的机敏,你已经一语中的。”
“快了吗,先生?”
“很快,我的一—,那就是,爱**,你还记得吧,简,我第一次,或者说谣言明白向你表示,我有意把自己老单身汉的脖子套上神圣的绳索,进入圣洁的婚姻状态——把英格拉姆**搂入我的怀抱,总之(她足足有一大抱,但那无关紧要——像我漂亮的布兰奇那样的市民,是谁都不会嫌大的)。是呀,就像我刚才说的—— 听我说,简!你没有回头去看还有没有飞蛾吧?那不过是个瓢虫,孩子,‘正飞回家去’我想提醒你一下,正是你以我所敬佩的审慎,那种适合你责任重大、却并不独立的职业的远见、精明和谦卑,首先向我提出,万一我娶了英格拉姆**,你和小阿黛勒两个还是立刻就走好。我并不计较这一建议所隐含的对我意中人人格上的污辱。说实在,一旦你们走得远远的,珍妮特,我会努力把它忘掉。我所注意到的只是其中的智慧,它那么高明,我已把它奉为行动的准则。阿黛勒必须上学,爱**,你得找一个新的工作。”
“是的,先生,我会马上去登广告,而同时我想——”我想说,“我想我可以呆在这里,直到我找到另外一个安身之处”但我打住了,觉得不能冒险说一个长句,因为我的嗓门已经难以自制了。
“我希望大约一个月以后成为新郎,”罗切斯特先生继续说,“在这段期间,我会亲自为你留意找一个工作和落脚的地方。”
“谢谢你,先生,对不起给你——”
“呵——不必道歉!我认为一个下人把工作做得跟你自己一样出色时,她就有权要求雇主给予一点容易办到的小小帮助。其实我从未来的岳母那儿听到一个适合你去的地方。就是爱尔兰康诺特的苦果村,教迪奥尼修斯.奥加尔太太的五个女儿,我想你会喜欢爱尔兰的。他们说,那里的人都很热心。”
“离这儿很远呢,先生。”
“没有关系——像你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姑娘是不会反对航程或距离的。”
“不是航程,而是距离。还有大海是一大障碍——”
“离开什么地方,简?”
“离开英格兰和桑菲尔德,还有——”
“怎么?”
“离开你,先生。”
我几乎不知不觉中说了这话,眼泪不由自主夺眶而出。但我没有哭出声来,我也避免抽泣。一想起奥加尔太太和苦果村,我的心就凉了半截;一想起在我与此刻同我并肩而行的主人之间,注定要翻腾着大海和波涛,我的心就更凉了;而一记起在我同我自然和必然所爱的东西之间,横亘着财富、阶层和习俗的辽阔海洋,我的心凉透了。
“离这儿很远,”我又说了一句。
“确实加此。等你到了爱尔兰康诺特的苦果村,我就永远见不到你了,肯定就是这么回事。我从来不去爱尔兰,因为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个国家。我们一直是好朋友,简,你说是不是?”
“是的,先生。”
“朋友们在离别的前夕,往往喜欢亲密无间地度过余下的不多时光。来——星星们在那边天上闪烁着光芒时,我们用上半个小时左右,平静地谈谈航行和离别。这儿是一棵七叶树,这边是围着老树根的凳子。来,今晚我们就安安心心地坐在这儿,虽然我们今后注定再也不会坐在一起了。”他让我坐下,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
“这儿到爱尔兰很远,珍妮特,很抱歉,把我的小朋友送上这么今人厌倦的旅程。但要是没有更好的主意了,那该怎么办呢?简,你认为你我之间有相近之处吗?”
这时我没敢回答,因为我内心很激动。
“因为,”他说,“有时我对你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当你象现在这样靠近我的时候。仿佛我左面的肋骨有一根弦,跟你小小的身躯同一个部位相似的弦紧紧地维系着,难分难解。如果咆哮的海峡和二百英里左右的陆地,把我们远远分开,恐怕这根情感交流的弦会折断,于是我不安地想到,我的内心会流血。至于你 ——你会忘掉我。”
“那我永远不会,先生,你知道——”我不可能再说下去了。
“简,听见夜莺在林中歌唱吗?——听呀!”
我听着听着便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再也抑制不住强忍住的感情,不得不任其流露了。我痛苦万分地浑身颤栗着。到了终于开口时,我便只能表达一个冲动的愿望:但愿自己从来没有生下来,从未到过桑菲尔德。
“因为要离开而难过吗?”
悲与爱在我内心所煽起的强烈情绪,正占上风,并竭力要支配一切,压倒一切,战胜一切,要求生存、扩展和最终主宰一切,不错——还要求吐露出来。
“离开桑菲尔德我很伤心,我爱桑菲尔德——我爱它是因为我在这里过着充实而愉快的生活——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遭人践踏,也没有弄得古板僵化,没有混迹于志向低下的人之中,也没有被排斥在同光明、健康、高尚的心灵交往的一切机会之外。我已面对面同我所敬重的人、同我所喜欢的人,——同一个独特、活跃、博大的心灵交谈过。我已经熟悉你,罗切斯特先生,硬要让我永远同你分开,使我感到恐惧和痛苦。我看到非分别不可,就像看到非死不可一样。”
“在哪儿看到的呢?”他猛地问道。
“哪儿?你,先生,已经把这种必要性摆在我面前了。”
“什么样的必要性?”
“就是英格拉姆**那模样,一个高尚而漂亮的女人——你的新娘。”
“我的新娘!什么新娘呀?我没有新娘!”
“但你会有的。”
“是的,我会!我会!”他咬紧牙齿。
“那我得走——你自己已经说了。”
“不,你非留下不可!我发誓——我信守誓言。”
“我告诉你我非走不可!”我回驳着,感情很有些冲动。“你难道认为,我会留下来甘愿做一个对你来说无足轻重的人?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能够容忍别人把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把一滴生命之水从我杯子里泼掉?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本来就如此!”罗切斯特先生重复道——“所以,”他补充道,一面用胳膊把我抱住,搂到怀里,把嘴唇贴到我的嘴唇上。“所以是这样,简?”
“是呀,所以是这样,先生,”我回答,“可是并没有这样。因为你已结了婚——或者说无异于结了婚,跟一个远不如你的人结婚——一个跟你并不意气相投的人 ——我才不相信你真的会爱她,因为我看到过,也听到过你讥笑她。对这样的结合我会表示不屑,所以我比你强——让我走!”
“上哪儿,简?去爱尔兰?”
“是的——去爱尔兰。我已经把心里话都说了,现在上哪儿都行了。”
“简,平静些,别那挣扎着,像一只发疯的鸟儿,拚命撕掉自己的羽毛。”
“我不是鸟,也没有陷入罗网。我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现在我要行施自己的意志,离开你。”
我再一挣扎便脱了身,在他跟前昂首而立。
“你的意志可以决定你的命运,”他说。“我把我的手,我的心和我的一份财产都献给你。”
“你在上演一出闹剧,我不过一笑置之。”
“我请求你在我身边度过余生——成为我的另一半,世上最好的伴侣。”
“那种命运,你已经作出了选择,那就应当坚持到底。”
“简,请你平静一会儿,你太激动了,我也会平静下来的。”
一阵风吹过月桂小径,穿过摇曳着的七叶树枝,飘走了——走了——到了天涯海角——消失了。夜莺的歌喉成了这时唯一的声响,听着它我再次哭了起来。罗切斯特先生静静地坐着,和蔼而严肃地瞧着我。过了好一会他才开口。最后他说:
“到我身边来,简,让我们解释一下,相互谅解吧。”
“我再也不会回到你身边了,我已经被拉走,不可能回头了。”
“不过,简,我唤你过来做我的妻子,我要娶的是你。”
我没有吭声,心里想他在讥笑我。
“过来,简——到这边来。”
“你的新娘阻挡着我们。”
他站了起来,一个箭步到了我跟前。
“我的新娘在这儿,”他说着,再次把我往身边拉,“因为与我相配的人在这儿,与我相像的人,简,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仍然没有回答,仍然要挣脱他,因为我仍然不相信。
“你怀疑我吗,简?”
“绝对怀疑。”
“你不相信我?”
“一点也不信。”
“你看我是个爱说谎的人吗?”他激动地问。“疑神疑鬼的小东西,我一定要使你信服。我同英格拉姆**有什么爱可言?没有,那你是知道的。她对我有什么爱?没有,我已经想方设法来证实。我放出了谣言,传到她耳朵里,说是我的财产还不到想象中的三分之一,然后我现身说法,亲自去看结果,她和她母亲对我都非常冷淡。我不愿意——也不可能——娶英格拉姆**。你——你这古怪的——你这近乎是精灵的家伙——我像爱我自己的肉体一样爱你。你——虽然一贫如洗、默默无闻、个子瘦小、相貌平庸—一我请求你把我当作你的丈夫。”
“什么,我!”我猛地叫出声来。出于他的认真,尤其是粗鲁的言行,我开始相信他的诚意了。“我,我这个人除了你,世上没有一个朋友,——如果你是我朋友的话。除了你给我的钱,一个子儿也没有。”
“就是你,简。我得让你属于我——完全属于我。你肯吗?快说‘好’呀。”
“罗切斯特先生,让我瞧瞧你的脸。转到朝月光的一边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细看你的面容,转呀!”
“那儿,你能看到的无非是撕皱了的一页,往下看吧,只不过快些,因为我很不好受。”
他的脸焦急不安,涨得通红,五官在激烈抽动,眼睛射出奇怪的光芒。
“呵,简,你在折磨我!”他大嚷道。“你用那种犀利而慷慨可信的目光瞧着我,你在折磨我!”
“我怎么会呢?如果你是真的,你的提议也是真的,那么我对你的感情只会是感激和忠心——那就不可能是折磨。”
“感激!”他脱口喊道,并且狂乱地补充道——“简,快接受我吧。说,爱德华——叫我的名字——爱德华,我愿意嫁你。”
“你可当真?——你真的爱我?——你真心希望我成为你的妻子?”
“我真的是这样。要是有必要发誓才能使你满意,那我就以此发誓。”
“那么,先生,我愿意嫁给你。”
“叫爱德华——我的小夫人。”
“亲爱的爱德华!”
“到我身边来——完完全全过来。”他说,把他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用深沉的语调对着我耳朵补充说,“使我幸福吧——我也会使你幸福。”
“上帝呀,宽恕我吧!”他不久又添了一句,“还有人呀,别干涉我,我得到了她,我要紧紧抓住她。”
“没有人会干涉,先生。我没有亲人来干预。”
“不——那再好不过了。”他说。要是我不是那么爱他,我会认为他的腔调,他狂喜的表情有些粗野。但是我从离别的恶梦中醒来,被赐予天作之合,坐在他身旁,光想着啜饮源源而来的幸福的清泉。他一再问,“你幸福吗,简?”而我一再回答“是的”。随后他咕哝着,“会赎罪的,——会赎罪的。我不是发现她没有朋友,得不到抚慰,受到冷落吗?我不是会保护她,珍爱她,安慰她吗?我心里不是有爱,我的决心不是始终不变吗?那一切会在上帝的法庭上得到赎罪。我知道造物主会准许我的所作所为。至于世间的评判——我不去理睬。别人的意见——我断然拒绝。”
可是,夜晚发生什么变化了?月亮还没有下沉,我们已全湮没在阴影之中了。虽然主人离我近在咫尺,但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七叶树受了什么病痛的折磨?它扭动着,呻吟着,狂风在月桂树小径咆哮,直向我们扑来。
“我们得进去了,”罗切斯特先生说。“天气变了。不然我可以同你坐到天明,简。”
“我也一样,”我想。也许我应该这么说出来,可是从我正仰望着的云层里,窜出了一道铅灰色的闪电,随后是喀啦啦一声霹雳和近处的一阵隆隆声。我只想把自己发花的眼睛贴在罗切斯特先生的肩膀上。大雨倾盆而下,他催我踏上小径,穿过庭园,进屋子去。但是我们还没跨进门槛就已经湿淋淋了。在厅里他取下了我的披肩,把水滴从我散了的头发中摇下来,正在这时,费尔法克斯太太从她房间里出来了。起初我没有觉察,罗切斯特先生也没有。灯亮着,时钟正敲十二点。
“快把湿衣服脱掉,”他说,“临走之前,说一声晚安——晚安,我的宝贝!”
他吻了我,吻了又吻。我离开他怀抱抬起头来一看,只见那位寡妇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神情严肃而惊讶。我只朝她微微一笑,便跑上楼去了。“下次再解释也行,”我想。但是到了房间里,想起她一时会对看到的情况产生误解,心里便感到一阵痛楚。然而喜悦抹去了一切其他感情。尽管在两小时的暴风雨中,狂风大作,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暴雨如注,我并不害怕,并不畏惧。这中间罗切斯特先生三次上门,问我是否平安无事。这无论如何给了我安慰和力量。
早晨我还没起床,小阿黛勒就跑来告诉我,果园尽头的大七叶树夜里遭了雷击,被劈去了一半。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