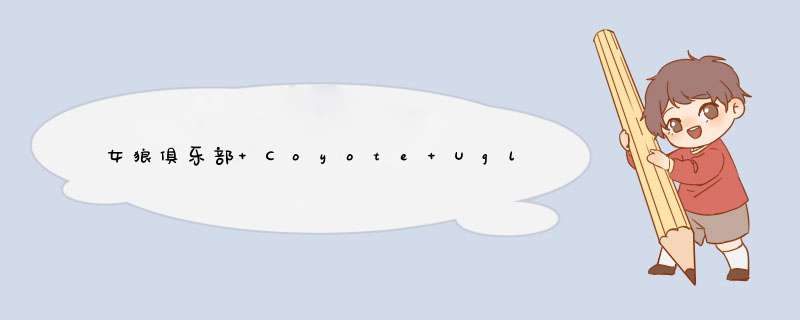
主演:派珀·佩拉博 亚当·加西亚 约翰·古德曼 玛丽亚·贝罗 伊莎贝拉·米珂 提拉·班克斯 布丽姬·穆娜 梅兰妮·林斯基 Del Pentecost 迈克尔·温斯顿 黎安·莱姆丝 杰雷米·罗利 艾伦·克莱格霍恩 John Fugelsang 巴德·库特 艾力克斯·班德 Aaron Kamin 格雷格·皮特斯 Whitney Dylan 维克多·阿尔果 彼得·阿佩尔 约翰·蒙丁 弗兰克·梅德拉诺 Tara
别名:
导演:David McNally
编剧:吉娜·温德科斯
年份:2000
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片长:100分钟
上映日期:2000-07-31
类型:剧情 喜剧 爱情 音乐
剧情介绍
维奥莱特(派珀·佩拉博PiperPerabo饰)是个小镇姑娘,21岁时独身一人来到纽约闯荡,试图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但命运并没有厚待她,住进狭窄小屋,经历一次次碰壁后,维奥莱特几近走投无路,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一家名叫“女狼俱乐部”的酒吧,结识了泼辣自信的女老板(玛丽亚·贝罗MariaBello饰),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女狼俱乐部”是由一群女孩子们做主导的特色酒吧,她们每个都性感美艳,夜里用火辣舞蹈和精湛的调酒技术赢得客人欢心,维奥莱特获得了登台演唱的机会,也结识了凯文(亚当·加西亚AdamGarcia饰)开始一段爱情。维奥莱特最终明白,追梦的路途,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还在于自己Jeremih Felton,中文译名杰雷米费尔顿。Jeremih出生在芝加哥的一个音乐家庭,3岁时就已经开始玩弄乐器了,后来自学学会了打鼓,弹钢琴,吹萨克斯管。在摩根公园中学时,他成为了marching band的一员。
Jeremih16岁高中毕业后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主修工程学,其间在业余歌手演唱会上的演出让他大受欢迎,也使他意识到了自己在唱歌方面的才能,随后他进入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
在哥伦比亚学院期间,Jeremih与音乐制作人Mick Schultz合作,创作了一首名为My Ride的歌曲。随后,Jeremih得到堂弟Day26成员之一Willie Taylor的引导,于2009年2月会见了Def Gam董事长和执行副总裁,经过一番面试后,Jeremih在当日便与Def Gam签约。
2009年初Jeremih发行了自出道以来的首只单曲"Birthday Sex",并登上了BillBoard第四的位置。2009年6月30日Jeremih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Jeremih》,这张专辑凭借5万9千张的首周销售量排在美国Billboard专辑榜的第6位。2010年9月发行第二张专辑《All About You 主打R&B曲风获嘻哈巨星 50 Cent和Ludacris强势加盟,再次掀起Jeremih热潮!
国际R&B巨星Jeremih将于11月5日于天津杜尚酒吧,11月6日厦门杜尚酒吧公开演出,届时中国粉丝将有机会近距离一览巨星风采, 还有望获得亲笔签名!
专辑:
1)Jeremih
专辑歌手:Jeremih
专辑风格:R&B
唱片公司:环球音乐
发行时间:2009月6月30日
专辑曲目:
1That Body
2Birthday Sex
3Break Up to Make Up
4Runway
5Raindrops
6Starting All Over
7Imma Star (Everywhere We Are)
8Jumpin
9Hatin' on Me
10My Sunshine
11My Ride
12Buh Bye
13Birthday Sex [Up-Tempo]
(2)All About You
专辑歌手:Jeremih
专辑名称:All About You
专辑流派:R&B
发行日期:2010-09-28
压缩码率:Mp3 192-256KB
压缩大小:5638MB
专辑曲目:
01 All About You
02 Xs And Os
03 Dawn On Me (Feat 50 Cent)
04 Take Off
05 I Like (Feat Ludacris)
06 Waiter (The 5 Senses)
07 Broken Down
08 Holding On
09 Wanna Get Up
10 Sleepers
11 Love Dont Change
主演:麦茜·威廉姆斯,艾米莉亚·克拉克,伊萨克·亨普斯特德-怀特,斯蒂芬·迪兰,彼特·丁拉基
集数:10集
导演:杰雷米·波德斯瓦
状态:
编剧:戴维·贝尼奥夫
年份:2016
地区:美国
首播时间:
首播平台:
类型:剧情,战争,奇幻,冒险
剧情介绍
故事进行到第六季,提利昂(彼特·丁拉基PeterDinklage饰)和瓦利斯(康雷斯·希尔ConlethHill饰)渡海投奔龙母丹妮莉丝(艾米莉亚·克拉克EmiliaClarke饰),可后者却亦处于困境之中,复国计划停滞不前。
另一边,太后瑟曦(琳娜·海蒂LenaHeadey饰)的权利被教会彻底架空,裸体游街的耻辱之后,是唯一的儿子如今的国王托曼(卡鲁姆·瓦尔里CallumWharry饰)的背叛。北边,珊莎(索菲·特纳SophieTurner饰)在骑士布蕾妮(格温多兰·克里斯蒂GwendolineChristie饰)的保护之下最终顺利同哥哥琼恩(基特·哈灵顿KitHarington饰)汇合,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即是夺回被小剥皮拉姆齐(伊万·瑞恩IwanRheon饰)所占领的临冬城。
现役詹姆斯·怀特跳最高 他可以罚球线跨下和大风车 可以证明他跳最高了吧 不然以他这样一个基本打不上比赛的人 哪来这样的知名度 所以我说他跳最高你可以相信我 詹姆斯·怀特还差2厘米就摸到上沿篮板上沿是395
你说他是不是比卡特,乔丹他们跳的高呢
不过据说”山羊”可以放硬币上去 而且纽约有很多人证实自己见过 因为以前和他打赌的人现在还活着 贾巴尔那么牛比的人都认为自己打不过山羊 要知道山羊只是个后卫的身材 贾巴尔七尺大汉....真的假的我们就当个传奇看待吧 不用去深究 不过现役是没有人摸的到的 不然你看加内特一场不要抢50个篮板了...........他自己都承认那只是个传言
数据分析:卡特:纵跳 112CM 摸高 381CM 篮板高:395cm
乔丹:纵跳 112CM 摸高 380CM
科比:纵跳 107CM 摸高 375CM
土豆韦伯 纵跳 139CM 摸高 363CM
麦克格雷迪 :纵跳 105CM 摸高 378CM
艾佛森:纵跳 113CM 摸高 366CM
佛朗西斯: 纵跳 116CM 摸高 376CM
巴伦戴维斯 : 纵跳 107CM 摸高 368CM (看了不少资料,大致相同,也有点误差,有错误之处,请原谅,看了不少评论,看到有人说乔丹的助跑起跳达到155cm,这我就不感赞同了,乔丹跳高两米,如果他助跑起跳达到155cm 的话,再加上他脚到重心的大概一米的高度,如果再练习一下跳高技术的话,那就可以破世界记录了,摸高也达到四米以上了,这我真是不敢相信的)
再说一下,前NBA巨星张伯伦于拉赛尔都是身体素质惊人的家伙,他们的都能摸到篮板顶
尔斯和玛利比尔德在他们的名著 《美国文明的兴起》中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 这不仅仅是因为内战解放了四百万黑奴和废除了奴隶制,而且是因为比尔德夫妇认为内战推动了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路易斯海克后来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认为内战中的政治权力转移替“工业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提供了完成其经济蓝图的机会。 海克引述为证的战时措施包括关税、 银行法、 铁路土地赠与、 宅地法、 莫里尔法、 以及契约劳工法等等。 在比尔德和海克看来,内战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转折点。 他们这种进步主义的史学观一度在学术界居于统治地位。
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尤其是经济史学家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内战及其影响作了多方位的研究,既掌握了新的数据,也形成了新的看法。从成本来看,他们发现战争并不是解决奴隶制问题最经济的方式,而且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于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都难以在经济上直接受益;从战时经济来看,内战发生的1860年代是十九世纪经济最差的十年;从长远影响来看,内战固然有其产生正面作用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作用还很大,但就总体而言很难说是什么经济发展的转折点。这些学者的某些观点也许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过他们所做的研究给人的启示却相当清楚:美国经济在十九世纪的成功不是一场“战争”或 一次“革命”所带来的突变就一锤定音的,它实际上是内战所无法涵盖的多种因素长期发展的结果。
一
美国内战在对奴隶主不作任何赔偿的情况下立即解放了全部黑奴。 这在当时的美国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不过,就整个美洲大陆而言,战争和无赔偿解放并不是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唯一方式。事实上,渐进赎买式解放才是更为常见的做法。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内战确实如比尔德所言是一场革命,但它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
以渐进赎买方式解放黑奴在西半球不乏其例。英属西印度群岛就是如此。众所周知,大英帝国范围内结束奴隶制的政治斗争是在1787年由教友会教徒发起的。他们所形成的反奴隶制同盟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在国会争取到压倒多数,取缔了国际奴隶贸易。到1830年代,这个同盟不仅在英国国会控制了足够的多数支持解放英属殖民地黑奴的决定,而且迫使国会中的西印度群岛多数集团投票赞成这一做法。1834年,英国政府开始实施废奴计划,规定在大田劳动的奴隶6年获得自由,其他奴隶4年获得自由。英国国会还从国库拨款2千万英镑作为对奴隶主的赔偿。这个数字虽不足以对奴隶主作出全额赔偿,但也相当于1830年代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 委内瑞拉奴隶制的废除,是这个国家独立战争的副产品。不过,该国在1821年亦通过立法规定,奴隶儿童出生后要为母亲的主人工作18年才能获得自由。后来,获得自由的年龄先后被提高到21岁和25岁。1854年,委内瑞拉终于通过废奴法,解放所有奴隶,但同时给他们的主人以全额赔偿。
其实,美国北部在西半球废奴过程中曾经领风气之先,并有渐进赎买式解放的经验。1777年,佛蒙特州首先宣布废除奴隶制。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宪法均被法院解释为禁止奴隶制。北部奴隶最多的宾夕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州,还有康涅狄格和罗德艾兰州,则采取了渐进解放的方式。它们分别宣布新出生奴隶在成年时获得自由,而获得自由的年龄从21到28岁不等。据罗伯特W佛格尔与斯坦利L英格曼研究,奴隶到9岁左右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开始超过维持其生活的开支。这样累积下来,奴隶到20多岁时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可以抵消其全部生活开支。 此时给奴隶以自由,奴隶主就不会因为曾负担其生活开支而在经济上有所损失。这等于是部分赔偿。因此,北部几州把新出生奴隶获得自由的年龄都定在20几岁。定得太小,奴隶主会觉得不划算而抛弃奴隶儿童;定得太大,又会推迟了奴隶的解放。
到美国内战前夕,西半球除了荷属殖民地、波多黎各、古巴、巴西和美国南部以外,其他地区都废除了奴隶制。赎买式解放是摆在当时美国人面前的一种选择,至少是他们知道的一种选择。然而,他们选择了战争。如果他们选择赎买式解放,情况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比内战的经济代价小呢?经济史学家克劳迪雅D戈尔丁从这个反事实假设出发,分三种情况对赎买式解放黑奴的成本进行了计算。第一种情况是立即解放并全额赎买。戈尔丁根据当时的遗嘱记录和奴隶买卖帐单上不同年龄奴隶的价格,估算出1860年所有奴隶的资本价值为27亿美元,几乎占当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42亿美元的三分之二。这样大一笔赔偿费如果靠政府发行为期30年,利息为6%的长期债券来偿付,那么每个公民(不包括前奴隶)一开始每年要负担75美元,占人均年收入的5%,此后这个负担会在30年还款期内逐渐减轻。如果南部人不肯负担,那么每个北部公民每年要付966美元,占人均年收入的7%。如果前奴隶也愿意参加还款,那每个公民的每年的负担只有63美元,占人均收入4%。要是除了赎身以外还负责把获得自由的黑奴送回非洲安置,那总开支就不是27亿美元,而是30亿8千4百万美元。由黑奴以外公民负担,每人每年8美元;由北部公民负担,每人每年107美元;由包括前奴隶在内全体公民负担,每人每年69美元。上述还款额占人均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8%和5%。
第二和第三种情况是渐进式解放。前者让新出生奴隶儿童在劳动所得抵消了养育费后获得自由。后者则让所有奴隶在30年后,即1890年获得自由。如果仅解放1860年后出生的奴隶儿童,奴隶主唯一的损失是现有女奴可以生孩子为奴的价值。戈尔丁估算为2亿1千万美元。如果30年解放全部奴隶,那么成本除了上述2亿1千万美元外,还要加上除儿童以外的其他奴隶30年劳动未能还完的奴隶资本价值。这样,总额应为5亿5千万美元。黑奴以外全体公民还款,每人每年负担15美元;北部公民还款,每人每年付2美元;前奴隶也参加还款,每人每年则负担13美元。还款额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5%和1%。
以上是赎买式解放的成本,那么美国内战实际付出的经济代价究竟有多高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要考虑政治不稳定这一类战争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时,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因此,克劳迪雅 D 戈尔丁和弗兰克 D 刘易斯将内战的代价分两种方式计算。一种方式计算内战的“直接代价”,即将与战争有关的开支和损失加在一起。另一种方式则是计算“间接代价”,即先算出假设没有内战美国经济按战前速度增长时美国人的消费可以达到的水平,再减去他们在发生内战后实际达到的水平。二者之差就是“间接代价”。它包含的内容比“直接代价”要广,即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直接代价”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的结果,例如比尔德和海克所说的内战带来的政治权力转移或者劳动力构成变化等因素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是正面的,就必然可以抵消部分“直接代价”,使整个“间接代价”的数额少于“直接代价”,即“间接代价”减去“直接代价”的差应为负数。这种计算方式不仅能使我们对赎买和内战的代价进行比较,还可以让我们检验比尔德和海克所说的政治权力转移等因素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戈尔丁和刘易斯计算的“直接代价”包括联邦政府和南部同盟政府的所有战争开支、州和地方政府的有关开支、战争造成的物质财产和伤亡损失,其结果如下表:
表1: 内战的直接代价
(以1860年美元计算, 单位为百万美元)
北部 南部
政府开支 2,291270 1,011158
征兵增加之开支 11053 20368
物质资产的损失 0000 1,487241
人力资源的损失
阵亡 954922 683939
伤残 364734 261231
减去: 军人工资中的风险保费 256155 178037
直接代价总额: 3,365846 3,285900
从表中可以看出,北部和南部为内战付出的直接代价高达66亿美元以上,两倍于1860年立即全额赎买全部奴隶要付的27亿美元。据经济史学家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估算,这66亿美元不仅足以赎买全部奴隶,而且可以给每个奴隶家庭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并对过去100年所欠前奴隶的工资作出赔偿。
戈尔丁和刘易斯计算的“间接代价”依照定义就是因战争减少的消费总额之1861年价值。他们假设北部在1860年以后没有战争情况下人均收入继续以1839-1859年的年增长率156%稳定增加,结果发现人均实际消费水平受战争影响最初低于根据假设算出的人均消费水平,到1879年时这两种消费水平终于相等。这就是说北部消费水平在1879年赶上了经济不受战争影响下应该达到的消费水平,即北部消费水平自1879年开始不再受到战争代价的影响。这两位学者对南部在1860年以后如果没有战争的情况也作了假设,即人均收入按1839-1859年的年增长率130%稳定增加。结果他们发现,南部实际消费水平受战争影响不仅低于根据假设算出的消费水平,而且直到1909年还未赶上没有战争应该达到的水平。这就是说南部消费水平直到1909年仍然受到战争代价的影响。当然,这里还有黑奴获得解放减少劳动时间及其他因素对消费水平产生的作用。
这两位学者用根据假设算出的北部和南部1860年以后的消费水平,与实际消费水平进行比较,并考虑其他要调整的因素,算出了北部和南部的战争“间接代价”
从表2 可以看出,北部的战争“间接代价”为52亿3千万美元,南部的“间接代价”为94亿8千万美元,总和为147亿美元。参考表1可以算出,北部的“间接代价”减去“直接代价”得出的差为18亿6千万美元。南部的“间接代价”与“直接代价”之差更是高达42亿3千万美元。前面以经提到,“间接代价”等于“直接代价”加上如政治权力转移等其他因素对经济产生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如果这个影响是负面的,“间接代价”就会比“直接代价”大,二者之差为正数。反之,如果这个影响是正面的,就会抵消部分“直接代价”,使“间接代价”算出来比“直接代价”小。那么二者之差应为负数。现在连北部的“间接代价”与“直接代价”之差都是正的,而且高达18亿6千万美元。我们即便不说政治权力转移等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至少也要说它们的正面影响不大或者被我们还不清楚的“直接代价”给抵消了。因此,戈尔丁和刘易斯得出结论:“我们看不出有证据显示内战那怕是在总体上有利于北部或者整个美国。”
二
事实上,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哥尔曼根据新掌握的数据对十九世纪美国商品生产和国民收入进行的估算,得出了和当年比尔德、海克等人的估计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内战并不是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没有成为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转折点。首先从美国商品总产值的平均年增长率来看,1840-1859年为46%,1860-69年为20%,1870-1899年为44%。发生内战的1860年代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全国商品总产值年增长率最低的十年,而战后的年增长率和战前大体差不多,并无显著提高。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平均年增长率亦复如此,1840-1859年为78%,1860-1869年为23%,1870-1899年为60%。内战发生的1860年代在制造业产品增加值年增长率上也是十九世纪最低的十年。不仅如此,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1860-1870年猛跌13%,同样为十九世纪之仅见。
有些数据看上去似乎可以为比尔德和海克的观点作佐证,但仔细推敲则不然。例如人均产值在1870-1900年的年增长率确实比战前20年的年增长率高,前者为210%,后者为145%。可是,斯坦利 英格曼认为,战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战前,主要是因为这个增长率在战时下跌太厉害,战后的“赶上”过程当然也就来得快一点。 我们如果看看下面这个1839-1899年人均国民总产值每十年的年增长率变化图, 那英格曼的上述论点便跃然纸上。以186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产值年增长率在有内战的十年从战前十年的230%猛跌到-077%,到1870年代又急升到312%,才算大体恢复了战前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内战不仅没有加速经济增长,反而是中断了战前就已开始的增长趋势。从恢复这一趋势的角度来看,战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上升得快一点,一点也不奇怪。另外,制造业在商品产值中所占比重确实从1860年的32%上升到1870年的33%。不过,这个上升幅度不仅很小,而且主要是因为南部农业的萎缩所致。
统计数据中真正能显示内战对战后经济产生了正面作用的是总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其百分比在1869-1878年比1849-1859年上升了大约8%。这说明战后投资速度大大加快。之所以能如此,和战时政府举债有密切的关系。1861-1865年,联邦政府发行有息债券达20多亿美元。据杰弗里G威廉姆逊计算,这笔战时联邦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5%。他还发现,战前十年总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为194%。因此,战时债务数额之大可能等于甚至超过了和平时期的净投资(总投资减去用于折旧的部分)。由于国债把本来用于私人投资的钱吸引走了,所以战时债务大大降低了战争期间的净投资。这种情况被经济学家称为“挤出”资本。战争结束后,情况颠倒过来。由于联邦政府优先还债而不是急于绿背纸币的回收,结果流通的绿背纸币在1866-1893年期间仅从4亿2千9百万美元下降到3亿7千4百万美元,同期内私人握有的政府债券则从23亿3千万美元下降到5亿8千7百万美元。这些偿还的债款被用于私人投资,从而导致战后总投资在国民生产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经济学家称之为“挤进”资本。威廉姆逊认为内战后总投资比率增长有一半是因为战债的偿还和债务利息支付造成的。
综上所述,除了总投资比率以外,经济史学家计算出的其他大部分数据都使人难以苟同比尔德和海克有关内战经济影响的观点。那末,这两位学者当初为什么会得出那样的结论,并得到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认同呢?现在看来,除了不掌握今天经济史学家手中的数据以外,他们过份强调内战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比尔德和海克以及很多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那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们在研究内战时也从现代战争的角度加以考量。可是,最先根据哥尔曼的数据指出内战妨碍了经济增长的汤玛士科克兰认为,内战其实不是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机械化战争。“它是由步行或骑在马背上的人用来复枪、刺刀和马刀来打的。炮虽然比过去的战争用得多,但消费的钢铁还是比较少。铁路也用上了,但是军用线路的修建只能抵消从战前民用铁路建设全面下滑的一小部分。如果不是这样,工业发展相当有限的南部同盟根本不可能在封锁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打四年的战争。” 据英格曼统计,战争中小型枪械生产使用的铁只占1861-1865年美国铁产量的1%。如果用来修铁路,可以铺650英里的铁轨。战争期间少建的铁路里数是这个数字的 7倍。
消
第二,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当时人和后来的史学家容易形成战时经济繁荣的错觉。据统计,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在1859-1869年上升了70%。这样,国民生产的名义总值(按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当时价格计算)和实际总值(按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不变价格计算)相距甚远。1860年代的名义总值给人高增长的印象,其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6%,甚至超过1850年代经济繁荣时的610%,可是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其实际年增长率只有165%。从下面有关1839-1899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图2 和前面有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的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以当时价格计算,我们眼前出现的是战时经济繁荣和战后1870年代的衰退。可是用不变的1860年价格计算,那又是另一番图景:我们看到的是战时经济停滞和战后1870年代的增长。正如罗杰L冉森姆所言,“尽管他们肯定知道战时的通货膨胀和1870年代的通货紧缩,对于当时人和很多历史学家来说,得出战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奇怪。”
,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跌,从而导致利润增加,是一些学者认为内战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现在有的经济史学家对实际工资下跌是否一定与利润增加相联系表示怀疑,有的则认为即便有联系其实际作用也不象过去估计的那样大。威斯利C密契尔在1903年曾指出:“内战期间实际利润不同寻常地高,… 是因为实际工资、租金和利息都低。”据他计算,实际工资指数从1860年1月的100上升到1861年7月的104以后,在战争期间大幅度下降,到1865年1月跌到了67。 后来赞成比尔德和海克观点的学者便以此为根据,论证内战中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滞后使实际利润上升,结果刺激了工业的发展。问题是实际工资下降不一定导致利润上升,因为造成实际工资减少的原因也许不是引起收入再分配(工资滞后)的通货膨胀,而是其他的缘由。例如,劳工素质下降就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学者们没有关于劳工素质的可靠史料来加以证实或否认。瑞本A科瑟尔和阿明A爱尔琴则认为,导致实际工资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美国对外贸易形势恶化和战时税收的增加。 然而其他学者觉得他们尚缺乏有关这两个因素与实际工资关系的足够资料数据。史蒂芬迪卡纽和玖尔莫基洱在1977年尝试把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滞后与其他因素造成的实际工资下跌分开来。结果他们发现1861年没有工资滞后,但在整个内战期间实际工资下降有47%是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资滞后引起的。这就是说战时实际工资下跌的确有利于收入再分配向资方的倾斜,即利润的增加。不过,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指出,内战中只有28%的劳工在制造业工作,靠通货膨胀把他们微薄的收入转移到利润上的数额即便有,也相当有限。
除了分析统计数据以外,学者们对内战中政治权力转移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也作了新的探讨。事实上,比尔德和海克在立论时就非常强调这种影响。海克在《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一书中明确指出:
这些经济立法如果没有内战和它所带来的政治权力转移是否就无法在国会通过,是一个尚有商榷余地的问题,但不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内战中通过的这些立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不是具有形成分水岭的作用。
内战中共和党人占统治地位的国会从1861年就开始通过增加关税的法案,到1865年关税收入翻了一倍。经济史学家们承认,增加关税无疑是共和党内主张保护本国工业发展的派别的胜利。不过,关税保护主义的作用不宜夸大,因为关税是当时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战争开支猛增的情况下,政府求助于关税,并没有什么破天荒的地方。事实上,当时关税税率的增速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据黑哲C理查逊对内战中共和党经济政策所作的最新研究,1861年关税法的主要起草人共和党众议员杰思亭史密斯莫里尔虽然主张关税保护,但他反对以牺牲农业利益来保护工业利益。因此,莫里尔关税法案增加的不仅是制造业关税,而且包括农业与矿业关税,兼顾了南部与西部的利益。南部参议员在1860年反对它,害怕的就是其政治吸引力。1862年关税法和1861年一样,仍然是全面增税,不过农业关税的增加对农场主已无好处可言。因为此时的北部基本上已不进口农产品,倒是有大量农产品出口。1864年关税法也大体如此,莫里尔第一次承认他提出的法案保护了工业,但他强调关税并非“没有节制或者高得无人敢于问津”。
1865年以后,战时的高关税被保持下来。受到关税保护的部们固然是受益了,但整个经济的增长是否也得益于高关税政策呢?这是一个经济史学家至今都难以回答的问题。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最近曾指出:“尽管长期以来关税对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就引人关注,有关它们作用方向和规模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所以进展不大,有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复杂性和获得适当的经验度量的困难性。另一个因素则是学者们在如何估量关税保护的作用上意见分歧。”以关税问题权威学者弗兰克W陶星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关税对整个制造业的成长起的作用很小。近年来的研究则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不过,当学者们肯定关税的正面作用时,他们一般都注目于内战前的时代,因为那时很多工业部门还处于幼年时期。内战以后的高关税则是在美国工业已经走向成熟的时代实施的,如何评价又是一个问题。美国学术界对此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与结论。
不过,杰弗里 G 威廉姆逊倒是指出了内战及其以后的关税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一个正面作用。从他提供的表3可以看出,资本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内战及其以后有大幅度下跌。这自然刺激了投资,加速了固定资本的形成。问题是资本商品相对价格下跌的原因何在。不少经济史学家认为答案还不清楚。威廉姆逊则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说原因在关税。因为关税保护的是制成品,而不是资本商品和中间产品。资本商品中最明显的例外是钢铁类,不过威廉姆逊认为受到关税保护的钢铁成本在耐用商品总成本中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总的说来,缺乏关税保护的资本商品的相对价格要比制成品低。 这是不是对资本商品价格下降恰当的解释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现在从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中还难以找到答案。
表内战中的银行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战时财政开支压力下通过的。财政部长蔡斯在动员银行认购国债时遇到困难,乃于1861年建议国会进行货币银行方面的改革,削弱由州政府发给许可证的现行州许银行体系,代之以由联邦政府发给许可证的新的国许银行体系。新的国许银行必须购买政府债券存于财政部,换取统一的银行券。1863和1864年通过的国许银行法就是旨在建立这样一个新的银行体系,既有利于债券的销售,又可以削弱州许银行体系,并进而统一货币。为了加强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两个法律对开办国许银行的资产和准备金也作了比较高的要求,而且在银行业务范围上多有限制。结果很多州许银行不肯就范,拒绝换取联邦政府的银行许可证。这样,国会不得不在1865年3月决定对州许银行的银行券征税10%,使之几乎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州许银行才被迫纷纷改为国许银行。到1866年,国许银行从1863年的63家增加到1644家,其流通银行券价值高达2亿8千万美元,州许银行则从战前的1600多家下降到297家,1868年更是跌到最低点:247家。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立法支持横贯大陆大铁路的修建,功过如何评价?这是经济史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而且讨论了多年。那些赞成联邦政府给铁路公司以土地赠与和补助的人所持有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超前建设”。“超前”的意思是指当时如果完全靠私人投资建铁路尚难谋利,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机会成本高于私人回报,即把钱用于修铁路不如进行其他投资。在私人回报不高而社会回报很高的情况下,政府当然应该通过土地赠与等手段来刺激私人投资进行铁路建设。事实是否如此?罗伯特W佛格尔就此对联邦太平洋公司作了研究。他发现按照帐面记载计算,联邦太平洋公司在1870-1879年的平均回报率为51%,而当时好的公司债券回报率在5%-7%之间浮动,政府资助似乎确有必要。问题是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帐面开支不仅包括现金开支,还包括倡导铁路者的利润和公司债券的折扣。净收入又是以当时美元计算,而1870-1879年是价格猛跌的时期。佛格尔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重新计算后发现,公司平均回报应为116%,高于机会成本。 劳埃德墨塞尔对其他几家大铁路公司的回报与机会成本也作了一个计算,列出下表:
表4: 铁路投资回报和资本机会成本
至于1862年宅地法,它显然不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土地法案,而是1800年以来逐渐放松的联邦土地政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项土地立法长期以来就有学者加以批评。保罗W盖茨在1930年代就认为过于宽松的土地政策导致了投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佃农制的扩展,而不是杰佛逊梦想的小农土地所有者的乐园。西奥多萨洛托思则批评这种土地政策把劳工和资本吸引到农业部门,对制造业在资源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罗伯特W佛格尔和杰克热特勒两位经济史学家利用经济理论模型论证了联邦土地政策对整个经济的积极作用。不过,他们并未专门讨论宅地法的影响。据 《美国历史统计》提供的数字,在宅地法实施后获得土地的农户中最后能真正靠农场为生的只占40%。 另外,把土地赠与各州开办农业和机械院校的1862年莫里尔法虽备受好评,但它和宅地法一样绝非具有转折性的创新之举。早在1787年土地条例中,每个镇丈量好的36块土地中的第16块就一律定为公共教育用地。后来联邦政府赠地给州办学也不乏其例。 最后还要提一下的是1864年契约劳工法,它除了有助于引进华人劳工修铁路,或者偶尔被用以招募国外熟练技工来美破坏罢工以外,此后很少沿用。 因此,契约劳工法对于美国劳工移民的多少从未产生过重大影响,更不会形成什么分水岭。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