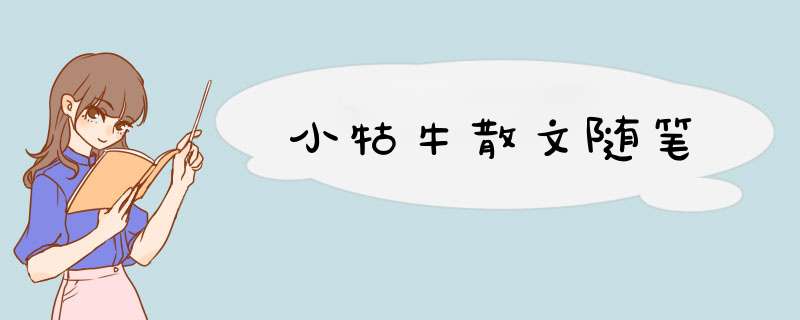
其实讲故事的周老头并不识字,只是记性很好。夏天热的青蛙都齐呐喊睡不着,人更娇贵,自然要想法子熬过前半夜。白天热气全压到地上了,不易消散。
逢夏夜家乡十几户人家,都变成了夜猫子(熬夜),小娃儿热的不盖铺盖(被子),大人一吼,精勾子(光屁股)上一巴掌是少不了的。小子只有猛哭这武器,但无效,更多招来连续巴掌到精勾子上。大人消暑有法子,那就是邻家的周老头。都到周老头家听他讲故事,一来消暑,二来懂些道理。一场故事没完,上半夜就过去了,屋外已凉风习习,下半夜回家睡觉。
乡村啥事都简单,人多没凳子了,自己带上。独凳没人挤,独腚坐江山,好着呢。来时带上还在嚎哭的小子,不听话,大不了再赏几巴掌。恶狠狠地说,今天在人家屋里,就不给你算到河里洗澡的账了,回去再说。小子回嘴,我没洗。大人抓住小子胳膊用指甲一划,晒黑的胳膊上一条白印。还说没下河,哄我!家乡大人用这个法子验证很灵,小时我们都 试过。只要下河洗澡了,加上太阳一晒指甲一划,必定有白线,赖不掉的。小子顿时不再吭气,也不哭了。
周老头摆故事当然是免费的,他年少时到城里当裁缝学徒,刚好隔壁茶馆里有说评书的。三五年间,学成手艺回家乡办了裁缝店,记性好的很,一转眼几年过去了,若干的评书,诸如《三国》、《水浒》、《说岳》《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哎呀,他居然都记住了,成了有文化的人儿。
平日里邻居磕磕绊绊的吵嘴,田边地角的争夺,儿女不孝等等。都请他来评断,一言既出,结果即定。
小娃儿下河不能洒尿,洒尿就是做孽,会遭罪。成年人不能骂长辈,忤逆不孝,会遭报应。诸如此类引导人心向善,是个好老头。他讲故事,参杂某件事某个人,有一定针对性。
周老头个矮,生了儿子却是膀宽腰圆,力气大,个儿高,人送绰号:乜牯牛。家乡有谚语:三岁牯牛十八的汉。小牯牛是说最壮实年轻的牛。小牯牛要上道,先要调教(治理)。调不好,耕田耙地不顺犁路。调好了就是宝贝。他家儿子小牯牛心眼活,见啥会啥,农家极好的劳力。这等小子在乡间招蜂引蝶也是正常,少不了小媳妇大姑娘对他暗恋。
小牯牛说了门亲,是邻村王家姑娘,她爹是个教书的,与周老头家很配。其实哪都讲个门当户对,虽然大家都在批判是旧思想,老封建。但扪心自问,谁家不是这样在衡量呢 小牯牛能让周老头省心不谁年少时不是头不听话的牛呢这小牯牛况且这么好,他不说不喜欢王姑娘,又偏偏喜欢上了本村杨姑娘。当周老头听到有点风吹草动时,周老头暗骂儿子:这头牯牛,没调好的牯牛。问儿子有没有这事小牯牛说你也信这种话还好,周老头踏实多了,我家的人能没教养自与那教书的王亲家正常走动。小牯牛也没说咋地,也许是与杨姑娘相互爱慕罢了。村里村外都近,都知道谁家女是谁家媳妇,脑瓜子定了,从没人怀疑有二样。这号(种)事,日子久了,都会烟消云散的,还会沿着原来步子走下去。
邻家们坐着互问:二道(第二次)草薅(除)了没
邻家人说,头道都没薅完,洋芋挖不赢(完)。
哦哦,慢慢来。周裁缝摆龙门阵噻,你看,娃儿都有瞌睡了。
周老头看了看常听的邻居都在,让乜牯牛把马灯(没电灯)调大些。给没凳子的`端了凳子坐下,他感觉小牯牛今晚很听话,很满意。
闲话少说,且说薛仁贵当了将军,他正返乡去看望独守寒窑的妻子王宝钏。在离寒窑不远的芦苇江边,换了一身当年旧衣服,背上旧弓箭往家走。他想试探妻子是不是还在寒窑,是不是为他守身,会不会不认一事无成的他,会不会早已见异思迁,众多的问题让他步子越来越慢。
正思处,恰是当年他射雁度日的芦苇江边。抬头一行大雁正飞过,他张弓搭箭只等雁叫便射。薛仁贵武艺高强,尤善弓箭。大雁飞过,只需张口一叫,他能箭无虚发,只中雁喉。射其他部位,买家会说伤了雁身,价值低。只有射最难的喉咙处,不会让人闲弃。雁张嘴叫,身体必缓。薛仁贵能恰到好处射中颈部, 这叫射的张口雁。除了英雄薛仁贵,还有谁能有这般能耐
常言说的好:一山还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正当薛仁贵等大雁开口叫时,芦苇对岸一少年,连发十数箭,大雁接二连三掉下来。那弓箭真了得,箭箭只中颈部。
薛仁贵大惊,还有人能射闭口雁!世间还有此等高人是敌是友友则罢了,是敌如何是好高我太多,敌友难分,恐此人对我不利,不如趁此杀之。心念起,胆以恶边生。对准少年一箭过去,那少年应声倒地。正急步查看结果,突起狂风,大风中跳出一花纹吊眼大虎,叼起少年,瞬间不见。薛仁贵目瞪口呆,惊异万分。心道,本想掩埋了你,不想老虎叼了,且不要怪我。
周老头喝水换气时,习惯抬头一扫众人,哪曾想,却看见杨姑娘和小牯牛坐在一起!他与薛仁贵一般,目瞪口呆起来。这条犟牛……
他一慌,突然忘了向下说。
邻人叫,周裁缝,那少年是谁呀,薛仁贵回家看见了啥呀说呀。
周老头,晕了晕,有气无力地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四叔是本家四叔,在村子里,除了二爹,就顶数四叔近了。
四叔没有儿子,对此,四叔很伤心。记得有一年正月里,四叔在我家喝多了,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四叔就抱着婆的腿,跪在炕头上呜呜大哭,满脸都是泪,哭说自已命不好,不孝,断了后了。四叔只一个女儿,好像大我五岁,乳名叫棉花,记得长的真像棉花一样白,模样儿也周正,只是四叔不喜欢,加上念书也不得要领,只念到小学,便不再上学,早早地就被四叔叫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后来嫁出去,家里便只剩下四叔、四婶两个人。
实话说,小的时候,我是极不喜欢四叔的,甚至是恨了,恨的时候,有好几次想把四叔那杆枣木烟袋扔进水井里,再往四叔的烟荷包里抓上两把土。只是,想归想,到底是不敢的。这之中,也不为别的,只因四叔嘴快。要是做了什么坏事,比如去深水处漤澡或偷了人家的瓜果梨桃,再比如从家里偷出油来去烧青蛙吃,都会唬着脸先打顿屁股。这也罢了,不会当会事,因不会使劲打,倒是打完了还要拉着去跟婆说,这事却是能让我在心里生出恨意来。因为,当拉着来跟婆说我这些“劣迹”时,总受不了婆此时脸上的忧色以及连连的叹息声。每到这时,心里就会后悔,就会暗暗恨自已又让婆生气了,心里就会难受。不过,也有打疼的时候,因为打的疼,所以至今仍记着。
那是一个蝉鸣六月天,要做套蝉的扣子需要一根马尾,便去了马棚,因四叔就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除了吃饭,白天黑夜都在马棚里干活睡觉。
老远就看到四叔把大牲口们都拉了出来,在用刷子给牲口刷毛:大灰骡子,小二马蛋子,老黑马,特别是那匹外号叫“杨贵妃”的枣红马真是漂亮,毛色也鲜亮。就直奔它去,揪着尾巴一拽,长长的几根马尾就得到了。这时,我见四叔脸都变色了,惊恐地一边瞪着我,一边慢慢拉紧僵绳,把“杨贵妃”领得离开我后,才“嗷”地一声吼了起来:“兔崽子,不要命了。”说着就过来把我按在地上扒下短裤,颤抖的手按住了,另一只手轮圆了就是一顿狠揍。这次是真揍,不是往常那种脸上发狠而手头轻落地假打,可能是打累了,竟然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手掌还在发抖。我先是给打懵了,后来觉着了疼,才“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可能是哭声使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又狠揍了几下,才一把提起来拉着就去见婆。当说到就站在“杨贵妃”的腚后拔马尾时,二爹也“啊”了一声,脸也变了色。
原来这“杨贵妃”顶不是东西,虽是母马却野得很,常伤人,从买来到如今就没干过活,因伤人谁也不敢使。头年冬里,车老板在队长的授意下,牵出去栓牢,三四个大人,皮鞭木棍照死里猛打一气,然后硬套在马车辕里,车上站满人便哪难走往哪赶,上坡处再也不肯拉车了,便又是打,打得倒在地上,上去拉,居然隔着马车撕下车老板一截棉袄袖子,差点伤了人。从此,驯这牲口的事,就再也没人提了,只想等发情了配上种,下个马驹也是好的。因整天光吃不再干活,命好,长的也光鲜好看,就得了个“杨贵妃”的名号。头年冬天,夜里四叔起来给牲口添料,披着的棉袄,竟然被这“杨贵妃”一口叼了去,甩在马厩里一阵乱踏,这牲口记仇,因上次驯服它时四叔也在场……
见这样说,才知二爹方才闻知揪马尾时,为啥会“啊”地一声脸色变了;同时也知四叔方才那顿打,那也是打了也白打并且是该打。不过除此之外,记得还有好些事当时总弄不明白,比如,好些事四叔来家告诉婆,总弄不明白,四叔他是怎样得知的那样清楚?像揪马尾这事是在他眼皮底下做的,不算。可剩下的那些也偏都能知道,这就奇怪了,这使我一度曾确信四叔是得了诸葛亮的道行:能掐会算。无奈何,以后只要是想去做什么事,总要前后左右先看看,确信四叔不在才去,走在路上,也会心惊肉跳地时时回头瞅瞅,看有无在后跟着,都坐下病了似的。
四叔当生产队的饲养员,手底下有五匹大牲口,近十头牛和二十多头毛驴,此外还有四五圈猪。小时候在村子里“绕世界”转悠着玩时,这马棚是断少不了要转到的,而且,也多半是能够驻足的地方。
“铜栓,准是去朱家茔抓青蛙儿了,你看腿上那些泥,也没抓着,对不对?”四叔边铡草边问铜栓。
“抓着了。”铜栓眼一翻不服地说。
“新民是不敢下水,因为腿上没泥,胆真小。”又对新民说。
“下了!不过不是在朱家茔。”新民也翻着眼不屑地回击。
“秀江、恭瓶儿不用下水,因沙矜矜对他俩最好,吃的还多。”
“你咋知道?”秀江瞪眼问去。
这时,四叔会“嘿嘿”地先笑几声后才说:“我能掐会算,我还知道你们烧青蛙吃是弄不干净的,因为那朱家茔大湾里的水不清。”
“净胡说,我们是在金翅岭那塘坝里抓的,那有泉眼,水可清了。”铜栓紧着辩解说弄得干净。
“那也不会好吃,因为没油盐。”说完还要加上一句:“谁敢从家里偷油啊?”
闻说,大家都一齐把目光对准了我。
……
四叔也有让我喜欢的时候,那是去马棚玩时,四叔常常是总能不知从哪摸出一两个桃、杏、瓜果什么的递给我,吃时看着他们手里没有,会觉着格外香甜,这时再看四叔,就觉着四叔也不那么遭人恨了。
更让我开心的是,四叔也会讲故事,而且讲的多半是《三国》,四叔讲《三国》,总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从来不能连起来,常常是前头讲“千里走单骑”,后面的又多半成了赵子龙怀揣阿斗大战曹操的五十六员上将了。而且,常常是这次讲的和上次讲的有不一样之处。比如:曹操屯兵长江这事,一会说是五十万,一会又可能就成三十万了;再如,两将相拚,这一回斗的是三十回合,下一回就可能就成五十回合了。对此心下也会犯嘀咕,到底哪次是作准的?就回家问二爹:“诸葛亮跟曹操到底斗了几个回合?”
“你听谁说的?”二爹这时多半会惊瞪着我问。
“四叔。”
“真是误人子弟,他俩何时斗过?”
“赤壁大战,曹操打不过,还割了胡子。”
“简直胡说八道,你以后别去听他瞎掰掰?”
“你又不讲给我听。”
四叔另外还有一个本事挺使人佩服。那就是不同时期的英雄好汉到了四叔这儿,一眼就能分出高低强弱来,而且说得是那样的肯定和有自信,由不得你不信。致于关公战秦琼谁赢谁输的问题,那简直不值一提。
“四叔,诸葛亮和吴用两个人比,谁的智谋高?”秀江常爱问这些问题。
“诸葛亮,这还用问吗?”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这么简单的事也来问。
“要是和姜太公比,谁的智谋高?”铁栓接着又问。
“这个……该差不多吧。”我以为会说姜太公厉害些,因为是神仙。没曾想却评成差不多,这个答案也蛮合心意,因常听《三国》,心里不免就更爱诸葛亮一些。所以,也不愿听到诸葛亮还有不如人的时候。
“《三国》里谁的武艺最高?”铁栓的弟弟铜栓嗑巴着小眼睛,认真地又在发问。
“关公!”新民抢着回答。
“不对!是赵云!”秀江一向喜欢赵云。
“应该是吕布!”我说。
“对!对!因为刘备他们三个人都没打得过。”沙矜矜也附合着我说吕布厉害,推断也一样。
这话一出,包括四叔在内都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四叔学问大,说那是怕伤了刘备,讲义气,不得已才都上手的。要不然,单是关公一人,那吕布也讨不了好去。
“关公跟关胜比呢?谁赢?”
“关公!”
“秦明跟张飞比谁赢?”
“张飞!”
“关公跟孙悟空呢?”
“除了如来佛祖,谁能打得过孙悟空?”在四叔的心里,竟然有能打过关公的,这真令我一是惊奇,二是敬佩四叔的大公无私。同时,也更印证了从前四叔所评过的所有的输赢,那自然是都有权威和可信的。
当时的人们,文化生活是相当的聩乏,尤其到了农闲的冬腊月,漫谩长夜,唯一的消遣,便是听人聊故事。而聊故事聊得最好的,那还得数我家二爹。二爹聊故事,真是绝了,那是有许多个“不”的:不间隔着一段一段地聊;每晚只聊一个钟头;除了冬腊月,其他季节不聊,聊时不用家乡话,是纯正的书场里的腔调。特别是这个不用家乡话来聊故事,在当时,听惯了日常的乡音俗语,乍一听这样的说故事,真是一下子就给镇住了。其实,在当时被镇住的岂止是我,村长、支书、队长等,哪个不是被惊得目瞪口呆?那惊堂木往桌上一拍,开口就是一句:“上回书咱们说到……”哪个不是给镇得傻了眼似地只是张着嘴巴听。讲的确实是好,简直就是在从头到尾在背书,但背得好、背得活、背得有味。因为,背书中还要有夹叙夹议外带插科打浑,真是幽默中有纯正,纯正中又带了些诙调,当慢则慢,当快则快,风声雨声江涛声,喊声杀声金戈声……总是讲到紧要处,来一声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再说,便嘎然而止。任你再三来求,也只是些闲话了,让你心痒难当,总是不破例的。唯有一样好,明晚肯定会按时来的,让你天天有盼头,盼着明晚快些来到。
天终于又黑了,晚饭吃罢,我会主动拿上二爹常用的惊堂木,拎着二爹常坐的马扎,再将那把小茶壶递给慢悠悠下地穿鞋的二爹:“二爹快点。”
“不急!”又穿上那件皮袄,才带着我向四叔的马棚而去。
进屋时,屋里早挤满了人,这时,大家都笑脸相迎,并闪出一条道来。每到这时,我心里总是美滋滋地往里屋走,里边是支书和上了岁数的人坐在炕上,有四五个,也忙着先打招呼。炕的正中是一张夜桌儿,上面摆了把暖瓶,桌的里边中间位置空着,地下是塞满了年轻人,见二爹进来,四叔早从炕帮的位置跳下来,先把二爹手里的茶壶接过去,往夜桌儿上放好,又接过马扎递到炕上桌后中间位置支好,待我跳上炕,才扶二爹上炕坐上马扎。二爹通常是先拿起小茶壶喝一两口,清清桑子,这时底下早已鸦雀无声,只听那惊堂木“啪”的一响,接着便是:“上回书咱们说到……”这就开始了。一部《三国》,一个冬天,到春节时差不多正好讲完。
其它时节也有农闲时,比如下了大雨,午饭后仍在下,没法下地,许多人便会聚到我家。这时,四叔总是在场的,而且冲茶到水的工作都是四叔包揽,尽管也奢望着二爹能讲一两段,但总是闲话加喝茶,最多也只是讲一些当年在关东的一些异闻趣事,《三国》是断不提的。耐不住,便会有人说:“四哥来一段。”随着不断有人怂恿、邀请,这时,四叔会放下茶杯:“好,我说一段。”接着是用他那枣木烟袋往桌上一敲:“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一顾茅庐,没见着那诸葛亮……”
“轰”地一声,大家便都笑翻了,就连二爹也忍俊不禁喷出口茶来。
“要说那诸葛亮的架子也真是忒大,那刘备的脾气也真是忒小,张飞可不乐意了,那脸郎挡着更黑了……”仍在讲,而且是也学着夹叙夹议,这时都笑得不行了。
“笑什么,讲的不对?”终于停了下来。
原来四叔讲这些的时候,也是学着二爹的口气腔调用普通话在说,但又学不对,发出的字音却是地道的胶东味,普通话加胶东腔两者合在一起,由四叔的口中冒出,简直能笑断肠子。
“没错没错,你还是用土话讲吧。”
于是,又用土话来讲:“打老远来了一个骑驴的人,嘴里念着诗,很有学问……”
“念的是什么诗?”
“就是下着雪骑着驴过着桥那个呗。”
“背来听听。”
“你又不懂,背什么背。”又接着说道:“就以为是诸葛亮,哪知道又不是,别人还好,张飞白磕了头,满心的火没处杀,上去揪下那老头儿,拔拳就想打……”
听到这里,别人还罢了,二爹直听得鼻子都歪了:“是那样的吗?是那样的吗……”
“那你讲、你讲。”四叔赶紧说这话。
只见二爹微一迟疑,便摇摇头先哑言失笑下,然后才说:“一肚子熊道道。”
在那些年代里,这可都是些美好而又精彩的日子。而这些美好精彩的日子,是因为有了二爹和四叔,才得以实现的。
二00二年那年的冬天,家母的身体已很不好了,请了假,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过了有五六天的样子,正想如何与母亲辞别,母亲却开了口:“你去老宅看看你四叔,小时候没少操心。”
“噢!”
“你怎么还不走?”见我坐在那好长时间仍不动身,便不悦地说道。
这才知道这是要我这会儿就去探望四叔去:“噢噢,这不在想带些什么去吗……”
“带什么?又不缺吃的,一辈子就好喝点酒,你带些去,不用好酒,只多带些就好。”说着叹了口气又道:“那个闺女棉花也不行,怕女婿怕死了,除了吃的,什么也不敢给娘家,你再留下点钱给你四婶。唉!”
见这般说,赶紧起身答应着:“我这就去,这就去!”
“你吃一顿你四婶做的饭,天黑前再赶回来也不迟。”
“哎!哎!”
二爹去世后,那老宅就给了四叔,进了老宅,一切都还是那样,就连地下的那火炉也仍在,只是这会没有生火,显得清冷得紧。两个老人炕头上一边一个,盖着棉被头对着头闷坐着。见我来了,先是吃惊地辩认,才亲热地让上炕。上炕后,四婶紧着下地忙开了,我知这是忙吃的了。
一会,搬上了夜桌儿,刷好了茶具,沏好了茶,这才细看四叔:“老多了,全然没有了当年在马棚时的笑容与机智了。”看着四叔我心里这样想着,很有些感慨,感慨中儿时的时光飞转眼前:“铜栓准是去朱家茔抓青蛙了,你看腿上那些泥,也没抓着,对不对?”
“新民是不敢下水,因为腿上没泥,胆真小。”
“秀江和恭平儿不用下水,沙矜矜对他俩最好了,吃的还多。”
“那也不会好吃,因为没油盐。谁敢从家里偷油啊?”
……
“唉!人要老也真是眨眼间的事。”看着四叔,回首往事,我这样想。
要走的时候,说是酒全留下,钱死活不要。而且,还叫四婶快去把那二斤鸡蛋糕拿来给三嫂捎上。这使我很感动,尽管当时我的母亲哪里还吃得动这蛋糕。
无奈何我只好对四叔说:“这蛋糕我带上,你知道,我妈顶愿吃这东西。你也叫四婶把钱留下,这是我妈叫给的,我这次来看了你二老,下次还指不定哪年哪月,你留下,我也好受些。”
“四叔:你和四婶硬郎郎的。”出四叔屋时,我看着四叔在心里这样祈祷着。
2006年家母祭日时,也曾回过一次老宅,门上有铁将军把门,街坊说被闺女接走了,接去住几天。我听着倒喜欢,细问时,方知身体并无大碍,只是,酒是喝不动了。
到如今,转眼这又过去了四年,不知四叔如何了,要是还健在,我只但愿我那棉花姐姐能不那么怕女婿,能时常回家看看,才好呢。
火盆旁的美丽冬天
作者:
吕清明
来源:《吉林农业 ·下半月》 2013年第 01期
童年,火盆是老家的冬天必不可少的一个取暖物件。冬日的夜晚,外面冷风呼啸,雪花弥 漫。一家人坐在火炕上,围在火盆旁,温暖惬意。那时每家都有一个泥做的火盆。母亲每天做 完饭后,把炉灶中红彤彤的木炭盛放在火盆中,用力压实,炭火的热量能维持一天。在外疯玩 后,一进屋就把双手放在光溜溜的火盆沿上,暖流一下袭满全身。
我时常在火盆里埋上几个土豆,一会工夫,热气腾腾,香味弥漫,吃得津津有味。或者在 火炭上放一铁片,在上面炒黄豆,伴着噼噼啪啪的声音,浓浓的大豆香扩散开来,惹得我顾不 上晾凉,就往嘴里添。
一边品尝着自制的独特美味,一边听爷爷讲故事,那是令人无比期待的事情。
借着火盆里的点点光亮,爷爷衔着烟斗,语气轻缓,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妙趣横 生。例如一个贫穷的光棍汉,每天干活回来,饭锅里都做好热腾腾的饭菜,一天光棍躲在门 口,到了吃饭时间,一个姑娘从墙上的画中走下来,后来姑娘嫁给了光棍汉。
有时爷爷也讲一些狐鬼神仙的故事。听得我脊背发凉,紧紧拽着爷爷的手,害怕得不敢到 外面撒尿。爷爷讲完后,总会往烟斗里拈上一袋烟,吧嗒吧嗒抽几口,我就拉着爷爷的手说:“ 爷爷,再讲一个。 ” 爷爷吐了口烟圈,一张永远也讲不 完。
爷爷的压轴故事是《三国演义》,什么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赵云单骑救主,每讲一 段,爷爷就留下一包袱,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天分解,于是我天天盼着天黑,盼着黑夜里的 故事会。
讲完了故事,母亲会和我们猜谜语,例如 “ 一母生俩郎,一个脸圆,一个脸长,一个生在 春三月,一个死在秋风凉 ” ,我和姐姐轮番猜也猜不到,我着急地向母亲要答案,母亲笑而不 语。父亲在旁边不断的提醒:“ 是一种植物,咱家后院就有。 ” 我说:“ 是榆树! ”“ 榆树上都有 什么啊 ”“ 榆树钱! ” 每年开春三月我都爬到树上摘榆树钱吃,这时姐姐抢着说:“ 我猜到了, 是榆树钱和榆树叶! ” 我当仁不让地说:“ 是我猜到的! ” 我和姐姐争论起来,爷爷和父母哈哈 大笑,一家人其乐融融。
评书
开头: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中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尾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你说的”欲知……,听我慢慢道来。“这个指具体事物了
抒情散文以抒发主观情感为出发点,往往借助具象,写景状物来抒发主观情感。那么叙事的抒情散文我们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叙事抒情散文800字满分作文,供大家欣赏。
叙事抒情散文800字满分作文篇一:蒲公英的天空风,用一种神秘而单纯的脚步游荡着——山坡上,于是,白绒绒的一片。飞向天空……
他,是一个农村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记忆中的某一天,奶奶指着那片随风飘远的蒲公英,告诉他,总有一天,他也会像那群蒲公英一样,飞起来!飞出大山!飞向世界!于是他记住了!以后,那个蒲公英飞起的山坡,就多了一个男孩的背影……
终于有一天,他离开了那个农村,那个他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考上了城里的一所高中。
乍来到这个繁华的城市!他怔住了!那闪烁耀眼的不再是萤火虫的舞蹈;那强灌入耳的不再是晚风合唱团……那大街上的车水马龙,那大街旁的灯红酒绿!有点头晕,他真的有点分不清东南西北!考试一次次的失败,每每看着那不合格的试卷,手就不由地攥紧了口袋里那看了无数次的家信。泪水中,他仿佛看见母亲希望的目光……他恐惧,逃避!他开始出入网吧,沉迷网络,企图用急促的心跳来填充那空白的世界——那没有了蒲公英的天空。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受不了了!他飞也是的跑出房间,奔下楼,穿过那一条条繁华的街道,甩下那一个个装了发条似的行人……一直跑到郊外的山上!他累的瘫软下去了,他听到他的心跳了,他把手放在胸前,一种强烈的挣扎……
闭眼……呼吸……
心,突然变得异常得平静,思绪中那一片空白……
山坡、风、他、蒲公英。
许久!许久!他回过神来,呆望着远方。风凌乱了他的头发!记忆中高中那一段时间在渐渐淡去,模糊,消失……他好像刚睡醒似的,擦着眼——小时候的梦,又如熊熊烈火,在燃烧,胸间,有股力量在挣扎,爆发……
“我要考上清华大学!我要飞!”于是,山谷里多了一首激荡的歌,在夕阳下,久久回音……
风,伴着花谢了又开!吹过山坡,有人在等着它,让梦飞……“有风,蒲公英会飞!”,许多年后,他这样对一个同样也在风中望着纷纷的蒲公英的男孩说……
叙事抒情散文800字满分作文篇二:永不落幕的爱他们是平凡的人,他们也是特别的人,所以,我们说他们是特别平凡的人。。
平凡的他们,演绎着平凡的事,而正是这些平凡的事,却唤起了我们那内心深处那不为人知的感触,世上没有不伤人心的感情,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会在你的灵魂上留下伤痕。
一个寂静的早晨,当一个14岁的小女孩打开自家的煤气的那一刹那,灾难降临了。爆炸震碎了邻居家的玻璃,震醒了正在熟睡中的父亲,听到女儿的叫喊,他冲向火海,在烟雾迷茫中寻找自己的女儿。
医院的急救室内,身体表面90%的烧伤度让小女孩疼痛难忍。然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快救我爸爸!
我想,就是爱,带着痛苦的爱,只有在灾难的面前,爱才会变的很坚强。
手术室外,哭得天地变色的母亲已经麻木地失去了知觉,只知道女儿还没有脱离危险,而丈夫还在昏迷。
手术结束后,一直紧咬嘴唇不肯喊疼的小女孩在麻醉药过后终于凄厉地叫了出来,那叫声撕碎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
人们往往能记住痛苦,因为痛苦比快乐更为深刻。
家毁了,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医药费的问题,为了女儿,父亲毅然办了出院手续,母亲憔悴地晕倒在亲人面前,那一刻,所有的人已经再也流不出眼泪了。
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不知不觉地就伤害了别人,相反的,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不知不觉的地就牺牲了自己。
学校里,小女孩的伙伴在繁华的街道上站了一个多礼拜,冻红的手捧着那沉甸甸的捐款箱,没有医生抱怨。
当你真正爱上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语言是多么地脆弱和无力,文字与感觉永远有隔阂。
是谁在唱他们的歌,是谁在弹他们的琴。他们走后依旧的街,有着美好依旧的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他们的事。
歌声形成的空间,任凭年华来去自由。依然保护着热不曾改的笑颜和一场博大而没有落幕的爱。
叙事抒情散文800字满分作文篇三:恩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十年,生死,思量,难忘。
王弗,是你的妻子,你更是将她视为一个可以与之商讨大事,筹划未来的同路人。可惜好景不长,情深不寿,王弗年仅二十七岁就因病去世生死永隔又难以忘怀,这样的岁月已持续十年之久,其情之深,其情之痛,可以见也。
道是那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深,这种情感,烙印于心,无须多想却难以忘怀,非时间,空间,生死可以阻断。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千里,孤坟,凄凉。
深情虽在,却无处诉说那凄凉。王氏坟在眉州,与你身处之地的密州相距千里。那两句写尽爱侣生死永隔的凄苦,如唐孟棨《本事诗》载孔氏赠夫张某诗:“欲知肠断出,明月照孤坟。”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相逢,不识,满面,如霜。
相逢不相识,王弗离去,你还是一名锐意进取的青年,名满天下,仕途畅通,春风得意马蹄疾。十年过去了,你经历了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屡次贬官外放,意气风发早已不在,有的只是满心的疲惫与那风霜、那满怀悲愤辛酸却也无处可诉说。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幽梦,轩窗,无言,千行。
你在梦中梦见了王弗,凄楚哀婉,用梦境写人,描绘出妻子对镜梳妆,见到久别的丈夫喜极而泣的情景表现了你对她生死不渝的恩爱之情。那似乎呼之欲出,历历可见,几使人误以为回到了年少情浓的十年前是十年风霜后的梦中相见,而那千言万语却无法说出,只有那相对流泪的伤神心意相通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肠断,月夜,松岗。
梦已醒,人已逝去,无处追寻,只有月下怀想:千里之外,短松冈上,年年肠断。
父亲一生中最后的目光,留恋却也绝望。俯首于身旁的儿子,切肤地痛感到一个人到了生命尽头,是多么地无奈。这便是生离死别。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长幼,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漠视死亡,因为造物主确定了人总是会死的,没有谁可以续在世上。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死亡便会光顾每一个人。祖父去世后,父亲曾悲哀地感叹说,该轮到我这一茬人了。好像在说一茬庄稼,种了又熟了。如今,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长眠在自家耕种的土地的深处,孤独的是我,愈是敬畏于生命的意味了。
按老家习俗,人咽气前须备口含的麻钱,穿好寿衣,左手握金,右手拿银,怕步入阴间显得穷困。麻钱是旧币,寿衣是长袍短褂,金银也是纸质的,葬俗的惯性看来可能顺延一百年,起码给以后的考古者留下误读的理由。此时,须从窑背上扔下一块石头来,大喝一声“泰山倒了”。于是哭声大作,四邻赶来,有长者主事,开始部署丧葬的诸多环节。过去报丧,孝子先翻沟过梁告知老舅家,然后是亲戚和村邻,得在门外磕头且不得入内。如今一个电话,告知去世时间和葬埋的日子。乐队过去叫“门上阿”或“龟兹”,已演变为唢呐加老戏及洋鼓洋号歌舞,曲子是《祭陵》、《女儿歌》及《送别》。得请冰棺、棺轿、布置灵堂、包席厨师、置办酒宴、上礼簿、制孝服等各路人手。主持是曾祖父辈的老先生,吆喝接待吊唁者、把握程序和各种礼数。家祭即献饭,到村口迎舅家的`饭,祭品花样繁多。宗法文化的礼俗,是以尊重死者为核心,同哀共悲,顺其自然,讲究礼尚往来,一起面对不可战胜的死亡,凭吊死者,宽慰生者。
在入夜的追悼会上,我作为长子,泣读了祭父文:
父亲和府(讳)忠贤,生于一九三三年农历十月初八,因病于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即农历闰四月二十三日七时十五分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父亲自幼农耕,卖柿子担草,吆骡子驮炭,靠自学识文断字。农业社时是突击队标兵,去西侯铁路当民工,社教后当过多年生产组长、副队长、队长、大队农机站长,平整农田,兴办煤窑,淘气劳神,料理村政,改善社员生活。合股办煤矿当矿长,因意外事故坐牢十多天,忍辱负重。晚年与母亲修地栽树,自食其力。患病后,艰难度日,明白世事生死,心境淡泊,超脱安然。
父母亲侍奉曾祖父多年,孝敬祖父母,侍候瘫痪的祖母,尽其孝心。毕生勤劳智慧,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养育三男四女,供养念书,成家立业,操心孙子辈成人,四世同堂,家业兴旺。
父亲一生正直善良,尊重长辈,教子有方,爱戴儿孙,宽严相济,勤俭持家,乐观向上,知足常乐。与兄弟姐妹情同手足,宽容大度,与自家和亲戚及友人和睦相处,亲近和蔼。待人诚实热心,处事公道平和,礼让乡邻,乐于帮人,接济困难户,有情有义,德高望重。
儿女将永远不忘父母养育之恩,铭记父母的教诲,继承父亲的遗志,团结协力,履行养老送终、抚养子孙的责任,把父亲的精神代代相传下去。父亲永远活在儿女子孙们的心里。安息,父亲。儿女子孙叩首。
之后,是招待亲戚村邻的“唱戏”。秦腔声声,辣耳酸心,歌舞动情,也是一诉人间真情。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八十有一算是高寿,也称喜丧。婚丧嫁娶,给平时冷冷清清的乡村,给离多聚少的乡邻们提供了一个“见人”和娱乐的机会,算是悲喜交集的事。父亲患病六载,村上从十几二十岁至六七十岁的人已陆续有二十多位去世,也添了许多新生的孩子,人口基本保持平衡。一辈人换一辈人,像庄稼一样,老母亲这话在理。
太阳冒红的时候,乡亲们和孝子簇拥的棺轿离家出了村子,缓缓前往墓地。土原上的麦子熟了,金黄的土地泊了一片核桃树苗。唢呐嘶鸣欲断魂,黄土飞扬,父亲入土为安了。这块地方叫老陵,千百年间,多少先人在这里化成了泥土,只是在族谱中留下一个个名字,连接起远逝与活着的人。我的故乡,我的父老兄弟姐妹啊,就这样生生不息。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