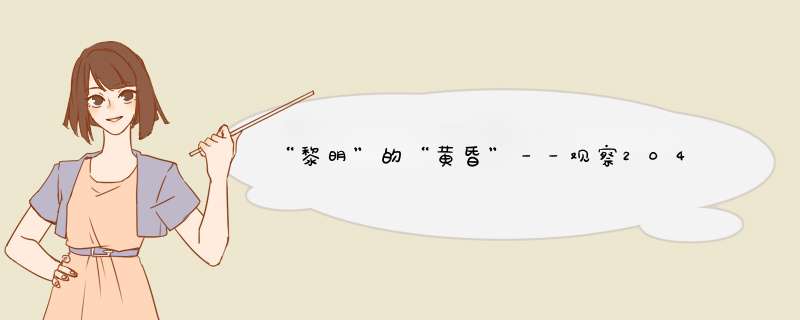
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历史性(拉赫曼,Lachmann,2013)。如果深究这句话,你就会发现,无论成熟度多低的社会,都会存在其历史。这是因为它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社会”,一定会存在一个发育的过程。在现代,我们几乎没有可能去观察一个从零开始发育到“成体系”的社会,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率地观察到一个社会是如何以极高的改造速度和反应速率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种案例的趣味就在于它的历史之短,短到让人不相信它会发生这种巨变,而不是所谓的传统之深厚。
东北地区的社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说东北地区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可是我在这里写的这个东西,既没有那些基于某种优越感的“批判和反思”,更没有所谓的情怀和眷恋。应该说,这是一部我的家庭史,父母各自原生家庭的两代人,见证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巨变,见证了部分国有企业从极盛到衰亡的全部过程。可是这样广博的话题,以我们所见,并不能做出详细和客观的描述,只能选取我生活的地方去观察和描述,而这个地方就是题目中那个数字——“204”。
“204”是什么?它又在哪里?
“204”是一个代号,指的是沈阳黎明厂生活区。如果现在来实地考察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大片的苏式楼和一部分分厂厂房。熟悉东北大型国企的人应该知道,生活区是与企业紧密相关的。204地区就是和黎明厂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航发黎明)公司前身始于1919年张作霖创办的奉天军械厂。1954年3月31日,公司作为国内较早的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正式组建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航空涡轮喷气发动机制造企业。”(中国航发黎明简介,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 )。黎明厂成立之后,除了依靠原有的东塔机场之外,还营建了生活区,生活区内有各式居民住宅,按照职务级别的不同进行分配;兴建了医院、学校、商店、游乐设施,有着属于自己的市政设施。可是这些基础建设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并不是靠着这个企业的“一己之力”,就像沈阳黎明简介中所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有根基的。
要回答这个根基是什么,就要说明204究竟在哪里。众所周知,沈阳是一个历史不大长的城市,其能称之为“都会”的历史,恐怕只能追溯到后金改称为清的时代。由此,沈阳的城建史也是十分简短的,前近代城建历史的简短,反而成就了近代沈阳城建的张力和空间。清建都盛京之后,沈阳内城的范围也随之稳定了下来。内城的中心就是现在沈阳故宫和中街路一带,四周拓展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这也是受到了传统帝都营建思路的影响。在内城的四个角之外,又营建了四座佛塔和配套的四座寺庙。这就是沈阳作为都会的早期的全部空间范围。近代之后,随着东北开放和奉系军阀的大举开发,沈阳的城市范围才又一次得到了拓展。大致来说,这时期的城建史主要是向西拓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在沈阳站一带和老铁西工业区。澎湃新闻中曾经连续报道了沈阳建筑大学建筑史研究所对于沈阳近代建筑风格的研究,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一个研究小组也对沈阳站附近的城建布局进行了十分细致的调查,对于沈阳工人村和工人住宅形态的研究也相当成熟,有兴趣的诸君可以搜来看看。这里笔者想提及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沈阳西部的城建历史,也就是出怀远门(大西门)以西的区域。而沈阳的东部的城建史,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象。
204地区,就是在这个广袤而荒芜的东部。从正阳街和沈阳路交叉口出发,一直向东而行,经过大清门和文德武功两个牌坊,出抚近门(大东门)。抚近门外和小东门里的大片地区,曾经是守城八旗兵丁聚居的地方,再往东走,出小东门。出了小东门,实际上就已经走出了老沈阳城的范围了。再向东行,就是沈阳城东的角落之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塔”。
东塔以北,滂江街以西,就是所谓黎明新城的范围,而这个地方,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当中,长期被人们视为偏远和破败的象征。其实,导致这一地区开发程度低的另一个原因恰恰与清代以后沈阳的兴起有关,那就是,再往东面走,就到了清代皇家的祖陵——福陵。至迟乾隆年间,福陵附近的大片区域都被划为了禁区。家里人回忆1990年我家刚刚搬到这一地区的情况时说道,在这附近甚至还能看到大片的一人高的野草和连片的农田,这些景观和大片的居民区以及厂房杂处,确实也能感受当时工业布局的用意,关于这一点,之后会述及。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开放了东北地区,出现了我们熟知的“闯关东”群体,沈阳人口开始膨胀。接着,就进入了奉系控制东北的时代,很多人都怀念那个时期东北的繁荣,事实上,人们有这种情感也可以理解。因为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204地区所在的沈阳东部,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开发,确切地说,这种开发是一种军事和工业相结合的布局。除了上面提到的奉天军械厂之外,这一区域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东塔机场和东北陆军讲武堂了。关于东塔机场,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就不在此赘述了,而对陆军讲武堂的发现和研究,是近些年东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建立后才兴起的。
日本侵华时期,侵略者开始在这一地区大兴土木,盟军战俘营旧址就是证据。关于这一监狱的情况,已有诸多研究,近几年该博物馆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复原和抢救性保护。可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在这座监狱对面的大片工业建筑,也曾经是这座监狱的配套设施,最醒目的就是一个变电所和一个零件加工厂。零件加工厂现属于中航黎明,还保存着一些原有的建筑(见下图)。而变电所现由国家电网沈阳分公司管理,原有建筑已经在2001年改建时被彻底拆除了,只有西面的围墙保存了下来。记得在拆除变电所的前夕,大量的办公家具被清理出来准备当作旧物变卖,其中有一个柜子上面的铁标签上还写着“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字样。时至今日,监狱原有的战地医院(后成为沈矿职工医院)已经成为了地铁工地。不过,医院附近的军官宿舍和士兵宿舍还存在着,甚至还居住着大量的老人和租房户,这些建筑竟能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仍旧没有任何损坏和坍塌的迹象,我想起了大学时老师们形容旅顺博物馆的一句话:“日本人把建筑修得如此坚固,足见其亡我之心!”这话在盟军战俘营身上也同等适用。
由于史料缺乏整体性,我们难以对东塔204地区社会在建国前的全貌做出一个系统性的描述。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判断。第一,近代是这一地区开发的起始,也是社会系统形成的起始;第二,虽然有一定居民在此地定居,但是这里很有可能只是工业区和居民点的复合体,也就是说,城市空间并没有拓展到这一地区,这种巨大的城乡撕裂感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第三,早期工业的畸形发达和社会发育的迟滞,也决定了沈阳城市东拓的范围长时间止步于此。
而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带来了大型国有企业,也带来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
未完待续。
故宫开门时间应该是8:30—17:00去世博园可以跟旅行团一日游,市府广场早上应该有发团的去年我去过。自己去可以到马路湾或北站坐168去,也可以坐火车去。坐火车每天沈阳站6:53和9:10有车,北站6:31和9:27有车,回来时17:44和19:55有车
延安位于陕西北部,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她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延安地处黄河中游,陕北高原南部,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省接壤;北靠本省愉林地区;南接我省渭南,铜川,咸阳三市地理位置为东经107度41分至东经110度31分北纬35度21分至北纬37度31分之间,市区南北直线距离23912千米,东西间距25785公里本地区有很好的植被覆盖,延安有森林27699万亩森林覆盖率为429%,有天然草场18569万亩,中草药品种约500余种全市已探明 矿产10多种,其中煤炭储量71亿吨,石油43亿吨,天然气储量33亿立方米,紫沙陶土5000多万吨 延安,广义上是指延安市所辖的13个县(区),既宝塔区,延长县,延川县,子长县,安塞县,志丹县,吴旗县,甘泉县,富县,洛川县,宜川县,和黄陵县总面积370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559万人,其中城市人口5964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5人平均海拔1000米,平均降水量500毫米,无霜期平均170天,在气候上属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我们通常说的延安,就是指广义上的延安
狭义上的延安就是指今日的宝塔区,是延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陕北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全区土地总面积3556平方公里,总人口3319万人(农业人口1987万)人均耕地面积248亩1982年被国务院发布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2,1994,1996,2000年被民政部军委总政治部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延安位于”两黄两圣”所构筑的陕西北线旅游”金三角”的顶端优秀文化积淀丰厚,所以延安又是一座旅游名城,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城”之美誉
延安古称延州,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延安之名,始出于隋。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同年设延安市,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1949年,改称县,1972年,再设市至今,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市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天然次生林163万亩,木材蓄积量308万立方米;以甘草、五加皮、寄生、牛蒡子、柴胡为主的中药材近200种;有豹、狼、石鸡、杜鹃等兽类、鸟类100余种;而且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适生作物品种多,具有发展种植业、畜牧业、林果业的良好条件。除小麦、玉米、谷子、荞麦、黄豆、绿豆、红豆等粮食作物外,还盛产烤烟、蔬菜、花生、瓜类、薯类等经济作物。
地处黄河中游的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相传人类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三黄一圣”(黄帝陵庙、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革命圣地)享誉中外,为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市有历史文物保护景点848处,有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群洞18个,石窟寺14处,有建于唐代的宝塔山等12处古建筑,有革命旧址6处。目前可供游览的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7处,年接待中外游客70万人次。近年来,大力开发旅游业,恢复了摘星楼、烽火台、摩崖石刻等50多处景点,“天然公园”万花山新增200亩牡丹,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万花山“四山”森林覆盖率达554%,被国家林业部批准建设国家级森林公园。
来自红色之路的感动
——本报“重走延安路”系列采访活动札记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句。4月上旬,当《中国艺术报》重走延安路采访组陕西分队到达延安,宝塔山真的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句诗,梦想终于成真。山西分队在太行山区、河北分队在西柏坡、贵州分队
在遵义,同样感受到延安精神的无处不在。半个月时间里,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圣地延安、在巍巍太行、在西柏坡、在遵义深入采访,挖掘《讲话》发表60周年以来的珍贵记忆,采撷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神州大地所孕育的艺术之花,寻访那些在民间流传的关于艺术、关于伟人、关于革命的动人故事。从4月5日开始到6月初,我们推出了“重走延安路”系列报道,共推出通讯、消息、等各类报道近40篇和专版5个。这些报道刊出后,采访组的同事们觉得十分安慰,因为我们深入了生活,记录了历史,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变迁。但我们也觉得遗憾,因为篇幅的限制,采访过程中许多生动的故事,无法容纳在报道中。时间虽然过去两个月,但是这些细节却不断地在我们的脑海中回放。今天,我们愿意为大家讲述这些深深印在我们脑海中的细节,让我们分享感动。
毛泽东伏在这张小炕桌上写出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
我们为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这大气磅礴的诗句,我们曾无数次地反复吟诵。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毛泽东竟然是伏在农家的小炕桌上写就这首词的。当我们在瓦窑堡听人介绍了这张小炕桌,当我们终于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第二展厅“红军东征”部分与这张小炕桌相逢,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它。年轻的讲解员介绍说,1936年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东征部队来到了清涧县袁家沟,住在农民白育才家中。为了方便毛泽东晚上办公,房东主动将这张小炕桌搬来。2月6日,陕北普降瑞雪,袁家沟的山山岭岭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中。毛泽东触景生情,浮想联翩,于2月7日趴在这张小炕桌上写下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毛泽东离开袁家沟后,房东将这张小炕桌精心保管,并作为传家宝传给后代。 1972年6月,延安革命纪念馆征集到这张小炕桌,开始将它作为重要展品陈列展出。讲解员深情讲述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了小炕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沁园春·雪》的思想内涵,也让我们为毛泽东艰苦奋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赞叹不已。
这样的乐观与豪情也体现在陈毅的诗篇中。在采访延安市文联的艺术家时,大家不经意地提到陈毅赞美清凉山的诗篇。他们介绍说,位于延安城东北方向的清凉山,不仅是名胜古迹荟萃之地,也是延安时期新闻出版机构的集中之地。新华社、《解放日报》、中央印刷厂、新华广播电台都设在这里。党中央的声音通过通讯社、报纸、电台迅速传遍抗日根据地,并通过由英国友人林迈可指导建立的英语广播部传向世界。因此,清凉山就成了延安与外界联系的桥梁。陈毅有感于此,赋诗一首: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后来,在与当地艺术家座谈时,也有不少人提到这首诗。革命前辈不畏艰辛、执著追求的精神尽在诗中。
在山西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我们也感受到革命者在困境中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和豪迈的诗情。在纪念馆中,我们看到了朱德离开自己战斗了3年的太行前线回延安之前写的一首诗: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经过浴血奋战、千难万险考验的朱德,依然意气风发,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当然,并不仅仅是炮火硝烟中的革命者才有这样的情怀。对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一样面临着艰苦环境的考验,并且交出了优秀的答卷。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后面的山坡上,有一间低矮、促狭的平房。听了延安市文联的同志介绍,我们才知道,这间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当年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谱曲的地方。在低矮的屋顶下,在简陋得近乎于无的条件下,冼星海以他的灵气、才情和热爱,写下了撼人心魄的《黄河大合唱》。
“我就是想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几首歌”
我们为艺术家与延安、与人民的深情所感动。
在陕西,我们通过采访前去采风和慰问演出的艺术家和当地文艺界人士的介绍,了解了一位位艺术家与延安的动人故事。
在北京采访著名画家张仃时,我们专门给他捎去了从延安带回来的大枣和小米,这个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人十分高兴,似乎延安的生活就在眼前。
对**艺术家于蓝来说,延安不是遥不可及的梦,而是慈爱可亲的母亲。“延安是我的母亲,1938年,我18岁那年就投向了她的怀抱。我吃过延安的小米,喝过延河的水,更重要的是,我和延安人民一起接受党的教育。《讲话》指引了我的一生,教会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使我的一生充满快乐。”当一个人的青春、事业乃至爱情都与延安紧紧相连时,那将是一种怎样刻骨铭心的记忆?从年逾80的于蓝的脸上,从她那激情难捺的言语间,我们找到了答案。
同样对延安满怀深情的画家李琦,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在延安清凉山脚下的解放影剧院前,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剧场走去的李琦驻足不前,凝望着前方笼罩在暮色中的宝塔山,陷入了沉思。此情此景,站在他的身旁,我们不知道这位9岁就来到延安并在这里度过了9个年头的老人,记忆中珍藏着多少年少的快乐与无忧。他只是轻声告诉我们,更像在自言自语:“每次来延安,我都要好好看看宝塔山……”
令我们难忘的,还有歌唱家郭兰英在杨家岭与延安老乡一起扭秧歌的情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郭兰英和一位头扎白羊肚手巾、挎着腰鼓的当地农民扭起了秧歌。在大家的掌声中,郭兰英深情地唱起了《绣金匾》,当唱到“三绣周总理……”时,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哽咽得唱不下去。郭兰英边擦着脸上的泪水边说:“我就是想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几首歌。”
当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树文、副书记覃志刚与赴延安采风的老文艺家来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旧址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在《讲话》发源地照张相吧。这一张合影,大家的感情非常投入,因为大家要把它当做永远的珍藏。
陕西省文联主席、从延安走来的著名作家李若冰说起延安,脸上浮起的是少年般开心的笑容。他始终心怀延安,称延安是自己的母亲,是他的生命之泉。“写那些关于延安的诗,我投入了很深的感情。”历经种种生活磨难的著名作家胡征,在西安的家中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得最多的是对延安的深情和对艺术的热爱,而绝口不提生活对他的不公。延安时期的音乐家曾刚也时常惦念着延安。他在一首名为《念延安》的诗中写道:陕北山河秀,延安同志亲。离家常惦念,梦里也牵情。并将这首诗置于诗集《心声录》的开篇,对延安的深情跃然纸上。听说采访与《讲话》有关,延安时期的艺术家张炎手、汪素华夫妇,马上打车赶到我们正在采访的韩维琴、常美容夫妇家中,两对延安时期的艺术家,给我们讲起延安的故事时,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期。有意思的是,退休后的韩维琴和其他一些老战友,把当年由两个人演出的《兄妹开荒》改为由十男十女来表演,很受欢迎,并一举夺得首届中老年健身舞蹈大赛一等奖——“兰花奖”。老人们说,虽然节目形式变了,但《兄妹开荒》所蕴涵的延安精神没有变。
在河北石家庄,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员、如今已经85岁高龄并卧病在床的著名作曲家张鲁一说起延安就打开了话匣子,采访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为两个小时,让我们采访能否顺利进行的担心显得多余。而张鲁已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并且在我们到达石家庄前一天不慎摔伤了腿。面对后辈关于延安、关于《讲话》的提问,张鲁显得十分兴奋,如见故人。我们知道,我们的采访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应该感谢的是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张鲁对延安的深情。
在贵州习水三岔河,几个苗族小朋友唱着动听的山歌、跳着苗族的舞蹈,为我们献上美酒。遵义舞协副主席王瑚玫在与其中一个小女孩的交谈中,得知她家境贫寒,当场决定捐助她。本报记者深受感动,也认捐了一个女孩。但是,当地民政部门的同志建议本报记者换一个捐赠对象,因为这两个女孩是姐妹,如果换一个,可以使更多的家庭得到帮助。本报记者马上表示,不用换,我认捐两个!有关部门当即决定现场搞一个仪式,仪式上,本报记者认捐的那个女孩一直不说话。但当记者将捐助款交到她手中,她突然跪在记者的面前。记者被震惊了,赶紧将她扶起,勉励她好好学习,争取将来成为栋梁之材。此时记者发现,同行的一些文艺家已经落泪。后来同行的人们笑谈,年轻的本报记者还没结婚居然有了 两个孩子,可谓“拉家带口”矣。
老人以毕生精力收集关于延安的资料
我们为延安精神和优良传统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天然的自觉传承而感动。
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我们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曾经给毛泽东闹过秧歌拜过年的两个老汉。当68岁的贾宜策老汉和88岁的冯志成老汉出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讲述当年给毛主席闹秧歌拜年的情景时,我们感到历史如在眼前。据说,贾宜策老汉经常到鲁迅艺术学院旧址来,给游人讲述当年的故事。正是这种讲述,让我们感到了活生生的历史,让延安精神和优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传承下来。而当贾宜策老汉唱起他自己创作的两首《送给江主席的歌》时,我们发现,哪怕就是在最普通的这些老汉中间,延安精神也注入了新鲜的时代内容。
“小小纺车吱扭扭转,摇起了那个纺车纺线线;别看这纺车小呀,力量大无边,边区闹生产,打碎敌人封锁线……”在枣园,在杨家岭,年轻的讲解员为我们唱起了反映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纺线谣》。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唱起来的是歌谣,留下来的是精神。在山西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身着军服的讲解员田悦慧也为我们唱起了《武乡开花调》。在随后的讲解中,她多次哽咽。讲到左权在做父亲不久就牺牲了时,她禁不住潸然泪下。而我们当中,多数人也早已经眼圈发红,噙满泪水。我们随机采访了一位年轻游客:你感动吗?他说,这样的时候感动是很苍白的词语,我内心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毕业于山西忻州师范学校的田悦慧如今是该馆最优秀的讲解员,为了提高讲解质量,她到全国各地采访老将军、老战士,购买有关书籍。当一个年轻人以讲解革命传统为职业,并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讲解中去时,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延续。
刘伟华是延安市延川县一个以自己的毕生精力收集跟延安有关的一切资料的老人。当我们慕名来到刘伟华的家中,才发现这根本不能算是一个家。几平方米的一个传达室里,除了一张床,就是满墙、满地的资料,各种有关延安的专题资料,挤在破旧的书柜里,等待着人们来发掘。近年来,不少延安时期的著名艺术家都来找他帮忙,复印资料,而他也是有求必应。虽然经济困难,家里人也不热心,住房也没有着落,但是刘伟华依然投入全部心血继续收集整理延安资料。当记者赞叹他的资料是一个宝库时,他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希望延安时期的资料不要越来越少。
而在贵州红军一渡赤水河渡口所在地土城镇,当地六七十岁的老阿婆自发地组织起来,穿上红军军服,又唱又跳,给外来的游客义务讲述红军的故事。她们把这当作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从她们略显苍老的歌声中,我们听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这就是后来者对传统的理解,和建立在情感认同基础上的自觉的传承。
“什么都可以被淘汰,民间文化不能被淘汰”
我们为民间深厚的艺术底蕴而感动。
当老伴用驴拉的地排车,赶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将66岁的延川剪纸大师高凤莲送到县城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我们被深深打动了。当她一边说话一边剪出一匹匹活生生的马时,我们只有惊叹。当她用一句“就是喜欢剪,拉着牲口就剪牲口,下着雪花就剪雪花”来回答我们的提问,当延川著名的布堆画家冯山云发表“为什么剪得好?就是因为用心剪,没成名之前用心剪,成名之后还用心剪”、“什么都可以被淘汰,民间文化不能被淘汰”、“画完了之后你最好跟农民探讨,农民的评论那叫一个精彩”、“女人剪纸是生命的艺术,男人剪纸是生存的艺术”等评论,我们禁不住感叹:与这些地地道道的民间艺术家相比,我们对艺术、对生活的理解还差得很远。这些其貌不扬的人们,才是真正的大师。
更加让人称奇的,是由延川县文联主办的一张小报《山花》。这张小报自20世纪70年代创办以来,已经连续出版近200期。“文革”之后,由《山花》报编辑的诗集《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发行达到28万册,并由香港三联出版社重印,向海外发行。几十年来,《山花》共采用稿件近5000篇,海内外不少报刊曾转载《山花》的作品。《山花》不仅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且还将路遥、闻频、陶正等一大批后来的著名作家团结在《山花》的周围,创造了“山花奇迹”。这是黄河与黄土地所孕育的一朵民间的文艺山花,正是因为它扎根生活,所以才常开不败。
在赤水四洞沟,陪伴我们的30多岁农民王德华,一路不停地为我们唱山歌,青山绿水间,他的歌声打动人心。同时,他还随手拾起路边倒伏的竹子,根本不借助其他工具,而是用手把竹子撕成细细的篾条,给我们编出了各种充满想象力的竹编工艺品。
生活,真的是艺术的源泉;艺术,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而生长在民间的艺术,永远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体会。
生活,永远值得我们感恩。
大家都愿为宣传延安精神和《讲话》精神做一点事
我们为大家的鼎力相助而感动。
中国文联党组领导对我们“重走延安路”整个采访方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多向地方的同志们学习。陕西省委副书记张保庆对我们深入一线采访的做法十分肯定;陕西省文联党组对我们的采访给予了大力支持;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著名文艺评论家、本报陕西记者站站长萧云儒不仅事先帮我们策划选题、联系采访对象、落实采访用车,而且还一路陪同我们到延安采访;陕西省文联办公室主任、本报驻陕西记者黄道峻全程陪同采访,为我们做了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延安市委副书记张勋仓、忽培元在接待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依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张勋仓还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延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曹振乾、延安市文联主席艾生以及一大批延安的艺术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延川县委副书记高凤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为我们组织了当地各门类艺术家的座谈会;延安历史资料收集者刘伟华无偿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延安电视台的同行对我们的采访活动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并于“5·23”前夕播放了专题片。本报河北记者站站长张从海和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陈宋良等也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重要帮助。山西焦煤集团党委书记薛山、副书记李瑞林,山西灵石县煤运公司总经理张建新、办公室主任王洪亮,山西长治农行行长牛子良等给本报记者的山西之行提供了大量帮助。而山西武乡农行副行长孙晋刚始终陪伴我们颠簸在太行山区的崎岖山路中,不辞辛劳,让我们深深感动。
所有这一切,我们不会忘记。而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么多关心和帮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采访的主题:重走延安路。大家都希望我们的采访获得成功,都愿意为宣传延安精神和《讲话》精神做一点事情。
“这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在我的生命中也有重要意义。”采访组一位刚刚毕业一年的年轻记者这样说。她的话也代表了我们采访组所有同事的心声。我们在那些用一生去追求理想的前辈身上感受到了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真诚、对信仰的执著。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走向广阔的生活。本报所在地是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文苑”。我们从采风中得到的启示是:作为从事文艺新闻报道的记者,也应该“走出小文苑,走向大文苑”,去捕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文艺事业的精彩和文艺家在实践“三个代表”、发展先进文化过程中的身影,为传播先进文化做出自己应有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