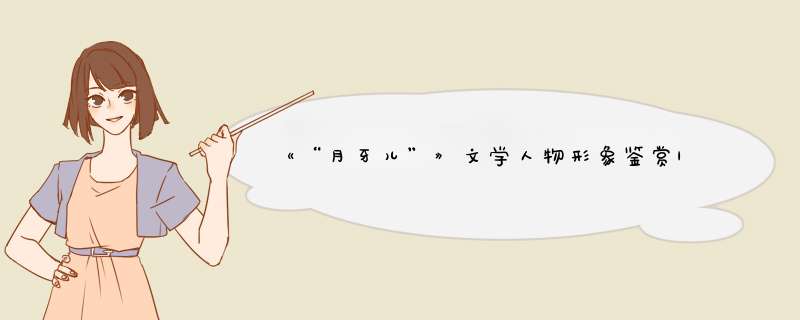
一九三○年老舍自英国转道新加坡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以日本军国主义在济南挑起的“五三”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书稿在上海“一二八”的炮火中被焚毁后,作家在一九三五年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改写成中篇小说《月牙儿》发表。
和许多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一样,“月牙儿”的童年是惨淡无光的。仅仅七岁,她已失却了本应属于她的天真和欢愉,家里的一切无法慰安她那颗稚嫩而寂寞的心。屋里是药味,烟味,妈妈的眼泪,爸爸的病;没有人招呼她,也没有人顾得上给她作晚饭。唯一能点缀她生活的是斜斜挂在天中的那轮月牙儿。她倚着那间小屋的门垛。或者独自在台阶上,“看着月牙儿”,那轮带着“寒气”的月牙儿,它“那一点点微弱的浅金光儿”照着她的脸,照着她的泪。月牙儿成了她的伙伴,伴着她给爸爸送殡,清泄她从当铺高长柜台回来的疲乏,并且也教会她可怜那整日给人洗衣的妈妈。当妈妈下了狠心带着女儿改嫁时,也正是那月牙儿像个“要闭上的一道大眼缝”,把轿子送进了小巷。月牙儿呵,你是那样的令人想到生活中还有着希望,“那一点点光,那一点寒气”,老在她的心中, “比什么都亮,那清凉,像块玉似的,有时候想起来仿佛能用手摸到似的”。
奇怪的是,随母亲改嫁后的三、四年间,她竟“想不起曾经看见过月牙儿”。她有了自己的“小屋”,白白的墙,还有条长桌,一把椅子,被子也比从前的厚实暖和了; “妈妈也渐渐胖了点,脸上有了红色,手上的那层鳞也慢慢掉尽”,她好久没去当当了,“新爸”叫她去上学,有时候还会跟她玩一会儿。有了活气的生活使她想不起月牙儿,月牙儿那“一点点”的希望,在十岁的孩子心目中实在太不令人舒心快意了。
犹如天际中月牙儿的出没不居,过了一段安稳日子后,新爸不明不白地“出走”了,妈妈又叫她去当当了。没有维持多少日子,妈妈再无求生的门径,不得不被迫走入“暗门子”。中天的月牙儿又敏感地钻出了云层, “无倚无靠的在灰蓝的天上挂着,光儿微弱,不大会儿便被黑暗包住”。妈妈的屋里常有男人来,嫖客的眼却像狗似地看着更年轻的女儿,“舌头吐着,垂着涎”。于是,她慢慢地学会了“恨妈妈”,她得保护自己,同时这又使她特别的难过,严酷的生活时时会使她“原谅”妈妈。当仅仅在她的同学中听到女子的“卖肉”这类事时,她还不大懂,而她在她妈妈的“打扮”和“戴花”中得到了最初的教育。她的心是苦楚的,一如在黑暗中悸动着的月牙儿。
妈妈要求她的“帮助”,因为妈妈的身心和肉体来不及伺候许多男人了。但是,她是矜持的,她能原谅妈妈,而压根儿相信自己应该卫护自己,有时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是有力量做到的。正在妈妈从伺候许多男人走向“专伺候”一个馒头铺掌柜的当儿,她住进了学校,得到了校长慈心的关照。尽管日子是难挨的,无穷尽的对于妈妈的思念使她很少觉得有希望,然而少女的青春使她又“自傲”着,因为她出落成“一朵娇嫩的花”了。由于校长的离职,她又得出去找事了。 “不找妈妈,不依赖任何人,我要自己挣饭吃”——她是有志气的,但结果却粉碎了她的希望, “走了整整两天,抱着希望出去,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这当儿,她才真正明白了妈妈,真正原谅了妈妈, “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想到自己“年轻”, “好看”,想到要活下去,她差不多决定什么都肯干了。久违的月牙儿,带着它春天的“清亮而温柔”又来到了她的眼前,而她心里说: “这个月牙是希望的开始。”
她开始放松自己,尝试着新的生活。一个少年的男子向她走来,他是那么温和可爱,他老是笑着, “笑脸好像笑到”人的心里。作家用散文一样优美的文字叙述着女主人公的心绪,随着她的诉说,我们看到——“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从他的头发上我看着那也在微笑的月牙。春风像醉了,吹破了春云,露出月牙与一两对儿春星……河岸上。……我听着水流,……什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然后放出一些香味,像花蕊顶破了花瓣。我忘了自己,我没了自己,像化在了那点春风与月的微光中”。然而,女人的“卖肉”毕竟没有如许的诗意,几乎就在这第一次,她忽然发觉月儿被云掩住,她“失去那个月牙儿,也失去了自己”,她和她的妈妈一样了!
于是,她开始了没有月牙儿的生活了。说她和她的妈妈一样,但是她的实际遭遇却比妈妈又多了一层精神挣扎的痛苦。她被那个老笑的少年男子欺骗玩弄后,少女特有的羞耻心使她做过拚死的抵抗,她不愿做出格的女招待,她甚至恨那些专打女人主意的男人。不过,她见不到月牙儿,早知道没有希望,她的命运远不在自己手中,饥饿的煎熬和社会的种种胁迫,还是把她整个儿地推上了母亲走过的那条路。 “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文明的男人买她,粗野的男人买她,鼻子上出着汗的中学生由她喂,那些想在死前买些快乐的老头也由她喂。当母亲最终又被馒头铺掌柜遗弃,找到女儿的时候,小说这样写道: “她找到了女儿,女儿已经是个暗娼!她养活我(指女儿)的时候,她得那样;现在轮到我养着她了,我得那样!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她是拿着“十年当一年活着”,染上了性病, “干了二、三年”, “皮肤粗糙了”, “嘴唇老是焦的”, “眼睛里老灰不溜的带着血丝”,过去被人称为“小鸟依人”不再有了,她“得和野鸡学”了。
当她再次见到那轮挂在中天的月牙时,她已在监狱中。她由于不服“感化”教育,竟然向检阅的大官儿吐唾沫。她,一个卑微的被摧残的灵魂,最终发出了她愤怒的抗争。
《月牙儿》中的这位女主人公,作为旧中国备受蹂躏的妇女典型,如同在黑暗中颤栗和 的月牙儿,作家是怀着深沉的悲哀,代她们“伸冤诉苦”,笔锋所向是造成这批苦人儿的私有制社会。
女主人公的命运变迁是作家倾力的所在。母亲的两次改嫁在作品的结构中成为相当有意味的情节:第一次改嫁后,母亲卖*;第二次改嫁,女儿卖*。整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月牙儿,凝聚着人的巨量的同情,它的出没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它有着双重的意义,既是女主人公凄苦命运的见证,同时又多少寄托着女主人公的希望。
我们说过,女主人公较之她的母亲有更深一层的精神苦痛,小说结尾月牙儿的复出,自然有着回叙方式的方便,同时也是女儿不同于母亲的地方。作家充满人道精神的平民立场决定了他的全部同情所包含的新内容:借着月牙儿的象征意蕴,作家瞩望着女主人公新的求生意志的萌生,尽管他也感到渺茫,但多少有着某种对于未来的期待。
老舍笔下月牙儿的特点是斜挂在夜空中带着寒气,总是残损的,带着微弱的光,周遭永是暗夜,伴随着主人公的遭遇时隐时现,以象征的手法谱写了一个女人悲剧的一生。
老舍先生的中篇小说《月牙儿》,却以高悬在空中的月牙儿为线索,通过主人公韩月容不同时期观看月牙儿的不同感受,讲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命运,谱写了一曲凄美哀怨的悲歌。文笔清新自然,内涵却无比厚重深刻,算得上老舍先生作品中的一个“另类”。
在小说的开篇,作者用散文诗化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凄清冷艳的画面。暗夜寂寂,一钩浅金色的月牙儿悬在天边,饱经风霜的女子在狱中,孤伶伶地望着那一点透着寒气的光。湿漉漉的回忆,从心底涌上来,很轻易便抓住了读者的心,与主人公一起开启这段回忆之旅。
老舍写作
小说以月牙儿为题,在整篇小说中,月牙儿这一意象出现了十多次,可以说伴随了主人公韩月容的一生。在小说中,月牙儿已不再仅仅是自然中的事物。更像是主人公在孤独寂寞时唯一的伴侣,它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孤独着韩月容的孤独,感伤着韩月容的感伤,见证着韩月容的心路历程,是主人公情感宣泄的一个窗口。
月牙儿
在饥寒交迫父亲去世时,是月牙儿伴着月容;在妈妈改嫁的时候,是月牙儿伴着月容;在新爸爸去世后,是月牙儿伴着月容。乃至后来许多孤独而迷茫的时候,都是月牙儿在伴着月容,悲凉的,喜悦的,凄清的,都是月容情感的外在展现。此时,月容已经与月牙儿融为一体了。
残缺的人生——浅评《月牙儿》一轮月牙儿,带着点寒气,以微弱的光亮照着大地。它的软光儿清亮纯净,但只要一片云飘来,便能笼罩住它的光芒,让世界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这便是老舍的《月牙儿》,在月光般的诗意语言中,渗透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小说用一个少女的回忆讲述了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苦楚生涯,“我”幼年丧父,安葬父亲和随母亲上坟的时候,月牙儿都带着寒气挂在天际。母亲在贫困得折磨下不得已再嫁,过了一段安稳日子后,继父却又无端失踪,母亲走上了做暗娼得道路,当母亲与我分离后,我经历了一连串的失意——失业、被人完弄、沦为暗娼,月牙儿蒙受了一层乌云,“我”终于理解母亲别无选择的困境,当母女团圆的时候,我已经重蹈母亲的覆辙,为了生存下去而出卖自己的肉身,最后被捕入狱。小说用舒缓从容的笔调,刻画了“我”一步步走向坠落的经过。这种坠落背后有一只黑手推着,而我全是茫然无措。虽然继父的出现与青年的出现让我暂时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但这宛若是月牙儿的光芒,一会儿就消失了。在她关进监狱以后,发现“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多少”,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简直就是监狱的缩影,黑暗阴冷,令人窒息。在这里,“月牙儿”代表着一种残缺,它是“月牙儿”是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诗意象征:首先是社会的残缺,正是整个旧世界把母女逼上了绝路,社会中缺乏良好的秩序,只有钱、权、肉的赤裸裸的交易。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如我一样的花般的少女成为暗娼。胖校长虽然大度地容留了我,但是也给不了我钱。甚至有的嫖客手里就攥着一块钱,唯恐上了当。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极端的贫苦之中,这个时候钱成了财富的象征,成了沙漠中的水,对于“钱”与“人”的关系,“我”认识得很透——“钱比人更利害一些,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其次,社会的残缺引起人性的残缺,人性变成了兽性,真善美一步步地走向泯灭。岁月磨去了“我”的天真,“悟”出了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做的事。一个少女竟然对爱情都失去一份天真,那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母亲不择手段地挣钱,不择手段地抢嫖客的钱,因为她觉得她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啊,连肚子都顾不了,哪里有工夫去顾什么善呢?至于美,我和母亲青春的容颜,便一点一滴地消磨在生活的折磨中。“我的皮肤粗糙了,我的嘴唇老是焦的,我的眼睛里老是灰漉漉地带着血丝。”更重要的是,她们心中那份对美的追求的泯灭。母亲从每天照镜子,再嫁后还喜欢戴花,到最后的全然不顾形象,而我对于那纯洁清凉地月牙儿也很久没有看,不敢去看。人性的真善美都被社会“强大的黑手”蹂躏着,扭曲着,发出无力的呻吟与悲凉的呐喊。再次,是“爱”的缺失,就像女主人公所说的“爱死在我心里”了。她和母亲之间隔着一层用穷做成的障碍,男女之间的爱更是“织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地选择一下。”女人永远是男人附属品。至此,我也只能退缩到爱自己了——“‘我’老在我的心上,因为没有人爱我,我爱我自己,可怜我自己,鼓励我自己,责备我自己。……我身上有一点点的变化都使我害怕,使我欢喜,使我莫名其妙。我只能顾眼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如此幽幽的自伤自怜之中,也控诉着旧社会中下层人民非但生活无处容身,精神上的栖息空间更是狭小得可怜。面对人生的残缺,母女俩也不是完全地放任自流。像“我”刚开始也在寻求一份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却不得已地失业,“我”告诉自己:“我年轻,我好看,我要活着。”还有最后的“我这样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可惜的,可是它到底是个生命,我不愿撒手。……我爱活着,而不应当这样活着。我想象着一种理想的生活,象作着梦似的。”这些都是本能的对命运的反抗,对生活所抱的一种模糊的憧憬。虽然“我”已经堕落,却又始终比周围的许多人单纯善良。当青年的妻子找上门来的时候,“我”不不预备跟她发生什么冲突,很容易就离开了,甚至在青年抛弃他的妻子后还对他的妻子产生了一丝同情。由于不甘心为挣钱而讨好小饭馆的客人,“我”愤然放弃那份工作。当母亲为了钱与嫖客发生争执的时候,“我”觉得母亲那样做有点过分——“不错,既干了这个还不是为钱吗?可是干这个似乎不必骂人。”但是,这些就像那月牙儿,这点光是极其微弱的,很快就会被黑暗吞噬。当时农村经济的破产,败兵抢掠敲诈,民不聊生,月牙儿是这场人间悲剧的见证者。这不禁让人想起安徒生陆续写于1840至1855年间的小品文《月亮看见了》,那是一部以童话形式写就的散文集,通过月亮的口吻记叙了月亮每夜的见闻,通过月亮的视角写了城市角落里落魄的妓女,荒原山丘上的饮酒诗人,还有逃难的农民和绝望的小丑演员。这个世界就象月光一样冷清真实。而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个月牙儿的见证下,还有着多少如母女两人一样的人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着?月牙儿对此也只能旁观而无能为力,它的光是冷的,给不了她们温暖。它只能目睹或喟叹,或陪伴着她们,而无计可施。这种状况也是老舍当时的心态吧。老舍只是用笔去书写他们内心的挣扎和抗争,但是并无随着“潮流”为人物安排一条“革命的道路”。就像老舍说的:“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但是,艺术作品不同于宣传材料,为什么一定要它给人找到出路,或者一定要说出穷人应该造反呢?”老舍来自下层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能够比老舍更深切的体味到社会角落里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群,没有人比他更贴近下层人民的心。他的作品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对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热爱,使他的笔端迸出生命的火花,异常的灿烂。本篇没有老舍惯用的幽默,而是严肃沉痛的,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揭露和控诉。这大概是因为《月牙儿》是烈火过后的重生吧。1928年春夏之间,对于济南来说是一个累累弹痕,斑斑血迹的回忆。“五三惨案”(称“济南惨案”)在这里发生,1930年暑假,初到济南老舍,在惊讶于济南的“来自天然”的美丽与“诗境”的同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那次惨案留下地遗痕,并由此牵动了创作的欲望。这个时候,《大明湖》也就是《月牙儿》的前身,新鲜出炉了,这是老舍归国后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书写了一对母女的悲惨命运。然而,这个鲜活的“婴儿”,刚刚离开母体,就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毒火烧死了。《大明湖》被焚后,老舍十分沉痛,他写作素来没有留底稿。从记忆中抢救出来的一篇短篇《月牙儿》,使一对母女的命运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再现,故事的进展仍以爱情为联系,这里所谓的爱情并不是花前月下的那一套,而是直截了当地追求肉与钱的获得。然而,这种重新的整理毕竟已经变形,而且离开了“五三惨案”的大背景,她们的真实面目似难以复制的,随着上海“一、二八”的那场大火,全都付之一炬。但是,日本侵略者的毒火没有能够把它烧掉,由此也可以看出它顽强的生命力。似乎老舍的创作也需要这样一场火的洗礼,后来才能写出笔尖上滴出的血与泪的《骆驼祥子》等名篇。另外,因为对故事已经写过一遍,所以对情节和人物和情节也是烂熟于心,刻画人物心理十分细嫩,“我”对母亲的感情变化从敬佩,惊讶,埋怨,到理解,再到有了自己的看法。人物思想感情一步步的变化,从容不迫,舒缓玲珑,读来如饮清泉舒心宁静,又若春雨润物于无声。这是老舍唯一的一篇“以近似散文诗的笔法”写的小说,这无论对老舍,还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有益的尝试。在老舍先生诞辰105周年的时候,电视剧《月牙儿与阳光》开拍,《月牙儿》的故事也即将搬上银屏,用另外一种形式去诠释老舍先生的作品。这表明《月牙儿》是现实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有着极大的艺术空间可以让我们去挖掘。《月牙儿》对残缺人生的诠释十分独到,品读《月牙儿》眼前展开一副城市底层贫苦市民的生活图景,耳边响起一个受尽蹂躏,而又常常被忽视的群体发出的撼人心魄的呼喊和控诉,一股月光般的清冷和苍凉,直抵内心的深处。 《为奴隶的母亲》简评:春宝娘,一个具有奴隶和母亲双重身份的社会底层劳动妇女形象,带给我们的心痛、怜悯、愤慨是不可言喻的。特别是女性,和已为人母的。但是我想今天的我们再来看这篇小说,更多的已经不是对那两个丈夫(如果秀才也算的话)的谴责和对那个时代的声讨,而应该从艺术的角度来欣赏评价人物形象和它的思想价值,毕竟每部作品都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的。重要的是要知道它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会引起大家的共鸣,作品的魅力何在?只是因为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吗?只是因为说的是母亲吗?………………多读几遍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