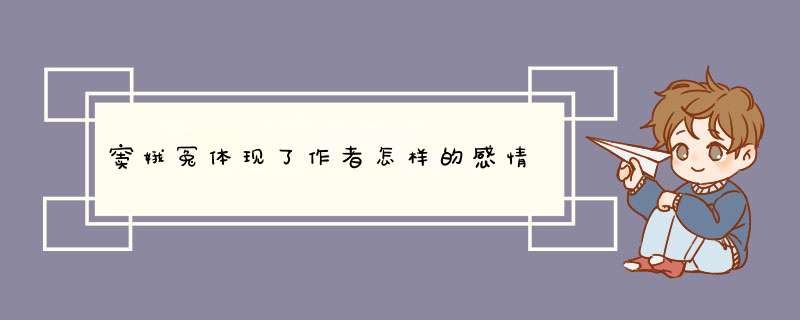
对于窦娥的三桩誓愿,常有用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手法来作解释的,这当然是对的但又可视为我国传统中“天人感应”观的一种反映《元史》中的《王恽传》和《邓文原传》都有民间有冤狱,就出现久旱不雨的记载,元人文集、奏章和笔记中有关天变与人事相应的记载不可胜数,说明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在这以前,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有一种说法:“匠夫至诚感天地,固有此理,如邹衍之说太甚只是盛夏感而寒粟则有之,理外之事则无如变夏为冬,降霜雪,则无此理”(《遗书》卷十五)窦娥所唱“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恰像是对程颐上述那番话的回答窦娥还用了“东海孝妇”的故事说明并非“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传说汉东海郡有孝妇被郡守枉判死刑,该郡大旱三年后冤狱昭雪,天立降大雨(见《汉书.于定国传》)窦娥这一愿望也得到了回答这回答不是属于事理逻辑,而是深化了的感情逻辑关汉卿的这些描写在深层意义上也已突破了“天人感应”的观点,它们为作家对黑暗势力的愤懑、抗议所充实,成为强烈的对正义呼唤的感情依托,化为一种复仇愿望的象征,一种揭露和谴责的深深力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窦娥誓愿六月飞雪,不仅要求证明她的冤屈,还要求“免着我尸骸现”,白雪葬身,胜过埋在古陌荒阡,这同不要血洒红尘一样,表明了对那个污浊社会的最后决裂,也表现了她的品格的高洁
读《窦娥冤》[滚绣球],耳畔响一曲回肠荡气的悲歌,心中烙一个敢于反抗的形象。读《窦娥冤》[滚绣球],更读关汉卿,窦娥唱出的悲苦辛酸,更是汉卿心底的柔肠婉转。
读《窦娥冤》的[滚绣球],一读窦娥冲天之冤。她三岁亡母失母爱,七岁抵债做媳妇,成婚两年又亡夫。后又有张驴儿父子招亲的煎迫,公公死后的含冤认罪,被定成死罪。将赴刑场处斩时刻,她所受苦难,所遭痛楚,一定了然于胸;悲愤情怀,不平念头,肯定块积在心,有激愤之词,自在情理之中:她呈冤屈,说无辜,直接控诉没有正义的天和地。关汉卿抓住主人公激愤难平的这个契机,大做文章,借窦娥唱出[端正好]、[滚绣球]等曲词,确实让人心生感叹。
读《窦娥冤》的[滚绣球],二悟窦娥道怨之妙。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是说现实有其固有秩序,人们的命运掌握在天地秩序之中。下面“天地也!”一声浩叹,蕴蓄无限感慨:有愤激和委屈,有埋怨和抗争,更有指责和期待。下一句“只合”“可怎生”是对天地强烈的质问:主宰万物、维持秩序的统治者——本应公正无私地廓清世界,却为何是非不分、曲直不明?“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铿锵直指现实的不公:坏人得志,好人受欺,这与应有的公理形成鲜明对比。“天地也!作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这句指责,对天地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做了深刻颠覆。接下来,悲愤之极的窦娥,便直接指责和痛斥代替上天来行使统治权的“天子”:“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末句“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是愤怒致极后的转折,是悲愤到底的叹息。在句式上,全用口语,既贴近老百姓的语言,又自然流畅,气势充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一曲[滚绣球],巧妙道出窦娥深深怨,可以让人感叹千年。
读《窦娥冤》的[滚绣球],三窥汉卿胸中之悲。窦娥一曲[滚绣球],把所受冤屈之由直接归结到了天的身上,把控诉矛头直指统治者所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端倪,这也是关汉卿借窦娥之口抒一己之愤的载体。《析津志·名宦传》中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而他却饱受不公平社会的磨砺,怎么会不于心底郁积悲愤?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借窦娥一张嘴,唱自己无限悲,传百姓长久愿,自然会传盛不衰 。
一、元杂剧之形:四折一楔子的戏剧组织结构与主唱、宾白相结合的表演艺术
《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共四折一楔子。课文节选的是楔子和前三折。楔子置于剧首,通过蔡婆、窦天章的念白与对话介绍剧情,交代故事缘由。第一折由窦娥内心独白式的唱词交代窦娥被父亲送入蔡婆家做童养媳,直至丈夫死去的情节及窦娥内心的悲苦。中间穿插赛卢医与蔡婆以及张驴儿父子的宾白,交代了蔡婆要账未果反遭赛卢医陷害,被张驴儿父子救下后,又遭张驴儿父子逼婚的情节。第二折则写张驴儿逼迫窦娥不成,反而药死自己父亲,却将窦娥告上法庭,贪官居然颠倒黑白,将窦娥屈打成招,判了死刑。第三折写窦娥在刑场发下三桩誓愿后引颈受戮。以上三折为课本节选部分。第四折的主要内容是:窦娥鬼魂向已经做了肃政廉访使的父亲窦天章托梦、诉冤,使其千古奇冤得以洗雪。
该剧所采用的四折一楔子的形式,是元杂剧结构组织的基本形式。现存元杂剧中,大多是四折一楔子这种体制,在四折之内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可有所突破与发展。所谓折,“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也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它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每一折大都包括了较多的场次,为演员的活动留下了广阔的天地,也给观众提供了想象的余地”。〔1〕四折的形式是为了适应戏剧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任何一个戏剧故事一般都有起、承、转、合(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环节。楔子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似现代戏剧的序幕和过场,起交代剧情、衔接上下场的作用。楔子一般都不长,简明扼要,能够说明故事情节。如果没有楔子,只是一段一段地唱,会让观众理不清头绪。楔子在剧本中的位置极为灵活,虽大多数放在第一折前,但放于其他两折之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总的说来,四折一楔子是元杂剧的基本形式,但根据戏剧的发展和表现内容的需要,也会有变体形式。
《窦娥冤》也集中体现了元杂剧的表演艺术。元杂剧表演由唱、云、科组成,《窦娥冤》中综合运用了这三种表演艺术形式。唱,顾名思义指歌唱,元杂剧比较特殊之处在于一般由一个主角儿从头唱到尾,当然也有约占1/3的剧目则是角色不变,主唱人物可换,这叫做改扮或倒扮。一人主唱可以集中力量刻画主要人物,使之形象鲜明。《窦娥冤》就是由表演窦娥的演员主唱,因此,也可以称《窦娥冤》是旦角儿戏。云即宾白,由于元杂剧以唱为主,那么白自然为宾,故也称宾白。宾白多语言质朴,重在叙事。科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相见、作揖、进拜、舞蹈、坐跪之类,身之所行,皆谓之科”。〔2〕简单说,科就是指演员的舞台动作,基本上通过多种多样的身段动作,虚拟地反映生活,同时又具备一定的程式性,尽管元杂剧的科还不够完善,但它为中国戏曲别具一格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
《窦娥冤》较为典型地采用了元杂剧主唱与宾白相结合的表演形式,即一人主唱,旁人宾白。主唱人用不同宫调表现不同的情感内容。从课本选用的三折剧本来看,基本上都是由窦娥主唱,唱词以抒情为主,兼以叙事。其他角色则主要用宾白来叙事。《窦娥冤》中的配角多利用宾白插科打诨或讲陈叙事,比如剧中人物(特别是反面人物)的上场诗。赛卢医的上场诗“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个欺世盗名的假神医形象。而贪官楚州太守桃杌的上场诗则是“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二、元杂剧之神: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强烈的抒情性以及大团圆收煞
《窦娥冤》之所以成为元杂剧代表作,不仅是因为其形式,更主要的是它体现了元杂剧的精神实质。
首先,《窦娥冤》体现了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元杂剧中有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社会剧。关汉卿的多数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窦娥冤》尤其突出。该剧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集中书写了窦娥的反抗和悲剧,是对黑暗势力的血泪控诉。其中,最为精彩的高潮段落是:“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经典的唱段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
其次,该剧体现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特点——抒情性。中国戏剧因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又称为戏曲。正如王国维所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3〕以歌舞演故事正是中国戏剧的民族特点。这一点体现在戏剧中,造就了中国戏曲抒情性这一显著特征,元杂剧尤为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征。元代文人创作的杂剧感情强烈、层次丰富、抒情性特征极为明显,某些大段的念白或唱词,将创作者内心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比如《窦娥冤》中著名的几段唱词: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煞尾……直等待雪飞六月,亢旱三年呵,(唱)那其间才把你个屈死的冤魂这窦娥显。
从这些激昂悲怆的唱词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创作者内心的激情。
由此看出,即使在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著称的《窦娥冤》中,仍然充满了诗化的抒情情怀。而且结尾窦娥的三桩誓愿赋予了该剧浪漫主义色彩。
最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境界——大团圆收煞。结尾是戏剧情节结构的主要要素之一,戏剧的完整性正在于此。元杂剧,尤其是大都杂剧多以大团圆收煞。《窦娥冤》的团圆结局,虽体现了善恶有报的道德准则,却难免有牵强之感,主观色彩浓厚。《窦娥冤》被王国维誉为一个“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4〕的大悲剧。通过这部戏剧,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无赖游民横行,欺骗打劫等案件盛行,昏官当道,只认钱财,混淆黑白。该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其结尾,却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窦娥鬼魂向已经做了肃政廉访使的窦天章托梦、诉冤,最后平反昭雪。
之所以采用这种具有幻想性质的浪漫主义结尾,无外乎是要追求大团圆结局。这种外在的团圆式的戏剧结构,隐含着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乐观的审美心理。正如王国维所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5〕典型的大团圆式结局比如: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才子佳人式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有阖家团聚、子孙满堂、物阜财茂等。只要我们对古典戏曲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大团圆结局在经典戏曲中比比皆是。
团圆收煞,一方面体现了民族审美理想,同时也体现了受众的需要。我们知道元杂剧是舞台艺术,我们从课本中看到的仅仅是剧本,而元杂剧则是活生生的表演艺术。剧本只是创作的一个方面,只有加上演员的表演,一出元杂剧才算完整。既然是舞台表演,自然要考虑观众的口味与情感接受程度,特别是当时的元杂剧作家与表演者还是靠演出维持生存,如何满足观众的口味,从而提高收入,是元杂剧创作者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不管剧情有多么曲折,结尾都应该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窦娥的滔天冤情最后也终于得以申雪。
表现了窦娥善良、孝顺、安分守己的性格特点。
《窦娥冤》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杂剧代表作,也是元杂剧悲剧的典范,该剧剧情取材自东汉"东海孝妇"的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位穷书生窦天章为还高利贷将女儿窦娥抵给蔡婆婆做童养媳,不出两年窦娥的夫君早死。张驴儿要蔡婆婆将窦娥许配给他不成,将毒药下在汤中要毒死蔡婆婆结果误毒死了其父。张驴儿反而诬告窦娥毒死了其父,昏官桃杌最后做成冤案将窦娥处斩,窦娥临终发下"血染白绫、天降大雪、大旱三年"的誓愿。窦天章最后科场中第荣任高官,回到楚州听闻此事,最后为窦娥平反昭雪。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