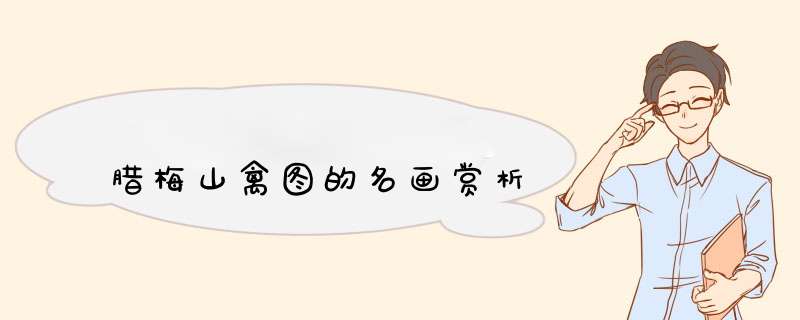
视之所画,唯有双白头翁栖于寒枝,下有二草本,未有他物。时值腊月,而鸟何为白头?
观徽宗题左下五言绝句,“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约者,丹青也,亦知己也。千秋之白头,不畏风雪,愿得相伴相守。而花靓妆淡景,秀而不媚,清而不寒。
而其笔法,全应物而生,未有张示。线笔笔精勾,羽片片细染,其虽写实而不失灵逸,而鸟之神岁经千年而不改。
为得物之神秀,传徽宗以生漆点睛。沉丹青者,徽宗也;全其愿者,丹青也。
今此画为台北故宫所得,至今保藏。
题字出自《腊梅山禽图》。在《腊梅山禽图》中,宋徽宗自题“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一诗”,借双关语意,表述自己作这幅《腊梅山禽图》构思立意的初衷。
由于画作中无法表现出“鸟语”的声音,亦无法描绘“鸟语”的内容,因此用“矜逸态”的诗句,将白头翁自鸣得意的神态描绘出来,使观画者彷佛听到了它吱吱喳喳的鸣叫声。而下一句的“弄”字,则在腊梅花绽,粉蕊呈露的姿态之外,带出了“花香”。
下半首诗由“白头翁”联想到古语“白头同所归”,意指朋友间情谊坚贞,白头不渝;而“丹青”是古代绘画中常用的颜色,其话色不易泯减,故以此二句喻友谊坚贞,指著白头翁,表白千年不变的心意
宋徽宗在绘制这幅作品内心充满了希望、理想、爱情与富贵,一种美丽幻想的宁静安闲绘画王国,不经意地浮现在笔意之中。他借腊梅、白头鸟(长春鸟)、山花、蜜蜂等动植物来描写情感和生命的关系。用寒冬季节的植物来诉说生命的坚定,把人们日常生活里,眼中最常见最熟悉的鸟类呈现在画里,借禽鸟之情来表明人间友情和爱情的坚贞。
暗香浮动月黄昏
当我带着一种尝试的心情翻开那本曾被朱光潜先生称为“是在世界范围里已受到热烈欢迎的一部作品”,被美国学者金介甫盛赞为“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精巧的《边城》时,我的心情是怎样为这位在文学史上几度沉浮、几度受人非议的作家所描绘的一切而感动。于是在这种激情的诱发下,不禁斗胆提起笔来,谈谈我的一点感受。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不想再在沈从文是不是一个自觉的民主主义者、是不是把他的创作和时政紧密相连而达到“文以载道”的效果等问题上纠缠不清。我想说的只是作为理想主义者、作为抒情小说家的沈先生笔下描绘出的那种从容不迫的韵味和平静舒缓的格调;那种将诗和散文相融合,用亲切素淡的语言塑造的或者讲述人生的善恶与悲欢,或者歌唱生命与人性的艺术境界;那份无处不显示作者的聪灵雅静而又暗藏苦闷、孤寂灵魂的和谐。记得冰心曾说过: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而作为青少年时代在湘西特殊历史环境下生长并且有士兵生涯的沈从文,正是将自己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亲身经历到的一切叙述于笔端。在我们眼前展现一幅幅宁静淳朴的田园诗般的湘西人民风情画,同时又寄托了他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各得其乐的人生理想。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主要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的,是“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 在其代表作《边城》中,作者娓娓道出湘西的边境“茶峒”的住户——“老人、女孩子、黄狗”与“傩送、顺顺、天保”等人之间的故事,充分展示了湘西的古老民俗与人物的善良心地。无论是植根于当地悠远历史土壤里的“爷爷”那种自甘贫苦而生性达观、洞悉世情而信守天命的善良,还是在古老传统里出新枝、尚未沾染世俗尘埃的“翠翠”“傩送”那种初涉人世而摒弃旧俗、虽历风雨而其志不渝的聪慧,作者无不凭着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力,捕捉最能传神的自然景物于一体,达到自然与人性美的映照,并使自然景物的描写成为人物情绪的延伸和扩散。如成为大人的“翠翠”会在黄昏来时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而感到凄凉,从而萌生“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的意念。既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又暗示出人对自己命运自主把握的主题。说起《边城》的人性美、人情美,首先体现在翠翠身上。作者所着重表现的是翠翠的品性美、童贞美和爱情美。他笔下的翠翠,与青山绿水作伴,心灵上没沾染一丝尘埃。她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嫩,就如湛蓝的天空下刚长上青枝翠叶的嫩竹,而她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爱美,则更是真切感人。从课本所节选小说的13、14、15章来看,翠翠对“爱”的到来是怀着既向往又担忧的复杂心理的。当夜幕降临,祖父仍“忙个不息”时,她心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她“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她担心在这个“规矩”中听歌的日子过去了,顿生“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的念头。而这正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理最细致入微的生动写照,洋溢着爱和美的柔情蜜意。包括祖父试探地问她“你试告我,愿意哪一个”时,她立刻娇嗔地把话题岔开,掩饰内心的真情,无一不包含一个初涉爱河的少女的羞涩。当翠翠想到自己走后,爷爷的孤独、凄苦、伤心与焦虑时,她又不免担忧起来。于是认真地说:“爷爷,我一定不走……”这是怎样一幅充满祖孙之爱的人间情画啊。作者用其清新细腻的笔触,生动地写出了湘西淳朴的社会风气。这种处处洋溢的自然、纯洁、真挚的人性美,同样体现在天保兄弟身上。作者既写出了他俩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爱翠翠,都是以感情为重的。在他们心目中,爱之所在,与世俗的钱财、地位毫不相干,甚至头脑里没有这些概念。他们慎重选择爱人,但在自己的幸福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又能忍痛割爱,成人之美。正如小说所写:“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爱情本身有“排他性”,按茶峒的习俗也是不兴“情人奉让”的,但他们却都以互助互爱的德性,以一种作者所理想的优美健康而自然的“人生形式”,演绎出一曲平凡而崇高的爱情之歌,不能不让人为之动情。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曾这样写道:“我除了用文学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着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他这样说了,他也努力这样做了,很有闭门编织理想梦、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味道。他的确为自己造了座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块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纤巧,是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就是沈从文这位多产作家的所有作品中始终蕴涵的主题。不重在骂谁讽谁,不在模仿谁,不过是一种属于精神方面而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情绪的体操”。他的对农人和士兵的温情,他的对健壮、勤劳、诚实、善良、充满生机、具有各种人类美质的理想人的热爱,他的对勇敢、天真、爱美等人性美的讴歌,无不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他文字的海洋中汩汩涌出。说他的作品带给人的是“暗香”,也正是因为他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风格而独具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清新的故事中蕴藏的热情,朴实的文字中说隐伏的悲痛。时而含隐深沉,诉说着人世的悲凉与不平;时而慷慨欢悦,歌唱着生命和人性、风俗和人情,最终共同交织成理想的独具一格的乐章。这便是我眼中的沈从文,纯洁如天使,质朴像脱俗的“翠翠”“天保”“傩送”……就是活脱脱的跳跃在他笔下的人物——美丽如传说,神奇似仙境。而沈从文呢?却退隐在人物事件背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会在他们的演变之中。他没有作为革命者和诗人的郭沫若作品中那种直抒胸臆的强烈燃烧的感情,更没有作为思想家和斗士的鲁迅作品中反映国民灵魂的精深透彻,他只是怀抱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温暖的情感,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用人心人事作曲歌咏出别样的情致和韵味,以其缠绵委婉的曲调轻轻叩击你的心扉;又描绘出一个个动人的情境,产生滋润心田的诗的意境、诗的情绪、诗的韵律。“在乡下住,黄昏时独自到后山高处去,望天空云影,由紫转黑。天空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色,夜尚未来。远望滇池,一片薄烟,令人十分感动。”作家在《长庚》中曾这样感叹。而此刻让我感动的却是幻想中的黄昏,我仿佛看到一枝驿外独放的腊梅,在朦胧的月色下微微浮动,暗香袭人……
暗香浮动月黄昏
⊙ 广东省深圳红岭中学 马佳妮
(一)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卜算子•咏梅》陆游
驿外断桥,疏影横斜。兀自开放,兀自凋零。此恨何人省?白梅之恨,亦是放翁之恨。青山外,是子规泣血的啼鸣。
曲终人散,满腔愁苦凝结为一脉清香——冷冷的,缘自孤独的花朵;淡淡的,弥散于黄昏的风雨;暗暗的,浸润在子夜的月光里。这香气自屈平的太古吹来,冠绝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胸臆,为他们流动的文辞注入似有还无的灵气,为他们微薄的身躯笼上清雅高洁的气质。
“香”这一意象多见于咏花诗词,且常用于传达花的神韵和品性。香气于此已不再是风中无形的分子,它可嗅,可见,可听。它是勾连花与人的暗线,是无觅佳人残存的一丝踪迹,一缕余音。香远益清,婷婷净植,是遗世独立的君子,清净的馨香由心生发。花香亦是人香。
书香墨香乃至酒香,填满了文人雅士的生活间隙。松花酿酒,春水煮茶,这香充盈了山间隐士的精舍;读书消得泼茶香,这香见证了才人夫妇的闲情雅致;琴棋书画诗酒花,这香是羁旅天涯的措大相识的契机。或淡或浓的香气,点缀了敏感的文人抑郁的日子,包含着他们几千年来的生活理念——诗意地栖居。苦涩的茶,泛黄的书,浓重的墨,辣口的酒,更多地象征着一种生活情趣。
古人爱熏香——趴在一个大香笼上,贪婪地抱裹住升腾起的烟雾;或在腰间系一个精巧香囊,将植物的精髓随身携带。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屈子行吟泽畔,身上佩着江蓠辟芷与秋兰,一步一叹,步步生香;三五佳节,花灯如昼,香雾扑面,混着甜美的欢愉。纤纤玉步,挪移于满布椒香的殿阁。更有佳人,冰肌玉骨,吹气如兰,体有异香,绝世独立。缥若惊鸿,留一段迷惘的香气供后人凭吊,衣香人影太匆匆。体香,亦是美人的专属。
君子如兰如玉,切磋琢磨下透出质朴的气息,燃起温暖的轻烟。空谷幽兰的绽放,等待的是以云为车以风为马翻越层崖的观众;蓝田美玉的成熟,憧憬的是漫溯河边涉水而来的伯乐。文人相逢,往往“闻香识人”。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肚中的笔墨经了多少岁月的烘焙,受了多少思想的催化,举手投足间便展露无遗。疏食饮水,曲肱而眠是他们的信仰;三顾茅庐,虚席受教是他们的梦想。君子之香,是脱俗的气质,宛如香水的后调,温婉蕴藉,微弱而不散,平凡却耐人回味。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禅宗是佛教在中国的土壤上开出的绮丽花朵,是一个香气四溢的世界。夜来风起满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树。顺从香气的指引,回归生命之本真吧。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孟浩然、王摩诘、青莲居士,他们将己身化作白莲,献于释迦光辉的足底。被尘埃荫蔽的心灵,归于澄澈空灵。
撷取一个“香”字,探寻中国文人的心灵世界,一段段风景在我眼前铺开。点数一番,那“香”总是藏而不露,却暗地里勾人心神;那香总是淡极,仿佛香气的主人为了躲避喧嚣而隐遁到了某处;那香总是冷色,透着清雅同样透着孤绝;那香总和高士妙人相伴,而极少停驻于短褐黔首的身畔。像煞了中国文人。或者说,这香那香,是他们内心的表达。
中国文人于笔者看来是一个矛盾的词,可爱可气可笑亦可叹。明明干禄心切却偏言舟楫,明明穷途末路却穷酸嘴硬,明明被世界遗弃却要说是我遗弃了世界,明明皇帝都降了却还要顽抗到底。殊不知阳春白雪必然曲高和寡。情疏迹远的乖僻,茶熟香温的自适,木兰舟上的清泪,辛夷花下的眷恋,隐藏着一种病态的自命清高和孤芳自赏,流传到孔乙己的嘴边,俨然成了落魄。看客的笑声渐远,只剩下死一般的沉默。
夫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窘迫如此,子贡的质问被他一句“君子固穷” 淡定地化解,却化不开千年后的我心头的郁结。既然我们都微妙如芥子短暂如浮游,何必执著于那不可为?既然个体于体制正如蛋之于高墙,何必争先恐后地受那炮烙热瓮?文天祥、于谦、方孝孺、东林党人,他们留给我的是一串串问号。夫子,天地太大,我对它没有概念。
(二)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苏轼前文提到的香在诗文中被具体化、多元化,读者的各种感官被充分调动起来,切实地感受到这看似难以言说的无形之物。而在画作中,高明的画家则采用诸如晕染、留白的技巧,甚至蜂蝶飞舞的暗示,辅以清净淡雅的设色,达到人立于画前,而感花香拂面的境界。赵佶《腊梅山禽图》有“朱栏白雪夜香浮”之味暗香浮动月黄昏
《腊梅山禽图》是画家赵佶所创作的一幅画,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宋徽宗在绘制这幅作品内心充满了希望、理想、爱情与富贵,一种美丽幻想的宁静安闲绘画王国,不经意地浮现在笔意之中。他借腊梅、白头鸟(长春鸟)、山花、蜜蜂等动植物来描写情感和生命的关系。用寒冬季节的植物来诉说生命的坚定,把人们日常生活里,眼中最常见最熟悉的鸟类呈现在画里,借禽鸟之情来表明人间友情和爱情的坚贞。
“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是令人低回不已的诗句,似是话外有话:谁有这千秋丹青约?不是那对比翼鸟儿,却该是这执笔的人吧。
这是出自宋代画家赵佶画作《腊梅山禽图》上的一首题诗,:“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译文为:这一对白头翁立于这丹青笔墨的虚空中,没有风,没有阴影,没有俗世喧嚣、红尘侵染,一千年恩爱如初,一千年只不过黯淡些羽毛上的墨色,艺术比生命更长久。
创作背景
北宋时期,其社会经济形态的繁荣推动了绘画创作的发展,尤其是现实主义的写实绘画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绘画是用极端的写实主义倾向来表达这种科学的探寻精神的,这一时期的画家可说是最为忠实的自然观察者。
作者赵佶就是宋代绘画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代表和潮流推动者之一。而他的花鸟画历来被公认为成就最高,作品也最多。风格多样,既有精巧入微、秀丽华美的细笔重彩,也有质朴豪放、野逸天趣的墨花墨禽。《腊梅山禽图》即是其花鸟画传世代表作品之一。
另外,《腊梅山禽图》亦有说非赵佶所作。如,现代书画鉴定家徐邦达认为:此幅作品同大多数《宣和睿览册》收入的作品一致,为画院画家代笔之作,虽然上有徽宗题诗,但与真迹与否无关。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