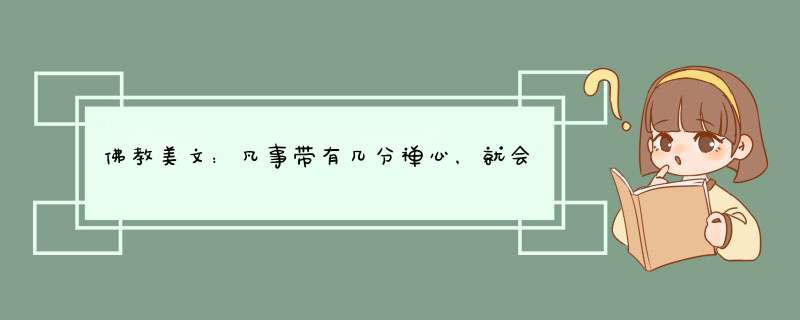
禅心是禅门常用的谜样字眼之一,他们用这个字眼来提醒弟子们跳出文字障碍,刺激弟子对自己的心和自身的存在产生惊奇。这也是所有禅训练的目的——让你产生惊奇,迫使你用你本性中最深邃的表现来回应此一惊奇。
我们谈“大心”、“小心”、“佛心”,以及“禅心”,这些用语都有其意义,但它们的意义不应该以经验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谈到开悟的经验,而这种经验与一般意义的经验不同,它不被善与恶、时间与空间、过去与未来这些范畴所囿限。开悟是一种超越二分法的经验或意识。
真心就是一个观看的心,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自我、我的小心或者有限的心,那才是大心。”你这是画地自限,是把自己的真心给窄化、客体化了。达摩说过:“想要看到鱼,你必须观看水。”事实上,当你观看水的时候,就会看到真正的鱼。要看到佛性以前,你就要去观看你的心。观看水,则真性自在其中,真实本性就是那被观看的水。当你会说“我坐禅坐得很差”这样的话时,表示佛性已在你之中,只是你没察觉罢了,你刻意去忽视它。
你观看自己的心时,“我”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的。但那个“我”不是“大我”,而是这个总是动个不停的“我”。这个“我”总是在水中游,也总是振翅飞过浩瀚的天空。我所谓的“翅”是指思想与活动,浩瀚的天空就是家,是“我”的家,既没有鸟儿也没有空气。当鱼儿游泳时,鱼儿与水都是鱼儿,除鱼儿之外,别无一物。
禅”并不是只为那些懂得盘腿打坐和有极大慧根的人而设立的,人人皆有佛性,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出某种方式体现自身的佛性。修行正是为了直接体验人人皆有的佛性,你做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对佛性的直接体验。佛性就是指“觉知佛性”。你的努力应该延伸到拯救世间所有的众生。
修禅修心,倘若自己心中对禅理一知半解,只凭嘴上空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禅机的参悟需要一颗玲珑的禅心,与佛学融为一体。
有一天,奕尚禅师从禅定中起来时,刚好传来阵阵悠扬的钟声,禅师特别专注地竖起心耳聆听,待钟声一停,忍不住召唤侍者询问道:“早晨敲钟的人是谁?”
侍者回答道:“是一个新来参学的沙弥。”
于是奕尚禅师就让侍者将这沙弥叫来,问道:“你今天早晨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敲钟呢?”
沙弥不知禅师为什么要这么问他,他回答道:“没有什么特别心情,只为敲钟而敲钟而已。”
奕尚禅师道:“不见得吧?你在敲钟时,心里一定念着些什么?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声,是非常高贵响亮的声音,那是正心诚意的人,才会发出这种声音。”
沙弥想了又想,然后说道:“报告禅师!其实也没有刻意念着,只是我尚未出家参学时,家师时常告诫我,敲钟的时候,应该要想到钟即是佛,必须要虔诚,只有敬钟如佛,才配去敲钟。”
奕尚禅师听了非常满意,再三提醒道:“往后处理事务时,不可以忘记,都要保有今天早上敲钟的禅心,你将来必定会有所作为。”
这位沙弥从此养成了恭谨的习惯,不但敲钟,做任何事,动任何念,一直记着奕尚禅师的开示,保持着敲钟的禅心,终于大彻大悟。
他就是后来有名的悟由禅师。
禅心是专心致志,是心无杂念。凡事都应带有几分禅心,即使再小的事也应如此。带着几分禅心去做事,终会有大悟有大得。
人世间的光阴岁月来去匆匆,纵使活到百年,也不过是浮云过眼。百年之中,截尾去头,便十有天大的富贵,又能享得几时?有人才大如山,过不得百岁光阴,与草木同腐。有人财源如海,更不消六七十年,只等精神一退,有钱没处使用。更何况世事无常,财多召祸,可见是件最不中用、靠不住的东西。
我们这些凡人偏偏勘不透,把人生有限的岁月,尽放在声色名利之中。一旦无常猝至,万事皆休。平时斤斤计较,逐逐以争,究竟带得一些回去不曾?
有禅心者,便在天堂,因为他们有一双勤劳的手,而无禅心又懒散者,哪怕生活条件再好,也如同身在地狱一般。太过安逸的生活,本来就是对心志的消磨,所以,不要再抱怨自己的生活太过辛苦了,正因为辛苦,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嘛!
一个人历尽艰险去寻找天堂,终于找到了。当他欣喜若狂地在天堂门口欢呼“我来到了天堂了”时,看守天堂大门的人诧异地问他:“这里就是天堂?”欢呼者大惑不解:“你难道不知道这儿就是天堂?”守门人茫然摇头:“你从哪里来?”“地狱。”守门人仍然摇头。欢呼者似有所悟,慨然嗟叹:“怪不得你不知天堂何在,原来你没有去过地狱!”
你若经历过痛苦,那么体验到幸福便是进了天堂;你若遭受过失败,那么获得成功便是进了天堂。
总之,若没有其中一样,你是断然不会拥有另一样的。
感悟:坐禅只是一种进入禅定的途径,假使只为坐禅而坐禅,即使枯坐成骨,心不曾抵达禅的深处,成佛的愿望也不过是空梦一场。禅既是一种精神上的休息,也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智慧。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佛教的修行,在于戒、定、慧。对世俗物的外在和欲望的放弃;内不动心,心念绝对止息;自发地生起,完全证悟真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修一切善而不执著所修之善,断一切恶且故不为一切恶所缚,当下这念心便是归於中道…禅开人心智、助人成长,使人感悟到世界的和谐、心境的清澈、生命的圆融……文/单眼老表
很多人忏悔时至诚心不够,没有大悲心慈悲你的冤亲债主,没有入心,就不能入理,没入理就不通,不通就不能解脱。
★为自己离苦而忏悔的就不会得利,因为真诚心不够。没有惭愧心、没有大悲心、没有从内心忏悔业障,业力不散呀!
★亲近善知识很重要,因为你没有亲近善知识,被人盲引盲导,你才迷惑颠倒。
★你起什么心、动什么念、怎样忏悔才真正了你的业?你用心造业,用嘴忏悔,入口不入心,这样不能解脱。多少人忏悔时是嘴忏心不忏,你这样忏也是枉然。
★佛讲“罪由心起将心忏”,到我们这里不要变成口号,你根本就没有入心忏悔,你怎么能离苦呢?只为离苦你才去忏悔,就不能离苦!要知罪忏悔。
★定业的确是难转,但能否消减,要看你是不是用一颗至诚的心知罪忏悔。定业虽难转也是能转的,重罪轻报也是消减。
★佛教你至心忏悔,永不复造,你要依佛所说。佛法就是宝藏,众生解脱的路在哪里?就在佛法中。佛理不通你才病苦,你才沉沦,你造作罪恶,冤亲债主都来找你,你能出轮回吗?怎么办?你要接受你的果报,认账啊!首先转念,然后经过你的忏悔、对冤亲债主做种种开示,他们才能纷纷地离去。
★“身是心的用,心是身的主。”这就是佛法里讲的唯心造。如果杀生、吃肉、造恶,不耽误修行,因果哪去了?
★怎么解脱?先从破无明开始,破无明就要懂因果。
★讲因果的目的就是教化众生明因识果、增长智慧、明辨是非,不再迷惑颠倒。只有觉悟,才能成就。
★有因就有果,清清白白,丝毫不爽。现在如果正法不能正用,众生怎么能离苦?
★想要道心不退转,不造业,唯有相信因果,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理,给你个世界你都不要了,你还会造业吗?
★为什么不能降伏其心?就是因果不明了,唯有知苦才能乐法,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是断恶的。修行也难也易,说容易就需要你懂两个字,因果。
★心外没有法,善恶由心生,想求得健康、长寿、快乐、富贵,你得修呀,一切流转的业因果报,无人抵挡得起,把握当下修自己吧!
★看破放下、持戒念佛。严持戒律,不持戒律就不能成就。何为修?持戒就是修,反观自己,忏悔自己的业障。
★拿“五戒十善”这把尺子量自己,好好看住自己,不要看别人如不如法。你总拿尺量别人,就能把别人量到西方吗?不能,量好自己是最关键的。我们拿一把戒尺量自己,从行、住、坐、卧都要表好自己的威仪。
★受戒的修行人,一定要回头拿戒律好好地量自己,哪里错了赶紧忏悔,弥补过失,当生觉悟还来得及。
★你见别人的错,就是凡夫,凡夫才能见别人的错。来一个人你就拿佛这把尺子量,能修行吗?你要观想:“他是个迷惑众生、罪苦众生,我能为他做点什么?”
★不持戒就难以修行,会障碍你的修行。不长智慧,不持戒,永远都是盲修盲练。自觉才能觉他,觉行才能圆满。
★你度人时还在颠倒,你发心时还在罪恶,这就不行,你这边授戒,那边还造业,怎么能不沉沦?
★偷盗、贪占的人赶快忏悔,还要赶快归还,因为“日涨三分、夜涨七厘”。我慈悲你,你也要慈悲你自己。罪苦的众生往往不懂得修心,不修本性。要知道你的罪业有多重,赶快的卸债吧!因为“无常”无处不在,随时随地拿走你。你贪心不断,等眼睛一闭上就来不及了。
★总观别人的错,一定是你的错,总见别人的错是没有办法修行的。观别人的错对自己的号,他的错就是你的警示灯。
★你障重业深,赶紧觉悟吧,别人没有错,正法没有错,是你的知见错了。你的知见错了一定会走错路。
★“孝养父母是天德”。修行人要拿“孝”这把尺子量自己,你对老人供养得再多,但态度不善,高声大气,语气生硬,也会和老人结怨的,这就谈不上孝顺了
★既然你受了戒,你就要持戒。如果你犯戒,在没有受戒之前打你五十大板,受戒后就要打五百大板。
★如果人们早一天能得到佛法,人间就会减少太多的灾难,国与国不战了,人与人不争了,天下就太平了,每个家庭都会幸福,每个人就不会有病苦与灾难。
★千求万求不如求你这颗心不造业,把这颗心看好,就不用担心后来的路。善恶由心生,心是罪福的种子。
★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真修的人应该少言寡语。看住你的心,护住你的口。
★说话前先要思考,此话是不是利益众生,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说就是禅。
★末法时期的人最难护的就是这张嘴,什么都敢说,修行人能护住这张嘴就很了不起了。
她总是端坐在贡桌边上,枯槁的面目看不到一丝神情,就像头上的古佛像一般,目色安详平视着远方,四下静悄悄的,只有外婆口中呢喃声和那受教的生物。 ──题记
(一)
打从我记事起,外婆就已经吃斋念佛了。不知道是真的看破红尘,还是真如她口中所说的“前世债,今生还”。总之,一切在外婆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作为一个严格的佛教信徒,外婆是不沾荤的,甚至,鸡蛋她都不曾亲手打过,每次都要假于我手。而每天早午晚三柱清香是外婆必做的功课,然后就是坐下,静伴青灯古佛,打打禅,念念经,很难想象外婆一坐就是几十年了。所以如果没什么事,外婆一定在佛堂里。以至于无论谁找外婆,外公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去佛堂看看吧,应该在那里。如若,那天外婆要是不在佛堂里,如果不是出门“做法事”,那想必就是我放假回来了。
高中生活比较忙碌,每个月的假期也被压榨的为可怜的一天半,说白了就是回去打个照面再拿点生活费,仅此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期待。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还有两个人要比我更期待这一两天,那就是外公外婆。
打小跟着他们长大,我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了在每顿饭前出门把我寻一番;习惯了我的顽劣,而不伸手打我;习惯了在我思念父母时候给我一个拥抱。上高中后见他们的机会陡然间减少了。屋子内外早已习惯了我在时候的灵动,突然间我的离去,让整间空荡荡的屋子塞满了孤独,寂寞,二老的世界也从此落寞了,没了言笑。
然而,这一切,在我回来的这两天便会一扫而空。对于二老而言,这两天更是如同过节般隆重。一大清早她就到佛堂烧完香,做完一天的祷告,然后他们就跟商量过一样,外婆生火烧水,外公到镇上的集市赶上早集买点小菜和五花肉给我准备那道米粉肉。虽然外婆家离镇上也就二里路,但是相较于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徒步走过去,抑或是一步一步艰难履至这似乎都显得有些残忍。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我了。这让现在的我多少有些愧疚的幸福。
摘菜上水,洗米,添柴生火……等忙里忙外,来回转上几个圈,就已将近正中了,饭菜都闷在锅里,灶里还零星的闪着点点火星。锅盖上冒着丝丝蒸气似乎预示着这顿菜肴,刚熟不久。特别是那道米粉肉的香味,在我离家老远的地方都能闻到。然而,在我回来之前,一切都静默着,外婆,外公端坐着在堂前,像是等待着接待一个领导,兴奋,焦急,期待……这时一切与佛无关了。等我风尘仆仆迈进家门时,外婆那仿佛仅剩一张皮的脸顿时便有了生机,颤抖着笑了,几层皱纹层叠起来如波浪一般,是那样美丽却充满着无言的心酸。我心头一紧,随后搀扶着他们入座。就这样紧凑的屋子里霎时间充满了温馨。由于外婆吃素,她不得不压抑住兴奋的心情,避开我们桌上的荤菜,独自一人就着一碗咸菜,有时候是不知道剩了几餐的一点青菜,清汤寡水,粗茶淡饭。本就不充裕的餐桌上一经我的扫荡,很快就所剩无几。更多的时候外婆只吃白饭,生怕自己的摄取会让我食不饱,当我实在看不下去时,将她仅能涉足的青菜端上她面前时,她总是一再摆手道,你吃吧,我这点咸菜就够了,你要是不回来呀,我也就懒得吃这饭了。说完顺手将盘中白菜亦或是萝卜倾到于我的碗里。不管我是否喜欢还是吃不吃的下。当然,我还是会很开心的把其当做人间美味吃下去。此时,外婆总是一脸满足的笑笑说:“这就对了,多吃点长身体。
也是我的原因,外婆这几天也就不再整日的待在佛堂里。不过每晚的功课还是像例行公事般雷打不动的。外婆家离佛堂不远,其间有一条临河的小道,有点窄,路旁杂草丛生,藤蔓遮天蔽日,阴凉的同时也充满阴森。一经下雨,路上泥泞不堪。对于老人来说也许有些危险了。所以到了晚饭时间我会顺着小道去接外婆,当然也是怕外婆一个人出什么岔子。夜里,四下无光,窄窄的小道上,一片漆黑,只有那此起彼伏的昆虫的叫声提醒着我,这还有生机。没有灯光,只有摸索着向前移动,相信外婆也应该这样走过的吧,也许更加艰难,毕竟年龄是我们之间永远的差距。
走着走着,佛堂已赫然立于眼前。那若隐若现的油灯在偌大的佛堂中显得有些昏暗,与释迦摩尼一字排开的还有好些小的佛像,观音,玉帝,王母,寿星公,弥勒佛等不计其数。外婆就在里面,念经,打坐。她总是这样端坐在贡桌边上,枯槁的面目看不到一丝神情,就像头上的古佛像一般,目色安详平视着远方。四下静悄悄的,只有外婆口中的呢喃声和那受教的生物。如若不是我的打扰,或许她的世界就剩自己和那樽佛像。我虔诚的顿了顿,怀着敬仰与忐忑走了进去。外婆见我,连忙起身,问了声,肚子饿了吧!这就回去给你做饭。来,先给菩萨磕个头,说完就拉着我东西南北,拜满了诸天神佛,生怕怠慢了某位上仙,口中还念叨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我什么也没说,权当给外婆进孝了。要知道,一个人活着的有点信仰,这与诸天神佛的存在与否毫无瓜葛。试想没有了这个信仰,恐怕外婆这点精气神,早已驾鹤西游了。
(二)
说到佛。于外婆而言,或许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这么简单了。毫不夸张的说,它给了外婆一次重生的机会。用佛教的言语说就是:“佛,成功的渡她走过了生活这条苦海。”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这个小村,或许能称得上是个安宁的桃花源。乱世之中,能求此一处,也不知道是几世能修来的福分了。外公外婆又恰好都是不折不扣的地主,乡绅家境。于是乎,古老的指腹为婚于此就是个再好不过的事。就这样,外公外婆结婚了。生活又或许太喜欢跟我们开玩笑。这段婚姻好像并没有期望的那么幸福。期间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变革也许为此分担了些骂名。再加上叔伯父母也不知道些许恩怨纷争,让她走向吃斋念佛这条路。
外婆的学历说出来有些见笑,她在小学一年级,就因为打架而辍学了。一则没有学习的兴趣,再者旧社会从来就没有把任何一个女子的学业看重过。就在所有人以为,外婆与学习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的时候,信佛,念经,又让她不得不从头学习认字。两条平行线就这样奇迹般的有了交点。值得一提的是,她所需要学习和写的字都是繁体字,这对于小学还没毕业的外婆而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兴趣,还有毅力。这期间的历程,恐怕仅“努力”二字是难以承载的。事实是:她做到了。在老屋壁橱上罗列着基本旧书,其中,我还记得那本小学时候买的《新华字典》因为外婆的翻阅早已破烂不堪。如若碰到我正好在家,外婆也时不时拿了一本佛经问我那其间一些晦色的字。有时候愚钝的我也会被卡住。想想也觉得好笑,可她从来没有这么想,不认识就应该学习,哪怕只是早已弃用的繁文。在这种毅力坚持下,外婆认识的经书渐渐的多了,几十年下来堆积的经书却也毫不逊色于我那中学时代铺天盖地的资料书。有时候两下一比较,心生敬佩的同时也百感交集。也许在某个领域,她是个三好生。
佛堂的那尊释迦摩尼一直这么静默着。对任何人都是这幅尊荣,也包括她。他好像没有打算渡她得道成仙。不然,为何岁月在她脸上雕刻艺术的'片刻,他有的仍然是熟视无睹呢!
时光荏苒,光阴的飞逝像是变着一场没有谢幕的魔术,道具换了又换,观众走了又来,面孔绝无雷同。这场表演放在外婆身上也许更加明显,稻草般的头发已不知不觉被魔术师染成了银色,几根黑发赫然其中也显得格外耀眼。干涩的眼珠丝毫没有光泽,似乎暗示着那视力也几近于无。有时候想和她说些家常唏嘘一番,无奈也得扯着嗓门喊。想到这里,反而觉得“佛”也未尝不是对她的一种解脱。至少活在与佛的世界里,用自己仅有的能力虔诚向佛祈祷着家族的平安是她认为最有效也是最高兴的事。她的黄表(相当于呈上天宫的奏折)里面总写满了我们的名字,从老到少,一个不拉下,当那表单随火而飘上空中,飞舞,散开空余一缕青烟时,她总会兴奋的像是个孩子,是的,是她的愿望已呈上极乐净土,等待着佛祖的批示。
(三)
外婆给予佛一颗虔诚的心,佛给予外婆博爱无私的胸怀。 外婆如佛,很多人这么说,认识的,不认识的,陌路的,乞讨的。尽管,现实压力重重,没有固定的经济维持这份有些奢侈的信仰,甚至是当基本的日常生活也成问题,她也没有放弃过。这里,是农村,党的光辉还远远没能穿过层层“阻挠”普照人民。
生活与信仰迫使外婆重拾锄头,开始耕耘,一个月二老的生活加上开支不菲的香火钱全依赖于这点田地。这天黄昏,我从镇上回来,穿过一片田野时,在一望碧顷的庄稼里多了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时不时扬起那粗壮的锄头除草,又间或背一个大药壶来回打药。累了,坐会儿再来;实在不行了,就坐下望着田地,想想我们,看看自己,穿过她深邃的眼眸看到的是希望和微笑的脸庞。待忙完这些,已是夕日欲颓。她便扛了锄头,提了铁桶,带上草帽朝路边走来,我假装偶遇她,接过锄头,铁桶谐同她回家去了。落日西下,一老一小,一高一矮比肩行走于泊油路边。这是我所喜欢的意境,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这年,外婆用收得菜子打了几壶油,还卖了几百块。心想以后手上可以宽裕点了。这年是2008年。后来发生的一场灾难让很多人都措手不及,那段时间她干涩的眼里时常浸润这泪水。她什么也帮不上,只是摇摇头捐出了刚到手的一百块。
作为后辈,外婆,外公的无人奉养,我们都难脱干系,几个叔伯之间的矛盾,也羞于道说,或说我没有资格去介入并且评头论足。母亲已为人妻,只能时常偷偷打些钱给外婆。我那时候还小气的问过母亲,既然外婆信佛每月要花那么多钱烧香,而这些钱用来生活大可过去,我们何不劝外婆不要再迷信下去呢?母亲只是无奈的摇摇头叹道:“如果是那么容易,也就好了。眼见外婆已如此沉迷,便是真想劝,也没什么意义了。况且她这身子骨还能有几个年头的日子,谁也说不好,就当是给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愧疚。趁现在还在,苦点也无所谓了。”说完,母亲眼中闪过一丝泪光。我仍似懂非懂的琢磨着。也是,这风木之悲又岂是那时的我所能了解的。我那时只明了:外婆很好,对任何人,尤其是我。我是从没想过,她会去的。也大抵如此了,套用外婆的哲理:命运造化,来去匆匆,本是浮云一片,又何必纠结于一时的蓝天。
转眼,我也要回到我的战场继续拼搏。望着外婆潺弱的身躯,心里多少泛起一些愧疚与不舍。心想,万一那天……算了,我止住了那可恶的想法,强忍着挤出了一丝笑容,好让外婆心安而回。只见外婆想起什么似的,跑回屋里,一会不到便拿了几盒钙片塞到我手中,说:“上次有个活菩萨来卖药,说是大型医药房打折下乡活动,我见它们便宜,就买了几盒给你们几个补补钙,兴许高考就用上了。”说完后,我一阵惊讶,随后拿着药盒看了看,不禁倒吸一口气。显然,外婆受骗了,可悲的是那禽兽竟成了外婆口中的活菩萨。不过我没说什么,只是定了定神,深叹道:“我会注意的,您自己保重吧。”便拿了药转身上了车。客车缓缓启动后,车后外婆,外公还追了几步,而后就只是站着了,雕塑一般的站在马路当间,一直到没了影子。
路上,我拿出药盒,端详一阵,无言以对。我闭目摇摇头,药没有扔,也没有吃,随即收了起来。我在想,那尊佛像知道这事后,会不会仍旧心安理得的接受外婆笃信的朝拜呢!?
想如今,我已略微了解到母亲当初的悲哀了。也不禁想念起我那远在故乡的外婆。前些天,听母亲说外婆手臂摔断了,我满心忧愁,想那年老体弱的外婆又岂堪如此折腾。我不敢想象她痛苦呻吟的样子,可是我愈是逃避,那影子愈是清晰。可怜的她,莫要糊里糊涂的去了,留我在异乡独自啜泣。想到这里,情不能已,不禁一声长叹,泪眼下的星空却也如此闪耀,同在一片夜空下,愿繁星带着我的思念与不安飞向远方……
如果说,给我一份天长地久的爱情,我愿把她留在心里;如果说,给我一份三世同堂亲情,我愿留在她身边,即使我心早已纷飞,我情愿为她画地为牢,伴其走过岁月的最后一程,此生足以。 ——后记
拜谒乐山大佛是久有的愿望,如今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
从陡峭的九曲石壁栈道,托危岩,扶铁栏,自上盘旋而下,低头是深渊,只见江水滔滔,便觉头昏目眩,心惊魄动。然抱着一仰大佛全貌的向往,酸痛着大腿,颤抖着小腿,坚定地往下爬。终于站在了佛座下。
仰视乐山大佛,深感自己的渺小。大佛顶天立地,雄踞凌云山栖霞峰崖,高峻伟岸,依山而居,临江危坐,头齐山顶,足踏大江,双手抚膝,是一尊真正的巨人。这就是我神往景仰的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佛像啊。
细瞻大佛尊相,不禁思绪悠悠。大佛面对江水,体态匀称,神势肃穆,俯视众生,在凝眉沉思、在聆听来自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聚的争论,默然不语,安详庄严之中带点沧桑,眉宇间隐隐透出一股悲悯之情,是在痛惜苍生的苦痛不幸,还是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舍身成仁之心,欲以一已之力渡万民出苦海?
这一尊弥勒佛像,他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笑呵呵的"大肚能容,笑口常开"的布袋弥勒,而是早期弥勒菩萨像。弥勒,梵名即MAITREYA,意为慈氏,是慈爱众生之佛,其有偈语云“宁当燃身破眼目,不忍行杀食众生。”“宁破骨髓出头脑,不忍啖肉食众生。”“如佛所说行慈者,此人行总不满足。”正是慈爱众生的明证。
而弥勒端坐于此,或许正是佛理禅机的人间宣示……。
青山隐隐,碧水迢迢,悠悠岁月,凝聚千年旧事,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历史超越时空地凸现……
传说,未建大佛以前,这凌云山下,三江汇流,江水湍急,过往的船只在经过山脚时,稍不谨慎,往往触壁倾覆,葬身于激流旋涡之中。唐玄宗开元初(703年),前来此地讲经参禅的海通法师,看见船毁人亡的一幕幕人间惨剧,便据佛教之道,认为水中有妖怪兴风作浪,如能依山傍崖凿一佛像,就能镇服妖孽,保佑过往船只。于是,海通法师便萌生了造佛镇水的宏大计划。他为了广集资金,便云游天下,风餐露宿,足迹遍及“江湖淮海”千辛万苦历尽千辛万苦,募捐凑足一笔经费。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到公元730年,大佛终于动工开凿了,自然,选中大佛就是这慈悲为怀的弥勒。海通就在距工地不远的山壁,凿洞而栖,指挥这一空前巨大的工程。殊不料,作威作福的州官,突然传讯海通法师,敲诈勒索,妄图取得一笔贿赂。海通法师义正词严地表示:“要我的眼睛可以,要修佛银钱休想!”州官恼羞成怒,喝令皂吏拿来托盘和尖刀,扔在海通脚下。海通义无反顾。操起尖刀挖出了自己的双眼……州官惊得目瞪口呆,但仍不放过海通,将他投入大牢,最后冤死狱中。一千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场景至今仍然令人震撼,发人深思……
时至唐德宗李适执政的贞元初年,韦皋受命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这位能文善诗的中书令,这位后来为蜀地的平和作出贡献的开明官僚,一路风尘,来到成都,得知海通冤死,大佛半途而废之事,便亲临嘉州,为海通平反,并拿出国库资金,资助修佛工程。到公元803年,延续73年之久的弥勒大佛终于落成。那“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的恢宏气势,那超凡脱俗的神韵风采,那博大精深的佛文化氛围和气象万千的山光水色,给我们“极天下佛像之大”壮观,给我们以生命意念的启示,给我们以坚定的登山拜佛的朝圣心志。
仰望高71米,头高147米,有1021个发髻,肩宽24米脚背宽9米,长11米,可围坐百人以上的巍然大佛,我的心中充满的是崇敬和赞叹。在当时有限的生产力制约下,前人到底要付出几多代价,才始有今日传世的乐山大佛?其间经历多少曲折,遭遇几多风波,我虽然未能一一亲眼目睹,但不难想象到!千载的风霜湮没故侣旧事,洗净当年的陈迹,唯有三江之水依旧东流,唯留大佛千载不变!这期间有多少人为此呕心沥血,为其献出一生的春青和宝贵的生命,但无悔无恨,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中间多少禅机让人品味,让人深思,让人增生前仆后继的信念……
转头见凌云山边佛座之下的三江江水汇聚至此,似乎一下改变了那汹汹翻腾咆哮的险恶,变得温顺平和,在这儿一路欢歌地汤汤而行,真的'是大佛顶烈日冒风雨,披一身青苔而不悔,执着佛意,点化了这汹涌与澎湃?……
俯身礼拜大佛,大佛不语,而我却感到一种理性的禅悟在心胸涌动。大佛似乎在警示我什么,佛道与人世其实同理。大佛成就的九十年历程,大佛居世的数千年岁月,有着多少让人思考的话题,然而却都可以从佛道禅理来参悟来阐释……
拜别大佛,沿着凌云栈道艰难地返回山顶,在“海师洞”前,我静静地站在新塑的海通法师的石像前献上我的敬意。海通像约2米高,海通法师盘膝而坐,面容清瘤,神情刚毅,手捧装有眼珠的一个托盘,展示着献身成仁的凛然与悲壮。尽管岁月悠悠,尽管流水脉脉,其实,即使没有石像,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位瘦骨嶙峋而又大义凛然的老法师。是他,以罕有的牺牲精神和实践促成了大佛的诞生。而这种精神与实践正呈示着佛道禅理,又闪耀着人类的气节情操。佛祖释加牟尼的刎肢喂虎、观音的以身劝*,地藏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佛的示范,而海通把这化作了人间的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成就了一项伟大的永载世界史册的艺术,更是弘扬了一种精神和信念,一种力量和情操。这种精神和信念,力量和情操,一旦官民同具,同心一德,共同奋发,便会创造出人间的奇迹,便会有流传后世的福祗。多一些海通,多一些韦皋,少一点作威作福的“州官”,我们的前景才会更好。郭沫若先生为乐山大佛题写的楹联“大江东去、佛法西来”蕴涵着乐山大佛的神、灵、性的禅理,让人顿生感悟。
拜谒大佛,我们献上崇敬和诚心!
拜谒大佛,我们祈愿美好和平安!
拜谒大佛,我们承接洗礼和禅机!
拜谒大佛,我们把任何艰难踩在脚下,坚定地去干就我们的事业……
看郭敬明的《爱与痛的边缘》,余秋雨的也不错《三峡》
建议看书本的好,网络上面看没什么效果也不深刻
《三峡》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一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他既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
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