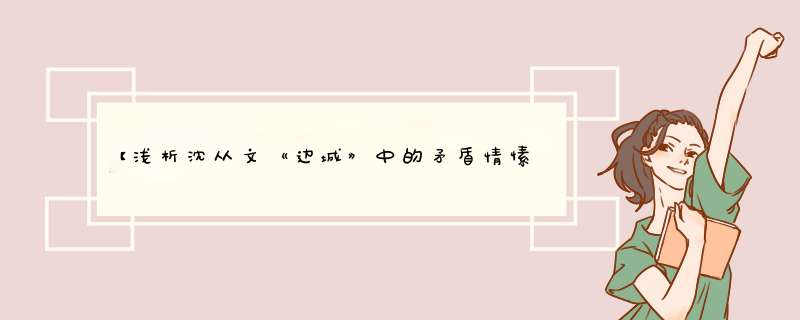
摘 要: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是希望用古老的湘西文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种蓬勃的原始生命力;然而,他还发现,湘西文化是人们在内心深处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但真正的价值,是他自己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中的城市和偏远农村的又爱又恨的情感体验与现实的沉浮和沉重,这就导致了沈从文深刻的矛盾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社会理想矛盾
一、沈从文的社会理想
沈从文出生在传说中的风景如画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奔流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的血液,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还有少数民族遭受长期压迫和堆积在心里沉重的悲伤和痛苦。十几岁的沈从文经常会目睹家乡饥荒、骚乱、杀害和抢劫现象,他产生了一种人类的天性:人道主义以及产生到大城市去找到理想的想法。沈从文离家的导火线是本地的几个绅士财主,想纳他作女婿,这其实是一种策略,那些在当地称王称霸的人,以联姻的方式,能建立和巩固上层社会错综复杂的统治网络。但是独立性较强的沈从文拒绝做他们的女婿,拒绝做乡村绅士,他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初恋”。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并深信她也爱着自己。沈从文的思想和《边城》中傩送的思想是相同的,他真正需要的是生命的活动,想出去,不愿意遵循固有的乡村绅士的路混沌的走下去。沈从文最终毅然走出了湘西,思考着更为严肃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
沈从文从乡村到大城市,见证了堕落的上流社会生活,对城里人庸俗、卑鄙、自私有着一种莫名的厌恶。,这引发了他的乡愁,让他对自己家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摧毁了诚实的民风十分向往。回到故乡的所见又令他十分失望。在《长河》的题记中,他说:“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葆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的人生观。”这就不难理解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渲染湘西人的简单的风格,作品中有很多章节用显式或隐式批评湘西社会隐患和丑陋和那些美丽的田园的图画经常形成鲜明的对比。
沈从文离开茶峒后,接触了一些社会底层人物,感受深刻的世俗观念和真实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距离。他感触到的社会现象 ,全是“黑暗”和“邪恶”,但在邪恶的后面,却又有为“人”的东西,还有着耀眼的光。他发现了湘西豪侠、仗义、慷慨、雄健、粗犷等民风中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湘西人自然不做作、葆有真性情的自然人性。在社会生活中,沈从文强调城市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人性和伦理的失去,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传统的道德和封闭、保守的粘连,所以他在对“乡下人”的弱点的思考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去进行新的竞争问题。沈从文反思湘西文化,觉得湘西的人们对自然妥协,表面更加人性化,更自然,但结果却是不能适应潮流,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沈从文对家乡的情感是爱与恨交织,希望与失望兼有。
《边城》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民国初年湘西小城茶峒,外公与翠翠在渡口摆渡,翠翠的婚事成为老船夫最大的心事,老船夫唯一的心事就是要将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船总有四条船的家业且有两个儿子,大佬天宝天性淳厚却木讷寡言,二佬傩送眉目清秀活泼善良。翠翠年方十五,情窦初开,于端午节邂逅傩送,心里产生异样,在二佬面前却躲躲闪闪,这让老船夫很苦恼。船总家派人来给大佬提亲,老船夫为难。兄弟俩将话说明,相约山头唱情歌,翠翠听到情歌喉心有所动,老船夫喜极将此事告知大佬,半个月老船夫在未听到过山歌,却得天宝遇难噩耗,天宝一家将天宝的死怪罪于老船夫求亲时的躲闪。时间久了,老船夫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遇到傩送他招待傩送却被报以冷眼,老船夫不甘,亲自去船总家提亲遭拒。王团总给女儿提亲以碾坊为嫁妆,船总答应了,傩送以出去闯闯为由出门。老船夫心力交瘁,死于雷电交加的晚上。经历了这件事后,翠翠有所成长,常年摆渡守候傩送。在《边城》中的沈从文不是实际存在的时间描绘30年代的湘西社会,而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试图重建他的脑海里对过去湘西的渴望和萌生出的痴迷的感情。沈从文严肃的思考着社会的未来,把握我们民族所有问题的症结,了解民族的人生观的弱点,徒劳的迷信,懒惰和由于历史的不良影响,已有的报应。并且在作品里足以告诫人们,千万不能再糊涂愚昧下去了,否则,会出现更悲惨的场面。作者在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做。
《边城》中作者在浪漫的氛围下,写他的精神积累,难以忘记的一段感情。这是一个既荒凉又有梦想的歌,但是作者也总是关注社会改变,希望找到变革民族精神的良药。可在原始湘西文化中又存在着一些人性的阴暗面,例如迷信、愚昧、笃信因果报应等,而且湘西已不像过去那样纯净,它正在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人们内心深处产生了维实维利的价值观。这些使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中有着深刻的矛盾。
二、沈从文的美学追求的矛盾
《边城》是一个著名的讴歌人性美,人情美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却经历了最不人道的,最缺乏人性的事情。一对真正爱的人——翠翠的父母:一个茶峒士兵和湘西的女人手牵手走进死亡。其实逃去不好吗?为什么要选择结束生命?逃去就毁了一个军人的名誉了吗?直到翠翠长大后,她的祖父仍然自卑和自责交织在一起,当有月老来为翠翠提亲时,爷爷看出了翠翠的心思,作者写道:“他还记得那可怜的母亲的过去,有一点点痛在心里,却带着微笑。”他们的死是不负责任的,是一种逃避,根本没有敢爱敢恨的豪爽。他们对对方的爱没有大于对虚无荣誉的爱和对刻板规则的恐惧。他们的爱是真的,互相吸引的,并有一个结晶,他们应该建立婚姻,是因为他们是在有婚礼之前就怀上了孩子,就让他们失去三条生命?
这并不是美好人性,也并不是对于死的无所畏惧的伟大。
另外在《边城》中对妓女极其宽容,显得茶峒人男女之情的淳朴、真挚。“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在一个女人身体上的贸易,因为民风的诚实,当事人不感到羞耻。这可能表明,沈从文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已经拒绝了这个没有道德约束的,开放的性,但又这种感觉是原始人的本质而加以褒扬。 《边城》中的生和死的自然,爱恨自然,但这种自然只是因为湘西一直经历着动荡的社会,长期不接受新的观点,人们的观念是继承了长辈的,没有什么会引起人们思想的激烈冲突,认为这一切是正确的。沈从文在描述这个生死爱恨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浪漫,诗意的风格,是远观,田园情调。给人感觉是一幅画,与自然完美融合,那里发生的真实生活的故事远离我们的边境小镇,所以这平静的残酷背后将很难让人感到和认识。
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
如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温柔的个性突现出来。
最突出的是心理描写手法。通过暗示去展开人物内心。
一、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便是我们认识的翠翠。闭上眼睛,可爱的形象很快进入脑海。翠翠对祖父的爱带着一些任性、一些娇气,而对天保兄弟的爱则带着少女的羞涩和幻想。由于她感觉到祖父不理解自己,便设想着自己出走给祖父带来的“惩罚”——让祖父尝尝失去她的痛苦;可是当她想到祖父的无奈便又为他担心起来,于是一次次地叫祖父回家,生怕两人真的就会分手。这生动地反映出翠翠对祖父的依恋之情。再看翠翠对天保兄弟的态度。天保选择的是走车路,通过祖父询问翠翠,翠翠不理不睬。祖父不知原由,其实翠翠心中早已有了二老,但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子只能选择沉默和躲避。对于二老,翠翠喜欢于心,仍只能沉默。我们不仅为这小女孩担心起来了呢。 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社交需要(也可称为归属和爱的需要。包括社会交往,从属于某一个组织或某一种团体,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得到承认;希望同伴之间保持友谊和融洽的关系,希望得到亲友的爱等等),翠翠对祖父的爱与对天保兄弟的态度是不同的,从祖父那里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从傩送那里得到异性的爱。这正是翠翠所追求的,然而从整部小说来看,翠翠似乎一直生活在一种梦幻中,她只能在梦中才能品尝到爱的甘露,而现实却似乎离她很远,于是,她只能凄凉地守候,孤独地等待。
二、祖父
《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作品”。小说正是通过祖父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祖父是一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在祖父的身上,流淌着炽烈的爱,也存在着难以排遣的矛盾与孤寂。祖父对翠翠的爱寄托着对不幸的女儿的哀思,他的后半生是为翠翠而活,他的惟一的生活目标就是要使翠翠快乐。但他并不真正了解孙女儿内心的情感躁动,他只能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的话语来安慰孙女儿:“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情都不许哭泣。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孙女儿能有一个好归宿展开的。但他又害怕翠翠会重蹈母亲的悲剧,所以,他去探天保的口风,征求翠翠对天保兄弟的看法,给翠翠讲她母亲的故事,唱那晚听来的歌,也因此他没有把天保兄弟的选择直接告诉翠翠,只是提醒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让翠翠理解,也没有成就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反而导致一些误会。 祖父的角色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讲,应该是尊重需要(即自尊、自重,或要求被他人所尊重。包括自尊心、信心、希望有地位、有威望,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以及高度评价等)。他所要想得到的就是翠翠生活的好,得到翠翠的敬爱;得到老友杨马兵的信任和帮助;以及船总顺顺父子的信赖及评价。但他并不想得到那些地位、威望等,那是不需要的。
三、天保
这篇小说对天保的刻画不多,但这个人物的性格却同样鲜明地突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爱翠翠,但无法让翠翠同样爱上自己,当得知弟弟也爱着翠翠,便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退出了角逐,既表现出浓重的手足之情,又流露着失败的落寞。从他对老船夫的冷冷的神情和生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和痛苦。为了爱,他孤独地外出闯滩;又为着爱,孤独地客死他乡。在这里,天保所需要的也是社交需要,对弟弟,他需要保持亲情和融洽的关系;对翠翠,他需要异性的爱。
四、傩送
“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人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 ’。虽无什么人亲眼看到过岳云,一般的印象,却从戏台上小生岳云,得来一个相近的神气。”傩送用现在的话来讲,是个很帅的人,他与翠翠的相互爱慕是真真切切的。“ 傩送的爱情选择实际上是在义和利之间的选择,是在金钱和爱情之间的选择。正因为他的选择是渡船,正因为他坚持了民族的义利取舍标准,所以他在作者的心目中才成为民族优秀品德的象征。而他的出走,也就具有了象征的性质,它暗示了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失落” 。这篇小说对傩送的刻画花了不少的笔墨,就人物主次来讲,我认为傩送仅次于翠翠。傩送喜欢翠翠,但是因为哥哥先说的缘故,他不得不建议采取兄弟隔夜唱情歌的来获取翠翠的心。及至哥哥被水淹死,他的心里有了隔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讲,他的爱的需要是首位的,但因哥哥的意外死亡,这种需要不得不被暂停。 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思想。
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的联系起来,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是顺顺父子不自觉的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来做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是选择了爱情,却未能想着翠翠在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毁灭,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行。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
沈从文的《边城》告诉我们: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相互友爱。
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边城》写以歌求婚、兄弟让婚、外公和翠翠相依之情,这些湘西人生命的形态和人生的方式,都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的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
作者推重湘西人的人生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扩展资料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或通过对话、独白、行动、姿态、面部表情等直接剖析;或采用幻想、梦境间接揭示;或借助景物描写、气氛渲染及周围人物的反映等侧面烘托。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边城 (沈从文著中篇小说)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