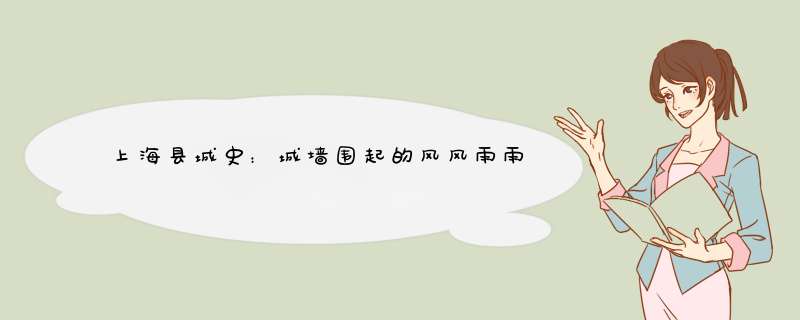
今人看上海,繁华当以外滩周边为最盛,而这其中,许多是源自租界时期的遗产。自清末国门大开,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在洋人进驻的屈辱底色下,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并最终跻身国际大都会。
这段历史激荡不已,而又光怪陆离,从来都是文学、**、学术研究的宠儿。然而,上海在“蜕变”之前的历史,却鲜有人关注。那时,她的朴素与普通,与无数的中国县城别无二致,却倒有一些不得不讲的趣事。
城墙围起的沧桑
不同于众多“古都”城市,历史上,上海从未做过都城,甚至连建县都很晚。
1291年,元朝批准以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两岸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五乡二十六保设立上海县。这是上海建县之始。
不过,尽管在名义上是县城了,上海却一直没有建城墙。一来,上海作为滨海城镇,本就极少受到战争困扰;二来,当地居民大多出海为生,有了城墙,出海反而极不方便。因此,尽管古人将城墙作为“正统”城市的标配,上海仍维持了200多年“无城墙”的状态。
宋末至元中叶上海镇市及县市复原图
至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抑制流窜海边的农民军活动,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或限制沿海的海上运输,下令沿海百姓必须向内地迁移。此举阻碍了日本商人的生财之道,也促使其与流落至此的农民军从“武装经商”发展为“武装掠夺”。
“倭乱”随航海技术的发展而愈发激烈。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上海则饱受着倭寇最严重的骚扰。仅上半年,上海县遭倭寇三次洗劫,掠夺无数财产。
明嘉靖时期的上海县城
为应对侵犯,“松江知府采纳了原光禄寺卿顾从礼的提议,决定立即修筑城墙。是年农历十月,砌墙工程正式开工。整个县城顿时成了工地,上海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顾从礼捐粟4000石,助筑朝阳门(小南门)。太常寺卿陆深的夫人梅氏,不仅捐田500亩、银2000两,还拆毁了自家宅屋若干,助筑宝带门(小东门),故小东门又名"夫人门"。"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两个月时间,上海县城墙就巍然挺立起来了。”
建好的上海城墙,长9里,高二丈四尺,城壕长1620丈、宽6丈、深一丈七尺,辟城门6座,设水门3座。
这是后人根据史料记载描绘清代时期的“上海老县城”景观
老城墙所开6门,分别为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老西门)和晏海门(老北门)。
今天上海市区的中华路、人民路,解放前叫“中华路”和“民国路”,在1912年(辛亥革命第二年)以前,那些更为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是以“城墙”为载体而存在。通过今天的上海地图,我们仍能依稀看见县城的轮廓。
从城墙里密集的里弄,和颇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我们仿佛回到一个典型的古中国城市——文庙代表着古人对教育的尊重,豫园的亭台曾环绕着诗词曲赋,城隍庙则香火旺盛。“火腿弄”、“天灯弄”、“巡道街”等街名,仿佛将人带回过去热闹的街市,那里有贩夫走卒、衙门巡捕,有着中国人延续了千百年的市民生活。
贸易都市:资本主义的萌芽
城墙,代表了古中国“安定”的城市理想。
城墙筑好后,确实有效的抵御了数次倭寇攻击。1559年,上海境内的倭患基本被肃清。上海于是又回到了安稳的小城生活。但如今看来,一道城墙保障了城内居民免于倭寇袭击,却也将刚刚萌芽的国际贸易拒之门外,可谓“成也城墙,败也城墙”。
直到清康熙年间,上海的封闭状态才真正有所改变。
一是口岸逐渐繁华——靠近上海县城的十六铺,起源于晚清的1860年代。当时,为了防御太平军的进攻,清朝地方官员将县城内外的商号组织起来,形成16个“铺”,负责治安和公共事务。十六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铺”,包括县城大、小东门外,西至城濠,东至黄浦江,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万裕码头街及王家码头街。
1871年的上海县城图
二是商业组织明显增多。1654年(清同治年间),上海诞生了第一个移民同乡组织——关山东公所(关东+山东商帮)。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 颁布“弛海禁”政策,放宽对沿海运输的禁令,海上贸易恢复,沿海各省商帮人士来沪经营手工业、棉纺织业、沙船业等,上海逐渐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各地来沪移民和流动商人为联络同行和同乡情感,建立了一批同乡同业组织,大多都在老县城周边。
据不完全统计,从关山东公所建立此后的三百年间,上海曾有会馆(公所)400余个,绝大多数由各地商帮集资所建,上海开埠前,会馆(公所)大多雕龙画栋,立有碑碣,用于供奉祭祀、联络乡情和调节同乡同业矛盾纠纷,带有浓烈的封建地方保护主义色彩。
商船会馆,2012年媒体报道其年久失修
以商船会馆为例,它是“清代上海从事南北沿海沙船运输业商人的同业公所,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集资建造,内有双合式大殿,殿前为两层楼戏台,上有八角形藻井,殿前左右两侧各建二层楼的厢房作看戏用;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殿右有二层楼的会务楼”。
地域认同所形成某种难以言明的情感,使得机构内的人员能够自发遵守会规并恪尽职责,而其在遭遇社会结构猛烈变动的清朝中后期,则更为异化和繁荣,“是上海以港兴市历史的重要见证”。
上海老城厢附近的同乡组织,大多既通同乡之谊,又设行业之规,以便灵活应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所带来的压力。而开埠后所建会馆(公所)则融合中西方建筑风格,性质也逐渐转为资本主义行业组织,并参与到上海的城市建设当中,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加强民族工商业发展、抵制外国侵略者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陆其国,《上海城墙》,//archivesshcn/shjy/shzg/201203/t20120313_6409
张姚俊,《上海城墙的故事》,//archivesshcn/shjy/shzg/201203/t20120313_6290
新民晚报,《沪上最老会馆年久失修成危楼 门楼题字难辨》,//chinanews/cul/2012/05-03/3862520s
本文节选自《寻路上海滩》项目,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查看同系列文章:
上海如何从小渔村变成魔都?每一条道路都蕴含着往事
《大话西游》是一部**,其中城墙上的女子和孙悟空之间的眼神可能是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或者情节而设定的。
在《大话西游》中,孙悟空和城墙上的女子都拥有着不同的身份和经历。城墙上的女子可能曾经认识孙悟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他的过去,也许她曾经是孙悟空的某段感情纠葛的对象,或者是他的故友。但是,在**的情节发展中,孙悟空和城墙上的女子之间并没有出现太多的交集,因此他们之间的眼神可能是在表达彼此之间的某种默契或者情感共鸣。
此外,城墙上的女子也有可能是孙悟空的转世或者后世,她和孙悟空之间的眼神可能是在暗示某种前世的缘分或者宿命的联系。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眼神的设定都是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中的情感和情节。
作品原文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1]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 咏怀古迹(其三)
[2]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3]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4]
其四
怀禅微刻《咏怀古迹五首》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5]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6]
编辑本段作品注释
其一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开首咏怀的是庾信,这是因为诗人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写安史之乱起,漂泊入蜀居无定处。颔联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颈联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末联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1]
其二
这是推崇宋玉的诗。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索寞鸣不平。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3]
其三
这是杜甫经过昭君村时所作的咏史诗。想到昭君生于名邦,殁于塞外,去国之怨,难以言表。因此,主题落在“怨恨”二字,“一去”二字,是怨的开始,“独留”两字,是怨的终结。作者既同情昭君,也感慨自身。沈德潜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4]这是《咏怀古迹五首》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此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可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亦与此意相接近。究竟谁是谁非,如何体会诗人的构思,须要结合全诗的主题和中心才能说明白,所以留到后面再说。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一下之后,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想到这里,这句诗自然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略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略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咏梅名作《疏影》里曾经把杜甫这句诗从形象上进一步丰富提高: 昭君不惯胡沙远, 但暗忆江南江北。 想佩环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独。 这里写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不是长安的汉宫特别动人。月夜归来的昭君幽灵,经过提炼,化身成为芬芳缟素的梅花,想象更是幽美!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 话又回到此诗开头两句上了。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是值得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的。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说明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情。他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象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相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的确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其四
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5]
其五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