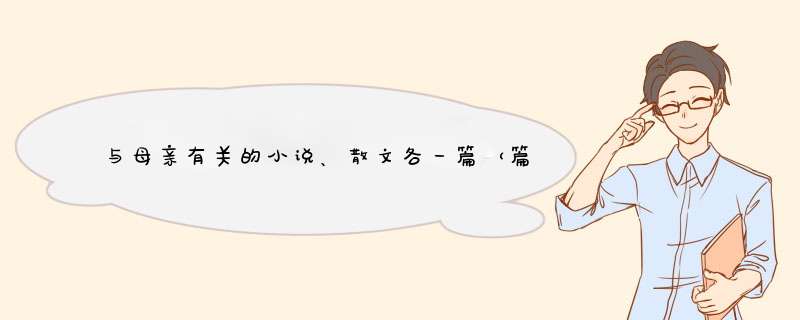
小说
母亲是无知的,小学念了三年就辍学了。十一岁开始割猪草、煮饭、洗一家人的衣服,帮着外婆拉扯其他六个兄弟姐妹。年少时的我在念了几年书后,便开始拿学到的生字回家考母亲,看到她困窘的表情,我就得意的摇头晃脑拖长了音将生字念出来,来表示我的轻蔑。但我一直奇怪,无知的母亲简单的头脑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深不可测的智慧,怎么可以将一团团毛线织出花样繁多的毛衣,怎么可以将白衬衫发黑的领口洗回原色,又怎么可以在过年的时节将家里大大小小烦琐的事打理得妥妥当当,我更无法想象,母亲几十年来怎么能将买菜做饭洗衣服打扫屋子这些纷繁的家务在一个个重复的日子里重复着再重复。
母亲是吝啬的,总想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我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和母亲上街,我哭了闹了还赖了地,为了要买一瓶三毛钱的汽水,在对峙了十分钟后,屈服的仍然是我。于是在学到“吝啬”一词后,便毫不吝啬地将这个词冠于母亲头上。直到多年后,母亲用她吝啬下来的钱供我念完了高中,念完了大学,我才由衷的感谢母亲的吝啬,才体会到母亲度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艰辛。三年前,父亲下了岗,拿微薄的下岗工资,母亲就揽了织毛线手套的活,每双一块钱,一天下来最多织上十双,就是十块。每次回家,我看着母亲在灯下穿针线,两鬓竟已斑白,心不由的总是阵阵发酸,就叫她别再做了,我可以给足家用,母亲便拿眼瞪我:“你自己那点工资也不多,大城市里开销大,我每天做几块钱,到时候你买房子也好补贴你一点……”其实她也知道,她织一年手套的收入也买不了城里半个平方的房子。
母亲是虚荣的,或许身为一个女人的天性吧。每次回家看她,她都要找个理由拖着我上街,到街坊朋友那里转一转;给她买的衣服,她总是在走亲访友的时候穿,然后告诉别人是我买给她的。我知道她是想在别人面前炫耀一下她的儿子。其实我只是个小小的城市打工仔,又没钱又没权。而我知道在母亲眼里,我大学毕业,是有学问的;我在大城市里上班,是有出息的;我常回家看她,是孝顺的,于是简简单单地,我成了母亲最大的骄傲。
母亲五十四岁了,一天天在老,她手上皱纹弯曲,如最古老的文字,记述着她一生平凡的经历,一世坚强的性格,一辈子对这个家伟大的爱。十一月初二就是母亲生日,我想给母亲买一束花,告诉她我爱她。
散文
人生旅途,我们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不幸,这样或那样的困苦我们寂寥的心灵何以慰藉,向谁倾诉,谁又能倾听,为我们掬一捧同情的泪水,抚摸那孤独的灵魂,我想,那人肯定是母亲母亲不仅给我们生命,而且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是我们生命航船的灯塔
我们小时侯不谙世事,曾做过那么错事,给家人、给亲戚、给朋友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可母亲却很少责骂我们,用她那慈祥的眼光感化我们,教我们如何改正错误,如何坦荡的去做人,做个好人。
稍大后,我们在学校争强好胜,或出尽风头,因而遭到白眼和各种打
击,幼小的心曾承受不了,几回痛哭,或欲要轻生。是母亲用她那温暖的胸膛融化我们冰冷的心境,让我们从梦魇中醒来,看清自我,认识自我,找回自我,看到前途,看到光明。
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人世间的风风雨雨几曾袭来,挫折和失败不断困扰我们,使我们焦头烂额、举步维艰,苟延残喘。是母亲用她那柔弱的臂膀,挽起我们几欲崩溃的沉重头颅,教会我们怎样宽厚的看世界,怎样挺起胸膛走路。
我们与母亲相比,那是不能比的,用渺小来形容都是抬高自己、怜悯自己。我们骂人打架、旷课逃学、要吃要喝,可曾想过母亲的感受;我们总怨恨母 亲给的钱少,读高中、上大学、结婚总向母亲伸手要钱,可从来没想过那是母亲一口饭、一口菜节省下来攒的,那是因为爱你才付出而苛刻自己的。我们什么时候真 正的关心过自己的母亲,是在外面漂泊了许多年以后、是受到他人孝敬母亲的触动、是母亲那七十岁、八十岁耄耋之年整数的寿诞之日、还是母亲病重你守在母亲病 榻床头那个不眠之夜?也许是,也许都不是。许在你蓦然回首间,你发觉母亲已白发苍苍,满脸皱纹,母亲的青春已不在,母亲的岁月已不多,只有这时,你才真正 关注母亲。可那又能怎样,一声问候、一盒礼品、一沓钞票就能赎回心灵的愧疚吗?在母亲看来,这也就够了,也就很知足很幸福了。可那与母亲为你付出相比,怕 万分之一都不到啊。
我们时常带着这样的愧疚和无奈看望母亲和离开母亲,带着这样的感觉走入茫茫的人海,带着这样的感觉走上疲于奔命的工作岗位,同样,也带着这样 的感觉走入母亲节。在此时,我们除了对母亲说声快乐、健康、幸福、长寿外,是否还要说点什么。一句儿行千里母担忧,已道出了母爱真谛,一首“游子吟”已写 尽儿女抱恩情怀。
李福今天过生日,人间走过一个甲子。
早上,吃了老伴特意煮的面条和鸡蛋。这种吃法具说是图个吉利。饭后正要出门遛弯儿,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老李忙看来电,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是老母亲的,忙恭敬的按下接听键问道:″吗?一大早儿打电话有事呀?”电话那头儿传来老母亲苍老且颤颤微微儿的声音:″福儿啊?今天你生日。忘没?一早吃没吃面条呀?煮鸡蛋没……"
老母亲八十五了。虽然自己身患脑血栓多年,年岁大了,脑子有时不太灵光,时而有些糊涂。但对儿女们的生日记得还是相当准,这就母亲!
接完电活,老李的眼睛有些湿润,他仿佛想起了什么,忙跑到商店买了些水果,直奔老妈住处走去……
文/王金波
吵架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特别是家人之间,儿女与父母的思想有着几十年的差距,之间的不理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思想有一些新潮和不足,这是不可否认的,父母的唠叨是对你的一种关心,不要等到失去才追悔莫及。当吵架时,你想一想你母亲为你所受的苦,想一想你将成为母亲会怎么做,和你母亲谈一谈,人之间的争吵时因为不够了解。
有许多小说都写了男主角和妈妈与女儿在一起的故事情节,以下是一些例子:
1《红楼梦》:贾宝玉和他的母亲王夫人、表妹林黛玉在一起生活。
2《水浒传》:宋江和他的母亲、女儿扈三娘在一起生活。
3《西游记》:孙悟空和他的母亲、女儿小龙女在一起生活。
4《聊斋志异》:许多故事中都有男主角和母亲与女儿在一起的情节,比如《画皮》、《聂小倩》等。
5《儒林外史》:范进和他的母亲、女儿在一起生活。
这些小说中的男主角和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情感都非常复杂,而且这些小说也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池莉的《怀着夏日母性的心肠成为一棵树》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给你老舍的<我的母亲>吧,你自己挑选以下,不过我认为,全文皆是经典!
老舍: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送到医院里去。
我看见妈妈穿得很少,穿得很少很少,很单薄。我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过我妈妈穿得什么,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我妈妈会穿得这么陈旧,我赶忙帮她穿着我的衣服,把她的鞋小心翼翼的穿上,这时三姨已在门外把她的车打着了,她高叫着“我们先去医院等你们了啊”。她要先走!!!这对我来说是多么无助啊,我一个人要去送我妈妈到医院,以前一直是我倚靠妈妈的,买个东西也是靠妈妈的,现在要我一个人去送妈妈去医院,而且我是那么的怕,我多想有些人会在我身边帮我呀。
我没有再多想,时间不得延误。我赶忙把妈妈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在艰难的骑着,慢慢的骑着,避开每一个迎面赶来的人,在一个转弯处,和一个骑车的差一点撞在一起,我很气愤的骂他,骂“妈的车子也不会骑,瞎逼的往那骑呢?”那人回过头来骂道“这个后生是想挨揍了,他妈的”。这时妈妈对我说着“别理他好好骑车吧”要是以前我肯定不耐烦的说知道了,可是今天没有,我是那么的诚心的那么认真的回答着。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妈妈和我说她的肺疼呢,我就理也没理的说疼你疼去,疼是因为你有肺的原因。之后也见过她脸色难看的捂着胸口,我还是想我妈身体可好呢,一定没事。可是今天我妈靠在我的背上靠的是那么的紧,她是不行了,我知道的,我应该早知道的,可是是我的原因,我现在是多么伤心啊,我奋力的骑着自行车,可还是骑得很慢很慢。我伤心的眼泪也快流下来了,可是我还是忍着没有流下来。
妈妈这时在后面唱起了我们这里的民歌,唱的是那么的好听,特别的好听,我还不知道我妈妈唱歌这么好听,这么婉转悠扬,她现在很洒脱,我想她是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唱歌,我越来越伤心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再也停不下来了,我妈妈这时听见了我的哭声,在后面安慰着我,你要好好的生活,日子还长着的,别累坏了身体,要对媳妇好点,你好了妈也就放心了,我那时只顾着哭,回答她的声音低得听也听不见,我是多么的伤心啊,其实我是一直很爱母亲的,其实我也是一直很关心母亲的,可是我还以为她身体会很好,等到了老了再孝敬她,可是现在已经很迟很迟了,我真想用眼泪把世界都冲垮。我真的是知道错了,可是我知道事情已无法惋回了,可就在这时前面偏偏有个人骑车停了下来,我赶紧捏紧刹车,妈妈因为巨大的惯性重重的撞在了我的身上,我妈“啊”的一声,我感觉我背后的衣服沉沉的,我知道妈妈又吐血了,而且吐了我一背,我伤心,我难过,我简直是没有言语的形容,这时就象从天上有一个雷劈中了我,那种感觉我………………这时我揩干我耳根的眼泪,把沾在脸上的头发全弄起来,我一想到那种伤心的感觉,一想到妈妈真的永远的离开我的时候,我又一次流泪不止。而幸运的是我得救了,是上天把我又一次的救了回来,而上天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梦,让我记住要善待我的母亲。
这一个梦做得真是太好了,如果没有这一个梦,我可能还会对我母亲是那个样子,还会爱理不理,还会经常骂她,甚至还动手。可是现在不会了,我要爱护我眼前的,不会让后悔后的伤心再一次袭击我。在这里希望还对自己父母不好的人们,对自己父母还不够太好,对自己父母还没达到最好,对自己父母还没有上升到更好的做儿女们,从现在开始善待自己的父母吧,我今天真的知道有多伤心了,我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也还在流着泪,我是真知道伤心而又无助是个什么滋味了!!! 那个周六,我们回去看父母。摩托停在院门口,母亲来开院门,我看见她戴着老花眼镜,手里还拿着一支笔。我随口问:“妈,你在干啥?”“没干啥。”母亲回答。进了屋,又见母亲把一个本子随手往旮旯里一扔。我没再问她,却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拿起那本子一看,竟然是母亲在写自传。母亲文化水平不高,现在六十多了,居然拿起笔写东西,这让我感觉很有意思。我便在没人时悄悄笑问母亲。母亲见我发现了她的秘密,不好意思地笑,眼里竟然涌出泪花。
是夜,我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母亲满怀感慨地回忆起她辛酸坎坷的大半生,我认认真真地听着。其实,母亲已不是第一次讲她的故事,但,我从未像这次一样认真详细地听。
母亲属鼠,今年已六十二岁。母亲姐弟四个,姨比她小八岁,大舅比她小十三岁。小舅更小,小她十八岁。外婆是个爱干净、“爱生病”的人,大多时间喜欢躺在床上,不下田地,不做女红。我说外婆“爱生病”,并非是大不敬,单看她现在已八十八了仍精神矍铄,就可知她其实一直身体很好。母亲是老大,外婆“教女有方”,把她训练得勤快能干,自然,下边的三个弟妹都由她多付出喽,哄着玩就不说了,大舅小舅的衣服什么的都是妈妈做妈妈洗的。特别是小舅,棉袄棉裤棉靴全由妈妈一手操办。
外爷是个老实肯干却没有眼光的人,当了一辈子农村校长,却不知道重视教育,四个儿女没有一个上成学。母亲读书时成绩优秀,比同班的孩子年龄都小,但终因读书条件有限,只读了个高小就辍学了。
母亲辍学那年十三岁,开始下地挣工分。每天很早下地,很晚回家,稚嫩的双手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晚上和下雨天也很少歇着,还要纺棉花,还要做针线。
十八岁那年,母亲已出落成一个清秀稳重的大姑娘了,背上拖着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温柔善良聪明能干。曾经和大人一样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镇上去挑煤——挑了120斤的煤!而挑煤,在别人家那可都是男人干的活。十里八村的媒人轮番登门,母亲很羞涩,说自己还小,还要在家里多干几年活,等着妹妹弟弟长大,外婆喜得直夸妈妈懂事。从那以后,直到妈妈二十多岁,关于妈妈的婚事,外婆从不吐口。
在其他长辈的操心和张罗下,母亲终于在二十四岁那年,和父亲结了婚。结了婚的母亲,是我们村有名的巧手,家务活地里活,没有她不会做的。父亲那时在南阳工作,由于交通不便,很长时间回来一趟,所以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
母亲生了四个儿女。这四个儿女,让她的一生多了很多煎熬。
大姐一两岁时不知因为什么,动过一次小手术。
我是老二,更让母亲费尽了心。1985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为了我,母亲不仅求爷爷告奶奶筹钱,还要在医院伺候我。我呼吸困难,得坐着睡觉,母亲几乎就整夜整夜地坐在那里让我靠着她睡。为我治病,家里东凑西借,花了一千多元。那时候的一千多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无疑就是天文数字。许多人曾对我父母说放弃算了,但母亲态度坚决,毅然坚持。历尽辛酸,终于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现在还仍然记得我病好后医生对我说的话:“你捡回了这一条小狗命,以后可不要忘了你妈妈呀!”
我的弟弟,小时候由于没人照看,经常地哭,得了疝气,又让母亲受尽熬煎。
1982年,小妹出生,计划生育罚款,又让一家人的生活喘不过气来。
好不容易日子过得好些了,子女却大了,要考虑他们的前程了。1994年,我们市里的丝织厂招工,父母为了大姐的前途,咬咬牙花了2000元为大姐买了个工。1995年,我考上大学,需要学费和生活费。1997年,弟弟接了父亲的班,也需要交一大笔钱。就在这一年,我们家厨房倒塌,又新盖了厨房,花了一两千块钱。厨房建完,奶奶又去世了,可真是“雪上加霜”。我不知道这两年母亲是怎样过的,我只知道我在学校里是特困生,经常自卑得抬不起头来。我还记得那年春节我去姨家,姨给了我四百元钱,说一百是压岁钱,三百算借我的,等我参加工作后还她就是。我把这钱拿回家了,母亲却又还给了姨,连压岁钱也还了。这事现在我想起还有点生母亲的气。
终于我参加工作了,小妹又到考高中的时候了。家里拮据,父亲一心让小妹退学,酷爱读书的小妹很不愿意。母亲当然支持小妹,但架不住父亲整天地吵,终于,小妹失学了。为这事,小妹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母亲提起此事也是泪水涟涟,总说对不住小妹。
外爷是有工资的人,所以和外婆也就过着比较滋润的日子,几乎整天都在院子里和邻居打芝麻叶牌。大舅接班,教学在外;小舅娶了舅妈,没事俩人也去打牌,生的小孩也很幸福,肉吃得这一辈子看见肉就想吐。
我之所以写外婆家的事,妈妈之所以想写自传,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事。
外婆是个一辈子逞强好胜之人,外爷在世时仗着外爷的工资傲气,外爷去世后又仗着自己的存款傲气。小舅和小舅妈都是极老实极善良之人,只是有点懒散,都爱花钱,不太会过日子(当然,这都是外婆家有钱惯出来的)。外婆很生气,认为自己给他们钱了有资格管教,便经常对着舅妈指桑骂槐,时间久了,就和舅妈处得很僵。发展到去年,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外婆竟然拄着拐杖跑到舅妈娘家骂了一个村。自此,舅妈再也不搭理她。
外婆和儿媳处不好,便想住女儿家;住了女儿家,又不时地生事,不是嫌伙食不好,就是嫌女儿和她说话少。好不容易女儿闲下心来和她说说话,她不是数落舅妈的不是,就是旁敲侧击地给女儿讲例子,讲村里哪位老人靠女儿养老,女儿如何孝顺等等。母亲和姨也都算是老人了,操了大半辈子的心,现在也是儿女一大家子人,每天为儿为女的已很烦恼,所以听见外婆这样不体谅他们就有点不耐烦,免不了要顶撞两句,外婆就不高兴了,不是威胁要自杀,就是闹着要回家。这个倔强的老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不,前几天又和我小舅生气了,便拄着拐杖跑到我们村(两村有二三里地)。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开始讲起我小舅和舅妈的不好了,母亲不高兴听,说了外婆两句:“您老以为有钱就是功劳,实际是您的钱毁了两辈人(意思是小舅还有小舅的儿女)。”外婆一听大怒,拄着拐杖就走,父母亲怎样劝也劝不回。这下可好,外婆一路走一路见人就诉,说自己女儿如何如何不孝。母亲也是远近闻名的贤惠妇女,自然不怕外婆说什么,可母亲很伤心。
母亲说:“我从十三岁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结婚。结婚后你爹在工厂里发有粮票,我省吃俭用偷偷存下来拿回家给他们,不知给了多少次,不知给了有多少!最多一次我是缠在线疙瘩里的,有四百斤。养几只鸡下蛋,积攒几十个就给他们送回去,积攒几十个就给他们送回去。我那时瘦的已经不成人样了,你们也整天饿得嗷嗷叫。过个端午节,我打上俩鸡蛋,再兑一碗面,哗哗一搅,炒出来你们几个争着吃。就这个样,我拿回去的鸡蛋,你外婆从来没说不要。他们不种菜,我种的豆角北瓜,成箩头的拿回去让他们吃。他们没有腌鸡蛋的坛子,你爹从南阳拿回来一个,我又拎回去算他们的,那坛子又重又不好拿,我走一阵歇一阵,走一阵歇一阵。为你大舅盖房子,我送回去几袋粮食;为你小舅盖房子,你爹住在那里干活。算一算,我为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呀!可是你外婆是怎么做的?从年轻时起就不干活,到现在从没心疼过我这个当闺女的。你外爷有工资,你大舅又接了班,他们从未缺过钱。1985年你生病,花了一千多,你外爷送去350元,那是我偷偷塞给他们的,他一分钱也没多添。最伤心最伤心是你上大学那几年,家里穷得整天不吃肉,你们穿的都是旧衣服。你和你弟弟几乎都断了生活费。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整夜整夜流眼泪。
你外婆在干啥呢?在打牌!她的孙子孙女娇惯得连肉饺子都吃够,可她从来就看不到她这个女儿的难处。我现在已是六十多的人了,已是一身毛病不说,整天还为儿女们的事烦心,她还是不心疼我,还是要我来心疼她,要我去照顾娘家。你说我能怎么办?我真是心凉,心凉啊!这几天,我回忆起我这一生,心里像过**一样。我觉着我的经历真是能写一本书,所以我就试着想写几句了。这样写着,有了点事做,我心里还好受一点。”
说到这里,母亲的声音已有些哽咽。而我,早已是泪流满面。我的母亲,先是为她的娘家,现在又是为她的儿女,劳心劳力,从未考虑过她自己。现在,还住着旧房子,种着几亩地,我们做儿女的,不孝啊!最关键最关键,什么时候,做儿女的能把母亲的事写出来,编成书,遂了母亲的心愿?
唉,我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吧! 回答者: 薰衣草味小 这 1980 年 6 月我进入了 第二中心小学,开始了长达 16 年的读书历程。在小学六年中,我认真学习,争当先进,在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也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986 年 7 月,经过初考,以优异的成绩进入 一中的校园。初中三年,我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要求上进,努力当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1989 年 7 月,中考来临,由于准备充分,我继续升入 一中高中部升造。高中三年,我积极要求进步,并向校共青团递交了申请书,并于 1992 年 5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92 年的夏天,经过黑色七月的洗礼,我进入 大学资源工程系,实现了我的大学梦。在大学里,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在学好专业的同时,积极参与系学生会工作,担任系科协副主席。在系党委直接领导下组织开展了一些活动,使自己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的同时,也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定了。
四年后, 1996 年 7 月大学毕业,我分配到 办,一直至今。参加工作以来,我坚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每一件事,不管大事、小事。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转正以来已连续三年被评为 “ 优秀公务员 ” 。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我于 1997 年 6 月慎重地向 办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于 1998 年 6 月被 办吸收为建党积极分子, 2000 年 7 月经机关党工委批准,光荣地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2001 年 11 月经过 办党员大会讨论,一致同意通过我的转正申请。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以新的更大的成绩回报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和培养。 那个周六,我们回去看父母。摩托停在院门口,母亲来开院门,我看见她戴着老花眼镜,手里还拿着一支笔。我随口问:“妈,你在干啥?”“没干啥。”母亲回答。进了屋,又见母亲把一个本子随手往旮旯里一扔。我没再问她,却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拿起那本子一看,竟然是母亲在写自传。母亲文化水平不高,现在六十多了,居然拿起笔写东西,这让我感觉很有意思。我便在没人时悄悄笑问母亲。母亲见我发现了她的秘密,不好意思地笑,眼里竟然涌出泪花。
是夜,我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母亲满怀感慨地回忆起她辛酸坎坷的大半生,我认认真真地听着。其实,母亲已不是第一次讲她的故事,但,我从未像这次一样认真详细地听。
母亲属鼠,今年已六十二岁。母亲姐弟四个,姨比她小八岁,大舅比她小十三岁。小舅更小,小她十八岁。外婆是个爱干净、“爱生病”的人,大多时间喜欢躺在床上,不下田地,不做女红。我说外婆“爱生病”,并非是大不敬,单看她现在已八十八了仍精神矍铄,就可知她其实一直身体很好。母亲是老大,外婆“教女有方”,把她训练得勤快能干,自然,下边的三个弟妹都由她多付出喽,哄着玩就不说了,大舅小舅的衣服什么的都是妈妈做妈妈洗的。特别是小舅,棉袄棉裤棉靴全由妈妈一手操办。
外爷是个老实肯干却没有眼光的人,当了一辈子农村校长,却不知道重视教育,四个儿女没有一个上成学。母亲读书时成绩优秀,比同班的孩子年龄都小,但终因读书条件有限,只读了个高小就辍学了。
母亲辍学那年十三岁,开始下地挣工分。每天很早下地,很晚回家,稚嫩的双手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晚上和下雨天也很少歇着,还要纺棉花,还要做针线。
十八岁那年,母亲已出落成一个清秀稳重的大姑娘了,背上拖着两条又黑又长的大辫子,温柔善良聪明能干。曾经和大人一样到离家二十多里地的镇上去挑煤——挑了120斤的煤!而挑煤,在别人家那可都是男人干的活。十里八村的媒人轮番登门,母亲很羞涩,说自己还小,还要在家里多干几年活,等着妹妹弟弟长大,外婆喜得直夸妈妈懂事。从那以后,直到妈妈二十多岁,关于妈妈的婚事,外婆从不吐口。
在其他长辈的操心和张罗下,母亲终于在二十四岁那年,和父亲结了婚。结了婚的母亲,是我们村有名的巧手,家务活地里活,没有她不会做的。父亲那时在南阳工作,由于交通不便,很长时间回来一趟,所以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
母亲生了四个儿女。这四个儿女,让她的一生多了很多煎熬。
大姐一两岁时不知因为什么,动过一次小手术。
我是老二,更让母亲费尽了心。1985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为了我,母亲不仅求爷爷告奶奶筹钱,还要在医院伺候我。我呼吸困难,得坐着睡觉,母亲几乎就整夜整夜地坐在那里让我靠着她睡。为我治病,家里东凑西借,花了一千多元。那时候的一千多元,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无疑就是天文数字。许多人曾对我父母说放弃算了,但母亲态度坚决,毅然坚持。历尽辛酸,终于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现在还仍然记得我病好后医生对我说的话:“你捡回了这一条小狗命,以后可不要忘了你妈妈呀!”
我的弟弟,小时候由于没人照看,经常地哭,得了疝气,又让母亲受尽熬煎。
1982年,小妹出生,计划生育罚款,又让一家人的生活喘不过气来。
好不容易日子过得好些了,子女却大了,要考虑他们的前程了。1994年,我们市里的丝织厂招工,父母为了大姐的前途,咬咬牙花了2000元为大姐买了个工。1995年,我考上大学,需要学费和生活费。1997年,弟弟接了父亲的班,也需要交一大笔钱。就在这一年,我们家厨房倒塌,又新盖了厨房,花了一两千块钱。厨房建完,奶奶又去世了,可真是“雪上加霜”。我不知道这两年母亲是怎样过的,我只知道我在学校里是特困生,经常自卑得抬不起头来。我还记得那年春节我去姨家,姨给了我四百元钱,说一百是压岁钱,三百算借我的,等我参加工作后还她就是。我把这钱拿回家了,母亲却又还给了姨,连压岁钱也还了。这事现在我想起还有点生母亲的气。
终于我参加工作了,小妹又到考高中的时候了。家里拮据,父亲一心让小妹退学,酷爱读书的小妹很不愿意。母亲当然支持小妹,但架不住父亲整天地吵,终于,小妹失学了。为这事,小妹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母亲提起此事也是泪水涟涟,总说对不住小妹。
外爷是有工资的人,所以和外婆也就过着比较滋润的日子,几乎整天都在院子里和邻居打芝麻叶牌。大舅接班,教学在外;小舅娶了舅妈,没事俩人也去打牌,生的小孩也很幸福,肉吃得这一辈子看见肉就想吐。
我之所以写外婆家的事,妈妈之所以想写自传,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事。
外婆是个一辈子逞强好胜之人,外爷在世时仗着外爷的工资傲气,外爷去世后又仗着自己的存款傲气。小舅和小舅妈都是极老实极善良之人,只是有点懒散,都爱花钱,不太会过日子(当然,这都是外婆家有钱惯出来的)。外婆很生气,认为自己给他们钱了有资格管教,便经常对着舅妈指桑骂槐,时间久了,就和舅妈处得很僵。发展到去年,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外婆竟然拄着拐杖跑到舅妈娘家骂了一个村。自此,舅妈再也不搭理她。
外婆和儿媳处不好,便想住女儿家;住了女儿家,又不时地生事,不是嫌伙食不好,就是嫌女儿和她说话少。好不容易女儿闲下心来和她说说话,她不是数落舅妈的不是,就是旁敲侧击地给女儿讲例子,讲村里哪位老人靠女儿养老,女儿如何孝顺等等。母亲和姨也都算是老人了,操了大半辈子的心,现在也是儿女一大家子人,每天为儿为女的已很烦恼,所以听见外婆这样不体谅他们就有点不耐烦,免不了要顶撞两句,外婆就不高兴了,不是威胁要自杀,就是闹着要回家。这个倔强的老人,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不,前几天又和我小舅生气了,便拄着拐杖跑到我们村(两村有二三里地)。第二天吃过早饭,又开始讲起我小舅和舅妈的不好了,母亲不高兴听,说了外婆两句:“您老以为有钱就是功劳,实际是您的钱毁了两辈人(意思是小舅还有小舅的儿女)。”外婆一听大怒,拄着拐杖就走,父母亲怎样劝也劝不回。这下可好,外婆一路走一路见人就诉,说自己女儿如何如何不孝。母亲也是远近闻名的贤惠妇女,自然不怕外婆说什么,可母亲很伤心。
母亲说:“我从十三岁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结婚。结婚后你爹在工厂里发有粮票,我省吃俭用偷偷存下来拿回家给他们,不知给了多少次,不知给了有多少!最多一次我是缠在线疙瘩里的,有四百斤。养几只鸡下蛋,积攒几十个就给他们送回去,积攒几十个就给他们送回去。我那时瘦的已经不成人样了,你们也整天饿得嗷嗷叫。过个端午节,我打上俩鸡蛋,再兑一碗面,哗哗一搅,炒出来你们几个争着吃。就这个样,我拿回去的鸡蛋,你外婆从来没说不要。他们不种菜,我种的豆角北瓜,成箩头的拿回去让他们吃。他们没有腌鸡蛋的坛子,你爹从南阳拿回来一个,我又拎回去算他们的,那坛子又重又不好拿,我走一阵歇一阵,走一阵歇一阵。为你大舅盖房子,我送回去几袋粮食;为你小舅盖房子,你爹住在那里干活。算一算,我为这个家我付出了多少呀!可是你外婆是怎么做的?从年轻时起就不干活,到现在从没心疼过我这个当闺女的。你外爷有工资,你大舅又接了班,他们从未缺过钱。1985年你生病,花了一千多,你外爷送去350元,那是我偷偷塞给他们的,他一分钱也没多添。最伤心最伤心是你上大学那几年,家里穷得整天不吃肉,你们穿的都是旧衣服。你和你弟弟几乎都断了生活费。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整夜整夜流眼泪。
母亲总是伟大的,我所知道的一些农村母亲,能写东西的如实很少。可能是受文化影响,很多人根本就没机会享受更多的文化教育。作为子女的我们,如果爱好写作,能把母亲的一些事迹写进自己的文章,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无声报答。
粉丝群组滚滚红尘中一普通女,蒙春风雨露之滋润成长,怀热情感恩之心态处世。曾以物喜,也以己悲,故成就不了大业,更做不了女中豪杰,实俗世中一小女人也。
然而这小女人有喜,有泪,有梦,喜泪皆在文中生,化成幽幽文学梦。文学梦支撑,觉得这世界花香月明,人爽风轻;文学梦不醒,心理年龄较轻,待人处事常不设防,为人太过直诚。
写过小说,写过剧本。并非想“在文学这棵树上吊死”,心性使然,文字给了我心灵栖息的家园,满足了我表达倾诉的欲望。
编辑推荐作品
顺便问一下,你是谁? 回答者: 1317594068 | 二级 | 2011-2-26 14:39
1996年初冬的一个凌晨,随着一声婴儿的哭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降临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里。
我的名字叫郑艺。你别看它听起来普通,意义可大了呢。之所以我有正义感,是应为跟正义同音;之所以我跟**姐吵架,是应为跟争议同音。
瘦是男孩们畏惧的事情,可我的身体偏偏就是瘦,所以四五年级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叫我“小不点”其实我个子又小又矮。妈妈让我多吃饭,可我依然是每顿只吃一点点。我妈妈常说我还没有老家的小狗吃得多呢==我真后悔不听妈妈的话多吃饭,要不然能长这么矮吗?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可是我现在长dé有点胖了。
听妈妈说,第一次进幼儿园的大门,我感到既高兴又害怕。当听到妈妈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时,我哭着闹着不让妈妈走。妈妈只好骗我说她在大厅立等我。结果放学后我没见到妈妈,又大哭大闹起来。
转眼之间,我已经步入了小学的大门。在二小里,让我学到了许多新的内容,开阔了眼界,结识了更多的好朋友。在四年级时,我转学了。在深圳的学校里,我又学到了新的知识,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五年级时,我又转学了,转回二小。
不知为什么,调皮的我爱上了读书,不过那时读得都是一些故事书,似懂非懂。虽然我酷爱文字,却无文采,喜欢读书,却过目便忘。不管在学校学习还是在家里娱乐,我常用笑话来制造欢乐的气氛。
我的理想是走进北大。我相信,在我的努力和老师、父母的教育下,我一定会实现我的理想,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和老师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