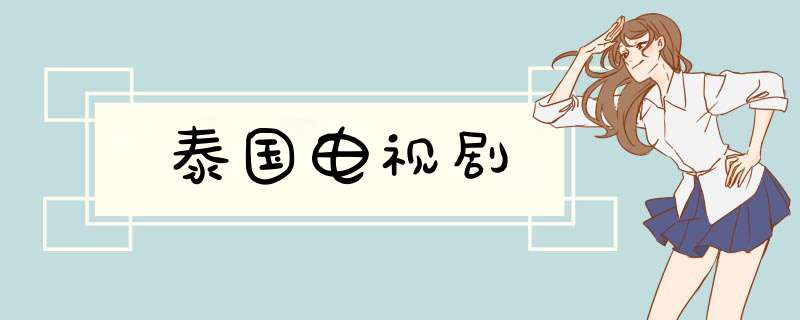
应该是《甜心巧克力》,中央8套播出过 巴迪潘·巴塔威甘MOS,拼塔安(AOM)
剧情是:阿淳(MOS饰)是一位家境富裕的贵公子,家族经营酒店生意。阿淳从小和莎莎一块长大,某日他将求婚戒指放入精心准备的蛋糕中,没想到被莎莎误食,求婚未成莎莎还被送进了医院。此时他觉得两人的感情已不像往日(莎莎劈腿另有男友),心生冷意之时正好父亲安排其去瑞士学习,以便日后打理生意。在瑞士,阿淳遇到了因男友屡次出轨而远走他乡的酒店女招待阿婉(AOM饰),两颗孤独受伤的心互生好感。 回国后,两人进展得不太顺利,除了有莎莎的百般阻挠外,阿婉自身也对这段感情也缺乏信心,于是以怀了朋友孩子(孩子是阿淳的)为由离开了阿淳。几年后,两人再次相逢,阿淳发现阿婉的孩子如自己一样对巧克力过敏,由于判定这个小孩是自己的,他深爱阿婉的心一直未变,阿婉不再压抑心中的爱,把实情全盘托出,一家人最终如同甜心巧克力般走到了一起。
剧中的小男孩不是对花生过敏,是对巧克力过敏
又到情人节,“爱与亲密”的话题兜兜转转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年复一年借节日之名获得数不胜数的叙事关注。尽管2月14日的圣瓦伦丁节源自基督教传统,爱情的感召力及其极富煽 彩的特质却能够跨越不同的文化语境,使其从私领域中出走至大众视野。爱是命定的天赋,在亲密爱、 、人 、公共爱的交迭对话中丰富其内涵;爱亦背负了历史和文化的重担,它之所以成为人们创作与研究的重要母题之一,正是因为它以内在于语言的形式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验绑定在了一起。
人们对于爱情主题的文学影视作品并不陌生。今天,我们希望这里呈现一些谈论爱的另类视角:博物馆与艺术馆中的展品如何能够成为凝结的爱的意象?艺术家们对当代爱情有哪些观察与思考?爱情能否与更具公共性的社会关怀相联系?
亲密是爱。云图映画联合今日美术馆推出了“爱的艺术:亲密”全球影像艺术大展,展览于2018年11月24日至2019年2月24日在今日美术馆2号馆展出,以视觉媒介的形式呈现当代艺术家对亲密关系的热切思考与积极探索。展览既涵盖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草间弥生、小野洋子等颇负盛名的艺术家的作品,她们从女性体验情感的角度出发,以大胆创新的行为表演与艺术装置探索“爱”的多元表达形式。同时,该展览也展出了一组实验性与未来感十足的影像作品,旨在讨论社交网络、虚拟空间与消费主义对亲密关系的形塑,作为对当代无数新型亲密形式的回应与反思。
心碎亦是爱。2018年6月,世界第一家、也是最负盛名的克罗地亚心碎博物馆在上海迎来了它的第50场全球巡展,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慕名前去,这也是它首次来到中国办展。坐落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市上城的这家心碎博物馆诞生于2006年,拥有世界各地失恋者捐赠的1000多件展品,并在2011年被授予“欧洲最有创意博物馆奖”。心碎博物馆的联合创始人奥林卡·维斯蒂卡和德拉任·格鲁比希奇原是一对情侣,在分手之际萌生了一个“安放曾经亲密无间、千金难买的记忆”的想法。以更富有诗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已然结束的恋情,这是他们创办心碎博物馆的初衷。
克罗地亚的心碎博物馆
2011年,心碎博物馆的同名官方出版物《心碎博物馆》上市,书中收录了200件藏品,每一件藏品的旁都附有捐赠者的说明文字,讲述此件展品背后的故事。去年10月《心碎博物馆》中译本面世,将200个“人类失恋心理学研究标本”呈现到中国读者面前。
亲密关系的当代形式:情欲碎片与心碎物品
情书、情诗、当面告白,人们习惯于且偏爱以文字和语言传情,这是因为它能较为直观地传达表白者的心意,也是人们默认的正统交流方式。而将抽象暧昧的情感转译为声形俱备的语言也并非一件容易的工活,更何况情感的曼妙之处往往在于其难以诉之于口的特性,不过这番劳累也是恋爱者乐意承受的甜蜜负担。表达情感的方式与承载情感的媒介也因时代的变迁、地域的区隔、风俗的流变等变换不同的面目,就算是最基本的文字传播,也不再仅限于在纸笔之间做文章。在当代,数字媒体技术、社交网络与人工智能都参与了这场情爱的转译活动,也使得现代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更为多元立体。“爱的艺术:亲密”中的诸多展品都展现了这份裹挟在亲密关系中的现代性。
独白剧场(Monologue Theater)展出了翠西·艾敏的作品系列《承诺爱你》。将霓虹灯作为表达媒介是翠西·艾敏典型的创作风格,这也造就了她对情爱语句的另类书写。《承诺爱你》由数块电子屏幕组成,每一块屏幕上都有一句经典的表白话语,比如“When I hold you, I hold your heart”,“Love is what you want”,“I listen to the ocean and all I hear is you”。霓虹灯管被弯曲成手写字体的模样,拼接出了这些与爱相关的感受和思想。与《承诺爱你》有着相似呈现方式的,还有刘诗园的视频装置作品《情诗》。该作品将九首来自各个国家的古今爱情诗歌的诗句打乱,再重新拼接为一首高度抽象的冗长诗歌。这首长诗被翻译为十三种语言,以视频滚动播放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尽管这首被重组的诗歌读来并没有连贯的叙事与深刻的含义,但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它在述说关于爱的故事。
翠西·艾敏的作品《承诺爱你》
刘诗园的视频装置作品《情诗》
这些告白的话语和情诗就像爱一样,就其本质而言,既令人困惑,又有一种凝聚的力量,正如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反复剖析的爱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我爱你,这一具体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呼唤本身。”作为结构主义者的巴特将恋爱体验与恋人之间的情绪故事演绎为语言的蒙太奇游戏,用极富象征意味的符号描绘了诸多经典的恋爱情境。而当语言负荷了过载的情绪能量之时,它也导向了模糊不清的情爱路途。
《恋人絮语》
[法]罗兰·巴特 著 汪耀进 武佩荣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7
程然的录像装置作品《信》在未来剧场(Future Theater)展出。该作品由刘嘉玲演绎,呈现了一个艳丽女子的心事独白,她穿梭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向观众诉说一些朦胧的心迹与真假参半的回忆。刘嘉玲独白内容的灵感来自于程然收到的一封包装成 邀请函的欺诈邮件,其中充斥着挑逗的语句和暧昧的邀约。图像强化了文字的表现力,借由演员的自述表演,杂乱无序的文字自然地拼接为一个立体的女人影像——寂寞、神秘又充满诱惑力。她既是都市人对于情欲形象的惯性想象,又映射了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复杂联系。
程然的录像装置作品《信》
除了语言文字,物品也是承载感情的重要媒介。《心碎博物馆》的藏品就展现了人们将抽象的亲密关系实体化的诸多尝试。比如一张写着“Pay attention to me”的纸条、一双不合脚的红色运动鞋、一款同时送给妻子与外遇对象的海龟挂坠。奥林卡·维斯蒂卡在《心碎博物馆》的引言中写到,他们希望心碎博物馆成为所有逝去的、痛苦的爱情记忆的保险柜。尽管有形之物终会消散,但总比人转瞬即逝的感情与似是而非的回忆靠谱,这也是为何许多人会在恋爱时互赠物品、将它们视作感情的确证和依托的原因。物品作为感情的能指而拥有了意义,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它甚至扮演或替代了感情本身。
《白色绅士鞋》:“我很开心,再也不用时不时穿上这双白色绅士鞋来取悦她了。”
因此,维斯蒂卡与格鲁比希奇试图通过“展示”这些物品,帮人们完成“告别这段感情”的仪式。但心碎博物馆的别出心裁之处,或者说颇具当代性之处,在于创始人将所有物品统一在了“失恋”、“心碎”的主题之下,以一种庄严的方式来纪念一段不完美、痛苦甚至是毁灭性的人生体验。对“大团圆”故事与完美叙事体的破除,也映射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某种思潮:以直面的姿态对待残缺但真实的生活图景。作为构筑对特定群体有意义的生活秩序和集体身份的文化性机构,博物馆对“心碎”面向的选择和参与者的积极反馈,也反映了“肯定苦难”与“重新开始”在当代价值观念中的重要性。
《心碎博物馆:人类失恋心理学研究标本》
[克]奥林卡·维斯蒂卡 德拉任·格鲁比希奇 著 王绍祥 译
未读·文艺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0
身体与在场:爱与艺术成为艺术家的生命本身
爱将人与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要求参与者全身心的投入与专注,在“爱”自身的话语框架中保持“在场”状态。但现代工作生活的快节奏使得“爱”的时间成本显得如此高昂,与此同时,正如程然的作品《信》所揭示的,虚拟经验与真实情感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且难以分辨,“爱”似乎也成为了若即若离、飘忽不定的闪烁存在。“将时间与爱可视化,”这是塞尔维亚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面对这场“爱的危机”所给出的回应,通过这场活动,她也在探寻爱之于自身的意义。
2010年春夏之交,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行了大型回顾展“Marina Abramovic: The Artist Is Present”(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她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艺术家在场”行为艺术项目的表演。在展览进行的三个月里,阿布拉莫维奇每日都会坐在一把木质椅上,等待观众轮流坐到她的对面。双方都被禁止通过语言或肢体动作交流,只能够通过对视的方式接触。报名参加这场行为艺术实验的人不计其数,还有无数特地从大洋彼岸赶来的参与者,围观的人也总是把场地堵得水泄不通,许多观众在短暂的沉默对视中感动落泪。此次展览的 莫过于阿布拉莫维奇与其前情人兼艺术搭档乌雷的重逢,二十余年未联络的两人在木桌的两端以泪水与紧握的双手达成了和解。纪录片《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跟随记录了此次展览的全过程,并回顾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之间的爱恨故事。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在“艺术家在场”的表演上重逢
“爱的艺术:亲密”永恒剧场(Eternity Theater)为观众们呈现了这部纪录片,同时该展览也收录了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年轻时共同制作的两部行为艺术影像作品《剩余能量》与《恋人:长城徒步》。两人相遇所带来的火花和艺术能量极大地丰富了他们作品中的情感张力,并使得“爱与亲密”的母题与他们一生的艺术创作紧密缠绕。《剩余能量》以身体对抗的方式展示了亲密关系的脆弱、不确定性和关系给双方带来的恐惧与创伤;《恋人:长城徒步》则更像是一场告别仪式——两人分别从山海关与嘉峪关出发,花了三个月走向对方,在陕西二郎山相遇后,两人拥抱挥别,从此不再联络。
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共同创作的作品《剩余能量》
对于阿布拉莫维奇而言,爱既是艺术表达的话题,也是艺术创造力的源泉。她在纪录片中表示,她的身体是她工作的主题、对象和媒介。她不仅以挑战生理极限的行为探索两性关系的边界,还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创造了一个“爱的空间”。在她看来,“艺术家在场”的意义在于任何坐在她对面的人都能够和她产生直接、独特且紧密的联结并得到关注和尊重,这是对一个速度太快的世界的抵抗,她要求人们慢下来。阿布拉莫维奇和参与者在沉默注视中互相给予的无条件的爱与注意力,给她带来了“不可思议的轻盈与和谐的神圣感”。在这些冒险式、实验式的创作实践中,爱与艺术都成为了艺术家的生命本身。
宏大之爱:超越私密情感的社会力量
爱之于个人的意义纷繁变幻,对于《心碎博物馆》展品的捐赠者而言,爱是一场回味无穷的情欲体验或一份稳定熨帖的精神支持;在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眼里,爱与艺术相伴常在。但爱是否是独属于私密领域的个人体验?它是否拥有更为普世的意义?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发明了“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一词,强调未定型的社会意识与过程中的鲜活经验——我们所体验的人类感情不全然是“主观感性”的结果,也受到具体社会经验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不同于严谨的学术分析,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爱的人们与艺术家们以一种更直观、更具美感的方式阐释了爱的社会性意义。
狗项圈灯、弹簧床垫、从胫骨里取出的螺丝钉、伽利略温度计、填字游戏……《心碎博物馆》中的展品既有平淡无奇的,也有荒诞怪异的,但每一件展品都有着共通的特性:不事修饰地讲述某次极其私密的感情体验。它们展现了过去一百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真实生活的瞬间,也反映了这些人们所处时代的政治、伦理和社会问题。
怀着“无私的爱能够改变世界”的想法,小野洋子与约翰·列侬曾将1969年的蜜月旅行转化为一场反战行动。彼时越战已持续14年。两人先后在阿姆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和蒙特利尔的伊丽莎白女皇酒店举行了“在床上”(Bed-in)行动,旨在宣传“ 不作战”(Make love, no war)。这是一场空前未有的行为艺术表演,行动持续期间,这对夫妇穿着睡衣在床上与媒体、政客、粉丝等各类人群会面,谈论人权与战争等议题。
小野洋子与约翰·列侬的“在床上”反战行为艺术表演
这场行动的影像记录《床上和平》(Bed-in for Peace)也在“爱的艺术:亲密”行动剧场(Action Theater)展出,展览还重现了这场表演发生的场景——一间贴满反战标语的酒店房间内,一张摆放着乐器与鲜花的大床。纪录片中,列侬将他们看似偏激的行动定义为一次日常性的尝试:“就像卖肥皂,会有人说这没有用,那么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你能做的有用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尝试过和平,所以默认暴力是唯一的途径。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和平和暴力是不一样的。”48年后,小野洋子再度回忆起她与约翰·列侬共同发起的“在床上”行动,坦诚承认“1969年,约翰和我都太天真了”,但她同时也相信, “这个影片是有力量的,我们当时说的话,现在也可以被听见。”这封独白信同样也作为一件展品被收藏展出。对和平与善意的信仰和追求使得爱情不再局限于一份私密情感,而转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反战的社会潮流相结合的爱,拥有了更为多元的公共面向。
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众的目光中,是1988年。那一年,她和自己的恋人、艺术合作人乌雷分别从山海关和嘉峪关出发,相向徒步长城。经过三个月的行走,两人最终相会,拥抱在一起,宣布结束长达12年的恋情。这个作品名叫《情人•长城》。它真是个绝妙的暗喻:一对恋人在长途跋涉的相会后,迎来的,却是爱情的结束。号称“行为艺术老奶奶”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她的爱情和艺术缠绵不休,也因此惊世骇俗……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于1946年生于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从小就受到压抑式教育,甚至经常挨打,被忙于革命的父母所忽视,因此敏感而脆弱。但同时,她的母亲丹妮卡为她安排了很多文化课程,学习法语和英语,去古典音乐厅、歌剧院、俄国芭蕾舞团,甚至在12岁那年去了威尼斯双年展,看到了众多激进的新材料艺术作品。她开始对绘画产生极大的兴趣,并因此获得母亲给予的一间工作室。
也许是童年经历和性格决定了阿布拉莫维奇后来的创作风格,她最终走了叛逆传统艺术的道路。阿布拉莫维奇虽然毕业于贝尔格莱德美术学院,受的是苏派美术教育,但她开始尝试用传统的技法画一些极端的题材,比如车祸现场的暴力性和即时性。之后,阿布拉莫维奇和几个同学组建了一个艺术小团体,并逐渐接触行为艺术。
阿布拉莫维奇长期居无定所,四海为家,先后旅居德国、荷兰、巴西、美国等地,是标准的“国际公民”。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探索,她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从1970年代开始,阿布拉莫维奇利用自己的身体创作,通过制造险境及各种自残的手段进行有关身心极限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节奏系列”(Rhythm)。她将自己置身于浓烟烈火之间的木质五星围栏中直至烧伤昏迷、濒临窒息,最后被抢救出来(《节奏5》Rhythm 5, 1974);或者服用下大量的精神类药物,在身体和意识陷入混沌之后等待缓慢复苏(《节奏2》Rhythm 2, 1974)……而最著名的一次行为艺术表演,是1974年的《节奏0》,她首次尝试现场互动。观众可任选包括枪、菜刀、鞭子等72种危险道具,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阿布拉莫维奇不作任何反击。直到有人用上了膛的手枪顶住了她的头部,她才流出了眼泪……
在这些极端的作品中,她像一个被遗忘的孩子,通过不断弄出声响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她一辈子都在求关注,各种极端的行为艺术,相当于小时候干坏事吸引大家的目光,得到关爱。或者,她希望寻找到一种生命的平衡,可这平衡又在哪里?或者,她一直在等待,那个叫乌雷的男人的出现。
1975年,29岁的阿布拉莫维奇遇到了乌雷(乌维·赖斯潘),从此在爱情和艺术上都改变方向。而也因为乌雷作为她艺术上的合作伙伴,使她的爱情和艺术一直缠绵不休。爱情的开始,带来艺术上的改变,而爱情的终结,也必将让她的艺术之路从此颠覆。
据《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传》(金城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詹姆斯·韦斯科特著)里的详尽描述,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在一次节目中相遇,乌雷被安排作她的助手。而在节目后的聚餐上,两人发现彼此的生日都是11月30日,而且日记本上的那一页都被撕去。他们都憎恶的自己的生日!神奇的缘分将他们拉到了一起。这期间,阿布拉莫维奇本有一个丈夫内沙·帕利帕维奇,但他们更像一对不居住在一起的朋友。
在跟乌雷热情的缠绵之后,阿布拉莫维奇回到贝尔格莱德,更加感觉到故乡的压抑。她感觉自己像呆在监狱,每天躺在床上给乌雷打电话。重新回到从前的艺术圈子,进行新的创作,可她一点不开心,在煲了无数的电话粥之后,他们相约再见一面,地点定在布拉格,阿姆斯特丹和贝尔格莱德中间的一个城市。他们在这里决定正式在一起,并准备了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写上两个人的名字。热恋中,他们合作了第一件作品。阿布拉莫维奇决定搬到阿姆斯特丹去,跟乌雷同居。
两人开始合作实施一系列与性别意义和时空观念有关的双人表演的作品。他们共同创作的作品主题鲜明,影响广泛。其中的一些作品被命名为“关系系列”,如:《空间中的关系》、《移动关系》《时间关系》《劳动关系》等,表演的地点则横贯欧洲的多个国家,参加了包括卡塞尔文献展、巴黎双年展、科隆艺博会在内的多种艺术活动。在《空间中的关系》作品中,他们赤裸着身体,在20米开外相对奔跑,让裸体撞击在一起。在无数次的撞击中,阿布拉维莫奇甚至跌倒在地。这种看上去像互相伤害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彼此的信任。
两人的关系犹如异首同躯的联体生物般难以分割。为了在一起创作行为艺术的理念,他们买了一辆雪铁龙篷车,把所有东西都搬了进去,生活在里面。他们开着车在欧洲旅行,一起创作行为艺术。
他们创作了一个名为《休止的能量》的作品,两人各持弓和箭的一头,倾斜站立,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麦克风放大着两人逐渐加快的心跳和乌雷不均匀的呼吸声。行为持续了四分钟,如果乌雷有一秒钟不专注,箭头就会刺入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这种高强度的“信任”除了更多的艺术意味,似乎也在无限“升华”他们的感情。热情和压力并存,绷得太紧的爱情之绳,正在带来阴影……
谁也没想到。这对看上去无比般配的艺术家情侣,却渐行渐远。1984年,阿布拉莫维奇有了外遇。
在遭遇阿布拉莫维奇之前,乌雷是使用照片来进行行为艺术作品的,一度是宝丽莱公司的顾问。他用拍立得拍下自己的自残照片,令人震惊。在与阿布拉莫维奇走到一起之后,他们开始合作完成一些作品。但是,阿布拉莫维奇逐渐成为驰名世界的顶尖艺术家,游走于各种社交场合,而乌雷更多时候成为一种陪衬。
更多的矛盾开始出现。1982年,他们在一些作品中做禁欲试验,此后,乌雷因为患疝气进行治疗。两人不再有性生活,交流渐次疏远。这种生活给阿布拉莫维奇带来乏味感。1984年,阿布拉莫维奇到旧金山艺术学院授课,遇到了罗宾·温特斯,他们在艺术上进行合作,并走到了一起。这是一次背叛。但乌雷奇怪地原谅了她。阿布拉莫维奇再次无可救药地回到乌雷身边。
但是,到了1987年,他们终于遭遇了更为严重的现实。乌雷的儿子马克·亚历山大冒了出来,又冒出一个名叫朱利安的15岁儿子来。朱利安的出现,成为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关系的最后一击。因为从1975年相遇以来,乌雷一直隐瞒了这些真相。
阿布拉莫维奇认为自己根本不了解乌雷。他们一起相爱、生活,完成艺术作品,彼此完全信任,她认为他们应该是一种心灵相通共生关系,但乌雷隐瞒了自己最重要的秘密。
他们开始公然在客人面前争吵,甚至在对作品的处置上,比如是否出售,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为他们要准备徒步长城的经费。之前禁欲时期短暂的外遇和背叛,再度被提起。
徒步长城的计划已经准备很久,虽然貌合神离,他们还是必须一起去完成。这注定成了这对艺术情侣12年关系的最后一站。
1988年3月30日早晨,《情人·长城》开始,阿布拉莫维奇登上山海关,向西行走。而乌雷在同一时刻登记上戈壁滩中的嘉峪关,向东行走。这种相向的徒步行走,施行者又是一对情侣,难免让人产生过度升华的,关于爱情的联想。但只有他们自己清楚,这次相遇的仪式,将不是他们爱情的高潮,而是结束。
在经过90天的跋涉之后,他们筋疲力尽地在陕西省神木县二郎山的一条布满道、佛、儒三家庙宇的峡谷里相遇。他们互相拥抱,却一点不像**里的浪漫画面。阿布拉莫维奇泪流满面,那么温柔、小巧地缩在乌雷的怀里。可是,他们分手了。
这让世人感觉惊诧不已。直到很多年之后,乌雷的一个女性朋友问他:“你为什么跟阿布拉莫维奇分手?她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人。”乌雷回答:“我想我没那么多魅力。”
当爱情被打上文艺范儿的光环时,总是给人过于浪漫的幻想。但事实上,所有的爱情在遭遇世俗困境之后,都会变成一地鸡毛。传奇而叛逆的阿布拉莫维奇也不能例外。
分手之后,乌雷拿走了他们早期共同创作的所有物件、影像与底片,阿布拉莫维奇不得不为使用这些材料而付钱。此后多年,他们都在为这些档案的保管和使用争吵不休。
阿布拉莫维奇只好中止了“二人组合”,开始单独面对公众,独自完成作品。她一度有众多男朋友,跟很多人发生关系。这些男朋友分布在欧洲各地,他们坐飞机见面,或者通过传真信件调情。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彼此都认为自己在12年的关系中受到了伤害,是受害者,糟糕得不能再糟糕。
在与乌雷分手差不多十年左右,她与艺术家保罗·卡内瓦里相识,并最终走到一起。2006年,阿布拉莫维奇与保罗举行了世俗的婚礼。她已经快60岁了,终于找到安全感,或者说是——爱情的归宿。保罗在自己的左臂上刺上了阿布拉莫维奇的名字。也就是在这时候,阿布拉莫维奇突然想到:“如果我还年轻,我们应该有一个孩子。”她感觉到了没能成为母亲的遗憾。
看上去,阿布拉莫维奇正在回归世俗。另一方向,她更加擅长社交,光芒四射。有人说,事实上,阿布拉莫维奇有了越来越多的媚俗的一面。但于艺术而言,这很难界定。
2010年,阿布拉莫维奇在纽约现代美术馆进行作品“艺术家在现场”的表演。这场行为艺术持续736小时30分钟,过程中,成千上万观众被邀请轮流坐在阿布拉莫维奇对面,静静地看着她的眼睛。1500位陌生人中,有些人甚至接触她的目光不过十几秒, 便宣告崩溃,可阿布拉莫维奇却没有一丝情绪流露。但是,乌雷也来了,坐到她对面。阿布拉莫维奇没能继续保持无动于衷,而是与乌雷握了手。这是在阿布拉莫维奇之前表演中从未出现的境况,强烈感情的冲击与回忆使她当场潸然泪下。
阿布拉莫维奇曾说:“一位艺术家要避免爱上另一位艺术家。”而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她却说到:“我的艺术宣言充满了矛盾。我人生中最至爱的两个人都是艺术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避免爱上别的艺术家。”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12年的合作与爱情,被称为旷世奇恋,也是一场与艺术缠绵不休的爱情。或者,正是因为艺术家锋芒毕露的才华,让他们彼此刺伤了对方。要避免爱上别的艺术家!可是,除了爱上更加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爱情又到何处去寻觅?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