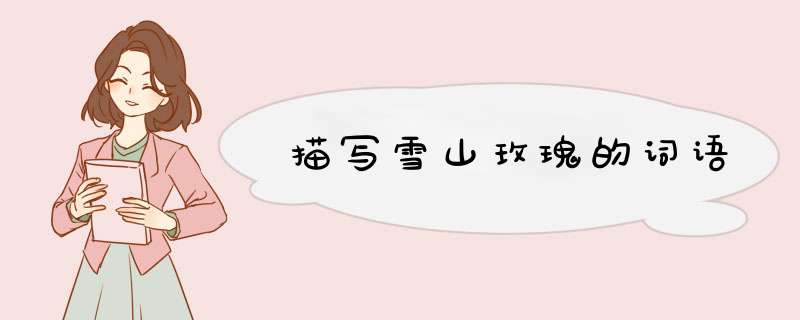
1雪山玫瑰花语,送雪山玫瑰有哪些寓意
雪山玫瑰代表着我与你圣洁清新的爱。
雪山玫瑰是白玫瑰中的一种,花色为淡绿与纯白之间,雪山玫瑰是白玫瑰中的高档品种,也是较新的品种,英文名字叫做Avalanche,在我国云南和台湾有生产。
未全开放的雪山玫瑰,花瓣紧凑在一起,层层包容很有内涵。象征着纯洁、高贵、天真,淡绿色调在话语中又有钟情于你及青春常驻之寓意。
雪山玫瑰与不同的鲜花搭配所代表的寓意:
19朵雪山玫瑰+叶上花+灰足球
19朵玫瑰寓意期待和忍耐。
在有的人看来,爱情是神圣的,是不容亵渎的。只不过,当爱情陷入现实,就会慢慢的改变原本的容颜,会变得世俗起来。于是,纯真的爱就了一种回忆或者期待,留在青涩懵懂期的美好,一直会有的期待。
花语:“聘聘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最美好的爱,往往发生在青涩懵懂的时光。不知爱为何物,可就是恋恋不忘。
鲜花/帕巴拉的爱
16朵雪山玫瑰+叶上花+小果实
16朵玫瑰代表爱的最高点。
有的爱,纯洁、高贵,只不过大多被憧憬,从未遇到过。所以,就有了各种美好的传说。传说里,帕巴拉是藏民心中圣洁的地方。那么,帕巴拉的爱也就是传说里最圣洁的爱,爱到最高点的爱。
花语:传说,帕巴拉位于香格里拉,是西藏戈巴族人世代守护着的圣洁的地方,是人们的梦想所在。就好像我们都会期待至真、至纯的爱情。
鲜花/青春派
6朵雪山玫瑰+1枝紫色绣球花+3枝白色乒乓菊+中国桔梗+叶上花+灰足球
6朵玫瑰的花语是愿你一切顺利。
把祝福、希望和美满都盛放在粉色的盒子里;盒子打开,满满的幸福和浪漫弥漫开来,弥漫出一个爱的世界。青春,就是这般美好!
花语:《青春派》是一部**,演绎了90后的青春生活,有疯狂的追求,有甜蜜的初恋,更有刻骨铭心的感动。爱,就应该如青春一般沸腾!
2描写雪山的好词好句,多多来玉龙雪山不仅气势磅礴,而且秀丽挺拔,造型玲珑,皎洁如晶莹的玉石,灿烂如十三把利剑,在碧蓝天幕的映衬下,像一条银色的矫健玉龙横卧在山巅,作永恒的飞舞,有一跃而入金沙江之势,故名“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不仅巍峨壮丽,而且随四时的更换,阴晴的变化,显示奇丽多姿。时而云蒸雾涌,玉龙乍隐乍现,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神态;时而山顶云封 ,似乎深奥莫测;时而上下俱开,白云横腰一围,另具一番风姿;时而碧天如水,万里无云,群峰像被玉液清洗过一样,晶莹的雪光耀目晃眼,具有“白雪无古今,乾坤失晓昏”的光辉。
即使在一天之中,玉龙雪山也是变化无穷:东方初晓,山村尚在酣睡,而雪山却已早迎曙光,多彩的霞光映染雪峰,白雪呈绯红状与彩霞掩映闪烁,相互辉映;傍晚,夕阳西下,余辉映山顶,把雪峰染抹得象一位披着红纱中的少女,亭亭玉立;月出,星光闪烁,月光柔溶,使雪山似躲进白纱帐中,渐入甜蜜的梦乡,显得温柔、恬静。 终年积雪的山峰由北向南排列成十三个高峰,在蔚蓝的天幕衬托下,宛如一条玉龙凌空飞舞。
当你沿此旅游线深入其中,雪山会展现给你奇花、异树、雪海、冰川、草甸、溪流等无限风光,还有那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会让你一路留连忘返。 “郡北无双岳,南滇第一峰。
四时光皎洁,万古势龙从。绝顶星河转,危巅日月通。
寒威千里望,玉立雪山崇。”这首五言八句诗是明朝丽江第八代土知府木公(公元1494--1553年)土司写的《题雪山》,诗句豪迈。
丽江玉龙雪山自古就是一座壮美的风景雪山,唐朝南诏国异牟寻时代,南诏国主异牟寻封岳拜山,曾封赠玉龙雪山为北岳,至今白沙村北北岳庙尚存,仍然庭院幽深,佛面生辉。拜山朝圣者不绝于途。
3描写雪山的成语描写雪山的成语 :
天寒地冻
[tiān hán dì dòng]
形容天气极为寒冷。
人迹罕至
[rén jì hǎn zhì]
罕:少。人很少到的地方。指偏僻荒凉的地方很少有人来过。
高不可攀
[gāo bù kě pān]
攀:抓住高处的东西向上爬。高得手也攀不到。形容难以达到。也形容人高高在上,使人难接近。
冰天雪地
[bīng tiān xuě dì]
形容冰雪漫天盖地。
白雪皑皑
[bái xuě ái ái]
皑皑:洁白的样子,多用来形容霜雪。 洁白的积雪银光耀眼。
连绵起伏
[lián mián qǐ fú]
连绵:连续不断的样子;起伏:高低不平。连续不断而且起伏不平。
来源:新京报
一位女地质学家的44年 在浪漫孤寂中与高原雪山相伴
46亿年的地壳构造运动碰撞、挤压出一片片高原与山峦,鲜有人类生存的高海拔地带,积雪铺天盖地,一眼望不到边际。荒野时而沉默,时而暴躁,与其相伴44年的付小方深谙它的脾性,她在野外得到过山川的馈赠,也领教过自然的威严。
资源的获取,往往依赖地质工作者与自然的博弈。1977年,因一场**与地质结缘的付小方,先后来到四川地矿局攀西地质大队、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加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在川西高原寻找矿产,深入汶川地震灾区调研,勘探亚洲第一锂矿甲基卡,和无数地质工作者一样,她所经历的每个项目都是一场未知冒险。
4名调查人员在哀牢山中遇难的消息牵动着人们的心弦。而悲伤背后,仍有一群人正在茫茫荒野中,在浪漫与孤寂中,与高原、雪山,生死相伴。
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沿着全长5476千米的川藏公路进藏,需要翻越10余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大山,穿过长达13459米的新二郎山隧道,跨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江,路上多险弯,路面多暗冰,即便是最有经验的司机,跑在川藏线上,也要浑身绷紧了弦。
平原、高山、峡谷、河流、冰川、草原、森林、湖泊,随着海拔高低起伏,路边景致不断变换,车辆在山脊上疾驰,远处云朵缠绕雪山腰间,行至开阔处,蔚蓝色天空低低地压下来,宛若一匹触手可及的绸缎。
11月29日早上9点,山间雾气还未散尽,63岁的付小方穿着粉色冲锋衣,靠在越野车后座,半个身子向前微躬,出神地盯着车窗外,不时掏出手机拍下路边闪过的岩石与山体。
2013年退休后,付小方被四川省地质调查院返聘为首席专家。此次踏上川藏线,为的是到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检查地质项目进度,以及在雅江县苦乐村为当地人检测水质。
她已经数不清自己在这条路上往返了多少次,路的一端是她的家乡成都,另一端连接着她的工作地点——川西高原、青藏高原。
川西高原与青藏高原一直是地质研究的重点区域,几乎每一位在西南工作的地质工作者都有一段关于进藏之路的回忆。路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付小方的记忆里,通往高原的路原本还要更加艰险。
上世纪90年代,军绿色的解放牌越野车冲上高原,付小方和同事挤在露天车厢里,脚边是数个硕大的行李包,塞满了地质勘探的仪器、图纸与样本,路途颠簸,车一抖,人和行李包被颠得左摇右晃。
那是地质工作蓬勃发展的时期,国家需要偏远地区更详尽的土地调查图,需要大量能源助力发展,三十多岁的付小方和同事在露天车厢中一路唱着歌,走遍了高原、山区,在少有人迹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个测量、勘探标记。
山间多是土路,一趟走下来,每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灰突突的,“简直分不清谁是谁”。工作途中,付小方和同事遇到过狼和熊,遇到过持枪的土匪,更危险时,还有车辆翻入雪地,半个车身挂在悬崖边的经历。
高原缺氧、山路难走,让付小方练就了骑马的本领。旧照片中,个头小小的付小方骑在马背上,背着大包,昂着头,一脸骄傲神情。
“藏区的马没见过雨伞雨衣,雨伞撑开‘砰’的一声,都可以让马受惊,雨水打在雨衣上‘沙沙’的声音也让它害怕。”付小方曾因此被马甩下,“当时被甩得老远,掉在地上还伤了头”。
早年间,野外勘探没有住宿地点,常常只能睡在越野车和帐篷里,遇到下雨,就在帐篷里撑着伞,身上盖着毛巾吸水。高原上蔬菜水果匮乏,方便面、压缩饼干一吃就是几十天,每次勘探结束,队员们从山上下来,个个脸颊黑红,嘴角带着深深浅浅的皲裂和溃疡。
“腿上摔的、划的口子密密麻麻,干这行之后,我再没穿过裙子”。曾经的艰苦经历在付小方身上留下不少伤疤,她却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讲起过往她总是带着笑声,语速极快,掩饰不住地兴奋,“有一次两个车胎同时爆了”,双手一拍,“啪!来了个双响炮!”
三十年过去,如今,进藏之路已无当年波折,越野车驶进穿山隧道,车速慢下来,橘**灯光映进车里,给野外作业必备的羽绒衣、棉帽、围巾笼罩上一层温暖光晕。
地质人的浪漫与孤寂
下午2点,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十几名施工与科研人员纷纷围着钻机忙碌,即将进入12月,岩层将被冻得更加坚硬,再不抓紧施工,恐怕要等到来年的春暖时节。
北大地质学博士孙丽静戴着动物造型棉帽,捧着卡通水杯,缩成一小团,正蹲在雪地里清点样本。
几十盒圆柱体岩石样本被塑料布盖住,每取出一段岩石,她和同事就要进行初步标记,待稍晚运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为此,她已经在山上守了近一个月。
谈及选择地质工作的原因,孙丽静没有思索,小圆脸上带着笑,只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喜欢嘛”。
许多年前,付小方也曾给出过一模一样的理由。
17岁时,在部队大院里看到**《年青的一代》,地质队员不畏艰险,在青海高原上为国家寻找矿产的故事,让她对地质工作心生向往。
19岁时,付小方加入攀西地质大队,前往攀枝花从事岩矿鉴定、选矿试验等工作,他们勘探的矿石将被用来锻造钢铁,那是当时急需的资源。当时正在开展攀枝花钢铁大会战,军人出身,曾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大凉山的父母理解女儿的热情,没有阻拦。
地质队少见女生,第一次随队野外调查时,付小方和男队员同住一个帐篷,有些不好意思。
但付小方知道,“工作起来,就不能分男女”。每次野外调查回来,地质队员都要背几十公斤重的石头样本,男人背多少,她也背多少,最多时,她一个人背了25公斤的石头,而她当时的体重只有40公斤。工作一段时间后,付小方考入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地质调查专业。
1987年毕业时,已经成家,刚有了孩子的付小方本可以到税务局工作,但她左思右想,还是申请加入了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嘛。”
来到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后,付小方想进入院里的高原研究室,又怕自己带着一岁多的儿子,会被研究室的人当成“累赘”,试探地提出了申请。没想到时任研究室主任侯立玮二话没说答应了她的申请,“可以啊,很欢迎”。
为了侯老师的这份信任,四十多年来,付小方全身心投入地质调查工作。她说不清那份喜欢从何而来,但那些年,山川湖海真实地滋养过她的人生。她在雪山上看过日落,在荒野看过彩虹,在路边看过秃鹫啃咬牦牛尸体,阳光下的寺庙通体金光,贡嘎山顶变成粉色,无人山区待久了,世界安静得仿佛只属于她自己。
只是浪漫背后也有数不尽的孤寂,“我从没听过搞地质的前辈过多提及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付小方说。
只有在日记里,她才敢释放自己的脆弱。“上高原的日子又到了,心里有些兴奋,可昨晚戈戈哭着不要我走,心里又不放心儿子。”
她在山里给儿子写信寄托思念,“戈戈你好,妈妈在很远的大山里工作,很想你,有时就把你的照片拿出来看看。这里山很高,天很蓝,云很白,站在山顶上,手都能摸到天似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带你来看看大自然的风光。”
而在一次任务途中,付小方的丈夫因脑动脉瘤陷入昏迷,马上要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手术,需要她签字。可那时她刚抵达300公里外的高原,又赶上二郎山暴雨塌方,怎么也出不去。等待道路开通的日子,为了不耽误进度,付小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发了疯般,狂奔着完成了所有工作。
道路开通之时,付小方第一时间冲出大山。所幸最终手术顺利,付小方这才卸了劲,瘫坐在椅子上。
尽管当时情况凶险,但丈夫和家人没有一句责备,“但凡有人说句重话,我都没办法坚持”。再提起往事,付小方的丈夫也只是笑笑,“她要工作嘛,都莫得办法”。
雪山上的锂矿
结束折多山行程,11月30日一早,付小方和同事又驱车赶往了一百公里外的雅江县苦乐村。当地即将开建水厂,邀请付小方来做水质检测。
从村口到水源地尾端有近三公里山路,走在苦乐村旁的原始森林中,付小方脚步极快,她总是习惯性地抬头望望,沿途古树枝叶繁茂,一阵寻觅后,她指指树叶缝隙中透出来的雪山,“那里就是甲基卡”,她在那里往返了整整八年。
甲基卡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贡嘎雪山脚下,平均海拔4600米,空气稀薄,常年落雪,又是雷击区,上世纪70年代曾有多位地质队员因地滚雷长眠此地。但那里有着最丰富的稀有金属——锂。
2011年,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下达任务,要在全国范围内摸清稀有资源储量,2012年,付小方所在的四川省地质调查院接下了在甲基卡寻找锂矿的任务。
2012年10月,地调院副总工程师付小方带领团队兵分三路,运用地质、物探、化探三种找矿方式,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现了两条锂矿化脉,为后续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团队再次前往甲基卡,5月中旬积雪刚刚融化,放眼望去四周一片荒芜,那一瞬间,付小方突然有些心慌,到了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确定下钻位置的时刻了。
高原上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融雪在路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坑,沼泽地里也蓄满了水,走路都困难,工作进度慢了下来。土壤采样有几公里的作业线,正是挖虫草的季节,请不到背样本的民工,只能靠年轻的队员多背一些。
各组对讲机不时传来有人掉进水坑的消息,一位地质队员掉进被雪覆盖的沼泽水坑里,为了赶工期,不愿意回到30多公里外的驻地休整,硬是拖着半身泥在风雪中跑了一整天。有的队员脚底冻伤复发,只能在鞋里垫上厚厚的海绵,一瘸一拐地走在山路上。
尽管每个人都拼尽全力,但能否真正找到锂矿还是个未知数。此前甲基卡找矿、勘查工作不断,但由于环境恶劣,开展工作难度太大,也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那段时间,付小方每天的日记里都写满了担忧,“哪里才是我们的突破点,我心里真的没有底”。
直到2013年6月28日,一个雨后初晴的早上,付小方掐着指头倒计时,经过前期勘探,团队布置的先导孔即将开钻,过去近一年的努力能否有结果,将在此刻揭晓,每个人都提着一口气盯着钻机。
当施工到7米深的围岩时,队员唐屹突然大叫起来:“见矿了!见矿了!”所有人都跟着大叫起来,第一管锂辉石矿芯出现了,付小方接过矿芯,像抱孩子一样,手止不住地抖。
又经过近三年的努力,2016年5月3日,经中国地调局专家审定,付小方团队承担的项目新增氧化锂资源量共计8855万吨,为国家新兴能源提供了资源保障。
直至2018年,甲基卡外围新增氧化锂资源量共计11431万吨,居亚洲首位,而这在将来会带动万亿元的锂电上下游产业。
几代地质人的努力
11月28日,前往折多山的前一天晚上,付小方参加了一场大学同学聚会。十多位地质人聚在一起,刚刚发生的哀牢山森林调查员遇难事件成了绕不过的话题。几番讨论,未知原因,一位同学感慨道:“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都是福大命大的人。”
事情发生后,很多年轻的地质同行在朋友圈分享《勘探队员之歌》以表哀思,“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付小方见了轻轻叹了口气,她理解年轻人的心思,“如今地质工作者的努力被看见得太少了。”
付小方入行之初就听遍了第一代地质人的事迹。“很多老同志在野外勘探时遇到暴风雪、迷路,干粮耗尽倒在路上。找到他们时,身上还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样本”。
她见过那一代地质人的执着与付出,“很多老同志身体其他地方都特别好,就是因为年轻时跑得太狠,腿脚不行了,不得不坐上轮椅。”而她的前辈八十多岁时仍坚持亲自带着学生到甲基卡上讲课,最后体力不支,晕倒在路边。
她也了解更年轻一代地质人的努力。在甲基卡时,队员郝雪峰接到妻子电话,女儿肺炎发高烧,情况严重,可郝雪峰赶不回去,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在队伍后面悄悄抹眼泪,付小方看到了也跟着一阵心酸。
同事唐屹从研究生时期便跟着她在甲基卡上奔波,她眼看着戴着黑框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每天背着几十斤样本,在山间摸爬滚打,皮肤晒得黝黑,脚常常被泡得发涨,还在给自己打气,“越是这样越是需要坚持”。
“以他们的科研能力,完全可以去做更赚钱的事。但没办法,选了这条路,就是选择了奉献和孤独。”付小方只能尽力为年轻人筹划未来的发展,取水样回来的路上,她连问了几遍,“孙丽静毕业后会去哪里?”
回程路上,她特意去找孙丽静,山上暂时还无法施工,她想顺路带女孩去康定市区,让她在低海拔的地方好好休息几日。
女孩又戴着动物造型的棉帽出现了,笑着说道:“算了,下去会醉氧,一连几天都想睡觉,回来又要重新适应高反,不如就在这继续写论文,等着开工那天。”付小方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也无奈地跟着笑。
四天的高原之行结束,抵达成都已是正午,那是冬季里难得的晴朗天,街边公园有三三两两晒太阳的老人。奔波几日,付小方脸上毫无疲态,一手从后备厢里拎出两桶水样,样本需在48小时内完成检测,她顶着阳光,脚步轻快地走向了实验室。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