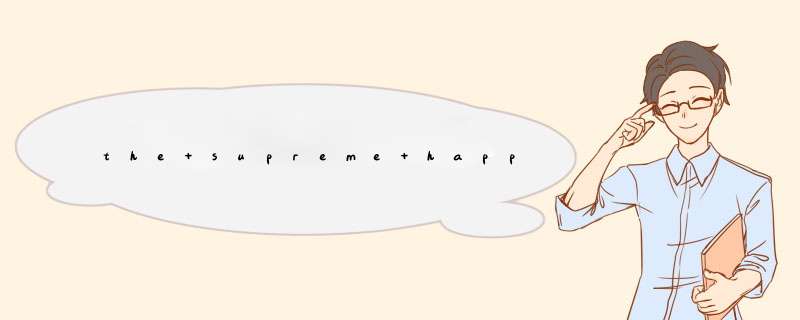
是法国小说家雨果说的。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作家,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
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在法国及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维克多·雨果的创作特色:
一、作品主题
雨果一生的创作时期长达六十年之久,是个多产的作家,也是个多产的诗人。他前期的创作,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同情人民疾苦,希望通过改良社会,解决矛盾。后期创作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素。
二、创作主调
赞颂真、善、美,鞭挞黑暗、丑恶、残暴。
三、艺术手法
雨果在艺术手法上的一个特点:描写经过夸张的、非凡的人物和非凡的情节。他的主人公或者是作出了极其英雄的行为,或者是做出了极其残暴、卑劣的行为。他们的性格特点都经过夸张。情节也是非凡的。矛盾一个紧接一个而来,又充分运用巧合、偶遇等手法,曲折有致,引人入胜。
雨果的创作是他关于对比的美学见解的实践。他喜欢显著的对比。作品的环境描写就离不开这个原则。
雨果善于描写巨大的场景和巨大的事件,例如滑铁卢战役等。同时作者喜欢在作品中站出来书写自己的主观感受,他充满激情的表现自己的爱和憎,从而引发读者共鸣。
积极浪漫主义运用非凡话、夸张、强烈的对比构成情节,和消极浪漫主义有本质的不同。雨果的作品在非凡的形象和实践中再现典型的性格和现实现象的社会历史实质。它从本质上反映现实,反映作者的进步理想。
雨果善于巧妙地结合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方法。在他的浩瀚的浪漫主义巨著中,就有真实的典型人物,有时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方法塑造一个人物。
扩展资料
一、这句英文的译文:
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
二、这句英文的结构
主系表结构,即:主语+系动词+表语。
The supreme happiness of life(主语)+is(系动词)+the conviction that we are loved(表语)。
中国日报网-The supreme happiness of life is the conviction that we are loved
人可以不用穿着华丽长相惊艳,但一定要做一个浪漫的才子。即使世俗浮躁会充斥我们的生活,也不要对生活产生厌倦。生活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怎样,决定我们的生活怎样。
其实你游荡于人海满贯的街上,那些不经意的浪漫与你擦肩而过。不论是街头卖艺的魔术师向观众变出的白鸽,煎饼铺子老奶奶做的一手爱心早餐,还是下午六时40分太阳归山映射的晚霞,都是生活中的浪漫。
浪漫不是金钱攀比的对象,不是口头上的甜言蜜语,我理解的浪漫是不经意形成的微小细节所造成对当事人的愉悦情感,就像是走在路上,你突然伸出手递给我的一束花;或是你绕了十几圈来制造我们不经意的偶遇;也可以是打开门发现家里一堆人等着给你庆祝生日。
自然界的浪漫原抵不过人与人之间制造的小浪漫。 ro man tic翻译过来就是浪漫,发现了吗?它是需要人去支撑的,人是其中的调和剂。解调与浪漫相冲的一系列物质。
I want to weave you and the stars into my dream §
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
永远做一个浪漫的人,Forever
启蒙运动(法文:Siècle
des
Lumières,英文:the
Enlightenment),通常是指在18世纪初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与音乐史上的巴洛克时期以及艺术史上的新古典主义时期是同一时期。我们来讲浪漫主义对西方文明的影响首先,它诱导了西方人走极端的趋势西方人最喜欢走极端,觉得不如此不过瘾我对西方文化中的一点精神是非常佩服的,那就是向极限冲击比如说有那么一个教授,他要写十几本书,要带二十几个研究生,还要去当杂志主编,还要主持国际会议,还要当好妻子,好妈妈,好爸爸,还要去旅游这就是向极限挑战啊这种极限挑战是什么意思
极限挑战就是,人经常是在自己生命的临界点上生存,并且把这种生存当做了生命运行的正常节奏也就是说,人喜欢把一个东西的全部内涵都掌握,都征服,以为舍此无法真正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这,当然是一种走极端的形式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西方文明具有脆弱的一面例如,这个浪漫主义就是很脆弱的,西方文明缺乏弹性,但容易走极端,美其名曰求新,求异文明的底座也不稳,却喜欢不断追求高,精,尖西方文明底座不稳却要对外扩张,容易造成很大的悲剧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浪漫主义精神的激励下,西方人做事情时行为的矛盾性很小,尽管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的冲突性很大为什么行为的矛盾性很小呢
就是做起事来,一个本能冲动,马上就能去做这之间的限制性因素很弱浪漫主义还造成一种文明在取代另一种文明时的冲突性,常常以不妥协的革命方式进行西方文明里面有这么一种浪漫机制,做了就做了,不考虑后果我们看到,东方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东方文化比较倾向综合考虑,西方文化比较倾向于分析考虑;西方文明的底座不稳,却追求高精尖;东方的底座很稳,却过于宽泛;我们发展了的是高情感,西方发展了的是高科技西方那个高精尖底座不稳,我们底座很大,也有深厚的传统,但需要发展高精尖还有西方人的那种分析性,批判性的思维习惯,那种逻辑思维,那种深度,精度,广度,强度,都和我们的形象思维,我们的强调广度,经验,具体的综合性思维习惯有所不同西方人从古典时代起就发展出一种征服感,他们用石头造房子,一有机会就想造个城堡,征服世界征服世界以后他怎么办
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也许是继续野蛮下去,继续搞征服,另一种可能是由智及仁
第一辑:看得见的城市
抒情的终结
海子: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
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1989年3月26日下午5时30分左右,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仿佛呼啸而过的时代,驶过山海关附近冰冷的铁轨——铁轨上那个温暖的身体顿时一分为二。现在谁也无法知道,躺在坚硬枕木上的海子,在最后时刻会写下什么样的“绝句”?那是一段火车慢行道,尽管如此,生与死之间最多也不会相隔001秒。
后来的写作者,迅速将这个短暂的时刻定格成永恒的瞬间。关于诗人之死,我们可以听到无数种说法:有形而上的,比如将之称为“诗歌烈士”;有形而下的,认为自杀只是一种文坛登龙术。同行们的想象力在这个方面尤为擅长,最终的结局却无非是“文人相轻”或“文人相重”。但是,更多的诗歌外行包括海子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后张扬的自杀案?海子原名查海生,如果说“海子之死”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查海生之死”则是一个儿子的意外死亡。“儿子之死”不像“诗人之死”散发着文化的芬芳,却更能体验到致命的疼痛感。
查海生是一个农家少年。即便他后来没有成为著名诗人,在十五岁考上大学的1979年,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查湾,已经称得上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居住于乡村的那些诗歌外行们,并不明白“凤凰涅盘”的道理,在他们看来,不管“为诗歌献身”还是“为荣誉献身”,都是不可理喻的。如果要在活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查海生和死了的著名诗人海子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家里人高兴得不得了,”母亲曾这样回忆儿子刚刚工作后的情景,“第一个月90元的工资,他寄了60元回家”。或许,诗人们会对这种外行的评论不以为然。但在那种看似目光短浅的说法下面,却隐藏着朴素的生活伦理。
狂人书信
在绝大部分诗人身上,都存在着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的紧张。生活伦理常常属于“近视眼”,特别强调平淡无奇、触手可及的现实世界;艺术法则往往属于“远视眼”,比较注重遥远的甚至虚无飘渺的幻想世界。如果在两者之间无法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像没有对准焦距的兔子,一头撞在艺术或生活的树桩上。遗憾的是,作为儿子的查海生是“近视眼”,作为诗人的海子又是“远视眼”,最后的悲剧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一年,查海生在家乡过寒假,专门给自己所在的哲学教研室主任写信,打算请半年病假,但他后来又改变主意,还作了一个书面说明,表示要安心上课,在教学上做出成绩,争取年内评上讲师。在奔赴山海关之前,海子写下几封不是遗书的遗书,其中一封这样写道:“两个道教巫徒使我耳朵里充满了幻听,大部分声音都是他俩的声音,他们大概在上个星期四那天就使我突然昏迷,弄开我的心眼,我的所谓‘心眼通’和‘天耳通’就是他们造成的。”
一边是“争取年内评上讲师”的生活伦理,一边是“耳朵里充满了幻听”的艺术法则(这不能仅仅归结为气功问题),它们足以撕裂一个血肉之躯。这些书信仿佛鲁迅的《狂人日记》,那部小说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在文言文写成的序言里,狂人不狂,他遵循着生活伦理,已经“赴某地候补”;在白话文写成的正文中,狂人却遵循着艺术法则,俨然是一个凡高式的艺术家。
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
医生和校方都以“精神分裂症”来处理海子自杀这件事情。他的朋友西川不同意这种看法,特别指出海子另外一封遗书写明:“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据此认为诗人相当清醒。这种辩护非但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海子其人”,反而将海子想象成一个“单面人”。事实上,每一个稍微有些敏感的写作者,都容易患上现实和艺术互相悖谬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在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很有可能误打误撞地闯入精神病家园。
海子不是两面神雅努斯,很难在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游刃有余,他更像“一分为二的子爵”(准确地说,是“一分为二的外省青年”),死后无法缝合的身躯就是一个无言的隐喻。作为家中长子,他一定深切体会到“长兄如父”的沉重;作为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各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重与轻、乡村与都市,仿佛剪刀的两翼,将一个生命断然剪开。
正文 第2节:第一辑:看得见的城市(2)
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者必须面对一定的精神困境,就像37度2的低烧病人会有美丽的幻觉。但如何既不像海子一样走向崩溃(那等于发高烧),又不像狂人一样被彻底治愈(那等于泯然众人矣),却是一个问题。美国有一家麦考林诗人精神病院,普拉斯、洛维尔和塞克斯顿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都曾以此为家。在我看来,与其像柏拉图一样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还不如像麦考林一样将疯癫的诗人送进精神病院,这虽然不会阻止却能延缓诗人的自戕。
“疯癫”不是一个褒义词,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一种与诗人如影随形的现象。可是我们要么盛赞狂人的精神症候,要么断然拒绝承认这种疾病的存在。如何在生活伦理和艺术法则之间获得平衡,如何保持略高于常态又不影响健康的恒温低烧,恐怕只有认真思考而不是回避这些问题,才能避免走向从精神家园到精神病家园的不归之路。
最后需要声明,以上这些分析丝毫不影响我对逝者的敬重,以及对他那些天才短章的热爱。
(本文参考了燎原、余徐刚等先生的相关文章,谨致谢意)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
永葆青春的秘诀是死于青春——这是一个让人苦笑不得的真理。就像海子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年轻的“小冬子”,谁也没法想象他会成为一个文学中年;就像三毛总是那个滚滚红尘里的灰姑娘,谁也无法描绘她六十岁的面容。巧合的是,海子的忌日恰恰是三毛的生日。这又是一个隐喻,一名写作者的生命往往是从他(她)的死亡才真正开始。或许,他们并没有离开世界,只是躲在一个秘密的角落,故意用死亡来检验自己的作品,然后看着人们的泪水偷偷地笑。
三毛去世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当她自杀的消息传到那个偏僻的县城,已经是若干天之后的事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三毛不是张乐平老先生笔下的漫画人物,才开始寻找她的文字。必须承认,我是一个文化上的后知后觉者,在大学时才开始读金庸,在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听罗大佑。当他们已经被嘲笑、被PASS的时候,我才接近这些明日黄花。也正是这种时差,使得我一直缺乏“偶像崇拜”的激情。我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暂时麻醉,但又算不上正宗的“歌迷会”成员。第一次读三毛,是她那篇《梦里花落知多少》。这首飘来飘去的“长恨歌”,仿佛一杯甜蜜的苦水,慢慢浸透我的那个下午。长期以来,我一直为当时的“感动”而羞愧,以为那不过是小情小调的青春期病症。但三毛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她会让你在某个瞬间“返老还童”,虽然你的青春记忆里肯定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章节。
三毛和琼瑶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仿佛是同一场文学舞会的两个舞伴。事实上,三毛和一个时代有关,而琼瑶和每一个时代都有关。换句话说,前者有些不合时宜,她的痛苦可能让年轻的读者笑出声来;后者却游刃有余,随时可以让观众慷慨地奉献出泪水。罗兰巴特曾说过,嘉宝的脸象征一种“理念”,而赫本的脸则代表一种“事件”。如果说三毛具有那种“令人绝望的美丽”,琼瑶已逐渐连“可供把玩的妩媚”也不复存在,只能让人想起赵薇的脸——表达着撒娇的“美学”。
有时,我会很残酷地暗自庆幸:幸亏海子和三毛都“及时”地离开了人世。一个神话般的时代,纷纷扬扬地落下红色幕布。或许,对他们来说,死亡将是一种体面的退场方式。文化英雄在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只能是一些“苟延残喘”的文化遗民。他们要么变成小丑,要么被别人当作小丑。而那个精神酒精随时可能点燃的年代,是幸福的也是危险的。虽然我曾无数次想象那些少年意气的岁月,却没有为自己的生不逢时发出过太多的感叹。
今夜,我不关心人类,只愿他们安息——如女诗人陆忆敏所说:“可以死去就死去”,或“温柔地死在本城”。
胡河清:十年生死两茫茫
我不认识胡河清。当他在上海的风雨之夜跳下窗台时,我还在安徽某个小城读中学;等我到上海求学时,他的灵魂或许已经返回祖籍安徽。但我似乎又与胡河清相识已久,他的很多文章我都熟读成诵,每次在默念时总有灯火阑珊之感,尽管其中并无任何悲伤的词语。我们之间是一种生者与逝者的往来,我愿意把这种交情称作“生死之交”。
正文 第3节:第一辑:看得见的城市(3)
淡绿色封面的《灵地的缅想》和墨绿色封面的《胡河清文存》,曾陪伴我度过荒芜的大学生活。当时,一位颇有些魏晋风度的古文字学老师,破天荒地在课堂上向我们推荐一本当代文学批评著作——作者就是胡河清。出于对那位老师的信赖,周末时分我们赶到福州路将书买回,整个宿舍楼因为本地学生的离去显得空空荡荡,我们和隔壁两个房间却一边传阅着胡河清的文章,一边发出着兴奋而忧伤的声响。那些文字所闪现出的灵光,足以照亮不谙世事的少年和黯淡的青春岁月。这种“阅读集体反应”在1980年代屡见不鲜,人们很容易被一篇文章激动得彻夜难眠;但在1990年代却是惊鸿一瞥,稍微有些深度的书籍只会让读者哈欠连天。
十年生死两茫茫,今天很少有人还会想起胡河清了。这不是坏事,胡河清生前曾说过:“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一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房子里,如寂寞的守灵人,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他很容易忘却被曹丕称为“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功业,更愿意像自己喜爱的钱锺书一样生活:“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虽然孔子也激赏过类似的话:“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他们的抱负却不尽相同。从单数的“我”到“二三素心人”再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这不仅是人数的多寡,也意味着他们的理想就像“素心人”和“素王”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胡河清终身未婚、孑然一人,钱锺书、杨绛和女儿、“我们仨”形影相伴,孔子则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们每个人按照着自己心向往之的境界生活。胡河清和钱锺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一个愿意终生关闭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一个喜爱息影杜门、居住于“荒江野老屋”,两者几乎拥有同样的清澈情怀。但或许正是“我”与“我们仨”的区别,使得胡河清和钱锺书同途殊归,一个从容赴死、一个安享晚年。
当我写下此文的时候,正值西方的愚人节。按照胡河清的说法,在聪明伶俐哥儿们多如牛毛的上海滩,他和另一位批评家朱大可只能列入愚人吉尼斯大全之列。他自称是一名“很土的”文学评论员,这也并非自谦。胡河清的文学批评几乎看不到来自西方文艺理论的十八般兵器,而是通灵宝玉般浸润在本土文明的柔和光线之中。即使他的学术论文,也被钱锺书一语点破,评判道:“整篇亦诙诡多风趣,不同学院式论文。”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不管“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还是“荒江野老屋”,都只能存在于学院围城之中。但随着学术规范和学科体制的建立,大学中文系也开始以学理化为借口排斥具有敏锐触觉的文学批评家。后者只有两条殊途同归的选择:要么西化、要么学院化,这对于胡河清来说都是绝路一条。据说他不无偏执地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自然无法成为西化的“后主”。一位学殖渊深的国学前辈,读过他的作家论笑道:“哦,这哪里是一篇评论,实实的是一篇小说哩。”胡河清回忆起这件事时,称:“这话当然是过奖了;但如果真能把作家论写成小说似的东西,那却也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既然如是说,他也就与善于书写学报体的“专门家”们无缘了。李劼曾用他一贯夸张的口气把胡河清之死与王国维自沉联系到一起。两者相去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但陈寅恪追悼王国维的话同样可以用在胡河清身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胡河清比较偏爱晚唐的许浑,曾请朋友将他的一首诗写成条幅:“劳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红叶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不知他是否想到“满天风雨下西楼”一语成谶?不知他在1994年4月的最后那个夜晚,会不会想起许浑的另一首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
正文 第4节:第一辑:看得见的城市(4)
罗大佑:当他已成往事
“你的样子”
长期以来,我一直不知道罗大佑的模样。艺术家通常有两种面孔:一副是演员式的,他们把自己当作作品,亲自上演着各种丑闻、传奇或者艳遇;另一副是导演式的,他们把自己隐藏在作品背后,选择沉默甚至悄悄消失。很难说罗大佑属于哪一种:作为文化工业的一枚螺丝钉,他必须遵守其中的游戏规则,参加新闻发布会、举办个人演出以及接受采访;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抒情诗人,他又必须面对自己、时代和家国的隐秘的疼痛。
后来我看到罗大佑的照片,他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形象,戴着眼镜,很斯文甚至还有着弱不禁风。2001年的《北京晚报》有一幅罗大佑的文字素描:“头发染成**、戴着紫色墨镜、斜挎着书包,穿着绿色衬衫、亮绿裤子、脚踏白色休闲鞋。”然而,这种老顽童式的装束只是身体的迷彩服。仔细看上几遍,会发现他的体内似乎流淌着酒精,随时都有可能点燃。
罗大佑曾经招供,他创作歌曲的思想源泉是“生气、愤怒之类的”,因为“愤怒代表一种集中”。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染上愤青的愤世嫉俗症,也幸免于知识分子的洁癖。罗大佑属于巨蟹座,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即使把那些星象学的知识全部抛弃,也无法否认蟹类“骨包肉”的生物学常识。虽然巨蟹外刚内柔而罗大佑外柔内刚,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防弹衣。这种防弹衣保护了那些黑夜中寂寞的心脏。我们都还记得《你的样子》:“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光阴的故事”
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我所能听到的音乐都来自街头喇叭,千篇一律的声音使得我至今五音不全。我与罗大佑“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是在大学时代。那是一所N流大学,“空气中都是情侣的味道”。相对那些精致的女声,罗大佑的声音几乎有些简陋。但它使我的血液在瞬间沸腾起来,与热火中烧不同,这种高原式的沸腾同时带来了温暖和寒冷。如果说罗大佑的追随者大都是1980年代的遗老,我愿意称自己为1980年代的遗少。“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不仅“改变了一个人”还“改变了我们”。喜欢怀乡的1970年代中后期出生者,几乎都是1980年代“在场的缺席者”。虽然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却只能在想象中感受到它的灿烂。
罗大佑和崔健是1980年代的两个文化英雄。他们堪称“南帝北丐”:一个打造着“家国之梦”,一个是渴望水和姑娘的假行僧。校园民谣歌手高晓松曾“毕恭毕敬”地说过:“我不敢和罗大佑谈音乐,就像你看见灯塔,在灯光指引下游了过去,但你难道能用一个手电筒照人家吗?”罗大佑肯定不会同意“灯塔”这种雄纠纠的比喻,他更愿意提着“易碎的灯笼”——虽然努力照亮那些黯淡的面孔,却随时会熄灭。当网友告知有人把他的音乐当圣经,他的回答非常简洁和干脆:“我不是耶稣。”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仿佛1960年代的欧美,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这奇迹既有可能是重建的文化长城,也有可能只是一座文化的海市蜃楼。很多人在幻觉中无法自拔,但罗大佑例外。在各种场合,他都拒绝称自己是“英雄”,也拒绝称自己的作品为“经典”。
“告别的年代”
如果说罗大佑已是“明日黄花”,不知是否太残酷,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残酷。根据南方网的调查,绝大多数1980年代出生者对这位昔日的“音乐教父”一无所知。人们的胃口需要不同的营养——“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终不须诉说出口”。某些追随者喜欢把罗大佑归到“高雅“的阵营里,似乎他们也可以狐假虎威得高雅起来。
1990年代诞生了另外一个文化英雄周星驰。微妙的是,这位英雄以小丑的形式出现;更微妙的是,大话文化的“狂欢精神”被小燕子姐姐(赵薇)翻版复制成“撒娇美学”。与此同时,经昆德拉之口传播出一句被反复“误读”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在笑声中,“过时”的罗大佑理所当然地成了笑的对象。笑声并不可怕,但把笑当作拒绝思考的理由,那就接近于无聊了。
正文 第5节:第一辑:看得见的城市(5)
在我看来,“罗大佑”和“周星驰”绝非一对水火不相容的敌人。罗大佑不是皱着眉头的“愁容骑士”,他对“英雄”这种荣誉称号的回答是:“拜托——英雄都是很容易死掉的!”周星驰也不是只会嘻嘻哈哈的“喜剧之王”,合作伙伴毫不客气地说他“非常严肃,太严肃了,一点也不搞笑”。生活既需要可笑的泪水,也需要认真的笑声。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