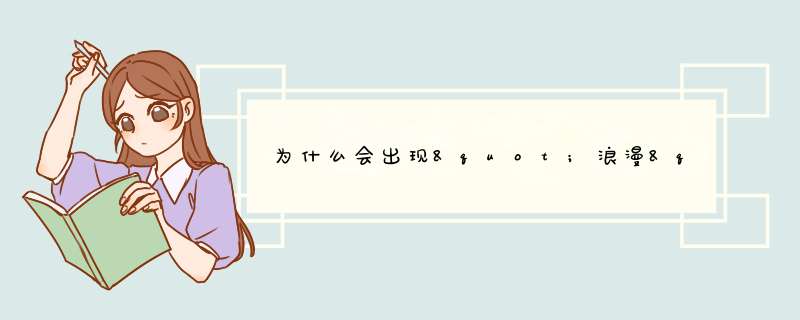
说起李易安《渔家傲》,前代有识之士津津乐道,高调称赞。本来以婉约词风见长的她竟能写成如此豪放之作,抢了一回词范苏辛的风光,仿佛这样的别样佳作是一颗闪耀的流星,给李词温柔的夜空增添了奇异的光彩。先照录原词: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前代好评甚多,这里仅摘取数例: “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中苏(轼)、辛(弃疾),非秦(观)、柳(永)也。”(沈曾植《菌阁琐话》) “此似不甚经意之作,却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自是北宋风格。”(黄了翁《蓼园词选》) “这首词把真实的生活感受融入梦境,把屈原《离骚》、庄子、《逍遥游》以至神话传说谱入宫商,使梦幻与生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构成气度恢宏、格调雄奇的意境。近人梁启超评曰:‘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宋词鉴赏辞典》,徐培均语) “……这首词却写得极为豪放,涵溶(融)庄骚,风云交会,洋溢着浪漫主义的奇情壮彩。”“通观这首词,以清虚之笔写大阔之景,词情笔路有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读之令人神魂摩荡,飘然欲逝,不愧为女中豪杰,声家妙手!”(臧维熙《宋词名篇赏析》) 然而细察这些评论,会发现一个共同倾向,就是都看重这首词的写法、气势、风格等,至于思想理念、社会内容则付诸阙如。是论者们无意中忽略了这些写词论词的构成要素?显然不是,是词作本身就缺少这些要素。 词作外景奇异,壮美动人,内情也蓬勃、充盈,只是此内情何解,难经细剖。李氏学诗初成,只是“谩有惊人句”,不满于此,还想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但路在何方?她在梦中与天帝对话,“我报路长嗟日暮”,好像心灰意冷了。但结尾突然振作,仍要沿着理想的道路继续前行。这里表现的是一个旧时代女子或妇人的宏大而虚无的理想,推测其理想约有二端:或成为空前绝后的词人,或依恃其旷世奇才积极入世兼济天下。她在那个时代大概只能成就前一理想,后一理想几成空谈。因此总的说来,这首词表达人生奋斗的激情和路在何处的疑虑,一种内在的矛盾冲突浮现于纸上。有人认为这首词写于晚年,以“梦魂归帝所”和“路长嗟日暮”为据,我看似是牵强;我推断写于早年,因为词中既有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又有年轻人的迷茫失落,更有规划长远人生道路的志气。那么,这里的“人生道路”内容之狭隘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词作凸显了个人化的情怀,而缺少了对社会群体性人生的关怀。论其价值,仅有气势、风格、写法等,充其量可名为“有意味的形式”。 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李氏《渔家傲》气势、器量之恢弘,风格之鲜明独异,声语之优美和谐,不也令此作成为词苑独秀奇葩?不然,以这些名世能成佳作而难成杰作,或者说仅为能品而难成神品。翻开诗词历史,那些最优秀的精良之作、神妙之作,哪一首不有深广的思想内容、高超的构造形式和炉火纯青的语言运用?尤其是思想内容,成为诗词作品中石质、铁质乃至金质的沉甸甸的东西,这些东西大概包括:对社会生活、时代风云的缩略的留影,对苦难民生的深重的同情怜悯,对时代历史召唤的主动回应,对文人道义、社会责任的自我担当,对个人与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的痛苦品味等。 这些当然概括是现代人的说法,在古人那里是以“兴寄”“兴托”“寄托”名之,这里的“兴”不仅指诗词起兴,也指作品微小方隅里容涵深广宏大的内容,如古人所解,“兴者,托事于物”(汉代郑众《周礼注疏》),“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那么,所兴者理当何事,所托者理当何物?南朝钟嵘《<诗品>序》的论说可供参考:“至于楚臣(指屈原)去境,汉妾(指王昭君)离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此处为古代诗人词家展现了多么广阔的天地的创作天地! 现代论者不是以屈原、李白来对比李清照吗?可是《离骚》所展现的广阔的社会图卷远非《渔家傲》可比的。《离骚》的兴寄和取比古人早已阐明:“《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飘云霓,以为小人。”(汉代王逸《离骚经序》)这些全是真真切切的社会生活。屈诗和李词二者都有瑰丽想象、浪漫情怀,但李清照的想象和浪漫是一眼能见底的,而屈原《离骚》的想象和浪漫却是浮在浅层的东西,内中无限深广的拯国救民的思想和难与同流合污的忧愤情怀才是诗人最想表达的。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对《离骚》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贯穿在这酣畅淋漓言辞中的,主要是思想内容的评价、社会人格的评价。司马迁对诗中的浪漫想象好像“视而不见”。 李白诗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亚于李清照词,如论所言:“读者都会感到,李白的诗里有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回荡着,使人不得不慑服于他的力量。李白的诗,综而论之,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析而论之,有气骨、有气象、有气势。”(袁行霈《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注意语中的“历史”“气骨”这类字眼,显然含有思想性、社会性的评价。可以拿李白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与李清照的《渔家傲》的浪漫精神作个对比。两人都写了游仙梦,李清照梦而未醒,想终生一直梦下去,直到“蓬舟吹取三山去”,如果追索其中真确的社会意义,稀薄得很,是棉质的、木质的、雾质的;李白则酣梦中断,梦境与现实强烈对比,显出诗人内心与社会环境的巨大冲突,最后吟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名言,坚如如铁石,掷地有声,表达了绝意仕途、蔑视权贵、向往自由的反抗精神和高尚情操,社会意义远胜于李清照词。试想,如果李白此诗删去结尾几句,则变成纯粹的游仙诗,与晋代的何劭、郭璞等人的作品混同一流,何能独拔于千古诗坛? 因此,李清照的浪漫佳作有如流星一闪而逝,夜空复归温柔婉约;而屈原、李白的浪漫杰作则永远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光照历史的空间和人类的心灵。结论: 诗词仅有“有意味的形式”是不够的;诗词可以有个人的浪漫情怀,但要超越个人局限,延伸至广袤的社会空间。
格利高里・哥戴克
(美国)Gregory JPGodek——中文名翻译为格利高里·哥戴克,格利高里・哥戴克最近刚刚结婚,是位作家和职业讲演人,还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远在浪漫宣传成为他的副业之前,他就已经有很浓的浪漫倾向了。之后,浪漫宣传又成了他最为关心的事业,以至于成为他的终身职业。在过去的十七年里,格利高里一直在研究两性关系学,并在十分著名的“浪漫讲习会”上讲授了十七年。Gregory JPGodek(格利高里·哥戴克),以“美国浪漫权威”而闻名全球,他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受大众欢迎的演说家。格利高里在欧普拉和多纳休公开露面,在他的浪漫学习班上向美国军队、妇女组织以及企业机构等众多的团体开班授课。
是6本最畅销书的作者,也是备受欢迎的浪漫研究班的创办人,他的忠实读者们都称他为“美国浪漫教练”。他曾帮助成千上万对爱侣重新激发出久违的创造力和日日常新的浪漫。他是一位奇才,一位名人,以行动落实了他所追求的东西,他拥有幸福的婚姻。哥戴克认为“浪漫是对爱的表达”。他的书是务实的,能启发人们,帮助人们对爱采取行动的。
他的演讲与书籍帮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浪漫创造力,使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充满激情。1996年到1997年,哥戴克访问了50个地区的150座城市,他办的浪漫研究班遍布各地,哥戴克同时是一位非常有阅历的作家。
这本书是应数千名妇女的要求而写成的。格利高里曾说,世界并不需要另外一本指南书来讲授最新的心理学疗方。我们也不再需要另外一本专讲“爱情”指南的书(不管怎么说,男人一般也不会读那样的书)。人们真正需要的――而且一直在不断寻找的――是要回到最基本的东西上面:在本例中,那就是“好的老式的浪漫”(其中有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而做的一些更新)。人们需要的是一本实用的书,里面有具体的点子――因为他们不需要说教,而是需要一本随手可得的参考书和(有时候)恰到好处的妙主意。本书可谓两者兼备。
格利高里还说过,本书可以称作“我的世界,欢迎来访”。因为这实在是一本关于他自己的书:他对人生的看法,他的个人哲学,他对妇女的爱(其中一位是特别的爱,其他则为普遍的爱),他对两性关系的观察,还有他对大量文章、资料、参考书、个人笔记和漫画的收集。对于想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欢乐、幸福、安宁、乐趣和激情的人,本书都是实用的。格利高里当然不敢斗胆妄言浪漫即是全部问题的答案,可是,他暗示说,它是其中的一种办法。这是他的办法。
本书自出版以来,格利高里所从事的事情包括:在奥普拉讲习浪漫法;讨论过“你的爱人是否有‘浪漫伤痕’”;给美国陆军讲浪漫;又写了九本书;计划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之旅――五十个州/一百座城市/五年的“浪漫穿越美国”书之旅。格利高里是个少见的人,一位身体力行的名人:他的确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对格利高里来说,浪漫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学术理论、时兴的概念或者劝告。它就是生活本身――过美好的生活,完整地体验生活,并在爱的氛围里共享人生。
1、富有诗意,充满幻想:富有浪漫色彩。
2、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常指男女关系而言)。
引证:
1、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2、老舍《二马》第五段二:“你老说我太注重事实吗,我得学着浪漫一点,是不是?”
3、冰心《寄小读者》二十:“轻柔的笑声,从水面,从晚风中传来,非常的浪漫、潇洒。”
1、富有诗意,充满幻想:富有浪漫色彩。
2、行为放荡,不拘小节(常指男女关系而言)。
引证:
1、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
2、老舍《二马》第五段二:“你老说我太注重事实吗,我得学着浪漫一点,是不是?”
3、冰心《寄小读者》二十:“轻柔的笑声,从水面,从晚风中传来,非常的浪漫、潇洒。”
在中国,历来的理论家都认为风格与作家的个性精神和生命状态有关。《周易·系辞·下》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虽然说的不是文学风格,但却影响了后人从心理—语言—文学风格的思路去探讨风格问题。汉代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理论的起始期。司马迁根据“诗言志”的观点评价《离骚》的风格,指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爝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认为《离骚》文约辞微、意旨深远,与作者屈原高洁的志向密切相关。此后,扬雄提出“心画心声”说。他在《法言》“问神”篇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认为“声画形”是人的情感的表现,从中可以看出人的品位等第。至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的自觉和繁荣,对文学风格的研究也进入了成熟期。当时出现了“体”、“体格”、“风格”等概念。“体”的本义是人的身体,引申到文章学,就指文章的体貌风格,也可以指文体、体裁。曹丕始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在当时也是一个流行的概念,指人的气度、气质、襟怀、才性,总之与人的精神个性有关,起初人们用“气”来品藻人物。曹丕把“气”与“体”相联,以文气论文体和风格,品评当时的作家作品。指出:“王粲长于词赋,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气”和“体”在这里均有生命意味。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指的就是文章风格。司马迁所说的“志”,扬雄所说的“情”,曹丕所说的“气”都是作为风格的内在根据提出来的,涉及作家禀赋和创作个性的方方面面。只是他们分别从一个侧面来强调人格志向、审美情趣、个性气质对文学风格的决定作用。而刘勰则把三者整合丰富,以专论的形式充分阐述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性)对文学风格(体)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明确提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各师成性,其异如面”,“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这就是说,作家的精神气质充实浸透他的思想感情审美情志,思想感情审美情志决定语言格调,文章所流露的风采才华,都是作家创作个性的表现。各个作家按照自己的创作个性进行创作,作品的风貌就各各不同,正如他们的面貌各各不同一样。才性的差异,造成了风格的多姿多彩。对此,他列举众多作家的例子加以说明:贾谊才气英俊,所以文辞洁净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行为狂放,所以文理虚夸而文辞夸饰;扬雄性情沉静,所以辞赋含意隐晦而意味深沉;刘向性情平易,所以文辞的志趣明白而事例广博;班固文雅深细,所以文章的体裁绵密而思想细致;张衡学识广博通达,所以考虑周到而文辞细致;王粲急躁而勇锐,所以锋芒突出而果敢有力;刘桢性情偏急,所以言辞雄壮而情思警人;阮籍行为豁达,所以文辞音节高超而声调卓越;嵇康豪侠,所以兴趣高超而文采壮丽;潘岳轻浮而敏捷,所以锋芒毕露而音韵流动;陆机庄重,所以情事繁富而辞义含蓄。他由此得出结论:外表的文辞和内在的性情气质,必然是相符合的——“因内而符外者也”。“风格”一词起先也是用来品藻人物的,见于葛洪的《抱朴子》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渐渐由评人转向评文,如北齐颜子推在《颜子家训·文章》篇中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这里所说的文章的“体度风格”,同样与作者的生命状态有关。总之,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的文论家们已经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成因说,把文学作品的风格看成是作家内在情志和生命状态的外化和表现,这一点一直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风格研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西方,持相似观点的也不乏其人。瑞士著名美学家海因里希·沃尔夫林在《艺术风格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路德维格·利希特(1803-1884年,德国画家、雕刻家、插图画家)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有一次同三个朋友外出画风景,四个画家都决定要画得与自然不失毫厘,然而,虽说他们画的是同一画题,而且各人都成功地再现了自己眼前的风景,但是结果四幅画却截然不同,就如四个画家有截然不同的个性那样。述者由此得出结论,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视觉,人们对形和色的领悟总是因气质而异的。”把艺术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即风格的不同,最终归结为气质、性格等主观条件的不同,这在中西都是一致的。在西方,此种观点同样导源于古希腊,因为那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时代,后世的理论大多可从这个时代找到源头,甚至找到同一个鼻祖。如亚理士多德虽然强调从外部形式和修辞学的角度研究风格,但与此同时,他在《修辞学》中也曾指出:“外部的语言符号”“也表现了你个人的性格”。因为“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气质的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的表达方式。我所说的‘阶级’,包括年龄的差别,如小孩、成人或老人;包括性别的差别,如男人或女人;包括民族的差别,如斯巴达人或沙利人。我所说的“气质”,则是指那些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气质,因为并不是每一种气质都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这样,如果一个演说家使用了和某种特殊气质相适用的语言,他就会再现出这一相应的性格来。”显然,亚氏所说的“气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同一“阶级”的人可能具有相似的气质,只有“某种特殊气质”才“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而“外部的语言符号”也只有与之相适应,才能表现个人的性格,从而呈现为风格。在西方,而后在中国,都广为流传过一句名言:“风格即人”,其实与亚氏的观点倒是一脉相承的。这句名言出自18世纪的法国博物学家、文学家布封(Buffon,1707-1788)之口,他在1753年一次论风格的演说中指出:“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的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与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写的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是人的本身。”换句话说,“风格是当我们从作家身上剥去那些不属于他本人的东西,所有那些为他和别人所共有的东西之后所获得的剩余和内核。”这是对前一段话的最好注解,虽然可以商榷,但其本意却是强调风格的重要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这与从伦理学意义上所说的“文品即人品”或“文如其人”则相去甚远。西方人的理解往往更切近原意,如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正确地引用过这句名言。黑格尔说:“法国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马克思则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形式。‘风格就是人本身’。”无论是黑格尔所说的“他的人格”,还是马克思所说的“我的精神个体”,都是就人的独特的精神个性而言的。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与众不同的精神个性才是造成风格差异的最后根源。不少作家、评论家也都倾向于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文学风格,至少把这作为风格论的重要内容。歌德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的标志。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别林斯基也说过:“风格——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风格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风格里表现着整个的人;风格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在理解这一观点时,需要知道对此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主要是针对布封而发的。如瑞士理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Wolfgang Kayser)指出,“风格就是本人”是一种“天真的信念”。他提出的理由是: “盛行的风格规律、公共的嗜好、代表性的模范、世代、时代等等,它们统统对创造作品的作家发生影响,正如选择的类别本身已经对他们发生影响一样。它们抓住了作家,把他带到这里来,对他施加暴力。”仅这句话就涉及风格形成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公众的趣味、典范的作家作品、时代和传统的影响,以及文学类型的约束等。这些影响使风格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如布封所说的剥去一切共有的东西后的“剩余和内核”,而必然兼有个人性和共同性,因而也就有了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地域风格和流派风格和所谓文体风格。当然,凯塞尔也承认,“就是那些共同支配的超个人的力量到底也永远需要人来阐明。作家生活着和使这些力量发生效果,因此他的人格不仅只隐藏在大量减除之后所剩下来的东西的后边。我们也可以相信,渊博的学识,最小心的考虑和非常细致的感觉也可以把那种由于盛行一时的风格规律、公共的嗜好、束缚的模范等进入他的作品,但是在个人方面却是‘不适合的’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之下重新剔除出来。”①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即公共的东西和个人的东西需要相互适合,成为统一的东西在作品的风格中得到呈现。
认为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这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考察,从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来理解,这无疑是必要的。历来的理论家从此出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并从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方面来分析他们的作品,描述其风格特征,对读者的鉴赏和把握也有较大的帮助。事实上,这是一种广义的心理分析,具有前一种本体分析即言语分析所不及的一面。但是,如果只看到内心表现的一面,忽视外在表达的一面,那么还不能完全理解风格。此外,日常个性不等同于创作个性,不能直接转化为文学风格,对此我们稍后再作分析。在此需要对“心画心声”说,或流传更广的“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诗品出于人品”、“风格即人格”等说,作具体的分析。这些习惯性用语有较大的模糊性,适用于笼而统之、泛泛而谈的场合。但如果较真起来,却是不甚准确的。如晋代诗人潘岳曾写作《闲居赋》,似有隐逸之志。然而据《晋书》记载,此人“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既仕官不达,乃作《闲居赋》。”金代元好问曾以潘岳为例对“心画心声”说提出质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都穆在《南濠诗话》中同意此质疑,认为“有识者之论固如此”,并进一步指出:“盖言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字,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不足以观人者。”这就不仅反驳了“心画心声”说,也诘难了“文如其人”、“文品即人品”、“风格即人格”诸说。世人常说“道德文章”,把“道德”与“文章”相联,但两者既可能一致,也可能大相迳庭。所以,如果仅从伦理着眼,就难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清人叶燮就犯了这个错误。他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每诗以见人,人又以诗见。”纪昀说得更简单化:“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诗教堂诗集序》)近人钱钟书对此类说法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辨正,他列举历代文人言行不一或言言不一、“如出两手”的种种事实,说明“以文观人,自古所难”。同样,“‘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少先见之明。”他精辟地指出:“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钱氏的意思很明白,写什么容易作伪,而怎么写却不易作伪,所以“文如其人”主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如言语的“格调”、行文的“笔性”等。故如以此评说作品,当“不据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之词气”;“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也。”此言所论,甚为精当。其实古人也有反对把人品和文品等同起来的,如梁简文帝就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说明为文不同于为人。宋代吴处厚《青箱杂记》说:“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为之邪人,兹不尽然。”明确反对以文断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诗品与人品不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无须讳言的。这里所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如一个商业社会,老板与雇工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那么作家的意识自然也会有一个倾向于谁的问题,如果在文学描写中表现出来,自然也就会有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例如描写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写山水花鸟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的普遍之情。这些道理是明显的,无须多讲。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就是说,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与人类的共通的意识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意识,常常是与人类的普遍的意识相通的。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例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下层人民的歌谣,但那种表达恋人对爱情的忠贞这种感情,则不但属于下层的百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重要表现。
第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功能上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当然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不合道义的弊端的评价与认识;有的作品则表现为对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的认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不然。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不包含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文学的反映包含了认识,却又不能等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们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这种规律性的揭示,不是在发议论,不是在写论文,他是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通过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暗中透露出来的。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2]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发挥黑格尔的“情致”说时也说:
艺术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3]
这应该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它的形态是“诗的思想”。因此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识,就往往是难于说明的。例如《红楼梦》的意识是什么,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今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仍没有满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十分丰富的,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由于是情致,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认识就像盐那样溶解于情感之水,无痕有味,所以是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的。
第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学是审美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游戏,就是娱乐,就是消闲,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仔细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就是说它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这两者的交织。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个作家正在描写一处美景,却在想入非非地动心思要“占有”这处美景,那么他的创作就会因这种“走神”而不能艺术地描写,使创作归于失败。一个正在剧场欣赏《奥赛罗》的男子,若因剧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恼,那么他就会因这一考虑而愤然离开剧场。在创作和欣赏的时刻,必须排除功利得失的考虑,才能进入文学的世界。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Diderur 1713-1784)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谴,写不下去。[4]
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的确,只有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中,才会发现事物的美,才会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文学的世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Brandes,1842-1927)举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关心的是金钱,所以他要算木材的价值;植物学家关心的是科学,所以他关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艺术家是无功利的,这样他关心的是风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说那样:“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康德的理论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审美意识形态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对的。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 因此风格不构成作家成败的读者关键 风格只是一个作家在个人个性的表达,而这个风格是否被读者认同 才是作家成败的关键。 有问题请加374979564 惯性自恋为好友 或者是baidu luckly20110310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