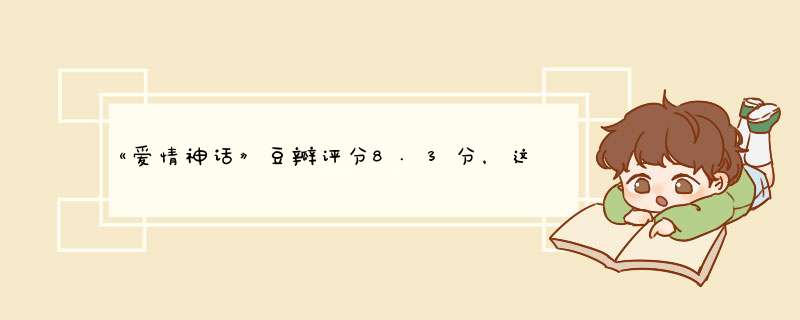
《爱情神话》自上映以来,反响热烈,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这部影视作品之所以能受到观众的好评是因为在剧情设置和演员角色安排上都是比较到位的,剧中的情感与观众产生了共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爱情神话》豆瓣评分83分,这部剧是今年最有腔调的爱情喜剧片吗?
剧情紧凑,感情色彩丰富、生动在上海的生存人才能感受到这部影片的好处。当老上海人看到**中的一些细节时,他们会微笑。他们用上海人的口头禅“非常聪明”来赞美这些作品。这部剧最大的优点是,它展示了生活在城市中的这些成熟男女的真实爱情心理。它说这是一部从女性角度看的爱情**,这是站得住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情感的思维和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这部剧也捕捉到了时间上的变化。故事围绕着几个中年人的婚姻、爱情、往事和纠纷展开,有时还迸发出一些富有人生哲理的金句。可能需要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其本质。扮演一个角色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和体验这个角色。为了不愧于剧本和观众。
演员演技精湛,与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部影片描述了市场和日常生活中的烟花爆竹,没有暴力冲突,注重展现生活情趣。邵一辉非常担心,因为她觉得剧本不够商业化,也不是标准的三幕风格。她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甚至有一个流水账。但制片人、制片人和公司都认可她的剧本,并希望有这样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是最绚烂的花!这部非常精致的**在寒冷的冬天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看完后,我被整部**的气氛感动了!充满回忆,**中有许多要点要讲,而配乐点燃了气氛!演员作为一部悬疑片,情节的严重伤害是无法忍受的。一两个问题可能是创意团队的错误。普通观众和文艺青年都能找到乐趣,感受到乐趣。
这部**中的爱情没有太多的情感起伏,也没有绝望的冲动。只有平凡的向前和向后看,流水和烟花在市场上显得平静。事实上,这是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中年人的爱情,尤其是经济独立的文艺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爱情。在某个时刻,他们会被文学风格、经济条件和体贴的中年人老白打动,但理性使他们回归现实和平静。希望其独特的海派浪漫喜剧风格和良好的声誉使更多的人愿意去看,并在票房上掀起反击。这部**更像是一群普通人的生活写生。人物形象生动,细节细腻,构思巧妙。演员们演绎小市民的故事。导演想要表达的愿望真的很强烈。有中年人对感情的态度。从礼节上讲,你来我走。
立意新颖、独特,创新性强在之前的**中,有太多的伤感女性、圣洁女性、蛇蝎女性和妖艳女性,爱情神话中的女性不再是传统男性想象中的凝视对象和象征。他们都反对客人,让主人公被动,以试图恢复他们的身体和情感主观性。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部**都是去标签的。但相对而言,女性的角色更加模糊。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也具有女性对家庭细腻温柔的关怀,有着无法控制生活的无助的一面,不只是释放荷尔蒙,过着粗野的生活。女性角色也具有男性强势自我的特征。他们不局限于封建性别关系的规则,也不象传统思想所要求的那样善良、可爱、温柔。即使讨论的问题对社会非常敏感,这部**也没有侵略性,也没有女权主义和阳刚之气的宏伟愿景。它只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与你讨论。没有评价和结论,观众可以看到它们。
京海之争名词解释: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派、海派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22世纪37年代的“京海之争”是一场在当时颇受关注的文学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南北文 学之间的潜在对立被公开化,提出了具有地域文学色彩的“京派” “海派”概念。
京派:主要指30年代活跃在北方文坛的一个文学流派。作家们主要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俞平伯、凌淑华等,以及后起之秀林徽犬、萧乾、芦焚、汪曾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等。
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水星》、《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海派文学特质:商业化、市俗化、现代性。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取代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现代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都市漩流”的海派文化形态。物质性、消费性、娱乐性、文化先锋探索。
桃花小妹。玛丽外宿中。我的完美男人。黑糖群侠传。下一站,幸福。霹雳mit。恶魔在身边。换换爱。命中注定我爱你。公主小妹
书;家之女神。心跳小夜曲。草莓帮。追爱抛物线。仲夏夜之恋。214度恶龙王子。森永高中三年二组
door品牌是中层档次。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door是石库门牌子的女装,上海佳盛名品服饰公司岀品SKDoor石库门,源于上海的本土品牌SKDOOR石库门,作为海派浪漫、精致、崇尚自然时尚悠生活的推广者,《石库门》女装熟知女性特质,不断推出真正适合女性肤色、身型又具有海派范儿的时尚产品,采用整体设计思路、流行元素应用、上乘考究的面料、别致的产品设计、与个性的顾问服务,满足休闲娱乐、公众场合、私人聚会不同场合的需求。
“京派”:指30年代活跃于北方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它以《水星》《骆驼草》等杂志为阵地,重视文学的审美特性,主张文学远离政治,主要作家有李健吾、沈从文、朱光潜、林徽音等。
一、概述歧出的“京派”观念
在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文学现象。人们对它究竟何时何地以何面目存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在不同研究者和当事人那里,京派的能指和所指常常滑动不定,有的甚至否认京派的流派特征。现代学界也也远未能达成一致。许道明先生甚至把左翼精神盟主鲁迅也归为京派,他说:“对于鲁迅,从他的经历、教养、情感、趣味、作风中相当部分倒是同‘京派’连在一起的,说他曾是一个京派人,也不是没有根据的。”[1](24)一般被认为京派标准成员的萧乾,在王嘉良先生看来不但不是“京派作家”,倒属于“人生派”作家。[2](44)这种关于京派流派存在与否及其流派性质的认识分歧,其实是现代文学史中各家各派对京派各持己说的延伸。而且关于京派观念歧出的问题,至今没被厘清辨正。
为了解决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我们首先要看看京派人自己怎么说的。曾被人们视为京派文学理论的台柱的当事人之一朱光潜,在事过境迁后回忆起来,也仍旧用的是春秋笔法。他在自传中说:“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的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 [3]在1980年第5期的《花城》中《从沈从文的人格看沈从文的文艺风格》一文中,他又说:“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说“海派主要指左联”,然有乖史实,只说对了一半。“占据”“纠集”“阵地”等战争术语的移用,也透露出其在被批斗后所认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明达如朱光潜后半生也难免受其蔽。而他所说的“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号中一“博”字,也委婉地暗示“京派”不过是被虚构出来的。 萧乾也说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来研究,“本身就不很科学”。[4]再看看沈从文。他早期见赏于徐志摩,属准新月派;当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后为胡适提携当中国公学的老师,接着又应杨振声之邀执教于一时学者云集的青岛大学;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海之争的始作俑者;卷入过林语堂鲁迅关于“文人相轻”的论争;1936年又挑起了关于“差不多”的论争,与茅盾打笔仗;1946年又以“自由主义”的招牌提倡“第三种力量”从而与郭沫若等发生论战。从文学运动的阶级立场上看,他整个现代文学史期间的言行都与高度政治化的左翼相龃龉;从文学的独立审美的角度看,他始终坚持自由、严肃、健康的文风,指斥商业化了的浮薄文风。无论创作、批评、经历或者文学观念,他都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京派人物。那么他笔下的京派是不是就清晰明了呢事实不但不然,反而正是他,模糊了流派界线、取消了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给人一种京派无派、京派没边的印象。而且他根本就没提“京派”一词,只提“京样”“北方文学者”等指代不确的词。在1931年发表的《窄而霉斋闲话》一文中,他视“京样”的文学为“人生文学”,与“海派”相对立。他说:“京样的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 [5](93)他那篇挑起京海纷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也根本不在讲流派,而是在批评文坛的浮薄空气,尤其是批评玩票白相文学者的玩文学的创作态度。因为旨在评议一种当时普遍的文学风气,所以沈从文并没存心歧视或抬举某地,于京沪两地,几乎各打了五十板。他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 [5](154)如此看来,我们说沈模糊流派界线取消文学流派的应有之义似乎是欲加之罪。
但事实上,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一石激起千层浪。沈从文在1933年10月18日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竟招来了象阿Q奚落王胡时所说的“谁认就骂谁”的自认者。上海的苏汶在同年12月《现代》第4卷第2期上发表《文人在上海》,尽诉上海文人的委曲,并拂违沈之本意地把“低级趣味等同于那种浮薄文风等同于上海作家的作风”作沈之观点进行驳斥。沈对此则作了“人不知而不愠”、和善又稳健地回应,于1934年1月10日发表《论“海派”》一文。文中用了大量笔墨诠释“海派”:“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从官方拿到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出一书,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的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5](158)文中虽未提京派,但论争的气氛已经明显呈现出京海对立的态势。京派观念(区别于京派史实)也就是在这次论争中作为海派的“他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在京海对立的二元语境中诠释海派,完全可以视为反面地说银币的另一面——京派。他不该把本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海派无边的诠释成一种创作风气。我们知道,一种风气不仅可超跃空间,如不拘限于北京或上海,而且可以超跃时间,可以是一种古已有之遗流难绝的东西。他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就指出白相票友文学乃是魏晋以降一直都有的。他这种以论一种超跃时空的文学创作态度去诠释进而等同一个在时间空间都很具体的文学流派——海派时,其不妥之处就不揭自彰了。不幸地是,论争中与海派二元对立存在着的京派,因其作为海派的否定性存在和海派他者形象而跟着从一个具体的流派概念泛化成一个说明正经严肃文风的形容词了。可见,在京派巨子沈从文那里,京派的能指与所指、名与实依旧是含混不清、黄白难辨。
其次,我们看看当时超然于京海之外的人是怎么看待京派的。
曹聚仁曾利用沈从文《论海派》一文中所诠释的海派内涵,进行过一番京海“无以异”的论证,作后索性把两者等同起来模糊京派与海派的界线。他说:“胡适博士,京派之佼佼者也,也讲哲学史,也谈文学革命,也办《独立评论》,也奔波保定路上,有以异于沈从文先生所谓投机取巧者乎曰:无以异也。海派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而京派则独揽风雅,或替摆出百年周纪念、千年周纪念,或调寄《秋兴》十首百首律诗,关在玻璃房里和现实隔绝,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海派文人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吃吃喝喝;京派文人,则从什么什么基金会拿到了点钱,逛逛海外,谈谈文化,彼此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6]
与曹聚仁之于京海两派一视同不仁的看法近似,鲁迅也给京海各赏五十板。他由北京上海两地的地域本质发挥开来,用近乎四六韵文,侃趣十足地将京派海派漫画成官商的帮手,且各事其主。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乎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 [7](655)
第三,我们看看后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眼里的京派是个什么角色。
曾在“五四”时纵火赵家楼、又是“沉钟”社的干将的杨晦本与京派也渊源颇深,但后来熟练地操起了阶级分析法。他在1947年春季的《文汇报•新文艺》周刊首次用阶级观点将“京派”“海派”利索地等量代换为“农民派”“人民派”。从解放战争到文革结束,随着***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左翼的这种思维得以迅速蔓延、强化。京派分子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文人集团。如郭沫若在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中所登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文中,萧乾被斥为麻醉人民的黑色鸦片,并用四海皆通的“凡是”句式判定:“凡是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冯乃超同在这一辑上撰文《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判定沈从文的作品《熊公馆》为“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企图重新团结一些反人民的精神贵族来反抗人民的胜利”,所以是“今天中国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沈从文因与熊希龄的老乡关系、曾为后者所知遇培养、又写过一篇评颂熊氏熊母的文章等诸种缘由,被冯乃超认定是延续清客文丐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朱光潜则被邵荃麟在与上同一组文章中抨击为“笔管下飕飕的闪出残忍的杀机。这正是你们御用文人不见血的最恶毒的地方”。(《朱光潜的怯懦与反动》)这种把本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阶级分析法简单僵化为“不革命即反革命”的思维逻辑,严重歪曲了京派的派性及其本质,并长期左右着人们的认识。
二、透视歧出的“京派”观念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其任务之一是要科学利用以前阐释者所给予的启示和所提供的路径,辨析史料、考证史实,从而透过各色的历史迷雾,发幽显微,揭示历史的原生态。上文中不厌其烦、琐琐碎碎的罗列加诸京派的各种分歧性认知,目的就在于希望能利用各种对京派的记忆、言说及阐释,发现存在于各种分歧性认知之间的差异当中所内涵的京派的质的规定,并为考辨京派的原生态作准备。
首先,京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一股文学思潮是否合法它是不是只是三十年代京沪两地争论者用意气生出的一团虚火事实是不是真如萧乾所说的“把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分作京派和海派”,只是“文学史家为了省事” [8](62)
这一切还得从京海论争说起。从论争的时空角度看,这次论争是1933年10月由北京的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挑起的。同年12月上海的苏汶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辩驳。1934年1月沈接着写了《论“海派”》以解释之。随后便引起文艺界的全面反响,鲁迅、曹聚仁、胡风、杨屯阝人、徐懋庸、姚雪垠、森堡、祝秀侠等纷纷介入。最后于1934年2月17日刚从家乡回来的沈从文失望的写了《关于海派》一文,以因严重歪曲其本意而气得“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作结。[5](164)但从论争性质的逻辑顺序看,此次争论,其上可追溯至沈从文1931年6月发表的《窄而霉斋闲话》说起。此文较之于《文学者的态度》,其所反对对象的明确度、挑衅对方的刺激性都鲜明强烈的多。从此文中也可以看出,左翼、现代派等作家的反弹决不是意气用事、借题发挥或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请看文中是怎么写的:“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还说:“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人沾沾自喜的习气。” [5](93)以后多年一直念叨的什么“琐碎”“菲薄”“玩具”“白相”“讽刺”“诙谐”与“趣味主义”概念,他在本文中悉数提出,并寄以希望地教训了一番。而循着逻辑顺序往下,此次论争则延续至双方都偃旗息鼓一年后的4月14日鲁迅的另一篇《“京派”与“海派”》的发表。他老人家再次揭穿两派“帮”的共同本质及其因此导致的对立之后的同流合汇现象。 尽管京海论争只是京派文学活动的一部分,但正是它使得京派从无名有实的自由状态走向有名有实的自觉状态,使得其在与海派的对立中丰富明确了自己的本质内涵。这一点,在今天学界几成共识。 正如旷新年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次“论争成为京派成熟和壮大的一个重要标志。‘京派’和‘海派’论争的‘京派’含义和文学史上的‘京派’的含义并不是完全重叠的,但是‘京派’和‘海派’论争的爆发显示了‘京派’的独立存在以及雄视文坛的气势。” [9](260)我们也不妨归纳一下在京海论争中所透显的京派的本质内涵。
沈从文虽无意在其仅视为一种风气的代名词——“海派”的对立面再设立一个“京派”,以造成流派的对立形势,但他在坚持“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 [5](93)时却用了一套标准:即,要求有“尽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10](4)“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 [5](24)的文学者的岗位意识;要求有不要只“记着时代,忘了艺术”所应有的尊严与品格的文学的审美本体意识;坚持“怀疑否认”“修正改进”“天真勇敢”的理性精神和自由原则;坚决反对文学成为商业、政治的工具,反对“差不多”现象与专事模仿稗贩的非艺术化倾向。[5](56-59)这一整套文学观念恰恰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虽然微弱却非常坚韧的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文学观念体系。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外各自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是在各种文学内外条件的因缘会合下,籍京海论争的机会得以成为一个以“京派”为名,与现代派、左翼文学、国民党党治文学及各种以市民口味、商业利润为导向的种种末流文学(如鸳鸯蝴蝶派)等文学流派相生相克的文学流派。
我们已然从各种复杂的材料中分出无名有实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有名有实的京派文学。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作为历史史实中的京派与个人观念中的京派的区别。历史史实中的京派文学不论有名无名,它总是客观存在着,但在个人观念中的京派却不大一样。每个人都可能从自己的先见和视域出发,根据一定的历史现象构造出个人的京派观念。分析不同人的京派观念可以挖掘出他们各自的论说基点。而这些论说基点不仅可以解释当时的京海纷争的乱象,还可以见出京派流变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更能从本质上认识有名无名的京派的来龙去脉,也因此能更准确地界定京派。�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切入京海论争取得是基于其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底蕴之上审美本质角度,而苏汶的反弹则基本上是为上海作家申诉被误解甚至被轻视的委曲,切入的角度乃是地域本质。他对作家居处的敏感很难说是冲着沈从文那篇淳厚的文章去的,多半还是因为沈从文稍带着的籍贯论据触动了他心中因深味着人们对海派文化的历史性歧视而所积压的不满。因为长期以来,无论绘画、戏曲、服饰,京派都代表着正统而海派则联系着轻浮。 除了从审美本质、地域本质立论外,像杨晦、郭沫若、冯乃超、邵荃麟及晚年朱光潜等则是从阶级本质的认识基点出发形成了自己的京派观念。这一点笔者已在前文阐明。在诸多的论说者中,最深刻的还得算是鲁迅、曹聚仁。鲁迅那看似诙谐超然的文章也最让沈从文生气。他在《关于海派》一文中不无痛惜地说:“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浑”,“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且照流行习气作着‘只在那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 [5](93)鲁迅在1934年1月30日连写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两篇名文。从文章表面看,确如沈所言的不过是随意兴感而已,但实质却透露出沈鲁之间更深隐的不和谐的底色。终鲁迅一生所立文字,我们可以毫无迟疑地得出鲁迅也是主张“文艺本身乃是独立自由、审美感性的”结论。他对文坛各种浮薄油滑文风及其公式主义创作方法的批判可以说较沈激烈得多,也深刻得多。 沈鲁在文艺的审美本质观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有时连表述都神似,如沈之“名士才情”“商业竞卖”与鲁之“才子+流氓”“商定文豪”。也正是由于他们在审美本质观上一致,有人如许道明才认定鲁迅曾是个京派。但所有这些都掩盖弥合不了从文化本质的基点出发对待京派的深刻分歧。鲁迅一贯用包涵很浓的阶级眼光但比阶级眼光深广的文化眼光去批判中国文化中所充溢着的惰性、迂阔、无聊及贵族气,尤其是集中代表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他也正是以这种文化批判的犀利眼光,看到了京海两派在深层的文化层面上的一致,并揭示了他们“帮”与“有闲”的共同本质,且无不悲观的担心“无所用心”与“言不及义”的南北交融将产生“不祥的新劣种”。[11](656)这种预测竟果然发生在1934年后的南北文坛上。如,1934年1月上海的巴金、郑振铎北上与章靳以合编《文学季刊》,“初步打破了‘京派’和‘海派’的樊篱”。1934年4月5日海派刊物登出了周作人五秩自寿诗。之后,经林语堂精心策划,一时京海争诵、酬唱不绝。1935年4月14日鲁迅再写的一篇《“京派”与“海派”》中也举了实例映证了他所预测的不祥的新劣种——“京海杂烩”:“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指施垫存编印《晚明十二家小品》——引者注),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指周作人——引者注),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指1935年2月在上海创刊的《文饭小品》—引者注),真正老京派打头、小海派煞尾了。”1936年10月现代派的戴望舒与京派的卞之琳、孙大雨、冯至、梁宗岱等合办《新诗》月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海派与京派的合流,象征诗派与格律诗派的合流”。再如,1936年4月沪版《大公报》开设,萧乾从此长驻上海了,且经巴金介绍与鲁迅保持接触。
综上所述,京派观念的歧出,乃是因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京派的结果。沈从文切入京海论争取得是基于其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底蕴之上审美本质角度;苏汶的反弹则基于他人们对海派文化的历史性歧视而所积压的不满,切入的角度乃是地域本质。而杨晦、郭沫若、冯乃超、邵荃麟及晚年朱光潜等则是从阶级本质的认识基点出发形成了反动落后甚至凶残的京派观念。鲁迅超越单一阶级的眼光,从文化本质的基点出发对待京派的深刻分歧,批判中国文化劣根性,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从而揭示了京海两派“帮”与“有闲”的共同本质。只有看到审美的、地域的、阶级的、文化的不同立场,才能见出京派观念歧出的内在原因,也才能历史的揭示京派的流派特性。在概述和辨正歧出的京派认识之中,我们清初的看清了它的流派特性,即,京派乃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自由主义文艺观为本质,籍京海论争的机会得以成为一个以“京派”为名的一个文学流派。归纳起来,该派坚决反对商业化、政治化等非艺术化倾向,主张文学家要持存有文学者的岗位意识、审美本体意识、理性精神和自由原则。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