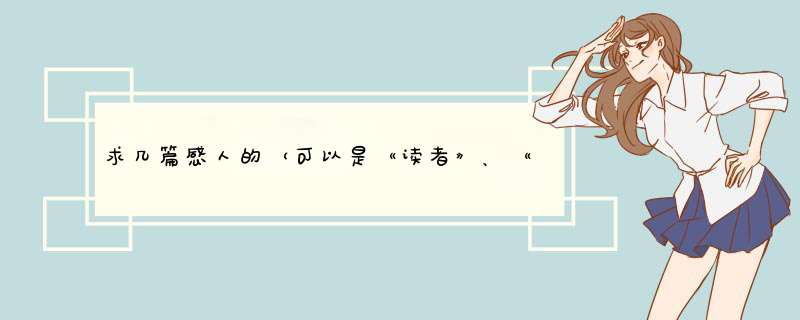
两颗钉子
每晚8时左右,有一位衣着褴褛然而神情坦然的老头,总会准时来到大院捡破烂,然后就默默离去,从不晚点,也不久留。
第一次见到老头时,他正在与门卫大吵大闹。他要进来捡破烂,门卫不让,说这是县委大院,而且又是晚上。老头便粗着脖子说:“我靠自己的双手捡点破烂糊口,凭啥不让?当我是小偷不成?!”老头很瘦,脖子上扯起根根青筋。他的缕缕白发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当时认为老头有些倚老卖老、无理取闹的意味,然而几天后,我发现自己错了。
后来也不知门卫怎么就让老头进来了。老头每天都来大院垃圾箱里翻找破烂。但与别的捡破烂的不同,他每次都在天黑以后才来,白天从不进来,而且他捡垃圾就是捡垃圾,除垃圾之外的东西秋毫无犯。这对一度饱受“顺手牵羊”之苦的大院住户来说实在是个惊奇的发现。后来,我们知道了关于他的一段凄楚的身世:老头是某国营工厂的退休工人,由于老伴长年体弱多病,老两口没少受儿媳的气,倔强的老头不甘过仰人鼻息的日子,与老伴租了间破房相依为命。由于原单位倒闭了,生性高傲的他为了凑足妻子抓药的钱,不得不背上了捡垃圾的蛇皮袋。
了解了这段隐情后,大家都唏嘘不已,从此看他的眼光中就多了几分同情与敬重。一次,邻居大伯担心他晚上捡不到什么,便将一袋上好的橘子递给他。老头一愣,随即嘟哝了一句:“我是捡破烂的,不是乞丐。”拍拍手,提着瘪瘪的蛇皮袋起身就走。接下来的好几天里他都没有再来。
大伯默然。几天后,老头终于又出现在大院的垃圾堆旁。趁他离去时,大伯回屋拿出铁锤,在垃圾旁的大树上一上一下钉了两颗铁钉。第二天黄昏,大伯将一些包扎好的食品,挂在上面的钉子上。又将一些旧书、旧报捆扎在一起挂在下面的钉子上。第二天,捡破烂的老头来了,他取走了挂在树上的那两个食品袋。他当它们是别人舍弃不要的垃圾了。
后来,大院里的许多住户都知道了这一秘密,于是树上的钉子上便常常多出许多涨鼓鼓的食品袋来。门卫也很默契,晚上除了让老头进来外,对其他捡破烂的则一律拒之门外。每天晚上老头进来后总要先在垃圾堆里翻找一通后,再去取那些食品袋。据经常晚归的小王讲,一次他看到老头在取那些食品袋时,竟然泪流满面。
尊严无价!面对他人脆弱易碎的尊严,有时无声的呵护更胜过万语千言,比如,大伯钉在树上的那两颗钉子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收音机里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甜甜的泥土
黄飞
西北风呼啸着,残雪在马路上翻卷。虽已立春了,天还是很冷。
她,倚着学校门口的一棵杨树,一动不动,宛如一座雪雕。
一阵电铃的急响。她黯淡的眼神里,射出热切的光。
一群唱着歌儿的孩子,跨出了校门,没有她的儿子;又一群说说笑笑的孩子,踏上了马路,也没有她的儿子……人影稀疏了,零落了,没有了。
吱呀呀的大铁门,锁住了沉寂的校园。
她一阵晕眩,几乎站立不住,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双手紧抓铁栏使劲地摇着。
“干什么?”传达室的老头面带愠色走了出来。
“亮!我的小亮!”像喘息,又似哭泣。
“都放学了。”
“知……道……”她目光呆滞地低声喃喃着,无力地垂下脑袋,慢慢松开手,从大襟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包裹得很紧的、还带着体温的糖:“大伯,麻烦……给孩子。”
“叫什么?”
“王小亮。”
“几年级几班?”
“今天,刚过,八岁生日。”
“我是问几年级几班!”老头显然有点不耐烦了。
“哦……大概……”她又惶然地摇摇头。
老头奇怪地打量着这神经质的女人:“你到底是什么人?”
回答他的是夺眶而出的泪水和踉跄而去的背影。老头在疑惑中叹了口气,似乎明白了什么。
下午,这包糖终于传到二年级二班王小亮手中。孩子惊喜极了,这最喜欢吃的奶糖好久没尝过了。他那双小手在衣服上来回蹭着,微微思考了一下,笑眯眯地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颗,给要好的伙伴发两颗,又恭恭敬敬地给了老师五颗。“吃呀!”他快活地叫着、跳着,连那只张了嘴的破鞋都甩掉了。同学们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和他一起分享着欢乐,只有老师悄悄背过了身……
放学了,小亮还沉浸在欢乐之中,蹦蹦跳跳地朝家中走去。蓦地,他站住了,摸摸口袋里还剩下的舍不得吃的糖,一股恐惧感袭上心头。他好像又看到:现在的妈妈扬起细眉在爸爸的耳边嘀咕什么,爸爸抓起一根柴棍,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他愣怔着,不知如何办才好。他使劲拍拍口袋,不行,咋瞧都是鼓囊囊的。他低下小脑袋,吮着指头,想了许久,瞅瞅四周无人,迅速将糖埋入路边的雪堆中,还特地插上一根小棒棒。
这一夜,小亮睡得特别香,特别甜。他梦见过去的妈妈笑着回来了,现在的妈妈垂着头走了,真高兴。
第二天,小亮起得特别早。他照例先把全家的便盆倒掉、涮净,再淘米、添水、捅火、坐锅,然后才背上书包拿块冷馍悄悄溜出门。他要赶紧去挖他的糖。不想,一夜之间地温回升,冰雪消融了,糖浆和雪水混在一起,渗入大地。潮湿的地面上,歪躺着几张皱巴巴的糖纸和那根作为标记的小棒棒。
小亮眨巴眨巴眼睛,忍不住滚下泪来。他伤心地蹲在地上,呆呆地凝视着。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伸出冻裂的小手指,抠起一点泥土放在舌尖上--
他,又笑了:那泥土,甜丝丝的。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