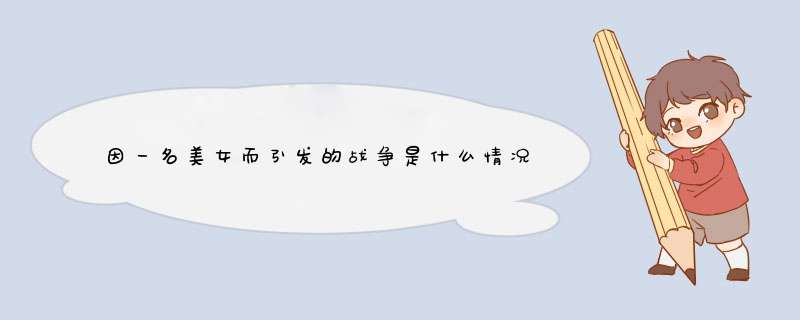
这位美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息夫人,传说她容颜倾国倾城,很多君主为了得到她开战,其中就有楚国、郑国和齐国,楚军去攻打郑国,郑国上演了一场空城计,楚军撤退,但是留下了自己国家的旗子,让郑国怀疑,也上演了一场空城计,这就是鼎鼎有名的“双响空城计”了。
楚国的公子元很喜欢息夫人,就想去攻打郑国,来表现自己的男子气概。公子元为了获得息夫人的芳心,带兵去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军队人数不够多,所以处境是有点艰难的,但是这个时候郑国的叔詹想出了计谋,就是打开城门,让百姓按照平时一样生活就好,不要惊慌,军队和军旗全部藏起来。
公子元带领楚军到达了郑国,但是郑国城门打开,军队不敢前行。到达郑国之后,郑国的城门是开着的,就只能看到里面的百姓在悠闲地走来走去,该干什么就在干什么,公子元决定很惊讶,于是就带领将领到了高一点的地方去看郑国,隐隐约约看见了郑国的军旗,所以他就觉得这是有诈,就带着军队走了,但是却留下了自己的军旗。
第二天,郑国的人发现楚国的军队走了,但是他们也看到了楚国的军旗,所以心里还是很害怕,怕会有诈。郑国军队出来看到了楚国的军旗都在城外,但是却没有一名楚国士兵,心里还是很害怕的,这时候叔詹就跟他们说楚国的军队确实是走了,这是他们的空城计。
春秋战国的故事,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秦、晋、齐、楚等大国摁着中原的小国如宋、鲁、卫、蔡等随便狂揍,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实际上,在春秋之初,最先走上主要舞台的恰恰是这些中原小国,他们当时其实并不小,真正小的是周天子分封的边缘诸侯,他们才是舞台旁边真正的看客。
然而,中原诸侯并没有把这台戏演好,几个人在那里抢戏,最终所有人都演砸了,然后淡出舞台,由之前的看客们粉墨登场,最终完成这部春秋战国大戏。
中原诸侯们是怎样把这出戏演砸的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演——郑国。
郑国,是西周末期才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它的国君和周天子周平王是近亲,郑国的前三代国君“郑氏三公”(郑桓公、郑武公、郑庄公)分别是周平王叔祖、叔叔和堂弟,相比于很多从周初就分封的诸侯国,这种关系不知道要亲近多少倍了。
所以,从一开始,郑国就凭借和周天子的这种特殊关系,控制了周朝廷的话语权,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郑庄公以此小霸中原,成为诸侯之首。
这时,盟国齐国向郑国抛来了橄榄枝:齐僖公提出将自己的小女儿文姜许配给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齐、郑两国联姻,强强联合。文姜是当时有名的美女,齐国又是东方的大国,联姻对于郑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政治强人郑庄公倒是满口答应,可是当他咨询公子忽的意见的时候,却被公子忽断然拒绝了。公子忽的理由是:“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齐国虽然强大,但不是我的那道菜,求人不如求己,别人再强大,都不如自己变得强大!
看来这个公子忽还是有点骨气的人,又或许他另有心上人?想寻找真爱?
故事还没完,几年后,北戎犯齐,公子忽率郑军驰援齐国,大败北戎。在庆功宴上,齐僖公不计前嫌,再次提出联姻,可这个顽固不化的公子忽又当面拒绝了齐僖公,理由是:“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宝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意思是:以前都不敢接受,现在立了点寸功,便有非分之想,国人将怎么看待我呢?这理由真是冠冕堂皇。齐僖公这老脸真不知往哪儿搁,便回击道:“吾有女如此,何患无夫?”,后来将文姜嫁给了鲁桓公。就这样,齐、郑两国失去了最好的联姻机会,公子忽即位后(是为郑昭公),郑国就开始走下坡路。
关于公子忽两次拒婚的原因,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按照常理,当时的政治婚姻是很常见的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说什么自由恋爱,都是扯淡;文姜和他的哥哥吕诸儿(齐襄公)确实存在**,但这种丑事怎么可能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公子忽耳朵里呢?
公子忽没有政治眼光是肯定的,不用讨论了,关键的是他拒婚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从后来公子忽上台后对待齐国(包括宋国)的态度可以看出,公子忽并不是不喜欢齐僖公的女儿,而是不喜欢齐国,他不喜欢被别人钳制,他喜欢做真实的自己,公子忽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郑国,维护自己的尊严,不肯向强权屈服!而这种精神,正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仅存的一点儿“周礼”!
应该是妹喜、褒姒、夏姬、孟赢
1妹喜,“妹”读作“mò”,又名末喜、末嬉、有施氏女,有施氏原为喜姓。夏朝末代国王夏桀姒履癸的宠妃。生卒不详。据说,妹喜是后世红颜祸水的第一例证,此后陆续出现商朝妲已,周代褒姒……
夏桀代有施氏(今山东省腾县),有施氏是东方小国,国弱力薄,不敢与夏朝为敌,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夏桀乘热凌人,不准有施氏投降,一定要血洗有施氏,有施氏探知夏桀是一位好色暴君,投其所好,选了美女妹喜进献请降。夏桀见妹喜貌美,十分高兴,遂罢兵带妹喜回到王都斟(左边是寻右边是个耳刀,打不出来)今河南省偃师二里头),妹喜见王都宫殿陈旧,很不高兴,桀王为了讨好妹喜,造倾宫,筑瑶台,用玉石建造华贵的琼室外瑶台,以此作为离宫,终日饮宴*尔,不理政事,
由于桀王的*奢暴虐,人民不堪其苦,商汤乘机起兵讨夏,桀王于鸣条(今河南省封丘东)战船败,挟妹喜同舟渡江,逃到南巢(今安徽省巢东南)之山一道死去。
补:夏桀的宠妃。原为有施氏人,夏桀在征伐有施氏时,有施氏的首领把她献给夏桀。夏桀对她十分宠爱。据《列女传·夏桀妹喜传》载,桀“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妹喜于膝上,听用其言”。又据《帝王世纪》记载,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把缯帛撕裂,以博得她的欢笑。
2褒姒,西周幽王的宠妃,生卒年不详。褒人所献,姓姒,故称为褒姒。有谓她是龙沫流于王庭而变玄鼋使女童怀孕所生女,弃于路被一对夫妇收养于褒。她甚得周幽王宠爱,生下儿子“伯服”。
周幽王姬宫涅的王后,褒姒原是一名弃婴,被一对做小买卖的夫妻眉头,在褒国(今陕西省汉中西北)长大,公元前七七九年(周幽王三年),周幽王征伐有褒国,褒人献出美女褒姒乞降,幽王爱如掌上明珠,立为妃,宠冠周王宫,翌年,褒姒生子伯服(一作伯般),幽王对她更加宠爱,竟废去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册立褒姒为王后,立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叹气道:“周王室已面临大祸,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不出伯阳所预料,原来褒姒平时很少露出笑容,偶露笑容,更加艳丽迷人,周幽王发出重赏,谁能诱发褒姒一笑,赏以千金,虢国石父献出“烽火戏诸侯”的奇计,周幽王同褒后并驾游骊山,燃起逢火,擂鼓报警诸侯一队队兵马闻警来救,至时发现平安无事,又退兵回去,褒心看见一队队兵把,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往往,不觉启唇而笑,幽王大喜,终回此失信于诸侯,公无前七七一年,犬戎兵至,幽王再燃烽火,诸侯不再出兵救援,幽王被杀,褒姒被掳,(一说被杀),司马迁说:“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知,”(《史记·周本纪》)意思是说,褒姒不喜笑,周幽王为了她一人的笑,天下百姓再也笑不起来了。西周遂亡。
3 夏姬是一个颠倒众生的人间尤物,她具有骊姬、息妫的美貌,更兼有妲己、褒姒的狐媚,而且曾得异人临床指点,学会了一套“吸精导气”之方与“采阳补阴”之术,因此一直到四十多岁,容颜的娇嫩,皮肤的细腻,仍然保持着青春少女的模样。
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自幼就生得杏脸桃腮,蛾眉凤眼。长大后更是体若春柳,步出莲花,羡煞了不知多少贵胄公子。由于母亲管教严格,并无私相授受的机会,但却异想天开地编织了不少绮丽的梦境。也许是幻想,或者是真有其事,在她及笄之年,曾经恍恍惚惚地与一个伟岸异人同尝禁果,从而也得知了返老还童,青春永驻的采补之术。之后她曾多方找人试验,当者无不披靡,因而艳名四播,于此也就声名狼藉,父母迫不得已,赶紧把她远嫁到陈国,成了夏御叔的妻子,夏姬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夏御叔是陈定公的孙子,他的父亲公子少西字子夏,所以他就以“夏”为姓,官拜司马,算是陈国的兵马总指挥。由于他是国君的孙子,因此在株林地方有块封地。夏姬嫁给夏御叔不到九个月,便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虽然夏御叔有些怀疑,但是惑于夏姬的美貌,也无暇深究,然而外面却沸沸扬扬地传说:“这个孩子哪里象是不足月的早生婴儿?怕不是夏姬从郑国带来的野种吧。”
这个孩子取名夏南,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身体结实得活像一头小牛犊,十岁以后骑在高头大马上驰骋如飞,时常跟着父亲在森林中狩猎,有时也与父亲的至交孔宁、仪行父等人,一齐骑马出游。
夏南一边读书一边习武,十二三岁便显示出一股逼人的英爽之气,为了承袭父亲的爵位,被送往郑国深造,以期待将来能够更上一层楼。
郑国文人荟萃,地当交通要道,向称礼仪之邦,不管是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均较偏僻的陈国进步许多。夏南以郑国外孙的身份,自然得到了最好的教育,从而也造成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
夏御叔壮年而逝,有人就说是死在夏姬的“采补之术”。夏姬成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小寡妇,花开花落,独守空闺,没有多久,经常进出株林豪华别墅的孔宁与仪行父,先后都成了夏姬的入幕之宾。
夏姬的美艳与风情,特别是床笫之间的旖旎风情,使得孔宁与仪行父两人欲仙欲死。这种三角关系一直持续了数年,终于在长时期的争风吃醋心态下,把当时的国君陈灵公也拉了进来,使得彼此的关系进入白热化的高潮。
大约是孔宁遭受了冷落,于是向陈灵公盛赞夏姬的美艳,并告诉陈灵公夏姬娴熟房中术。不可失之交臂。陈灵公将信将疑,说道:“夏姬的艳名是久已听到了,但都快四十岁的人了,恐怕是三月的桃花,已经没有昔日的盛况了吧!”
孔宁怂恿道:“夏姬天赋异禀,而且熟谙驻颜养生之术,年龄虽快四十,风情却更加成熟,眼见为真,为什么不抽空到株林去看看呢?”
正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政简刑清,闲来无事。于是陈灵公的车驾在陌上花开、春阳送暖的季节里来到了株林,一路游山玩水,薄暮时分到了夏姬的豪华别墅。
事前已经得到消息,夏姬命令家人把里里外外打扫得纤尘不染,更张灯结彩,预备了丰盛的酒馔,自己更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等到陈灵公的车驾一到,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夏姬出身君侯世家,风范礼仪,举止进退,自然是中规中矩。陈灵公眼见面前的这个美人儿,云鬟雾鬓,剪水双瞳配着白里透红的肌肤,雪藕般的皓腕,简直就是初解人事的及笄少女!特别是她那银铃似的声音,风吹弱柳的体态,真像是一团熊熊的火焰,直烧得陈灵公方寸大乱。
酒不醉人人自醉。似乎还没有喝上几杯,陈灵公便惺忪欲醉,斜盼着一旁作陪的夏姬,直觉她犹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而夏姬也秋波流盼,娇羞满面。在跳跃的烛光下,陈灵公不时以亵语挑逗夏姬,夏姬笑而不答,低首不语,一切尽在不言中。
夜阑更深,侍从人员悄悄退出外厢,偌大的厅堂上只剩下陈灵公与夏姬。趁着酒兴,陈灵公开始移近夏姬。首先握住她的手,没有反抗,便将她抱在怀中,仍没有反抗,于是一把抱起来,夏姬浑身没有骨头似的,瘫倒在陈灵公怀中,走向内室,走向情欲,走向罪恶。
对于这个一国之君,夏姬使出了浑身解数,陈灵公身心俱醉。从此,陈灵公有事没事便经常跑到株林夏姬的豪华别墅中来,夏姬事实上已成了陈灵公的外室。
时光荏苒,夏南已经学成归国,不但见多识广,而且精于骑射。陈灵公为了讨好夏姬,立刻任命夏南承袭了他父亲生前的官职与爵位,夏南成为陈国的司马,执掌兵权。
为了报答君侯的恩遇,更为了光耀门媚,夏南恪尽其职,干得有声有色。然而一首歌谣也无情却刺伤了夏南纯洁的心灵。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治酒欢会兮!从夏南!”
意思是说陈灵公的车驾经常来往于株林道上,都是要去会见夏南;而株林别墅中的笙歌美酒,也是陈灵公与夏南在通宵达旦的欢会!
讽刺是十分明显的。夏南本人一直在郑国“留学”,回国立即被委以重任,哪里有时间与陈灵公私下在株林见面与欢会呢?有没有与陈灵公私会,夏南本人最清楚。那么陈灵公以国君之尊,经常风尘仆仆地往株林跑,究竟所为何来?株林住着的就是自己的母亲,答案不难找到。年轻气盛的夏南脸色大变,血脉贲张,他暗地里发誓:如果事情就此打住,那就算了,倘若继续发展下去,使他难以立足做人,那么将来就会产生连他自己也不敢想像的严重后果。
夏南回国后,陈灵公虽然收敛了一些时日,终于忍不住对夏姬的思念,又仗待着自己是一国之君,而且还重用了夏南,于是偕孔宁和仪行父,在夏南归国后的第二个月初,再度驾临株林别墅。夏南听到消息,连忙赶回,初时夏姬还知道略避嫌疑,等到酒酣耳热,就已经了无禁忌,彼此放浪形骸。
夏南忍无可忍,拂袖而起,迅即传令随行吏土把宅第团团围住,接着带领得力家丁,手执弓箭,凶神恶煞般地来到厅堂,对准陈灵公,一箭就结束了他的老命。随即率兵入城,只说陈灵公暴卒,立世子妫午为君,史称陈成公。
孔宁和仪行父仓皇逃到楚国,隐匿了*乱的事情,只说夏南弑君,是人神共愤的事情。楚庄王偏听一面之词,竟决意讨伐。
陈国的民众大都知道陈灵公与夏姬的*乱经过,并没有拥戴楚军,面对楚国的大军压境袖手旁观,夏南被捉,处以“车裂”的刑法。夏姬被带到楚庄王面前,但见她颜容妍丽,对答委婉,不觉为之怦然心动,然而楚庄王必竟是“春秋五霸”中的人物,比较明智,为了楚国的形象,不得不把她赐给了连尹襄公。
不到一年,连尹襄公战死沙场,夏姬假托迎丧之名而回到郑国,此事原本可以就此结束,不料大夫屈巫久慕夏姬美艳,于是借出使齐国的方便,绕道郑国,在驿站馆舍中与夏姬成亲。
欢乐过后,夏姬在枕头旁问屈巫:“这事曾经禀告楚王吗?”屈巫也算一个情种,说道:“今日得谐鱼水之欢,大遂平生之愿。其他在所不计!”第二天就上了一道表章向楚王通报:“蒙郑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肖,遂不能辞。恐君王见罪,暂适晋国,使齐之事,望君王别遣良臣,死罪!死罪!”
屈巫带着夏姬投奔晋国的时候,也正是楚庄王派公子婴齐率兵抄没屈巫家族之时。夏姬以残花败柳之姿,还能使屈巫付出抄家灭族的代价,真是红颜祸水。她在新婚之夜的枕头旁套问屈巫,使屈巫下最后的决心,可说心计也是很深的。
4孟赢,即小说家笔下的无祥公主。纪元前五二六年,熊弃疾派大臣费无极前往秦国为太子迎亲。费无极是一个满肚子坏水小聪明层出不穷的无聊政客,从骨子里仇视所有美好的东西,当他把孟赢迎接到郢都后,象卫国新台事件的那位使臣一样在君王面前盛赞孟赢的美丽天下无双,所不同的是费无极心怀歹意,因为他极力撺掇熊弃疾作“爬灰佬”,把儿媳据为己有。熊弃疾和费无极是一路货色,君臣二人臭味相投,自然对这个“忠心耿耿”的建议报以热烈的欢迎,君臣二人开始有步骤地实施这个邪恶的计划。费无极告诉秦国的护送大臣说,楚王国的风俗,新娘要先到皇宫拜见公婆,然后才可以正式举行婚礼。于是孟赢进宫,老爹就霸王硬上宫,把儿媳变为妃子,而把一位陪嫁的齐国少女,冒充孟赢嫁给熊建。一年之后,孟赢生下一个儿子熊轸,他就是后来的楚昭王。
因为这件事,平王逼死了伍奢一家,才引出后来伍子胥鞭尸的故事。
宫城谷昌光用中国历史题材的十几部长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集,以寻求日本人精神故乡的心情进行创作,以古汉字为切入点,把中国历史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将取材的重点集中在古老的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向当代日本读者讲述中国历史,描述中国古代人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蕴含着大量的中国历史知识,也有不悖历史逻辑及事物情理的高度的想象力,趣味醇正,雅俗共赏,自成风格,是日本继陈舜臣之后中国题材历史小说的新旗手。
殷商题材的三部长篇小说
《王家的风日》(1991)取材于殷商代的殷纣王时期,这个时期属于缺乏可靠历史记载的史前史时期。宫城谷昌光的《王家的风日》以《史记》中的简略记载为基本依据,以箕子、商纣王两个主要人物为中心,以殷纣王时代为舞台背景,力图呈现历时六百年的殷商王朝的历史和文化。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箕子在《史记》中虽然出现过,但身份面目不甚清晰。《殷本纪》记载纣王*乱不止,不听大臣劝谏,反而将其中一人的心剜了出来,于是“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在《周本纪》中,又记载周武王灭殷纣王后,将被囚禁的箕子解放出来。武王推翻殷二年后,问箕子殷朝灭亡的原因何在,但“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意即不忍心说殷商的坏话,只说如何让已灭亡的殷朝的黎民百姓生活下去。由此可推测,箕子这个人是殷朝的一个王公大臣无疑,也有研究者认为箕子是殷纣王的叔父。宫城谷昌光根据这样的记载,将箕子设定为殷王朝的宰相和殷纣王的叔父,并将箕子描写为殷商时代的思想家和殷商文化的代表人物,把他作为一个殷商文明的化身和“中国人头脑的原型”。同时,宫城谷昌光又塑造了殷纣王(受王)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暴君的形象,描写他的野蛮暴行,特别是所使用的火刑、炮烙、烹杀、腌人肉等骇人的情节。但宫城谷昌光主要并不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描写纣王的暴虐,而是把他作为人类“野蛮”的代表,以便与箕子的“文明”构成相反相成的矛盾关系,这就抓住了由野蛮时代走向文明时代的殷商时代的基本特征。宫城谷昌光依靠自己从殷商甲骨文的观照中、从上古史料的研读中得来的灵感,广泛反映了殷商时代中国人的政治、宗教祭祀、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可以说,借助殷商王朝的兴亡,来演义上古时代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和变迁,显然是宫城谷昌光在《王家的风日》中要表达的基本主题。所以当小说写完后,宫城谷昌光自己也觉得:《王家的风日》实际上是“献给商民族的颂歌“。
宫城谷昌光取材于殷商时代的另一部小说是《天空之舟》(1990),副题是《小说·伊尹传》。《天空之舟》一开头就写刚刚生下伊尹的母亲预知大洪水来临的神秘的梦,仿佛将读者带进了充满异变的大禹治水的远古时代。伊尹的母亲按照梦中的神秘启示,将孩子置于桑树中,使孩子躲过了灭顶之灾,漂流到了异国。大洪水以及桑树舟漂流的故事,是一个的古老的故事原型,也是世界各国英雄故事中常见的情节。宫城谷昌光以大洪水的故事开头,一下子将读者带进了远古的蛮荒时代。大洪水淹没了一切,伊尹在桑树舟上顺黄河漂流,到了济水流域的诸侯有莘氏的部落,有莘氏给他取名为“挚”,交御厨收养,从事烹调。这一情节的设计显然是《史记》的“负鼎俎,以滋味说汤”的敷衍。挚十三岁时,作为厨师刀法已经出神入化,操刀解牛,游刃有余,令观者叹为观止。这不禁使读者想起《庄子》中的“庖丁解牛”的情节。挚的才能传到夏王室,常常被召进王宫,学习天文地理。但毕竟身份低贱,受到夏王子桀(夏桀)的欺凌和迫害。当桀成为夏王朝君主的时候,群雄割据,天下大乱。挚心灰意冷,隐居荒郊。那时新崛起的商王求贤若渴,亲临草庐延请挚,挚深为感动,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处写商王汤亲顾茅庐求贤,与《史记》中的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完全不同,情节构思上显然是受到了《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的影响。伊尹此后协助汤王灭掉夏朝,成为殷商王朝的开国功臣。就这样,在《史记》中面目不甚清晰的伊尹,夏商之交的乱世英雄,在《天空之舟》中成为血肉丰满的人物。
宫城谷昌光的殷商题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太公望》(1998)。太公望(姜子牙)在日本也较为知名,在宫城谷昌光前后,有关作家曾写过太公望,例如,近代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写过《太公望》,旅日华人作家邱永汉也写过《太公望》,日本学者还出版了多种研究太公望的专门著作,如高田穰的《太公望的不败的极意》、悴山纪一的《太公望吕尚》等,当代日本还有专门以太公望为主人公的漫画也很有人气。在《太公望》之前,太公望曾作为非主要人物,在宫城谷昌光的《王家的风日》和短篇小说《甘棠的人》中登场。宫城谷昌光决定写一部以太公望为主人公的长篇,与他对太公望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认识有关。他觉得:“商王朝实际上是靠太公望一个人扳倒的。”抱着这样的想法,宫城谷昌光决定写《太公望》。《太公望》上中下三卷,是迄今为止在日本文学中以太公望为主人公的篇幅最大的作品。宫城谷昌光从望幼年时代写起,写望所属的羌族及其父兄全家如何被商王杀戮,望如何逃出,发誓杀死商王,从此开始了反对商王朝的斗争,后来如何与以周公为中心的诸侯策划密谋,又如何将入狱的周公救出,如何壮大力量,最后革了商纣王的命。《太公望》以太公望的生平为线索,将殷周之交的风云激荡的中国历史呈现了出来。宫城谷昌光的《太公望》出版两年后,作家芝豪又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太公望》(2000),将太公望写成了军事天才和中国兵法的始祖。由此,太公望在日本的名望更扩大了。
春秋战国十大人物的复活
宫城谷昌光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所描写的春秋时代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夏姬春秋》(1991)中的夏姬。夏姬是郑国公主、历史上有名的美人和*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按传统的道德标准,对夏姬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和否定的。在日本,夏姬的名气似乎仅次于同时代的西施,作为可爱的美人而受到喜欢,现代日本女性将“夏姬”二字作名字者也不乏其人。在宫城谷昌光之前,曾有近代作家中岛敦、现代作家海音寺潮五郎、当代中国文学翻译家、作家驹田信二在有关作品中描写过夏姬。在宫城谷昌光看来,夏姬是中国春秋时代第一美人,“比西施还要美”。宫城谷昌光在谈到《夏姬春秋》的创作时说:“我在写夏姬春秋的时候,有意避开老套的表现手法,不是从正面描写这位绝世的美女,而是从背面加以描写。这是我对夏姬的爱的表现。”带着对夏姬的这种审美感觉来塑造夏姬的形象,使宫城谷昌光刻意回避对夏姬的*荡的渲染,而是通过众多不同的男性对夏姬的觊觎、染指、合法与不合法的占有,而表现夏姬的魅力,表现夏姬的命运的流转和变迁,并从这一侧面描写列国之间的关系与交往。在小说中,夏姬少女时期便为胞兄及其他公子所染指,婚后丈夫早逝。在困窘中为了保住其子的贵族身份,而不得不献身于陈国国君及大臣们。儿子虽享受了王公贵族的荣华富贵,却因无法忍受母亲夏姬的堕落而弑君,僭越为王,但后来又遭到楚国讨伐而败亡。夏姬也被掳掠到楚国,楚庄王将她赐给一个武将,但不久她又成新寡……在这里,夏姬的个人的命运与郑国、陈国、楚国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由此传达出春秋战国时代特有的时代氛围,同时也对夏姬的命运遭际寄予了同情。
宫城谷昌光以长篇的形式所描写的春秋时代的第二个人物是《重耳》(1993)中的重耳。《重耳》的基本情节与《左传》《史记》相同,但作为上中下三卷的篇幅较大的长篇,细节大为丰富,小说的主题是写春秋战国时代永恒的主题——列国征战和国内权力斗争。上卷的主人公是重耳的祖父、晋的一支、曲沃之王“称”,写“称”如何征服本家“翼”,建立了统一的晋国,其中有大量古代战争场面的描写。中卷开始写道重耳的父亲晋献公诡诸。晚年的晋献公贪恋女色,将作为人质掳掠来的异国公主骊姬立为正室,骊姬遂招致宫内有关人物的嫉恨。骊姬为了自保,处心积虑地欲将自己的幼小的儿子姬奚齐立为太子,谋求将来登上王位。为此,她利用了晋献公的昏庸,密谋陷害对她的计划构成威胁的申生、重耳、夷吾三兄弟,挑拨献公与这三个儿子的关系,让父子生隙成仇,使得已经被立为太子的深深孝敬父亲的申生自杀身亡。下卷描写重耳为避杀身之祸也仓皇逃出,接着骊姬又派宦官阉楚追杀重耳。重耳被迫便开始了漫长的开始了流亡生涯。其间骊姬母子被杀,重耳的异母兄弟夷吾(晋惠公)即位后,继续追杀重耳,但在从者介子推等人保护下每每有惊无险。重耳在列国备偿酸甜苦辣,与列国君主发生种种恩怨。在流亡十九年后,重耳在身边众多家臣的及秦国秦穆公的帮助下,终于率兵打回国内,推翻晋惠公,即位为晋文公,并使晋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见,《重耳》中的既是重耳流亡与奋斗史,也是一部生动的晋国兴衰史、春秋列国关系史。
宫城谷昌光描写的春秋时代的第三个人物是《介子推》(1995)中的介子推。介子推这个人物,在上述的《重耳》一书中已经作为重要的人物登场。在重耳的身边的重要人物中,介子推的身份低微,不是重耳的直接臣下,而是重耳的重臣先轸的配下。然而就是这个小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民间文学中,却成为广为人知的“大人物”,而受到人们的景仰,因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理想人格。也许正因为如此,宫城谷昌光觉得在《重耳》中对介子推的描写还不过瘾,因而接下去创作了以介子推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介子推》。在小说中,宫城谷昌光对介子推的生平事迹的描写与评价基本依据了《左传》和《史记》,但也有许多的丰富与虚构。在他的笔下,介子推作为一个非常孝敬老母、老实本分、而又有高远理想的农夫,其唯一的超人之处就是擅长拳棒、曾以木棒打死咬伤自己的老虎。他之所以决定离开母亲去投奔重耳,就是认定重耳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所以在重耳流亡列国的困难时期,舍生忘死保护重耳,都是发自内心的、无功利的,甚至重耳本人也不知晓。所以,当重耳即位后对功臣论功行赏,而唯独落下介子推时,介子推并不介意。但当他看清做了晋文公的重耳原来和别的贪得无厌、处事不公的君主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后,他绝望了,于是悄悄地离开了宫廷,和老母一起隐遁到了故乡的深山中。宫城谷昌光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重耳苦尽甘来之时,介子推却悄然而去,“想到这事,就感到心酸”。宫城谷昌光从介子推这个人物身上,发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家的人格典范,因而对介子推最后不辞而别、悄然隐居的原因写得十分充分,十分合乎人物的性格逻辑。宫城谷昌光在《介子推》中没有取历史的悲剧来结尾,他写介子推及身边的几个人物快和地在山中生活和谈笑。宫城谷昌光通过介子推形象的塑造,表现了那个兵荒马乱的残酷时代人们对和平与宁静生活的渴望。
春秋时期第四个人物出现于长篇小说《沙中的回廊》(2001)中,宫城谷昌光又描写了重耳的身边的另一个侍从——士会。和介子推一样,士会也有着超群的武术并精通兵法,受到晋文公重耳的赏识,由一个微臣,到晋景公时代晋升至宰相,显示出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宫城谷昌光从《重耳》到《介子推》再到《沙中的回廊》,通过三个主人公及其生涯的描写,反映了构成了晋国历史题材的兴亡历程,也构成了内容联贯的晋国题材三部曲。
宫城谷昌光所描写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五和第六个人物,是齐国的著名宰相晏子——亦即晏弱和晏婴父子。在四卷册长篇小说《晏子》(1994~1995)中,宫城谷昌光把晏婴塑造为震撼自己灵魂的人物。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包括《左传》、《史记》、《晏子春秋》等,以艺术想象解决了史料中的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在经历了数年的沉淀与构思之后,他决定将晏弱和晏婴父子合称“晏子”,写成同名长篇小说。宫城谷昌光将晏弱和晏婴父子合称“晏子”,显然与海音寺潮五郎在长篇小说《孙子》中将孙武和孙膑合称“孙子”属同一思路,这样一来就加倍地延长了小说的时间跨度和艺术容量。《晏子》是宫城谷昌光在1995年之前出版的篇幅最长的作品,它以晏弱和晏婴父子的生平事迹为中心,以齐国的兴衰为轴线,将当时齐国及晋、鲁、卫、楚、莱、郑、吴、莒等列国在史料和经书上出现过的有关重要人物,共六十余人都纳入了故事架构中。鉴于有关晏子的中国史料很丰富,可供宫城谷昌光选择与发挥的故事原型也很多,所以《晏子》的情节蕴含也相当绵密充实。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宫城谷昌光除了参照《左传》《史记》的记载外,关于晏子的部分主要依据《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是以晏子的事迹为中心的历史传说故事集,共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每章都讲了一个有关晏子的独立的故事,而且大都生动传神。宫城谷昌光将《晏子春秋》中那些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按照人物生平与性格演进的逻辑,有选择地纳入了一个有机的框架结构中,并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丰富和发挥。例如晏子出使楚国,面对楚王令他钻狗洞进来等一系列蓄意的羞辱,晏子如何机智地加以回击,维护了自身及其国家的尊严等等情节,都写得有声有色,十分精彩耐看。作为有一定文史修养的中国读者,有关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而缺乏新鲜感,但对于绝大多数日本读者而言,《晏子》中的这些故事此前恐怕闻所未闻,其产生的艺术魅力可想而知,《晏子》出版后销售四十三万册,成为畅销书。归根结底,《晏子》的成功取决于宫城谷昌光的出色的想象力,更得益于《晏子春秋》等中国古典本身的艺术魅力。
宫城谷昌光所描写的第七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是孟尝君。五卷册长篇小说《孟尝君》(1995)的主人公是孟尝君(本名田文)。宫城谷昌光在《孟尝君》的前言中,提到由于资料不齐,写孟尝君时他一直感到有心无力,但在查阅史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特殊人物——白圭”,便把这位大商人与孟尝君联系起来。查阅史料,即可知道宫城谷昌光原来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发现”白圭其人的。白圭是魏国的大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二百来字写白圭如何擅长做买卖而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原本白圭与孟尝君应毫无关系,但宫城谷昌光却设想田文被生母及家臣送给了风洪(后改名白圭)抚养,白圭即成了田文的养父。这一大胆的“发想”大大地开拓了《孟尝君》的舞台空间,白圭实际上成了《孟尝君》前半部分的主人公,由于白圭的生平几乎没有史料可依,宫城谷昌光便根据作品内在的需要而展开想象,遂使白圭这个人物血肉丰满起来。据说在《孟尝君》连载的过程中,白圭的经历与命运牵动着读者的心,一位女性读者曾给宫城谷昌光来信,说:“母亲几乎天天嚷着:白圭今天怎么样啦?”可见白圭形象塑造的成功。尽管由于白圭着墨很多,但对白圭的描写还是与孟尝君的命运流转紧密相关的,并没有出现喧宾夺主的问题。在《孟尝君》中,宫城谷昌光紧紧围绕着孟尝君的出生、流浪、刀下余生、战场驰骋、养士三千、位及人臣等曲折动人的经历,使小说的情节显得十分紧凑,可读性很强。此外,宫城谷昌光完全从正面塑造孟尝君的形象,将他写成一个多情多才、重义轻利、有勇有谋的人,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孟尝君的“好客自喜”的总体评价也有出入。
宫城谷昌光所描写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第八个人物是《青云扶摇》(1997)中的范雎。宫城谷昌光的小说题名“青云扶摇”(原文《青云はるかに》)此。司马迁的《史记》对范雎的生平遭际具体生动的戏剧性描写,为宫城谷昌光在《青云扶摇》对范雎形象的再塑造打下了基础。宫城谷昌光在《青云扶摇》中,是将范雎作为时代的俊杰来描写的,写他的辩才,写他在秦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与司马迁稍有不同。司马迁对范雎这样的口辩之士虽如实描写他们的聪明智慧,但对这类人凭三寸不烂之舌而挑拨离间获取官位并没有多少好感。《青云扶摇》则完全将范雎塑造为英雄豪杰,将口辩、复仇作为战国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加以表现,既写范雎的有节制的复仇,也写他的杰出的政治与军事才能。
宫城谷昌光所描写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第九个人物是《乐毅》(1999)中的乐毅。乐毅是战国时代中期的名将。宫城谷昌光在四卷本长篇小说《乐毅》中,基本史料来自《史记》,但只以《乐毅列传》的开头几十字介绍乐毅身世的文字做基本依据。那段文字极其简略,却为宫城谷昌光的艺术想象提供了空间。宫城谷昌光的四卷本长篇小说《乐毅》对《史记》中记述较详的乐毅如何助燕伐齐的故事只在小说最后一部分有所描写,而是小说将主要矛盾设定为赵国与乐毅的家乡中山国(今山西省境内)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而按上引《史记》中的记载,中山国先后被魏、赵所灭的时期,乐毅恐怕尚未出生或至少还处在幼儿时期。宫城谷昌光为了表现乐毅的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的主题,而将乐毅的生年提前了许多。小说描写了乐毅为了保家卫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所而进行的一次次顽强出色的战斗,但最终因中山国的君臣昏庸,疏远排斥乐毅,导致亡国的结局。乐毅最终为赏识自己军事才能的燕昭王延请至燕国……全书是围绕着乐毅为“天才军事家”这一主题而展开故事情节的。
宫城谷昌光所描写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第十个人物是《子产》(2000)中的郑国宰相子产。此前,宫城谷描写了好几位宰相,但子产的形象在众多的帝王将相中有所不同。《子产》描写了子产如何在昏庸无能的国君统治中使郑国得以安全生存,并建立了太平安定的社会;描写了子产如何邦以民为本、如何善于倾听民意、如何广纳贤言,如何对郑国进行内政与外交上的一系列改革,并为此如何与政敌所展开较量,突出表现了子产以德治国、以礼治国、依法治国的理念的和行动,以及他作为“春秋时代最高知识人”的言语表达智慧和人格魅力。总之,宫城谷昌光是借子产的形象塑造,表达了对理想的政治家和改革者的憧憬,而《子产》对当代日本读者的魅力,似乎主要也在于此。吉川英治文学奖的评委们对《子产》的赞誉和推崇,也主要是从这一点着眼的。例如评委之一、作家杉本苑子说:应该让永田町(东京地名、日本政府所在地)的那些“不知羞耻的政治家诸公们”好好看看这本书。
通过十大人物形象的塑造,宫城谷昌光不仅使这些古代人物得以复活,而且通过这些人物,将春秋战国时代深邃的历史图景展示了出来。自从海音寺潮五郎的《中国英杰传》、《孙子》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还没有一个人在春秋战争题材中做如此系统全面地开拓和耕耘,更没有一个人在春秋战国题材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