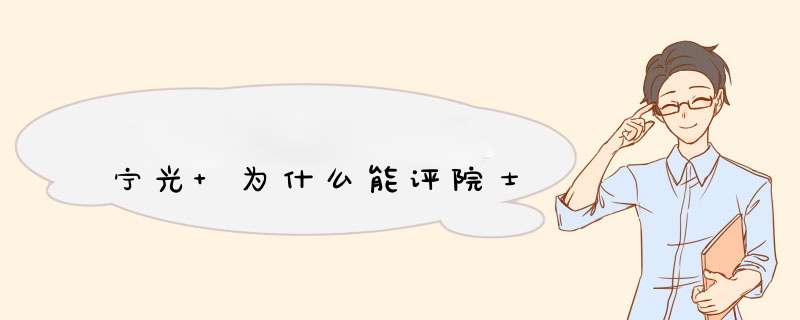
宁光能评院士是因为科研成就高。
宁光发现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I型、胰岛细胞瘤与肾上腺库欣综合征发病机制及致病基因,规范并优化诊疗方案,显著提升内分泌肿瘤基础研究与临床诊治整体水平;致力于通过大型队列创建生物样本库的研究模式,全面阐述中国代谢性疾病严峻形势,深入探索危险因素及防治新方案。
根据2019年12月中国工程院网站显示,宁光先后在Science、JAMA等SCI收录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宁光先后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课题20余项。宁光先后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排名第一,1项排名第二)。
宁光
生于山东滨州,1994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兼任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擅长难治性糖尿病、血糖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等内分泌代谢病的诊断与治疗。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潘云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离开我们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伟业丰功,永垂科学史册,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聪颖好学,成绩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进,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联合中学、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和北京大学地质系读书时,都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进步活动。他在学习上极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学生活中,他从未回过一次家,一方面由于他家远在四川,当时交通条件差,另一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学习中去。
黄汲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期间,成绩特别优异,1927年,他上三年级时即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奥陶纪层》一文,被授予“优秀论文奖金”(140块大洋)。1928年,他毕业前夕,与同班同学随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去热河省北票等地调查地质,他野外记录簿文图俱佳,显露基本功的绝活,深得翁的青睐。同年夏,他毕业后即考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当年夏,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北平后,该所归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管辖)。翁文灏竟安排他这样一位还没转正的“练习生”在他的大办公室里与他的秘书并排办公。这简直是破天荒的礼遇。说明翁真是相中黄汲清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伯乐”他实在是当得太好了。黄汲清入地质调查所一两年间调查了东北煤田地质,特别是随丁文江从事了西南地质大调查,又在两年内撰写出版了6部关于古生物学、地层学、区域地质学的专著。他初出茅庐,锋芒毕露、业绩辉煌,深为丁文江、翁文灏所青睐和器重,并物色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颢去南京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8届年会,特意带上黄汲清去经风雨、见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并推荐他去瑞士留学。1933年,丁文江去美国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到欧洲游历,特别在日内瓦约见黄汲清,告诉他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二叠纪古生物地层学权威查尔斯·舒克特在1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讲述世界二叠系地层对比时,采用了黄的中国二叠系划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临别时,丁更是语重心长地对黄说:“你还年轻,前程无量,我们对你的希望无穷,我的这架布朗屯罗盘,用了几十年,已经旧了,送给你作纪念吧!”令黄十分感动。
黄汲清1935年在瑞士浓霞台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又游学欧美列国,于1936年1月满载收获和荣誉回到祖国,才知丁文江先生于月初病逝于长沙,不禁失声痛哭。他向当时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汇报情况后,翁满心欢喜,当年即任命他为该所地质主任,一两年内就晋升为副所长、代所长、所长。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上说:“适之我兄……地质所事交黄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与弟共同选定为继任所长者”道出了个中底细。当时翁文灏身边能人如云,不但有黄汲清在北大地质系的三四十岁的老学长,更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40多岁的“元老”,而翁却按照与丁久已内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给刚留学回国,才三十二三岁年龄的黄汲清,这一惊人之举自然使整个地质界同仁衷心仰慕黄的天才,当然也许免不了有少数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灏任人唯贤、不搞论资排辈、大胆提拔青年精锐的举措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无比英明的。
黄汲清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器重和全体同仁的期望,他尊老爱幼,上下一心,把地质调查所办得欣欣向荣,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杰出的第二代***。后来,他辞去所长职务,潜心野外调查和科学研究,在基础地质、应用地质若干领域都有辉煌的建树。在古生物学、地层学、地史学方面,他建立了中国二叠系生物地层学划分对比的基础,有“黄二叠”的美誉。在区域地质学与构造地质学方面,他开拓了中国地质图类的编绘事业,20世纪40年代他主持编了14幅《1/100万国际分幅的中国地质图》及整幅《1/300万中国地质图》,60年代初他又领导编绘了国际分幅的1/100万全国整套地质图件(地质图、大地构造图、成矿规律图),他又是我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创立和发展了“多旋回构造运动学说”,成为我国大地构造学五大学派之一的代表。在应用地质学如矿床地质学方面,他发展并运用了“陆相生油学说”及“多旋回成矿学说”指导了石油天然气及其他重要矿产资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纪地质学、地貌学、冰川学以及地质科学史等方面都有若干贡献。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西南地质局局长,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常委、地质部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兼大地构造研究室主任、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
1948年,黄汲清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质学界6位院士中最年轻的(44岁)。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并长期担任中科院地学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他当选为该学会第32届理事长,再一次担当起全面领导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重任。他曾率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26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又出席了在莫斯科、华盛顿、东京举行的第27~29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他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优秀奖。在国际上,他曾获美洲地质学会名誉会员、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光荣称号。
我从中学时代就听说过黄汲清先生的大名,他当时作为西南地质局局长、也兼任重庆地质学校校长。我所在重庆市一中初中的高班同学有考到重庆地校的,回母校谈起他们的黄汲清校长是著名的大地质学家。我也听我第二位母亲(也是我的大姨)刘尊一(西南师范学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则信说,黄汲清先生和母亲是北京大学同学,还倡议过北大同学会的活动,而他与汲清先生的长子浩生还是儒英小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他们一起玩时,浩生突发急性阑尾炎,还是则信背他回家,然后送医院治疗的。他还说姐姐则智在儒英小学与浩生的姐姐洁生也是同班同学、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经常听说黄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两点:有人说他骄傲自大、趾高气扬,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说他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保护过了关,但也受过批判和冲击,在那“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虽是大科学家,也根本吃不开。而我本人在“红专辩论”中又被批判为“白专典型”,很受压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去找黄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报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院士(学部委员)的研究生,虽然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但杨老却从北大组织上和群众中听到关于我“白专典型”的很多微词,因而公开放出话来:“潘云唐尽管成绩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这对我无疑是沉重的打击,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后一搏,从其他地方寻找慰藉和补偿。我就在当年夏天一个下午。不揣冒昧,到百万庄卯区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宿舍去登门拜访黄汲清先生,自我介绍之后的由头是代表则智姐姐、则信弟弟问候洁生姐姐和浩生弟弟,并告知****。汲清先生和夫人陈传骏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关系后,对我十分热情亲切。并且留我一起吃晚饭,慢慢叙谈几十年两家的友谊,真是一见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对我回忆与父母亲的友谊:“我和你妈妈20年代在北京大学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系,但常常一起参加进步集会,又一起上街去示威游行,你妈妈不畏强暴,敢与军警搏斗,堪称女中豪杰……你爸爸抗日战争时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经济部常务次长,我是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他虽然位高权重,但很平易近人,体恤下属。我按规定每两个星期一次去部机关汇报工作(述职)。你的爸爸见了我总是热情招呼,亲切握手,坐下来仔细听我陈述,然后认真研究工作,有时也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拉家常。我偶尔遇到所里有急事,去到部机关,翁文灏部长不在时,找到你爸爸,他对地质业务不熟悉,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一些要求时,他也不跟我们斤斤计较,看我们说得头头是道,八九不离十,就大笔一挥,为我们签字,然后盖章,办各种手续,使我们能及时领到钱和东西,解决我们所里的问题……”陈传骏夫人说她也认识我的两位妈妈,并多次去过我们家。后来,他们又问了我个人的若干情况,特别是政治表现、业务功课,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亲切周到,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黄伯伯”、“黄伯母”。
这次突然造访的意外成功,对在极“左”形势下怀才不遇、穷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极大的抚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质科学事业发展历史的掌故,以至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在杨钟健先生那里遭到冷遇和厄运,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这里却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宠若惊,实在有“相见恨晚”之感。我回到学校后,立即给汲清老伯伯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国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一文中的话:“我以一个毫无阅历的、并且满怀知识饥渴的年轻人,能够有缘认识马克思并得到他的教诲这种好运,更是使我感到万分庆幸的,只不过把‘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对我勉励有加,特别是提到最近与我的老师乐森 先生见面时谈起我的情况,更表明了他对我的关心。那时毕业以后不像今天这样自谋职业,有选择工作的自由,而是强迫命令,硬性分配。考研失败,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临行前又和弟弟一起去拜会黄伯伯,他说:“你学地质,研究古生物,西南区、四川是个好地方。你回老家去好好干,照样是很有前途的。”我到了成都之后,也给汲清老伯伯夫妇写过信,报告当时的情况。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类”挨整对象,与汲清老伯伯一家就中断了联系,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严重冲击,很为他担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形势有了好转,我们开始恢复业务工作。我也听说汲清老伯伯夫妇都从江西“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也很为他们高兴。
1974年,我为编撰《西南区古生物图册·四川分册》而出差北京地质科学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们家从原来的一个套间被压缩到一个单间,十分拥挤。但他们仍十分坦然,随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刚恢复工作又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听了汲清老伯伯给青年科技人员的报告,又特别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宾馆去拜望,传骏老伯母也在。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中华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我投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到北京来复试,复试结束后又在北京出差,为公家办一些事,并且与则智姐姐一同在友谊医院侍候患膀胱癌手术成功后康复过程中的母亲。听姐姐说,母亲刚住进友谊医院时,汲清老伯伯夫妇都到医院探视。汲清老伯伯还特别托他的老朋友、该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钟惠澜教授多多关照,再加上母亲的老友邓妈妈(邓颖超)又请曾任总理医疗组长的吴阶平教授(后为两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员长)参加会诊,所以母亲的手术和康复治疗才很顺利。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和则智姐姐、则仁哥哥去三里河南沙沟6幢1门2号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见他们从局促的一间小屋迁到了一个豪华的大套间,还带后花园,深深为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而由衷高兴。
后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先生,在召开全院招生工作会议时说研究生院要成立师资班,把成绩合格者培养成为研究生院未来的教师,于是中科院地质所招办就高姿态将我划拨给研究生院师资班。1978年10月来京报到后,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从那时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过从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对我说,他大半生发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图书馆查文献时,逐渐把他的著作目录编出来。我欣然接受这个任务,我结合研究生课题运作,在图书馆、资料馆查文献时,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张,一篇著作一张,包括公开发表的和内部印刷的,我另抄了一套,连同一个卡片盒一起送到他家,他很高兴,审阅之后又提供新的线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编成了他的著作目录,以后在很多刊物、专著上发表。
当年有一天,汲清老伯伯打电话约我去他家,并告诉我,当时很多单位部门在争着出科学家的传记,让我抽时间听他口述,进行笔录然后整理,我们就在星期日花一整天做了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传稿后交他审阅修改,后来,最先发表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徐志春主编而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家辞典·第一分册》上。我从给他编传记中深深体会到他的优秀品质,高风亮节,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给他们一首旧体诗,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伟矣高哉夫子黄,学坛薄海颂声扬。
煊煊大业如徐士,赫赫丰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共事,感怀家母旧同窗。
余侪晚进承霖雨,铭谢栽培恩义长。
落款是“卑职、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云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过去反复吟诵,并说:“你的古典文学功底真是深厚,精通旧体诗词格律,写得很好。不过,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
当时我在家书中向母亲汇报了为汲清老伯伯做了一些事的情况,母亲很高兴,在回信中勉励我继续努力,多为黄伯伯服务,也在黄伯伯领导下多作出些成绩来。1979年,母亲在重庆因膀胱癌复发第二次手术失败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后,请假回重庆奔丧,临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们二老及其他亲人也对母亲的逝世感到悲伤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发唁电并嘱我转达对家乡亲人们的慰问,望我们节哀顺变。我从重庆回来后,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们二老表达兄弟姐妹亲人们的感激和问候。我又对他们二老说:“我从小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喜欢的儿子,黄伯伯、黄伯母是爸爸和妈妈们最好的朋友,我一定按他们生前的嘱咐,忠心耿耿、踏踏实实为黄伯伯效劳”。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说他原来在中央大学地质系兼课时的高足许靖华教授是美籍华裔学者,当时在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任教,为该校100周年校庆,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学家名誉博士学位,许先生特推荐了他的老恩师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关材料寄过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约好时间,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约好的那天傍晚,朔风怒吼,大雪飞扬。我骑着自行车,到他家,在门外脱掉大衣,抖掉满身雪花,然后才进到屋内。汲清老伯伯夫妇和其他亲人很惊讶很感动地说:“下这么大的雪你还来了”我恳切地回答:“有约在先,诚信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可以行之哉?答应了要为黄伯伯做这么重要的事,慢说下雪,下刀子也得来啊!”然后大家坐下来,忙了两三个小时,把有关材料,主要是汲清老伯伯生平业绩的中英文简介,主要学术著作目录等,都整理完毕了,他的著作目录涉及的文种很多,好在我为了学习和科研的需要,涉猎了多种文字,除英、俄文较熟练外,德、法文乃至日文也可勉强抱着字典查查专业文献。汲清老伯伯面对我为他整理好的材料大发一通感慨,也连带了几句牢骚话。他说:“我身边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三下五除二,很好地把我预定的任务完成得干净利落。朱效成、孟继声简直不怎么样,1957年就要把我打成右派,报到部里以后,何长工、宋应等部领导保了我,他们还组织大会、小会批判我。文化大革命又整我,诬蔑我是丁文江、翁文灏的走狗,是美蒋经济特务,把我关进牛棚。‘文革’后期我都解放了,成了三结合对象,当上了地科院革委会副主任、副院长,身边竟然还没配助手,催得急一点,才派刚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跟我穷对付。这小伙子人很憨厚,很勤奋,我并不反感,但毕竟在‘文革’期间学到的东西有限,帮不了我太大的忙。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传骏老伯母插了一句:“你能把云唐要到身边来吗”他回答:“可惜我官还小了一点,要副部长以上才有资格点名调人。”
1982年10月7~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春昱、高振西、张文佑及美籍华裔著名地质学家吴景桢等出席了开幕式。汲清老伯伯作为学会 理事长在会上致了贺词,开始就说:“近几年,地质学史的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绩,参加的同志越来越多。据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吴凤鸣、孙荣圭、王根元、李鄂荣、王仰之、闻广、潘云唐等同志都做了研究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被地质科学大师点名表彰。两年后,我进了该 研究会第二届10人干事会班子,想来与汲清老伯伯及诸位师友的提携也是不无关系的。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班子里执行领导意图,与同仁们亲密共事,在我的诸多社会兼职中,这无疑是最令我无比执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质学史研究与著述工作中都约我参加,1985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系列中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由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何绍勋等具体运作,何先生特请汲清老伯伯和他并列全书主编,汲清老伯伯向编委会推荐我写章鸿钊、丁文江、谭锡畴、田奇 、李春昱、计荣森、程裕淇七位老地质学家的传记篇目,我写完后,编入了该书第1集,总共52人,我写的篇幅大概占了1/7。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卷》编纂过程中,约汲清老伯伯写“赵亚曾”、“朱森”的简传条目,汲清老伯伯特写信给该卷编辑楼遂,推荐我来写。后来楼遂又让我写了其他地质学家的简传条目。我也帮他们做了相关的工作。1993年该书出版时,我被列入“特约编辑”名单。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约我编《翁文灏选集》,他运筹全局,负责选题,我做具体编辑工作,此书赶在翁文灏老伯伯诞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署名“黄汲清选、潘云唐编”。他在“序言”中说:“汲清应翁先生亲属和冶金工业出版社的请求,在潘云唐同志和其他同志帮助下,从事翁先生学术遗产整理工作……编成此书”。
1989年9月1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该书作为大会文件之一,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和翁老伯伯亲属的诚挚感谢。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台湾“中国药学会”秘书长)特代表海外亲属来参加大会,见到我时说:“我在台北已经知道,我岳父的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来就是您啊!”紧接着,汲清老伯伯又指导我和他的秘书谢广连编纂了《丁文江选集》,署名为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我先后为汲清老伯伯写了很多宣传报道文章,他看了以后都高兴,不过,他也常提醒我,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写完初稿都请他过目,反复修改,后来我把发表这些文章的报纸、刊物给他送去时,他很满意,特别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华英才》总101期上发表了《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一文,他看后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参加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上千人的队列中,向这位卓越的地质科学大师告别。
20世纪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亲任主编,策划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一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也写了其中的《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一文,该书于2001年出版,读者从中外大科学家们青年时代的努力奋斗中能够汲取不少开拓创新、铸造辉煌的动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学会等单位事前筹划举行纪念活动,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要编撰《黄汲清年谱》一书,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纪舜院士等领导下,具体运作此事,此书赶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诞辰之前出版。当年6月7日,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路甬祥副委员长、曾培炎副总理两位国家***、数十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学者等出席,此书也发给了每一位与会者,署名是“中国地质学会编,执笔人潘云唐”。当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岁生日,他的家乡——四川仁寿县的领导特别邀请我去他的母校——仁寿县第一中学作报告,讲述他的生平业绩,受到师生员工热烈欢迎,副县长王利清、县政协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鲁出席了大会,大会上我和他们还为“黄汲清奖学金”得奖者颁了奖。
回想我们两家三代人大半个世纪的情谊,不禁感慨万分。我有时想,如果我选对了专业,投对了人,也许我的人生、事业又是另一番情景。具体说,我如果早些利用上这个宝贵的世交关系,分专业时选学构造地质,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后做他的秘书、助手,加入他领导的科研团队,那就极有可能是院士了。因为他是翁文颢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爱将,我如果到了他身边,他一定会把我带出来,尤其是他对我本人学识才华又是那么青睐,那么赞赏,那么器重。可惜我在极“左”形势的压抑之下耽误了宝贵的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百年风水轮流转,三十河东四十西”。等我熬到了云开雾散的改革开放太平极乐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边时,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横向的关系,只能帮他做做编写传记、年谱、著作目录这类打杂的事了。当然,历史是无情的,生活没有“假设”、“也许”,走过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对现实,从零开始,向前看,不向后看,人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算满意了。
再过四年,将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诞辰,我想,学术界也许会酝酿新的纪念活动,他的《年谱》可否扩编、再版?可否为他写出一本长传?这些问题都可以考虑考虑,让汲清老伯伯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更多地惠及国家民族和社会。
参考文献
[1]潘云唐黄汲清在地层古生物学上的卓越贡献化石,1983(1,总35):8~10
[2]黄汲清选,潘云唐编翁文灏选集见: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家选集丛书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1~359
[3]姜江大地构造学家、古生物地层学家、石油地质学家黄汲清(1904-),见:黄汲清,何绍勋主编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74~288
[4]姜春发,黄汲清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342~362
[5]黄汲清,潘云唐,谢广连编丁文江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47
[6]潘云唐,黄汲清数着地球的脉搏走中华英才1994(17,总101):42~43
[7]姜春发黄汲清(1904~1995)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刘东生本卷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444~460
[8]潘云唐诚挚的悼念深情的缅怀——黄汲清老世伯逝世三周年祭见:中国地质科学院编黄汲清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98,115~118
[9]潘云唐杰出的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创新辉煌:科学大师的青年时代(路甬祥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783~803
[10]何起祥黄汲清先生荣膺ETH荣誉博士学位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634
[11]禹启仁设立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的前前后后,见:中国地质学会8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634
[12]潘云唐黄汲清与二叠纪——纪念著名地质科学大师黄汲清院士百年华诞,化石,2004(3):32~34
[13]潘云唐黄汲清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地球,2004(2,总136):7~8
[14]潘云唐参政议政的楷模——纪念黄汲清院士百年华诞民主与科学,2004(3,总58):51~52
[15]单卿(潘云唐)四川仁寿县隆重纪念黄汲清百年华诞中国地质学会会讯,2004(1,总94):57~58
[16]中国地质学会编黄汲清年谱,北京:地质出版社,2004,1~341
[17]黄洁生黄汲清(1904~1995)见:钱伟长总主编,孙鸿烈本卷主编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学卷·地质学分册(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387~396
我只说我知道的,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胡适、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
去美国的 陈省身、李书华、吴宪、 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者9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内地迎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这是一楼引用的数据,但我的了解怎么和这数据对不上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以上我列举的人都没留在大陆。其实情况挺复杂的,比如吴大猷先去美国,后去台湾。
王宠惠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
李济1948年去台湾,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董作宾1948年去台湾,1955年后在香港任教。
王世杰赴台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
还有萨本栋院士死于49年初。
其他人留在大陆。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特痴迷院士。我又特爱国,所以我对你提的这个问题也特感兴趣,查了很多东西。目前网上除了袁贻瑾和李宗恩的资料极少,其他人都可以查到。
附中央研究院第一代院士名单
数理组院士28人
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李四光 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
王家揖 伍献文 贝时璋 秉志 陈桢 童第周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贻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济 梁思永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达 陶孟和
据最新消息报道,吴孟超院士,年轻时候的照片被曝光出来,顿时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是啊,大家觉得,年轻时的吴孟超院长,帅吗。个人认为非常的帅。别说是年轻的时候,哪怕现在他老了。我都觉得他很帅。一个人的帅与不帅,美与不美,与外观没有很大的关系,而是在于她的心灵,只要他心灵美,那么他就是美的。作为肝胆之父,吴孟超,给人类带来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因为一些原因,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但是,虽然我们难过,可是我们也无法改变什么。我们只能坦然接受。是啊,无论怎么好,我们的生命没了,那么啥都没有,所以,对于大家来说,我们一定要珍爱生命,一定要保持健康。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下面我们一起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是,改善生活习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的生活习惯都是不规范的,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好,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要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其次,增强锻炼,除了生活习惯之外,锻炼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锻炼,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而使得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增强,自然对于我们的健康更有利。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定要增强锻炼。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拥有更长的寿命。才能去享受这美好的世界。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因为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密切相关,也是与我们非常近的东西,只有我们重视起来,我们才能真正做到。
中科院院士与中科院的关系是院士是中科院评定的职称。中科院院士是国家在各个科研领域评选出的优秀科研人员,且在各自工作中有重大贡献和创新的人员才有资格评选为中科院院士。同时,中科院院长是一个管理岗位,在工作中是有行政管理职能的,而院士是一个学术职称,这两者并不直接相关。
学术,简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般每两年增选一次,从国内外最优秀的科学家中选拔,每次总名额不超过60人。“两院”是部级单位,直属国务院,向国家提供专业意见。
院士大会
中科院院士注重学术类型的培养,主要依靠综合性大学和大师的熏陶。他代表的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系统性、创造性成就的高级人才。导弹之王钱学森,数学奠基人钱伟长,物理学家钱三强,气象学家竺可桢等等。近年来,备受媒体关注的石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关注技术,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主要依托理工科大学和工程实践。工程院院士大多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的专家。比如水稻专家袁隆平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两院院士有重叠的部分,医学部分,基础医学的学者一般进科学院,临床医学一般进工程院。很多科学家在这两个领域都有造诣,两院院士可以兼任。
院士和院士待遇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院士在医疗方面享受副省部级待遇。但在一些院士较少的省市,院士不仅享受医疗待遇,在其他方面也享受副省部级待遇。如果是部级以上的人,被评为院士就享受更高一级的待遇。院士在晋升、申请经费、工作安排、奖励、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国家出台了院士相关待遇。比如,从2018年7月起,两院院士(包括退休院士)可以在全国所有开放口岸出入境,可以使用“特别通道”优先通行。经陆路口岸出入境时,可下车查验,以待批方式办理通关手续。
为什么最新的规定是处级以上干部不得作为院士候选人?
中国科学院成立很早,1949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工程院成立时,中科院院士的学术贡献、国际权威和世界影响力都是无与伦比的。关键原因是工程院成立时,有大量的“官方院士”。有校长、院长、副院长、副部长、部长等。为提升中国工程院在国际上的权威,共有3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过工程院院士。这些院士后来成为“双院士”,包括钱学森、王大珩、王选、卢永祥、朱光亚、张光斗等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权威认可的科学家。自那以后,他先后任命了水利学家、冶金学家邵向华、医学家吴阶平和建筑师吴。
卢永祥
然而,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2009年两院增选院士时,工程院85%的新院士都是现任官员。逐步与世界科学接轨,进一步释放科技生产力,摆脱“官本位”思想带来的弊端。自2015年起,两院院士增选取消了科级选拔,科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和荣誉的本质。院士越来越年轻化。、张亚平、支、任永华等都是40岁以下的当选院士。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