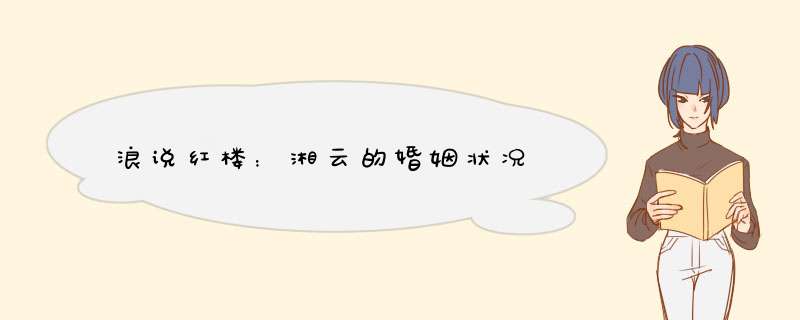
一、湘云结婚了
此节先 说出结 论,再用 假说演绎 论证。三十一回的史湘云已经结婚,这次来荣府就是省亲回门。
首先来分辨一个概念: 大姑娘。
按中国习俗,已到婚龄的女孩历来被称为大姑娘。二十回的史湘云刚一出场,就被荣府大小人物称为史大姑娘;第三十一回亦然,都有“史大姑娘来了”这句话。
当然并不是说,女孩到了婚龄成为 大姑娘 ,就一定非嫁人不可。
还有一种情况: 假设,湘云已经嫁人;她在娘家的时候, 即: 无论史家或相当于娘家的荣府,她还会被称为姑娘;这个姑娘是女儿之意。
也就是说: 史湘云如果是史家头生头长的女孩子,她在史家或荣府,从小到大永远都是史大姑娘。
湘云被称作 史大姑娘 ,说明她已到婚龄应该没错。
顺便插说: 倘如此,红楼众钗到了婚龄的人应该很多;林黛玉就是其中一位。因此,史湘云到了婚龄一说,必然会给文本带来新的矛盾。
而事实上,红楼众钗的年龄,一直都是困扰读者的主要问题,但并不影响阅读与体味。因为《红楼梦》不是学术论文,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事事都要做得严谨。
闲言少叙。前文一再提说,史湘云的 某次表现异常 ;于平时的个性有冲突,并且十分矛盾。这次表现,就是指她在 三十一回下半阕 的高调亮相。三十一回史湘云登场,有两笔很奇怪。
第一笔, 说她穿戴十分齐整、貌似也穿得很多。因此,贾母见她来了,就让她赶紧脱下外面的衣服,怕捂得热着了。
这个情节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 湘云应该从较冷的北部地区而来。
其二, 说明湘云这次着装与平时有异。或者说,与平时比较,她这次的穿着比较讲究。但以她豪迈、随意、不拘小节的性情而论,又不会这样。那么是不是说,她这次来荣府,应该是受到某种礼仪的约束。不要急,先不下结论。
第二笔, 更令人多意。说她这次来荣府,竟带着一伙媳妇丫环。这个情节颇费思量。前文一再念叨,从相关情节和言语判断,史鼎夫妇平时对湘云十分苛刻;那么,湘云这次来荣府,忽然成了史家公主一般,还前呼后拥呢?
因此是不是说,湘云此次来荣府一定是什么情况有变?不急下结论,再看后面的情节。
接下来,先有一个随行的嬷嬷对贾母说:“她衣服都带来了,可不住几天”。就是说,湘云这次是 有备而来 ,原打算就要在荣府住下。
再下来的情节,就是前面曾论述多次的 湘云赠戒 。其中隐含一些详细的有关荣府下层人物的身份问题,论金钏儿之时已经详细说过,不再重复。此节主要来分辨湘云两次赠戒的意义。
请注意,是两次。
从湘云当时及三十二回之初与袭人的对话判断: 史湘云在前一阵儿,已经向钗黛等主子**,赠过戒指。这次她亲自带来的四个戒指,是赠给平儿、袭人、鸳鸯、金钏儿四个身份不凡的丫头。
湘云赠戒 ,能引发一些重要的矛盾和问题:
1 、按湘云在史家窘迫的处境和收入,她为何会突然大面积地向荣府的**和中层好友丫头赠送礼品?
2 、倘说是见面之礼倒也无妨;略能讲通。但三十一回的相会,并不是她们的初见。
3 、为何在前一阵子,只向主子**钗黛二人赠送?而这次来荣府,又亲自向四大丫头赠送?
以上所辨,貌似总有不通的情理。因此,必须重新换个思路,来分辨 三十一回 令人奇怪的描述。
我判断:湘云前一阵结婚了。
要证明这个判断,先理一理头绪先做个假设。 假设: 史湘云在结婚之时,像她这样的孤女,应该说有两个娘家:第一个是史家;另一个就是她从小生长的荣府。
不论她是不是忠靖侯史鼎的亲生闺女,毕竟是名义上的侯门之女。如果结婚倘要讲究排场,史家会向她的婆家提出一些要求;或者说,她的婆家原本就很有脸面,也应当为史府和荣府一些重要的主子**比如钗、黛等人,备一份无关轻重的礼物,表示尊重。
当然,湘云的第一娘家史家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个礼节;向湘云的婆家提出类似要求。毕竟史家是名义上的娘家,其次才是从小生长的娘家荣府。
但这样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比如湘云从小交好、又在心中挂念的平儿等四大丫头,对湘云婆家来说就不必如此周道多礼;因为她们毕竟是下人。
但湘云的心里明显又过意不去;因为这些人跟她自幼相好或还服侍过自己,就像袭人后来说,毕竟是她的 心真 。结婚之后,湘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梯己来置办这四份额外礼品。
婚前,赠给主子**钗黛的礼品因是正规礼仪,自然可以上名账;所以,无论湘云的婆家或史家,都可以由专门负责婚事礼品的仆人来荣府赠送这份礼物。书中确实也这样交侍:赠给钗黛二人的戒指,是由一个男仆送来。这个男仆,应该就是史家负责湘云婚事礼品的执事主管。
而赠给平儿袭人等四大丫头的戒指,因是湘云的私意,只能由她婚后亲自赠送。
以上虽是假说,但如果以这个思路理解,前文次生的所有矛盾和问题就能轻松解决;从情理和礼节上也讲得通。
因此, 湘云已经结婚的假说 ,能够成立。这么说来,三十一回的史大姑娘来了,应该就是史湘云在婚后的 省亲 。民间此举称作回门、或叫住食、或称初次熬娘家。
婚后的第一次回门省亲,是人生大礼。 自然,湘云的婆家或史家就要讲究排场,派有许多媳妇丫环一起陪同来到荣府。
再下来的情节,也都顺理成章。
因湘云已是新婚**、大小成了夫人;她的着装,就不能像从前那么随便。因为新婚之后来到荣府走亲戚,此时湘云的着装多少牵扯着婆家和史家、还有自己的面子。
诸位已婚的女性红友,如上推断可是有些道理?
一般女性,婚后思想都会“急速成熟”;其实不论她究竟真的成熟了没有,也都会表现出一些成熟之状。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即湘云的“阴阳之论”、以及她劝勉宝玉“操心仕途经济学问”也都顺理成章。
以上结论,都附合谶曲“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这段词的含意。
其实,三十二回之初湘云和袭人的对话,也能够说明这个问题。袭人说:“大姑娘,听说你前儿大喜了。”
湘云红着脸不答;接着她俩回忆小时候说过的、有关婚嫁之事的闺蜜私话。无论把大喜之意做何解,而当作婚礼解释总是没错。从袭人的一番话判断,还能看出两个问题:
1 、宝钗把湘云的礼品戒指已转送袭人。因为宝钗明白:依照礼节,湘云的婆家不可能给荣府的丫头也备一份礼品;一个戒指也不值什么,于是做个顺水人情转送袭人。
但湘云送给四大丫头的戒指,含意不同;那里面不只是结婚礼品的一层意义,而还有女孩子之间自小的闺蜜情义。
2 、袭人叫湘云帮自己为宝玉做一双鞋面,而湘云开始并不愿意;因为黛玉曾又一次吃错醋,竟把湘云老早为宝玉做的一件扇套铰坏。
史湘云有点马大哈:她很气恼黛玉疯狂的醋意,是没搞明白黛玉的酸火其实是针对宝钗的“金玉良缘”而发。
以上事例说明: 宝玉和湘云之间, 并没有婚恋的迹象 。
至于考证家说,后来贾宝玉变成了曹雪芹,史湘云演化成脂硕斋;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人生、爱情、婚姻的结局,其成因复杂多变,不可预知的因素太多。尤其 皇帝治下 ,自己更是做不得主。
那么,史湘云既然结婚,她的夫君究竟是个什么人物?这个问题关系湘云的婚姻结局,不得不提出 “金麒麟” 之说。
二、金麒麟的寓意
清虚观打蘸 那段情节说:宝玉的爷爷贾代善有个出家替身,就是张道士;张道士让徒弟的观赏宝玉的通灵宝玉;接着又给宝玉馈赠一盘礼物;其中,有一块较大的赤金点翠的金麒麟;宝玉很喜欢,把它揣在怀里。
从后来的情节观照,宝玉揣下金麒麟,就是想转赠湘云。 以上文的结论进一步推测: 宝玉已经知道湘云结婚的消息;他想把这个金麒麟作为礼物送给湘云。
贾母为打击 王家党 炮制的金玉良缘神话,故意提出另一个金玉良缘:即与史湘云的金麒麟之配。黛玉领悟外祖母意图,配合相当给力;她借事为由跟宝玉大闹一场,把木石姻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公诸天下。
显然,钗黛爱情争斗,的确存在。
前文已详: 黛玉不仅把自己给宝玉做的玉穗铰了;后来竟然连湘云老早为宝玉做下的扇套也给铰了。从文本逻辑推断,黛玉吃醋并无多少道理,只是行为艺术,是一出抗争王家党金玉良缘的表演。
但倘从另一个角度看,会不会是曹雪芹、脂硕斋夫妇有感于命运的诡谲而加进去的一段 写实艺术 ?也未可知。或许曹雪芹兼而有之。猜谜式的探索,于文本的意旨不大,还是 另劈溪径 。
史湘云和丫头翠缕论完阴阳、走到蔷薇花底下,捡到了宝玉遗落的金麒麟。 前面说过: 这是宝玉痴迷 龄官画蔷 之时、因突发暴雨而不小心丢下的。史湘云举目一验,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戴的又大又有文彩;湘云伸手擎在掌上默默不语,正自出神。
湘云为何出神?
因为她和翠缕才刚论完阴阳。显然,宝玉从张道士处得到的是一块雄性金麒麟;而湘云佩戴的是雌性。 所以翠缕大笑: 可分出阴阳来了。
这回的标题是“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因此产生或次生的红楼学术和红楼八卦太多。
刘心武先生的原型辨证 就转了几个大圈:先是湘云和卫若兰的婚变,接着还猜测张道士和贾母之间的原生态恋情; 最后结论说 :宝玉湘云二人因受到打击太大而早早白头;这就是白首双星之意。
读罢感觉总不如意,一旦跌进脂批的八卦炉中,将永远转不出来。所谓白首双星,不过是曹雪芹婉转地表述自己的文化理念。
前面说过: 阴阳学说,抛开其主观臆测部分,其实有许多优点,即思维的多样性。麒麟与龙,都是古中国人民想像出来的多元化、多功能、多组合神兽;都是中华文化的图腾标志。
神兽麒麟身上具有许多优点,代表中华先祖的优秀品质。
之初的 阴阳学说 ,是道家学派对 世界本因 片面的猜测式解释;自北宋张载起把该学说全面推向高峰。此后的阴阳学说,被两宋理学大师借鉴并发挥。
所以,宋之后的新儒学基本是道儒释三家学问的结晶,一直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的意识形态。
前面不至一次地指出: 两宋及之后的理学家因自己的高级奴才地位,共同犯下最要命的错误,如丫头翠缕一样,主观地为人类、为自己分出阴阳等级。翠缕提出人分阴阳的想法后,湘云立即就啐了她。
曹雪芹的绝招就是双关、多关和谐音。所谓翠缕,就是春绿;其实是蠢驴的谐音。曹雪芹在此表达对理学糟粕的蔑视。
宋之后的宋明理学即所谓新儒学,从主观上抛弃了道释两家文化精华即平等自由的思想而走向反面,沦为极权的帮凶。尽管元明之后也有许多理学大师疾声呼吁平等自由,但始终无法形成主流。
曹雪芹即有感于此,重新发出了白首双星的感叹。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道儒两家文化精华,果真能够实现金玉之间的配对,那么就像白头偕老的夫妻一样,才能够天长地久。
史湘云咏菊花作《对菊》诗曰: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正是对道儒两家文化精华之所指。诗里的 别圃 ,又牵扯到史上王朝更替之际的一位文化精英,他叫熊禾。
熊禾才华盖世、风格高洁;他是南宋末年至元初时代的文化大师,曾做过一首《题林氏药圃》有关咏菊的著名古诗。 南宋灭亡, 熊禾立誓不事蒙元蛮夷,从此隐居。他专心研修理学,对朱熹极为推崇。熊禾的学问修养极其高深。
但怪异的是: 同一种文化竟然能教化出风格截然不同的精英。难道说,作为南宋初年的秦桧就没读过、还是没读懂理学大师的著作?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猫腻和把戏?还是有人故意捣鬼? 真是个谜! 因此不得不说,这又是皇帝治下一桩文化悲剧。
读罢湘云此诗再联想到熊禾;可以判断,她虽为满清高级奴才但应该不会事于满清,这正是曹雪芹魏晋风度的文明理念和文化风骨。但他的理想在皇帝治下究竟能不能实现、他会给史湘云安排怎样的人生结局呢?
唐都浪子《浪说红楼》之:论史湘云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