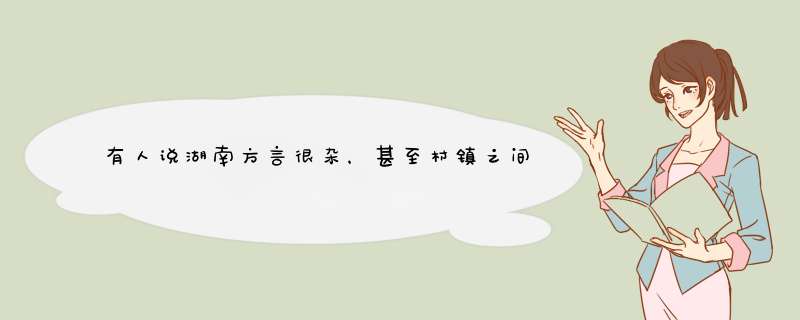
另外,中华文明历经五千余年,虽从未间断,但所历朝代、大小分制众多。这种文化与分封诸侯等因素,导致了文化或语言上的一些互通不畅。因此,形成了当前我国的省与省、巿与市、村屯与村屯之间方言各不相同的现象。
但无论方言如何不同,各民族语言如何不同,但中文(汉语)却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 历史 文化的传承,形成了我们当今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趣的中国方言。
我是湖南邵阳人,我们村就是这么奇葩的一个村,一个村有两种方言,新化方言和邵阳方言,而且两种方言的差别还非常大,说新化方言的人和说邵阳方言的人初次打交道,两人不用普通话是完全没法交流的。
我是湖南邵阳新邵县的,我们县是1952年成立的,是由当时的新化县和邵阳县两个县各拿出一部分来组建成新邵县。邵阳县属于邵阳市,新化县属于娄底市,我们新邵县成立后属于邵阳市,因为新邵县大部分是邵阳县的,新邵县划分11个镇和4个乡,龙溪铺镇、坪上镇、迎光乡、大新乡属于之前新化县,其他镇都是属于之前邵阳县的。
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镇,那就是我们巨口铺镇,这个镇是之前邵阳和新化的边界,所以我们巨口铺镇有讲邵阳方言的和讲新化方言的。我们草鞋铺村是讲新化方言,我们村过去800米的马落桥村讲的是邵阳方言,记得小时候我们村一群小朋友经常和马落桥村的小朋友吵架,他们会骂我们“新化佬,吃茅草”。
读高中后去了县城一中,我们县一中是湖南省重点高中,除了县城的学生,其他地方学生,必须是班上前三名才有可能考上一中,等于一个学校只有10个人能考上一中,一个镇差不多也就20个人能考上一中。所以上了一中后,发现学校90%的同学都是讲邵阳话的,我们讲新化方言的成了另类一样。
所以那时读高中,同学们经常学我说话,觉得我们新化方言很有趣,让我叫他们说新化方言。刚开始我听他们的邵阳话也是听不太懂,更要命的是我们化学老师讲课时也是用邵阳方言讲,我听了都是懵懵懂懂的。大概是一个月后,我也就基本能听懂所有邵阳方言了,可是同学们却没有我这么聪明伶俐,我的新化方言他们始终都是听不懂,导致每次和他们说话我很纠结,我将普通话吧他们会说我装,讲新化话他们又听不明白,于是我只能学他们说邵阳话。
如果说起我们邵阳最奇葩的,那肯定是网上有名的邵阳北站高铁站,邵阳目前有三座高铁站,分别是邵阳北站、邵阳南站、邵阳西站。邵阳北站是邵阳建的第一座高铁站,为什么说它奇葩呢?因为它离邵阳市中心有70多公里,它建在我们新邵境内的坪上镇,但是离我们镇距离还挺远的,而且交通不方便,我们那里没有到高铁站的车,去坐高铁还必须先坐车到市客运站,而衡阳东高铁站离我们邵阳市中心也大概是70多公里,于是很多人会选择去衡阳坐高铁。邵阳北站对于邵阳人来说毫无意义,在大家的一片声讨中才又迎来了邵阳南高铁站,如今的邵阳北站每天冷冷清清。
造成这种多方言也是有原因的
第一,地理位置原因
第二,战乱原因
由于战乱,百姓先后经历多次迁徙,由于每次迁徙来源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由于地形的阻碍,长期各地缺乏充分的交流,又把这种说话的方式固化下来,再加上湘地的原始居民就形成了湖南丰富多彩的方言。
尤其是元末明初时期,朱元璋和陈友谅旧部进行了多年的拉锯战,导致湖南百姓深受其害,大量的湖南居民外逃,等到明朝控制湖南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大量人员迁入湖南,遍布了三湘大地,致使湖南人口来源复杂,方言众多。
对于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去看一下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等的著作《湖南方言》。书中对湖南的方言做了全面研究和描述。
湖南省境内的这些方言形成的 历史 文化错综复杂,在巜湖南方言》书中有详细记载。
湖南当地的汉语方言分布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是湘语和官话,其次是赣语和客家话,还有归属不明确的土话(包括平话和瓦乡话);湖南的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有苗语、土家语、侗语、勉语以及壮语。
根据湖南的 历史 及所处的地理环境,湖南的方言众多,加上少数民族的语言和土话,你说的相邻村的话都会有区别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建议大家都用官方语言交流。
常话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有些地方大同小异,有的地方差异较大,如同南北田地生长的作物一样,千差万别,是种人文因素与当地自然环境紧密融合长期形成的特殊现象。
当年小日本打到湖南、他们大的失败就是情报失误所致,晓得为什么吗?就市因为我军用的谍报密码是湖南各省土语做了一套密码本,小日本汪汪叫硬是冒搞明白哒……
不是湖南,江南山区大多方言复杂难听懂。古代没有好的交通,人们都到闭于一 小范围内,长而久之的自给自足生活导至语言千百不一,在我小时候,老人还有许多方言,十里一变。现在消失了。在南方不论什么方言,但文字都是汉字!
我我就是湖南人湖南话我全都听得懂。
整个湖南的民族地图可以看到湘西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这里有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而湖南的东面基本都是汉族,大部分都是江西移民的后裔。
而从湘西到贵州,四川,云南,是这种民族杂居地图的延续。
这些地方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地区,汉族大部分都是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
由于民族复杂,语言就会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种地方方言。每一个地区民族不同,语言调和程度就不同,少数民族人口多,语言就会偏少数民族语言特点,汉族人多就会偏汉族一方,造成各地语言乱杂,互相交流困难。
以后有了西南官话,所有人无论你是什么民族都讲西南官话,这样陈旧的语言逐渐被西南官话取代,只有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原来的土语。
这就是云贵川地区语言相近的概况。
而湖南没有云贵川语言杂乱,西南官话,没有普及到湖南,湖南仍然保留着原来的语言方式,结果,云贵川的西南官话反而普及程度超过湖南,而使湖南普及率低于云贵川。
你从云南经四川,贵州,再到湖南,你会感觉一到湖南语言就变调了,而且难懂。
但是你到了湘东地方,仔细听,你会发现,湘东与赣西的语言近似。语言词汇一样。吃饭都叫掐饭,睡觉都叫困告。
湖南除了湘西受到西南官话影响,湘东地方没有受到西南官话影响,而保留至今,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湘东地方,语言近似,又有不同,初听者不懂,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也就听懂了。
中国的语言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也是按照地区的延伸,逐渐变化的。
各个族群之间有原始的孤立的语言岛,这就是少数民族语言,比如贵州的苗族语言,深山沟里还保留着,西南官话没有改造他们。贵州人大部分听不懂这种语言。
而湖南湘东地方,也保留着古老的汉族地方方言,这种方言只是发音微有改变,词汇是一样的。
保留汉族古老的地方语言的有赣语,粤语,闽南语,等许多语言。这些语言属于汉语地方语言,尤其是赣语,湘东语受到楚文化影响重,而闽南语,粤语受到百越民族语言影响重。这些语言属于受到其他民族影响的汉语。
中国有没有没有受到其他民族语言影响的古老纯正汉语呢?
基本没有!
今天的中国正受到英语的影响,比如再见,许多人不用这个词汇了,而叫拜拜,慢慢的再见这个汉语古老词汇就会丢失,而用拜拜来取代。
湖南的湘东地方,还保留着古老的汉族地方湖南话,在今后普通话的普及下,这些地方语言也会缩小,最后丢失。
湖南的方言确实很杂 ,但也不至于村镇之间说话都听不懂 ,这话有一点夸张 ,可以把这一个范围扩大一点 ,县与县之间说话速度快了会听不懂 ,但是说慢一点仔细听 ,还是能够听懂的 。
我的老家在原株洲县王十万 ,(现为渌口区龙船镇 ),与衡东湘潭搭界 ,是三个县相交之处 。我们那里与湘潭县的口音基本上差不多 ,属于同一个语系 ,如果是外地人听 基本上是一个口音 ,本地人只要开口说话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据说我们的祖先是湘潭县马家堰乡移民过来的 ,所以我们与湘潭县属于同宗同源 ,最初株洲市属于湘潭 ,后面才划分出来 。记得早些年乡下的老人修族谱 ,建祠堂 ,我们的马氏祠堂也建在湘潭县的马家堰乡 。按照当时的传说是在台湾的马英九出钱建祠堂, 修族谱 ,说是为了这个事情他本人出了80万美元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从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台湾的马英九是湘潭县人 ,他还有个姐姐在湘潭县某中学 ,按照马氏族谱的字辈算 ,他属于我们的爷爷辈了。因为最初株洲是属于湘潭 ,人员的流动比较频繁 ,语音基本上都差不多 ,即使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别 ,两地的人交流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困难 。
我们与衡东县以一条湘江为界 ,与衡东县的口音差别就比较大了 ,如果对方说话的语速太快 ,双方又不熟悉的情况下 ,那基本上就是在听外语 。在我们王十万乡的湘江河中间 ,有一个小岛叫挽洲岛 ,他们的口音一半是我们这边的 ,一半是衡东的口音 ,也称“夹山腔”,受到两边的语音影响 ,所以形成了独特的口音 。记得在我们的小时候 ,我们生产队里的一个小伙子讨的媳妇是衡东人 ,在这边已经生儿育女 ,生活了很多年以后仍然不改口音 ,不管大人和小孩都有学她的口音 ,当做生活中的一个“乐子”,我的衡东话就是那时候学下来的 ,在多年以后还派上了“用场”!
那时候是我已经到现在的单位上班了 ,到我们的一个同事家里去玩,他们家就是南岳衡山那里的 ,顺便到了南岳衡山风景区去玩,用他们本地的口音“免了门票 ”。那天去南岳山登顶的时候 ,我们在门口看了一下 ,每一个人都要买一张门票凭票进山,但是也看到有人不要门票进去了 ,他们都说着本地的口音 ,他们说的意思就是“本地人要什么票 ?”,用衡山山话说就是“丙地宁,要吗个票?”于是我也发挥了我的语言天赋 ,学着他们的口音说了这句话 ,免了我的门票 。
本人正是湖南一个偏僻乡村的人,我们的方言的确十分复杂,同县的人互相交流,有时必须高度制中注意力听,且有时也没听懂,又问对方,同一镇的方言有许多种,甚至一个村都有几种方言,一条乡村小街道,实际上就是一个稍大一点的屋堂,有两种方言,有时两种方言区别还比较大,一般以行政区划分界。也就是说,上半街属甲县(镇),就说甲县(镇)的方言;下半街属乙县(镇)就说乙县(镇)的方言。本人所在的镇,五县市交界,靠近哪个县市,口音高与哪个县市接近,但又不全是他们的口音,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口音就是这么怪怪的,不伦不类。当然,对方也许觉得我方的口音才是怪怪的,不伦不类。像本人这两个镇,口音与同县其他乡镇区别较大,反而与邻近的四个县的口音区别小一些。当然,正常情况下,我们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由于我们比较熟悉对方的方言,有人居然能随便模仿多种县市的方言,有的能惟妙惟肖,不露破绽,当然,也有的由于关键字音发音错误,一下就对方认出是某地的冒充者!交界地方常常利用对方方言的奇怪词汇或发音,互相编段子,取笑对方,编得十分 搞笑 !不该相同的字音在方言里有时相同,在普通话里相同的字音,有时在方言里只要字形不同,读音就不同。许多方言词汇,普通话里都没有。方言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远比普通话形象生动。由于十分熟练的缘故,使用起来速度很快,比打机会枪还快。方言的区别,笔者发现一是与行政区域划分有关,许多地方,从古至今的行政区域划分,变化不大,如上方的人总与上方交往,下方的人总与下方交往,久而久之,上方的人与下方的人方言就不同!如果恰恰在某一个村子或街分界,那么,这个村子或街就会出现两种方言。还有,笔言与河流的流经区域有关。笔者所在的两个镇,一条河基本是向东流入外县,我们的方言反而是与流经区域的方言不相上下。但我们这两个镇却是划入高山的反向的县,实际上,其他乡村是在一条河的流往区域,他们的河水是往西南流,也与我们不是一条河,他们的方言却不相上下。可以断定,古人的活动,与河流流经区域有很大的关系。回答供参考。
原意有贬低的意思,“别”,意为女性生殖器,湘潭土话,骂人的。现在延伸为称呼,没有了原来的意思。自然,上口,也就不以为然了,大家都习惯了,遂成了一种称呼。往往是姓后面带之;或是名字里一个字带之。显得亲切、亲近,一般都是玩得好的男性青年人相互间称呼,女孩子很少用这个词。
长沙话和湘潭话区别:长沙话(市区)全都是平舌音,湘潭话是有卷舌音的;其次,在有些词汇的发音上面,二者有些差别。例如,长沙话好热是好yue,湘潭话好热是好ye。湘潭话,如果是湘潭市和市区附近的和长沙话区别不大,彼此之间比较接近。长沙话,即长沙方言,属于新湘语。所谓长沙方言分布于长沙主城区和望城区、长沙县中南部以及宁乡市东北部所使用的语言。
长沙方言的特点是古全浊声母字舒声字清化为不送气清音,是新湘语的代表方言。与官话古全浊声母字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不同。以下几组字长沙方言声母相同:(情=尽)(桃=道)(同=洞),而普通话前者都是送气清音。
湘潭话,即湘潭方言,属于湘方言中新湘语的一支。狭义的湘潭方言指的是湘潭市区通行的方言,湘潭市区的方言与湘潭县的方言有所区别,与韶山市通行的韶山方言差异巨大。与长沙市区方言大部分相同,可以相通使用。广义的湘潭话,包括湘潭市区、株洲市区、及湘潭县、株洲县以及衡山县北部的方言,和以老湘语湘乡话方言两种。
地域
湘潭位于湘中偏东,湘江中游,东连长沙,株洲,南接衡东,衡山,西邻双峰,娄底,北毗宁乡,望城。现辖湘潭,湘乡市,韶山市,雨湖以及岳塘二区。狭义的湘潭方言指湘潭市区的方言,湘潭市区的方言与湘潭县话有所区别。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湘潭人讲什么话,用什么词与湘潭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湘潭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季长,降雨丰富,气候较湿润。湘江穿城而过,境内还有涟水、涓水,有韶山灌区总干渠、南北干渠,还有水府庙水库——水网密布,湘潭可谓之“水乡”。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湘潭的“水乡文化”,进而又导致了一些与水有关的湘潭方言词汇的产生和运用。比如拉关系、走后门被喻为“走水路”;作风不正派的男人被称为“水老倌”;不正派、庸俗下流叫作“水里水气”(也叫做“流里流气”);肤色被称为“水色”。另外,因为湘潭河道多,尤其湘江作为长江的一大干流,自古至今,航运都相当发达。驾船的人,在水上生活,以船为家,就不喜欢说“沉”,所以讲“盛饭”为“张饭”或“装饭”。
湘潭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水面俱备,与这些地貌有关的词语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就以之命名。习惯上,湘潭人把“山”叫做“岭”,比如砂子岭、塔岭乡;把山谷中的平地叫做“冲”,比如毛泽东故居所在地韶山冲;把山区和丘陵地区局部的平地叫“坪”,比如黄荆坪。与水有关的,湘潭人把屋门口的水池叫做“塘”,如洪塘乡,岳塘区,泉塘子,响塘。水多,桥自然也多,以桥为名的地方如青山桥,云湖桥,双板桥等。 一种方言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源头在某个时期就突然诞生了,它总是与该地域的古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湘潭方言中有不少词语就是与古湘语一脉相承的,这些词在现在依旧用得很广泛。
例如,崽。《方言》是这样解释的:“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现在,湘潭人基本上称“儿子”为“崽”。但“崽”的“儿子”义,在用于称谓词后时已经开始虚化,主要用来表示“小”及亲切喜爱的感情色彩,一般用来指称“小孩、男孩、女孩”等,比如“伢崽”指“男孩儿”,“妹崽”指“女孩儿”。但在具体使用中,又往往习惯称男孩为“某妹崽”,这其实是对小孩的贱称,用贱称来称呼男孩可以避凶趋吉,使之易于成长;又把女孩称为“某伢崽”,就带有那种喜爱意,也表现了人们对男性的重视和崇尚心理。不过,“满崽子”(小儿子,父母子女中排行最小的儿子)一词可以讲是“儿子”意和“喜爱”意这两种意思结合得最完美的了。
又如《离骚》:“凭不厌乎求索”。王逸注:“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按照王力的拟音,读[b‘下eη] ,就是“朋”的音。如今,湘潭人称“水满了”也习惯上说成“水朋咯哒”。 所以,湘潭话中的“朋”很可能就是古楚方言“凭”的后代。
再如,起。《汉书·武帝纪》里有“起建章宫。”桓谭《新论·识道》里有“大起宫室”。这两个“起”,均为“建造”意。现在,湘潭人也是称“建房”为“起屋”。
另外,像湘潭人常常用的“你几好”的“几”(“多么”意),“一兜白菜”的“兜”(“棵”意)等都是源自古湘语。还有“堂客”(“妻子”意)、“后日子”(“后天”意)、“样范”(“模样”意)等词就是宋元明清古白话遗留下来的。 自古以来楚人尚巫信鬼重祭祀,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湘潭也受着这种巫风盛行、习沿尚鬼的巫鬼文化的熏陶,所以湘潭方言中有关“鬼”“死”的词汇不绝于耳。
为了表达对于鬼神的敬畏,湘潭人对于“死”和与“死”有关的事物有很多忌讳。用 “白喜事”表示丧事;用“老嘎哒”、“过咖哒”或“去(读kè)嘎哒”表示人死了;“棺材”叫“料”,“出殡”叫“上山”、“出升”。不过,“死”也有“程度很深”之意。比如,“我爱死你了”一句中,“死”是用来表示爱之深的;“她懒死了”、“这糖甜死了”则是表示懒的程度、糖甜的程度。
“鬼”在湘潭方言中运用更多。可用来表达对于人的爱称、戏称,如“小鬼”是指自家的或通称的小孩儿;“鬼崽子”指调皮的小孩子;妻子还会笑嗔丈夫为“死鬼”。可用于朋友间的戏谑,“鬼五十七”戏称对方不正经,故意捣乱;“鬼相样子”表示别人装腔作势,或打扮作派不让人满意。可用来骂人,例如:饿死鬼、怕死鬼、胆小鬼、懒鬼、短命鬼、好呷鬼(好吃鬼)、讨厌鬼、替死鬼、冒失鬼、糊涂鬼、窝囊鬼。可用来表示运气不好,“背时鬼”指一个人不走时运,“碰哒鬼”表示碰到不好的结果,“鬼寻哒”表示遇到不好的事情,出乎意料之外。
另外,很多传统节日的存在也产生了许多有特色的词。七月初七至十五俗称“过半年”,也叫“接客”,“祭祖”,初七到初十接新亡客,初十以后接老亡客。腊月廿三“送灶神”,廿四“过小年”,除夕“团年”。大年初一凌晨,农民在大门内设香供天地,祈求好年成,放“千响”,是“出天行”,出天行后是“拜年”,规矩是“初一崽,初二郎(女婿),初三初四拜团坊”,若是“拜年拜到初七八”,便“洗嘎锅子浪嘎”,莫怪主人缺乏招待了。 “民以食为天”,湘潭方言中很多词汇都与这个“食”字有着莫大的关系。
湘潭基本上种植水稻,湘潭人以米饭为主食,甚至讲“吃饭”也大都表示“吃米饭”。以米为原料的食物,有甜酒(新疆人称之为“醪糟”),糍粑,灯芯糕等。
具有特色的还有湘潭中路铺产的“药糖”,毛家饭店的“毛家红烧肉”。另外,农历三月初三要煮蛋吃,也叫“三月三”。原是一种农村习俗,农民认为吃“三月三”可以治风湿,防风寒。农民每年这个时候还要做的一道菜叫“夫子肉”,也叫“粉蒸肉”,做法是:将米碾碎,配上切得较大块的猪肉,再加上食品红和几味中药一起蒸。
都说湖南人不怕辣,湘潭人更是如此,简直是怕不辣了。所以,湘潭人爱吃辣椒,家中必备的一种调料是“辣椒粉”,也叫“辣椒灰”。湘潭人做辣椒的方法很多,剁辣椒,浸班椒(辣椒),班椒酱,豆豉辣椒,盐辣椒等等。
“食”文化对湘潭方言词汇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特色食物上,还表体现在湘潭人根据“吃”发明了很多新词来表达某些意义。比如,“吃蕻子菜”用来批评接受奉承,“吃白豆豉”叫没本事,欺负人是“吃住(人)”,贪赃受贿叫“吃冤枉”, 白吃饭不做事是“吃空饭”。 新时期会产生大量新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湘潭方言中也汇入了一些新词。这些词主要是来自湘地的流行时尚。
一些被当红主持人在高收视率的电视媒体中巧妙而繁复运用的词语就很容易成为流行,被大众广泛接受并使用,像《越策越开心》的主持人汪涵、马可就在节目中频繁使用“那确实”、“妹陀”、“策”等词。奇志大兵和杨志淳在他们的方言相声和双簧中使用的一些词语,如“哈利油”“杨五六”“灵泛”,也是在湘潭迅速流行。
表示调解纠纷、解决难题的“了难”,指卖主设圈套引诱顾客上当的“带笼子”, 表示出丑、没风度意的“绊式样”,还有用来指骗子的“撮把子”,称呼人的“的哥”(开的士的人)、“满哥”(年轻男人),都是最近几年才被湘潭人广泛使用的时尚词。
透过这些流行时尚词,我们能窥见湘潭人求新和从众的心理,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些新的方言词汇一出现,就很快成为湘潭人男女老少茶余饭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某些词,甚至直接反映了湘潭人的性格特点,比如“舍得死”、“霸点蛮”、“耐点烦”、“恰跌苦”。
湘潭方言和现代汉语共同语之间存在一些词汇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词汇意义不同:有些湘潭方言中的词汇与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词汇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湘潭方言中的“噶杂”表示“干什么”,而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则没有这个意思。
2 词汇发音不同:湘潭方言的发音特点与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发音特点有所不同。例如,湘潭方言中的“噶杂”发音为ga3 zua3,而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可”发音为ke3。
3 词汇使用不同:有些湘潭方言中的词汇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可能不再使用或者使用频率较低。例如,湘潭方言中的“麻雀”表示“拳头”,而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则不常用。
4 新旧词替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词汇进入了湘潭方言,而一些旧的词汇则被现代汉语共同语所取代。例如,湘潭方言中的“摩托”表示“摩托车”,而现代汉语共同语中则使用“摩托车”这个词。
总的来说,湘潭方言和现代汉语共同语之间的词汇差异是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也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汉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