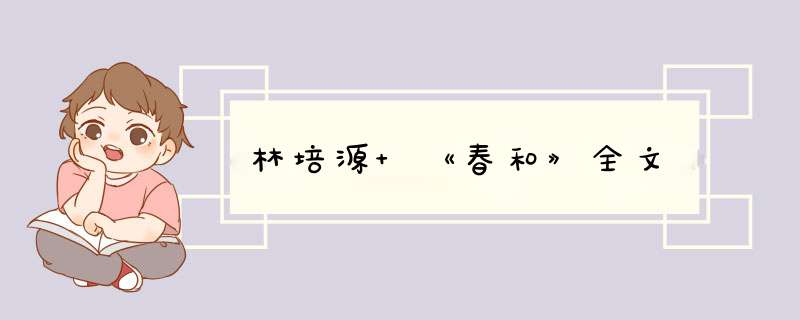
即使在梦里,春和也会惊出一身汗来。
冬末春初的南方,稍不注意就会跌入季节挖好的陷阱里。入夜之后,气温骤降。春和怕冷,手脚冰凉一片,她不得不把自己裹在一床厚实的棉被里。整夜整夜听着女人压抑的啜泣以及窗外呼呼的风声,寒夜漫漫,春和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孤单,她盯着天花板无法入睡。窗口被镂空的微薄光亮照进来。
阁楼里压抑的哭声让人背脊发寒,春和紧紧拽住被子,把头蒙住,但一闭上眼就会看见女人直勾勾的眼神,仿若暗夜笼罩下的泥沼,女人咬着嘴唇,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
春和觉得,女人之所以会疯,完全是因为心里的妒恨之火无法浇熄。它们积聚在心中,因为找不到发泄的出口,所以延烧出来,把这个濒临离散的家逼向洞窟。
十年了,春和再没有叫过她一句妈妈。
仿佛除了曾经待在女人的子宫里与她血肉相连外,再无任何瓜葛。女人将春和生在这个世上,抛给她一个清冷而幽寂的童年,然后再也不着一丝温煦。春和就是这么觉得,这个女人如果褪去一张冷艳的脸,就只剩赤裸裸的空壳了。
十岁之前的记忆,停留在这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春和肚子饿了,哭起来,但女人全然不理会,她坐在沙发上,手持一把剪刀卡擦卡擦把自己的头发剪断,剪刀和发丝摩擦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凄冷,咔嚓——咔嚓——,把旧时光一点一点剪碎。春和清楚地记得,女人的头发因为长期照不到阳光,干枯得好似一株缺水的植物。发丝掉下来,落在冰凉的地砖上,红色的地砖和黑色的发丝,形成一副诡谲的图案。春和满脸的泪痕,她把手撑在地上,地砖因为汲取了土层的寒气,摸起来极为清冷。春和拉着女人的衣袖,说了一句:“我肚子饿。”声音孱弱得像一只羊羔。
女人不说话,她的眼睛看看起来黯淡无光。春和不知女人心里究竟想写什么,春和只是肚子饿了,想要吃东西。女人已经十几天没有下厨了,这些日子,母女俩靠奶奶送来的饭菜,才不会挨饿。但前几日奶奶在井边挑水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小腿骨折,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治疗,所以现在母女俩只能挨饿了。春和记得那天,奶奶站在这间屋子里,她的身子已经明显发胖了。老人家连说话都很吃力,她气得浑身直颤,指着女人厉声呵斥道:“蒋芸,你怎么当孩子她妈的!”
蒋芸慢悠悠地抬起一双眼,眼底尽是无畏的冷漠。她回了一句:“你也是当妈的,怎么不叫你儿子去死。”
“有你这么说话的?”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你问问徐锦,他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
奶奶鼓胀起来的怒气被蒋芸一句话就给挡回去了。春和搬着一张小凳子在客厅里写作业,她读三年级,老师布置的数学题她不会做,她心里烦躁,耳边又是妈妈和奶奶争吵的声音,春和捂着耳朵,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些嘈杂难听的对骂挡住,可以让自己获得片刻的安宁。
但眼前的数学题忽然模糊一片,春和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她握着铅笔,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妈妈,你们不要吵了,我要做作业。”春和抬起头,看着蒋芸。
蒋芸蹲下来,捏住春和的手腕,咬着牙说了句:“别说话!”蒋芸的手很冰,捏住春和的力道很大。春和都被捏疼了,脸上显出难受的表情。但蒋芸并不松开手,好似拼了命要掐住什么似的。
奶奶看不过去,走过来拉起春和。春和很瘦弱,她的额头贴着奶奶的身体,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蒋芸。蒋芸却不看她,说:“你要走就走,我不会留你。”
春和抿着嘴,屋子里的晦暗和潮湿已经让她快透不过气了。她的小手藏在奶奶的掌心里,那一瞬间,她犹豫着要不要跟着奶奶走,但她不知道,没有人告诉她该不该走,她只是这样子站着,看了看一脸阴郁的蒋芸,又看了看那本被泪水打湿的作业本,那一瞬间,她觉得泪水打湿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本子,而是,整个世界。
奶奶拉了拉她,她踌躇了一下,就跟着奶奶走了。外面的阳光照着她,阳光并不耀眼,可她还是轻轻地闭上了眼睛,阳光的余温停留在视网膜上,留下浅浅的影子。
在奶奶家才待了一两天,老人家就出事了。她在井边打水的时候滑了一跤,小腿骨折。春和只记得那天,奶奶喊了一声,等到春和跑出家门口的时候,奶奶已经跌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水桶掉在地上,滚得很远,水流了一地,把奶奶的衣服都淋湿了。邻居听闻喊声,手忙脚乱地把老人家抬上自行车的后座,一个人在后面推,另一个扶着车,一路疾跑,慌乱的身影消失在巷子的拐角。
当天上午,大伯去了趟医院就过来接春和。春和潜意识里,是惧怕到大伯家的,只因为春和的家冰冷得像个洞窟,而大伯一家却是对比如此鲜明的温馨。唯一让她不惧怕的,是堂哥景明还有大伯。刻薄的大伯母常拿白眼看她,中午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春和一直低着头扒饭,大伯母有一句没一句地数落大伯:“你看你,别人家的闲事你干嘛要管?”春和知道她话里的意思,先前两家人因为爷爷遗产划分的事情吵架,从那时候开始,大伯母就非常讨厌春和一家。春和虽然年纪小,但这些事情看在眼里,她是懂的。大伯有些难堪:“什么叫别人家的闲事?徐锦好歹也是我弟弟!”
“你还有这个弟弟啊?人家都不当你是他哥!他骗你钱你还帮他说话!”
春和实在听不下去,眼泪啪嗒啪嗒就掉下来了,她拼命忍住,不敢哭出声,仿佛一旦被大伯母发现,所有她掩饰起来的倔强就都分崩离析了。饭后,春和躲在景明的房间里,拿枕头蒙着脸,这样子别人就听不见她哭了。景明坐在床沿上,拍了拍春和的背,又搬出他的所有玩具来哄春和。景明打心底是喜欢这个妹妹的,她的倔强,她的懂事,她那双即使浸*与黑暗之中仍然散发光亮的眼睛,都让景明心疼,甚至惋惜。
景明说:“妹妹,别哭了,要不你以后就住我们家吧。”
春和从枕头里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瞪着景明:“我才不要!”
景明以为春和是喜欢他家的,但春和眼神里透露出来的凛冽令他不安。景明比春和早半天来到这个人世,两人之所以取了这样的名字,全然是因为大伯这个书虫,大伯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云:‘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春光和煦,风景鲜明,都是好名字哇。”当天在医院里,两家人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没想到这一转眼,两个孩子的命运奔向了不同的疆界。
那天晚上,春和和景明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春和已经记不得,是第几次和景明睡在一起了。她的生命里很少有男孩子,小时候景明常来找春和玩。玩得累了,两个人就躺在床上,不久就呼呼睡着了。等到春和醒来的时候,往往是景明搂着她的小脖子。家人只当他们小孩子,从未过问什么。景明自幼没有什么玩伴,能够和妹妹这么投机,向来刻薄的大伯母居然也没有说什么。
春和记得景明有很长的睫毛,像个洋娃娃一样。这一点让春和十分嫉妒,因为小小的春和就知道,女孩子睫毛长才好看,但偏偏她没有又长又翘的睫毛。这是春和童年里拮据而难忘的快乐。
春和躺在黑暗里,她问景明:“你说我爸爸还会喜欢我吗?”
景明转过头来,盯着春和,黑暗中,春和的侧脸轮廓十分鲜明。景明看着她说:“一定会的,哪有爸爸不喜欢孩子的?”
两个人在安静的房间里压低着声音说悄悄话,说到累了,才睡着了。
第二天,春和要大伯送她回家。大伯拉着春和的手,这个面容和善的男人告诉春和:“现在回到家,要听话,知道吗?”春和看着大伯,印象里他是一个好人。春和记得,爷爷在的时候经常对她说:“世上的好人和坏人很容易分,你只要看着他的眼睛就知道了。”但具体怎么个分法,春和其实并不知晓,她只知道,大伯对她很好,春和很小的时候,大伯每一次来家里,都会捎上好吃的给春和,他的眼睛里盛满了阳光,那是和爸爸截然不同的眼神,温煦,柔和,甚至,带着春和生命里极为缺失的爱。所以一开始,春和就认定大伯是个好人。
大伯骑着自行车载春和回家。一路上,春和紧紧地抱着大伯,大伯的腰很粗,春和把脸贴到上面,可以闻到他身上的味道,一种不同于爸爸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春和突然好伤感,她的鼻子酸酸的,她想起爸爸了,想起这个乖戾的男人。春和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对这个经常不回家的男人如此想念,她也不明白为什么爸妈不能相亲相爱,春和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她搂着大伯,问道:“大伯,为什么我爸爸不回家了?”
大伯抽出一只手,摸了摸她的头说:“你爸爸会回来的。”
春和若有所思地说:“嗯,他会回来的。”
黄昏的街道上,并没有多少人,春和盯着路边几户人家的高墙,墙体上爬满了肆意滋长的青苔,春和看着它们,突然觉得自己和它们很像。
卑微地生长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阳光照不到,生命剩余晦暗的颜色。
微薄的光亮散落在这个南方的小镇上,路边紧挨着的人家已经开始生火做饭了,烟囱里冒出袅袅的炊烟,春和抬起头,看着一缕缕浑浊的白烟升到空中,一群鸽子盘旋着掠过。春和闻到散发在空气里的米香,丝丝入扣,引诱着春和的味觉,已经好久了,春和没有吃过妈妈亲手做的饭,奶奶送来的饭菜大多已经冷了。
春和望着天空,又低下头来,看着脚下不断向后延伸的石板路,耳边只有轻微的风声以及自行车脚踏板踩动发出的吱呀声。整个小镇像包裹在粘稠的蛋黄之中,天边的霞光慢慢隐退,小镇在这个时候显得无比安静,也无比寂寥。
到了家门口,大伯将春和抱下车。大门紧闭着,大伯敲了好久的门,蒋芸才走过来拿了门闩。这道沉重的铁门早已锈迹斑斑,蒋芸推开一条缝。看到大伯,她好像猝不及防被谁地叮咬一口:“你来干什么!”
大伯把春和推到前面:“春和,我给你送回来了。”
春和看见推开的窄窄的门缝,蒋芸露出半张脸,屋子里晦暗一片。春和站着不动,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蒋芸。
但蒋芸却不看春和,她对着大伯说:“你走!谁让你来的!”
大伯张了张嘴,迟疑了一下,便蹲下来,看着春和说:“大伯要走了,你回家吧。”谁知春和却紧紧地搂住了他:“我不回家。”
大伯抬起头,看了一眼藏在门缝后面的蒋芸。两人眼神交接的时候,蒋芸嘴里哼了一声:“我们家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眼里还有这个家?有心的话你就不会扔下春和不管!”
“你们姓徐的没一个好东西,我的事不用你管,给我滚!”蒋芸几乎是拼了气力在骂,春和从来没有听见过她以这样的语气骂人,即使是对爸爸,蒋芸也从未如此咬牙切齿过。春和听惯了这个女人各种恶毒的话,一想到她现在已经可以随口对她讨厌的人如此开骂,春和就觉得如芒在背。
大伯摸了摸春和的脸,眼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无奈。春和拉住他的裤腿,不让他走。春和背后的一道铁门,好像隔开了两个世界,一半安稳,一半动荡。
大伯面露难色,不知道应该怎么和春和说。
蒋芸冷笑着,她忽然把铁门推开了,光线稍稍照在她的脸上。她揪住春和的胳膊,硬是将她推到大伯的怀里。“怎么了?你不敢啊?”
大伯惊愕地看着蒋芸,这个女人总是有能力一针见血,把最难以面对的问题抛给对方,把隐晦的那些部分赤裸裸地揭开。
“你……蒋芸,我警告你!”大伯气急败坏。
春和夹在两个针锋相对的大人之间,好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想飞却飞不起来。她连自己哭了都不知道,眼泪顺着脸颊簌簌地流下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已经不属于她自己了。
“求求你们,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大伯被这难堪的局面搅得心烦意乱,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春和。一气之下,头也不回就走了。剩下还在原地哭着的春和,蒋芸紧紧抓着春和的胳膊,满院子被行将消散的霞光所笼罩。含苞的茉莉,在一片阴影之下,显得无精打采。
已经忘了什么时候,春和的生活被隔绝出艳丽的光景外。当别人一家子开开心心地围坐在餐桌前有说有笑的时候,春和的家却冷冷清清。妈妈煮了饭,菜都端上桌子了,爸爸却还不回来。春和饿了,想动筷子,但妈妈不让。妈妈说:“等你爸爸回来再吃。”春和嘟着嘴巴,看了一眼盘子里馋人的红烧对虾,吞了吞口水。母子二人枯坐在小院子里,巷子响起脚步声的时候,蒋芸都会走到门口探出头,但那脚步声永远不可能是爸爸的。爸爸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回家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晚。开始的时候,爸爸说,工地的活很紧,可能赶不及回家吃饭。妈妈说,我们可以等。但这一等,就是暮色四合了。爸爸依旧不见身影,她们等得实在饿,就只好开饭。但往往这个时候,饭菜已经冷了。春和吃不下去,蒋芸只好将菜重新热一遍,所以当巷子里其他人家的炊烟已经熄灭的时候,春和家的烟囱还突突往外冒着烟。
春和常常会抬头望着那些丝丝缕缕飘上天的烟,它们升及半空就突然消散了,再也寻不回踪迹。巷子里的大榕树遒劲的枝桠伸到了院子里,搁置住的烟雾缠绕在树枝上,也很快就不见了。春和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望着它们,她不知道,哪一天,人的生命也会像这样一缕烟,说散就散了。
家里如此的情形,直到徐锦喝醉酒被人从外面抬回家的时候才宣告终结。春和记得那天,半夜三更的,外面有人敲门,敲门声噼里啪啦,震得整个屋子都响了起来。蒋芸被敲门声惊醒,匆匆披了衣服去开门。春和跟在母亲后面。门一打开,一股酸腐味道就扑鼻而来。徐锦醉得瘫软在地上起不来。两个抬他回来的工友厌恶地说了一句:“快给他洗个澡,臭死了!”
蒋芸惊愕地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春和拉亮了门口的电灯,这下子,徐锦的样子清晰可见。他的醉态,他涨红的脸,褴褛的衣衫,全都一目了然。好似被人瞥见了生命里最为潦倒落寞的状态,春和也亲眼目睹了爸爸的这副醉态。他被血丝充满的眼睛,焦点不知落在哪里。稀里糊涂说着断断续续的话,听起来让人面红耳赤。
“再来一次嘛,再来……”
两个工友在一旁嗤笑:“嫂子,徐锦想你啦。”蒋芸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厌恶地说:“你们不要说了,回去吧。”说完,就将二人推推搡搡给送到了院子的门外。夜色迷蒙,巷子里的大榕树被风吹动,发出呼呼的响声,四下里暗得很。春和蹲下来,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春和细细地看他,他的坚挺的鼻梁,线条凌厉的脸,薄薄的嘴唇,敞开的胸膛……这一切对春和来说都是未曾细看的,她看着躺倒在地上的男人,却已经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陌生人了。春和伸出手摸爸爸的脸,爸爸的脸很烫手。春和还是第一次这么靠近去看他,平日里,这个男人留给他的永远是一副不着痕迹的冷僻。幼时被他抱过的温存,被他疼爱过的那些稀薄的记忆,都已经消散了。出现在春和眼睛里的,永远是一个被生活套住手脚,裹夹在萎靡以及轻浮之中浪掷时光的男人。
蒋芸使了好大的气力才将徐锦拖进屋子里。关上了门,蒋芸对着这个醉醺醺的男人暗自垂泪,她已经分辨不出,这个男人是什么时候踏上这样一条路。
春和才四五岁的样子,但她已经很懂事了。看到妈妈在哭,春和便走到柜台边上,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她。“妈妈,不哭。”春和的眼睛里写满了期待,还有一种蒋芸说不出来的复杂情绪,蒋芸看着春和。她才多小啊,为什么要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里?蒋芸似乎从春和的眼神里,瞥见她此后人生的走向。就好像在一面平静的湖上,看到春和的眼睛,春和的脸。倒置的人生境况,被映照在湖面上。而这个家,恰恰就是孕育这面湖水的子宫。蒋芸伸出手,把春和搂在怀里。屋子里剩下徐锦喃喃的自语以及蒋芸低声的啜泣。
蒋芸把徐锦的衣服脱下来,卷成一团塞进了垃圾筒。蒋芸这样做的意思很明了:既然他在外面惹了一身脏,就不应该在这个家里留下任何的污秽。徐锦全身因为喝酒过敏,已经冒出了密密麻麻的红点。蒋芸把手放在他的身上,一寸一寸地抚摸。不自觉又掉泪了。他身上还留着其他女人的味道,蒋芸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不愿承认和面对的事实,终究还是以这样直截了当的方式给了她重重的一击。她从徐锦的裤兜里摸出一张拮据,上面歪歪斜斜的字触目惊心。而更加让蒋芸心寒的是,拮据的落款,清清楚楚地写着徐锦的名字。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