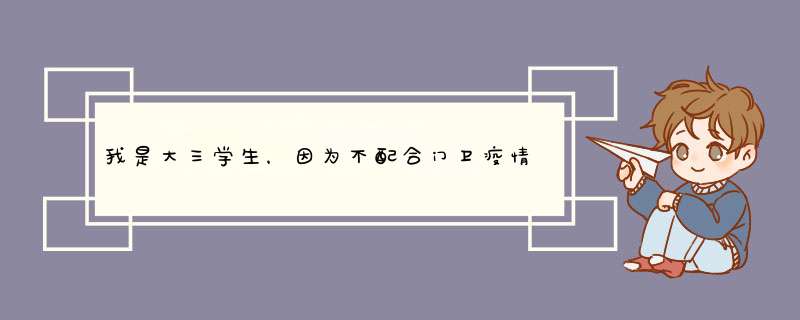
你是不对的,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就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 ,因为你是过错方 ,学校怎么处理你,你都得听着 还有一点就是学校是正当的 要求你 配合检查 ,你不应该在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跟他吵架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辅导员来了,你不应该跟他吵架 ,你要是听了辅导员的话 ,就不可能在你的档案上记过 ,只因为你是屡教不改的,所以才给你个惩罚 。
这其实是在讲辈分和尊卑关系。在字面上理解,是父亲和儿子不能同桌吃饭,叔叔和侄子不能对饮。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作为晚辈,在酒桌上就只能敬长辈。
而不能够像朋友一样,和父亲或者是叔叔没大没小,喝成一片。像一些划拳、行酒令之类的酒桌游戏,就更不能行了。
父子不同桌,这个说法很严苛,其实是出于儒家思想。当时,他们强调君臣不能同桌,父子之间也是。
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家庭中地位是最高的,所有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对父亲有一颗敬畏之心。如果是平日里的一些家庭聚餐,那么父子可以同桌吃饭。
但是如果是一些大型的场合,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外人看来,这是对父亲的一种不尊重和不礼貌。
再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代沟。父亲和儿子想的不同,如果非坐在一起吃饭,那么也聊不到一块儿去,而且还有可能因为话题而出现一些很尴尬的情况。
那么叔叔和侄子为什么不能一起喝酒呢?这是因为男人喝多了酒,就容易失去了分寸。
这两个辈分不同,如果在一起喝酒,万一要是喝多了,说了一些不合宜的话,这样双方都会显得很尴尬,而且也不敢放开了喝,会有所顾忌。与其这样,不如直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一些习惯了,现在大家都比较开明了,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父亲和儿子在一起吃饭,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叔叔和侄子一块儿喝酒,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戴志诚不仅和姜昆是金牌搭档,还是国家一级演员,《送你一支歌》、《合家欢》等作品观众都很喜爱,但是他的感情却不免让人诟病,戴志诚有过一段婚姻,早年曾和杨蕾结为夫妻。他年纪比杨蕾小一岁,出名也比杨蕾晚。成婚之时,杨蕾已经是电视上大家所熟知的小品演员,而戴志诚还是没有什么名气。而那个时候,两夫妻的感情还比较深厚。
在2004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下了台之后,杨蕾就接到了老公的一纸离婚协议书。前后22天,他们就结束了婚姻。婚姻的破裂,曾给杨蕾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她就淡出了小品的舞台,回到了山西老家。戴志诚的前妻杨蕾因此郁郁寡欢,十年间迅速苍老,脸上布满黑斑,由此可见对她的打击之大。
侯耀文的婚姻
31岁的时候,侯耀文和刘彦结婚,第二年两人的女儿就出生了,然而,在孩子刚刚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正式离婚。
三年之后,侯耀文娶了比他要小20岁的明星袁茵,袁茵是一名影视演员,曾出演过《特行警察》《使命》等。袁茵也是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的前妻,与侯耀文1993年娶亲,1998年生下女儿妞妞。五年之后,侯耀文已经48岁了,他们两个的女儿再次出生,可是,这种生活也没有维持太长时间,2004年,侯耀文再次在孩子六岁的时候离婚了。
袁茵在后来采访的时候也透露,两人分开的原因:侯耀文是一个工作狂,很少回家看望,所以,家庭中的事情,都由她一人承担,并且和他相处的过程中,的确在脾气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冲突。
不论的爱情戴志诚前妻杨蕾和袁茵是比较要好的朋友,而且,他们两家相邻,那个时候,侯耀文的前任妻子袁茵,比侯耀文小了20岁。
年龄的差异,必然让两个人生活中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而且侯耀文演出多,经常要奔赴外地。两个人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长期异地之苦,家里面经常有一些大事小情,都是戴志诚帮助解决。一来二去戴志诚就对就对袁茵产生了一种情愫,而袁茵也对戴志诚有了一种依恋。
那时候,杨蕾和戴志诚还是夫妻,戴志诚,算起来还要叫侯耀文一声师叔。
可是,最后的事情,出乎大家的意外。他们两个家庭都离婚之后,袁茵直接嫁给了戴志诚。
戴志诚和杨蕾离婚不久,侯耀文也和袁茵结束了婚姻,理由是袁茵对媒体说的,“两个人磕磕绊绊多年,缘分尽了。”后来侯耀文又找到了生命中新的伴侣。
袁茵与侯耀文离婚后,带着女儿嫁给戴志诚。
戴志诚加入侯耀文婚配的消息首先传开。本来友爱的两家首先,变得陌生乃至有了些冤仇的滋味。侯耀文首先避让和戴志诚的所与同盟。
分手后三年,侯耀文因心脏病离世。作为侯耀文门徒的郭德纲,屡次讽刺戴志诚,还编进了段子里,取笑意味非常彰着,固然戴志诚屡次否定了传闻,但这事儿曾经对他的气象导致了影响,现在的他固然还对峙说相声,奇迹却曾经是大不如前,使人感慨。
“叔侄”沟壑后来的俩情面况就非常少在公共的眼前发现,有人说他们也早已分手。详细怎样,没有材料证实。虽说夺人之妻不行宽恕,不过若真的是心有别属,相互何不放过本人。平常的分分合合谁的人生又不是呢
这一段往事之后,侯耀文和戴志诚这对“叔侄”心中都有了越不过去的沟壑,侯耀文生前再也不和戴志诚同台演出。
戴志诚对袁茵的女儿非常好,小时候妞妞开家长会运动会都是戴志诚作为家长加入,生活上也是无所不至的关怀,妞妞是韩庚的铁粉儿,戴志诚便专门带她到表演后台,让她完成和偶像合影的心愿!戴志诚对待侯耀文的女儿如同亲生一样。
戴志诚和袁茵,这样的结合方式,对二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戴志诚事业由此一蹶不振。
如今状况如今袁茵已很少出面了。不过,二人相亲相爱16年,虽遗憾无子,可是恩爱如初。
他们的这段感情,在外人看来,终究是有些不太正确。
可是,他们在一起,居然也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看似状态都非常的好。
叔父到侄子家吵架,一夜之间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套在颈部的麻绳圈及遗体姿态指向上吊自尽,遗体上诡异的伤痕却掀起层层疑云。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桩发生在明代卫所世袭军户家庭内部的人命悬案。明代的"卫所"是一种军队编制体系,兵士为世袭军户,携带家属同住,平时开荒、屯田、驻防,战时奉调出征。军士及其家人大多来自外地,且同一卫所的人口通常来源于同一地区,迁到驻屯地之后形成卫所移民"社区",内部关系十分紧密。
明朝为卫所制定赋税、抚恤、封爵、教育、祭祀等完整的配套机制,卫所不但具有军事职责,还拥有本卫辖区内的人口管理权。到了明代中后期,卫所的军事功能渐趋式微,对于辖区内军户人口的管理权依然存在。本案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成化年间,京畿某卫所军户马家的当家人是马骥,其叔父马鉴对家产分配意见很大,叔侄间多次发生争执,关系紧张,终于闹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马骥坚持不分家产给叔父,并威胁要上报本卫所,把马鉴一家遣送回原籍。马骥扬言,他在卫所有人脉,没有他摆不平的事。马鉴不服,跑到刑部告状,将马骥的上述言行原原本本地上报刑部,要求处罚马骥。
结果证明,马骥确实有手段。刑部郎中谢廉听了他的辩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下令将马鉴责打一顿——注意,打得不重。马骥说了什么?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个人推测是反咬马鉴诬陷、无理取闹之类。至于马骥的"人脉"有未发挥作用,更是无从揣测。我们只知道,谢廉打过马鉴,把马家叔侄转送到兵部,进行"联查勘问",以期厘清是非曲直。
兵部办事吏李纯负责送马氏叔侄去"后府"待审。途中,马骥再次展示他"混社会"的能力,说服李纯同意他和马鉴取保回家。获准担任保人的是同一卫所的军户,姓何,看样子和马家交情深厚。但是,此人的全名及身份出现前后矛盾的说法,是本案的未解之谜之一,留待后文再讲,暂时称之为"何某"。
李纯开立一张票帖,保人签字,马氏叔侄即告获释。正常情况下,李纯应该跟着他们一起回马家,履行看管护送的职责。可是马骥又建议李纯去保人何某家住宿,理由估计是何家住宅宽敞、马家人多拥挤什么的。李纯也答应了。何某带着李纯一走,就只剩马鉴一人与马骥相处,事态渐渐失控。而且我要提醒大家留意:从下一段文字开始、到马鉴的妻子刘氏登场为止,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都是马骥单方面的说法。
马骥主动邀请马鉴回他的住所叙谈,争取拿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避免一家人闹上公堂、给外人看笑话。马鉴同意展开对话,跟去了侄儿家。当然,他没有忘记把自己的行踪通知妻子刘氏。
然而叔侄间的沟通进行得很不愉快,到后来完全剑拔弩张。这也证明刑部打马鉴的确打得比较轻,他行动自如,头脑清醒,还有力气和侄子大吵大闹。争吵中,马骥大骂马鉴,旧话重提:"你个老不死的,我要把你发配回原籍,还要教刑部打死你!"狠话喷出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马骥称,叔父大为恐惧,身为侄子,他很快软下脸来,破天荒地留叔父在他的住所歇息。叔父马鉴接受了侄子的好(?)意,有史以来第一次留宿在侄子的住所——记住是"第一次",史料原文使用"初"字,这一点很重要,看后文就能明白。
另一边,刘氏到翌日天亮也没有等到马鉴回来,就去马骥的住所寻人。马骥答复婶婶:"我不知道叔父去了哪里呀!"马骥早起晃到别的地方去了吗?刘氏寻找半天无果,也查不到马骥离开侄子家的蛛丝马迹,心头疑窦丛生,折回马骥家,逼令他把马鉴的下落说清楚。
拖到午后,马骥实在无计可施,只好交待实情:"叔父昨晚在他的卧室自尽了!"他称,他安排马鉴独居一室,马鉴大概是把他说的气话"遣返原籍、交给刑部打死"当了真,恐慌过度,摸到一根麻绳上吊。他们天明之后才发现马骥不幸逝世。
刘氏惊闻噩耗,情绪激动,要亲眼看一看马鉴的遗体。马骥阻挠她行动,马骥的弟弟马骢出手与刘氏拉扯推搡,不让她看遗体。刘氏叫嚷起来,说她不相信马鉴会自尽,要报官查办。马骥听说她要报官,越发焦躁,跑出来阻拦。刘氏斗不过他一家子,跑回家搬救兵。于是,马鉴的儿子马贵出动,到法司指控马骥,怀疑他把马鉴骗回家实施谋杀,诈称为上吊自尽。
不过,法司采信了马骥的说法,认定马骥威逼叔父、致使叔父自尽,判决他杖责90、徒刑2年,李纯等6人因各自的不当行为处以杖责70。刘氏母子无法认同这个结论,案子上报至大理寺。
大理寺卿王槩阅览案卷,感到刘氏、马贵母子的质疑无不道理。本案主要有下列六大疑点:
第一,仵作验明马鉴的脊背、手臂遍布明显的"长、阔"伤痕。马骥一方主张那是马鉴自己不小心造成的磕擦伤,也许正是在试图上吊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于马骥的主张,法司予以采纳。
但是,在王槩的经验中,从来没有上吊自缢者会出现这种大面积外伤。换一个角度,伤痕会不会是刑部责打马鉴所致?对于该种怀疑,刑部郎中谢廉予以否认。王槩经过调查,也认可谢廉的答辩,认为马鉴之死与刑部先前的举措无关,应该是认定伤痕不匹配。
第二,马骥为什么要支开李纯、独自领马鉴回家?次日在明知马鉴已经亡故的情况下,为什么刻意隐瞒、拖延?
第三,马骥一家为什么极力阻拦刘氏察看遗体?莫非他们害怕刘氏看出破绽——那些诡异的伤痕?
第四,明朝人夜间照明不像现代人这样便利,半夜三更、黑灯瞎火,马鉴初次入住别人家,临时起意上吊,请问他是怎么在那间陌生的客室内找到麻绳的?
第五,关于保人的身份,兵部办事吏李纯的说法前后不一致。李纯起初说保人是卫所典吏何淮,票帖上也签着"何淮"的大名,后续突然改口称何淮那天恰好去通州领月粮——明代卫所军户的一种物质待遇,所以实际上由他的儿子何欢做保人,只是何欢使用父亲的名义在票帖上签字而已。
第六,马鉴忽然寻短见的动机是否充分合理?
王槩驳回原判决,指令下级法司作全面调查,解答以上疑问。然而,第二次上报的案卷及判决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搬第一次的结论。王槩再次驳回,下级第三次呈报,内容依然如故……此案最终如何了结?我尚未查到史料记载,谨在此谈一谈个人看法,文末请各位投票,选出你认为最接近真相的观点。
一、马鉴脊背、手臂上的伤痕问题。这些伤痕会不会是刑部责打马鉴造成的、而王槩存心包庇刑部郎中谢廉,践行"官官相护"?我们来看看明代的几种刑"杖":笞杖、杖、讯杖,长度均为3尺5寸,约合112厘米,算是"长"了;宽度尺寸最大者为4分5厘,约合144厘米,绝对说不上"阔"。
另外,上述刑"杖"的规定打击部位为臀、腿,而马鉴的伤痕都在脊背、手臂,位置不吻合。
并且,如前文所述,马鉴进入马骥的住所时依旧活蹦乱跳,完全没有身负重创的迹象。假如他当时已经是手臂、脊背"遍布长、阔伤痕"的状态,你相信他还能和年轻力壮的侄子马骥发生激烈的争吵吗?
所以在伤痕问题上,我倾向于赞同王槩的判断,即刑部只是做了职责范围内的事,在分寸的掌握上没有出现偏差,马鉴身上那些奇怪的伤痕并不是在刑部形成的。既然如此,伤痕的真相就只有一个——是在马鉴进入马骥住所之后形成的。
对此,马骥也不否认。但他关于伤痕形成原因的说法,不止王槩深表怀疑,我也觉得难以想象。难道马鉴上吊时没有在凳子上站稳、或者绳子断裂,他摔到地上、导致磕碰受伤,然后重新上吊成功?即便如此,仍很难解释大量"长、阔"——既长且宽的伤痕。因为在普通的家居环境下摔倒,几乎不可能造成这种形态、尺寸呈现鲜明规则性的伤痕。此类伤痕最有可能是因某种工具的击打而导致的,施暴者只能是马骥一家。你认为呢?
二、麻绳的问题。我感觉王槩的质疑也是有道理的。马鉴上吊是突发状况,在光线昏暗且不熟悉的居室里,麻绳还真不是说找就能及时找到的。你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初次去别人家做客的情景。
莫非房内本来就有麻绳放在显眼的地方、马鉴凑巧被安排住进了这间置有麻绳的卧室吗?客观地说,这种巧合不能武断地加以绝对排除。然而,如果把"诡异的伤痕"纳入参考,我不禁要把这种巧合发生的概率下调几个百分点——虽然不等于完全否定。你怎么看?
三、马鉴的自尽动机问题。个人认为马骥提出的动机站不住脚。他们叔侄"互撕"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马骥又不是第一次喷出那样的狠话,率先闹到衙司、把家丑公诸于世的还是马鉴。你说这个马鉴像是怕丢脸、怕麻烦的人吗?我看不像,似乎还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这样一个人,恐怕不会因马骥说出一句老调重弹的话就畏惧轻生。
四、马鉴留宿马骥家相关情节的真实性问题。王槩没有提出这一点,但我觉得,两个积怨已久的对头,正在恶语相向、吵得脸红脖子粗,突然180℃大转弯,瞬间冷静下来,一方挽留另一方住在自己家,对方也爽快应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有多高?我认为是极低的。
依照人之常情,当时的事态进展不外乎两种走向:1马鉴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偃旗息鼓,回家呼唤妻子刘氏、儿子马贵等人齐上阵。他们住在同一卫所社区,距离不远。或者当晚回家休息、商量好,改日再"战",未为不可。可是我们都知道,事情并未向这个方向发展。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