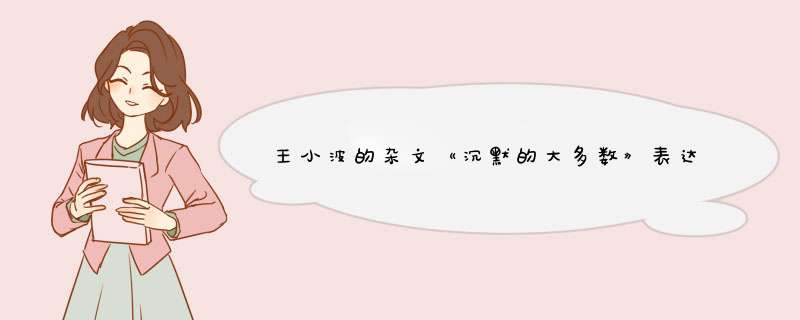
表达一个人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任何想将个人的思想凌驾于大众或迫使大众去遵从的都是不对的。沉默不等于没有主见,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他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从王小波的长盛不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还任重而道远。王小波的作品一直盛行不衰,王小波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创造出属于他的美,这美就像一束强光,刺穿了时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刚刚开始识字读书的青年的心灵。
扩展资料:
《沉默的大多数》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7月发行的图书,作者王小波。主要讲述了作者在该作品中倾注了其对中国民众命运的关注,以反讽和幽默的手法直面生活,从一个轻松的角度来解析身边复杂的事态。
相关例子:
他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后来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阅读那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
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前苏联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话;邻里之间起了纷争都不敢吵架。
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顺便说一句,前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萧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多有不便。
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其实萧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
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这使我不敢与他争辩—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
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中国当代学者、作家。代表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等。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他先后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王小波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
1984年赴美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游历了美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1988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92年9月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他的唯一一部**剧本《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节最佳编剧奖,并且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节。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5岁。2018年9月,王小波著小说《黄金时代》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沉默的大多数
读完《爱情的教育》发现爱情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力量。
爱情通常消失在结婚的那一刻。结婚后生活的压力仿佛突然袭来,房子压力,孩子教育压力。结婚前一秒父母还像个孩子一样呵护你,结婚后一秒就突然像个成人一样对待你。和伴侣很难享受想走就走的旅行,疲惫一天回家的男人依然要面对咆哮的媳妇,哇哇大哭的孩子。女人一样要面对只会刷手机的冷漠丈夫。爱情只剩下了婚姻这个空壳,就这样的婚姻却成千上万的存在着。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局面?想想当初为什么结婚?
因为人总是要结婚的,到了适婚年龄有合适对象就结婚了,没有合适的对象就要创造条件赶紧结婚。这是人生中必然要做的一件事,就像到时间要吃饭、睡觉一样。
所以重要的是完成结婚这件事情,有爱情然后结婚最好,没有爱情也可以结婚,之前有爱情结婚之后没有了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爱情已经完成了她的任务,结婚了就可以了。
所以爱情是荷尔蒙、是性欲,是可以被当做发展为亲情来歌颂的。但亲情是因为血缘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你和你爸无论多不合,他任然是你爸爸,摆脱不了。爱情却不一样,因为情侣是可以用分手来解除关系,夫妻是可以离婚的。爱情的存续一定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存在在里面。
《爱情的教育》里说了重要的一点是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
道德情感是一种价值观,比如情侣和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忠诚,在关系存续期间不应该与其他异性发生相似情感和只能是情侣夫妻才能发生的行为。比如,伴侣一方身患疾病,另一方任然不离不弃的照顾。这是一种基于道德的情感,是基础。
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级的是爱情中的审美情感。比如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王小波与李银河的爱情。钱钟书曾说和杨绛的关系是朋友、是妻子、是情人。李银河曾问自己两个找的不美的人之间能产生美好的爱情吗?后来遇到了王小波李银河认为可以。王小波也说:“每当我想起你,我的丑脸就泛起了微笑。”
经常也能听见有人说女孩以后就是要相夫教子的,不用读太多书,要读的话也最好读教师专业,然后一定要学会做家务,会照顾孩子。本身女孩做家务,读教师专业、照顾孩子这些事没有错,但她们不是生来就只适合做这些事。就好像男人也不是生来就必须是英雄男子汉不能流泪是一个道理。有很多美好的事物是人就可以追求,不外乎男女。
建立男女作为人,拥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实现彼此共同向着美好事物进发的动机,才能建立深刻的爱情。
这件事对女人尤其是如此,家庭的分工不可避免的会让女人困于厨房、家庭琐事。即便如此也不能放弃学习,不是为讨好,是为了自己和一份可能越变越好的爱情。
这个意识也同样适用男人。
你为什么总要和对象总吵架
婚姻里面没小事,能吵起来的也不会是“小事”。
其实,夫妻之间争吵的,往往都是“小事”比如答应我的事情没做到,你下班没搭理我等等争吵本来就是夫妻沟通方式之一,只是有的夫妻越吵越恩爱,有的夫妻总把分歧闹离婚。
“你今天吃枪药了啊”这句话经常能从吵架的夫妻对话听到。
他的意思就是: 本来能好好说的话,为什么你说出来那么有攻击性,火药味那么浓
不论是恋人吵架,夫妻离婚,上下级矛盾都是在沟通上出了问题一本来可以好好说的是,偏偏因为几句带着火药味的话导致剑拔督张。
只要出现了问题,双方当事人都会异口同声说:都是对方先找事的!
今天通过一些我自己的案例,来系统的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和人发生争吵 为什么我们的谈话这么容易充满火药味
一切问题的根源——因为无力感产生的愤怒
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
——王小波
这是我们一切争吵爆发的根源:
当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感,进而开启了自我防御机制,将不安全感转化为对对方的愤怒和敌意。
举个例子,妻子要求丈夫在下班回家之前把家里收拾干净,但是她回到家以后家里没有收拾干净甚至更加脏乱了。一瞬间妻子十分愤怒一本质上,是感受到了丈夫“可能”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妻子“可能”不能很好地管理他。
当我们感受到了事情的消极信息,且我们无法去改变时,我们就会产生无力感和焦虑感,但是我们自我防御机制总会为了让我们心里好受点而把这种情绪转移出去。
到底是什么话语让我们愤怒
最容易触发人的无力感和焦虑感的话语,大概分为这么几类:
定性式的评价:“你就是一条没有上进心的咸鱼”“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是经理吗”
模糊的标准:“你总是这个样子”“你一直以来都不重视我”
不恰当的类比:“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这是一个员工和老板说话的态度吗”
非黑即白的选择:“你和你的一屋子手办过日子去吧““我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错位的角色代入:“你怎么当老大的””不就是写个文章吗能有多难”“
一瞬间我们不由自主的从对方的话里解读出了这样的信息,然后我们的自我防御机制以我们都意识不到的速度开启了——因此我们的愤怒总是来得如此之快。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
即使我们的自我防御机制反应速度再快,依然有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情绪的导弹发射之前关闭系统--他们在解读阶段,避开了其他人的错误。
对方的信息进入,我们感受到威胁,自我防御机制开启,愤怒情绪产生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流程,我们还漏了重要的一环-解读处理对方的信息。
而这就是大部分人和那些看起来十分冷静的人区别——解读处理信息时,两者并不相同。
1负面的自我归因:认为对方话中的意思是对自己的攻击和否定。
2灾难化的解读信息: 认为自己遇到的情况是极其糟糕的。
3非黑即白的设置绝境: 告诉自己必须怎么做。
4责怪不可控的因素:都是别人的错,我很冤枉。
1997年4月中旬,《南方都市报》登载了一篇讣告:《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占了小小的一点版面。
此时,已经离王小波过世过了好几天了,《南方日报》才如此后知后觉,而当时的版面编辑却问写这篇文章的张晓舟:“他真的著名吗?”
是啊,王小波生前,真的算是无人问津。他自己曾经自嘲:“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的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起我身上。”
可到他死后,他的作品却从不断退稿,变成不断加印,王小波成为了出版界的神话,更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高晓松。高晓松曾经在节目中曾言:“王小波在我读过的白话文作家中绝对排第一,并且甩开第二名非常远,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王小波是可以和卡夫卡媲美的。”
但我相信,新的一代90后对于这些“捧上神坛”的论述大概是不感冒的。在90后的眼里,王小波只不过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罢了。
2003年,当年负责对接王小波的《北京文学》编辑李静写了一篇《王小波退稿记》,详细透露了王小波作品从不断退稿的过程。
李静研究生毕业之后上岗,她一直将出版优质的文学作品当做事业来做。也正是在这样的事业心驱动下,她“打着鸡血”给王小波写了封信,之后又打了通电话,询问王小波是否有作品需要出版。
王小波倒是很淡然,不紧不慢的说:“有一堆压箱底的。”
时间是1996年8月,李静第一次见到王小波。地点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李静拿到了《红拂夜奔》的稿件,她兴冲冲的上交给杂志的执行主编,没想到得到的回应是必须要改到3万字才能出版。
18万字的心血,王小波在两周的时间内吭哧吭哧改到了3万字,最后还是被认为“格调低下”,发不出去。
李静的笔下记录,王小波听到这样的消息后“咧嘴笑了起来,是感到了极大的荒诞的那种笑。”然后淡然的说了句:“没什么的。”
王小波曾写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别的猪被阉割、被安排生育,然后送上屠宰场,被规训着过着庸碌的一生。但这头猪像山羊一样敏捷,猪栏根本拦不住他,经常不见踪影。它要谈恋爱,它还学会了汽笛叫,最后一走了之,浪迹天涯。
王小波在文章的最后讲:“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这头特立独行的猪是王小波的自拟。他辞去稳定的教职(人民大学会计系)后专职写作,他和妻子结婚约定好不要孩子……种种,都与世俗不大相同。
当然,这头“特立独行的猪”显然是体会到了特立独行的“恶果”,在那个年代,王小波的作品大部分都难以出版。
《黄金时代》花了2年时间才在国内出版,但各类营销活动却无法开展。王小波和编辑就推着自行车,在路边叫卖起了自己的小说,直到死前,售价128元的《黄金时代》第一版都还没卖完。那些看似荒诞的却实足幽默、坦荡的文字,在风气未开的年代遭到冷遇,也算一种常态。
时代三部曲封面
总之,王小波的作品也只是小圈子里知道罢了。
但从不断退稿到不断加印,却只隔着一个“死亡”的距离。
1997年4月11日11点半,王小波楼下邻居听到两声非常痛苦的惨叫。第二天发现, 王小波已经故去。他死的时候头静静抵着南墙,弓着身体,墙上有几道牙齿的痕印。
那时候时代三部曲还没有印好,出版社赶制了封面,放在了王小波遗体上盖着的床单上。
而后,时代三部曲一路绿灯,再也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销量也是一升再升。
高晓松曾经在节目中曾言:“王小波在我读过的白话文作家中绝对排第一,并且甩开第二名非常远,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王小波是可以和卡夫卡媲美的。”
这样的说法存在于许多知识分子的视角当中,进入21世纪后,人们仍然是喜欢封神,喜欢给各类的文人扣上各式各样的名号。在书商和粉丝的热捧下,王小波成为一种“消费符号”,一种“上流”的、有思想的表征,仿佛谁家里没有一本王小波,谁就不是纯文化人。
这自然是王小波可能失望的事情,但实际上90后年轻人第一次听闻王小波,极有可能是他和李银河的感情故事。
“一想起你,我的丑脸就泛起微笑。”“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这些撩人的情话刻进了少男少女的青春故事当中,俗套中又流露出美好。
1977年,此时已经是《光明日报》编辑的李银河读罢王小波《绿毛水怪》,因为好奇心见了见王小波。
而此时王小波只是一个街道扫地工人,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李银河后来说:“没想到这么丑,不如不见。”
没想到第二次见面,王小波就主动找上门问李银河有没有男朋友,问他看看自己行不行。李银河嫌弃他丑,王小波说:“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我是觉得,现在这么跟姑娘说话的,可能要被扣上钢铁直男的帽子,可就是在3年后,两位情侣结婚了,而后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婚姻生活。
后来他们的情话,流遍了大学的校园中。
我真的不知怎么才能和你亲近起来,你好像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目标,我捉摸不透,追也追不上,就坐下哭了起来。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了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你肯用这样的爱情回报我吗?就是你高兴我也高兴,你难过时我来安慰你,还有别爱别人!……
以至于,不少姑娘的择偶标准一下子从韩剧里的长腿欧巴,变成了王小波那样“有趣的灵魂”。大学的图书馆里,王小波的书开始不断被借阅,长得和王小波一样丑的男孩儿们倒是希望从这位“撩妹高手”的故事里学上几招。
这个类似“屌丝追女神”的传奇故事,往往比起那一个个吓人的头衔,更显的有人情味。王小波以“撩妹高手”的全新标签,走进了新的一代人的视野当中。
人们向往这般爱情,而后去了解王小波,最后自封为“王小波门下走狗”。
于是乎,王小波被人们解构,人们像看待一个朋友一样看待王小波,从“神一样的存在”到“有趣的灵魂”,人们解构王小波,之后解构自己,也算是这个时代的人情味。
王小波这般通脱的人,若是在天看到他在今天人们的视野里是这样一个角色,大抵会高兴吧?
王小波活的通脱,算是淡泊名利之人。假如没有大红大紫,他亦不太可能像太宰治那般抑郁自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我大胆的猜猜,大约王小波对自己的短暂的人生,算是满足了吧。
当他的妻子李银河被问到,如果见到王小波,想问他一个什么问题?李银河说:“我想问小波: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王小波已逝,谁都回答不了李银河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能和这个有趣的灵魂进行沟通。人总说看书等于交朋友,看王小波的书,差不多也算和王小波交了朋友,也是我们目前和这个有趣的灵魂沟通的唯一方式。
有些朋友觉得时代三部曲读来甚是晦涩,由于其特殊的写法,不少人难免有时间的错乱之感。但王小波的杂文集还是非常好读的,也收录了他许多的“奇思妙想”。王小波自己都说“我以写小说为主业,但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
浪漫啊,但是感觉有点腻啊。
现在发一些互动话题或情感类的微博大佬们会向网友征集或自己总结了一些最动听的情话,“你好啊,李银河”常在榜列。这话出自王小波和李银河的信的集问《爱你就像爱生命》。
目前王小波的书只从头到尾看完的只有两本,一本是杂文集,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本小说叫《黄金时代》。我是先看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再看的《黄金时代》,当初之所以会买那本杂文集,就是被他的书名给吸引了,外加当时我的外号就是猪,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但是买回来后发现书的纸质太差,就随便翻了翻,就丢在一边了,好久都没看。有一天闲着没事随手拿起了一旁的那本杂文集,哇~~~太好看了!好有意思哦,文笔诙谐幽默风趣,特别喜欢看他嘲讽生活的样子。
后来就去百度了他的相关资料,发现他自己最为满意的一部作品叫《黄金时代》,于是趁热打铁找来来看了,真的很好看,竟然把黑暗的文革写得这么清新自然好诗意。看完真的觉得很满足,于是又想再看第三本,想看看他是怎么写情书的,于是就看了《爱你就像爱生命》,但是。。。。。。我看了开头一点点,我就看不下去了。。。。。。实在太肉麻。
虽然只看了一点点,但我还去查找了关于他们两个人的故事,我发现,他们的感情真的很纯粹,当时王小波只是工厂里爱写字的工人,而李银河却是个博士,但他们还是相爱了。李银河可以用自己的奖学金支持王小波进行文学创作不受干扰,光是这两点,就给了当下给爱情明码标价的人两记响亮的耳光。
也许会有人因为李银河新的爱情而质疑她和王小波的感情并没有书里描写的那么炙热。但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码事,作为看客的我们常常喜欢用苛刻的目光要求当事人,如果你那么爱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上别人?但生活总要过下去啊,有些人既然不在了,就应该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活,为什么要抓着别人的过去不放?他们的爱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真挚,所以才会有人念念不忘。
我他们的爱情是精神主义的,普通人很难做到。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特立独行的人吧。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