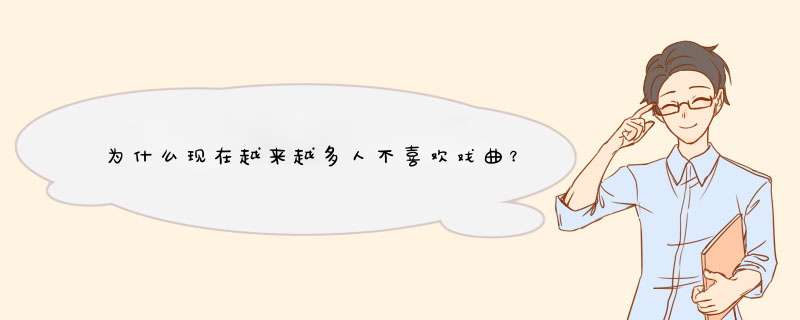
曾经被誉为国粹的京剧已经走在了艺术的边缘,很多地方戏曲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越来越多人不喜欢戏曲是因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人类的兴趣爱好已经因为社会改变发生了变化,戏曲仍然是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里面仍然是古老的东西,不是说古老的事物不好,只是不再适应这个时代发展,不再适合观众欣赏的口味,不再能满足大众对于文化艺术追求,这个时代主题就是变化,大家更喜欢新鲜事物,曾经辉煌的戏曲已经跌下神坛。
现在不仅仅是戏曲遇到了无人问津的困境,很多传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失传的问题。社会发展进入了快速车道,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新鲜事物,他们不喜欢一成不变的事物,更不喜欢陈旧古老的事故,很多的传统文化没有做出本质性的改变,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传统文化也要随着大众欣赏方向改变做出针对性的创新,文化最终服务对象是人,如果一直原地踏步最终会被社会淘汰。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戏曲,他们听不懂戏曲,他们无法理解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经典内涵。她们更加喜欢流行音乐,他们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人,现在想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在市场上改变传统文化才能让他们适应年轻人的文化需求,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绝对不能让经典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失传。在戏曲当中要不注入新鲜血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做出更多的创新。
近期,年代剧《鬓边不是海棠红》催热了不少话题。剧中涉及的20多出京剧、五六出昆曲、旦角八九个流派和戏曲发展史,让老戏迷们津津乐道。还原时代的置景与服化道也深入人心。华丽的戏服、典雅的旗袍、时髦的洋装,均精致细腻,十分养眼。还有京绣、苏绣等国家“非遗”的亮相,将传统文化的神采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视剧在服化道上的细节把握,直接影响作品的质感。“仅妆容一道工序,就能鉴别出作品是否具备品质剧、精品剧的基础。”上海戏剧学院李芽副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化妆史的研究,“妆容展现的不仅是对人物角色的理解,更是对文化历史的认知。古装剧、年代剧无疑是展示文化的最好平台,但对这些类型的妆容研究与设计,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虽然古代妆容研究比较“冷门”,但中华传统文化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就像一座宝矿,可以挖掘的历史素材数不胜数。正如学者们所言,“顺时制物,内外兼顾”的国妆精髓,充满了中国人的哲学与智慧,有着独特的造物理念。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没时间观看戏曲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喜欢戏曲,导致了戏曲文化的衰落。戏剧的衰落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方面在于自身,另一方面在于社会。
戏剧是一种高雅的舞台艺术,综合了音乐、舞蹈、文学、绘画、服装、武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一般人欣赏不了。“其曲弥高,其和欲寡”,舞台上是阳春白雪,舞台下或者舞台外多是一些下里巴人,它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注定了不能形成共鸣。阳春白雪没变,下里巴人越来越多,导致了戏曲只能够少数人看得懂、听得明白、欣赏的了。票友越来越少,所以戏曲文化越来越没落。
这是一个快餐化消费时代,人们越来越浮躁,别说是看两个小时的戏曲,就是五分钟的视频都看不下去。人们的定力越来越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静不下心来。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多的是寻欢作乐的人,年轻人更喜欢去酒吧、KTV、游乐场所玩耍,除了老年人之外,谁还会看戏曲呢?年轻人天天听的都是流行歌曲,谁要是听戏曲,肯定会被人当成奇葩来看待。
由此可知,当代人娱乐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了戏曲的衰落。人们更喜欢去那些轻松、潇洒、快乐的地方放纵自己,更喜欢听流行的、通俗的音乐,这些选择成为了主流,戏曲反而越来越小众化,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一点,戏剧缺乏创新,唱来唱去好听的还是那几十个剧目,早已听腻了。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新剧目加入的话,戏剧早晚有灭亡的一天。更严重的事实表明,优秀的剧作家越来越少了,学唱戏的孩子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戏曲只会越来越衰落,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了。
民国时期是戏曲艺术的黄金时代,四大名旦掀起了戏曲的一个又一个高潮。建国之后尚可,文革时期只有样板戏流行全国。改革开放之后,戏曲再度焕发了青春。新千年之后,戏剧就一落千丈,再也起不来了,令人唏嘘不已。
戏剧的没落从侧面反映了民众文化的衰落,反映了民众审美的衰落。真正展现一个国家魅力的地方,还是文化艺术,尤其是京剧、昆曲……
汕头市。
由汕头市委宣传部、汕头市侨务局联合主办,汕头融媒集团、广东潮剧院和汕头文化艺术学校承办的“四海潮音·全球潮剧票友汇”戏曲综艺晚会13日晚在汕头电视台首播。
活动中,汕头融媒集团投入精锐的策划、精良的制作团队,大胆创新,力求每个节目的设计、编创都有新意亮点,多层面、多角度向受众全面展现潮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西周时期,羌族不断被华夏文化所同化,最后加入到汉族的行列。东汉二二百多年,这种趋势尤其增加。当时很多 华夏人民都出身于羌族,例如姜太公就是羌族部落出身。由于羌民剽悍,统治者对于羌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更是 加剧了这种趋势。不能加入汉族的羌民则被迫流落至四方以及今天泰国和西藏一带,成为今日泰国的主要居民。
到达西藏的羌民则成为后来唐代的吐蕃,后来又演化为今天的藏民族。陕西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各种民族都在不断的冲突中磨合,滚雪球,造就了今日汉民族大家庭。陕西人民自古以来就能歌善舞,战国时期,赵王与秦王黾池之会,吝相如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为乐,”也就是用筷子敲击瓦罐,而这个瓦罐就是后世秦腔乐器的原型,以竹棒敲击发音,今天叫做“打板”,是今日秦腔戏剧最常见的打击乐器。
秦腔在古代是梆子戏的一种,由于关中为八朝首都的关系,秦腔也就成为各种地方戏剧之源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唱戏像吵架”也反映了秦人性格豪放不羁的一方面。秦腔表演艺术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用载歌载舞来形容。即使是简单的走场子(表现走路),也不会只是垂着两手转圈,而是边走边手舞足蹈,可以称之为载歌载舞。由于关中人疾恶如仇的性格,所以反映正义战胜邪恶内容的曲目尤其受到欢迎,成为具有永恒价值的保留节目,常演不衰,例如周仁回府、劈山救母、血泪仇等。
唱段句末拖很长的甩腔,是秦腔的又一个特点。在甩的过程中,还可以应用假声,从而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
在陕西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唱上几句秦腔,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反映初民的喜怒哀乐的艺术,也反映了关中人源于少数民族心理感情的民俗风情。
《锁麟囊》这出戏是程派的代表作。1940年由剧作家翁偶虹应程砚秋之约而作的京剧剧本,故事题材取自《剧说》。该剧1940年5月首演于上海黄金戏院。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某年六月十八,登州薛姥的女儿薛湘灵和赵禄寒的女儿赵守贞同时出嫁。嫁前薛姥按照当地俗习送女一个锁麟囊,而赵禄寒却只有借钱请来乐手。薛湘灵性情骄纵,左挑右选总不满意,薛姥为平息女儿,只得在囊中装满珠宝。薛湘灵出嫁中途遇雨,在春秋亭暂避,恰巧遇到贫女赵守贞。贫富相遇,赵守贞触景生情,因感怀身世凄凉而不禁啼哭。薛湘灵派仆人梅香询问,得知实情后颇为同情,慨然隔帘以锁麟囊相赠,雨止各去。六年后登州大水,湘灵与家人失散,漂流到莱州,应募在卢胜家照看孩子。一日,湘灵伴卢子在花园游戏,偶至一小楼上发现锁麟囊,不觉感泣。卢夫人即赵守贞,见情盘问,才知湘灵即当年赠囊之人,于是设宴礼敬,并助其一家重圆。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山东,是一个典型的施恩与知报的中国传统故事。开始最先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薛府上下乱作一团的仆人们,他们为了薛湘灵的嫁妆而人仰马翻,薛湘灵的撒娇使性使得全府上下忙个不停。她骄妗得唱道:
怕流水年华春去渺,一样心情别样娇。
不是我无故寻烦恼,如意珠儿手未操,啊,手未操。
仔细观瞧,仔细选挑,锁麟囊上彩云飘。
是麒麟为何生双角好似青牛与野飑。
是何人将囊来买到,速唤薛良再去一遭。
由此可见,薛湘灵当时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富贵之家。如意珠儿手未操,连自己都从来没有动过手。还有她对锁麟囊的挑剔,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而她只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简短地露了一个面,也许她知道自己的故事并不始于这里,而是始于那场婚礼。
于是她留下一句“怕流水年华春去渺,一样心情别样娇”便在全府人焦头烂额的辅垫下羞答答的轰轰烈烈的出嫁了。
出嫁的半路上却遇大雨,不过薛湘灵的心情倒没受什么影响。但就在此时,隔轿传来的啼哭声引起了她的注意。隔轿的女子叫赵守贞,父亲叫赵禄寒,他的名字和命运出奇的相似——企图蟾宫折桂而屡遭挫败,以致赤贫如洗。或许是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给女儿起名赵守贞,从此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改变命运而仅仅寄托在女儿可以安贫守志上。在女儿出嫁的前一天,他出门借钱未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倒不是人情冷漠,而是一帮亲朋好友谁也不比谁富多少——一个连女儿的嫁妆都要靠借的男人,又能交到什么达官贵人呢?女儿的回答倒是很通情达理,但是又透出极端绝望后的无奈:“父亲借钱不来,难道女儿明日就不登花轿了吗?”关于贫寒,或许她已经真的习惯了。这样的家境,注定赵守贞出嫁之时也是寒酸悲怆。
偏偏在出嫁的时候遇上了大雨,又偏偏和薛湘灵同在春秋亭避雨。不知道这场雨是冲赵守贞还是冲薛湘灵而来。对于薛湘灵来说,出嫁遇雨也没有什么,不会在她富贵耀眼的气势上留下任何灰色。而对于赵守贞来说,命运似乎无情到了让人觉得刻意的地步。似乎这场雨是对她出嫁的无情嘲讽。在那个以春秋命名的小亭子里,她和薛湘灵不期而遇。贫富相见,触景生情,不由得赵守贞不落泪。从本质上讲,这两个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的花样年华,同样的青春容貌,又在同一天出嫁。
论智慧论姿色赵守贞都未必会输给薛湘灵。但是当一个人因为贫寒而极度尴尬的时候正巧遇见另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未必强过自己但却偏偏比自己富有很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刺激。于是在薛湘灵华丽的轿子和百万的妆奁前,赵守贞没能做到像她的名字那样安于贫困,一场大雨就让她又一次深刻地体会了自己的寒酸。毕竟让一个人闭着眼睛守住贫寒容易,而让她在荣华富贵面前依然安贫乐道却是一件难事。
就像我们常常提起的执著和忠贞,想考验谁的执着和忠贞就把他带到诱惑的面前,看看他的反应吧。当一个人走投无路,死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时,实在算不上执著,因为没有选择,没有引诱,就没有资格用执著忠贞去粉饰和装潢自己,真正的执著在于面前有无数条路的引诱时,依然心无旁骛地固守着一条,这样的做法我们不忍鼓励,却又不得不钦佩。
轿子里的薛湘灵听到哭声,心中不由起疑心: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隔帘只见一花轿,想必是新婚渡鹊桥。
吉日良辰当欢笑,为什么鲛珠化泪抛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
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轿内的人儿弹别调,必有隐情在心潮。
同样是花样年华,同样是吉日良辰。她不懂隔轿的女孩为什么哭得这么可怜。
薛湘灵作为一个富家之女,却怀有普渡众生之心。一句“世上何尝尽富豪”就可以说明她时刻关心着穷苦的人们。
派人询问,丫环梅香说:**,咱们避咱们的雨,他们避他们的雨,雨过天晴,各自散去,您管他们干什么啊?这就是仆人的心胸狭窄之处。薛湘灵一听之下责骂了梅香,这是薛湘灵这个女人可爱的地方,撑得起奢华的铺张,却又不失对底层人民的关心,也许这也正是真正的贵族——奢华是一种对生活的要求,而不是用来炫耀的。
轿子里的薛湘灵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此时却又明白了,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哭嚎啕”,也许正是因为这句话,在日后改变了她的命运。因为她把一场雨中无意的相逢当成了一种怜贫济困的责任,而没有像梅香那样冷漠骄傲。她批评梅香的这种思想:
梅香说话好颠倒,蠢才只会乱解嘲。
怜贫济困是人道,哪有个袖手旁观在壁上瞧!
蠢才问话太潦草,难免怀疑在心梢。
你不该人前逞骄傲,不该费词又滔滔,
休要噪,且站了,薛良与我去问一遭。
同时,她又对赵守贞啼哭的原因作了一番猜测:
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同遇人为什么这样陶嚎
莫不是夫郎丑难谐女貌,莫不是强婚配鸦占鸾巢。
叫梅香你把那好言相告,问那厢因何故痛哭无聊
她在想,这位女孩莫不是被家人强婚配,又嫁给一个“丑夫郎”?可见当时婚姻自主的观念也成主流。试问,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呢?
这也正是**之所以被称为“**”,与丫环之所以被称成“丫环”的真正原因。轿子里的薛湘灵把身边唯一能够拿到的嫁妆——那件据说能保佑她早降麟儿的锁麟囊连同里面的各式珠宝都送给了赵守贞。薛湘灵是让人感动的,因为她对人生中的任何一次相逢都投注了情感,没有欺骗,没有冷漠,也没有嘲讽。这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最本义体现。
后来她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唱道:
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霎时间日色淡似坠西山。
在轿内只觉得天昏地暗,
耳听得风声断,雨生喧,雷声乱,
乐声阑珊,人生呐喊,都道说是大雨倾天。
那花轿必定是因陋就简,隔帘儿我也曾侧目偷观。
虽然是古青庐以朴为俭,那有这短花帘,旧花幔,参差流苏,残破不全。
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
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
于归日理应当喜形于面,为什么悲切切哭得可怜?
那时间奴妆奁不下百万,怎奈我在轿中赤手空拳。
急切里想起了锁麟囊一件,囊虽小却能做续命泉源。
她在得知赵守贞大哭的原因后,突然顿悟:
听薛良一语来相告,满腹骄矜顿雪消。人情冷暖非天造,何不移动半分毫。
我正富足她正少,她为饥寒我为娇。分我一枝珊瑚宝,安她半世凤凰巢。
忙把梅香低声叫,莫把姓名信口晓。
这都是神话凭空造,自把珠玉夸富豪。
麟儿哪有神送到。积德才生玉树苗。小小囊儿何足道,救她饥渴胜琼瑶。
她认为富贵并不由天,谁也不是一出生就富贵或贫穷的。所以说,帮助他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锁麟囊是一件宝物,有后来薛湘灵的唱词为证:
有金珠和珍宝光华灿烂,红珊瑚碧翡翠样样俱全,
还有那夜明珠粒粒成串,还有那赤金链,紫英簪,
白玉环,双风錾,八宝钗钏,一个个宝孕光含。
这囊儿虽非是千古罕见,换衣食也够她生活几年。
对于薛湘灵来说,这件宝物并不会带来什么麟儿。这件东西在她的手里也许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和美好祝福,对于她的百万嫁妆来说不值一提。然而,锁麟囊对于赵守贞来说,却是救命源泉。
生活中我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相逢,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遇到一个像薛湘灵那样的人,她在付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回报,只希望遇到的人会珍惜,会真诚,但往往我们碰到的人之所以会来到我们身边只是为了躲避一场突然而来的大雨,然后就会像梅香说的那样,“雨过天晴,各自散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忘记曾经在一场大雨中和我们相逢,忘记了自己避雨时的狼狈,甚至渐渐地,连那场大雨也忘记了。
于是心里就突然响起薛湘灵那段西皮二六: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这就是薛湘灵幸福的前半生,在此时此刻,她根本不会想到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但世事难料,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使她彻底明白人世无常。
傅谨
来源:《戏剧文学》(长春)2006年6期第10~14页
戏剧舞台并不是永远喧闹,如果说我们经历了世纪初几年戏剧界内涵各异的种种火热景象,那么,2005年中国戏剧舞台相对于前几年,确实显得比较沉寂。但这样的相对沉寂无需担忧,经历了多年不无泡沫的虚张声势之后,有一段时间让戏剧家们冷静下来思考中国戏剧的现状与走向,对未来的戏剧健康发展或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处。
相对沉寂的2005年,戏剧自有其亮点,回顾本年度戏剧发展,戏剧批评的繁荣与效用是值得特别反省的方面。21世纪初以来,戏剧批评在戏剧界成为为数不多的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人们关注戏剧批评的方式非常之特殊,它的主要体现方式,是业内外人士对戏剧批评未能起到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从而感到强烈地不满。戏剧批评比起以往更多地成为戏剧领域的反面角色,有关戏剧批评“失语”和庸俗的人情批评甚至对“红包批评”泛滥的抱怨,不仅成为有关学术会议的主题,经常出自关注戏剧发展、为戏剧的不景气现状忧心的人们口中,甚至也可以从戏剧界的编导、演员等创作人士那里听到,并且频繁见诸媒体。
作为职业从事戏剧研究与评论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对来自戏剧界内外的这些不满与抱怨既认同又不无保留。我觉得戏剧批评界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这个群体远远未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与艺术责任,对于戏剧界许多值得肯定的现象或必须指出的错误,确实都未能及时、有力地向世人揭示,戏剧批评现实的功能与正常的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健康发展所应该起到的作用相去甚远,因此,戏剧批评界无疑应该勇敢地承认自身的失职。但是如果从更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在戏剧批评领域,最关键与核心的问题恐怕不在于批评家们的“失语”。关键既不在批评家的集体懈怠,也不在于这个群体的堕落,真正的问题,或者说真正值得忧虑的现象,在于诸多批评在戏剧界经常处于被“消音”的状态。因此,与其埋怨和责备批评的不如人意,我们还不如调转目光,更多地去质疑戏剧批评在整个戏剧领域何以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未能尽到应尽的职责。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戏剧界的整体气氛和整个文艺界一样产生了不小的变化。诸多变化中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就是批评重新开始并渐渐地恢复其活跃景象。当然,无论是在哪个艺术门类,当我们在说批评渐渐趋于活跃时,很清楚就其活跃程度而言,还远远称不上“繁荣”这样的程度,在日渐活跃的批评中,不可否认地确实存在相当数量受人请托(包括收受财物)而写的一味吹捧的“伪批评”,也确实存在一些动机或文风不够健康、用眩人耳目的夸张语调刻意渲染某些流行现象以哗众取宠的所谓“酷评”,但是仍然可以看到,至少是在最近的数年里,戏剧理论界对于诸多业内外人士诟病的不良习气,始终在不懈地坚持展开立场坚定、观点鲜明的批评,批评家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
只要对戏剧批评家们的写作略加注意就不难看到,戏剧理论界一直在批评那些过度倚赖于舞台华丽的外在包装的技术主义或曰形式主义倾向,一方面呼唤戏剧精神内涵的回归,一方面也从不隐晦地指出某些所谓“前卫导演”的“创新”之空洞无物,因为这样的创作忽略了舞台艺术中最核心的表演以及人文价值;戏剧理论界一直在批评新创作剧目片面地追求豪华大制作的不良风气,尤其是由于这些剧目的大制作完全是为一时的排场而糟践公帑,在戏剧已经极不景气的当下却将国家划拨的大量经费用于只为一时获奖而非为公众经常性的艺术欣赏所需编排的剧目,忽视了普通百姓对戏剧的巨大需求。因为在戏剧最需要国家扶持的时刻它却将有限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少数人(尤其是越来越无节制地掌握了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与部门首脑)换取自己“政绩”的手段;戏剧理论界更在不间断地呼吁和强调要十分注重民族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对那些只学了点西方戏剧的皮毛就把中国传统戏剧贬损得一无是处,借助庸俗化的流行艺术手法以掩饰对于传统的无知的风潮痛加针砭。不仅因为我们的戏剧要有深度和文化内涵就必须尊重民族传统,而且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然延续更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当然,对于少数几位导演过度垄断当下的新剧目创作带来的各种弊端,戏剧理论界也都有直言不讳的、非常之坦诚与尖锐的批评。即使是对于那些往往是由官方主办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种各样泛滥成灾的评奖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戏剧理论界也从来不缺乏批评的声音。
现在,恐怕任何人都不能轻率地、随意地说当代戏剧界缺少批评的声音。对戏剧界上述种种直接影响着戏剧健康发展的趋势,理论界与批评家的态度十分鲜明,而且,批评的言辞也越来越趋尖锐。只要随便翻检近年与戏剧相关的报刊,尤其是那些专业的戏剧类杂志,都可以很方便地看到这样的批评。而无论是林兆华、孟京辉、李六乙等当红的话剧导演,还是曹其敬、陈薪伊等因经常担任多剧种新剧目创作的知名导演,都不会对各种各样经常是很坦率、很激烈的负面评论感到陌生;而对于新创作的剧本的文学性的剖析,以及对某些有影响的演员在表演上的得失,同样并不鲜见。而且,对于有关戏剧舞台上的创作泡沫的尖锐批评,非常集中地针对着那些国家级大剧团的创作,或许这些重要剧团的名称很少在批评文章中直接出现,但是业内人士只要对这些剧团略有了解,都不会误会批评的对象。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越是小剧团、越是地方性剧团就越是很少因其创作与演出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而遭到理论家严厉批评;同样,如果说某些导演和剧作家、演员的作品的缺点很少被批评家们指名道姓地提及,那么往往是由于他们在艺术上并不重要,因而才被理论界与批评家们所忽视。
当然,我并不想否认,在戏剧理论界,这样的批评至少从数量上看确实算不上主流,它们可能很容易被大量庸俗的“人情批评”淹没;而且这些批评里,也还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缺乏足够的理性分析的情绪化与即兴的牢骚,其理论价值与说服力之参差不齐也是事实。戏剧批评家们不够努力无需讳言,但我们仍然可以并且应该承认,当戏剧领域出现了各种弊端以及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时,戏剧理论界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缺席”与“失语”。批评的声音确实存在而且经常存在,武断地说戏剧批评在戏剧界众多不良现象面前“缺席”或“失语”,既不客观也不公平,更应该警惕的倒是上述诸多批评经常处于被“消音”的状态。我们所能够听到的这些批评,并没有在戏剧界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当人们抱怨“没有批评”时,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在说批评不存在,而是说在戏剧界,批评根本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戏剧批评对于戏剧创作与演出以及戏剧行业的健康发展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在一个健康的戏剧环境里,批评应该而且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指类似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足以致一部作品甚至致艺术家于死地那种判决书式的功能,而是指因为它是由一批职业从事戏剧艺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的专业见解,所以能够基于更客观冷静的视角给作品以解读和评价,以帮助观众欣赏作品以及判断作品的优劣;同时这样的批评有专业人士的职业素养为背景,因此有可能基于更开阔和更长远的宏观视野对戏剧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做出更有利于艺术健康发展的判断,帮助国家相关部门做出艺术领域的决策,因而能够为艺术发展提供重要导向,最终对艺术家的创作也足以产生不可或缺的积极帮助。
也正因为此,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对戏剧批评而言,它的繁荣与否就不能止步于有没有批评这样的事实判断,更重要的是还要看这些批评是否实现了它们的功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当下的戏剧批评才确实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批评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关键在于戏剧理论界对种种不良现象提出的哪怕是很尖锐的批评,事实上也很少起到实际的矫正时弊的作用,批评并不能真正实现它作为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一重要功能——真正悲哀的并不是没有批评,而是批评虽然发出了它的声音,这些声音却好像在真空中一样难以得到有效的传播——这种现象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批评的作用被畸形放大的现象一样不正常。
批评失效导致艺术领域的种种歪风邪气得不到及时纠正,健康良好的艺术氛围难以形成。由于批评丧失了应有的效用,当我们面对那些必须提出严肃批评或者原本只需要通过批评的方法解决的不良倾向和错误行为时,经常不得不动用刚性的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府与艺术家之间的紧张感;同时却不能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观众健康的审美趣味,以此营造一个能够有效阻滞劣作出笼、有利于佳作问世的社会氛围,推动艺术自然而然地健康发展。而戏剧界的诸多不良风气不仅不会因批评而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甚,长此以往,其后果之堪忧自是不言而喻。
批评失效的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所谓批评失效,一方面是指理论界的批评声音不能通过某些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有效地传递给公众以影响公众的审美趣味与判断,另一方面指的是专家的见解不能有效地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而如果要深入探究,当然也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讨论的,就是艺术理论界的声音如何才能有效地传递给公众。现代社会为专业人士面向公众的思想传播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因为现代社会的发育与大众传媒的发育不仅同步而且高度相关。但是它的前提是大众媒体要具有足够的公共性。这里指的是,现代社会环境里正常的大众传媒,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在这里,除了普通公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外,各行各业的专家更被优先提供了表达自己专业见解的机会,当艺术领域的专家的见解通过公共媒体传递给尽可能多的大众时,它对艺术、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也就同步放大了;专家的专业见解以及批评借此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批评的功能才能够得以充分实现。
然而,假如媒体失去了这种公共性,它一旦成为媒体的编辑记者们卡拉OK式的自弹自唱,它就由一个为公众提供资讯服务的公共平台成为媒体从业人员自己的发声筒,它的声音与立场,必然受制于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的视野与水平;更不用说,还会因为媒体从业人员对表达渠道的直接控制形成实际上的传播垄断,因而为传媒领域滋生各种腐败现象提供便利条件。因而,媒体的公共性是保证艺术领域的舆论监督充分实现其功能的重要前提。可惜,近年里,为数不少的面向大众的报刊以及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呈现出明显的非公共化趋向,它们因为有意无意地放弃公共性而沦为少数媒体从业人员私人空间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弊端也因之显露无遗。多年来,我们从大众传媒的戏剧类新闻报道与评论版上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的,不是专家的见解与独立的评论,而是大量的由创作者提供给媒体的宣传稿和他们自我宣传的言论,或者媒体人自己的看法,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且不说我们无法期望由创作者自行提供的宣传稿和广告式自我推介具有起码的客观与独立性,媒体人员的立场与见解的可靠性也很难保证——虽然不能说所有媒体从业人员都不具备艺术上的专业眼光与水准,但是要求一个长期从事面向大众的报刊采编工作的编辑记者像戏剧专业研究者那样长期、深入、细致地思考与研究戏剧,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有深度的见解,那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可以想见,这样的媒体并不能替代批评,并不能起到公正客观的戏剧批评所应起的作用,因为它既不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平也没有起码的独立性。
大众媒体不注重或者不愿意为研究者和专家提供表达渠道,并不意味着专家们无从表达自己的见解,无论是戏剧还是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都可以在专业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但是如果专业人士的观点不能通过大众媒体充分提供给普通民众,如果专家只能在专业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它干预社会的能力显然就会极度萎缩。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形,正是由于在大众传媒范围内,戏剧界的专家向公众提供专业见解的路径被严重堵塞,才导致整个批评对艺术家的影响力被严重挤压在一个远离公众的狭小空间里,公众所获得的信息是仅仅局限于经由媒体筛选过的那一小部分内容,而在这样的筛选中,专家的意见恰恰是遭到屏蔽的最重要的一种声音。即使在专家们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时,这些见解也经常被大众传媒波普化甚至歪曲,因而,也就必然直接影响到戏剧批评对戏剧创作与演出中种种弊端的矫正功能的实现。
其次需要讨论的,是专业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如何才能对政府的戏剧政策产生积极影响。应该说,戏剧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一直与政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将它与相关的邻近行业相比,无论是与美术、音乐、舞蹈比,还是与影视比,更不用说与文学比,在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方面,戏剧都体现出某种特殊性,而这种特殊关系,一定程度上缘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剧在文化部门的机构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尽管当时的政府架构深受前苏联影响,但是在文化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并没有照搬苏联将**放在至高无上的重要位置的模式,反而为戏剧和戏曲设置了专门的“戏曲改进局”,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佐证。诚然,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环境里,政府的决策与戏剧创作与演出之间的相关程度是很有限的,戏剧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特殊的艺术语境——这是由于戏剧已经越来越沦为一个处于市场化边缘的艺术门类,随着市场的萎缩,全行业对财政资助的依赖程度急剧提升。2001年全国文化部门所属文艺表演团体经费自给率首次下降到30%以内,而到2003年,每场演出平均所获得的国家补贴已经突破7000元,而在1995年这个数字是2100元,在1985年这个数字是200元。在戏剧表演团体对国家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升高的背景下,政府的文化与戏剧政策对剧团、对整个戏剧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力也同时在急剧膨胀。
政府以及公共财政对戏剧影响力的提升,本该同时使得戏剧批评对创作与演出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政府之所以能高效有序地治理社会,其秘密在于政府的决策过程,尤其是涉及到公共资源配置时,可以高度依赖因社会分工日臻细密而在各领域内出现的术有专攻的专家。当然这里所说的依赖,并不是指政府将决策与资源配置的权力完全托付给专业人员,而是指政府在考虑决策与资源配置时,会在相当程度上综合专家群体的分析与研究的结果,通过对众多专家不同意见的权衡,更深刻地理解一项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对它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也能够有比较清晰地预见;可以使得公共资源因合理配置而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
但是也正因为此,如同媒体一样,当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只相信自己的见解与判断而忽视了相关领域内专家的作用,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更趋向于按照官员们的个人意志行事时,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虽然我们的社会从整体上看似乎正在向更具现代色彩的方向演变,但是相反的趋势同样存在,那就是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教育以及其他公共事务领域,行政主导的趋向不仅没有减退的迹象,相反却在渐渐增大。而且,这里所说的“行政主导”,更应该读成是“行政长官主导”,行政长官的个人见解与好恶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影响力日渐显著,这里所说的决策权当然也包括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力。而当政府官员有过多的权力和过多的机会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按照个人方式做出决断以及分配公共资源时,我们当然很难期待政府会自觉主动地将这种决策权让渡给另一个专业人士群体。
在政府决策对戏剧的导向作用日益增大,公共财政对戏剧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具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从事戏剧研究的专家们的意见与作用没有得到决策者应有的重视,显然会更进一步导致专家的意见与批评的价值在艺术领域被边缘化,而直接从事戏剧创作与表演的艺术家们之无视理论和批评家的存在,更是必然的结果。坦率地说,政府在戏剧领域决策与资源配置方面相对仍比较封闭,这已经成为批评失效的直接原因之一。
客观、公正、坦诚而具备专业水准的戏剧批评对戏剧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但现实是我们既然希望鼓励与推动戏剧批评走向繁荣,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就是要为戏剧批评充分发挥其作用营造一个更良好的环境。这样的良好环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那就是要给专家们提供更多面向公众发言的机会,同时政府在决策与公共资源配置方面也要在更大程度上依靠从事戏剧研究的专家。它需要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意识与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政府官员对科学决策的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更需要通过某些特殊的制度性安排,以及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解决理论与批评经常被“消音”的尴尬局面。而从根本上看,其实这两个层面均可归结为一点,那就是需要加速全社会的现代转型。
因为无论是媒体的公共性还是政府决定的科学性,都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在戏剧批评领域所存在的上述疑惑与尴尬,其实远远不止于戏剧门类,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诸多艺术行业,类似的现象甚至更让人难堪的现象,难道不是普遍存在吗?
(文中部分内容曾刊于《文艺报》)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