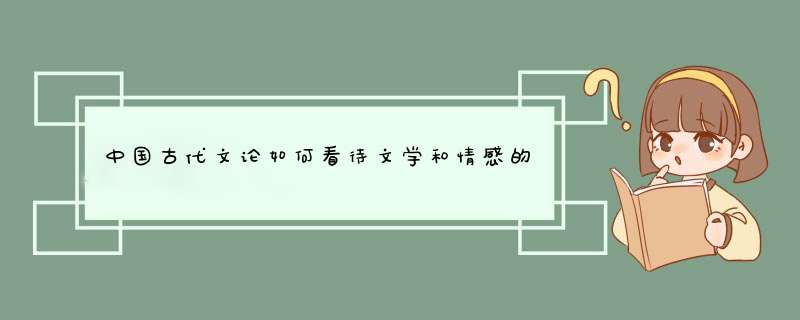
情感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正如诗歌是古代诗人歌手们表达真挚情感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表现了诗与情感,文学与情感的最直接、最朴素的联系。《缪称训》中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其中强调了感情对文学的作用
理智,是通过对周围环境或事物全面而深刻的观察,运用缜密的思维,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发展的结果以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逻辑思维扩展。
理智通常具有王者风范,来自于知识的积累,标志着一种成熟。象温暖的阳光一样,催生着个体不断从浅表的感性认知,升华到理性经验,从而形成一定的行为准则。处事态度,活动规范。
理智的经验和智慧,更多地来自于曾经地感情冲动受到挫折和惩罚。
然而,过于理智的生活既枯燥又乏味,活得累,无任何乐趣可言,因为理智多攻入心计,将自己装入过去生活的狭窄的经验中。享受不到感情带给人知觉体验的激励和鲜活。
感情是主观的,理智是客观的;感情的自然属性如潮水,如女人因女人多感性;理智的自然属性如高山,象男子因男子多理性。如果说感情年轻的,那么理智便象一个成熟的长者;如果说感情如鲜花,理智则如树长青;如果感情的结果是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那么理智的过程便是一部部法理经典。
感情越深厚,理智越成熟。这便是有朋友提到的,理智是感情的升华。爱得越深,越会为对方考虑,行为和言谈越理智。试问,一个薄情的人,怎么可能有成熟的理智呢?而真正成熟的人,又怎么可能不通情达理呢?感情流于表象,所以激昂;理智沉淀深沉,所以睿智。二者穿插交互,才能完美协调我们的精神世界。
我反对将感情与理智绝对对立的说法,那会将我们的认识引向极端。女人偏重感情,并非与理智无缘。女人,往往把感情看得高于一切,过分的理智带给女人的伤害要比爱护多得多。许多时候,女人宁舍理智不舍感情。这一选择使得她们要求生活更富梦想、浪漫和激情。所以说,真正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理智,更需要感情!
所谓:“情之所倾,心之所向”如果完全的理智,我们就无法看到生活中美的亮点。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也不会为后人所传唱,所讴歌。
然而,假如没有理智这个堤防,情感的洪水就会泛滥。历史上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显然是理智与感情的较量和搏斗。在法律面前理智是占上风的。当然,事实上,许多法律的设定,又多是符合正当情感需求的。
理智是理性的,感情是感性的,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基础,没有感性认识何来理性思维?可见,感情与理智互相作用,又相互促进。既矛盾又统一。感情是理智的基础,理智是为了不让感情轻易泛滥成灾。但是如果没有感情,那还谈什么理智与否呢?
所以合情合理,才会情理交融,才有最完美的境界。感性强的人唯美,易受伤害;理性强的人有点冷漠似乎没有人情味,世故。就象男人和女人,阳和阴,虽然矛盾,但永远不可分割,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不断平衡和协和感情和理智,让二者相互达到统一,才会有相对完美的人生。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1) -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2) -
虚伪的作品:余华的“真实”宣言
1989年第5期的《上海文论》上,余华发表了第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长篇论文《虚伪的作品》。这篇论文不仅全面地总结了余华自《十八岁出门远行》以来的先锋创作历程,还就自己的先锋理念和叙事哲学进行了深刻的阐释。最为重要的是,余华激动地向我们描述了他前期创作的美学核心问题:“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
余华认为,所谓“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当有一天某个人说他在夜间看到书桌在屋内走动时,这种说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也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经验只对实际的事物负责,它越来越疏远精神的本质。于是真实的含义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无论是走动的书桌、死人复活,还是后文史铁生那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自动跳出来的药片,余华选取这些“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的事件,其矛头的根本指向,都是“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我们的悲剧在于无法相信”。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却至少具备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它代表了“一些大众的经验”,或者“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这类新闻如国内国际政治新闻,表面上是对事实的客观记录,内里充溢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可以说是想象力的死敌,不允许有想象的空间;第二,它代表了能够被科学和逻辑赋予其发生可能性的事实,这类挑战可能性边界的新闻,基本上都带有“奇闻轶事”的色彩,比如某些社会新闻和花边新闻,甚至包括为大众长久吐槽的《走近科学》,它们需要不断地发掘新闻点对日常生活经验予以刺激,以不择手段地引起读者的关注为其最终目的。也就是说,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同时具备维护现实秩序以及刺激现实秩序这两个互相冲突而又并行不悖的层面;对于第二个层面而言,走动的书桌或者死人复活当然需要被排除在“真实性”之外,但它并不拒绝光天化日的抢劫,或者亲人之间的残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其素材来源正是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报道,余华的处理并没有在“荒诞”或者“难以置信”的意义上,赋予这份素材更多的内容。
余华的激动,使得他毫不犹豫地对两个层面同时做出猛烈的批判,但在随后的陈述中,“新闻真实”的双重层面,却使得余华的观点暧昧不清。当余华描述大众经验对一条街道所下的结论时,他的批判对象已经悄悄地退回到了“新闻真实”的第一个层面上;换言之,余华要做的,不过是颠覆成为真理的衰老经验,发掘出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实。“当我们抛弃对事实做出结论的企图,那么已有的经验就不再牢不可破。我们开始发现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 艾萨克辛格哥哥的告诫,也只是说不要轻易对事物给出明确的看法,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让我们依据自己的精神与想象捏造“真相”。即便将“大众经验”扩展到“现实世界的秩序”,也没有办法帮助余华在理论上迈进一步,因为逻辑也同时具有生活逻辑和客观逻辑两个层次。当我们对亲人之间的残杀报以“不可能”的态度时,我们说的并非“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而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生活逻辑对于客观逻辑不负责任的否定,但客观逻辑还是坚挺地存在着的。余华本人也承认,“《现实一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已经很残忍了,但是与现实中的某些事情相比,还根本算不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经验”、“现实秩序”、“生活逻辑”,这些“既有真实”才是余华火力的最终指向。先前大张旗鼓的激越,也许只是某种扫除思想障碍的叙述策略。
“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这里余华明确地澄清了他要颠覆的真正对象,那就是现实秩序。随后他又进一步对此予以肯定:“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现实一种》时期的作品,其结构大体是对事实框架的模仿,情节段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递进、连接的关系,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现实的必然性。但是那时期作品体现我有关世界结构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对常理的破坏。简单的说法是,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导致这种破坏的原因首先是对常理的怀疑。很多事实已经表明,常理并非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总是真理在握。我感到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面对现实秩序,余华对暴力的选取理所当然:“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余华自己对于选择暴力动因的描述,也印证了前文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余华的欲望,促使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施加暴力,由此那些可怜的人物全部以“本我”的形式在文本中纵欲,而纵欲又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在文本中,欲望和暴力摧毁的是血缘联系;跳出文本,余华真正的靶子乃至眼中钉,则是血缘联系背后的日常经验。
所以,日常经验/现实秩序与血缘联系的紧密联系,使得“冷漠”对于经验/秩序的腐蚀并不令人大惊小怪;而打破血缘联系、重新组建家庭,与构建“内心真实”的类似意义,则使得“温情”成为余华对于自己“内心真实”心满意足的评语。日常经验冷酷无情,“内心真实”其乐融融,余华对于“现实一种”的书写,不但从客观事实上展示了日常经验的不堪一击,而且还从主观感情上呈现出得意洋洋的胜者姿态,从而获取读者对于“内心真实”的更多认同——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余华将家庭伦理关系浓缩为“冷漠/温情”的二元对立的全部真相。
在这一层面上,柯勒律治对待“真实”的观点与余华颇为相似。柯勒律治同样对匍匐摹写的姿态嗤之以鼻:“如果与自然只有相似,没有差异的约束,结果就会让人厌烦,相似的地方越多,越让人难以忍受。为什么蜡像令人不快呢?因为在这种模仿自然的东西里,找不到我们所期待的运动和生命,那些毫发毕现的虚假细节曾经激起我们的兴趣,现在却突然让我们感到离真实更远了。你本以为会看到真实,结果却大失所望,非常不快,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余华在文学观念层面的建树,无法掩饰他在具体写作上的苍白。余华并没有像卡夫卡一样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汪洋大盗”,卡夫卡能够为我们呈现出《变形记》,而余华则注定只能写出《现实一种》。终于,余华也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大众经验之外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这块已经开辟出来的处女地虽然并不狭小,但面对日常经验的宽广,也不得不望洋兴叹。膨胀的野心,促使余华毫不犹豫地选择对现实经验进行重新书写——这无疑是一次冒险,然而这次冒险也势在必行:假如创作一直游历在现实秩序之外自说自话,“内心真实”的建构又如何谈得上完满?然而,这一冒险,却最终导致了余华反抗行为的全面溃败,“内心真实”本不充分的胜利果实也由此一点一点丧失殆尽。从“真实”的层面而言,余华向“传统”的“回归”,其实从一开始就蕴涵了深刻的必然性;在其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描写中,余华的“妥协”便表现在恢复了血缘联系与家庭关系的结合资格,并将“温情”逐渐归还给了血缘联系。
下一篇起,我们就开始谈谈,为什么在我看来,《在细雨中呼喊》才是余华出道即巅峰的长篇作品,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不由自主地走向了余华自己的反面。
(未完待续)
冷漠与温情:余华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关系(4) -
《伦理学》中的论情感的起源和性质。这一部分讨论各种情感是怎样惑乱我们的心灵,蒙住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理智认识的问题。斯宾诺莎提出了心身同一论,批评了心灵决定身体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意志自由论”。他还提出了“自我保存”说。自我保存是人的自然本性,心灵的首要的、基本努力就是肯定自我的存在,人的意志、情感和理性都是这种保存自我的努力的不同心理反应形式。
一、 朱自清散文的创作背景
在对作家的研究中,他们的作品的艺术、思想往往是其本身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所处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自清作为现代作群中最具影响的散文作家之一,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位卑而未敢忘忧国”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他践行“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使得其散文作品中也渗透着时代的声音。
(一)、时代背景
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明争暗斗,旧中国在风雨飘零中苦苦斗争,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自身背景
1、 作为当时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一分子,由于受到阶级的局限性,虽发现了社会的不平与黑暗,但并未能找出产生这种黑暗的根源及解决方法。
2、 家庭的离乱、变迁,父子之间存在矛盾冲突。
二、 朱自清的典范之作——《背影》、《荷塘月色》
朱自清散文的题材大致分为四类,其中有直接写感人至深的亲情作品,又有借助景物抒发心情的名篇。
(一)、感人至深之《背影》
1、《背影》的大致思想内容
描述了家庭遭变故的情况下,父亲送别远行的儿子的全过程。用朴素真切的语言,对父亲在车站给儿子送行的情景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表现了父亲的一片爱子之心和儿子对父亲的思念之情。符合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一种传统的纯真而高尚的感情。父子之间互相体贴,特别是父亲在融汇了辛酸与悲凉情绪的父子之爱中,含有厄运面前的挣扎和对人情淡薄的旧世道的抗争。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叹惋乃至强烈的共鸣!
2、《背影》的写作特色
内容上:(1)抓住人物形象的特征“背影”命题立意、组织材料,在叙事中抒发父子情深。
(2)文中四次出现“背影”,虽情况不同,但思想感情一脉相承。
语言上:(1)语言非常忠实朴素,又非常典雅文质。这种高度民族化的语言,和《背影》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气质,文章的完美结构恰成和谐的统一。
(2)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字眼,除夹入一些文言词语以外,没有华美的辞藻,生僻的词语,都是质朴的家常话,生活气息浓厚,提炼的非常简洁。
理智指作家有意识的理性的认知和思维。
情感分为情绪与感情。前者指由有机体生物需要是否获得满足而产生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后者指作家对外在事物或现象的态度评价及其体验。
理智与情感在文学创造中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促进,共同对同一创作过程起作用。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