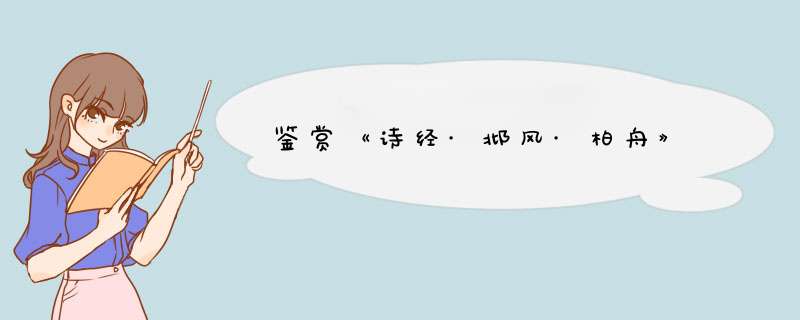
这是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俞平伯认为:“通篇措词委婉幽抑,取喻起兴巧密工细,在朴素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读诗札记》)关于此诗的作者和主旨,在历史上曾有长期争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毛诗序》说:“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鲁诗即以为是卫宣夫人所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我们观察整首诗的抒情,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确实不像男子的口气。从诗的内容看,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词)。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读诗至此,不由人从同情而至敬佩。那么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又是从何而来呢?诗的第四章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那么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呢?小人又何指呢?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似乎比较可取。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诗经·鄘风·柏舟》:女大不中留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测。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关于《诗经·鄘风·柏舟》的主题,姚际恒认为是“贞妇有夫蚤死,其母欲嫁之,而誓死不愿之作。”方玉润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诗经·邶风·柏舟》写贤臣忧谗悯乱,与这首《诗经·鄘风·柏舟》讲烈妇守贞不二同为向上主题, 均可为后世法则,又均冠于二风之首,可谓是相得益彰,各有所长。
孔子讲读“诗”当先存了“思无邪”之心,不仅仅是要净化所有读者的心灵世界,更是在督促大家不惹尘埃,不着俗套,不要拿自己经历的鸡零狗碎、一地鸡毛来理解“诗”。
姚际恒也好,方玉润也好,先有一个道学先生的帽子在头顶戴着,不由他们不屁股决定脑袋,说出“贞妇烈女”的话来。认真想想,若真如此的话,诗中女主人公的母亲,哪里还有人性好言,全然就是妓院老鸨的做派。自家女儿先夫的尸骨未寒,便要逼着女儿改嫁,这样的风尚,两千多年以来是罕见的,怎么可能在两千多年前却成了可以入诗的普遍状态?
《诗经·国风》由《周南》《召南》而《邶风》《鄘风》,不仅仅是政治、文化中心的变化,实际上也是礼乐文化影响程度强弱的变化。《诗经·周南》以《关雎》开篇,《诗经·召南》以《鹊巢》开篇,都是在讲以终为始、善始善终的爱情,无不饱含着包括父母在内的众人的祝福与看好。或“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寓意礼成,或“百两将之”“百两成之”寓意双方父母的赞许与祝福。
《诗经·鄘风·柏舟》讲“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显然已经“发乎情”——忘乎礼了。以至于频频发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抱怨之辞。孔子讲“不怨天,不尤人”,《诗经·鄘风·柏舟》的女主人公已经开始怨天尤人了,而且她所怨的恰是她的母亲,是什么促使她怪及爹娘和上天,抱怨爹娘上天不开眼的呢?不过是“髧彼两髦”所指代的那个年轻人而已。
相比较于《诗经·周南·关雎》和《诗经·召南·鹊巢》,《诗经·鄘风·柏舟》中主人公的情感更加热烈和奔放,已经完全不同于《周南》《召南》的“发乎情,止乎礼”了,对爹娘和上天的抱怨,恰恰表明女主人的情感已经不受“礼”的控制,情感的力量足以导引她冲破“礼”的藩篱。
情感本身是无所谓好,无所谓坏的。但发展到怨天尤人的程度,便有些问题了。之所以怨天,只是对天地的运行规律还不能洞悉和驾驭罢了;之所以尤人,不过是“不知人”而已。
古人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句话的潜台词不是讲父母都绝对正确,而是在讲之所以“有不是的父母”,不过是做子女的“不知人”而已。孔子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若能够做到“知人”,哪里还会去抱怨自己的父母?
对于女儿而言,母亲不过是几十年后的自己。她的立场和出发点当然是女儿的一生幸福,不幸的是,做母亲的常常会试图在女儿身上打下自己一生所遭遇“不幸”的补丁,希望女儿不要再走自己曾走过的弯路。殊不知,自己都绕不过的弯路,凭什么让自己的女儿去硬生生的绕过呢?
这或许便是《诗经·鄘风·柏舟》女主人公大声喊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根本缘由了!
随波漂下柏木舟,飘呀飘在河中流。发型酷毙美少年,让我心仪相耽留。宁愿誓死与白头,我的娘呀我的天,不遂我心让人愁!
随波漂下柏木船,飘呀飘在大河岸。蓄着分头那少年,值我余生永相伴。誓死不把心儿变。我的娘呀我的天,偏不相信这份缘!
《国风·邶风·柏舟》
先秦:佚名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译文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并非青铜镜,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
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凌辱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
赏析
从此诗的内容看,似是一首女子自伤遭遇不偶,而又苦于无可诉说的怨诗。其抒情口气,有幽怨之音,无激亢之语。
全诗共五章三十句。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独此“隐忧”非饮酒所能解,亦非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
次章紧承上一章,这无以排解的忧愁如果有人能分担,那该多好!女子虽然逆来顺受,但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此刻想一吐为快。寻找倾诉的对象,首先想到的便是兄弟,谁料却是“不可以据”。勉强前往,又“逢彼之怒”,旧愁未吐,又添新恨。自己的手足之亲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既不能含茹,又不能倾诉,用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话说,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寻寻觅觅》)。
第三章是反躬自省之词。前四句用比喻来说明自己虽然无以销愁,但心之坚贞有异石席,不能屈服于人。“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意思是说:我虽不容于人,但人不可夺我之志,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决不屈挠退让。其意之坚值得同情乃至敬佩。
第四章诗对主人公那如山如水的愁恨从何而来的问题作了答复:原来是受制于群小,又无力对付他们。“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是一个对句,倾诉了主人公的遭遇,真是满腹辛酸。入夜,静静地思量这一切,不由地抚心拍胸连声叹息,自悲身世。
末章作结,前两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于无可奈何之际,把目标转向日月。日月,是上天的使者,光明的源泉。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司马迁语),女子怨日月的微晦不明,其实是因为女子的忧痛太深,以至于日月失其光辉。内心是那样渴望自由,但却是有奋飞之心,无奋飞之力,只能叹息作罢。出语如泣如诉,一个幽怨悲愤的女子形象便宛然眼前了。对于女主人公是怎样的人以及小人指什么人等问题争议也很大,各家之说中,认为女主人公是贵族妇人、群小为众妾的意见支持者比较多。
全诗紧扣一个“忧”字,忧之深,无以诉,无以泻,无以解,环环相扣。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语言凝重而委婉,感情浓烈而深挚。诗人调用多种修辞手法,比喻的运用更是生动形象,“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几句最为精彩,经常为后世诗人所引用。
扩展阅读:诗经名句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这首诗的意义有三点:第一,据传这首诗是大美女卫庄姜所作,写对自己婚姻不幸的愤怒。第二,孔子将此篇为“变风”之始,即各诸侯国风的第一篇,可见孔子对这篇的喜爱。相比《诗经》首篇《周南·关雎》的温柔敦厚,此篇刚烈犀利,但二者都有大气之风,都可圈可点,所以都上了“头牌”,读之令人赞叹!第三,《诗经》中有大量的怨妇诗,但这一篇是王后所写,所以她没有普通妇女的碎碎屑屑,没有对自己辛苦的抱怨,也没有对男人忘恩负义的指责,她只是觉得自己糟糕的生活像衣服上洗不掉的污点,玷污了自己,她恨得夜夜难眠、捶胸顿足……在所有的怨妇诗里,女人们都想讨回自己的生活,而卫庄姜不是,她如同一个充满诗意的女王,渴望飞翔,渴望逃离这是非之地。
开篇是这样的: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这首诗的情绪非常强烈,开篇的“泛彼柏舟,亦泛其流”写出了卫庄姜内心的无助和迷惘。“柏舟”这个意象非常棒,柏木之舟坚实细密,卫庄姜以此比喻自己虽风华绝代、才华出众,但却是漂荡水中的一只空船和孤舟(子宫也是婴儿的舟船啊,但庄姜却无法生出一男半女),她感到孤独、悲伤,因为自己无法生育子女,丈夫也不爱她,“耿耿不寐”的“耿耿”,指眼睛大睁着睡不着;“如有隐忧”指自己的悲愤难以启齿。别的女人可以碎碎念,王后总不能到处诉苦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意思是:不是我没有美酒啊,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因为无处可以遨游!这句写出了庄姜性情的阔拓和豪放。女诗人大概都喜欢喝酒吧,唯有在微醺中,庄姜、李清照等才女,才能打开胸襟,一展才华。放到今天,庄姜也算是女人中的极品了。《卫风·硕人》篇里的美貌,《邶风·终风》篇里的温婉,《邶风·柏舟》篇里的豪放,既美,又才气了得,真是难得啊!
我们看第二章: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sù),逢彼之怒。
鉴,指镜子;茹,是容纳之意。第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我的心不是镜子,不是什么脏东西都可以容纳!北方女孩的倔强与刚烈表露无遗。“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说的是:虽然我有兄弟,但也指望不上。“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意思是:若向兄弟们诉苦,也只会让他们愤怒。在婚姻生活中,还真不能动不动就把自己的父母兄弟招呼来,谁不疼自家的女儿和姊妹?一旦他们过来,就会因情绪化而大闹,普通人家闹一闹都伤亲家的感情,王室之间一闹,还不得两国开战?
意思是柏木小船在漂荡,漂泊荡漾在水中。深意是以柏舟泛流起兴,首章以“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起兴,以柏舟作比。这两句是虚写,为设想之语。
用柏木做的舟坚牢结实,但却漂荡于水中,无所依傍。这里用以比喻女子飘摇不定的心境。因此,才会“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了,笔锋落实,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便显现出来。
《柏舟》原文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译文
柏木船儿荡悠悠,河中水波漫漫流。圆睁双眼难入睡,深深忧愁在心头。不是想喝没好酒,姑且散心去邀游。
我心并非青铜镜,不能一照都留影。也有长兄与小弟,不料兄弟难依凭。前去诉苦求安慰,竟遇发怒坏性情。
我心并非卵石圆,不能随便来滚转;我心并非草席软,不能任意来翻卷。雍容娴雅有威仪,不能荏弱被欺瞒。
忧愁重重难排除,小人恨我真可恶。碰到患难已很多,遭受凌辱更无数。静下心来仔细想,抚心拍胸猛醒悟。
白昼有日夜有月,为何明暗相交迭?不尽忧愁在心中,好似脏衣未洗洁。静下心来仔细想,不能奋起高飞越。
扩展资料:
《国风·邶风·柏舟》创作背景
此诗的作者和背景,历来争论颇多,迄今尚无定论。简略言之,汉代时不仅今古文有争议,而且今文三家也有不同意见。
《鲁诗》主张此诗为“卫宣夫人”之作,说:“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刘向《列女传·贞顺》),《韩诗》亦同《鲁诗》说(见宋王应麟《诗考》)。《毛诗序》说:“《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这是以此诗为男子不遇于君而作,为古今文家言。今文三家,《齐诗》之说,与《诗序》同。
自东汉郑玄笺《毛诗》以后,学者多信从《毛诗》说,及至南宋,朱熹大反《诗序》,作《诗序辩说》,又作《诗集传》,力主《柏舟》为妇人之诗,形成汉、宋学之争论。元、明以降,朱熹《诗集传》列为科举功名,影响颇大,学者又多信朱说,但持怀疑态度的亦复不少。
明何楷、清陈启源、姚际恒、方玉润等皆有驳议,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今人之《诗经》选注本、译注本各有所本,或主男著,或主女作。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均以为男子作,而袁梅《诗经译注》、程俊英《诗经译注》又皆以为女子作。
这些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是两派:一派认为作者是男性仁臣,另一派认为作者是女子。现代学者多认为是女子所作。
-国风·邶风·柏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