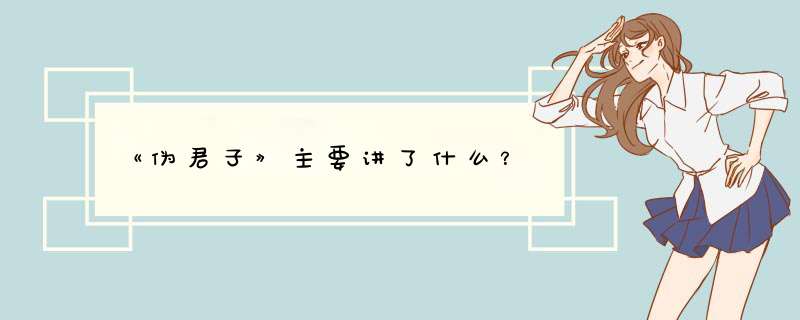
读过《伪君子》的人,谁都感到这个剧本锋芒毕露,讽刺的矛头直指天主教会,这在17世纪的法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勇敢的挑战。
当时的法国还是封建社会,虽然由于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达到了与贵族阶级势均力敌的程度,但是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去推翻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展资本主义,往往采取拥护王权,削弱封建贵族的策略。同时,国王为了制服那些桀骜不驯的封建主,强化自己的统治,也乐意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支持。
于是,“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在法国逐渐建立起专制君主制国家。到了17世纪中叶国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前半期,专制君主制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国王集国家大权于一身,宫廷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这种专制君主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
但是,专制君主制的阶级基础是封建贵族,同时它也离不开天主教的支持。天主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整个欧洲封建制时代中,它在思想意识领域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那时,亵渎神是要受到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就这样被烧死、被囚禁。路易十四对于教权势力有所不满,但也不敢忽视教会的力量。
17世纪法国的封建顽固势力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宗教谍报机构“圣体会”,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活动。天主教的宗教宣传本来就充满着欺骗性,教会人士也以伪善为其特点,他们宣传禁欲主义、出世主义,要人民群众忍受压迫和欺凌,自己却从不放过现时的权势和享乐。“圣体会”的活动更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虚伪性,它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干的是秘密警察的勾当。它派一些人伪装成虔诚的教徒,混进良心导师的队伍,打进教民家庭,刺探他们的言行,通过告密的手段来迫害进步人士。
莫里哀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当时法国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后来在10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广泛接触人民,确立了他的民主主义立场。因此,在他回到巴黎以后,对于教会的这种反动活动和伪善特性是深恶痛绝的。
《伪君子》里有一个扮演作者“代言人”的角色克莱昂特,他的一些台词很能代表莫里哀的思想。这个人物就说过:“没有比假意信教、貌似诚恳,和那些大吹大擂的江湖郎中更可憎的了。……这些人唯利是图,把虔诚当作了职业和货物,……沿着上天的道路,追求财富,异常热烈;他们知道怎么样配合他们的恶习和他们的虔诚;他们容易动怒,报复心切,不守信义,诡计多端;为了害一个人,他们就神气十足,以上天的利益,掩盖他们狠毒的私忿。”“这种虚伪的性格,我们今天看见的太多了”。莫里哀拿起戏剧作为武器与这种恶习作斗争。
剧本《伪君子》就是他针对这种宗教伪善,特别是针对“圣体会”这个以伪善为其活动特点的反动宗教组织发出的切中要害的一击。
莫里哀知道“圣体会”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伪君子》的演出必然要触犯一个庞大的封建顽固势力,正如他后来在《〈伪君子〉序言》中所说:“戏里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到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为剧本的演出而斗争。
1664年5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游园会,莫里哀就利用这个机会赶写了前面3幕,首次上演,主角达尔杜弗是一个穿着黑色袈裟的伪君子。“圣体会”闻讯,惊恐万状,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在太后的支持下,他们禁演了这出戏。“圣体会”的这一行动使莫里哀认识到自己的剧本打中了顽固派的要害,正是达尔杜弗之流在反对《伪君子》,因而更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他在各种场合朗读自己的作品,在私人府第里演出这个剧本。
1667年,太后死去,莫里哀取得国王的许诺,再次上演《伪君子》。莫里哀写成了全剧五幕,把剧名改为《骗子》,主人公改名为巴纽耳夫,还让他脱下袈裟,成了一般的教徒。这些修改并没有减弱剧本的战斗性。
所以,剧本只演了一天,第二天,巴黎最高法院院长乘国王出征之际就下令禁演。不几天,巴黎大主教也张贴告示,禁止教民朗诵或阅读,违者驱逐出教。这一来,杜绝了《伪君子》与群众见面的一切可能,1669年2月,当教皇颁布“教会和平”诏书,宗教迫害有所减轻,“圣体会”也已解体的时候,《伪君子》才获得第三次上演的机会。莫里哀索性恢复了原来的剧名,也恢复了主角原来的名字。这次演出哄传一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说明莫里哀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传统,表现出勇敢的战斗精神。因此,教会对他恨之入骨,并且竭力攻击这个剧本。
莫里哀的剧本深刻地揭露了教会,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于天主教会的愤慨情绪,因而几百年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欢迎,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剧目。
这出喜剧的中心人物是达尔杜弗,他集中体现了伪善的恶习。莫里哀成功地塑造这个人物,深刻地揭露他的骗子实质,完成了全剧的主题思想。
莫里哀笔下达尔杜弗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许多达尔杜弗式人物的艺术概括。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比较注意写出他的来龙去脉和社会联系,力图写出一个完整而丰满的艺术形象,这是他与当时某些古典主义作家不同,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剧中第2幕第2场,通过奥尔贡和女仆道丽娜的对话,交代了达尔杜弗的出身来历:他是外省一个没落贵族,“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但是后来他穷得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几乎成了叫花子,于是他走宗教这条路子,打扮成虔诚的绅士,混进良心导师的队伍,终于骗得富庶的资产者奥尔贡的信任,打入了他的家庭。达尔杜弗的这段身世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17世纪法国的封建贵族,经过30年宗教战争已经大大削弱,一批京城的贵族奔走宫廷,靠路易十四豢养,而许多外省的小贵族则破落不堪,走投无路。宗教就是他们的出路之一。正如李健吾同志分析的那样:“他们日暮途穷,有的强调特权,纠集同伙,打家劫舍,过强盗生涯;有的不嫌丢人,廉价出卖采邑,因而丧失爵位;有的不惜降低身份,和富商结亲,他们过去可能就是自己的佃户。有的一身傲骨,度日维艰,只得挎着篮子去赶集;有的象达尔杜弗,看中良心导师这种有利可图的宗教职业,装出一副虔诚模样,专门哄骗奥尔贡那种大富大贵的人。”达尔杜弗在贵族社会中养成了一套伪善的手腕,并且装扮得有板有眼、煞有介事。
其实,这个人从外表到内心都没有一点虔诚绅士的样子。论模样,长得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嘴红红的,和那些苦修士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论行动,他好吃喜睡,不放过一点世俗享受的机会。他一顿饭能吃两只鹌鹑和半条切成小丁儿的羊腿,吃饱之后就走进他的房间,立刻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逸逸一觉睡到天明,第二天一早又灌了满满4大杯葡萄酒。这哪象是一个鄙弃尘世的禁欲主义者的生活呢?他的行动又怎能与他平日所说的要“把人世看成粪土”的宣教相符合呢?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使奥尔贡入了迷,把他接回家来百般侍奉,把不可告人的、关系到他生命安全的秘密告诉了他,还打算撕毁原订的婚约,把女儿嫁给他,甚至听了他的话,“可以看着兄弟、儿女、母亲和太太死掉,……全不在乎。”
那么,达尔杜弗用什么手段蒙住了奥尔贡的眼睛呢?那就是他的假虔诚。他看准了奥尔贡的弱点,抓住不放,大肆进攻。他的假虔诚是三分做作,七分奉承,而这一些正是奥尔贡最欣赏的东西。奥尔贡并不是一个糊涂人,道丽娜说过,他象当时许多有钱的资产阶级那样,在内乱时期,辅佐国王,英勇有为。一旦得势,当了新贵,他就仿效上流社会的习尚,以宗教虔诚为时髦,而且喜欢别人的谄媚。
这正是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一些特征,莫里哀在《乔治·党丹》、《贵人迷》等剧中都揭露过资产阶级的这种虚荣心,达尔杜弗在教堂里的种种表演,全是投其所好,做给他看的。达尔杜弗并不急于求成,做得颇有心计,而且以谦卑为主要特色。奥尔贡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更由于虚荣心得到满足,便陶醉在对方的阿谀声中,把一个骗子接进家来还自鸣得意。所以奥尔贡的轻信和形式主义宗教热都与上层资产阶级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对于达尔杜弗,莫里哀并不限于从道德上揭露他表里不一的卑劣品质,而是在撕破他伪善画皮的时候,着重暴露他恶棍的本相,揭发他的罪恶用心以及这种伪善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这样就使剧本对于伪善的揭露更深入了一步。
达尔杜弗不仅是个酒肉之徒,而且是个*棍。他一上场就暴露了好色的劣根性:一见道丽娜穿着裸胸的裙子,心里就热烘烘地冒上一股*乱的念头。为了掩饰这种感情,装出绅士的假象,他故意耍弄一块手帕,要人家把胸脯盖上,不料被道丽娜用一句话点破了他的心理。好色是他的致命伤,莫里哀就从这里开刀,让他显出了原形。不过达尔杜弗并非无能之辈。当他色相毕露,向奥尔贡的续弦夫人艾耳密尔求欢,做出这种与绅士身份绝不相容的罪恶勾当的时候,他竟能把自己卑鄙无耻的情欲说成是敬爱上帝的一种表现:“类似您的妇女,个个儿反映上天的美丽,可是上天的最珍贵的奇迹,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上天给了您一副美丽的脸,谁看了也目夺神移,您是完美的造物,我看在眼里,就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您是造物主最美的自画像,我心里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哦!秀色可餐的奇迹,我将永远供奉您,虔心礼拜,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这简直是一首宗教赞美诗,可是,它表达的却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兽欲。一当恶行败露,面临险境的时候,达尔杜弗仍能毫不慌乱,冷静而熟练地装出一副无辜受诬、忍辱含冤的样子,说什么:“上天有意惩罚我,才借这个机会,考验我一番。别人加我以罪,罪名即使再大,我也不敢高傲自大,有所声辩”。甚至还跪下来请求饶恕揭发者。
这样一来,他把圣人的模样就装得更象了,奥尔贡对他更是无限地信任了。他也就自然地达到了化险为夷、嫁祸于人的目的。奥尔贡赶走了揭发奸情的儿子,把全部财产的继承权都赠送给他。这个家伙居然有脸在“愿上天的旨意行于一切”的名义下,把这一切统统都承受了下来。克莱昂特指出:他的这些举动,未免不合一个基督教徒的本分。达尔杜弗仍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巧言作为答对:“因为我怕这份财产落在歹人手中,他们分到这笔家私,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不象我存心善良,用在上天的荣誉和世人的福利上。”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既好色又贪财,掠夺别人财产、勾引别人的妻子,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这个人毫无道德信念,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宗教在他手里就象一块胶泥,他可以随机应变,熟练地玩弄教义来对付各种情况。
到了第4幕,他再次向艾耳密尔求欢。这一次却是别人设下的巧计,达尔杜弗尽管老练,然而他欲火中烧,色迷心窍,急于求得实惠,以至抛弃了上天的名义,剥下了绅士的伪装,奥尔贡终于认清了这是个大坏蛋,狂怒地叫道:“从地狱里出来的鬼怪,没有比他再坏的了。”当即要把他赶走。达尔杜弗再次陷入险境。
但是达尔杜弗并不示弱。当伪善再也骗不了人的时候,他索性抛弃假面具,露出了凶恶的真相。
因为这时他早已掌握了奥尔贡的财产和命运,假面具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他干脆就撕破脸皮恩将仇报,拿出流氓恶棍的招数。他利用法律,串通法院,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大门。他到宫廷告发奥尔贡违犯国法,亲自带领侍卫官前来拘人。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他同样能找到借口,说什么“我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圣上的利益,在这种神圣责任心的正当威力下,任何感恩的心思也不存在”,这真是无耻到了极点。道丽娜说得好:“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有鬼招儿给自己改成一件漂亮斗篷披在身上。”对于这样的恶棍来讲,不论在什么样不利的情况下,他都能厚颜无耻、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神圣的名义。
莫里哀通过达尔杜弗的行动告诉我们,这种伪善者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与官府衙门,甚至和宫廷势力都有联系,法律和制度也对他有利。这样的人横行霸道,奥尔贡一家不可避免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伪善的恶习包藏着祸心,它必将造成严重的危害。莫里哀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达尔杜弗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教会以伪善为其特征,推而广之,伪善也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恶习。
在专制君主的朝廷里,虚伪是一种求得宠爱和晋升的手段,在贵族阶级内部,虚伪又是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拿手好戏。达尔杜弗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作为教会的代表,作为以法院、宫廷为背景的流氓恶棍的代表,集伪善恶习于一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因此,在当时就不断有人指出它与某个真人相似,实际上,达尔杜弗绝不是个别人的写照,而是17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典型。在欧洲,达尔杜弗几乎成了伪善者的同义语。
喜剧的结尾出人意外,国王明察秋毫,认出了达尔杜弗是个大骗子,把他拘捕入狱。对于奥尔贡则记起他勤王有功,宽恕了他的罪行,一场灾难就这样烟消云散。古典主义的喜剧要求结局圆满,莫里哀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使奥尔贡一家得到喜剧结局的根据,他只能借助国王的权力来主持正义,这当然反映了莫里哀的政治态度——他是拥护国王的,同时,它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并不具备惩罚达尔杜弗的客观条件,莫里哀的设计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而已。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的喜剧大师,这出喜剧也是按照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
古典主义是适应17世纪法国专制君主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在当时法国文坛占统治地位,并且流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国。古典主义要求创作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古典主义者还根据自己的理解总结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把它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法则,要求当代的作家严格遵守,以便把文艺统一在专制政体的控制之下。
莫里哀是从学习民间戏剧开始自己的戏剧活动的,后来进入宫廷,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他并不墨守成规,有时还有所突破。古典主义要求戏剧遵守“三一律”,《达尔杜弗》也符合这个要求,不过莫里哀能熟练地运用这些法则,使它们有利于推动剧情、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例如,按照“三一律”的要求,剧中地点不变,始终安排在奥尔贡家。莫里哀就是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来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如第3幕达米斯藏在套间,第4幕奥尔贡躲在桌下,都造成了关键性的情节,另外一些戏剧动作,如达尔杜弗求爱、艾耳密尔的巧计也只有在室内才能发生,离开了这个环境,那些都成了不可信的了。
莫里哀的喜剧很注意塑造人物典型,因而被称为性格喜剧。《伪君子》一剧的全部艺术构思都为塑造一个伪善的性格,在塑造这个形象时,莫里哀一方面从剧本的主题思想出发,把主要的笔墨放在揭露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这一点上。
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如何掌握好分寸,把伪君子与真正有德之士区别开来,让观众自始至终看清这个恶棍的真面目,还可以减少演出的阻力。他在剧本的序言里明确地交代了这一点:“材料需要慎重行事,我在处理上,不但采取了种种预防步骤,而且还竭尽所能,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绅士这种人物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放在他的对立面,也衬出品德高尚的人的性格。”
全剧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1、第2幕是侧面交代达尔杜弗的虚伪性,为他的上场作准备;第3、第4幕,正面揭发达尔杜弗的伪善;第5幕进一步揭露他的凶恶面目和危害性。
莫里哀把达尔杜弗以外的剧中人,分成两派,奥尔贡和他的母亲是达尔杜弗的崇拜者,其余的人物都是达尔杜弗的反对者,在前两幕,达尔杜弗没有登场,但是这两派之间围绕着对于达尔杜弗的不同看法,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介绍了达尔杜弗的出身,达尔杜弗如何混进了奥尔贡家,以及他在那里的种种表现。这些都是刻画人物所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
莫里哀在人物出场之前就把它们一一作了介绍,等到人物上场,他就可以集中笔墨来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实质,而不至于为了交代往事而分散笔墨,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在描写这些戏剧场面时,莫里哀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第一幕第一场被歌德认为是“现存最伟大和最好的开场”。白尔奈耳夫人看不惯这一家人对达尔杜弗的不敬态度,急急忙忙就要出走,谁劝她都要被数落一顿,争论一下子就围绕着达尔杜弗开展起来,这样,一开场就提出了矛盾,吸引了观众,交代了每个人物的身份以及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的地位和态度,真是单刀直入,一举数得,第1幕第4场也是有各的场次。奥尔贡从乡下回来,不关心正在生病的太太,只顾追问达尔杜弗,他4次重复“达尔杜弗呢?”“可怜的人!”这样两句话,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一个外来绅士的魅力竟然超过年轻美貌的太太,可见其受迷惑程度之深。
第3幕,达尔杜弗一上场,莫里哀用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揭穿了他伪善的嘴脸和卑污的内心,其技巧之圆熟可谓惊人!在后面的几幕中,莫里哀抓住达尔杜弗勾引艾耳密尔这一个情节线索,为他安排了两次失败。达尔杜弗在不利的条件下两次都转败为胜,这样更突出地表现他手段之毒,用心之狠,表现了这类人物的危险和可怕性,而这正是主题思想所要强调的地方。达尔杜弗以自己的行动一层一层地撕下了假面具,剧本的揭露性也就逐步地加深。
莫里哀在这出喜剧中还不顾古典主义关于各种体裁严格划分不许交错的原则,在喜剧中插入了悲剧的因素。玛丽雅娜和法赖尔的婚姻几乎被破坏,奥尔贡几乎要搞得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这些悲剧因素的插入,使得这出喜剧的戏剧冲突更加紧张、尖锐,因而也就更有力地揭露了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莫里哀在剧中也向民间艺术学习,吸收了许多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和技巧,增强了剧本的艺术效果。
当然,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束缚了莫里哀的手脚,以至于剧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人物性格单一而缺乏丰富性。然而,瑕不掩瑜,《伪君子》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使它成为世界戏剧史上一出不朽的名剧,它那揭露邪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将鼓舞世世代代的人民向着形形色色的达尔杜弗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伪君子》写伪装圣洁的教会骗子答尔丢夫混进商人奥尔恭家,图谋勾引其妻子并夺取其家财,最后真相败露,锒镗入狱。剧作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答尔丢夫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其剧作在许多方面突破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结构严谨,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鲜明突出,语言机智生动,手法夸张滑稽,风格泼辣尖利,对世界喜剧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伪君子》戏剧锋芒所向,它对着弥漫于贵族上流社会中的伪善,特别指向了反动的教会势力。正是由于《伪君子》戏剧猛烈地抨击了遍及宫廷和教会的伪善恶习,触及了“天堂”和尘世的统治者的痛处,所以它才遭到反动集团的压制、围攻、禁演。这正是《伪君子》成为一部不朽之作,具有着深厚的人民性的本质所在。
《伪君子》是莫里哀喜剧的代表作,他所塑造的剧中人答丢夫的形象,因为其品行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其性格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行为带有很大的蒙蔽性,故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自从这个喜剧上演之后,答丢夫便成为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狼心狗肺的“伪君子”的代名词。
扩展资料:
作品鉴赏:
《伪君子》是一部典型的性格喜剧,全剧的艺术构思都是为了塑造一个伪善的性格。莫里哀把这一性格集中在答丢夫的形象上,一切都为刻画这一性格服务,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强调,使伪善成为答丢夫性格最突出的特征。
如答丢夫的身份是苦修士,作者写他一个人却能吃下六个人的东西;祷告中无意捏死一只跳蚤,也长时间在他人面前说自己罪孽深重,莫里哀就这样把答丢夫的高尚言语和卑劣行径加以对照,予以夸张,从而把他的伪善性格突现出来。
—伪君子
《伪君子》写作的目的是借助莫里哀手中的笔批判社会现实问题,反封建,反宗教统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伪君子》这部戏剧作品的主要内容。
《伪君子》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创作的戏剧作品,它的主要内容围绕着父亲为了女儿的包办婚姻冲突而展开。冲突的起因奥尔恭想让答丢夫变成自己家里的人,方法就是通过把自己的女儿玛丽亚娜嫁给他,为此就强迫自己的爱女解除与瓦莱尔以前就约定好的婚约。一对未婚情侣求助桃丽娜,侍女们也给他们出谋划策,让他们去找女方的哥哥和后妈帮忙。艾耳密尔请答丢夫当面谈判,劝他不要从中阻挠一对年轻人的婚事,不料骗子竟然趁机向他表白爱情。
这件事情被躲在套间里偷听的达米斯撞见,他立即就在奥尔恭面前告发,父亲认为是自己儿子所传出来的谣言,一怒之下就将儿子赶出了家门,并且取消了他的财产继承权。父亲一刻也没有犹豫,马上去办了法律手续,将全部家产赠给了答丢夫,并且宣布当天晚上就让女儿和骗子订婚。艾耳密尔设计让骗子当众出丑,这才让丈夫清醒了过来,伪装被撕破了之后,答丢夫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法院根据奥尔恭赠送财产的契约,通知原主,天亮之前需要全部搬走。接着骗子用奥尔恭私藏国事的这件事情去告发了,他带领着侍卫来到家里面捉人,多亏了国王察觉到了细枝末节,让恶人受到了惩罚,并没有污蔑好人。结局奥尔感谢了皇帝对自己的帮助,并且帮女儿与原定婚姻的瓦莱尔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事。
以上这个故事静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谅解。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