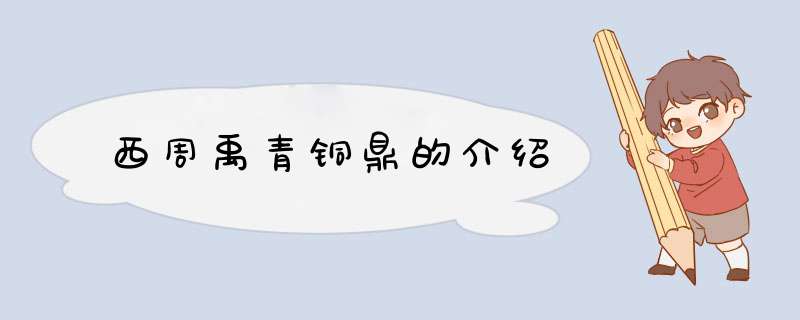
禹鼎 (Ding Tripod Made for Yu ),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为厉王时禹所作。禹鼎造型庄重,铸作精致。1942年在陕西省岐山县任家村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导读: 青铜器是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或铅)制成的器具,诞生于人类的文明时期,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的璀璨;研究它,我们可以共享文明的光辉。
“信以受器,器以藏礼”,中国的青铜器早期是生产工具,后来就主要发挥了礼器的功能,与古代的礼乐制度融为一体,既成为了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又成为了社会关系和政治的象征物。
在近几十年来,中国光正规出土的青铜器,都已经超过了十万件。
其中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作为青铜器的代表作,更是被当作“镇国之宝”,受到海内外无数人追捧,享有极高的美誉。
司母戊鼎因其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用陶范法制造而成,至少花费了一千公斤以上的原料,其中铜、锡、铅的含量分别为8477%、1164%、279%,反映了商周时青铜铸造技术的极高水平。由此断定,当时的采矿和冶炼业已经十分发达。
现在发现的商周时期铜矿遗址大部分都是分布在火成岩和大理岩的接触带上,因为这种地势的氧化矿集中又方便采集,比较符合古代人们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铜矿通常是一种颜色碧绿,纹理类似孔雀的氧化矿“孔雀石”。孔雀石含铜量很高,只要加热到1000度左右就可以练出铜,它又通常和自然铜一起出现,可能就是古人最早用于冶炼的铜矿石。
石器时代的人们在生活中需要寻找石料并进行加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就会发现自然铜和铜矿石。当他们发展到会制作和使用陶器时,就自然会开始发展铜的采冶和铸造。
早期人们对青铜器烧铸的方式就是来自于烧制陶器的经验,他们已经在制造陶器的时候积累了诸如应该使用什么温度、哪些材料耐火易燃、怎样塑造形态等知识。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烧陶的温度和铜的熔点很接近,陶膜用具也可以直接用来铸铜,两者使用的燃料也是一样的。所以古人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学会了铜的冶炼。
春秋时期的冶炼技术经过了商朝和西周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不仅发展出了配矿技术,能够将渣滓的含铜率降到07%,还出现了铜铁合铸,著名的“中华第一剑”就是至今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作品。
很显然,技术是作品的基础,没有逐渐发达的采矿和冶炼业,青铜器就不会在那个时代出现数量如此之多,价值如此之高的盛况。
在几百上千年的发展中,青铜器从最开始的生产工具逐渐衍生出其他的作用,特别是在礼器方面,可谓将器物的价值和人的信仰融为一体。而对于现代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而言,其所刻铭文作为一种文化媒介的功能更是极具特色。
1、礼器
《墨子 ·明鬼 》说:“故古圣王治天下也 ,故必先鬼神而后人者,此也 。”
因为特定社会环境的问题,商周时期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人们因为对神的崇拜和尊重而非常注重祭祀。
青铜鼎就是与神沟通的最重要的媒介物,用于获得神的启示来指导人的活动。商朝人普遍具有图腾信仰,相信兽面和眼睛的神奇力量,所以青铜鼎上常绘有兽面纹并突出眼睛。青铜礼器的形制和材质也同样是为了更好完成这种沟通。
到了周朝,这种迷信程度其实有一定的减弱,在周朝青铜器的功能已经逐渐从“神器”演变到普通的祭祀和文字记录。 《礼 记 ·表记 》 中说 : “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青铜礼器可以说从宗教领悟迈入了政治领悟和社会领悟,象征性被传播性所取代。
事实上到了周朝,许多商朝的青铜纹饰也都被否定掉了,并且衍生出了新的纹饰,比如说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波曲纹、凤鸟纹和瓦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社会的发展让人们的崇拜对象有了改变。并不是说周朝已经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人类进一步强大了,已经没有什么动物是人类的敌人,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实物信仰,而是超现实的虚幻的代表物。
2、媒介
铭文绝对是中国青铜器的一大特色。《公羊 》 疏引 闵因叙 日: “昔 孔 子受 端 门之 命 ,制 《春秋 》 之义 ,使子 夏 等 十 四人 求 周史 记 ,得二 十国宝书 。” 这里的“宝书”就是指铭文。
当青铜器的祭祀功能下降时,它的铭文作用自然就上升了,甚至从而产生了历史的性质。《左传》里就有记载将刑法刻在青铜鼎上的记录,除了青铜器更加坚硬,保存时间更长,也是因为青铜器本身就有一定的神圣和权威性质。
墨子就不仅认同青铜器的书写功能,还认为 “镂于金石 ”的信息比起其他记载方式更加重要。因为青铜器还具备了纪念碑式的意义,有些青铜器就会专门记载某些人某些时候的战功,可以长久的展示生者的荣耀。
青铜器作为礼器和作为媒介的功能之间是有所共通性的。前者跨越了空间障碍,后者跨越了时间障碍,作为一种带有“永恒”概念的存在而受到古代人民的喜爱。
青铜器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是经得起时光的侵蚀和岁月的考验的,所以它才始终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始终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1、礼乐制度的形成
青铜器因作为“礼器”而得以发展,而礼乐制度正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符号和仪式是传播文化观的思想核心,如果人类行动是一种文本,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解读这种文本。”青铜器就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文本,它是由抽象的“思想”转变成具体的“实物”的,围绕着它的礼乐仪式就是“符号”的互动和实施。
在商周时期的用鼎制度就是礼制的核心内容,成为了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法则。
2、汉字文化的推进
“以铜器记载文字,自商至汉陆续不绝”,中华文化以文字为基础,而文字早期的传播和普及则以青铜器作为媒介。
周朝取代商朝后就继承了商朝的汉字,周天子经常性的“赠器”行为又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后来也是因为青铜器刻字技术的广泛流传,才出现了春秋时代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全部攘括在内的庞大的汉字文化圈。
3、政治权利的宣示
政治传播包括了政治沟通、政治宣传和政治合法性建构。青铜器的创造是转换自然资源的过程,在知识贫乏的时代,能够掌握这一过程的个人最容易被赋予“神性”,也就最容易获得至高的声望。
政治社会学者本顿将权利分为“植人权利”和“施加权力”,青铜器就是同时发挥了这两种功能的。因为青铜器既是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一种显示,又是政治秩序的一种控制机制。
青铜器所在的时代都是等级社会,都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去实现统治的稳定,而青铜器就是其中最适用的工具。
青铜器的的政治意义始终远大于其他意义,它强化了国家的机能,保障了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当它的价值从普通的生产工具里脱离出来的时候,平民就不再有资格使用了。
青铜礼器里有爵、鼎、盘、孟等物,制作非常讲究,有精美的浮雕和花纹,象征了器物主人的身份和阶级。兵器里有戈、矛、成、饿等物,而战争又通常是政治的延续。《红楼梦》中就称豪门贵族为“钟鸣鼎食之家 ”,古文中的“鼎”也常关乎于王权和政权,比如“定鼎”、“迁鼎”、“窃鼎”。
至尊九鼎的说法就是来自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以此象征权利的的至高无上。也正是为了维持这种“神性”,古代王朝总是倾尽全国之力来铸造大鼎。
其实金字塔的建造意义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有金字塔这种巨型建筑的存在,古埃及人才永远相信法老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的不可僭越的区别。这种对法老所维持的2000多年的崇拜,就是对文明的崇拜。
维持统治需要武力,但更需要敬畏,更需要让其他同样拥有武力的人从根本上放弃争夺的想法。只有借助于文化的力量,塑造人们心中的敬畏之心,才能够真正实现统治上的说服,毕竟文化的崇拜永远是最持久、最难以动摇的。
早在6500年前,陕西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先民铸造出了第一块铜片;随后,从马家窑文化到龙山文化时代,先民们又遗留下来了陶寺遗址的铜铃,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残铜片、坩锅残片等;到了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时代,他们则开始冶铸或冷锻出铜刀、凿、锥、钻头、斧、匕、指环以及小饰件和镜子等铜器这些显示了中国文化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缓慢过渡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工艺在总结新石器时代器物制造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夏县东下冯遗址这一片独特面貌的早期青铜文化区域,同中国历史记载的夏王朝统治的范围大致吻合;考古发掘的大量青铜器,又与夏人的一些史实——如夏禹的 “贡金九牧,铸鼎物象”(《左传·宣公三年》)、“以铜为兵”(《越绝书·记宝剑》),夏后启的采矿冶铜等,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中发掘的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表明青铜器的冶炼作坊已初具规模因此,“青铜器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已进入中国青铜时代的发展时期”[1]夏代青铜器已经开始走出新石器时代青铜器制造的原始阶段,其大量的礼器和兵器形成了中国青铜器造型的基本格局,神秘的兽面纹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图案,庄严厚重的审美感受更是代表了中国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风格,这些均为商周青铜器艺术鼎盛时期的到来作了必要的铺垫
一 造型形式
以二里头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其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中的酒器爵、斝、角、盉,饪食器鼎,兵器中的戈、钺、镞,乐器中的铃,以及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和残存的圈足器等,从而奠定了中国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要形制的造型格局
在众多的器形之中,仅就青铜爵而言,“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爵大体上有两种造型,一类是原始型的,即爵的样式基本上是模仿陶爵的,它的外形和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手制陶爵有着相似的特征,细腰、平底、短足,呈荷叶状的边口部和流从口部的延伸不甚规整,外观颇像用手捏成的陶器另一类造型是比较精致型的,器壁匀薄流狭长而线条优美精细,虽然同是细腰平底,显然是在陶范上事先作过细致修整的,三足细长而微呈曲线形”这种原始型和精致型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从早期到晚期夏代青铜器造型由简单向复杂多样,由粗放向精致演变的审美历程
早期的青铜器形制主要受同时期的各类陶器的影响如夏代早期作为食器的青铜三足云纹鼎,矮小、无柱、口沿平直,其祖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鼎;作为酒器的青铜束腰爵,素面无柱,形体单薄古拙,充满着浓厚的原始初创气息,其流的长短、俯仰以及爵身趋扁宽的形式也同龙山文化的豫西三里桥类型和豫北后岗类型陶器如出一辙,并没有摆脱陶爵的三条矮尖足附于器底的外侧、形体圆润以及没有棱角变化等浓重特征,更“没有形成青铜器所特有的准确造型和挺劲的轮廓线,也未经精工磨砺”,这无疑是二里头青铜爵的最早形式铜鬲的口沿也与陶鬲口沿的折沿式和侈沿式相对应,其足仍沿用规整圆锥体的陶鬲足因而,这一时期的青铜容器“从其形制特征来讲,它们几乎全与同时的陶器相同,它们的发展演变也与相应的陶器同步”夏代早期的青铜器尚处于祖型于陶器的阶段,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
到了夏代后期,青铜器则相对精巧,造型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此时,青铜爵造型的陶器特征显着减退,在注重实用的同时,还十分讲究形式感,增设了距离很近且具有装饰性的两乳钉状柱,三足分布规矩,接近于等腰三角形,口沿呈凹弧流线型另外,爵的侧面设一折弧形大鋬,鋬面上又加铸两个狭长的镂孔,既有效控制了鋬的厚度,又增饰了具有装饰效果的镂孔纹;1959年上海博物馆自废铜中抢救出来的乳钉纹管流爵,其一侧设斜置的流管,流上铸两个方折形饰物,造型别具一格,其鋬下有一圈较宽的假腹,其上铸用多个空心圆孔,形成镂空的装饰效果;尤其是二里头出土的乳钉纹长流爵,流特别细长,作狭槽状,尾与其对应,既平衡了重心,又显得修长而纤细,三足尖端呈弯弧线状而外撇,这些与扁平直立式样规整的橄榄形爵身搭配和谐,刚柔相济,已经脱离了夏代陶爵的体制,并成为中国酒具的形象代表这时的青铜鼎,其腹部较为高深,配三只四棱锥形空心足,两耳立于口沿上,其中一耳与一足呈垂直线对应,另一耳则位于另外两足中间,整体造型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要求,给人一种规整中有生气,对比中显和谐的审美感受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创新型的高颈扁腹直壁斝(二里头遗址六区M9:1),口沿上设两个三菱锥状矮柱,腹部鼓起,下承三个大空锥足,器壁很薄,其先进的设计直接是二里岗文化铜斝的原始祖型夏代晚期处理器壁匀薄的技巧,也为商代青铜器物新颖造型的设计开创了先河
二 纹饰意蕴
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一方面对同时期的灰陶和礼玉的纹饰有所继承,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社会形成阶段的特征对其纹饰作了一定的扬弃,所以无论是纹饰的结构特征,还是其表现方法,均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夏代青铜器纹饰多以乳钉或圆饼状的实心的连珠纹,以及弦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为主,虽然还没有发现像商代青铜器上直接铸刻的饕餮动物纹为主题的装饰,但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用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动物头部图案的铜牌饰上,却已经形成了这一动物纹的基本模式,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动物纹的先河
(一)几何纹
几何纹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早已出现,而到了夏代,青铜器则开始模仿陶器的各种几何纹饰类型,出现了一些简单的连珠纹、弦纹和云雷纹,从而开启了中国青铜器纹饰的先河这些几何纹虽然相对单纯和平面化,却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体现了丰富的审美风尚和极具时代性的文化内涵
最早出现的连珠纹图案呈小圆珠状,有单排和双排两种横式排列,圆圈也有实心和空心之分,多饰在器物的肩上或器盖的边缘等部位,其形成也经历了一定的演变过程如青铜器上的乳钉等,首先可能是防碰撞的实用功能和相对规则的装饰功能的统一,后来其实用功能退化,渐渐演化为专门的装饰性图案二里头乳钉纹斝颈部突出的圆饼状乳钉纹(即连珠纹),作为青铜器上简单而原始的纹饰,就是在防滑的实用基础上而形成的据考证,连珠纹是用一个管状器在陶范上印制的,圈与圈间距的疏密,横行排列的整齐,虽不很严格,却显得自然如二里头铜爵上也饰有很不规矩的圆点纹,作单向或双向排列,类似的还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角,其杯体下部也铸有圆圈状的连珠纹
弦纹也是青铜器上简单的纹饰,为一根凸起的直或横的线条,简洁朴素它一般与乳钉状连珠纹配合使用,并且多作为连珠纹的边框如夏代晚期的乳钉纹管流爵的颈上也饰弦纹三道,其间夹杂疏密有致的双排乳钉纹,显得规整而又有变化;二里头出土的铜斝,与鋬相背的腰腹正面装饰有两道凸弦纹,中间则夹有一排五颗乳钉纹,从而在腹部形成了一周由凸弦纹与圈纹组成的宽带纹,显得简洁而利落,形成了夏代青铜器纹饰的特有形式,与青铜时代的其它阶段的纹饰风格迥异
云雷纹是夏代青铜器上最为典型的几何形图案,是用利器在陶范上刻划而成,圆柔形的云纹和方折形的雷纹连续出现,构成了回旋式线条,显得自然流畅夏代青铜鼎的腹部一般多饰以云雷纹,较特殊的是二里头六区(KM3:2)青铜戈,其曲内后部也铸有凸起的云纹,纹间的凹槽内还镶嵌有绿松石,将相对神秘庄重的云雷纹打扮得楚楚动人,寓庄严与审美于一体这种云雷纹的阳纹线条在纹饰中间均形成一个圆圈,颇似神秘而狞厉的斜角目纹,周围再搭配饰以抽象而富于变化的阳纹线条,整个构图简洁而生动,寓狞厉与生气为一体,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鼎上兽面纹的胎形
除此之外,二里头文化中出现的几何纹还有近似水涡的涡纹;阳纹线条纵横交错而成的网格纹,如二里头遗址五区M1:1青铜鼎腹部饰有粗疏的带状网格纹;以及绿松石镶嵌十字纹,如1975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圆形青铜器上就饰有两头粗中间细的十字纹,另外一件夏代晚期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在其中心圆孔周围的正反两面也用形状规整的小绿松石片镶嵌成两周十字图案,并在其内外用绿松石片组成两个圆周将其围住,整个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
(二)动物纹
到了夏代晚期,铜牌饰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国青铜器中以夸张形式或以幻想中的动物头部为主体的抽象兽面图案,这也是迄今发现的青铜器上最早的动物纹该纹饰的动物头部,除两眼之外的其他部分,均为抽象的,而不是具体表现实样的这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遗址中石锛上怪异的动物纹饰,身上横条沟曲形的刻线与青铜兽面纹就极为相似,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也有类似的怪兽纹饰夏代兽面铜牌上的兽面纹,图案设计简单质朴,特别突出兽目,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并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上兽面纹和饕餮纹的祖型李学勤分析山东日照两镇的玉锛饕餮纹、河南偃师二里头铅的嵌绿松石青铜牌饰饕餮纹时,也指出了其审美过渡性:“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和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夏代也有部分铜酒器在器盖的边缘饰以变形的动物纹图案,并且特别突出骇人的双目,营造了一种威严的氛围,既与使用者的礼仪和等级地位相呼应,也与夏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夏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装饰,当为商周同类青铜器纹样的滥觞,而且经过变形的动物纹图案也形成了后来青铜纹饰的主体
总之,夏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青铜器外在形式的华美与瑰丽,如青铜质料的器物表面,刻以单层平雕纹饰,且纹饰多作条带状,往往给人以既有力度和锐度的触觉感受,又有流畅和圆润的视觉感受,“灵活的线形纹饰弥补了青铜器体块特质的不足,赋予了凝重的青铜器以生命的气息”,形成了刚柔相济的艺术审美韵味;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夏代先民把现实以及臆想的物象铸刻在象征权力、威仪和用以祭祀的青铜礼器上,如夏代九鼎的纹饰既满足了其宗教性的龙崇拜,也通过把天下各地的自然资源和财富绘制成图象,刻铸于鼎上,以此作为帝王享有灵物和征收贡赋的象征,突出其现实的攫取权力和树立威信的政治意义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