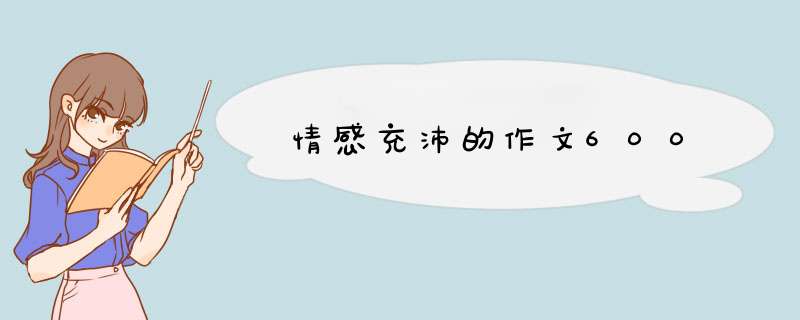
情感
感恩是美丽的,美丽如花。馥郁馨香,花儿在感恩春风的爱抚;晶莹露珠,是花儿在感恩细雨的滋润;姹紫嫣红,是花儿在感恩阳光的长养。
感恩是快乐的,快乐似鸟。寒来暑往,是鸟儿在感恩生命的多娇;悦耳吟唱,是鸟儿在感恩伴侣的痴情;奋力翱翔,是鸟儿在感谢蓝天的垂青。
感恩是崇高的,崇高若山。清音妙响,是高山在感恩流水的陪伴;苍翠挺拔,是高山在感恩松柏的装点;飘逸绚烂,是高山在感恩云霞的奉献。
感恩母亲
是谁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谁洗衣做饭,嘘寒问暖;是谁默默操持,殷殷期盼;是谁白了青丝,凋了红颜。春晖寸草,不管我们人生的果实如何丰盈饱满,压弯的,总是母亲的枝条,母亲的腰杆。
感恩老师
是谁三尺讲台,一生守候;是谁兢兢业业,不辞劳忧;是谁播撒知识,传承文明;是谁灌溉桃李,放飞希望;蜡炬春蚕,不管我们人生的峰峦如何巍峨壮观,奠基的,总是恩师的教诲恩师的箴言。
感恩朋友
是谁慷慨解囊,雪中送炭;是谁两肋插刀,共苦同甘;是谁心心相惜,不离不弃;是谁促膝而谈,真诚相伴,高山流水,不管我们人生的舞台如何绚丽多彩,谢幕的,总是朋友的掌声,朋友的呐喊。
我们每天着急忙慌地往前走,说是为了紧跟时代的步伐,紧随时尚的前沿,抑或是各种迫不得已,还是别人都前进了,我们总不能落伍。然后,我们急匆匆地行走在冰冷的水泥钢铁丛林间,可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去,也可以说,我们在丢掉过去的富足,寻找前所未有的陌生。然而,夜幕下,挤挤人流后,我们孤单彷徨的心,总会去寻找过去,回味无穷。甚至有些冰凉的叹息。
我们是进步了,方便了,舒适了,科学了,但我们同时也彷徨了,不安稳了。
周末假期,丢掉生活的必须,其实很多时候急切的想去寻找一份安宁恬淡,而非人潮拥涌,你推我搡的浮躁和紧张。说白了,我们并不喜欢现在的繁杂。
换而言之。我们的以前,我们的小时候,我们的农家小院,村前屋后,已然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山水画。
认不认同,且听且思。
屋前,细带如丝的小溪,平静祥和。炊烟扭动着柔美的腰肢,燕尔般升向湛蓝湛蓝的天空。几丝白云,若有若无。奶奶安静的步伐,走向鸡窝。双鬓的白发柔和的搭在耳朵上。围裙上的口袋里,装着热腾腾的两枚鸡蛋。
小狗吐着舌头,小碎步儿颠颠在她的身后。一群麻雀,叽叽喳喳落在门口的那棵老榆树上。圆溜流的眼睛盯着奶奶的一言一行。
对,这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一小节。
我们见过很多事与物,走过很多桥和路。但我们永远承认月是故乡明。
不知老家门口的那盘碾子还能不能推的动,能不能磨得出细香的面粉;不知村前的那个大戏台还有没有往年的热闹,过年了,大爷大娘们会不会依旧拎着凳子去听戏闲聊,戏台上的那些雕梁画栋是否还健在;傍晚,爷爷吃过饭了,大家还会不会走出来,坐到码头桥上看星像;还有,那些小孩会不会坐在铁锹上玩溜溜坡。
有时候,我们的记忆会出奇的牢固,尤其会专门为过去腾出一片好大的天地。
春天,我们包裹在大衣里,会想,往年这个季节,老家应该会种地了,那些厚实的土地,应该会变得松软肥沃。泥土的芬芳,在莺歌燕舞下,滋生着生命的希望。小学时候,往往在春天,我们会格外的皮,爬墻溜树。折把榆钱,要么带在头上,要么灌在玻璃瓶子里,反正,一切简单的顺理成章,一切美好的不可思议。槐花在太阳底下耀武扬威,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它们哗众取宠。每年的春天,家里会增添小鸡,小猪,还有一群洁白的小羊羔。放学后的我们,从来都不急不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逗狗抓鸡,去捉迷藏,去偷窥邻居家的晚餐丰盛与否。
现在的夏天,我们很热,很忙。顶多,在难得的周末,泡个啤酒摊,撸几个串,算是很惬意了。但,我们很多时候,在茶余饭后,有意识无意识挂在嘴边的还是一箩筐“以前”和“小的时候”。
以前的夏天,格外的清爽,即使是太阳,好像比现在小,现在的太阳,为什么那么刺眼,总之,没有遮阳伞和墨镜的夏天,就不是夏天。
我们在小时候,夏天五彩缤纷的美丽。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是满满的乐趣和笑声。
汗哒哒的小手,捧着一点馍馍,心不在焉地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因为,妈妈在的地方都很温暖。还有,最喜欢妈妈在菜园子转来转去的背影。妈妈总会说,小心踩着西瓜的藤蔓,别塌着番瓜,豆角开花了,些许日子就能吃了……
那时候的知了可烦人了,因为它会吵得没法午睡,只因为我们的午睡很多时候选择在树荫下。树叶斑驳陆离的影子,倒影在泛白的地面上,沙画一样随着日光流动着。
那时候的夏天很富足。我们不会刻意去寻找什么玩乐。摘一把桑椹,想吃了猴急猴急地塞进嘴里,不想吃了胡乱摸在脸上,京剧脸谱一样惊悚搞笑。那时候的我们不怕热,热了也好解决。奶奶晒在院子里准备浆洗的水,也是最好的玩乐工具,汗淋淋的脑袋,一头扎进盆子里,那叫一个爽。
这不叫庸人自扰、停滞不前,更不是悲秋伤春、无病呻吟。
不知你们可曾记得,那年的秋天,地里的土豆长的贼大,大得可以抗在肩膀上。最喜欢看着挖得晒在满地的土豆,粘着泥土,但觉得不脏,反而很美。还有,爸妈训责了,我们会钻进高粱地里,躺它一时半会。密密麻麻的高粱,头重脚轻,它们总爱随风摇摆,哗啦啦的叶子,很烦人,但蛐蛐总愿意呆在上面,不明其就。
小时候,我们不怕冷,不知道那会有暖气,有空调的冬天会是怎么一番场景。
我们会不会依旧冒着纷纷大雪,跑出去抓麻雀;会不会在厚厚的雪地里踩出深深的脚印,然后傻傻的比大小;会不会笑着议论谁家的小狗又在雪地里撒了一泡尿;会不会瞅着窗子上的冰花发呆;会不会大冷天把舌头伸得老长,去舔铁丝,即使粘掉一点皮,流血血,对着镜子傻笑。
我们不觉得这些回忆是负担,但害怕没有东西去引起回忆。依托储藏回忆的那些老宅子垮了,乡间小道换成了柏油马路,钢筋水泥代替了雕梁画栋。
有些东西丢掉了,可能再无法弥补。比如说落在榆树门槛上的缝隙,洋瓷晚上脱落的油漆。
早上,我宁愿被挂在村口树桩子上的大喇叭吵醒,而不是被叽里哇啦的闹钟叫醒。我宁愿写封长长的信,跑到邮局,盖上一个红红的章子,去表达这一年对爸妈的歉疚和想念,而不是捂着一部烫山芋一样的手机哼哼唧唧半天。
见到前男友时的心情因人而异,但一般而言可能会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感:
紧张:可能因为与前男友的过往关系,或者因为对见到前男友的未知感到紧张和焦虑。
不安:可能因为对前男友的感情还有所挂念,或者因为担心会遇到尴尬或尴尬的场景,而感到不安。
愉快:可能因为与前男友分手后成功地摆脱了痛苦,或者因为与前男友在分手后成为了好朋友而感到愉快。
悲伤:可能因为对前男友的感情仍然很深,或者因为想起与前男友的美好回忆而感到悲伤。
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去理解“随遇而安”这个成语的意思,“顺其自然,碰到什么就是什么”,都是其最基本的内涵。随遇而安,充分体现了古代先贤的“三观”认知和生活态度。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罢,理论上它是中国古老的生存哲学;实践中它也应该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取舍。顺其自然的本质,源于我们对自身命运无法改变的无奈。譬如,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我们生死的具体时间,无法选择我们与生俱来的姓氏,无法选择我们所要生活的时代,乃至国籍、家乡、自然和社会环境,等等。
在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上,一切生命的发源、生存、繁衍,无不是“顺其自然,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结果。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随遇而安的典范;唯独我们人类,自视处于所有生灵的顶端,因而并不安分守己,常常做出“改天换地”的壮举,企图改变束缚我们的自在的王国,而走向自由的世界。因而,也就唯独不会随遇而安。
主流科学告诉我们,地球诞生已经46亿年了。而地球上生命的诞生也已经有40亿年的历史了。可悲的是,我们人类的诞生的历程才仅仅是350万年左右。至今,无论是主流科学,还是宗教典籍,都无法说明人类的起源。无论是外国的亚当夏娃、还是中国的女娲盘古,其造人创世都无不是童话般的传说;即便是达尔文的猿人进化说,也被现代科学和人类考古学不断地否定着——截至目前,人们依然未能找到人类进化链条般的系列化石。地球上所有的动物植物,其生命的产生都有根基,唯独具有思想意识、能够直立行走、发明了工具和火种、从事劳动创造的人类,仿佛是在350万年前突然就凭空而来一般,找不到源头。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颗星球上,一切生命的发源、生存、繁衍,无不是“顺其自然,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的结果,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随遇而安的典范;唯独我们人类,自视处于所有生灵的顶端,因而并不安分守己,常常做出“改天换地”的壮举,企图改变束缚我们的自在的王国,而走向自由的世界这样一个事实,来理解我们人类之所以不会随遇而安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于人类于350万年前突然就凭空而来的缘由,理论上有许多假说和猜想,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人类很有可能来自于地球之外的某颗星球,是地球上的“移民”,或者是“殖民者”。且不说持此见解者提出的那些让我们很难接受的五花八门的理由与所谓的证据,仅就唯独我们人类不会随遇而安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存在中的“异类”,或者是“另类”。
这种人类不会随遇而安普遍存在的现象,证明了我们人类的先祖不满足于其原先的居住地,铤而走险,来到了地球,从而使得这颗星球从此有了新兴生命,并且保留了不会随遇而安的遗传基因,才有了从非洲大陆逐渐走向全世界的漫长的大迁徙,才有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群落、部族、社会、国家、创造、文明,乃至现代对外太空的不断探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人类对外太空的不断探索,甚至可以看作是我们人类本能的“回归意识”和“回归愿望”,是来自于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潜意识和骨子里的迫切要求,或者是使命召唤!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道家所崇尚的“道法自然”和儒家所崇尚的“君臣父子”的理论认识,又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中国的“道”和“儒”所倡导的人的定位,尽管貌似对立,有所谓的“出世”、“入世”之说,其本质上说的'还是“随遇而安”,不过角度不同罢了。道家说的是人与自然的对应,儒家说的是人与社会的对应,殊途同归,都讲的是随遇而安,和谐相处,不违背自然规律,不忤逆社会秩序。实际上,也就是人所本应该具有和掌握的生存之道,或者说是生存本能。
上述“道”和“儒”的核心思想,似乎与笔者所说的人类的永不安分、绝不会随遇而安的“本性基因”是相悖的,但它们实际上还是与人类的永不安分、绝不会随遇而安的“本性基因”是一致的。所谓的“道法自然,”就是说,我们“从哪里来”,还必须“回到哪里去”;所谓的“君臣父子”,就是说,我们不是乌合之众,只有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组织、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回归”到人类的本源世界。
再看,佛教和基督教,其思想内涵和基本教义都有所不同,但最趋同一致的却是它们都有“天堂”与“地狱”之说。在笔者想来,假如我们人类来自于地外文明,那么,无论是350万年前的星际移民,还是之后在地球上居住时的不断迁徙,历时数百万年不辞劳苦的长途跋涉,都是在摆脱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地狱”,寻找理想世界亦即“天堂”的举动。至于其中的“善”者上“天堂”、“恶”者下“地狱”,无非是说,大家都要有整体意识、集体意识,不得破坏社会秩序、残害同类、损害群体利益,从而避免到达“天堂”之前,被众生所遗弃,堕入“地狱”去受苦受难,也就是所谓的“从善如流”、“疾恶如仇”。
然而,笔者上述所说,是就人类的整体而言的。作为单个的人,作为当今全世界70亿人类中的一份子,我们在“胸怀世界”、“放眼全球”的同时,所考虑的最多的依然是我们个人的现实需求,现实命运与现实取舍。我们既不是“乐天”的“傻人”,也不是“忧天”的“杞人”,我们的命运、努力和付出,决定了我们作为当今全世界70亿人类中的一份子的现实社会定位;因之而形成的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亦即现在流行的说法“三观”,则决定了我们对于个人人生的现实取舍和态度。我们在人类历史上,仅仅是匆匆过客;我们在茫茫人海中,仅仅是沧海一粟。所以,我们无法“改天换地”,只能“随遇而安”!
古人云,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永远都是事事如意的,理想与现实有着永远难以缩短的距离。个人的许多遭际,在特定情况下,是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处在诡谲多变、绝非个人理想的社会和生活的环境当中,唯一能使我们不会自不量力,去强行扭转乾坤,而略感心情愉快的办法,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去尽量做到使自己“随遇而安”。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何缘如此?水土不同使然。细想,人便也如同此橘,适者生存。社会千变万化,境遇各有不同。每个人一生当中所处的社会、工作和生活环境绝不会一成不变,我们将怎样面对?的确需要大智慧。也就是说,在坚持自己的信念的同时,必须随遇而安,乐意去充当一个适者生存的“橘”或“枳”的不同角色。
偶然阅读佛家经典,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值得我们深思。
有一个寺院住着一老一小两位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一些花种,让他种在自己的院子里,小和尚拿着花种正往院子里走去,突然被门槛绊了一下,摔了一跤,手中的花种洒了满地,这时方丈在屋中说了一句“随遇”。小和尚看到花种洒了,连忙要去扫。等他把扫帚拿来正要扫的时候,突然天空中刮起了一阵大风,把散在地上的花种吹得满院都是,方丈这个时候再说了一句“随缘”。小和尚一看这下可怎么办呢?师傅交待的事情,因为自己不小心给耽搁了,连忙努力地又去扫院子里的花种,这时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小和尚连忙跑回了屋内,向方丈哭着说自己的过错,然而老方丈微笑着,还说了一句“随安”。冬去春来,一天清晨,小和尚突然发现院子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便蹦蹦跳跳地告诉师傅,老方丈这时又说了一句“随喜”。
对于随遇、随缘、随安、随喜这四个“随”,可以说就是我们人生的缩影,在遇到不同事情、不同情况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具有的心态,就应该是“随遇”、“随缘”、“随安”和“随喜”,也就是随遇而安。一个人不管际遇如何糟糕,如果能够始终保持像老方丈一样恬淡乐观的心态,那真是你此生用一辈子的感悟修来的享用不尽的福气!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曾经多次被贬职流放,可是,他说,要想心情愉快,只需要看到松柏与明月也就行了。何处无明月,何处无松柏?只是我们这些人不具有他那般的情思与心境,不能做到物我两忘,只能戚戚然,而不能坦荡荡罢了。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做到随遇而安,及时挖掘和享受身边的趣闻乐事,以苦为乐,知足常乐,心境自然也就会如此。元代白朴的散曲《沉醉东风》说道:“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其逍遥自在,相忘于江湖间,不为功名所累,便有此等境界。
因为心无所恃,所以随遇而安。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正如《菜根谭》中所说: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展云舒。人的心境本应该就是这样平和吧?宠辱不惊,波澜无意,不该在乎的不在乎,不该留意的不留意,以恬淡乐观的心境度过一生,忘我而我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乐乐呵呵,坦坦荡荡,优哉游哉,那该多好啊!
托物言志,表现了作者希望自己的堂弟也如松柏一样坚贞自守,不应外力而改变本性。
《赠从弟》
作者:刘桢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译文:
高山上挺拔耸立的松树,顶着山谷间瑟瑟呼啸的狂风。
风声是如此的猛烈,而松枝是如此的刚劲!
任它满天冰霜惨惨凄凄,松树的腰杆终年端端正正。
难道是松树没有遭遇凝重的寒意?不,是松柏天生有着耐寒的本性!
扩展资料:
1、《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古人谈读书》第一部分分别选自《论语·公冶长》、《论语·为政》、《论语·述而》。
2、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古人谈读书》第二部分选自《训学斋规》。
3、曾国藩,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代表作品有《曾国藩家书》等。
《古人谈读书》第三部分选自《曾文正公全集》中的《与诸弟书》。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